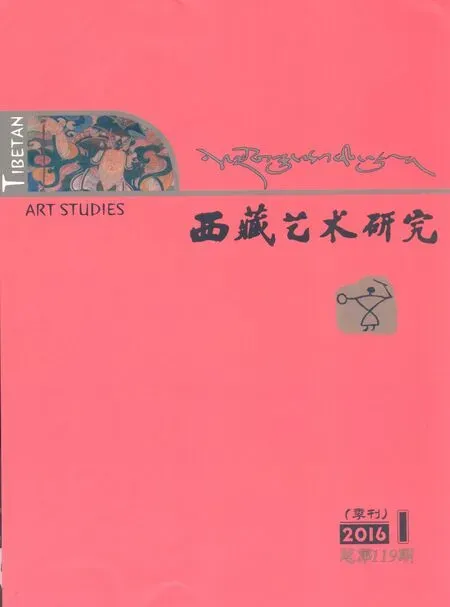影像重构与文化深描
——万玛才旦电影论略
杨伟
影像重构与文化深描
——万玛才旦电影论略
杨伟
【内容摘要】作为藏族母语电影的代表人物之一,万玛才旦自2002年开始电影创作以来,凭借其独特的电影作品,奠定了他在中国藏语电影的重要地位,引起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他的电影从藏族的现实出发,走上了一条文化深描与影像重构的艰难道路。影片看似非常简单,但却充满了深刻的文化内涵。导演以其特有的镜头语言真实地展现了他对于本土文化的理解、认同与坚持。而这种主位视角的坚持与以往所有关于藏区的表达形成一种强烈的对比,在这种对比中,我们看到的是导演在多元文化背景下试图实现民族文化影像文本的深描和藏族文化气质的重构。这种重构有别于香格里拉式的描述,也有别于政治话语式的地域描述。
【关键词】藏族电影;万玛才旦;文化深描;影像重构
从2004年的《草原》、2005年的《静静的嘛呢石》、2007年的《寻找智美更登》、2011年的《老狗》、2014年的《五彩神箭》到2015年的《塔洛》,导演万玛才旦形成了他藏族母语电影的独特风格,为中国民族电影的创作开辟了一条新的制作模式。不同于以往的藏族题材电影,这一批电影以其缓慢的节奏、纪实的手法向观众娓娓道来有关藏区的信息,其间不乏作者对传统的眷恋,对现代文明的反思。这样的影像表达对于整个藏区现代历史的书写是极其有意义的。文化具有地域性,作为中华民族多元文化图谱中的藏族文化因其地域、宗教,以及一些客观原因,在过去的一个世纪中以影像的方式实现自我的表达基本上是缺失的,这一些作品的出现弥补了不足。
一
以照相机为标志的机械影像时代的到来,完全改变了以往的文字时代的传统,近一百年来,人们对世界文化多元性的认识更多是通过静态、动态的影像画面,借助于机械形式记述、传播文化。藏文化的影像传播历史最早可以追塑到1890年左右,在西藏和尼泊尔的边境出现了一些小型的照相馆,有极少数的藏族肖像被保留下来,拍摄者为翰斯顿和霍夫曼①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西藏亚东关档案选编[M].北京:中国藏研中心1999,后期不断有外来的各种身份的摄影爱好者对西藏文化进行影像的记录。二十世纪前半期关于西藏的各类影像的数量呈爆炸式的增长,西方人关于西藏影像的获得,完全操控在英国手中①转引自赵光锐,西方人反思西藏认知的研究评述[J].北京:民族研究,2011(6):97.,鲜有藏族人参与。1904年《拉萨条约》签订之后更多的英国人涌入西藏,他们对西藏充满了好奇,拍摄了西藏贵族阶层和街头的平民生活,这批珍贵的照片绝多数被带回英国或其他西方国家收藏。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开始以德穆·丹增嘉措、擦绒·东堆朗杰和车仁·晋美松赞旺布三位贵族,用照相机记录了西藏的一段历史。②索穷,二十世纪初的雪域摄影人[J].北京:中国西藏,2005(1):61.据说早在1912年,西藏贵族擦绒家族就曾用电影摄像机拍摄了自己家和拉萨的景象。这是最早关于藏族人自我影像建构的记录。当我们以西方学者萨义德东方主义理论为根本,去审视有关藏区的影像创作与传播不难发现西方电影人通过立体、真实的影像为西方读者重构想象的西藏的有限性,也使我们认识到已有的影像文本对藏族社会的描述,对于用影像来构建、追溯往昔历史文化和族群记忆是极为缺乏的。③张明,雪域深描:用影像重新写文化 [J].北京:中国电视 ,2011(6):75.这些由藏地符号构建的影片强化了藏族文化的神秘性,追逐奇观化与政治化的镜像表达,缺乏根本性文化内涵的表现。这种“他者”视角的表达成为西藏早期影像创作的一种主要类型。
自十九世纪末以来进入视觉文化迅速发展的时期,一批关注世界文化发展的影像人类学先驱爱德华·柯蒂斯、阿尔伯特·卡恩、罗伯特·弗拉哈迪竭力诠释和保护各种濒临灭绝的土著文化,试图以鲜活、形象的文化样式弥补由于工业化造成的文化动荡带来给人们的失落与焦虑。与这一批影像人类学先驱的努力相同的是新生代的藏族电影导演面对文化河流的巨变也在试图以自己的方式保留藏地传统文化的遗迹;不同的是前者以他者身份对世界文化的多元性做了客观的纪实影像的描述,而万玛才旦的影片则是以主位的视角客观冷静地记述了藏区的变异。他的影片是一种虚构与现实的融合,是故事片的,却又是纪实影像的。摄影机游离在藏区,所有群众演员以及被包容在电影中的每一个细节在导演的安排之下,在摄影机不断刺激中,缓缓流淌出所有关于藏文化的信息:慈悲、智慧、宁静、和谐与包容。
二
影像是一种文化解释,克利福德·格尔茨在其《文化的解释》一书中说道:“对文化的分析不是一种寻求规矩的实验科学,而是一种探求意义的解释科学。④克利福德·格尔茨,文化的解释[M].南京:译林出版社,1999:13.这样的分析展现在传统的文本中即是各种差异性的学术观点,当我们把影像看做是文化解释的另一种特殊文本时,影像所展现的各种文化也呈现出:或客观,或主观,或浅描,或深描的影像文本。万玛才旦的影像介于故事片与纪录片之间,界限的模糊性让这一批电影作品具有了人类学电影的品质。
导演的第一部短片《草原》讲述了安多草原上,措姆阿妈放生的牦牛被人盗走,得知消息的村长陪老阿妈来到邻村寻找丢失的牦牛。村长的执念,老阿妈的惶恐,关于藏区人们传统的惩戒观念扑面而来。措姆阿妈,小声低语,希望村长返回,不要因为小偷的被抓,而破坏了她放生的功德。三位邻村的惯犯,绕着煨桑台,手持佛经,向三宝发誓,他们没有偷盗。其间没有一个人站在道德的制高点,对事件进行评价,大家都在静静地等待,等待着最终的结果,整个事件从开始到结束,没有一个人试图将其诉诸法律。最后邻村村长的儿子自己主动承认了偷羊的事实。整个事件恰如藏族人生活中再平常不过的一件小事,没有波澜,没有高潮,人们相信佛祖的公允,人们坦然接受所有的事实,这就是藏区的现实。从公元7世纪以来的佛教信仰,已经完全渗入藏族人的生活中。通过说教、故事,或是戏剧的形式,将关于生命轮回、因果报应、慈悲等佛学理念渗透在个体的生命历程中,成为藏区每一个社会成员濡化过程中的必修课。我们说社会的和谐运转需要社会控制,外在的社会控制固然重要,但以宗教、禁忌、习惯法、道德等内化的社会控制更是我们人类自我约束的根本。
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藏族作家兼导演,如何在众多的藏族题材中选择自己独有的,为自己的民族寻找位置,展现一个不同于外来者眼中的藏区,作者是做了深入的思考的。第二部作品《静静的嘛呢石》选择寺庙、僧人作为的主要表达对象是也是意料之中的。宗教是藏族文化最为重要的文化符号,已有的对藏区的影像描述很难找到没有宗教痕迹的作品。作者迎难而上,在已有的符号化表达的陈规与惯例之中另辟蹊径,放弃了对藏区奇观化的物象渲染,以客观的镜像语言呈现了个体化的藏族人的生活,①韩敏,全球化时代西藏题材电影形象研究 [J].成都:西南民族大学学报 ,2015(8):165.寻找文化碰撞中的传统。在已有的涉藏影像的梳理中我们不难看到藏文化影像表达的有限性,由于文化的隔阂外来者关注了一些外在的东西,只看到枝干和叶子,没有看到根,对核心的东西理解得不很透彻,表达上就有了误差。对藏族来说,血缘、文化、传统这些东西是有根的。他们眼中的西藏,和一个藏人眼中的西藏是不一样的。②李宗陶,万玛才旦 惟一在拍电影的藏族导演 [J].广州:南方人物周刊 ,2006(16):25.
1958年,法国人类学家让·鲁什在影片《我是一个黑人》中,邀请了三位码头工人,即兴发挥表演,把码头工人的日常生活直接搬上银幕,从而形成了一种虚构与生活混合一体的特殊类型,这一类型在以影像的方式展示人类真实文化方面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万玛才旦导演的这批作品也大都通过虚构与现实的混合还原藏地民众的日常生活。藏语对白;藏族非职业演员出演;实景拍摄;生活化地展现了高原民族真实的生活。而这样的虚构式的文化触动是必要的。更进一步让·鲁什将摄影机看成是一个主动的调查过程,他指出:“一个文化的价值既存在于它的理想之中,也存在于它所建造的现实之中。调查者往往只有通过介入新的刺激,才能揭开覆盖在文化之外的面纱,显露其本质。”③大卫·麦克道戈,跨越观察式电影 载 影视人类学原理 [M].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 ,2001:136.具有人类学品质的这批作品以貌似故事片的形式讲述藏地的人,实则导演通过运动的摄像机表达自己对故土的认知。不同于以往的藏地文化的认知,导演以其自身族内人的观点,主位视角的表达方式,辅以电影灵媒不断地刺激,关于真实藏区覆盖的那层薄面纱才得以去掉。
深远的诵经声夹杂着叮叮当当敲打石块,雕刻七字真言的特写镜头中,在寺庙拜师学经的小喇嘛万代开始了他普通的一天,日常清扫、诵经、点灯、煨桑。新年临近,阿爸牵着马接他回家过年,沿途两人聊着一年来家中的变化,听闻哥哥买了电视,激动不已,半路碰到刻经的索巴老人。回到家中,见到年事已高的爷爷,爷孙两人拿着油馍来到羊圈给牲畜过年。哥哥和女友为新年期间公演的戏剧《智美更登》排练。新年的那一天全村老少汇聚在大院中观看《智美更登》,老人们泪眼婆娑,王子的善行是他们一生修行的目标;年轻人们只把它作为再普通不过的一次娱乐活动,演出的中间,饰演王子的哥哥被小喇嘛万代打断:“哥哥,给我几块钱,我要去看录像”。老人们感叹:“这么好的戏剧不看,偏要去看那些没意思的”。进入了简陋的录像馆,港台枪战片中的英雄美女情节,让小喇嘛万代气愤地跑出来,质问守门人:“为什么,让我一个出家人看这样的片子?”守门人无奈地将票钱退还给万代。万代和弟弟扶着爷爷提前回家,一路爷孙三人讨论者王子给乞丐施舍自己眼球的情节,老人叮嘱孩子们一定要有善行。三天的时间到了,万代再三央求父亲把电视带到寺庙,让师傅看看唐僧喇嘛西天取经的故事……。没有跌宕起伏的情节,有的只是生活流式的记录。格尔茨说:“理解一个民族的文化,即是在不削弱其特殊性的情况下,昭示出其常态。把他们置于他们自己的日常系统中,就会使他们变得可以理解。他们的难以理解之处就会消释了”。①克利福德·格尔茨,文化的解释[M].南京:译林出版社,1999:18.万玛导演非常高超地将藏文化的隐没在日常的琐碎中,这是作为具有族内视角的万玛才旦影像独有的魅力。
2007年《寻找智美更登》。导演和摄影师由一位还俗的老板做向导,一路寻找影片《智美更登》中扮演王子的演员。狭窄的车舱内,老板一路讲述着自己年轻时无疾而终的初恋故事,车内的人们都被感动。围着围巾,少言寡语的女主角也沉浸在这段爱情中。小车在前行中停留在藏区的村落、寺庙。在断断续续的展示中我们看到了八大藏戏之一的《智美更登》讲述的故事:在无数“劫”以前,有个国家叫白达,国王叫撒炯扎巴,他以正法治国,不枉人民。他虽然有一千五百名后妃,却不曾有嗣。国王按照占卜师的吩咐,上敬三宝,中供僧人,下施贫困。果然有一位名叫噶丹桑毛的妃子怀孕分娩,生下一个太子。……取名智美更登。平民百姓备受其恩泽。父王听信谗言将其流放到魔山上服刑。为了履行自己“有者尽施不逆人意”的诺言先后将自己的儿女、王妃、以及双眼施舍给了需要的人们,最终感动了上苍湿婆,回赠了他的财物和眼睛,全家得以团圆。并替父亲登上了王位”②才让太,智美更登初探 [J].拉萨:西藏研究 ,1988:(03)82.。这个贯穿了佛教布施观的藏戏作品,成为佛教在藏区广泛传播的重要形式。在佛教中布施为六度之首。是众生度过人生苦海,达到涅槃境界的首要途径。①才让太,智美更登初探[J].拉萨:西藏研究 ,1988:(03)85.也是藏族文学、哲学讨论的一个重要议题。以往的历史中人们毫无置疑地接受传统,而今在现实的冲击之下,传统被质疑,被解构。影片中一位现实生活中的老者将妻子转赠给他人,(导演组拍片过程中在甘肃夏河县确实碰到过一位转赠妻子的老人)遭到导演组的质疑,你有什么样的权利,替你的妻子做出如此的决定?古老的戏剧流经了时代,内容没有发生变化,意义却因了时空的转变,让人们难以理解。影片依旧是虚构与现实的不断互动,现实中的人们生活在戏剧中,戏剧中的人们活在现实中,在不断的虚实互动中,文化的核心得以显现。
2011年的《老狗》故事发生在20世纪90年代末,安多藏区的一个小镇到处在搞机械建设,商店、饭馆、斯诺克球案,随处可见的摩托车、大型货车……一个极为标准的奔向现代化藏区小镇的缩影。儿子贡布打算把家里的老藏獒卖给乡上的狗贩子,父亲坚持留住这只老狗,村里的狗贩子三番五次地领着外面的人来看狗,老人执着地坚守着……。以养藏獒出名的老者,儿子却以贩狗为生;小镇的大街上格萨尔艺人的歌声混杂着现代音乐;游手好闲的年轻人骑着摩托车游荡在街角;忧郁的贡布不知何去何从,醉酒的深夜高喊: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的……依旧是纪实手法的拍摄,镜头直面藏区每天上演的“小事”。一只藏獒的去留,引发了传统与现代的碰撞。在藏区几乎每个藏族人家中都有一条忠实的狗,不管是一只普通的土狗,还是一只体积庞大的藏獒,它仅是这个家庭中生命组成的一部分,它肩负着看家,守护牧场的职责,人们既不高看它,也不轻视它,是生命就应该珍惜。但是从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的经济高潮之下,藏区的狗被神话了,媒体报道藏獒:“体大如驴、奔驰如虎、吼声如狮、仪表堂堂”,作为一种符号,藏獒的拥有者被赋予成功者,地位尊贵的象征……,这样的文化错位是老人理解不了的,但这样的文化错位随处可见。
2014年的《五彩神箭》作为万玛导演最像电影的一部影片,是因为电影从故事内容的选择到镜头语言的建构都有别于他以往的影片。尽管是一部尖扎县官方背景的以弘扬保护传统“射箭”文化为目的影片,但作者巧妙地结合了商业电影的艺术特点,将宣传的意图融入到一项文化传统和一个美妙的爱情故事中:拉隆村和达莫村世代友好,两村历来有射箭比赛的习俗。射箭世家的大儿子扎东已经连续两年输给了达莫村的神射手尼玛,无缘象征神射手的“五彩神箭”。怀恨在心的他阻扰尼玛与自己妹妹的恋情。两个村的孩子暗地里也在通过各种形式比试箭艺,长一辈则对传统渐渐的流失而担忧。尖扎县政府将要举办的一场大型国际射箭比赛,扎东和尼玛将代表各自的村庄争夺唯一的参赛资格……有别于以往的影片从《五彩神箭》开始到2015年的新片《塔洛》,作者似乎放弃了纪实语言的拍摄风格,藏族专业演员的出演,浓郁的文学色彩,跨越时空的想象。成为这位新锐导演新的起点。
三
作为大众媒介的电影,在现代社会中扮演者重要的角色,是族群文化建构与传播的重要方式,同时电影在国际传播的语境里,也常常是民族国家自塑形象①胡谱忠,藏语电影的生产背景与文化传播 [J].上海:电影新作2014:(05)51.的重要途径。万玛才旦藏族题材电影拍摄、传播是新时代背景下我们的民族国家形象建设的路径之一。
首先作为藏族题材的影片,不可避免地要谈到创作者身份对影片的影响。摄像机诞生后的前七十年,于普通人来说摄像机的拥有和使用是一件困难的事情,“但在1970年代后期,影像摄制技术的进步,更为廉价易得和方便操作的磁带式电子摄像机(VTR)与剪辑设备的出现让越来越多的普通人进入影像制作者的序列中。从美国的索尔·沃斯与约翰·阿代尔主持的“纳瓦霍人电影计划”;加拿大国家电影局推动的“挑战促变革”行动计划以及巴西的“乡村影像”计划的实施中,越来越多的少数民族族裔掌握摄像机。当民族的成员拥有了影像创作的能力,本身便意味着文化权利的获得,他们不再只是在镜头前方被拍摄与询问的对象,而是能运用影像叙事,成为表达民族文化与自我价值的创作主体”。②朱靖江,影像权力的漂移:海外“原住民影像”运动简史 [J/OL] .http://www.chinesefolklore.org.cn/forum/viewthread.php.尽管这段评价是人类学者对社区影像运动的理解,同样适用于二十一世纪以来的中国少数民族电影的创作现状。自2005年以来,多位少数民族身份导演的母语电影创作,在某种意义上可以理解为文化权利的获得,这种权利的获得对于我们未来民族文化的传播;各民族间的相互理解;新时期民族国家形象的塑造是有意义的。万玛才旦是这一影像创作群落中成果较为丰硕的导演,作为一个深谙自己民族文化内涵的创作者,他的影像创作弥补了由于主位与客位之间的认知差异而导致的缺陷,同时通过主位观察的影像方式达成的文化描述满足了族群内部对自身的主观评价,而这一评价是重要的。我们已有的有关少数民族的影片在媒介传播的渠道中总会出现难以预料的问题,很难达到各方面的满意,主位观察视角的缺失是造成这些问题的原因之一。只有“这种影片的出现才能真正解决由汉族视角所带来的一系列问题。”③刘书行,略论中国当代少数民族电影中的影像奇观 [J] .南京:文教资料 ,2014:(04)83.才能实现民族文化的无障碍传播。
其二万玛才旦电影是一个由影像重新建构到文化深描的转变过程。区别于以往走马观花似,猎奇式,他者想象式的文化描述,发生在主位视角观察之下的影像活动,以新的视角细节化地呈现民族文化。这样的呈现打破了藏地在影像传播历史中的被动性,改变了藏族文化在影像历史中被书写、被传播的惯例,完成了藏地文化影像重构与文化深描历史使命。带给我们立体的文化认识。作为中国电影子系统中的藏区影像发生这样的变化,对于此类题材电影的创作是一个启发。
【作者:杨伟,西北民族大学新闻传播学院讲师】
(责编:敖超)
中图分类号:J9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ISSN 1004-6860(2016)01-0067-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