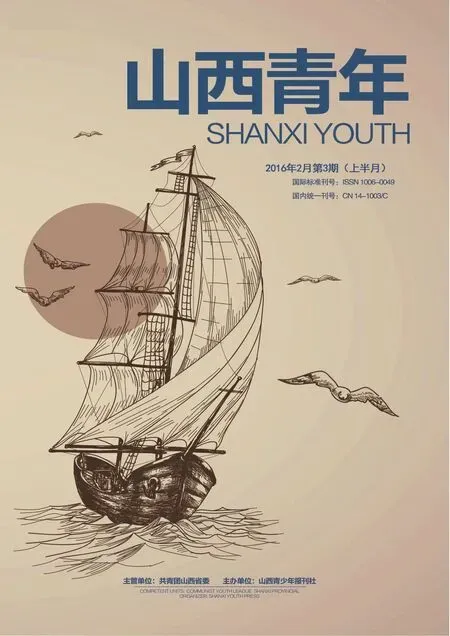失去“成员”感的性身份认同——《婚礼的成员》的精神分析视角
郭 运
暨南大学文学院,广东 广州 510000
失去“成员”感的性身份认同
——《婚礼的成员》的精神分析视角
郭运*
暨南大学文学院,广东广州510000
摘要:本文从贯穿全书的这一核心问题入手,运用拉康的精神分析方法,探究麦卡勒斯笔下跨越性别身份的人物的精神世界,尝试对其挑战传统二元对立性别区分模式的性别观做出分析,以期揭示麦卡勒斯“精神隔绝说”的性别批评之维。
关键词:麦卡勒斯;《婚礼的成员》;性身份;拉康
一、引言
《婚礼的成员》(the Member of the Wedding,1946)是美国南方女作家卡森·麦卡勒斯(Carson McCullers,1917-1967)的长篇力作,讲述了男孩子气的青春期少女弗兰淇寻求性身份定位的故事。弗兰淇因长得过快的身高、粗鲁的举止等,被排除同龄的女性团体之外;又因青春期逐渐成熟的女性身体,被排除在男性团体之外。这使她突然发现自己无所从属,被世界孤立。因此她希望通过成为哥哥婚礼的成员,来破除这种被隔绝的状态。
对于《婚礼的成员》的评论,无论是从成长小说,酷儿理论,抑或是从种族政治入手,都离不开对弗兰淇的性身份定位问题的讨论。而布鲁德(Broaddus)在博士论文中提到,还没有严格运用精神分析理论来分析《婚礼的成员》的评论,特别是拉康主义的阐释,虽然她在自己的文章中也较少运用精神分析理论来探析《婚礼的成员》,但她认为“尽管如此,用拉康的理论分析这篇文章是值得一试的”。
二、母亲缺席导致与女性身体的分裂
故事发生在弗兰淇十二岁,十二岁的弗兰淇被性身份定位的问题困扰着,产生特别强烈的自我与他者的分裂之感,“在她的意念中世界巨大、分裂而飘零,以一千英里的时速飞旋”(23)。就像夏天是一个过渡性季节一样:前面是象征着生命萌芽的春天,后面是象征着生命成熟的秋天,十二岁正值青春期,也是一个过渡的年龄:前面是童年时期,后面是成年时期。而精神分析在追溯精神创伤的源头时通常会追溯到人的童年时期,更早地甚至追溯到婴儿时期。弗兰淇产生的分裂感并非是青春期突然出现的,在分析这种分裂感产生的原因时,必然要追溯到青春期之前的时期。虽然故事时间是弗兰淇十二岁的夏天,但母亲的照片并没有摆在房间里,而是藏在抽屉里,与枪放在一起,象征着弗兰淇十二岁之前母亲的彻底缺席。
也有评论指出弗兰淇的母亲并非完全缺席,认为保姆贝丽尼斯不仅照顾弗兰淇的生活起居,还关心她的想法,替代了弗兰淇母亲的角色。贝丽尼斯确实部分扮演了日常生活中母亲的角色,但这并不意味着她成为了弗兰淇的母亲。她在讲述自己与鲁迪的爱情时用“比王后还快乐”来形容自己,而弗兰淇也觉得此时的贝丽尼斯“很像一位另类的王后”。王后一词的想象更多地是与法律、秩序,因而贝丽尼斯与其说充当了母亲,不如说是以另一种形式扮演了父亲的角色,行使了父亲的权利。她以另一种形式来行使“法律”——按照社会的规范,即按照当时南方白人“淑女”的标准来要求弗兰淇:否定弗兰淇关于婚礼的想象,鼓励她去找一个“可爱的白人小男孩”谈恋爱。
如果实在要说贝丽尼斯在哪一刻真正扮演了母亲的角色的话,可以追溯到她与弗兰淇在厨房里讨论完上帝后互相拥抱的那一刻,“弗·洁丝敏(弗兰淇的别名,笔者注)别转面孔,贴住贝丽尼斯的肩膀。她能感觉到贝丽尼斯柔软的大乳房贴在她的后背,她的软和宽大的肚子,她的温暖结实的大腿。弗·洁丝敏呼吸急促,但很快就平换下来,与贝丽尼斯的呼吸一致。她们俩贴近得如同一人”。在身体的亲密接触中,弗兰淇想象二者身体融为一体。凭借身体,他俩跨越了种族差异而获得同一性。就像镜像阶段的婴儿,在镜子中看到母亲的影像并将其与自己的影像等同起来,这个时候主体的状态也是同一而未分裂的。但这种同一之中是有潜在的异己性在场的,即虽然弗兰淇与贝丽尼斯的身体同为女性,但贝丽尼斯“柔软的大乳房”是弗兰淇所没有的。不仅潜在的异己性威胁着同一性,外在的他者也会破坏这种同一性,而外在的他者是以父亲的介入为代表的。表现在这种同一的状态并未持续多久,很快便因父亲的介入而结束,“然后大门开了,弗·洁丝敏听到父亲脚步沉重,慢慢走进门厅。……最后一个在厨房共度的下午至此结束”。以父亲进入门厅的脚步声来结束该部分别有深意,它象征着“镜像阶段”的结束。
弗兰淇短暂的同一后,再次回到分裂的状态。除此以外,母亲在镜像阶段基本上是缺席的。母亲在镜像阶段的不在场是弗兰淇最初分裂的根源所在,因为它导致弗兰淇缺失了关于女性最初的想象,包括对女性身体、女性气质的想象。“主体所欲望的东西正是主体所缺乏和本来不存在的东西,而欲望之不可能得到满足也正是欲望所以产生的原因”,最初的缺失造成了她最初的欲望——渴望与母亲同一。这也正是弗兰淇之后性身份定位问题产生的根源,她之后的行为都是对这最初欲望的模仿。贝丽尼斯告诉弗兰淇,她在鲁迪死后与其他几个男人的结合,都是对与鲁迪同一状态的模仿。她以此来劝诫弗兰淇不要插足她哥哥的婚礼,因为人一旦开始爱上某种东西,之后只会是对最初欲望的碎片的模仿,而这欲望是源于缺失,因而也根本不可能得到满足。弗兰淇想成为婚礼的成员,这种强烈的欲望就是对最初与母亲同一性的模仿。婚礼在当时的美国是异性恋人结合的仪式,妻子一方必然与关于母亲的想象相联系。母亲的缺席导致弗兰淇无法与女性身体同一,促使她在女性身上寻找关于母亲身体的想象。弗兰淇之所以渴望成为哥哥婚礼的成员,与哥哥的新娘嘉尼丝不无关系。弗兰淇对嘉尼丝的印象是“穿着一条绿裙子,一双很美的绿色高跟鞋。她的头发向上梳成一个髻,深颜色的头发,以小缕碎发散在外面”,贝丽尼斯把她形容为“跟正常人没啥两样……褐色头发,小巧好看”。身体小巧、穿裙子和高跟鞋,这些都是南方“淑女”的典型特征,也是弗兰淇无意识模仿的对象。弗兰淇见过嘉尼丝后,决定为婚礼精心装扮。在挑选衣服的时候,她放弃了符合少女身份的粉红色的裙子,而挑了一件橙红色绸缎的“成年妇女的晚装”,配上银色轻便皮鞋、银色发带。弗兰淇试图通过对成年女性外在装扮的模仿来寻求同一性,弥补最初母亲缺席而导致的缺失。但源自缺失的欲望是无法真正满足的,弗兰淇的努力也必然失败。贝丽尼斯的眼睛如同一面镜子,一下就照出了这些装扮与弗兰淇身体的分裂性:银色发带与剪成板寸的头发、橙红色晚装与胳膊肘上褐色的硬皮、银色便鞋与脚掌的大小没有一个是协调的,宣告弗兰淇通过成为婚礼的成员来弥补分裂性的失败。
弗兰淇扭曲对母亲的想象,根源于镜像阶段父亲对母亲的替代性在场。青春期之前,弗兰淇一直与父亲同睡。父亲一定程度上充当了母亲的替代者,介入了她关于母亲身体的想象。但二者的身体毕竟相异,这使得弗兰淇在寻求与女性身体同一时产生混乱。集中表现在弗兰淇对模仿父亲行为的热衷。她的父亲以维修钟表起家,弗兰淇的“血液里有强烈的钟表匠人的遗传”,她“向来喜欢坐在她父亲的工作台前。她会戴上父亲的眼镜,上面架着放大镜,蹙着眉头忙活着,将东西往煤油里浸”。血液与身体不同——血液是无性别、种族之分的,血液混合象征着与他人产生无等级、无差别的联系,捐献血液则是弗兰淇渴望自我扩张的一种方式。西摩尔这一关于血液寓意的分析,同样有助于理解弗兰淇模仿父亲修表的行为。弗兰淇在十二岁这年四月的一晚,因父亲提出分睡,突然察觉到自己的身体与父亲的身体之间的差异。她模仿父亲修表,是她试图抛弃这种身体的差异性,转而在无差异性的血液中,无意识地寻找与父亲同一性的努力。弗兰淇的身体第一性征是女性,但是母亲的缺席使她无法与女性身体同一;本来可能产生替代性在场的女佣贝丽尼斯虽然身体为女性,却在行为上扮演着父亲的角色,行使着父亲的权利;父亲在镜像阶段对母亲的替代性在场,又使她产生与男性身体同一的欲望。青春期之前的弗兰淇如同处于镜像阶段的儿童,虽然在“他者”身上发现了自己,但母亲在镜像阶段的缺席已导致了这些潜在的异己性,成为性身份定位问题在她青春期爆发的根源。
三、对女性气质的模仿又抗拒
镜像阶段潜在的异己性在青春期逐渐显现出来。进入青春期的弗兰淇明确地察觉到了这种分裂,因而迫切渴望同一,突出表现在希望通过成为哥哥婚礼的成员来寻求同一。弗兰淇的哥哥贾维斯在阿拉斯加当兵,要娶一个来自冬山的姑娘嘉尼丝,贾维斯会在周五带着新娘回家呆一天,然后在星期天去离家百英里以外的冬山举行婚礼。在表达与婚礼相关的事情或人物的时候,弗兰淇的表述能力时强时弱。她见到期盼已久的贾维斯和嘉尼丝后却无法用语言表述自己才经历过的事情,因而不断要求贝丽尼斯向自己复述与他们见面的场景。该场景明明是弗兰淇所亲身经历的,她却无法进行表述。弗兰淇将这种无法言说的体验定义为“感觉”:“有些事情,关于这场婚礼的,给了弗兰淇一种无以名状的感觉”,“有些人见过之后回想起来只剩一种感觉,而不是模样”。弗兰淇此时如同尚未进入语言秩序的婴儿,还未获得言说的能力。事物一经语言表达就会被扭曲,因此她此时无法用语言表达的感觉既分裂又同一。一般智力正常的十二岁孩童应已具备较强的语言组织能力,但弗兰淇的表述能力时强时弱,而且处于两个极端。可以说,麦克勒斯在文中对弗兰淇这捉摸不定的表述能力的描写,与她对自身同一性的设想密切相关。拉康认为“主体的确立过程就是掌握语言的过程”,弗兰淇通过不断复述自己成为婚礼成员的计划,建构自己与女性的同一性,以此获得确定的性身份。
但在小说第二部分,弗兰淇的表述能力又意外地增强,主要体现在她向陌生人诉说关于婚礼的计划上。在婚礼的前一天,弗兰淇在小镇里四处走动,逢人就讲述婚礼的事。在酒吧了一个葡萄牙人,“她直奔主题……随着叙述的展开,她的声音开始逐渐清晰,越来越明确而肯定”;碰到打扫前院的女士,“她关于婚礼的讲述有前奏,有尾声,很像一支歌的样子”。书中反复提到她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让他人了解她的“真我”。弗兰淇的“真我”是与之前的“假我”相对而提出的。在这个早上之前,她喜欢假装自己不会英语,而用西班牙语冒充墨西哥人,获取陌生人的关注。弗兰淇认为虽然这个早上向别人讲述婚礼行为与以前冒充墨西哥人的游戏相似,但她认为最大的不同是,她关于婚礼的叙述“没有愚弄别人,没有伪装自己,她只想以真我示人”。弗兰淇曾经假借其他语言来掩饰真我,又通过用英语叙述婚礼来表达真我。可见,她在此是通过语言来建构关于自我的想象的:她向他人叙述婚礼的计划,实际上是通过他者不断建构自己的主体。因为“语言之墙”的阻碍,使得言语发出者并不能与他者的主体直接对话,而是通过听话人把自己的话传达给无意识的自我,从而认识自己。
弗兰淇所谓的真我,是在婚礼的叙述中建构起来的,是在她找到与哥哥、嫂子同一性的想象中建构起来的。弗兰淇对婚礼的想象,是为了弥补在镜像阶段母亲的缺席所产生的性身份的分裂。在找到通过语言建立主体的途径之前,弗兰淇如同仍处于想象界、尚未进入象征界的婴儿,还未进入先在的语言结构中,因此她虽感觉到分裂,却无法用语言表述。进入象征界后,她试图通过语言来建构同一的自我。她试图通过语言来建构并不断巩固她自认为的“真我”,因而表述能力突然加强。她却不知进入语言就意味着能指和所指的分裂。她越是反复叙述婚礼的计划,越是意味着所指的不在场,以及她所欲建构的与女性同一的“真我”的缺失。因此,她试图通过语言来建立与女性同一的性身份定位策略,仍然是无疾而终:她哭喊着“‘带上我!带上我!'但听到的只有婚礼的来宾,因为新娘和她哥哥已经绝尘而去”。无意识是他者的话语,主体进入语言象征秩序就意味着进入“他者的话语”。弗兰淇通过语言所建构的性身份认同,是被扭曲变形的。弗兰淇实际上渴望的并非女性/男性、女性气质/男性气质、对阳具的渴望/被阉割的恐惧这种二元对立的性身份定位策略,而是一种动态的、转换的性身份:“她计划人们可以随时来来回回地从男孩变为女孩,随他们怎么变,只要他喜欢并且愿意”。她通过成为婚礼的成员与女性同一,是二选一的性身份定位策略,违背了她的初衷。弗兰淇所谓的“真我”是被父权制话语扭曲变形后的自我。
弗兰淇真正渴望的是一种动态的、转换的性身份,因而她在成为婚礼的成员失败后,仍然决定离家出走。她打算乘坐两点钟的列车离开小镇,列车“如果到芝加哥,她就继续前进,去好莱坞,写剧本或者演些小角色……如果列车是去纽约,她就扮成男孩,谎报年龄和姓名参加海军”。弗兰淇听到嘉尼斯说自己身高正好,便吹嘘自己是时装模特和电影明星的身高,听到派特姑妈说自己气质不错便四处吹嘘自己“应该去好莱坞”,可见好莱坞在弗兰淇心目中是女性气质的肯定。她把性身份定位交给一辆列车,这实际上是一种动态的、非既定的性身份定位策略。虽然最后弗兰淇出走的计划也失败了,但这一策略是对社会支配性话语中二元对立性别规范的反抗。
弗兰淇对女性气质的态度也是不稳定的。她的某些行为中透露出对女性气质的强烈渴望,她不仅通过穿上成熟妇女的晚礼裙,还试图通过改变名字来来模仿所谓的女性气质。弗兰淇是出生以来父亲取的名字;洁丝敏是弗兰淇按照贾维斯和嘉尼斯的名字皆以Ja开头的特点,给自己加的中间名;弗兰西斯是她离家出走时给父亲留信的落款。她试图通过抛弃“弗兰淇”男性化的名字、使用“洁丝敏”这一女性化的名字,来模仿女性气质。然而,弗兰淇在试图通过以上行为成为一个符合社会规范的淑女的同时,又摆脱不了对男性气质的向往。她拒绝在性行为中确认缺失,而渴望拥有菲勒斯的力量。在士兵企图亲吻自己时,她用玻璃水罐砸破他的头,在惊慌的同时回忆起了前几次懵懂的性经历:“记忆纷乱地掠过心间,前屋里一场普通的抽筋,车库里的那些话,还有可恶的巴尼”。在与巴尼和士兵懵懂的性经历中,弗兰淇感到“痉挛似的恶心”。具有菲勒斯的男性身体是对弗兰淇是具有威胁性的,因为异性恋的性行为是确认女性身体缺失的仪式。在惧怕被确认缺失的同时,弗兰淇还渴望拥有菲勒斯的力量。“飞刀”这个意象在小说中反复出现:第一次是用刀挑脚板上的刺;第二次是在贝丽尼斯嘲讽她为婚礼着迷后,违背父亲禁止玩飞刀的禁令,扔飞刀扎在楼梯门正中间,通过显示自己的力量来威胁贝丽尼斯闭嘴;第三次是回想起巴尼的罪恶想用飞刀刺进他的眼睛;第四次是弗兰淇拿着刀绕着桌子疯跑来排解无法通畅地表述关于婚礼的计划郁闷。“飞刀”成为弗兰淇借以显示力量的物品。自从与父亲分睡、与巴尼发生“罪行”,巴尼、父亲具有法律的强制力量——“她害怕,但已和从前不同,只余下对巴尼、父亲,以及法律的畏惧”。她畏惧巴尼、父亲和法律,却又渴望拥有这种力量。弗兰淇不顾父亲的禁令玩飞刀、渴望用飞刀向巴尼报仇,“飞刀”在这里无疑是菲勒斯的象征。
弗兰淇通过服饰或名字来扮演女性的同时,又拒绝性行为、渴望菲勒斯,这种矛盾的行为证实了单一的选项是无法使她获得性身份定位的。她最后通过选择了玛丽作为以后环游世界的伴侣,并使用弗兰西斯这个中性化的名字,从而在与同性恋爱关系中找到了男、女性身份自由转换的空间。拉康有过关于女性的论断:“女性并不存在”。这并不是男性中心对女性他者而言的“女性并不存在”,而是指那个“被划掉”的女性并不存在,指根本不可能对女性进行全称判断,或者说,女性不是一个可以明确界定的集合。“男性和女性之间没有明确的界限,主体的欲望不同,具体的性别特征就不同”。这恰恰是弗兰淇所渴望的性身份认同状态,但她所身处的父权制社会又不可能允许她真正做到这一点。因此弗兰淇在寻找性身份认同时异常矛盾:既通过改变表演来模仿女性气质,又通过来拒绝性行为来反抗所谓的女性气质。最终暂时在同性恋爱关系中缓和这一无所从属的性身份定位的危机。
四、结语
拉康的精神分析理论,对于解读弗兰淇性身份问题产生的根源,以及她寻求性身份定位的策略与社会对性身份定位的规范之间的关系,具有重要意义。镜像阶段的理论,解释了弗兰淇性身份认同问题产生的根源;“无意识是他者的语言”,为分析弗兰淇进入青春期后模仿女性气质及其失败的原因,提供了依据;而反过来,弗兰淇最终在同性恋爱中寻找性身份自由转换空间,亦是对“女性并不存在”论断的印证。既帮助对其产生的原因进行了溯源,又为她最终所采取的突破二元对立的性身份定位策略,提供了理论依据。
不可否认,拉康作为一个男性研究者,做出“女性并不存在”的判断时,肯定无法摆脱男性话语强权的本质。他和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在本质上并非研究女性欲望,而只是将女性作为欲望对象来考察的男性精神史的一部分。但是,把他的理论武断地看成男性中心话语,肯定是一种女性主义的陈词滥调。之所以用拉康的理论解读弗兰淇性身份定位问题,是因为他在研究思路上的巨大开创作用给我们提供了某种观察性别身份的原创性立场,亦即我们可以沿着这个路径获得一种摆脱二元对立的张力系统。
[参考文献]
[1]Broaddus,Virginia Blanton.Sowing Barren Ground:Constructions of Motherhood,the body,and Subjectivity in American Women s Writing,1928-1948.Morgantown:West Virginia University,2002:96-128.
[2]Gleeson-White,Sarah.Strange bodies:gender and identity in the novels of Carson McCullers.Tuscaloosa:University of Alabama Press,2003.
[3]黄汉平.拉康与后现代文化批评[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
[4]林斌.卡森·麦卡勒斯20世纪四十年代小说研究述评[J].外国文学研究,2005(2):158-164.
[5]Seymour,Nicole.Somatic Syntax:Replotting the Developmental Narrataive in Carson McCullers's "The Member of the Wedding".Studies in the Novel,2009(3):307-308.
[6]伊丽莎白·赖特.拉康与后女性主义[M].王文华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中图分类号:I71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049-(2016)03-0066-03
*作者简介:郭运(1992-),女,汉族,四川巴中人,暨南大学2014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