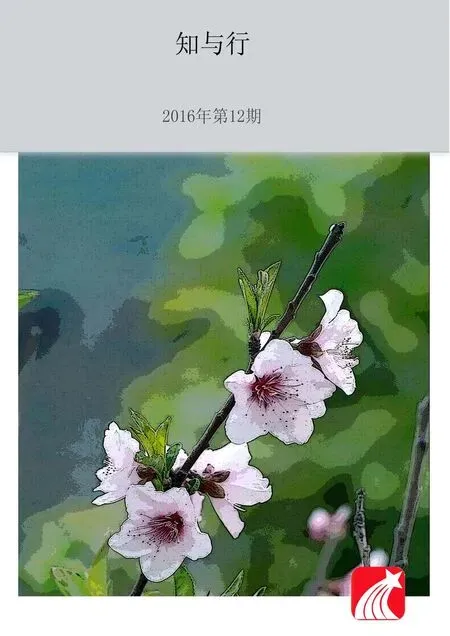中华历史反腐立法的比较与启示——以唐代与明代为例
王仲海
(苏州大学 王健法学院,江苏 苏州 215000)
博士硕士论坛
中华历史反腐立法的比较与启示
——以唐代与明代为例
王仲海
(苏州大学 王健法学院,江苏 苏州 215000)
我国历代封建王朝为了维护封建统治和稳定社会秩序,对官员自身及其施政过程进行了严格的监督,并逐渐形成了一系列较为完整的惩治贪污腐败的立法制度。唐明是我国古代历史上两个非常重要的朝代,王朝的更迭、经济的繁荣和秩序的稳定容易滋生腐败,也会导致国家重视反腐。因此,两朝的反腐立法制度也异常完整和典型。唐代的反腐立法以《唐律疏议》为代表,内容完善,并且宽严适中。明代的反腐立法以《大明律》和《大诰》为代表,辅之各种行政和监察手段,体现重刑反腐。立法特点中,唐代讲究“法密不严”、官德教化和权力制约,而明代却主张“重典治吏”、大兴监察。在对唐明立法进行比较时主要从君主个人经历、法律文本规定、考课监察办法、官员待遇地位四个方面进行,并得出反腐要宽严适中、吏治要提高官员待遇以及唐明反腐具有阶级局限性的结论。以史为鉴,当下中国反腐可以从加大反腐范围、抓住关键少数、建立配套机制、加强廉政教育和提高薪资待遇等六个方面吸收借鉴,渐次推行。
唐明;立法特点;反腐;借鉴
从古至今,贪污腐败被人们深恶痛绝,同时它也严重动摇着一个政权统治的根基。所以,历代统治者和贤明的政治家都十分重视对各级官吏的约束和管理,以期望达到所谓的廉政。“廉”作为一种政治文化在中国传统社会占据重要地位,关于政廉和品廉的言论更是不胜枚举。它作为判断吏治清浊的标准和对官员的价值要求,被历代统治者所推崇。与其他朝代相比,空前繁荣开放的唐代和皇权达到顶峰的明代,其关于惩治官员职务犯罪的立法也异常完备、全面、有代表性。我国古代政治家管子曾说:“疑今者察之古,不知来者视之往”[1]。
所以,从纵向的大历史观看,我国古代的反腐立法对今天仍有借鉴意义。鉴于此,谨选择唐代和明代反腐立法进行研究,释明差异、胪陈利弊,力图为新形势下进行的反腐提供有益的制度参考。
一、唐代反腐立法的特点
《唐律疏议》源于经济、政治和文化鼎盛发展的唐朝,承继秦汉的立法成果,吸收汉晋律学的成就,表现出高度的成熟性,对后世反腐立法产生深远影响。《唐律疏议》全书共三十卷,十二篇,五百零二条,是我国古代最完整的一部整治贪腐的立法。其关于反腐的条文多达七十条,并对贪污贿赂的罪名、形式和惩罚措施作了详细的规定。唐律的反腐立法为唐代经济发展、吏治清明、社会稳定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并为后世所吸收借鉴。作为我国历史上反腐最持久、最具成效的朝代之一,唐代反腐立法独树一帜,并具有鲜明特点。
(一)法密而不厉。所谓“法密”,指唐律关于反腐立法堪称完备,几乎囊括了唐代社会所能发生的各种情况。元人柳贯曾盛赞唐代法制完备说:“盖姬周而下,文物仪章,莫备于唐。”从犯罪主体看,十分周详:监临官、非监临官、使官、监狱官、退休官员、一般官员、请求者、甚至官员的家人都可以成为相应犯罪的主体。可以说,只要是可能成为贪污贿赂犯罪的主体都被纳入惩治的范围。从犯罪行为看,可谓细致:受财枉法和受财不枉法、事前受贿和事后受贿、请求和许请求、出使受财和不因公事受财、向部属借贷以及买卖得利、征收监临财物送人,等等,无不一一规定。可以说,立法者把所有能想到的贪污受贿行为全部规定为犯罪。所有这些形成了一个完整的罪名体系,构就了一张惩治贪污贿赂犯罪的严密法网。所谓“不厉”,是指对官员的处罚并不一味求重,不滥施酷刑,用刑有度,处罚适中。首先,在刑罚的设定上,唐律是限制重刑的适用的。唐律反贪腐立法重刑并不算多,只有死刑和加役流。在实际适用中,重刑以下的笞、杖、徒、三流也可以用官当或赎铜来代替。其次,在刑罚的执行和适用上也维护官员尊严和体现特权。在官员犯罪的大多数情况下,其刑罚可以通过议、请、赎、官当等制度的运用被替换或减轻执行。再次,在追究官员贪腐的法律责任时又以“贬官”这一行政责罚代替刑罚。这在唐代是一种普遍的现象,最后导致很多官员“有罪无刑”。最后,在频犯者的处罚上,对官员也较为有利。《唐律疏议》规定“频犯者累科”,但是累科的原则是“累而倍论”和“重赃并满轻赃”也就是说按照赃值的一半和计满轻赃进行处罚。
(二)注重官员官德的修养。唐代吸取隋朝因为贪污腐败、官逼民反而亡国的教训,异常重视官员官德,并在选拔官吏的时候,把官员的人品和德行放在第一位。唐代《选举令》规定:“铨拟之日,先乎德行。德行同,取采用高;才用同,取劳效多。”在通过科举选士时,科举通过者还要通过吏部的考核才能做官。吏部择人的四项标准:“凡择人之法有四:一曰身,体貌丰伟;二曰言,言辞辩证;三曰书,楷法遒美;四曰判,文理优长。”[2]由此看出,身、言、书、判作为官德的基本标准被唐代统治者所重视。唐太宗曰“朕看古来帝王以仁义为治国,国祚延长,任法御人者,虽救弊于一时,败亡亦促。”[3]也就是说,唐代统治者通过教化不断提升为官者的道德修养,为反腐打下基础。官德的修养有助于吏治的清明和廉政的形成,后来的贞观之治和开元盛世莫不与此相关。
(三)以权力制约权力。正如法国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所言“没有限制的权力必然产生腐败”所以加强权力的监督,以权力制约权力是防止贪腐的一种有效的手段。在唐代反腐机制中,监察制度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唐代在继承前代得失的基础上,建立了一整套自上而下、行之有效的监察体系。君主作为最高统治者,任命和废黜百官,对官员有生杀大权。中央设立御史台,以御史大夫为长官,御史中丞二人为副,“掌持邦国刑宪典章,以肃正朝廷”。在御史台下设台院、察院、殿院,推行三院制。台院的侍御史地位较高,负责纠察百官弹劾违法失职者;殿院的中侍御史掌纠察朝仪,参与案件的审理;察院监察御史品级低,主要监督地方官员。三院各司其职,分工合作,共同监察百官的行为。唐玄宗时令监察御史六人分别监督尚书省六部,称为“大察官”,明代“六科给事中”即源于此。创设三院制解决了自前代以来监察机构重叠、职权不明的情况。它有利于监督各级官员的施政情况,防止官员胡作非为,更在一定程度上预防腐败,对官员的贪腐行为形成威慑。
二、明代反腐立法的特点
元朝末年,吏治腐败,纲纪废弛,农民起义风起云涌,元朝最终被推翻。明朝建立之初,经历“连年征战加之饥馑疫病,十室九虚”,百姓仍然处在水深火热之中,但是贪污腐败现象却愈发严重。正如朱元璋所说:“掌钱谷者盗钱谷,掌刑名者出入刑名。”当时的户部侍郎郭桓与地方官勾结,贪污、侵吞国家粮食达两千四百万石,成为震惊朝野的明初大案。针对当时贪污贿赂成风,百姓苦不堪言的问题,朱元璋为了维护统治、安抚百姓,在“重典治吏”和“明刑弼教”思想的指导下大力惩治贪官污吏,《大明律》和《大诰》应运而生。朱元璋“重典治吏”在我国历史上影响重大,关于其反腐运动主要呈现以下几个特点。
(一)严刑峻法惩治贪腐。在朱元璋“重典治吏”指导下,明代惩治贪官污吏的立法异常严酷,执行之残忍更是耸人听闻。《大明律吏律》规定:“受赃枉法者,一贯以下杖七十,每五贯加一等,八十贯绞。”《大明律职制》规定:“官吏监守自盗仓库钱粮,不分首从,并赃论罪,一贯以下杖八十,四十贯斩。”对比《大明律》的明文规定,《大诰》这部法外之法的惩治力度则空前绝后,令人胆战心惊。大诰又称为《御制大诰》,是朱元璋亲自制定的一部特别刑事法规,锋芒直指贪官污吏。《大诰》的酷刑数不胜数,剥皮实草和凌迟就是其中的代表。剥皮实草是指把贪污官员的皮剥下填充干草挂在衙门,以警示继任者。“新来接任的官员一见到它,触目惊心,哪里还敢贪污。”[4]凌迟是用小刀去割贪官的肉,而且刀数有限制,一般要一千刀以上,在行刑完毕之前受刑人员还不能死,直到最后一刀。通过以上两例,反腐刑罚之严酷可见一斑。除此之外,各类野史也记载了种类繁多的酷刑,如“醢刑”“抽肠”。
(二)监察制度一枝独秀。明代的监察制度在吸收前代经验教训的基础上,不断丰富完善、发展创新,成为维护统治、监督百官、整顿吏治之利器。明代的监察机构主要包括都察院、六科给事中和按察司。都察院由御史台演变而来,据《明史职官志二》记载,在中央设正官左右都御史二人,正二品;左右副都御史二人,正三品;左右佥都御史,正四品。三部门监督百官直接对皇帝负责,不受其他部门的干涉。在地方,则设立十三道监察御史,专司地方各种事情,但是也分工监察中央各部院衙门,甚至其主管部门也在监察之列。都察院中还设有独立性较强的监察御史,他们可以不受都察院节制,有事单独进奏。都御史和监察御史同为皇帝耳目,监察官吏又相互监督。六科给事中源于唐代的“大察官”,但是职权和组织形式随着君主专制集权的增强而发生了变化。给事中的职权在于“稽察六部百司之事”,同时也拥有对官吏的弹劾权。按察司则和十三道监察御史构成地方监察的主体。按察使掌一省刑名按劾之事,“纠官邪,戢奸暴,平狱讼,雪冤抑,以振风纪,而澄清吏治”。通过论述我们发现,明代的监察制度形成了交叉分工、相互配合又相互监督的多元化网络监察体制,有力的监督了百官的行为。为了确保监察效能的正常发挥和监察权的正确行使,明代不仅建立了一整套完善的监察人员铨选、考核、升黜等人事管理制度,还建立了严密的监察责任制度,对监察官员的经济犯罪加重处罚[5]。所有的这一切就像一张无形的大网把各级官员包括监察官员牢牢地控制住,而网口就在皇帝手中。
三、唐代和明代反腐立法的比较
唐代和明代作为我国古代两个人口众多、经济繁荣的朝代,都异常重视反腐,立法严惩贪污腐败行为。但是,最终结果却是唐代反腐富有成效,吏治清明,明代反腐归于失败,统治混乱。这不得不引起我们的深思。接下来,笔者将从君主个人经历、法律文本规定、监察考核办法、官员待遇地位四个方面进行比较,力求找出其中的原因。
(一)君主个人经历
在皇权专制和人治的封建王朝,往往最高统治者一人决定了一个国家的兴盛和衰败,所以君主的个人思想和经历对包括反贪在内的一个国家的方方面面至关重要。隋末,炀帝横征暴敛,官吏鱼肉百姓,以至于民怨沸腾,纷纷揭竿而起。据《隋书刑法志》记载:“帝(隋炀帝)乃外征四夷,内穷嗜欲,兵戈岁动,赋敛滋繁。有司皆临时胁迫,苟求济事,宪章遐弃,贿赂公行,穷人无告聚为盗贼。”最后,在波澜壮阔的农民起义中强隋转瞬即亡。领导过反隋斗争的唐太宗即位以后,有感于农民起义力量的强大,积极反思隋之弊政。他认为:“为君之道必须先存百姓,若损百姓以奉其身,犹割股以啖腹,腹饱而身毙。”因此,李世民十分注意整饬吏治,不断减轻百姓负担,轻徭薄赋,避免再出现官逼民反的悲剧。而且,他本人“深恶官吏贪浊,有枉法受财者,必无赦免”。所以,他任用贤臣,广开言路,惩治贪腐,最后出现了我国历史上“贞观之治”的盛世。可以说反隋斗争的经历对唐太宗以后的统治政策和反腐斗争影响重大。
明太祖朱元璋的布衣出身和领导农民起义的经历,对他以后的反贪腐影响很大。1328年,朱元璋出生在濠州钟离(今安徽凤阳)一个贫苦家庭里。朱元璋年幼时家庭贫困,无法读书,他只好给地主放牛,有时还经常遭到毒打,这在他年幼的心里留下阴影。后来家乡发生旱灾和蝗灾,走投无路的朱元璋到了皇觉寺做了和尚。后来元朝的统治日益黑暗和腐败,汉人被称为“贱民”,生命还不如一头毛驴。目睹这一切的朱元璋十分痛恨元朝的黑暗和腐败决心起来反抗,拯救人民于水火。他加入义军,并逐渐成为领军人物,最后于1368年在南京称帝,国号大明,年号洪武。因为农民出身,朱元璋对元朝的灭亡印象深刻,因此十分理解百姓疾苦,痛恨贪官污吏。在1364年正月朱元璋对他的谋士说:“建国之初,首在正纲纪,元末之所以引起天下骚乱,统治腐朽,是因为统治者内部昏庸无比,主荒臣专,威福下移,法度不行,人心涣散,上下腐败所造成,这是我们必须引以为戒的教训啊。”[6]此时的朱元璋对腐败已经有一个清醒的认识,为他以后整顿吏治埋下伏笔。后来,在朱元璋的领导下,明代先后颁行了《大明律》和《大诰》整治贪污腐败。
通过比较可以发现,君主的个人经历和对官员贪腐的惩治力度密切相关。唐太宗出身贵族,深受儒家经典的影响,参加过反隋斗争,认识到百姓力量的强大,因此它仁政爱民,他的“君民舟水论”被后世传诵。受过良好教育的他也懂得吏治的智慧——刚柔并济、恩威并施、宽严适中。后来,唐初吏治清明,百姓安居乐业,反贪腐效果显著。而在另一位布衣出身的皇帝朱元璋的领导下,明代的反贪立法却异常严酷,酷刑比比皆是,如枭首、弃市、凌迟、墨面、文身。此外,他还自创了许多的酷刑如铲头会、刷洗、抽肠。关于明代反贪腐令人发指的原因也和朱元璋个人有关。正如我们前边讲到的一样,农民出身,同情百姓,痛恨贪官污吏,并没有受过良好教育导致吏治的指导思想也有问题。反腐虽然取得一定的效果却无法持久,后来随着朱元璋的去世反腐最终失败。
(二)法律文本规定
唐代在反腐立法上继承和总结秦汉以来历代的经验教训,立法严谨、体系完善。《唐律疏议》条文共五百零二条,其中关于反贪的条文就达七十多条,主要分布于职守律、户婚律、擅兴律、杂律等法律中。关于唐代反腐立法,我们最为熟知的就是 “六赃”。《唐律疏议名例律》以赃入罪条说:“在律正赃惟有六色:强盗、窃盗、枉法、不枉法、受所监临及坐赃。自外诸条皆约此六赃为罪。”[7]六赃是关于赃物的犯罪行为的量刑标准,并分为六大类,统称为“六赃”。其他关于财产的犯罪也可以归附于六赃,依六赃定罪处罚。六赃除强盗和窃盗是关于侵犯一般公私财务的犯罪外,其他四项主要是对于关于官员贪污受贿的处罚。“六赃”的规定是唐代关于反贪立法的一大进步,使纷繁复杂的、混乱不堪的关于官员腐败犯罪顿时明晰起来。“六赃”被后来的朝代所吸收和借鉴,到明清时更加完善,并配上六赃图置于律首,广泛使用。
明代的反贪腐立法吸收和借鉴唐代立法,如我们所说的“六赃”,但是贪腐立法明代要比唐代更加精细和严厉。第一,范围增加和内容细化。关于赃物犯罪,唐代主要是在《职制律》中,并没有专章去规制,而在《大明律》为此设立《受赃》专章,并且内容极为详尽、细化。在渎职犯罪方面,相比《唐律》增加了“故禁故堪平人罪”和“凌虐罪囚罪”,使得惩治范围大大增加。第二,刑罚力度大大增加。《大明律》规定,官吏监守自盗,不分首从,八十贯斩。对比《唐律疏议》的规定30匹才绞,可见处罚大大加重。此外,明代还专门制定《大诰》这部刑事特别法规惩治贪腐,其刑罚残忍度简直骇人听闻。
(三)考核监察办法
我国古代的统治者为了维护封建统治,比较重视用人,唐太宗认为“治安之本,为在用人”。为了正确使用和监督官吏,让他们不胡作非为,唐代和明代都很重视对官员的行政行为进行定期考核。唐代对官吏的考核也叫作考试,是按照一定的标准考核官员的品质、才能、勤劳、功过,分列等第据以升降赏罚。官吏的考察机关为尚书省的吏部。考核方式有大考和小考。小考又称为常考,每年一次,评定官员当年施政的优劣,由本司或者州县长官主持;大考通常四年一次,对官员在任期内的施政情况进行评判,四品以下官由吏部考功司负责,三品以上官报皇帝裁决。这些评判的结果会作为官员晋升的依据。唐代对官吏的考核的正面标准为“四善二十七最”。所谓“四善”其内容为:“一曰德义有闻,二曰清慎明著,三曰公平可称,四曰恪勤匪懈。”[8]“二十七最”是根据各部门、各系统不同职责而提出的考核才能的最优标准。“四善”为官员规定了品德所要达到的最高标准,而“二十七善”则为不同部门、系统官员的从政品行和才能做出了具体要求。
到了明代的时候考核制度日臻成熟,形成了一个具有考满、考察的完整的、严密的体系。考满是考察官员在一定任期内完成本职工作的情况,决定是否加级、进俸或升职。考满的程序依任官的类别和职务的高低而有不同,京官与外官不同,高级官员与中下级官员不同。考满的期限,据《明会典》记载“国家考课之法内外官满三年为一考,六年再考,九年通考黜陟”。由此可见,明官的考满期限为九年,共分为三个阶段,每一阶段三年。考察是指在特定的时间内就官员的德行和能力进行考察,以决定去留。它的考察对象分为外察和内察。外察就是指利用朝觐对京师以外的官员的考察。内察则是对京官的考核,每六年举行一次,自弘治十六年奏准以后,自成定例。
(四)官员待遇地位
官吏作为封建统治的重要支柱,其廉洁性严重影响着政权的兴亡,而官员的待遇地位又影响着其是否贪赃枉法,因此,历朝历代的官员待遇就显得十分重要。唐代吏治清明而明代贪官“朝杀而暮至”官员待遇地位起到很大的作用。
“唐代有官职和爵位的人,基本上有国家规定的物质待遇,这种待遇主要包括土地(职分田)、禄米和钱货。”[9]以唐代前期京官正三品(相当于如今的各部部长)为例,禄米每年是400石(一石大约100斤),职田为九顷(一顷十五亩),可用杂役38人。此外,还用每日的常食料若干(米、面、肉等日用品),免费工作餐,至少五套的工作服,等等。就算官员致仕后,五品以上可以得半禄,六品以下至天宝九年也可以给到终身。此外,唐代官员办公以及杂用开支也有补助名俸料钱。因此,我们看出唐代官员的生活可谓衣食无忧,极为优渥。当然,官吏社会地位很高,有很多的特权,如亲属免役、子女封荫做官,在法律上的“八议”“官当”等等。在这样的待遇地位下官员会好好珍惜自己的铁饭碗,不会轻易贪赃枉法。
明官的俸禄是极微薄的,《二十二史札记》有“明代官俸最薄”一节,《明史》又有“自古官俸之薄,未有若此者”的说法。明官的俸禄部分是禄米部分是钱钞而且没有职分田和其他的补助。一个七品县令每月禄米7石,别说养一大家人连自己的温饱都是问题,何况还有自己的随从,这就使得官员十有八九生计难以维持。海瑞是我们熟悉的明官,死前位居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高位(相当于现在的省部级官员),可是死后所遗唯“俸金八两,葛布一端,旧衣数件”,连他的官殓都不够办。明官俸禄之低可见一斑。更严重所谓是官员致仕以后朝廷是不会发给俸禄的,这直接导致他们必须贪污腐败为退休准备养老钱。此外,官员也没有了很多特权,如官当制度。官员还经常受到厂卫机关的监视,没有个人隐私。明代还自创了廷杖制度,当众被杖打,在士可杀不可辱的古代真是莫大的羞耻,根本没有人格尊严。
四、结论
唐代和明代反腐立法各有其特点,通过比较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第一,反腐讲究宽严适中,刚柔并济,恩威并施。唐代统治者拥有高超的吏治技巧,反腐立法中他们并不像明代那样一味求重,而是宽严适中,强化官员官德和思想教化。如前所述,唐代官员享有很多特权,社会地位极高,并且刑罚处罚“法密而不厉”。结果,唐代吏治清明,社会稳定,百姓安居乐业,形成了我国历史上有名的“贞观之治”和“开元盛世”。并且唐代也成为我国古代反腐最有成效的朝代之一。反观明代,反腐立法过于严苛和残酷,被诛杀的官员多达几十万。但是在高压反腐之下,明代的贪腐虽有遏制但是并没有完全好转,以至于朱元璋感叹“奈何朝杀而暮犯”。并且明初制定的《大诰》随着朱元璋的去世而被束之高阁。最后,明代反腐以失败告终。第二,不断提高官员的待遇地位,建立合理的薪资制度。唐代的官员待遇地位和明代相比差距非常大,不仅仅是收入还包括社会地位。唐代各级官员收入丰厚,社会地位极高,并且家人也享受各种优待。各级官员完全不用为生计发愁,一心好好工作,全力要保住“铁饭碗”,从而减少了腐败的发生。明官收入微薄,生活拮据,如果不贪腐根本就无法维持生计。在千里做官只为钱的古代,指望官员在微薄收入下克己奉公、公正清廉是万万不可能的。同时也正是俸禄的微薄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明代反腐的失败。第三,唐明反腐都有其固有的局限性。唐明反腐立法的根本目的是维护剥削阶级的统治,更好地统治和奴役广大平民百姓。它不愿也不能铲除贪官污吏赖以滋生的土壤——封建剥削制度,因此,也就不可能真正清除贪赃枉法这一痼疾。此外,唐明的反腐立法只是皇权的附属品,皇帝的意志占主导地位,根本无法反映人民呼声。
五、以古鉴今:对当下我国反腐之启示
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经济建设取得长足的发展,社会财富急剧增加,但是随之而来的腐败问题也越演越烈,这引起了人民群众的不满,也会动摇我们党执政的根基。权力是一把双刃剑,如果执掌权力者没有足够的自律,又缺乏有效的制约和监督,必然导致权力的滥用。本着以史为鉴、古为今用的想法,笔者比较了唐代和明代的反贪制度,希望为我国当下的反腐制度建设提供借鉴。
(一)加大对贪腐行为的惩治范围。与唐代相比,我国现实反贪腐中对贪腐的处罚范围还太过于狭窄。一方面,《唐律疏议》严格区分了事先和事后受财:“诸有事先不许财,事过之后而受财者,事若枉,准枉法论;事不枉者,以受所监临财物论。”这样无论官吏事前还是事后受财,事有没有枉法裁判,都要接受法律的制裁,严厉打击了贪污贿赂犯罪。然而,我国现行《刑法》第385条只规定了索贿和接受他人财物两种情况,并没有先谋取利益,后接受贿赂“约定受贿”,这就在立法上出现漏洞,无法贯彻罪刑法定原则。因此,应吸收唐律中“事后受财”的合理内容,完善立法。另一方面,唐律关于赃物的范围也要比现在大得多,包括财物、人力和物力。如果监临官私用监临人的东西,“除各验日计雇赁钱外,还要以受所监临财物治罪”。相比我国《刑法》只是把贿赂定为财物,唐律的立法显然更完善,处罚范围也宽泛得多。因此,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我们应该给贿赂注入新的内容,使其更完善。此外,《唐律疏议》明文规定监临官不得接受下属的“馈送”,离任官员不得接受旧属、士庶的礼物,如有违反则追究刑事责任。综上,唐代的这些反腐立法现在看来仍不失廉政的好措施,仍具有借鉴意义。因此,我们应该吸收其合理部分,加大对贪腐行为的惩治范围,营造良好的官场政治生态。
(二)要紧紧抓住领导干部这个少数关键。在反腐严峻的形势下,我们应该学会抓重点,找到惩治腐败的“牛鼻子”,这个重点和“牛鼻子”就是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领导干部。在现行的反腐运动中,党中央已经认识到这个问题,于是在修改党纪党章中强调高级领导干部的主体责任,在反腐中坚持抓大放小,以求控制住上行下效的贪腐。顾炎武在《与公肃甥书》中说:“诚欲正朝廷以正百官,当以激浊扬清为第一要义”,其实说的也是自上而下整饬吏治的在重要性。高级领导干部的行为直接影响着整个官场的政治生态,并且其廉洁程度和社会风气息息相关。如果高级领导干部带头违法,那么整个官场正常的生态就会被破坏,就会形成“劣币驱逐良币”的局面。因此,只有领导干部以身作则、廉洁自律、官德高尚才能带动下级官员遵纪守法、克己奉公,从而保证自上而下的各级官员为政清廉,真正为人民服务。
(三)构建反贪腐制度的配套机制。反腐不能只靠严刑峻法,要想真正的减轻和减少腐败应该借鉴唐明的经验从考核和监察方面建立一个全面的反贪腐机制。现阶段,应该完善和认真执行公务员的定期考核机制,不再流于形式,而且将考核结果和薪资待遇、职务升迁挂钩,加大对不称职人员的处罚力度,坚决清理公务人员中的害群之马。建立健全自上而下的监督机制,完善和创新巡视制度。自中央开展巡视以来效果显著,绝大多数贪官因巡视落马。此外的专项巡视、“回头看”更是凸显了反腐的持久性,得到人民的好评。与此同时,也要加大对纪监部门和人员的处罚和监督机制,严防纪检部门和人员“灯下黑”问题。最后,也要鼓励和保护人民群众参与到反贪腐活动中来,积极监督各级官员,揭露他们的贪污腐败行为。只有让人民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
(四)加强对官员的廉政教育。在唐代就特别重视官员的官德,不断以儒家的思想教化官吏,正如《唐律疏议》说:“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犹黄昏晓阳秋相须而成也。”[10]在现行反腐中,要多管齐下,不能只靠法律,要加强对官员的廉政教育促使他们不断自我反省。可以通过参观监狱、观看落马官员庭审、参与法制教育栏目来对官员进行廉政教育,使各级官员深刻认识到贪腐的危害性和廉政的重要性,从而各级官员真正做到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最终形成廉洁自律的政治氛围和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
(五)提高基层公务员的薪资待遇。据媒体报道,公务员群体从2003年加薪后已经超过十年未进行工资变动。这就带来一个严重的问题——贪腐,当收入不足以维持生计,每一个公务员都是潜在的贪官污吏。我并不赞成高薪养廉,但是也要保证公务员特别是基层公务员的收入。因为他们和老百姓接触最多,最能影响老百姓切身利益,也最能代表政府形象。要不断提高基层公务员待遇,建立合理的工资增长机制,切实减少因低薪导致的贪腐。
[1] 管仲.管子(形势二)[M].李山,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09:17.
[2] 欧阳修,等.新唐书选举志下[M].北京:中华书局,1975:1171.
[3] 吴兢.贞观政要[M].刘配书,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6:415.
[4] [清]赵翼.廿二史札记·卷三十三·重惩贪吏[M].北京:中华书局出版社,1984:139.
[5] 刘双舟.明代监察法制研究[M].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2004:1.
[6] [清]夏燮.明通鉴[M].北京:线装书局出版社,2009 :160.
[7] 刘俊文,点校.唐律疏议[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214.
[8] 刘昫,等.旧唐书百官志(卷43)[M].北京:中华书局,1995:1823.
[9] 钱大群,艾永明.唐代行政法律研究[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233-234.
[10] 长孙无忌,等.唐律疏议[M].北京:中华书局,1983:3.
〔责任编辑:徐雪野 李彬琳〕
2016-11-17
王仲海(1991-),男,山东泰安人,硕士研究生,从事法制史研究。
D929
A
1000-8284(2016)12-0135-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