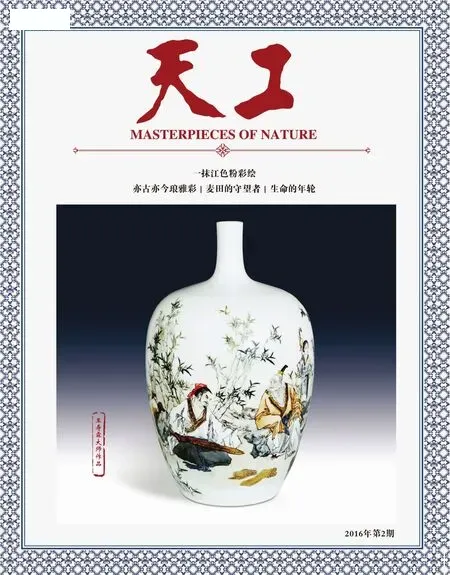卢光华:“大师”是顶荆棘编织的桂冠
文 吴旭华
卢光华:“大师”是顶荆棘编织的桂冠
文 吴旭华

红木竹节台屏《唐伯虎山水画》 卢光华/作
从教师到篾匠,再从篾匠到大师,年过花甲的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卢光华走出了一条并不寻常的道路。“人人都爱说‘不走寻常路’,可我还是希望自己的人生道路能够寻常,少些波折,多些顺遂。”冬阳下,站在自己即将落成的艺术馆前,粉壁黛瓦马头墙的东阳传统民居,再度唤起他对已然逝去的岁月的喟叹。
儿时的大宅院似乎回来了。是,却又全然不是。就像无数次的“否定之否定”,他再也回不去旧时光,好在有一座艺术馆聊以寄托自己的梦想。“卢光华艺术馆”,他自己题写的门额,抹去了任何修饰语,就连无数手工艺人趋之若鹜的“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头衔,他也舍弃不用。“年纪越大,越知道自己所求。”他淡淡地说,“庄子说‘物物而不物于物’,我们不能被大师的名号所累。大师,其实是顶荆棘编织的桂冠,也可以说是一条鞭子。”
这位在业界以“敢于直言”著称的大师,年龄越大,言辞越接近生命的本真,犀利的语锋间闪烁着真知灼见。品读他的原生态话语,处处可见他的思考与感悟——
关于大师名号:“死要面子活受罪”
我于2006年评上中国工艺美术大师。至今想起来,这真是件“死要面子活受罪”的事。我努力拼搏,执著创作了20多年,才具备“国大”评审入场券。大师评审时,按组委会要求,每人仅能选送3件(套)作品参加评比。我大胆地打了一个擦边球,钻了一个“空子”,把“件”成功转换成了“套”,将九件作品分成了“三套”,成功在国家博物馆进行了布展。让专家评委能在极其短暂的观摩过程中了解你的作品特点,这是一件难上加难的事情。为此,通过竹编书画及编织原料的展示,让评委系统全面地了解了我的竹编书画作品特点。既在题材上实现了突破,并着重体现了文化传承,实现了中国名画、名帖和竹编技艺完美结合后焕发出的异样魅力光彩,加深了评委们对我作品的印象。通过这次评审,淋漓尽致地展示了我的作品,并在组委会和评审专家中产生了极大的震撼。也是我一次自身智慧极致的冒险之旅。现在回想起来,我当时能成功,主要是敢想敢做,敢于突破,当老师时练就的口才也起了作用。不过当时也受了“罪”,心理压力极大。因此,还要归功于我年轻时的经历。如果不当老师,我就没有与人交往必需的口才,也不会养成勤于思考的习惯,更没有超前和超脱的思维方式;如果不把我从教师岗位上赶下来,我可能会是个好老师,但肯定成不了中国工艺美术大师。所以,想要有“面子”,就要敢“受罪”。

《醉中八仙》 卢光华/作
这几年,“大师评选”忽然成了一阵风。先不说这些“大师”有多少含金量,就说大家都冲着这阵风而去,这就很值得警惕。你的技艺是否真的达到了大师的标准?你的作品是否真正实现了创新?你评大师的最终目的是什么,是为了高自己的作品价格,还是想在行业中有所建树或者为行业作点奉献?这三个问题没想明白,你去评大师就要慎重!否则,一天到晚忙于评奖、忙于砸钱捞钱,静不下心来创作,拿不出过硬的作品,技艺上永远无法突破,最终是“死要面子活受罪”,瞎折腾!
如果有幸评上了大师,我倒是希望能有点“死要面子活受罪”的精神——为作品的创新、为技艺的提升而“死磕”。不要把“大师”的荣誉当成摆设,而是要把它当成鞭子,鞭策我不断创新突破。“大师”这类称号所承载的是一种文化责任和社会责任,要成为该行业创新的“带头人”,为传统工艺健康发展保驾护航,而不是谋一己私欲,哗众取宠。最好能为行业发展积极向政府建言,为行业与同仁争取发展红利,争取更多的话语权。比如,每年我都利用自己在工艺美术行业的影响力,用提案的方式为东阳传统工艺美术行业争取利益。像木雕城专业升级和木雕产业园区的规划建设,把世贸大道打造成“工美大道”等,及时向市领导提出意见和建议,并获得了认可得以实施。
你若安好,天自安排。评大师是个厚积薄发的过程,大师这顶荆棘编织的桂冠,是永不熄灭的航灯,永远勉励你马不停蹄继续往前。东阳木雕与竹编的传承危机远未消除,年轻人还是应该先练好基本功,夯实基础,践行工匠精神。
关于带徒传承:精心当好孵化器
传统工艺美术行业在技艺上都有家族传承现象,父传子居多。从这个层面讲,现在的评审机制大师子女占了优势,捷足先登,从某种程度上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可以用父子传承带动技艺传承。
但是,我的子女都不从事传统工艺美术,我的“大师”身份对他们而言,并无多少直接利益。这对我而言,我可以非常“超脱”地去思考:我应该如何发挥大师的作用?我的答案是:发现人才,挖掘人才,培养人才是社会赋予我们大师的责任,带好徒弟,当好孵化器。帮助他们孵化精品、孵化项目、孵化艺术,让他们既拿得出好作品,又过得上好日子。

《百马图》 卢光华/作
我的徒弟并不多。他们有个共同的特点:人品好,忠厚老实;手艺好,乐于钻研。这也是我收徒弟的两大标准。我这个人追求完美,在收徒一事上也是如此。事先我告诉他们:想要成为我的徒弟,就必须每年都创作新品,而且要经得起我的挑剔,经得起同行的检验。平时我经常教导他们:多看书,多学习,最好能练习书法与国画,提高作品的内涵。徒弟出了创新之作,我比他们还高兴,忙着给他们去作品研讨,忙着请媒体宣传报道,从精神上鼓励。
艺术馆正式开放后,这里将成为我和徒弟及年轻的工艺美术大师们的作品展览馆。年轻人经济实力相对不足,买地造房存在很大困难,我准备把他们的作品陈设在艺术馆内,利用我的人脉资源和大师品牌,推广他们的作品。只有让他们过上了好日子,才能让他们有信心继续从事工艺美术,传承手工艺。
我设想以后每年在我的艺术馆举办一次“卢光华师徒和年青一代大师作品展”,届时将邀请国家级大师、美术院校专家学者以及行业领导等,为他们挑刺点评;平时还将不定期地邀请专家为他们作讲座。总之,我将整合自己和徒弟们的资源,实现艺术馆功能的“活化”,实现东阳木雕与竹编这两大国家级非遗项目的“市场化”。
我反对传统师徒传承模式中的“门户之见”,把技艺限定在自己的艺术门类内。东阳竹编以立体竹编见长,如果依赖这种“门户之见”,我的平面竹编生源只会越来越少。于是,我关注与竹子相关的艺术,发现了卢培纲、周桂新、杨国强和赵伟阳等一批竹雕新秀,提出把东阳竹编扩展为东阳竹工艺产业。现在,东阳竹雕已成了金华市级非遗项目。后来,我又接受了东阳木雕新人王飞龙的拜师要求。对这个年轻人,我考察了很长时间,在这个过程中也曾犹豫过:一个竹编大师收木雕徒弟,会不会被人说成“手伸得太长”?但是,艺术是相通的,我或许不能指导他雕刻技法,但可以指导他主题、构图、造型以及外观设计。同时,我希望他转益多师,可以为他引荐其他木雕大师,指点他技法。
只收不教、只用不养,纯靠数量取胜,到最后收徒弟变成“聚山头”。长此以往,为祸甚烈。另外,社会上有许多靠自己的努力拼搏评上大师的人,他们虽没拜大师为师,他们的奋斗精神和技艺更为可贵。大家都是传统工艺美术事业的传承者和发展者,应该团结一致,共同进步。
关于经营:品牌才是压舱石
在业内,大家都说我善于资产运作。其实,品牌才是我最重要的资产。工艺美术品牌的构成在我看来一是要有过硬的手艺,二是要有灵活的思路,三是要有良好的人品。房子作为资产,是品牌的外在表现,也是衡量品牌是否成功的标准之一。

《人生悟理》 卢光华/作

精细仿古竹编《宫廷八角食盒》 卢光华/作
差不多30年间,我换了11次房子。最初3万元买下几间企业旧宿舍,精心改装后住了2年以8万元出售,换来一套三居室,靠着这种模式,20年后的我住进了一生不懈努力得到的小别墅。眼下这座我和子女们共同出资兴建的艺术馆,更凝聚着一家人的财力和物力,倾其所有打造的“卢光华艺术馆”,更是荆棘编织“大师桂冠”下的必然结果。但在我心目中,艺术馆的价值更大,因为它就是我的品牌。
为什么我在房产上的投资都能获得成功?除了国家发展房地产的政策,我想一个原因就是我把买卖房子当成艺术品经营,装修精致,使用过程中精心呵护,让买家很欣赏。这反映的其实是我的人品与艺品,也是实现我资产增值的法宝。
现在这座艺术馆,我把它当成了艺术品来营造,尤其在园林绿化上精心设计,精挑花木,几株百年罗汉松和许多名贵花木就花去了近200万元,这里充分体现了中国古典园林建筑与绿化的有机结合,反映的是园主的审美品位与人文修养。
东阳传统工艺美术行业也是如此,要结合另外一个本地品牌优势—东阳建筑。木雕国际创意园区如今已聚集了不少木雕·红木家具企业,通过东阳传统民居建筑风格,形成了鲜明的识别度,并正在向着“木雕小镇”迈进,打造东阳文化产业又一品牌。但在品牌的缔造上,政府还需处理好一些问题,比如与东阳中国木雕城的业态关系,同时要做到放水养鱼。一座占地5亩的艺术馆,整体投资在1500万元左右,就东阳木雕从业者来说,很难在短期内达到这种营收水准。“木雕小镇”品牌的培养非一日之功,不要急于将这个品牌“变现”,通过大师和企业主与政府部门携手,假以时日,“木雕小镇”一定能成为文化产业的亮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