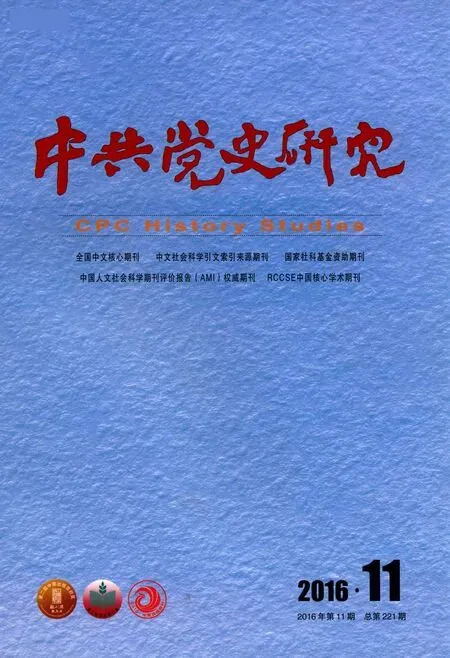一九四九年前后“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确立与演变
程 凯
一九四九年前后“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确立与演变
程 凯
本文试图梳理新中国成立前夕中共如何在从乡村转向城市、从占领转向接管、从战争转向建设的过程中找到并确立了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制度。这是一种复合性体制,其运行既依托协商式民主的组织形式,又依靠“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其功能既作为一种政府管理形式、诉诸“民主的回应性”来解决社会矛盾和民生需求,又须承担民主革命“团结人民”“教育人民”的任务;其性质既是一种根本制度,又是一种工作方法。它的生成和演变过程特别能体现这一阶段中共对“民主”的理解、需求和构造路径。
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实质民主;城市接管
新中国成立初期,“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一度被设定为地方政权的主要组织形式,在普选的人民代表大会召开之前由它代行人民代表大会职权*关于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与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产生方式的不同,刘少奇在1949年9月23日的指示中有明确说明:“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代表就主要是由各人民团体直接或间接选举的……人民代表大会是全权的,其代表主要应由人民直接选举或由下级人民代表大会间接选举,而不是由人民团体选举。”在职权方面,各界人民代表会议是协议机关,原没有选举产生人民政府、审议政府工作报告、政府预算等职能,但《共同纲领》中已规定“在普选的地方人民代表大会召开以前,由地方各界人民代表会议逐步地代行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8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第458、445页。,其常设机构(协商委员会和常务委员会)又成为全国政协在地方的分支机构。这一阶段的“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同时兼具权力机关、政权机关、协议机关、统一战线组织等多重职能。直到1953年底中央着手推行人民代表大会普选工作以及1954年宪法公布和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后,各界人民代表会议才完成其历史使命。
现有研究通常将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作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雏形与过渡形态,放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创建史”的脉络上加以把握。由此,它成为人大制度的“前史”,其“制度性”特质与形式规定的部分特别得到重视,尤其多与之后人大制度的确立、完善过程进行联系和比较。同时,它也常被放入新中国成立后“民主建政”的实践中加以理解,注重其对应的各地现实状况,考察其能否正常运行和发挥应有功能。*如由黎见春撰写的第一本研究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专著《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制度及运作——以湖北地区为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就聚焦于1949年后湖北地区的各级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围绕其职能转变、组织形态和结构、职权和运作及其与政府和执政党关系等问题作了多方面考察。
不过,与新中国成立后的人大制度经过了较为充分的制度设计,然后付诸常规化运行不同,各界人民代表会议本身是在革命战争的多变环境中摸索出来,于诸种不同的试验性作法中逐渐确立起来的一种有特别现实针对性的体制。虽然在其确立后,中共中央颁布了一系列组织通则试图将这一形式加以固定,但它在实际运行中仍保有高度的灵活性。事实上,从一开始,各级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召开就是在中央的反复督促下才实现的,之后的推广也常常依赖上级政府的督促。这固然显得缺乏自主性,但也表现出它不是一套“自动”运行的制度。它作为一种民主制度,更集中体现了主导者即中共的意图和意志,是用来解决问题的工具乃至工作方法。它的有效性必须要结合于中共革命实践中形成的一系列核心性组织原则和工作方法——诸如人民民主专政、民主集中制、群众路线、统一战线等——才能实现。这其中也贯穿着中共重新界定民主并使其为我所用的意图,尤其是在40年代围绕民主政治展开的舆论战与实践争夺中,批判、排斥诸如议会制、分权制和“普遍、平等、直接、无记名投票”的选举制等“资产阶级的形式民主”,试图构造一种具有实质代表性、协商性且有助于解决民众切身问题的“实质民主”*在延安时期,主持民主建政工作的谢觉哉就强调,民主政治的要义不在于选举产生官吏或“言论、出版、集会、结社自由”,而是“大家的事,大家来议,大家来做。在大家公认的条件之下(少数服从多数,个人服从全体……等),谁都能发表意见,好的意见一定能被采纳;谁都有出来做事管事的义务与权利”,因此特别强调“使人民首先从自己切身利害问题的解决的经验上感到民主的兴味”。谢觉哉:《民主政治的实际》,《延安民主模式研究资料选编》,西北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41页。。
基于此,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生成和演变过程便特别能体现中共对“民主”的理解、需求和构造路径。相比它最后获得的形态,其确立过程更值得关注。因为,中共是在从乡村转向城市、从占领转向接收管理、从战争转向建设的过程中,在遭遇种种困难与挑战、面对种种矛盾处境的过程中找到并确立了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制度,以之作为解决一系列矛盾状况且行之有效的阶段性体制。因此,只有还原城市接管、新区解放、民主建政过程中的具体状况方能理解其效用。同时,它与之前和之后中共推行的“人民代表会议”“各界代表会”“人民代表大会”构成何种连接与区别也需分辨,由此可以看出中共基于不同状况和时机展开反复探求与尝试的历史过程。事实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召开和推广既基于自下而上的实践,也诉诸自上而下的要求;既具有应对现实需求的迫切,更基于某种未雨绸缪的预见。特别是在1949年,就中共中央集中强力推动代表会召开的意图而言,除了实用性考虑,更包含着富有提前量的政治考虑。这种政治预见、时机感和带提前量地推动现实转化的意识,也构成这一实践引人瞩目的历史特征。
一、从“人民代表会议”到“各界代表会”
在中共七大上,毛泽东所做《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就已确立“人民代表大会”为未来新民主主义政权的组织形式。但在普选为前提的人民代表大会尚无条件召开的情况下,中共提出先在解放区范围内召开“解放区人民代表会议”。“人民代表会议”与“人民代表大会”的区别在于前者的代表非普选产生,“是由军队、政府民众团体选派的”,而“开人民代表大会就要调查年龄、有没有选举权等,普选还是在战争结束后搞比较好”*《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334页。。根据毛泽东后来的解释,所谓代表会议就是“苏维埃”*“过去我们叫苏维埃代表大会制度,苏维埃就是代表会议,我们又叫‘苏维埃’,又叫‘代表大会’,‘苏维埃代表大会’就成了‘代表大会代表大会’。这是死搬外国名词。现在我们就用‘人民代表会议’这一名词。”《毛泽东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36页。,而“人民代表会议”不同于苏联的苏维埃之处在于它囊括了工人、农民以外的其他阶层,“党外人士要占大多数”,以与新民主主义政权的性质相吻合。
这里的“解放区人民代表会议”并不是自下而上逐级建立的政权形式,而是在各解放区参议会基础上复选、推选产生的最高一级政权组织,最终要以之建立“中国人民解放联合会”——这是一个以“联合政府”为蓝本的地方政权,它不冠以政府名称,但实际上是“各解放区的联合政权机关”,同时“保持其抗日人民的民主阵线”的性质:它“不是第二中央政府”,但“又因为国民党政府必不承认它,固又是独立性质的地方政权”*《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5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第63页。。这是在“联合政府”号召未得到国民政府回应且国民党正加紧筹备“国民大会”的情况下,中共与之唱的一出对台戏。虽然由于形势变化,“解放区人民代表会议”并未开成,但自此,非普选的“人民代表会议”逐步取代抗战时期的参议会、乡议会等形式,成为中共建立各级政权时普遍采用的形式*如在筹备陕甘宁边区第三次选举时,1945年10月5日,陕甘宁边区选举委员会即发出指令,改乡议会为乡人民代表会,以往参议员与行政官员议行并立的体制随之被直选乡政权的“立法行政合一”取代。参见张希坡:《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创建史》,中共党史出版社,1999年,第489页。,各级政府和政权机关也相应统统冠以“人民”的称号。这意味着中共摆脱了国民政府体制的约束,开始独立建政。
“人民代表会议”一经确立,面临的具体问题是它从哪一级开始着手。按照“解放区人民代表会议”的设计,它可以从顶端开始,但实际上,随着国共谈判破裂、内战爆发,各根据地联合的必要性已经被各根据地自主行动、自我壮大的态势所取代。对一直扎根乡村的根据地政权来说,需要巩固的恰恰是乡村基层政权。于是,从1946年到1948年,中央都强调要在解放区自下而上地建立人民代表会议,“县以下由区、村人民直接选举(亦可说由人民直接委派),县以上由区、县代表会间接选举”*《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6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第590—592页。。但是,人民代表会议的建立并非水到渠成,是在土改基本完成的情况下,在组建贫农团与农会的基础上形成人民代表会议,还是以人民代表会议的形式推动解决土改中的问题,中共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指令。
1947年12月18日,刘少奇在给晋绥分局的指示中曾要求“立即召集县以下各级临时农民代表会或人民代表会去解决土改中各种问题,而不要等待农会通统成立,也不要等待各村代表会成立后再召集县区代表会,可先召集县区临时代表会再到各村成立村代表会”*《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6册,第600页。。在他看来,建立人民代表会的民主运动不能与土改脱节,也不能按部就班,要将民主运动与土改斗争融合在一起,使之深化为广泛的群众运动。他特别指出,老解放区因为封建残余已不多,仅在土地问题上着手难以发动群众,“而必须使土改与整党及建立从乡到县的人民代表大会的民主运动相结合,才能发动与组织广大群众运动”。因为,民主运动有更广大的群众基础,“离开这个基础或机械规定先反地主后整干部,先进行土改,后进行民主运动,都不能有广泛的群众运动”。同时,他提出工作重点应放在乡,以乡为基层组织,“如此即可大大免去村中复杂的组织形式,减少村干部,村财政,而工作效能会加强”。*《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7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第16—17页。
而1948年4月1日,毛泽东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则依据1947年冬河北平山县等地的实践提出“在贫农团和农会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区村(乡)两级人民代表会议,是一项极可宝贵的经验”,因为它是“基于真正广大群众的意志建立起来的人民代表会议”。他并且检讨以前的想法,“我们曾经打算在各地农村中,在其土地改革任务大致完成以后再去建立人民代表会议。现在你们的经验以及其他解放区的经验,既已证明就在土地改革斗争当中建立区村两级人民代表会议及其选出的政府委员会,是可能的和必要的”*《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309页。,由此确定了由区、村再到县、县以上的建政顺序。
事实上,在各级人民代表会议的建立过程中,县级是一枢纽。在县级以下,农会、农协实际发挥着决定性作用,而在县级以上人民代表会议中,则有必要吸收更多阶层代表。如果县级以下的人民代表会议可置换为农代会形式,那么县级以上的人民代表会议,无论在产生方式还是在成分构成上都会有很大不同。直到1948年底,中共中央仍强调先确立农协的主导地位再扩大会议代表性:“在双减阶段,新区县、区、村三级皆不应过早建立一士绅参加的人民代表会,而应先建立农协,并由农协所召集的农代会实际起人代会的作用,待群众业已发动起来时再召集正式的人代会。”但到1949年9月,中央纠正了这一说法,认为要等农协在乡村中建立了基础,再召开人民代表会议的方针是很不利的,转而推行在县一级召开“各界代表会”,“县的许多大政方针……均以召开各界代表会议,经过讨论,取得代表们同意,然后传达推行,比较不开这种会,长期限于党内干部的讨论、传达和推行,要有利得多”。*《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8册,第447、445页。
这里提到的“各界代表会”其实是一个在接管大城市过程中新出现的经验和办法。它后来进一步演化为“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并实际上成为县市以上“人民代表会议”普遍采取的形态,而乡村的人民代表会议实践相对被淡化,以至于董必武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总结人民代表会议的起源时直接将“各界人民座谈会”视为人民代表会议的萌芽:“这种座谈会我们各地人民政府成立后就召集过。把各界人民座谈会加以扩充,就成为建议性质的各界人民代表会议。”*董必武:《论加强人民代表会议的工作(1951年9月23日在华北第一次县长会议上的讲话)》,《人民民主政权建设工作》,人民出版社,1953年,第22页。这固然与人民代表会议在乡村的实现程度、影响远不如农会、农协有关,但也更对应着解放战争后期党的工作重心从乡村转向城市、从“农村包围城市”转向“城市领导农村”的历史性转折*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报告中提出:“从一九二七年到现在,我们的工作重点是在乡村,在乡村聚集力量,用乡村包围城市,然后取得城市。采取这样一种工作方式的时期现在已经完结。从现在起,开始了由城市到乡村并由城市领导乡村的时期。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移到了城市。”《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27页。。
二、接管大城市与摸索新的群众路线
在接管大城市的过程中,先期出现的问题恰恰与中共干部沿用一套乡村工作方式相关,如在较早解放的中心城市石家庄的接收过程中就出现了“极左的无政府主义倾向”,当时很多接收干部刚刚参加过晋察冀五月土改复查、全国土地会议、晋察冀边区土地会议,接受了当时在土改运动中强调阶级斗争、走“群众路线”、反对包办代替的一套工作思路,“有些从阜平参加了土地会议来的,满脑子装的是‘群众路线’,农村中依靠雇农,城市中依靠工人贫民,缺乏思考的认识与执行这一原则。看到工人就是好的……结果是走了‘一堆工人’的路线”*《石家庄市职工工作报告》(1947年11月12日至12月底),转引自李国芳:《初进大城市——中共在石家庄建政与管理的尝试(1947—1949)》,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第54页。。这表现出中共理论中设定的接收城市所依靠的主要对象——产业工人和城市贫民(所谓“半无产阶级”)在实际状况中严重“不纯”。石家庄的很多青年技术工人并非因为在农村失去土地成为“无产阶级”而进城,相反,其中很多人是中农、富农子弟,土改偏差影响到他们的政治思想。熟练工人加入国民党的比例相当高。而城市贫民则是造成接收时无政府状态的主因:“首先贫民是搬取公用物资,后来就抢劫私人财物,故有大批煤粮及其他公物被抢,许多公共建筑的门窗杂物亦被破坏或取去,私人被抢者亦不少,很久还不能停止,后来实行戒严、断绝交通,并枪决数人才停止下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7册,第55页。这样的群众基础状况使得接收干部有些无所适从,如接管大兴纱厂的干部就叫苦:“走群众路线吧,就走了国民党的路线,因为国民党员太多;不走群众路线,又不合乎土地会议的精神,就要变成包办代替。”*《石家庄市职工工作报告》(1947年11月12日至12月底),转引自李国芳:《初进大城市——中共在石家庄建政与管理的尝试(1947—1949)》,第54页。
造成“脱离群众”状况并给接收工作带来困难的原因,还在于接收干部不足以及接收干部的组成与工作方式。在内战初期立足不稳的情况下,中央经常提醒不要“把眼光集中于大城市,忘记乡村”,造成只有少数干部留在城市。如1946年占领哈尔滨后,市内来自根据地的干部只有140人,他们的工作方式常是颠覆性而非长期建设性的。从1946年到1947年底的一年多时间里,其工作始终以“发动群众”为中心,先后利用反奸清算、分红、增资、分房、诉苦斗争、反对“敌伪残余”“封建恶霸”等各种手段,不断动员工人、店员、贫民等原城市底层民众,试图以阶级斗争区别城市阶级,组织阶级队伍,进而颠覆旧有社会秩序,建立新的革命统治。这就造成城市经济秩序与社会秩序持续处于动荡状态。
但随着解放战争顺利展开,占领的中等、大城市越来越多,“这些城市收复后又可能长期归人民所有”。以往的“搬运”政策和激烈发动群众的工作方法必须调整。在中共的界定中,乡村的封建经济关系是全然落后的,只有铲除封建势力、重组基层政权才能释放生产力;而城市的功能在于生产,其工业和部分商业无论性质如何,都有完整接收过来为我所用的必要。1948年4月8日,毛泽东在给洛阳前线指挥部的电报中称:“不要忙于组织城市人民进行民主改革和生活改善的斗争。要等市政管理有了头绪,人心已经安定,经过周密调查,弄清情况和筹有妥善解决办法的时候,才可以按情况酌量处理。”*《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324页。
不过,随着新解放的城市越来越多,干部严重不足的困难日益突出。根据1948年8月中央所做估算,未来两年,解放军可能夺取的区域将包括500个县以及许多中、大城市,为此,需要从老区抽调53000名干部,其中7000人左右用于大城市工作*《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7册,第427页。。但现实进展远超预估,到1949年6月,中央不得不再次下发抽调38000名干部的通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8册,第328页。。对于北平这样的超大城市,相较200多万的人口,全市共产党员加在一起不过5000人(2000名地下党员,3000名从解放区调来的党员),即便全做干部使用也依然远远不够。
更要紧的是,依赖外来干部工作本身滋生很多弊端。在解放石家庄的过程中,一方面,上级发现石家庄原有地下党“极不纯洁”,“抢东西及后来乱斗乱捕没收东西等现象,许多就是他们带头干的”,“完全不能倚靠他们来管理城市”;另一方面,如完全依靠外面派去的干部,则“这些干部对石庄情形是不熟悉的,与石庄群众是毫无联系的。他们并还带了乡村中清算恶霸地主的一套经验进城”*《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7册,第56页。。事实上,华北局为接收石家庄而调配的干部很多,到1948年5月从各根据地抽调的干部达到1660人,其目的即在于摸索经验,以为将来接收其他大城市准备可资借鉴的蓝本。但外来干部的集中带来意想不到的问题,即派往城市的工作干部越多,反而更加阻塞城市领导机关与群众的联系和接触,“各领导机关每日所接触传达的,都是在外面派来的这些干部中打圈子,他们所反映的情况,又常常主观得很,与人民生活中的实际和群众中的真正舆论相距甚远”*《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7册,第529—533页。。这显然有悖于毛泽东要确立的城市工作原则——“城市已经属于人民,一切应该以城市由人民自己负责管理的精神为出发点”*《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324页。。对于中共的接收干部来说,迫切的问题是思考、摸索一套与城市工作相适应的,与乡村经验不同的走“群众路线”的方法和形式。
三、民主选举的“超前”与对“民主”的重新定义
事实证明,在情况不明、市民组织程度低、社会团体尚未组建的情况下,一开始就从基层入手动员群众搞阶级斗争的方法得不偿失。因此,中共逐渐明确接管大城市的要务是稳定社会秩序和恢复发展生产。为此,各地开始尝试用召集“各界座谈会”的方法,宣布政策,安定人心。有的地方还成立“临时参议会”,聘请若干工农商学各界参议员“作为市政府咨询机关”*《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7册,第56页。。但这只是停留于上层的统战工作,更进一步则需要有效建立联系群众的机制,落实“人民民主专政”,调动市民参与城市管理。
在像石家庄这样一些最初解放的城市里,中共曾努力推动直接召开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各级政府。刘少奇在最早给石家庄的工作指示中就提出:“要在半年内正式选出区、街政府,一年内选出人民代表,召开市人民代表大会,组织正式的民主政府。”*《黄敬同志传达刘少奇同志对石(家)庄工作的指示》,转引自李国芳:《初进大城市——中共在石家庄建政与管理的尝试(1947—1949)》,第122页。当然,实际上的推进速度不可能这么快。一方面,在保甲制被废除后,如何将零散市民再组织起来颇为周折;另一方面,“在城市搞民主是否大放手,敢不敢这样做,还没有把握”*《刘秀峰、柯庆施、毛铎等在石家庄市常委会议上的发言》(1949年1月8日),转引自李国芳:《初进大城市——中共在石家庄建政与管理的尝试(1947—1949)》,第129页。。这造成直到1949年初代表会议才开始真正筹备,名称也从“人民代表大会”变成了“人民代表会议”。
即便如此,1949年7月召开的石家庄第一次人民代表会议仍显得相当“超前”。因为,它的区域代表产生采用了直接选举的形式,“用直接、平等、普遍、无记名、秘密、复记式投票法选举”,且代表会议代行了部分人大职权——审议政府报告、议决政府工作大纲、制定政权组织法、选举人民政府委员会等。为保证选举结果可控,市委制定了“依靠职业团体”、区域代表比例要少的原则。在由职工会、劳动人民团体和其他人民团体产生的68名团体代表(区域代表62名)中,只有2人是选举产生,其他均为推举产生。由此造成的各阶层在代表中的比例份额固然符合了之前设计的“工农兵”占优势的预想(达79.2%),但工商业者只占8.5%(11名)的比例又与七届二中全会后制定的加强统一战线、团结资本家的政策不合拍。于是,随后又增聘各界代表30名,其中私营工商业者增加了9名。
可以看出,虽然选举之前存在种种担心,但经过充分酝酿、动员,引入直接选举的混合选举模式依然可以取得政府满意的结果。只是,这样一种尝试并未得到上级的肯定和鼓励,相反,它被认为带有太多“形式民主”的痕迹,费时、费力。《人民日报》的一篇文章特别就此提出批评,认为该市在选举问题上存在着严重的资产阶级“形式民主”的缺点:“该市第一届代表选了四十多天,整天大会小会,只审查代表就用了几十天工夫,耽误大家的生产。”记者调查了一位区政府工作人员、二位代表、六位选民的反映,“其中只有一人说‘普选好,投票认真,民主’,其余八个人都说:‘费时、费事,耽误生产,耽误买卖’”。这些人多认为还是分界、分行业选举好,这样代表性广泛,选举方法亦比较简便,举手就行。
即便被批为费时、费事,石家庄能够顺利举行普选式的人民代表会议还有赖于中共在当地已经营近两年,各级政权、政治团体、社会团体均已建立。而对那些刚解放、尚处于军管阶段的城市来说,搞选举就更不具备条件。彭真在接管北平之前,便在对接管干部的讲话中明确指出,在刚一进城、情况不明、敌我都难以分清时,不能采取民主选举、无记名投票的办法,而应首先采取座谈会的形式:“比如在工厂中找一些好的工人(人数不要太多,否则容易浪费时间,事倍功半)开座谈会,提出一些问题,互相讨论,彼此了解,做些调查研究工作,并解决其思想问题。然后再由市府召开全市工人的座谈会。”座谈会是民主建设的第一步,然后召开临时代表会,最后再召开人民普选的代表大会。在彭真看来,实行民主首要的前提尚非选举,而是“肃清敌人”,因为“在工人、农民不敢讲话的情况下,民主容易被流氓及反革命分子利用”。为此,有必要在接管初期实行军事管制,“在革命势力没有巩固,群众还没有都觉悟、没有从反动统治势力下解放出来、没有组织起来的时候,是必须实行军事管制的。例如,不准随便出版报刊,不准外国记者活动等,这就是军事管制。形式上不民主,实际上是真民主”。*《北京市重要文献选编(1948、1949)》,中国档案出版社,2001年,第70、448页。
这体现了中共一贯将“民主”“专政”视为一个整体的思路,即民主是在“人民民主专政”这一整体范畴下的民主,“对人民内部的民主方面和对反动派的专政方面,互相结合起来,就是人民民主专政”*《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75页。。所谓“民主”是只针对“人民”适用的民主,其实行的前提是将“非人民”的部分剥离出去,对后者实行“专政”。对“敌人”实行专政是对人民实行民主的先决条件,也是首要步骤。因此,彭真强调北平虽属和平解放,但“和平解放”不等于“讲和”,它的性质“叫革命”*《北京市重要文献选编(1948、1949)》,第448页。,敌我斗争仍是第一位的。但是敌我的界限、“人民”与“非人民”的界限并非依据“四大阶级”“三座大山”的笼统说法就可以泾渭分明。实际上,恰好要通过“专政”与“民主”的具体操作来培养、生成“人民”。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先指出“我们现在的任务是要强化人民的国家机器”,随后即强调:“有了人民的国家,人民才有可能在全国范围内和全体规模上,用民主的方法,教育自己和改造自己,使自己脱离内外反动派的影响……改造自己从旧社会得来的坏习惯和坏思想,不使自己走入反动派指引的错误路上去,并继续前进,向着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前进。”*《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76页。
与一般民主理论视民主为公民自然的政治权利不同,毛泽东这里所提的民主并非取其伸张自我权益的一面,而将其视为人民教育、改造自己的途径。这里的“人民”不单不是四个阶级的简单相加,而且即便被确认为“人民”的那一部分也随时处于道路的选择中,有转为“非人民”的可能,因为“内外反动派”的影响时刻存在。因此,“人民民主专政”的主体不是人民、不是国家,而是革命。革命政治中的人民既是主体又是改造对象,确切地说,是改造了自我、符合革命标准的民众才能成为人民,构成革命政权的基础。
对革命政权来说,由于“人民”是要不断调动、生成的对象,所以有必要教会人民使用民主,或者说,在一定阶段内,民主是调动人民参与(革命)政治的有效途径。因此,这里的民主就不是一套形式规则,而是一系列主动、被动地政治参与的方式。无论是座谈会、参议会还是各界代表会、人民代表会议,中共作为主导者都强调要解决实际问题,这样,群众才有积极性、才愿意参与,由此也生发出对“形式民主”的批评,认为只要帮助群众解决了具体问题,只要代表有真正的代表性,则采用选举形式还是推选形式已变为次要问题。刘少奇在1949年8月东北局干部会议上的讲话就集中阐述了这一点,认为公民登记、大家选举、议会制等只是资产阶级民主强调的形式,实质问题在于人民是否善于运用代表会议的形式来解决他们自己的问题,因此,“不要着重形式,不要着重选举”。选举可以搞,但要保证内容,不要流于形式主义,代表哪怕由推选产生,只要真正能代表大多数人的利益就行。他以村级人民代表会议为例,一个村子推选一两个能够代表人民的代表,“没有反动派或者是个别的,大多数人是好这就是好”。代表会要开得生动活泼,一个月一次,一次解决一两个问题,特别是群众真正关心的问题,如伕子不公,负担不公,军属、烈属代耕制有毛病等,这样大家才会积极地参加,反之,如果一个村子负担公粮重,人民代表会议却不讨论,实际上就是没有解决问题,起不到作用。*刘少奇:《关于人民代表大会问题》,《共和国走过的路——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49—1952)》,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第96、97页。
有研究民主的学者指出,在对民主不同意义的使用方法中,“民主是对人民的回应性”更接近民主的真实含义。因为无论强调法律条件、多元竞争还是大众参与,都“偏重政治过程的‘输入’端,而忽略政治过程的‘产出’端”。所谓“回应性”是指“政府的政策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了公民的需求、要求和偏好”,“如果一个政体在‘输入’端看似民主,但它的实际表现却与广大人民群众的意愿背道而驰,把它叫做‘民主’恐怕太勉强”。*王绍光:《民主四讲》,北京三联书店,2008年,第73页。另一种对民主的扩展式理解对于解读中共的民主实践也颇有帮助,那就是“民主不仅是一种政治体制,也是一种政府管理形式”*王绍光:《民主四讲》,第131页。。中共依靠武装夺取政权,其政权合法性不依赖形式化的认证,但它需要民众对政权的认同,需要“符合人民大众根本利益”的确认,因为革命的合法性来源于此。因此,了解民众的真实困难,满足他们的要求,并使民众理解政府的想法,配合政府工作——这些对刚执政的革命党来说是更真实地获得民众支持的方法,也是政府能有效管理的保障。所以,从一开始,找到能够下情上达、上情下达的便捷方式就是推行民主的题中之义,同时它又对应着中共工作方法中的“联系群众”和“走群众路线”。
四、“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确立与推行
经过一段时间的摸索,到1948年11月,中共中央最终明确“在城市解放之后实行军事管制的初期,应以各界代表会为党和政权的领导机关联系群众的最好组织形式”*《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7册,第529页。,之前曾采取的贫民会、座谈会、参议会等方式则被认为各自存在不足。
相比之前临时、不定期的座谈会,各界代表会力求成为一个常设性机构。每星期有一到二次会,每次不少于三小时,代表可提出各种市政建议,军管会和政府要派代表参加讨论、解答问题。相对之前参议会集中于上层的情况,各界代表会的代表来源更广泛,但基本限于团体代表,如工厂、学校、机关、革命团体、民主党派、商会等。代表大多由聘请产生,惟人民团体可由群众大会推选,“但必须尽可能地多请原与群众有密切联系的代表,切忌尽请一些从外边派去工作的干部”。各界代表会的定位是“市人民代表会议召开以前的临时政府的协议机关”,所以对政府没有约束权,“但我们如能运用得好,则我党的一切决议和主张,均可经过他们的协助,取得广大人民的拥护,并保持军管会和市临时人民政府与群众的密切关系,使我们能够听到群众的呼声,探知群众的要求,并取得群众的协助来解决各项困难问题,例如解决煤粮缺乏问题及煤粮配给办法等”。*《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7册,第532页。政府能够及时了解、因应民众的需求,得到民众的支持,这被称为“党的政策掌握了群众”,是“考验我们能否管理好城市的决定性力量”。
如果说,1948年11月的这个指示还是一种倡议的话,那么,从1949年7月到12月,中央则频繁发出指示要求在新解放的城市和县迅速召开各界代表会。会议的名称也逐渐确定为“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以涵盖之前尝试的“人民代表会议”和“各界代表会”,并区别于普选产生的“人民代表大会”。中央对各地召开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加以督促的频率和急迫性,从5个月内下发的一系列指示中可以明显体察到,如1949年7月31日,中央给各中央局、分局下发的关于迅速召开各界代表会议和人民代表会议的指示中就提出,凡三万人口以上的城市在解放两个月或至迟三个月内即应召开各界代表会议,并批评之前中央发出关于召集各界代表会议的指示后,为时已久,除太原、石家庄、西安等少数城市以外,各地均尚未召集,此种拖延应迅速纠正。相应地,党内干部中存在的不愿召开此类会议听受批评及建议的倾向必须克服。*《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8册,第395页。
1949年8月9日至14日,北平召开第一届各界代表会议,毛泽东到会发言:“希望全国各城市都能迅速召集同样的会议。”*《北京市重要文献选编(1948、1949)》,第660页。随后半个月内,中央连续下发指示,催促三万以上人口城市和各县一律召开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8册,第422、430页。,并针对执行迟缓的现象严加督促:“你们过去对于城市召开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一项重大问题,没有发出指示,自己亦未在上海执行,故对此事处于被动地位,并因此使城市工作受了相当大的损失。现在你们已经在上海开了一次各界代表会议,收到了良好效果,并已于8月24日给所属发了指示,你们因此就在此项问题上恢复了主动权。中央看了,极为高兴……现在请你们严催所属三万人口以上的城市,务于九月份一律开一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并一律将开会情形在报纸上公开发表,在广播电台上公开广播。不许可有不开的,不许可不公开发表和不做口语广播。”*《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8册,第432页。
到9月份后,中央除了继续下发指示催促之外*如1949年9月3日,毛泽东在《必须维持上海,统筹全局》的指示中强调:“积极利用城市的各界代表会议及各县的全县代表会议,将一切施政中的重大问题,逐一提出自己有了准备的、想过了的、有了办法的问题向会议作报告,并交付讨论,征求他们的意见。”(《毛泽东文集》第5卷,第336页)9月4日,《中央关于转发察哈尔省各界代表会议的报告的指示》中提到:“尚未彻底完成土改的省、县、区三级,均开各级(界)代表会议,乡村开农民代表会议,而以县的各界代表会为中心。”(《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8册,第442页)9月7日,《中央关于召开县的各界代表会议问题的指示》再次强调,县一级的许多大政方针“均以召开各界代表会议,经过讨论,取得代表们同意,然后传达推行,比较不开这种会,长期限于党内干部的讨论、传达和推行,要有利得多”(《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8册,第445页)。9月16日,新华社发表社论《迅速召开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8册,第562—566页)。,鉴于各地在有效召开各界代表会议方面缺乏经验,因此着手采取“典型带动”方式,先选取、培养典型,取得经验再加以推广。1949年9月3日,毛泽东在《必须维持上海,统筹全局》的指示中提出:“新区各县的各界代表会议我们尚无经验,请你考虑选择上海附近一二个县亲自领导,开一二次会试试。”*《毛泽东文集》第5卷,第336页。很快,这一指示得到回应。1949年10月,上海选取松江县召集了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取得成功。毛泽东立即将松江县经验下发各地,要求“仿照办理,抓紧去做”:“这是一件大事。如果一千几百个县都能开起全县代表大会来,并能开得好,那就会对于我党联系数万万人民的工作,对于使党内外广大干部获得教育,都是极重要的。”*《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第51页。
稍后,毛泽东又转发薄一波关于华北各城市各界代表会议的报告,并要求将此报告“用电报发给你们所属各市委省委区委党委并转发到地委县委及一切中小城市的党委,引起全党干部的注意”,要求各地“总结你们自己在这一重大问题上的经验教训,报告中央”。为迅速掌握地方执行情况,毛泽东于1949年12月29日致电华东局,急切询问:“全华东区内县市的人民代表会议共有多少县开过了,尚有多少县未开过?市的代表会议(三万人口以上的)是否均已开过?一九五〇年一二三月内,全华东区所有县市均应开一次人民代表会议,可以做到否?……此次上海市人民代表会议的经验及结果如何?”*《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册,第105、201页。
在五个月的时间里,中共中央连发关于召开各界代表会议的指示,密集时甚至一天一条,表明中央特别是毛泽东在这一阶段推动此项工作的决心。事实上,从1948年11月中央发出第一条指令,到1949年7月开始督促,其间半年多的空白说明关于召开各界代表会的指示并未得到地方的认真执行和回应,因此才出现之后不厌其烦的督促。不难看出,指导者与执行者对这一制度究竟能起到何种作用有着不一致的理解,对实行这一制度的必要性、急迫性也有认识上的落差。确实,各界人民代表会议这一体制并不是成熟的、已在实践中被反复检验过的工作方式。所以,毛泽东特别注意搜集各地执行这一制度时累积的经验,并随时把成功案例转发各级党委研究。而这种经验摸索、总结又与推行这一经验的坚定决心相配合。因此,指导者推动这一制度的决心并非来自对其实现状态的肯定而是对其可能性的信心,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对相关工作中存在的主要矛盾和解决这一矛盾的基本方向的判断。
五、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从对各界代表会议的定位可以看出,如果说各界代表会的召开主要针对接管城市和县级以上政权,那么其中蕴藏的巨大隐患首先在于接管机构脱离群众、陷入官僚主义的危险。
中共在各地接收时普遍采取的方式是成立军管会,以军事管制方式过渡。在军管会人手有限的情况下,通常对军政机关实行直接接管,而对行政机关、事业机关和生产企业等实行军事代表制,即维持原有人员、体制,仅派军事代表加以监控、指导。这样造成的问题是,一般民众接触的行政、事务机构人员仍是老一套人,给人以换汤不换药的印象。而军代表由于事事负责而很容易“陷入事务主义的圈子”,“代表整天忙于各种大大小小的事务,忙于接触接管人员与被接管人员,因此,代表对于重大问题的考虑被事务主义所阻碍,整天忙得不可开交,但多忙于小问题,而放松了大问题”。为此,有的接管工作报告称:“军管会这一机构,对于接是很便当的,对于管则不大适宜。”这些报告由此提出建议:“自上而下的系统接管,必须与自下而上的发动群众相结合……应注意各种工作均要通过会议、推动组织,发挥大家的力量去办。”*《北京市重要文献选编(1948、1949)》,第358、417、412页。
可见,顺利接收只是一个开端,真正的挑战在于百废待兴的状况下如何恢复秩序、发展生产。在战争尚未结束的情况下,很多新解放区都承担着征粮、提供税收、物资支持等重任。怎样摊派,怎样完成征收、税收任务,怎样调节因解放造成的各阶层间新的矛盾——这些问题如果不得到民众的有效配合很难顺利完成。问题是,在工作千头万绪,人手严重不足的情况下,接管干部更倾向用最“有效率”的办法工作,也就是干部会的方式,指令性地工作。相比之下,发动群众、组织团体、召集各界代表会、报告工作、说服教育等必然额外增加许多工作量,显得太过麻烦、损失效率。但中央对此针锋相对地提出,要学会使用“民主”的手段工作,“各界代表会议的召开,不但不会妨碍军管会的职权,相反地,只会增强政府的工作效能”*《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8册,第563页。。只是,这两种工作方式的相辅相成并未经过具体论证说明,而是诉诸应然如此的判断,依靠的是一种“道理”上的支撑——“究竟是依靠少数人工作好,还是让广大群众来共同负责好”。
实际上,采用了各界代表会这样一种“民主”形式不等于它一定能发挥正面效用,它是否能实现真“民主”也不完全取决于其产生过程。对于推动者来说,更真实的是以其内容来确保可以发挥对政府和民众的正面效用,对双方均有益,这样,它就是一种“好的”民主形式。因此,中共在召集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指示和经验总结中不断强调,它的核心是要解决群众关心的具体问题。换句话说,在大多数情况下,它不是讨论政治问题的场所,而是一个听取各方意见、建议,解决民众需求,听取政府工作解释的场所。
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就其形式而言,很容易被指认为“鸟笼民主”。它的代表由选举、推选、聘请等几种方式混合产生。不同时期各种选派方式所占比例不同,但整个代表中各阶层、各政治派别所占份额都按事先拟定的原则确定——通常中共代表不应超过1/3,共产党加可靠的左翼分子要超过1/2以保证政府决议通过,中间分子及“必须拉拢的少数右翼但不反动的分子”占1/3。会议要集中讨论的议题、最终通过的决议也通常经由政府和党组事先确定。按照毛泽东的说法,会议就是要“将一切施政中的重大问题,逐一提出自己有了准备的、想过了的、有了办法的问题向会议作报告,并交付讨论,征求他们的意见”*《毛泽东文集》第5卷,第336页。。这样看来,代表会议势必成为政府布置工作的工具。但是,之所以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得到大力推广,不只因其能成为布置任务的工具,它同时要进一步打造民众对政权的认同,提高其政治参与度和主动的配合性、积极性,没有后者就没有民主建政的基础。所以,在代表产生办法、议题设置、决议产生等程序性规则高度可控的前提下,中共更注意的是如何通过许多非程序性的规定使得会议可以给代表让出足够的表达和参与空间,使得会议起双向而非单向作用,乃至成为一个“干部和人民互相学习的学校”*新华社社论:《一九五〇年全国各级领导同志必须重视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必须开好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人民民主政权建设工作》,第170页。。
为此,中共总结出一系列经验。比如,在会议议题上“一般都以当前生产上的重要问题为议题”*《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册,第105页。,且这些生产议题又应多与民生问题息息相关,“如原料如何供给,产品如何推销,劳资关系如何调整,城市粮食如何供应等”*社论:《必须开好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人民日报》1950年3月3日。,产生决议也相应以“抓紧解决为广大群众所迫切要求解决的一两个问题”为主。因此,提案可以广为搜集、讨论,但决议则要集中,且以能否实现和落实为首要考量:“决议后一定要贯彻执行,不能执行的,不要决定;决定了但行不通的,应向代表和群众说明道理,加以解释,以示信于人民。”而于会议中贯彻“民主作风”,一则体现为政府对自身的工作,已做的、未做的、将做的进行认真的报告、说明,乃至公开政府财政接受监督;二则体现为让代表能有充分发言的机会——“使每个代表都有发言的机会,是开好代表会的关键”。为此,干部应该在讨论中少发言,尤其强调避免对那些“不正确”的言论采取斥责和打压的态度。同时,要创造多样而灵活的会议和讨论形式以提供更多发表意见的机会,“大会之前开了小组会,大会讨论与小组会之间又有个别交谈会,会外座谈。在小组会上发现问题,准备意见。在大会上集中几个问题进行深入讨论。在会议上不怕争论,允许发表反对的意见,让正面反面各抒理由大家郑重研究,然后使分歧意见归于一致”。*上海《解放日报》社论:《从松江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得到些什么经验?》,《人民日报》1949年10月15日转载。
正如很多代表自述的那样,最初他们是带着“听会”“举手”“领任务”的被动心态去开会的,只有当他们从“不说话”变成“说好话”再变成“提意见”“提建议”时,他们的主动性才被逐步调动出来。而这些代表由于多由行业选举、推选,会后要承担的任务就是“向其所代表的机关、团体、学校、工厂、部队和行业,分头报告和解释会议的决议”,这使得上情得以有效下达,“把一个代表大会化成无数的大会、小会”。*《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8册,第563页。在民众与政府的直接联系渠道匮乏的情况下,让民众能较为迅速、直接、准确地了解政府的部署和意图,以减少由于不了解、误解造成的不配合、摩擦与冲突,无怪乎有人称一个代表会可以起到几百个干部的作用。
可见,中共固然视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为一种“实质民主”的探索,但其实更将其视为一种政府有效联系群众的工作方法。《人民日报》社论在总结相关经验时称,代表会议“树立了新的领导作风”:“学会了经过人民代表会议布置工作,检查工作,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学会了通过人民代表会议把人民的意见集中起来然后坚持下去,变为各阶层人民大众的共同意志和行动。”社论认为,新政权在业务不熟悉、干部缺少以及各种复杂任务互相交错的条件下顺利完成各项工作的原因之一,便是依靠了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由此,“不但党外,党内也受到了很大的教育”。因为许多干部习惯于过去在农村的工作方法,即分散使用干部,将干部分散到乡村,巡回活动、单独指导,零散地处理问题,而不太懂得如何将主要问题汇集起来,有步骤有重点地集中力量加以处理。相对而言,各界人民代表会议是一种新的联系群众的方式,通过它可以汇聚带普遍性的问题,确认当务之急,集中力量予以解决。*社论:《必须开好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人民日报》1950年3月3日。
六、代表会议的内在矛盾与应对
虽然代表会议的目的是最终要上下一致,以便执行。但实际上,会议既然是不同阶层表达意见、诉求的场所,那就必然存在矛盾,且“民主作风”越充分,各阶层代表越敢于发言,相互之间的矛盾往往越明显。这里的矛盾表现在两个层面:一是各阶层间的利益冲突,政治性的如劳资之间、店员与店主之间,经济性的如房客与房东之间;二是政府贯彻中心工作与满足民众自身需求之间的矛盾,突出表现在征收工作、税收工作不断增加民众负担。
在各阶层的利益冲突中,政府反而担当起居中调节的角色。如在劳资矛盾中,政府在言论、道义上支持工人一方,针对资方的“错误”言论展开斗争,但在实际诉求层面,出于发展生产的需要,政府会抑制工人增加工资、禁止开除等诉求,甚至由政府出面提供失业救济以满足资方在一定条件下可开除工人的请求。在所谓“既团结又斗争”的原则下,工人需要学会既对资方的“错误”言论加以批评,又要对资方的接受批评表示欢迎,同时还得在争论时做到心平气和,避免态度过分激动。就此而言,代表会议提供的不单是一个各阶层、界别表达自身诉求的场所,也是一个听取其他阶层、界别表达的场所,并学会在争论、斗争与团结中获得超出自身利益视野的更宏观的眼光。这是一种对代表的政治教育,也是“人民”得以落实的基础。被树为典型的松江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总结报告就强调,会议“给参加会议的各界代表们一个最现实的教育”,特别是对于工农代表,他们“从这个会议的过程中进一步认识了自己的地位、力量与责任,开始具体了解各阶层团结的真正意义及其重要性,从而大大提高了自己的阶级觉悟”*上海《解放日报》社论:《从松江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得到些什么经验?》,《人民日报》1949年10月15日转载。。之前曾提到,中共进入城市之后需大力依靠工人阶级和工人阶级状况不理想的现实之间存在很大落差,解决这种反差的手段之一,以毛泽东的设想,就是要用民主的方法教育人民:“必须让他们参与政治活动,不是强迫他们做这样做那样,而是用民主的方法向他们进行教育和说服的工作。这种教育工作是人民内部的自我教育工作。”*《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册,第418页。
相比之下,在政府中心工作与群众需求之间孰轻孰重、孰先孰后以及如何吸纳民众意见减轻、合理分配负担等方面,政府必须发挥更主动的作用,制定更具有效性、为各方所接受的方案。在这方面,代表会议要发挥的是及时、准确地反映情况与实施监督和批评职能。像城市管理中至关重要且矛盾集中的税收问题就需经过代表会议的反复讨论和审议。北京市在第二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中一次通过了五种财税提案。在后来的工作报告中,彭真认为,北京的税本来不轻,但经过代表会议讨论之后就能顺利征收,而公债由于未能及时提交代表会议讨论,因此推销得费劲。不过,实际地说,税收方案是否能被接受,不完全取决于代表会议的讨论,更取决于制定过程中能否掌握各方情况、吸纳各方意见。北京市党组为准备税收提案事先进行了一系列工作,除做一般调查研究外,还辅以各种典型调查,举行一系列座谈会,派人到天津了解营利事业所得税和营业税情况,以资比较。草拟的征收办法草案与提案经党组会三次研讨和市委修改,并由市政府行政会议和第一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数次协议,最后才提交第二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由于准备充分,这些提案和办法在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上才得以顺利通过。然而,即便经过充分酝酿以及代表会议一致赞成,税收过重问题仍给工商业造成很大负担,“有卖出生产工具或房屋而缴税的;有为逃避税收、公债而抽资歇业或化为小户的;甚至有为逃避负担而弃铺逃跑的”。*《北京市重要文献选编(1950)》,中国档案出版社,2001年,第67、23、246页。为此,市党组又组织了详细调研,提出了调整意见。
上述情势说明,政府在制定政策方面掌握着绝对的主导权,代表会议相对只是在贯彻和执行的过程中发挥作用。当然,政府采取的政策通过代表会议加以充分解释,特别是就一些不得已的措施求得民众谅解,这本身也能起到实质性作用。如在松江县的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上,饶漱石就围绕合理负担问题进行了一系列解释,特别指出在群众尚未发动、区乡两级政权多未改造、新区工作干部少,以及对新区征收公粮和对城镇整理税收缺乏经验的现实条件下,新政权在进行第一次秋征时,只能暂时利用国民党时代各县赋册所载的赋亩或赋元,采取按户累进征收的办法。而对各城市和集镇税收的整理,除取消苛捐杂税与某些显然极不合理的税收外,也只能暂时按照国民党时代某些旧有税规税率,加以逐步改造和整理。这与当时仍需确保战争供给及为避免过急改革引起混乱的顾忌相关。当然,他也强调在暂时利用国民党旧有册赋和税规进行征收时要杜绝贪污自肥,在农村的征收则要辅以清查黑地、反对地主恶霸转嫁负担的斗争。*饶漱石:《关于减租减息合理负担与工商政策问题——在松江全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讲话》,《人民日报》1949年10月15日。
在征粮、税收这些实际负担没有减轻,甚至加重的情况下,如何使民众不因此加重疑虑乃至离心离德,代表会议所发挥的疏通作用显得至关重要。上情下达、下情上达固然不能马上解决所有问题,但无疑能起到疏导、凝聚人心的作用。毛泽东在七届三中全会上的讲话中着重谈到由于革命胜利、社会经济改组所引发的对立情绪以及在此状况下争取各方支持的急迫性:“由于社会经济改组和战争带来的工商业的某些破坏,许多人对我们不满。现在我们跟民族资产阶级的关系搞得很紧张,他们皇皇不可终日,很不满。失业的知识分子和失业的工人不满意我们,还有一批小手工业者也不满意我们。在大部分农村,由于还没有实行土地改革,又要收公粮,农民也有意见……为了孤立和打击当前的敌人,就要把人民中间不满意我们的人变成拥护我们……我们一定要做好工作,使工人、农民、小手工业者都拥护我们,使民族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中的绝大多数人不反对我们。”*《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册,第398页。
在民情多有不满的情况下,代表会议这一“民主”场合不单要起疏通、解释的作用,还要为各种批评意见提供出口,所以后来的各界人民代表会议越来越强调把“检讨工作和检查干部作风”作为一项固定议程,这也被认为是纠正主观主义和官僚主义的有效办法。本来民主体制的核心作用之一就是对权力的监督和制约,但这种制约能够常态而有效地实现,则需凭借一套行之有效的制度运行,而以鼓励群众批评的方式“检查干部作风”的主动权仍操之于执政者手中,这显然不是有保证的办法。
事实上,在推行民主实践的过程中,中共越来越将选举、分权等资产阶级民主的基本原则斥之为“形式主义”,越来越有意采取一套与之不同的方式。最典型的是,在早期人民代表会议的尝试中,无记名投票还是经常被采用的方式,但是到了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确立后,相关指导意见越来越强调用举手选举的方式取代投票选举,因为举手的方式降低了投票门槛,更简单便利,而投票选举会使很多不识字的人被排斥在外。然而,早在根据地时期,农村中就曾采取投豆的方式使文盲也可行使投票权力,可这现在也被认为是“形式主义”*“过去参议会选举的办法是人民投豆或者举手,投完以后就完事,那是形式主义,那样做法不对。”刘少奇:《关于人民代表大会问题》,《共和国走过的路——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49—1952)》,第97页。。这意味着中共对“形式民主”的理解本身亦趋于“形式”,即只看到它形式的一面,而看不到其支持民主实质内容的部分,更重要的是看不到一些繁琐程序因其形式化而具有的作用。换句话说,民主的许多程序固然由其形式化而显得繁琐、麻烦,乃至缩小了民主的适用范围,但它同时也是其能够独立运行的保障。相比之下,中共在打造其民主实践时一再强调方便、灵活、不拘形式、因地制宜,但恰好缺乏必要的分化与分立原则,也就缺乏独立性的体制保证。
结语:作为工作方法与作为根本制度的“各界人民代表会议”
从1949年12月开始,中央陆续制定了省、市、县、区各级的“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组织通则”,使得“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体制正式固定下来。从1950年到1953年,各地纷纷召开不同级别的各界人民代表会议。虽然中央对于召开代表会议的频率有所规定,但实际上很少有地区严格执行。而各地所召开的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数量、质量参差不齐。更重要的是,随着1949年后各级政府建制日渐完备,政府的主导能力日渐增强,使得代表会议中政府任务与群众要求孰轻孰重的天平更逐步倒向政府一边。
从1950年开始,诸如镇压反革命以及“三反”、“五反”、抗美援朝等一系列群众运动式的政治运动交替展开。在此过程中,由于在说服群众配合政府指令方面,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可以发挥独特效用,因此成为政府动员群众参加这些政治运动的重要工具。北京市在镇压反革命运动中,就是先在各界人民代表会议通过一个一般拥护中央镇压反革命条例的决议,然后再进行大逮捕*《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2册,第192页。。
一旦政府布置的中心工作占据了会议的主要日程,则群众关心的生活、生产问题势必受到挤压,且政治动员、报告增多,一般代表发言的机会、参与的主动性难免受到影响。1951年9月,《人民日报》曾刊发一系列文章,检讨基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召开过程中产生的种种偏差,其中河北定县地委副书记反映的情况颇具代表性。首先,各县的人民代表会议没有形成为基本制度,常常是在上级的督促下,单纯地为布置中心工作而临时仓促召开。其次,代表的产生有包办现象,分配代表名额没有一定原则标准,经常是在会前根据工作性质临时分配。在选举过程中,有的是由干部指定或先确定目标再经过组织保证,后经群众通过。代表会上的干部列席过多,干部民主作风差,使人民代表会变质为干部会、动员会、训练班。再次,会议单纯地布置中心工作,不讨论关于群众生活的提案。因此,群众就不再愿意提出提案。该县有70万人口,而第六次代表会议上的提案仅有13件。*范文兴(中共定县地委副书记):《我对定县专区各县人民代表会议的看法》,《人民日报》1951年9月2日。
事实上,很多地区都经历过提案锐减的阶段,这种情况说明如何使用民主工具对于大部分地方干部而言依然相当陌生。越是单纯将代表会议视为一种工作方法,以是否方便、适用要求它,反而越容易造成它的不稳定,如一位县长在检讨中所指出的那样:“对人民代表会议与人民代表大会是我们国家的基本制度、是人民民主政权的基本组织形式这一点认识不够明确。我们只是认为它是团结各阶层人民,发扬民主,推动工作的好方式。”*《为什么没有开好人民代表会议?——河北新乐县县长李纯良的检讨》,《人民日报》1951年9月7日。
新中国成立后,随着“民主建政”成为相对独立的政治目标,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制度化、正规化的诉求越来越凸显。1953年后,随着普选产生的人民代表大会开始筹备,各界人民代表会议渐渐退出历史舞台。那种融权力机关、政权机关、协议机关、统一战线组织等多重因素为一体的混合形态随之被分工更明确的各种机构代替。
相对之后更为完善、严密的人民代表大会体制,各界人民代表会议虽然带有过渡阶段的
历史痕迹和种种缺陷,但它因应现实状况的时效性恰好有益于我们贴切把握中共主导的民主实践的动机、意图与效能。事实上,从抗战中后期开始,随着创建“新中国”的意识越来越凸显,如何在中国发展出一种行之有效的民主政治,日益成为各党派、政治力量关注的焦点,也是争夺的焦点。中共在根据地推行的“三三制”、乡村选举等一系列尝试,为累积一种实用、有效且富于凝聚力的民主实践作出了有效摸索,而结合于生产、土地问题展开的群众运动则为在乡村社会实行民主革命开辟出道路。到解放战争后期,随着中共的力量从乡村转向城市、从占领转向接管,面对新的挑战与矛盾,中共又适时采用和推行“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制度作为这一阶段所强调的“实质民主”的对应性实践。这可以说是一个复合性体制:其运行,既依托于协商式民主的组织形式,又依靠“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其功能,既作为一种政府管理形式、诉诸“民主的回应性”来解决社会矛盾和民生需求,又须承担民主革命“团结人民”“教育人民”的任务;其性质,既是一种根本制度,又是一种工作方法。而这些不同的面相如何协调,其中蕴含哪些矛盾,其有效与失效与怎样的条件变化相关,尚需更深地回到具体而丰富的历史实践经验中加以考察与剖析。而把握这一历史转折时期中共在民主政治领域的实践方式与经验,无疑将有助于理解此后更长一段时期内中共运用和调动“民主”手段的逻辑、方式与效用等更深层次的历史问题。
(本文作者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北京 100732)
(责任编辑 吴志军)
The Establishment and Evolution of the System of the People’s Congress of All Circles before and after 1949
Cheng Kai
This paper attempts to sort out, on the eve of the founding of the new China, how the CPC found and established the system of the People’s Congress of All Circles, in the process of turning the country to the city, taking over to the occupying, and war to construction. This is a complex system, and its operation is based on the organization form of consultative democracy, and relies on the working method of “the mass line”. It functions as a form of government management to resort to the “response of democracy” to resolve social contradictions and people’s needs, and at the same time, it undertakes the task of “uniting the people” and “educating people” of the Democratic Revolution. Its nature is not only a fundamental system, but also a working method. Its process of generation and evolution can reflect the CPC’s understanding, demand and construction path of “democracy” in this stage.
D232;K271
A
1003-3815(2016)-11-0084-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