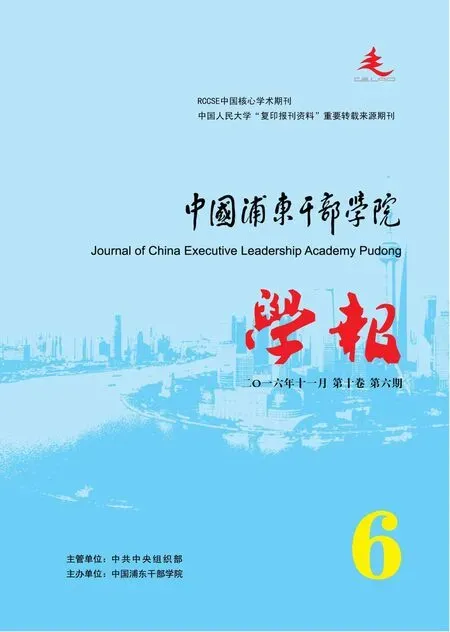保证改革发展正确方向的三次重大判断——学习习近平关于改革发展方向的论述
高建生
(中共山西省委党校,山西太原030006)
保证改革发展正确方向的三次重大判断——学习习近平关于改革发展方向的论述
高建生
(中共山西省委党校,山西太原030006)
党的十八大之后,习近平针对改革发展方向作出的三次重大判断,消解了围绕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关系、全面深化条件下改革开放的发展指向和结果评判问题上形成的认识困惑,为深刻认识关系改革发展性质、方向、目标的重大问题提供了科学方法,而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的五大发展理念与三次重大判断在内在关系上具有的吻合性、在实践要求上具有的一体性,决定了五大发展理念为把三次重大判断实践化提供了实现途径。
习近平;改革方向;三次重大判断
在当代中国社会30多年的改革发展中,关于改革发展方向问题的争持与疑虑,其实一直没有间歇过,只是争持与疑虑的方式、侧重不同而已。客观地说,在中国这样一个13亿人口的大国推进改革大业,对发展目标与方向的关注是非常正常的,因为在改革方向上的任何偏差,都可能“在根本性问题上出现颠覆性错误,一旦出现就无法挽回、无法弥补”。[1](P348)而面对这样的“根本性问题”,党的十八大之后,习近平同志作出过三次重大的判断,对保证改革发展的正确方向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
一、党的十八大之后习近平关于改革发展方向的三次重大判断
三次重大判断中的第一次,是党的十八大之后,习近平在中央举办的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十八大精神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中提出的关于“两个不能否定”的判断。
党的十八大之后,面对国内外对“举什么旗、走什么路”的极度关注,党中央通过不同的场合和方式,强调了将带领全国人民“紧紧围绕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奋力开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为广阔的发展前景”,[1](P6)对中国社会的发展问题、道路问题、发展方向问题作了明确回答。同时,党中央也敏锐地意识到,在改革进入深水区、发展面临多方面不确定因素的特定条件下,“旗帜”“道路”问题上存在的各种杂音,首先集中体现于对改革发展前后两个不同时期的判断与评价之上。有鉴于此,2013年1月5日,习近平同志在新进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候补委员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研讨班上发表的重要讲话中,对新中国成立后党领导的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的关系作出重大判断,明确提出,两个发展时期“不是彼此割裂的,更不是根本对立的。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1](P22-23)“两个不能否定”的重要判断,清楚地表明了党在涉及改革发展历史承续、发展性质、发展方向问题上的科学态度。
而具有深远意义的第二次重大判断,则直接关系到当代中国全面深化改革发展的目标选择。2014年,党中央在带领全国各族人民推进改革发展不断深入的过程中召开了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明确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三中全会关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深刻揭示,使“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目标要求更为具体,同时也表明了全面深化改革两个方面总目标在理论上的相互关联性、在实践上的相互促进性,任何厚此薄彼,甚至顾此失彼的认识与实践,都只能贻误改革的发展。基于这样的考虑,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全面深化改革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的讲话中,从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中两个方面要求内在统一性的意义上强调:“必须完整理解和把握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这是两句话组成的一个整体,即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1](P105)这里关于“两句话”的科学论述清楚地表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本身就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内在规定,其全部实践都服务和服从于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大方向,“我们的方向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1](P105)
引人注目的是,如果说30多年前,当改革开放的大幕徐徐拉开时,关于改革发展方向与目标问题曾经受到的广泛关注具有某种必然性的话,那么,当改革实践已经经历30多年的发展、当代中国经济社会业已发生极其深刻的变化之后,这样的关注继续存在,并以更为技术性、多样性的方式表现出来本身,则现实地反映出改革发展受内外环境影响所必然呈现出的复杂性,以及改革发展性质与方向对当代中国社会具有的深层次、决定性影响是何其关键。面对这样的复杂环境和关键性问题,2016年4月1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二十三次会议上,又一次对改革发展的方向、目标问题作出重大判断,提出了“改革既要往增添发展新动力方向前进,也要往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方向前进”[2]的“两个前进”的科学论断,对改革开放以来党中央关于改革发展性质、目标、依靠力量和评价标准等问题,在认识上实现了又一次的升华,也为全面深化改革中坚定把握前进与发展的正确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
方向问题至关重要,目标影响着改革的成败,这是不言而喻的。同时,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八大之后三年多的时间内,先后就改革发展方向作出的“两个不能否定”“两句话”和“两个前进”的三次重大判断,如果仅仅从一般性论述与强调的意义上加以理解,似乎是远远不够的。
二、三次重大判断消解了影响当代中国社会改革发展的三大困惑
关于改革发展性质、走向和对改革结果评判的困惑与争议,从改革起步时直到现在始终存在,邓小平关于“对改革开放,一开始就有不同意见,这是正常的”[3](P374)的判断,就是对这一事实的认定。而经历30多年改革发展之后,改革之于中国社会的每一个人说来,尽管已经不是陌生的话语,但越是随着改革发展的深入,这样的困惑甚至争论就越为明显。
首先是围绕新中国成立后党领导发展的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关系的认识形成的困惑。事实上,改革作为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本身就是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前提下,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修复功能,对束缚生产力发展的旧的机制体制的根本性变革。这就是说,新中国成立后党领导的社会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为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开始的改革开放奠定了制度与社会基础,改革发展是在这样的基础上对不适合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进行的调整。由此决定了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的关系,必然反映为前者是后者得以推进的制度前提,后者是对前者的完善与发展。这样一种非常清晰的关系,其实改革开放伊始,党中央阐述得十分清楚。邓小平当时就坚定地表示,改革开放前的发展为改革开放后的发展打下了基础,在他看来,“从许多方面来说,现在我们还是把毛泽东同志已经提出、但是没有做的事情做起来,把他反对错了的改正过来,把他没有做好的事情做好”。[4](P300)而为什么这样一个被党中央和党的领导人阐释得如此清楚的问题,却在现实生活中形成围绕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关系的认识困惑,其本质是有人力图借割裂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的联系,或者抹黑改革开放以来党和国家坚持的改革发展的正确方向,或者否认改革开放应当坚持社会主义的正确发展方向,二者都是对改革发展性质、方向与目标的质疑。
其次是围绕全面深化条件下改革开放的发展指向形成的困惑。党的十八大之后,党中央适应改革进入攻坚阶段、发展处于关键时期的实践要求,提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战略任务。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对全面深化改革的方向和目的作了明确揭示,这就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如此清晰、透彻的阐述,事实上把全面深化改革的性质与目标联系于一体,既阐释了它的基础所在、运行轨迹,也说明了它的发展方向、根本目的。但又是在一个本来不是问题的问题上发生了认识上的问题,这就是有人以选择性阐述的逻辑推断,断章取义地把全面深化改革的目标仅仅定位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含义上,而在涉及改革发展目标这样重大的问题上把“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大前提丢弃到了一旁不顾,由是在“两句话组成的一个整体”中只讲其中一句而忽略甚至否认另一句话,人为地造成了新的认识困惑。而之所以置国家性质和制度基础于不顾去谈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本质上还是对改革发展方向与目标的质疑。
第三个,是围绕改革开放发展进程与结果的认定与评判形成的困惑。改革开放的发展是以其实践结果为最终衡量尺度的。1992年,邓小平在著名的南方谈话中,对当时已经进行了十余年的改革实践,提出了判断是非得失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认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3](P372,373)邓小平当时的清醒判断,一方面固然是要求全党“不搞争论”,[3](P374)要把注意力集中于发展这个“第一要务”上;另一方面,实际上也反映出围绕改革发展出现认识困惑与“不同意见”的客观存在,后者既表现为对改革结果在发展性质上的不同认识,也表现为对改革进程中“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与“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孰先孰后次序选择的“不同意见”。可以说,类似的“不同意见”还有许多的版本和表述方式,但其本质,依然是对改革发展方向与目标的困惑与质疑。
面对事实上存在着的上述困惑,我们深入对习近平在党的十八大后就改革发展方向作出的三次重要判断加以分析,就很容易看出,三次重大判断消解了影响当代中国社会改革发展的三大困惑。
其一,“两个不能否定”从制度基础与制度完善的承接性上,揭示了当代中国社会改革发展的社会主义性质。这一重要判断,以全面统一的观点分析认识党领导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的相互联系和重大区别,表明了两个历史时期在坚持社会主义发展方向、基本制度、根本原则、奋斗目标基础上的一致性,区别了两个历史时期在坚持社会主义发展方向、目标、基本制度的思想指导、方针政策、实际工作上的探索进程以及不同时期实践探索在内外条件、实践基础等方面的差异性。在此基础上,这一重要判断更为突出地强调了必须把两个历史时期放到党领导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事业发展一脉相承的历史逻辑和实践进程中去观察、去把握,既注重前一时期为后一时期提供的重要思想、物质、制度基础和正反两方面实践探索的经验,又注重后一个时期对前一个时期价值精华、发展潜力、制度优势的挖掘、丰富和创新,从根本上廓清了由于割裂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联系而对改革发展性质产生的认识困惑,否定了抹黑改革开放以来党和国家坚持的改革发展正确方向的错误倾向,为新的历史起点上把握社会主义改革的正确方向提供了理论、实践和道义依据。
其二,“两句话”从发展结果与发展途径的统一性上,揭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这一重要判断,以目的与手段相统一的观点分析认识全面深化改革的发展,立足于经历30余年改革实践的当代中国社会现实,揭示了改革发展的进一步深入,只能是以“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重点的全面深化改革,而这样的重点,在实践引领层面上,与“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一起,构成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在“总目标”的层面,则完全服从和服务于“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这一根本出发点与落脚点。全面深化改革实践中这一发展结果与发展途径的内在统一关系,决定了无论是“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还是“治理能力”的“现代化”,都必须按照“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目标要求去推进,任何意义上的偏移,或者借口“现代化”兜售其他私货的做法都是错误的。这就在涉及全面深化改革方向与目标的根本性问题上,澄清了国内外一些人以“转向”“复制西方模式”的曲解诠释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的认识迷雾,为全面深化改革的发展提供了定盘星和压舱石。
其三,“两个前进”从发展动力与发展结果的吻合性上,揭示了社会主义改革的判断尺度与标准。这一重要判断,以改革实践要求与实践验证相一致的观点分析认识社会主义改革的缘由、进程与结果,通过“改革既要往增添发展新动力方向前进,也要往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方向前进”的定位,清晰地勾勒了当代中国的改革实践在不断增添社会发展新动力的过程中,始终坚持“新动力”缘于“社会公平正义”,也必然落脚于“社会公平正义”的大方向,形成了是否体现“增添发展新动力”和是否反映“社会公平正义”要求的改革验证标准。这就从社会主义改革坚持“增添发展新动力”和“社会公平正义”两个并行不悖的方向上,阐明了改革发展既要在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过程中,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使社会主义激发创造活力的制度潜力得到深度发掘;也要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保证广大群众在改革发展中有更多“获得感”,使社会主义维护公平正义的制度优势得到充分发挥。可以说,“两个前进”集改革发展方向、目标的全部要义于一体,不仅是对社会主义改革性质、目标的深刻揭示,同时也对那种或者对“增添发展新动力”和“社会公平正义”作主次关系注解,或者以先后次序曲解的认识作出了深刻的批判。
三、三次重大判断为深刻认识关系改革发展性质、方向、目标的重大问题提供了科学方法
关于改革发展性质、方向、目标问题的认识及其争论,尽管从改革实践起步时即已开始,在改革发展的过程中不断出现,有时甚至还非常激烈,面对这些认识与争论,党和国家也不断地表明了恪守社会主义原则、坚持正确方向的态度,但这都不能保证相关的认识与争论的止息,一些已经多时不见、甚至看上去似乎早已没有了市场的观点、看法,实际上也很难说不会在某些特定的条件下死灰复燃。从改革发展的现实实践看,在进入改革深水区和发展关键期的中国社会,这样的情形确实存在,关系改革发展性质、方向、目标的不少重大问题或者正在、或者试图影响人们对改革发展方向的认识与行动。所以,仅仅从某个单纯性问题回答的意义上认识与理解三次重大判断的意义是不够的,三次重大判断事实上为深刻认识关系改革发展性质、方向、目标的重大问题提供了科学方法。
方法之一:保证改革发展的正确方向,既要从改革发展的肇因上,也要从改革得以推进的条件上,认识理解改革发展性质、目标对改革实践具有的规定性。毫无疑问,促使30多年前中国社会作出改革选择的直接肇因,在于业已僵化的管理体制及其影响下濒临危机的经济局面,而非社会主义制度本身的失灵,由此决定了我们在改革发展的初始阶段,即以实现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与发展为改革目标,启动的是社会主义制度本身的自我修复功能。同时,对改革发展前后两个不同发展时期稍加分析即可看出,高度集中的管理体制、阶级斗争为纲的治国理念、平均主义的分配方式、封闭式的发展思路和无休止的政治运动等等,恰恰与改革发展前的发展时期如影随形,这很容易形成在制度与体制之间的混淆。而这种混淆,在改革发展以诸多实惠回报社会及其成员的初始阶段,人们往往容易厘清,而当改革步入攻坚阶段,深水区改革背景下诸多复杂的矛盾与问题与改革本身缠绕于一体,特别是“啃硬骨头”的改革遭遇某种进退维谷窘境时,“混淆”就会于有意无意间露头,企图弃体制而拿制度“开刀”的势力也就容易找到市场,尽管他们可能不会明目张胆地采用“改社会制度”的表达话语,这就是为什么在改革发展中关于改革前后两个不同时期的认识与争论不断出现的原因。事实上,导致中国社会改革的初始原因,既缘于旧体制对社会生产力形成的发展桎梏,改革本身是利用社会主义的自我修复功能,对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的调整,更缘于社会主义制度为社会主义制度自我修复功能发挥功效所提供的多重性条件。比如:社会主义具有的“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3](P377)新中国成立后20多年间奠定的经济与社会发展基础,20多年发展中形成的比较完备、独立的国民经济体系和从事各方面建设的人力资源,以及党领导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积累的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等。离开了这样的基础与条件,改革根本就不可能推进,改革命题本身的提出实际上也就成了问题。所以,如同坚持改革与坚持改革的正确方向是一个完整的统一体一样,改革发展的肇因与改革得以推进的条件也是不可分割的,这是分析认识改革发展性质、方向必须秉持的基本方法。
方法之二:保证改革发展的正确方向,既要从实践要求的确定上,也要从实践发展经验教训的总结上,认识理解改革发展性质、目标对改革发展具有的启迪性。改革发展的方向,无疑是改革本身的性质决定的。同时,作为推动改革发展主体的社会成员对改革发展正确方向的认可,更容易从改革实践发展经验教训的总结上获取启示。比如20世纪80年代末发生于我国社会的政治风波,随后在整个前苏联东欧地区出现的历史性剧变,以及当时在“华盛顿共识”影响下风靡全球的“私有化”浪潮及其给诸多发展中国家带来的发展悲剧等,显然对众多参与改革发展进程的社会成员以深刻的警示,其教育意义绝不亚于课堂、舆论、媒体的宣传。而仔细分析这些实践“案例”及其产生的经验教训就不难发现,其鲜明的一个特点,就是在谋划、设计和推进改革的发展时,改革的主导者全部的关注力(有意或无意的)都毫无例外地放诸“现代化”“转型发展”等亮丽的目标之上,而对实现“现代化”“转型发展”的制度性质、道路取向、本国国情限定,往往缺乏应有的坚持。而正是由于如是一种不顾性质、方向却盲目追求的所谓“现代化”“转型发展”,恰恰导致了不少国家的制度颠覆、政权易手和发展倒退。从这样的意义上,我们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是两句话组成的一个整体”的“两句话”的重要判断加以认识,就能够清醒地看出,改革在自身发展深入的过程中,肯定需要有具体的目标、重点与任务,需要有实现这些目标、重点与任务的操作性部署,但保证改革发展的基本性质与正确方向,始终是最具根本性的问题。如果把改革的具体目标、重点与任务当作替代改革发展性质、方向的东西,或者借口改革性质、方向之类的要求是业已说过而无需反复强调的“老生常谈”等,必然的结果就是由本末倒置造成的以末害本。可以说,由实践发展经验教训对改革发展形成的认识启迪,本身就具有方法论的价值。
方法之三:保证改革发展的正确方向,既要从现实实践的需要上,也要从过往历史的借鉴上,认识理解改革发展性质、目标对改革深入具有的重要性。改革是不断深入的过程,特别是在改革发展走出初始阶段之后,改革的尝试性、探索性特征极其突出,改革的艰巨性、复杂性异常明显。从世界范围内的改革实践,特别是原来与我国同为社会主义制度国家的前苏联东欧地区的改革实践看,改革初始时期发生改弦更张、变旗易帜的情形不是没有,但更多地发生在改革逐步深入的阶段。在这样的阶段,过往的历史发展提供给我们两条清晰的发展轨迹:一条是以前苏联东欧地区为代表的改革行进轨迹;另一条是以我国发展为代表的改革行进轨迹。前苏东地区改革走过的轨迹,是在改革开始深度推进之后,面对大量深层次的社会矛盾与问题,改革主导者把解决矛盾与问题的方向扭转到了向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和价值取向开刀的轨道上;我国改革走过的轨迹,尽管也出现过类似20世纪80年代末的政治风波,产生了围绕改革方向问题上的周折,但从改革发展大的进程上看,党和国家没有畏惧深水区和攻坚阶段改革发展面对着的大量矛盾与问题,始终坚持了围绕发展、完善社会基本制度基础上对具体体制机制的调整,并通过实践结果的事实导向,促进越来越多的社会成员对改革方向形成了最大程度的目标共识。两条不同发展轨迹在实践中形成的不同发展结果,特别是在世界范围内对“中国道路”“中国模式”“中国制度”抱有越来越强烈的关注,以及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本身也越来越“完全有信心为人类对更好社会制度的探索提供中国方案”[5]的现实状况,其实已经很明确地告诉我们坚持改革发展正确方向对改革深入具有何等的重要性,对于自觉抵制推中国发展至各种各样“邪路”“老路”上去的各类方剂和路线图具有何等的紧迫性。所以,党的十八大之后习近平关于改革发展方向的三次重大判断,从思想方法的意义上表明,分析、认识和把握改革发展方向的重要性,需要从现实实践的发展要求出发,但在改革深化使诸多未知因素存在于其中、探索任务比以往任何时候都突出的情况下,借鉴发展进程中过往实践积累的经验,往往能够对现实发展提供启示。
方法之四:既要从思想理论的坚持上,也要从思想认识可能遇到的干扰上,认识理解改革发展性质、目标对改革理念具有的影响性。党的十八大之后,习近平关于改革发展方向的三次重大判断,都有很强的针对性。这里的针对性,既包括对社会主义改革方向在思想理论和原则要求上的始终坚持,更多的则在于经历30多年改革发展之后,围绕改革发展方向的偏颇理念和错误思想,与改革发展进程并没有作别。30多年前,当改革开放刚刚开始时,改革发展方向问题上要么否认改革的社会主义性质,要么否认改革发展应当有正确方向的认识,一直是改革实践着力防止的两方面错误倾向。经历30多年的发展之后,简单地重复上述观点的倾向可能是不多见了,但以各执一端的两极化思维评判和力图影响改革发展的认识并没有失去市场。比如现实实践中面对当代中国社会执政党执政基础的不断巩固、中国国家实力的显著增强、全民族凝聚力的空前提升和中国社会进入近代社会发展的最好时期这样的现实,有人就是想把取得这一切成就的原因归结于“西方药方”“市场道路”和“西方经验”;有人面对我们的发展成就,就是在无法掩饰的某种妒忌心理驱使下,不惜以诋毁、歪曲、放大社会生活中的某些阴影等方式对改革发展方向予以攻击;也有人不是从中国改革的成功中寻找政治制度的优势,反而以西方某些价值观念为圭臬,试图导引中国朝着他们所希望的目标前行;还有人不愿意承认市场取向改革对中国发展产生的作用,总喜欢把改革与一些发展难题捆绑于一体,或者通过曲解现实社会发展的困难和问题,试图回到封闭僵化的老路上去,或者在持续性唱衰中国发展的同时,有意识地以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诠释一些问题的发生原因,不断地“预言”中国会在一些“根本性问题”上出现“变化”。所以,围绕改革发展方向上的思想认识干扰,会不断变换形式和花样出现,如何科学、清醒地分析、思考,揭示其危害所在,防止其在实践中找到呼应,是认识把握改革发展方向不能忽略的重要思想与工作方法。
四、五大发展理念为把三次重大判断实践化提供了实现途径
理论判断的科学性,在于实践的检验,也在于对实践具有的指导性。党的十八大之后,习近平关于改革发展方向的三次重大判断告诉我们,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建立、建设和逐步完善,是一个有机的过程,改革发展就是在推进这一过程的顺利发展。这就意味着,改革发展的方向问题至关重要,偏离公平正义、共同富裕的“邪路”和固步自封、僵化保守的“老路”都是不能被接受的。这是三次重大判断科学揭示改革发展性质、目标留给我们的基本结论。
从这样的意义上说,在新的历史起点上,面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三次重大判断对改革发展经验的总结,更突出的意义应当放到指导现实实践发展、保证全面深化改革发展正确方向的意义上去思考。换言之,在改革进入攻坚阶段、发展处于关键时期的条件下,特别是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实践带来一系列新课题、新要求的情况下,如何破解经济发展动力和后劲不足的问题,如何完成产业结构优化、提升创新能力和增强发展持续力的问题,如何深化体制机制改革、促进新的动力、新的活力不断释放,以及如何在人口红利逐渐消失、环境约束日益增强、传统优势明显削弱,发展不全面、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日渐突出的环境中战胜来自各方面的风险挑战,就需要更加提高“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和“往增添发展新动力方向前进”的自觉性;如何化解快速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发展失衡、贫富差距等问题,如何铲除贪污腐败、权力任性和道德失范等毒素,如何走出“只要解决了发展问题,其他的一切问题都会迎刃而解”的迷思,以及如何在教育、就业、住房、医疗、社会保障、司法案件、民主参与等问题上体现社会的公平正义,就需要更加增强“往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方向前进”“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自信心。
基于如是认识、分析、思考三次重大判断在改革发展中的实践路径,非常清楚的结论就是: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的推进创新发展、协调发展、开放发展、绿色发展、共享发展五大发展新理念,与党的十八大之后习近平关于改革发展方向的三次重大判断在内在关系上具有高度的吻合性,在实践要求上具有鲜明的一体性,这就决定了在当代中国社会,坚持三次重大判断对改革发展要求的目标与方向,就必须贯彻五大发展理念,五大发展理念为把三次重大判断实践化提供了实现途径。
从改革发展前后的承续关系上看,五大发展理念提供了科学把握“两个不能否定”重要判断在现实实践中的科学思想指导。当代中国社会的改革发展,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也非哪个人主观臆想出来的,其源于时代的发展、实践的要求,也是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的必然结果,由此在改革发展前后两个不同时期表现出明确的发展承续关系。同时,如何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保证改革发展在逐步深入的过程中,延伸并扩张这样的承续关系,直接关系到改革的进程与改革的方向。五大发展理念基于这样的发展背景,一方面,通过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共享发展等实践要求,把新中国成立之后20多年社会主义建设中强调集体主义、注重公平分配、体现共建共享的制度功能,在新的历史发展起点上赋予更具时代色彩的标志,由此从改革发展的制度属性上为改革发展保持正确方向提供保障。另一方面,通过创新发展、开放发展等实践要求,把改革开放30多年实践进程中浸淫的改革、创新、开放精神,注入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完善与发展实践中,由此从改革发展的强大活力中为社会主义制度不断增添时代养分。可以说,“两个不能否定”对改革发展前后两个时期明确的辩证统一关系,在五大发展理念中得到了充分的反映。
从改革发展不断深入的要求上看,五大发展理念找到了改革发展要“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和“往增添发展新动力方向前进”的实践路径。无论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还是“往增添发展新动力方向前进”,改革发展就是要朝着消除体制障碍、激发发展活力和提高发展质量的目标推进。而从影响改革发展的现实原因分析,五大发展理念是破解发展难题、增强发展动力、厚植发展优势的科学理念,它集中反映了党对我国发展规律的新认识,特别是创新、绿色、开放发展,是改革步入攻坚期、经济进入新常态的条件下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所在,是“十三五”乃至更长时期我国“增添发展新动力”“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必须明确的思路、重点、任务和切入点。按照五大发展理念的要求促进发展,通过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科学化、民主化和法治化建设,通过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减少无效和低端供给,扩大有效和中高端供给,实现由传统治理模式向现代治理方式的转变,由低水平供需平衡向高水平供需平衡跃升,为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不断发展进步提供源源不断的内生动力,更好满足广大人民日益增长、不断升级和个性化的发展需求,更充分地体现社会主义制度具有的发展活力,就一定能够实现改革发展“往增添发展新动力方向前进”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目标。
从改革发展性质要求上看,五大发展理念明确了改革发展“往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方向前进”与“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目标定位。五大发展理念是顺应时代要求、符合我国国情、反映人民意愿的科学理念,它系统概括了党对人民群众新期待的新回应,特别是协调、共享发展,在攻坚期改革发展面对多种利益关系调整、利益格局重组和利益矛盾突出的背景下,不仅揭示了改革的动力源泉是广大群众,改革发展成果的享有必须体现公平正义、防止被少数利益群体和少数人所独享,而且提供了发展是否为了人民、依靠人民,发展成果是否由人民共享的判断依据。毫无疑问,经历30多年改革开放的发展,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为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和有利条件。在这样的条件下,努力让最广大人民群众体会到社会主义制度完善与发展的成果,把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体现在改革的各个环节,坚持全民共享、全面共享、共建共享、渐进共享的有机统一,科学统筹各项改革任务,不断做大“蛋糕”,同时分好“蛋糕”,做到老百姓关心什么、期盼什么,改革就抓住什么、推进什么;什么因素影响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的发挥,就改革什么因素、消除什么因素,通过改革给人民群众带来更多获得感和幸福感,由此就一定能够实现改革发展“往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方向前进”与“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目标。
总之,推进五大发展理念实践化的过程,就是把三次重大判断实践化的过程;推进五大发展理念实践不断取得新的成果,就是三次重大判断实践化不断取得的成果,这是新的历史起点上我们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所应当具有的认识。
[1]习近平谈治国理政[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
[2]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二十三次会议强调改革既要往增添发展新动力方向前进也要往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方向前进[N].人民日报,2016-04-19.
[3]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4]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5]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6-07-02.
[责任编辑 郭彦英]
Three Important Decisions of Upholding the Direction of the Reform——Xi Jinping’s Statement of Upholding the Direction of the Reform
GAO Jian-sheng
(Shanxi Provincial Committee Party School of CPC,Taiyuan 030006,Shanxi,China)
Since the 18th National Congress,Xi Jinping’s three important decisions of upholding the direction of reform solved problems of the confusion abou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wo historical periods before and after the reform and opening-up.Xi also made a clarification of the direction and achievement of the deeper-level reform.Xi’s thought provided a scientific way of understanding the essence,direction,goals and other critical issues of the reform.Xi’s three important decisions have an internal connection with the“Five Development Concepts”proposed at the 18th National Congress.The internal coherence and consistency between two theories showed that the“Five Development Concepts”just paved the way for carrying out strategies of upholding the reform’s direction.
Xi Jinping;the direction of the reform;three important decisions
D61
A
1674-0955(2016)06-0005-08
2016-07-23
高建生(1955-),男,山西祁县人,中共山西省委党校原副校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山西省社会科学联合会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