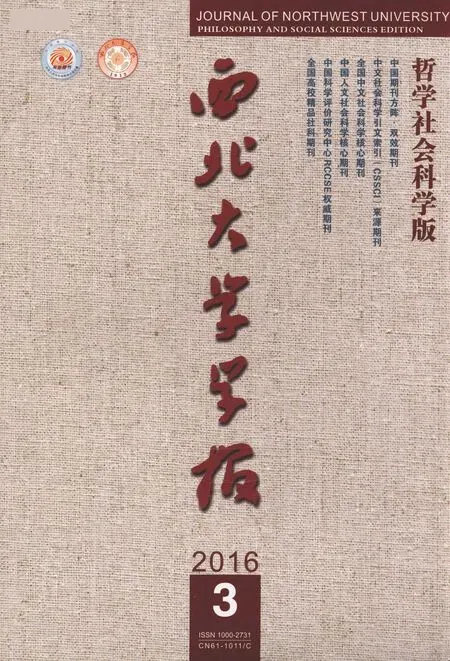《圆觉经》的真伪之争新辨
杨维中
(南京大学 中美文化研究中心、哲学系,江苏 南京 210023)
《圆觉经》的真伪之争新辨
杨维中
(南京大学 中美文化研究中心、哲学系,江苏 南京210023)
摘要:《圆觉经》的翻译是由个别僧人自发组织的“民间译场”完成的。完成之后,未履行向朝廷申报入藏程序,也未编订记载此经翻译过程的经录,或者可能编订但流传不广。古代佛教史家依据言必有据的原则书写,将有些许矛盾的传言都记录在案。其后,宗密访得流通于教界的《圆觉经》抄本并且多方收集当时的注疏,据此编撰《圆觉经大疏钞》等著作。此经逐渐在教界流通,对唐中后期的中国佛教产生了重大影响。智昇、宗密仅仅怀疑此经翻译过程记载的不完全或者舛误,从未曾怀疑《圆觉经》的“真经”身份。当代学者以古代文献记载分歧为由,以自己所认定的佛教某些派系的思想为准,将其判为“伪经”,是缺乏说服力的。
关键词:圆觉经;汉译本;宗密;真伪
《圆觉经》尽管在唐代方才流通,却颇得僧俗喜爱,在中国佛教很有影响力。但近代以来,此经却颇受质疑,一些学者将其判定为“伪经”,甚至有学者言之凿凿地指出此经是宗密伪造的。如吕瀓认为:“《圆觉经》本是由《起信论》经《楞严经》而发展出来的,它们的议论基本上一样,只不过《起信》还是一种论,现在以经的形式出现显得更有权威而己。”[1](P203)这样的论调,目前仍然有不少学者认同。但笔者以为,《圆觉经》的“疑伪”缘由在于流传至今关于此经翻译的时间、地点等事项的记载存在不同说法而已。那些判定《圆觉经》为中土撰著的学者,其实根本拿不出确凿的证据,至多只是猜疑而已。
一、经录所载《圆觉经》的翻译过程
最早记录《圆觉经》翻译过程的是智昇。他在《开元释教录》卷九中记载:
《大方广圆觉修多罗了义经》一卷,右一部一卷其本见在。
沙门佛陀多罗,唐云“觉救”,北印度罽宾人也。于东都白马寺,译《圆觉了义经》一部。此经近出,不委何年。且弘道为怀,务甄诈妄。但真诠不谬,岂假具知年月耶?[2](P564下-565上)
智昇在《续古今译经图记》卷一、圆照在《贞元新定释教目录》卷十二都照抄了上引表述。直至北宋赞宁撰写《宋高僧传·觉救传》时也没有多少新材料补充:“释佛陀多罗,华言觉救,北天竺罽宾人也。赍多罗夹,誓化支那。止洛阳白马寺,译出《大方广圆觉了义经》。此经近译,不委何年。且隆道为怀,务甄诈妄。但真诠不谬,岂假具知年月耶?救之行迹,莫究其终。大和中,圭峰密公著《疏》判解经本一卷,后分二卷成部。续又为《钞》,演畅幽邃。今东京、太原、三蜀盛行讲演焉。”[3](P717下)赞宁仅仅增加了宗密为《圆觉经》作《疏》的记载,而在照抄智昇的几句话时,甚至连语气都未改,特别是“此经近译”一句,殊觉不妥。
正是由于可以暂称为“原始记载”的智昇的《开元释教录》没有说出《圆觉经》翻译的准确时间,同时《圆觉经》的译主身世也不详,因此后世就有了不同的说法,这恰好给近代欲将其认定为伪经的学者提供了口实。
二、宗密有关《圆觉经》翻译的记载
宗密不辞辛苦地收集有关《圆觉经》的章疏,最终获得四种前人所作的《圆觉经》注疏。他自叙其经过说:
宗密为沙弥时,于彼州,因赴斋请,到府吏任灌家。行经之次,把著此《圆觉》之卷,读之两三纸,已来不觉身心喜跃,无可比喻。自此耽玩,乃至如今。不知前世曾习,不知有何因缘,但觉耽乐彻于心髓。访寻章疏,及诸讲说匠伯,数年不倦。前后遇上都报国寺惟慤法师《疏》一卷,先天寺悟实禅师《疏》两卷,荐福寺坚志法师《疏》四卷,北都藏海寺道诠法师《疏》三卷。皆反复研味,难互有得失,皆未尽经之宗趣分齐。[4](P478上)
从上文可知,宗密寻找到了四种注疏:第一种是报国寺惟慤法师《疏》一卷,第二种是先天寺悟实禅师《疏》两卷,第三种是荐福寺坚志法师《疏》四卷,第四种是北都藏海寺道诠法师《疏》三卷。唐代“北都”也称为“北京”,当时习称的晋阳,就是现在的太原。上述四位为《圆觉经》撰写注疏的僧人,只有报国寺惟慤法师在《宋高僧传》卷六中有本传,不过非常简短,主要记载其撰写《楞严经疏》的经过,大概是赞宁仅仅能够收集到当时仍然流通的《楞严经疏》中的一些记载。在同书卷四,宗密又补充了前三位疏主的简况,其文曰:
惟慤者,是《佛顶疏》主。悟实者,少小出家,曾禀荷泽之教。高节志道,戒行冰洁,久在东都,恩命追入内,住先天寺。八十六岁方终,焚得舍利数百粒。坚志者,实之弟子。[4](P537下)
关于惟慤的说法与其他资料记载一致。而悟实、坚志则为荷泽神会传人,二僧为师徒关系,宗密在之后的文字中,对坚志等人的疏文作了批评。
关于《圆觉经》的翻译过程,在早于《圆觉经大疏钞》的《圆觉经大疏》中,宗密综合几种资料进行了如下记载:
九、叙昔翻传者。《开元释教目录》云:“沙门佛陀多罗,唐言觉救,北印度罽宾人也,于东都白马寺译。”不载年月。《续古今译经图记》亦同此文。北都藏海寺道诠法师《疏》又云:“羯湿弥罗三藏法师佛陀多罗,长寿二年龙集癸巳,持于梵本,方至神都,于白马寺翻译,四月八日毕。其度语、笔受、证义诸德,具如别录。”不知此说,本约何文?素承此人,学广道高,不合孟浪。或应国名无别,但梵音之殊。待更根寻,续当记载。[5](P335上)
根据宗密这一叙述,道诠法师在其注疏中指出《圆觉经》是天竺僧人佛陀多罗于长寿二年(693)在洛阳白马寺翻译出来的,完成时间为当年的四月八日。宗密又说:“坚志法师《疏》说译主年月,并与藏海疏同。唯云‘天竺三藏羯湿弥罗’为异耳。”[4](P537下)根据现代学者考证,“羯湿弥罗”与“罽宾”在唐代时都是克什米尔的异名。可见几种《圆觉经》经疏的记载是一致的。
宗密后来在《圆觉经大疏钞》卷四中,对上述文字进行若干疏解,主要有以下两点:
第一,解释了“龙集”含义。宗密说:“言‘龙集’者,有释云:‘高宗大帝,当其年龙飞,以王天下。’此说恐谬。曾见有处说,长寿年是则天之代。然今亦未委其指的也,待更寻检。”[4](P537中-下)宗密的这一解释,暴露了其对当时纪年习惯的陌生,增加了近代学人的疑惑。其实,“龙集”犹言“岁次”,“龙”指岁星,“集”的含义是到达,即“次于”的意思,是古人以岁星纪年的惯常表述,与一般常见的“岁在某某年”意思相同。而宗密看到的经疏解释恐怕是误记传言,而高宗朝影响较大的飞龙显现事件发生在显庆六年(661)二月,《旧唐书·高宗本纪》载:“二月乙未,以益、绵等州皆言龙见,改元。曲赦洛州。龙朔元年三月丙申朔,改元。”[6](P81)
第二,对道诠等著述者所述“其度语、笔受、证义诸德具如别录”之中的“别录”,宗密进行了补充性解释:“《疏》‘具如别录’者,复不知是何图录?悉待寻勘。有释云:‘证义大德是京兆皇甫氏范氏沙门复礼、怀素。’又指度语、笔授云:‘在白马寺《译经图记》。’此等悉难信用。谓证义、笔授等,何得半在此记,半在彼《图》。乍可不知,不得妄生异说。”[4](P537下)宗密在此提供了一个极其重要的信息,即有一本被称为《译经图记》的书,书中记录了翻译《圆觉经》各类人员的情况。但是,由于宗密对自己收集的几种粗糙经疏极度不满,因此,不信任这种记载。
经过笔者考证,上文所说的承担《圆觉经》证义的正是复礼,他是唐高宗、武周朝的“译经大德”,被玄奘弟子惠立称赞为“译主”。
根据有关典籍记载,复礼参与翻译的日程如下:
其一,自高宗永隆元年(680)至天后垂拱末年(689),参与日照译场,于两京东京太原寺及西京弘福寺,助其译出经典18部合34卷。
其二,自永昌元年(689)至天授二年(691),参与提云般若译场,助其译出佛教经典6部合7卷。
其三,自武周证圣元年(695)至久视元年(700),参与实叉难陀译场,助其译出佛教经典凡19部合107卷。
其四,自久视元年(700)至睿宗景云二年(711),参与义净译场,助其译出佛教经典56部合230卷。
作为唐高宗、武则天任命的“译经大德”,自高宗仪凤元年(676)至睿宗景云二年(711)的35年间,复礼参加了当时大多数朝廷“敕命”的翻译活动。但是,仔细考辨智昇《开元释教录》和《续古今译经图纪》的相关记载,我们发现,唯独缺少长寿二年(693)至证圣元年(695)三年之间复礼的参译记录。而在这三年间,东都洛阳有如下三起翻译佛典活动。
其一,宝思惟译场。《续古今译经图纪》卷一记载:“沙门阿儞真那,唐云宝思惟,北印度迦湿蜜罗国人。刹帝利种,幼而舍家,禅诵为业。进具之后,专精律品,复慧解超群,学兼真俗。以长寿二年届于洛都,勅于天宫寺安置。即以天后长寿二年癸巳,至中宗神龙二年景午,于授记、天宫、福先等寺,译《不空羂索陀罗尼自在王咒经》一部(三卷)、《浴像功德经》一卷、《校量数珠功德经》一卷、《观世音菩萨如意摩尼陀罗尼经》一卷、《文殊师利根本一字陀罗尼经》一卷、《大陀罗尼末法中一字心咒经》《随求即得大自在陀罗尼神咒经》,凡七部合九卷。罽宾沙门尸利难陀译,沙门慧智等同证梵文,婆罗门李无谄译语,沙门德感、直中书李无碍等笔受。”[7](P369下-370上)这一译场是从武周长寿二年开始的,由朝廷敕命成立。
其二,慧智译场。《续古今译经图纪》卷一记载:“沙门释慧智,父印度人也,婆罗门种,因使游此而生于智。少而精锐,善梵书语。三藏地婆诃罗、提云若那、宝思惟等,所有翻译皆召智为证,兼令度语。智以天后长寿二年癸巳,于东都佛授记寺自译《赞观世音菩萨颂》一卷。”[7](P369中)这一译场也是从武周长寿二年开始的,也由朝廷敕命成立。
其三,菩提流志译场。《续古今译经图纪》卷一记载:“(沙门菩提流志)暨天后御极,方赴帝京。以长寿二年癸巳创达都邑,即以其年于佛授记寺译《宝雨经一部》十卷,中印度王使沙门梵摩同宣梵本。又于大周东寺及佛授记寺译《文殊师利所说不思议佛境界经》……已上二十部合三十卷,沙门行感等同译,沙门战陀、婆罗门李无谄译语,沙门慧智证译语,沙门处一等笔受,沙门思玄等缀文,沙门圆测、神英等证义,司宾寺丞孙辟监译。后至和帝龙兴神龙二年丙午随驾归京,勅于西崇福寺安置译《大宝积经》一部一百二十卷,……暨乎睿宗先天二年癸丑方始毕席。……逮睿宗嗣历,复于北苑白莲花亭及大内甘露等殿别开会首,亦亲笔受。并沙门思忠及东印度大首领伊舍罗、直中书度颇具等译梵文,北印度沙门达摩、南印度沙门波若丘多等证梵义,沙门慧觉、宗一、普敬、履方等笔受,沙门胜庄、法藏、尘外、无著等证义,沙门复礼、神目柬、云观、道本等次文”[7](P371上-下)。根据这一记载,复礼未参加菩提流志第一阶段即从长寿二年开始直至武周末年的翻译活动,而参加了第二阶段即神龙二年(705)至先天二年(713)的翻译活动。
综上所述,长寿二年,武周朝廷下敕在洛阳设立了三个译场,而一直参与各类译场翻译的“译主”(唐慧立称赞复礼时所说)复礼却都没有参加,这多少显得不合乎常规。从这个角度考虑,上述宗密所转引的《圆觉经疏》所说佛陀多罗译场的“证义大德”有可能是复礼。不过,笔者尚未查到怀素参与译场的材料,他是以律学见长的,早年拜玄奘为师,应该也参加过翻译。
此外,宗密在《圆觉经大疏钞》卷四中又补充了一条材料:
余又于丰德寺难经中见一本《圆觉经》,年多虫食,悉已破烂。经末两三纸才可识辨,后云:“贞观二十一年岁次丁未七月乙酉朔十五日己亥,在潭州宝云道场译了。翻语沙门罗睺昙揵,执笔弟子姜道俗,证义大德智晞、注纮、慧今、宝证、道脉。”然未详真虚。或恐前已曾译,但缘不能闻奏,故滞于南方,不入此中之藏。不然者,即是诈谬也。[4](P537下)
上述记载中,丰德寺在长安附近的终南山,道宣在未被朝廷征调到西明寺之前,就在此寺研究弘扬律学。这座寺院在唐中期以前非常活跃。寺院藏有许多佛典抄本,有一些是其他寺院的僧人从别处带来置于此寺的。宗密看到的这本《圆觉经》题记所写,其他内容已经无法考实,但经过笔者核对,其干支纪年以及纪日都是正确的。这至少说明,这一题记形成很早,并非接近宗密所处时段的人所写。宗密撰述这些著作在长庆二年(823)、三年(824),距贞观二十一年(647)长达176年,假设此经本破损之前已经存在流通五十年,也能说明这一题记中的说法其来有自,否则的话就是专业作伪者所为。一个直接的反证就是上文所辨析的“龙集”,不但对宗密收集的几种经疏作了错误解释,就连宗密自己也没有搞清楚。从这个角度说,《圆觉经》在贞观年间已经有一个译本是有可能的。
此外,北宋时期编写的《佛祖统纪》卷三十九又有一说法:唐高宗永徽六年(655),“罽宾国佛陀多罗,于白马寺译《大方广圆觉修罗了义经》一卷”[8](P367上)。这一记载一是晚出,二是没有说明任何依据,显系误传或误置。
三、《圆觉经》“疑伪说”驳难
《圆觉经》在近代被当作“伪经”,完全是由于对古代典籍对其翻译过程记载的理解分歧所引起的。之所以会产生这种现象,笔者认为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首先在于此经的翻译是在国家出面组织译场译经非常普遍的情况下,由个别僧人自发组织的“民间译场”完成的。完成之后,又未履行向朝廷申报入藏程序。其次,此经翻译出来之后未曾同时编订记载此经翻译过程的经录,或者是编定但流通不广,且未能被智昇等编写者搜集到。于是,佛教史家依据言必有据的原则书写,便形成了上引智昇所作的最初著录。其后,宗密访得流通于教界的《圆觉经》抄本并且多方收集当时的注疏,编写出几种优秀的注疏,此经便逐渐在佛教界流通,不久便风靡佛教界,对唐代中期之后的中国佛教产生了重大影响。
近代以来日本和中国的佛学研究,最主要的特色就在于引进了西方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和诠释方式。佛学研究中,对于古人“疑伪”标准的现代解释以及“疑伪”范围无限扩大,制造出了一个又一个佛教学术“问题”。对中土所流行的一些重要经典,如《大乘起信论》《楞严经》《圆觉经》《药师经》《心经》等的怀疑以及由此所引发的如来藏思想批判,都是这一方法的必然结果。近代以来针对如来藏经典的反思或“批判”,在方法上表现为“文献考据”与“义理辨析”的交替使用。一般而言,文献考据着力于从古代史籍,特别是经录的记载中,寻找文献中的混乱和漏洞,然后依据这样的原则得出“伪经”或“伪论”的结论。大凡记载有混乱者,肯定是其事情本身就不清不楚,基本上是虚构的“翻译事件”;凡是说法有漏洞者,都是有意识的“作伪者”。因为事情本身是虚构的,因而关于此“事”的言说,则肯定只能走“作伪”的道路,而大凡“作伪”都是内心发虚而欲盖弥彰,因此,今人通过文献的对勘,即可发现“作伪”者欲掩盖然不能取得全功而遗留下来的蛛丝马迹。而“义理辨析”则往往以佛教发展中某一些学派的特定学说为参照,凡是符合者就是“真佛教”“真经论”,凡是不符合者则是“伪经论”“非佛教”。
抽象地说,这两种方法是很合理的,符合现代学术界所盛行的“理性思维”或者“科学方法”的要求。但是,当研究者将这些方法应用于具体的佛教史或佛学史研究之中时,其局限性便立刻显露无遗。
以“文献考据”方法言之,最大的弊端是以如此整齐划一的标准严格甚至难免机械地比对评判历史文献中所显现出来的“漏洞”或“混乱”时,往往有意无意地忽略了这些“混乱”“漏洞”形成背后曾存在的各种各样复杂的“客观”原因。或者由于资料匮乏轻信“道听途说”而部分致误,但被当代学者抓住漏洞,强调或者扩大“伪妄”的比例,难免“诬枉”古人为有意的“作伪者”,由此直接宣判这些辛苦记载历史的人是“道德败坏者”。以“义理辨析”方法言之,最大的弊端是不能克服“学派偏见”,并且将“真佛教”仅仅局限于自己所认可的“一隅”,有意无意地忽略佛教实际上是一个历史的存在,不存在固定不变的面目。佛教特别突出的“应机说法”作派所形成的众说并陈,更使所谓“真佛教”的提法一定是现代学者以己宗己意纯化的结果。一言以蔽之,在什么是“真佛教”难以达成共识的情况下,任何学者,哪怕是佛学大师,仅仅凭借“义理辨析”便想将某一部经论宣布为“伪经论”,是难于服众的。
从上述古人的相关说法可知,智昇、宗密都仅仅怀疑关于此经翻译过程记载的不完全或者舛误,从来未曾怀疑《圆觉经》的“真经”身份。如唐宗密在《圆觉经大疏抄》卷四之上对智昇的说法作了评论:“余谓但云‘不知年月’即得,何必加此数言?”[4](P537中)宗密认为智昇后面几句话是画蛇添足,而近代以来力主其“伪”的学者将其当作是智昇的委婉说法,他们认为智昇实际等于说此经是“伪经”。在此,我们明确指出,智昇所言正如宗密所评论,有画蛇添足的嫌疑,但也是中国古代史学传统的要求所致。但是,今人断章取义的引申性解释,有以己意强加于智昇的嫌疑。智昇明明说译出年月不详,不影响此经为真经,而现代学者非要说这是智昇有意“曲说”。这是当代学者在考辨古代佛教译籍之时常常出现的方法论失当的表现,喜欢“疑古”者往往将经录中“疑惑”部分与“伪经”混为一谈,一旦对于译时、译地、译者以及流通过程等环节的记载发生一处或几处分歧,便决然将其统统当作“伪经”。对《圆觉经》的“伪经”判定也不出这一原因。
参考文献:
[1] 吕瀓.中国佛学源流略讲[M].北京:中华书局,1979.
[2] 释智昇.开元释教录:卷9[M].《大正藏》卷55.
[3] 释赞宁.宋高僧传:卷2[M].《大正藏》卷50.
[4] 释宗密.圆觉经大疏释义钞:卷1之下[M].《新纂卍续藏》第9册.
[5] 释宗密.圆觉经大疏:上卷之2[M].《新纂卍续藏》第9册.
[6] 刘昫等.旧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
[7] 释智昇.续古今译经图纪:卷1[M].《大正藏》卷55.
[8] 释志磐.佛祖统纪:卷39[M].《大正藏》卷49.
[责任编辑刘炜评]
The New Analysis on the Authenticity of theSutraofPerfectEnlightenment
YANG Wei-zhong
(CenterforChineseandAmericanStudies,DepartmentofPhilosophy,NanjingUniversity,Nanjing210023,China)
Abstract:The Sutra of Perfect Enlightenment was translated under the common circumstance that the country came to organize and several monks then completed by organizing spontaneously in the form of “folk translation workplace”. But after completing, the monks didn′t implement the procedure to declare the translation into Buddhist Scriptures. Also, they didn′t compile and revise the record of the translation process, or they did it but unfortunately, the translation scripture couldn′t be collected by Zhi Sheng or someone else. On the basis of “writing with reason” principle, the ancient Buddhist historians recorded the words which showed the reciprocal contradiction of the translation. After that, Zong Mi got the writing scripture of the Sutra of Perfect Enlightenment which was circulated in the Buddhist area and he also collected the exegesis of the scripture. Then, he came out with the book A Complete Commentary on Sutra of Perfect Enlightenment and some other books. Being published, the book was circulated gradually in the Buddhist area and it laid great emphasis on the Chinese Buddhism in the mid-Tang dynasty. Zhi Sheng and Zong Mi simply doubted the insufficiency and errors of the record of the translation process but never doubted the authenticity of the Sutra of Perfect Enlightenment. The modern scholars have excused the divergence of the ancient documents and standardized themselves in the consideration of Buddhist factions, and then came out with the conclusion that the Sutra of Perfect Enlightenment was a “fake scripture”. This result lacks persuasion.
Key words:Sutra of Perfect Enlightenment; Chinese translation scriptures; Zong Mi; authenticity
收稿日期:2015-10-20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12BZJ004);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13AZD030)
作者简介:杨维中,男,陕西千阳人,南京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从事中国佛学、佛教史研究。
中图分类号:K203;B949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152/j.cnki.xdxbsk.2016-03-006
【中国思想文化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