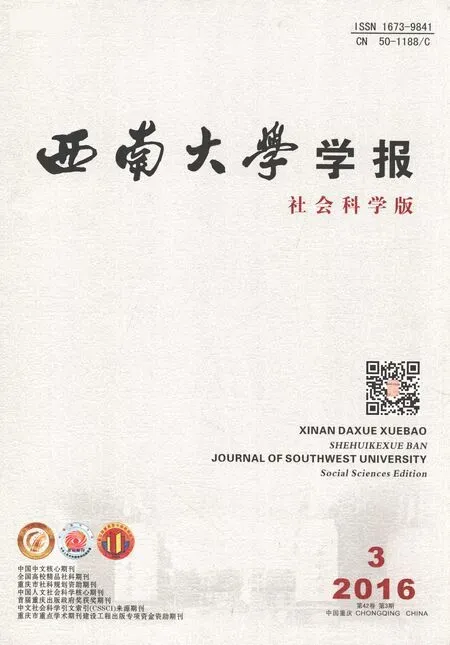新世界观的“纲领”还是“萌芽”?①
——对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的重新解读
刘 福 森
(吉林大学 哲学社会学院、哲学基础理论研究中心,吉林 长春 130012)
新世界观的“纲领”还是“萌芽”?①
——对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的重新解读
刘 福 森
(吉林大学 哲学社会学院、哲学基础理论研究中心,吉林 长春 130012)
摘要:《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是马克思哲学形成过程中的一篇重要的哲学文献。它包含了马克思的“新世界观萌芽”,但其思想并未完全成熟,其主要表现是:文献虽然弘扬了实践观点,但这里的实践概念还仅仅是一个包含了主体能动性的抽象的实践概念,而成熟的马克思哲学的实践概念则是一个现实的实践概念,即社会历史的概念。由于《提纲》还没有提出新唯物主义世界观的历史的解释原则、历史的思维逻辑和历史的评价尺度,因而在关于社会和人的理解上,《提纲》也未能实现从抽象的人和抽象的社会向现实的人和现实的社会的转变。因此,我们在对马克思哲学的研究中不能完全以此文献为标准,特别是不能用《提纲》的观点去消解和贬低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形成的成熟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
关键词:《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抽象的实践;现实的实践;新世界观;实践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
人们在关于马克思哲学的总体性质问题的理解上所产生的分歧,是与人们对马克思的哲学原著理解上的分歧直接相关的。如果我们把马克思哲学形成时期的一些不成熟或不完全成熟的著作当作完全成熟的著作去理解,就必然会模糊新旧哲学的界限,不能正确理解马克思实现的哲学变革的理论实质。我国学界关于“马克思哲学是什么样的唯物主义”问题的长期争论,在某种意义上说就与人们对马克思哲学形成时期的三篇文献——《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以下简称《提纲》)和《德意志意识形态》(以下简称《形态》)的不同理解相关。因为篇幅关系,本文主要对马克思的《提纲》进行重新解读,以期对成熟的马克思哲学的总体性质做出合理的解释。
一、怎样理解恩格斯对《提纲》的评价
《提纲》的写作时间,是在《手稿》和《形态》之间。《手稿》写于1844年5月底至8月,《提纲》写于半年之后的1845年春天,《形态》的开始写作是在1845年9月,到1846年初夏其他部分基本结束,其中第一卷第一章《费尔巴哈》到1846年下半年还在继续。也就是说,马克思《形态》中对费尔巴哈的批判,是在《手稿》的两年之后完成的,即《形态》与《手稿》之间相隔两年多的时间。在这两年多的时间中,马克思的哲学观点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从一个费尔巴哈主义者,变成了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他的哲学思想也彻底离开了旧哲学,创立了历史唯物主义。正是在这短短的两年多时间中,马克思实现了一个哲学的革命性变革。在这三篇文献中,《手稿》还是没有成熟的哲学文献,《手稿》中的马克思在思想总体上还没有摆脱形而上学,仍然停留在抽象的人本主义思想框架中,对费尔巴哈的旧唯物主义(自然主义的人本主义)持完全肯定的态度。《形态》则是完全成熟的一部哲学文献,其主要标志是从根本上颠覆了形而上学,创立了历史唯物主义。夹在这两篇文献中间的《提纲》,则是一篇过渡性的文献,它已经开始了哲学革命,但并没有最后完成,因而它还仅仅是包含新世界观的“萌芽”,还没有达到马克思哲学的最高境界。
在我国学界,很多学者把《提纲》看做一篇完全成熟的哲学文献,并完全从《提纲》出发去理解马克思新唯物主义世界观的理论特质,而《形态》则被仅仅看成是一篇阐述唯物主义历史观的文献。这种观点认为,《提纲》是“马克思新世界观纲领”,而《形态》只不过是《提纲》的“详论”或“具体化”,“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就是他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实践范畴”是历史唯物主义“得以建立的理论基础”。[1]
人们对《提纲》做出完全肯定的评价,是依据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书的“1888年单行本序言”中的评价做出的。恩格斯的评价是:“这是匆匆写成的供以后研究用的笔记,根本没有打算付印。但是它作为包含着新世界观的天才萌芽的第一个文件,是非常宝贵的。”[2]212-213
恩格斯对《提纲》的这个评价基本上包含了以下两个部分:第一部分阐述了《提纲》的写作目的:《提纲》“是匆匆写成的供以后研究用的笔记,根本没有打算付印”;第二部分阐述了《提纲》的总体性质和理论价值:“它作为包含着新世界观的天才萌芽的第一个文件,是非常宝贵的。”人们在引用恩格斯的这段话时,大都掐头去尾,仅仅引用第二部分,而在引用第二部分时,又仅仅引用“新世界观”和“非常宝贵的”几个字,而舍去了“萌芽”两个字。这样,就把新世界观的“萌芽”变成了成熟的新世界观的“纲领”。恩格斯认为《提纲》是一篇“非常宝贵的”文件,不过,这篇文献之所以“非常宝贵”,不是因为它包含着完全成熟的“新世界观纲领”,而是因为它“包含着新世界观的天才萌芽”。谁都清楚,“萌芽”与成熟的“果实”是不同的:“萌芽”仅仅是生长出“果实”的“不成熟阶段”。可见,在恩格斯对《提纲》的评价中,“萌芽”二字并不是可有可无的,它是对“新世界观”理论性质和价值的一种限制性规定。因此,恩格斯并不认为《提纲》是一篇完全成熟的文献,而是认为它是一篇“还没有成熟”的文献。
当然,我在这里并不否定《提纲》在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世界观形成过程中所具有的历史作用。虽然《提纲》仅仅包含了新世界观“萌芽”,但是,成熟的“果实”中总是包含着“萌芽”,并从“萌芽”发展而来,因而包含着新世界观“萌芽”的《提纲》为马克思的成熟的新世界观的形成开辟了一条新的路径,因而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马克思的《手稿》还是一篇“完全没有成熟”的文献:马克思在《手稿》中对费尔巴哈的哲学还是持完全肯定的态度的:“费尔巴哈是唯一对黑格尔辩证法采取严肃的、批判的态度的人;只有他在这个领域内做出了真正的发现,总之,他真正克服了旧哲学。”费尔巴哈的伟大功绩在于“创立了真正的唯物主义和实在的科学,因为费尔巴哈也使‘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成了理论的基本原则。”[3]很清楚,如果说费尔巴哈“真正克服了旧哲学”,那么费尔巴哈哲学当然是不包含在旧哲学之中的,它已经是“新哲学”了;如果说“费尔巴哈创立了真正的唯物主义和实在的科学”,那么,《手稿》就承认了费尔巴哈哲学就是“真正的唯物主义”,由此看出马克思那时还没有形成不同于费尔巴哈旧唯物主义的新唯物主义;如果说“费尔巴哈也使‘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成了理论的基本原则”,那么,马克思在《手稿》中所理解的“社会关系”,肯定还没有超出费尔巴哈理解的那种社会关系。从《手稿》对费尔巴哈的完全肯定的态度看,《手稿》的基本核心思想和立场还没有超出费尔巴哈哲学。《手稿》的核心思想,仍然是抽象的人本主义的形而上学,这种抽象的人本主义形而上学突出表现在《手稿》中关于“人的本质的异化与复归”的思想之中,它同马克思成熟时期的思想——历史唯物主义是完全对立的两种完全不同形态的哲学。也就是说,《手稿》还是“完全”没有成熟的文献,其中还没有新世界观的“萌芽”。恩格斯说《提纲》是包含着新世界观天才萌芽的“第一个文件”,这本身既是对《提纲》的肯定,也是对《手稿》的否定。因此,马克思新世界观的创立,对于《手稿》来说,不是继承,而是“告别”。正是从《提纲》开始,马克思才开始要创立一种既不同于黑格尔、也不同于费尔巴哈的全新的唯物主义世界观。对费尔巴哈的批判,则是建立这种新世界观的突破点。因此,《提纲》是马克思创立新唯物主义世界观的起点,尽管它只是一个还不成熟的起点。这就是《提纲》所具有的理论意义和价值。
二、“实践哲学”:《提纲》包含着的新世界观的“萌芽”
我们说《提纲》包含了新世界观的萌芽,突出表现在实践概念的引入。《提纲》总共有十一条,其中第一、二、三、四、五、八、九、十一条(共八条)都是讲实践问题或涉及到实践问题的,都是直接批判费尔巴哈不理解实践的意义这一缺陷的。在论述实践观点的八条中,第一条是最为根本的。因此,我在这里主要针对第一条来阐述马克思在创立新世界观过程中提出实践概念的理论意义。
在这一条中,马克思指出了旧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都不理解人的感性活动本身:旧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感性的人的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4]54。因此,旧唯物主义完全否定了人的主体性和实践活动的能动性;与旧唯物主义相反,唯心主义则是片面地、抽象地发展了感性活动的能动的方面,把实践的能动性和主体性变成了精神的能动性与主体性。在这里,马克思用“感性活动”(实践)的理论原则批判并取代了费尔巴哈的“感性存在”的理论原则,也同时捎带地批判了唯心主义实践观,形成了以实践观点为核心的实践哲学。这就是《提纲》所具有的主要的理论价值。
但是,《提纲》中的实践概念还不是马克思哲学的一个成熟的“实践”概念。我们说实践概念“不成熟”,突出表现在,《提纲》里讲的“实践”还是一个抽象的实践,而不是一个现实的(社会历史的)实践。在《提纲》中讲的实践,仅仅是一个包含了人的主体性、能动性的“感性活动”概念,“主体性”、“能动性”、“感性活动”正是对“实践”的一般属性的抽象,而在成熟的《形态》中,马克思讲的实践则是在特定社会历史条件下,由现实的个人所进行的特殊实践,这样的实践才是“现实的实践”。实践的现实性,正是表现为人的社会历史性。因此,《提纲》中的实践理论还不是马克思哲学成熟的实践理论:
第一,成熟的马克思哲学所讲的人是“现实的人”,即在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生活和实践着的人。成熟的马克思哲学的一个基本理论原则就是“从现实的人出发”,这一原则是在《形态》中提出并屡次特别强调的一个基本原则。但是,从《提纲》中的“一般实践”出发去看人,我们所看到的只能是具有主体能动性的“一般人”,而不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活动着的具有特殊性的现实的人;“实践性”还被看成是人的“一般本性”,并用这个“一般性”去解释现实存在的个人,这就违背了“从现实的人出发”的基本理论原则。单纯从这一点看,《提纲》与西方传统的形而上学的抽象的人本主义哲学仍然具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第二,抽象的“一般实践”概念还只是一个中性的概念:如果我们片面地、抽象地发展了感性活动的能动的方面,就必然把实践的能动性和主体性变成了精神的能动性与主体性,这样就必然走向唯心主义(如黑格尔);而如果我们片面地、抽象地发展了实践的“受动性”一面,就必然把“感性活动”理解成为失去主体能动性的“感性存在”,因而就会走向费尔巴哈的旧唯物主义。因此,抽象的“一般实践”概念本身,既不是唯物主义的,也不是唯心主义的,我们从《提纲》中的“一般实践”概念只能推导出一个一般的、中性的“实践哲学”(实践主义),而不能推导出“实践唯物主义”哲学。
第三,马克思的“实践唯物主义”的创立,实际上是在《形态》中最终得以完成的。在《形态》中,马克思创立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新唯物主义世界观,彻底颠覆了西方传统形而上学,为新哲学提供了一种历史的解释原则和历史的思维逻辑。这就为把《提纲》中的一般“实践哲学”转变为“实践唯物主义”提供了理论上的可能性。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认为:“历史的每一阶段都遇到一定的物质结果,一定的生产力总和,人对自然以及个人之间历史地形成的关系,都遇到前一代传给后一代的大量生产力、资金和环境,尽管一方面这些生产力、资金和环境为新的一代所改变,但另一方面,他们也预先规定新的一代本身的生活条件,使它得到一定的发展和具有特殊的性质。”[4]92马克思这段话的意思是,当我们把实践看成是特殊的、社会历史的实践时,我们就可以通过不同历史时代的特殊实践之间的历史性联系去证明实践的客观性:每一代人的现实的实践都是具有主体选择性的能动的实践。但是,每一代人在进行他们的创造性的实践活动之前,都必须面对前一代人留给他们的一定的“生产力的总和”、技术、资金和环境,前一代留给后代人的这些“历史性遗产”不是旧唯物主义所说的“自然物质”,而是前代人的实践结果,它体现着前代人的主体性创造能力和价值选择,体现着前代人的实践活动的特殊性质和力量。因此,尽管后一代的实践活动也是一种自主的、能动的主体选择活动,但是,对于他们来说,有一点是不能自主选择的,即对他们的前辈们的实践结果是不能自主选择的。前辈们的实践活动虽然也是一种自主的选择活动,但是,对于他们的后辈的初始实践活动来说,是作为一种客观因素起着决定性的作用的。这样,马克思就用前一代人的实践与后一代人的实践之间的历史性联系,证明了人的实践活动的客观性,从而形成了一种新唯物主义,即实践唯物主义。因此,只有依据历史性思维和历史的逻辑,才能证明在目的和意志支配下实践活动何以是客观的,也才能说明马克思在《提纲》中提出的以实践概念为核心的“实践哲学”是何以成为“唯物主义”的。没有《形态》创造的历史性思维和历史的逻辑,《提纲》所讲的实践哲学就不能成为“实践唯物主义”哲学。
第四,对费尔巴哈批判的不彻底性。按照在《形态》中马克思对费尔巴哈的批判,费尔巴哈哲学存在着两个方面的缺陷,其一是费尔巴哈哲学的直观性,其二是费尔巴哈哲学在历史观上的唯心主义。然而,由于《提纲》还没有把实践理解为社会历史的实践,因而还不能对费尔巴哈哲学的第二个方面的缺陷进行批判。对费尔巴哈哲学的第二个方面的批判是在《形态》中完成的:“当费尔巴哈是一个唯物主义者的时候,历史在他的视野之外;当他去探讨历史的时候,他不是一个唯物主义者。在他那里,唯物主义和历史是彼此完全脱离的。”[4]78由于《提纲》还没有形成历史的解释原则和历史的思维逻辑,因而不可能对费尔巴哈的历史唯心主义进行强有力的批判。而这个新的解释原则和思维逻辑是在《形态》中才形成的。
因此,我们可以说,由于《提纲》引进了实践概念,就使得《提纲》开始要超越西方传统哲学,具有“新世界观萌芽”的理论价值,但是,由于《提纲》的实践概念还是一个抽象的实践概念,还没有实现从抽象的实践向现实的实践的转变,就使得《提纲》不可能成为完全成熟的“新世界观”,而只是新世界观的萌芽而已。因此我认为,《提纲》的实践论哲学只是为实践唯物主义的创立提供了可能性和前提,通过《形态》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才使得实践唯物主义得以最终完成。因此,我们不能不得出这样的结论:即使在实践问题上,《提纲》也只是包含了新世界观的“萌芽”;《形态》创立了历史唯物主义,才使得这个“萌芽”成熟起来,开花结果。
三、“社会关系的总和”:《提纲》包含着的历史唯物主义的“萌芽”
《提纲》共有八条是谈论实践问题的,而谈论社会和人的问题的却只有三条(即第六、七、十条)。这一方面反映出马克思在写作《提纲》时主要关注的是用“感性活动”(实践)的观点批判费尔巴哈“感性存在”哲学的直观性,另一方面也反映出马克思这时还没有进展到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出发去批判费尔巴哈的历史唯心主义的阶段。
在《提纲》谈论社会和人的问题的六、七、十这三条中,对人和社会问题的理解还只是具有萌芽的性质,还没有达到新唯物主义(即历史唯物主义)的最高境界。在《提纲》的第六条中,马克思批判了费尔巴哈在宗教问题上表现出来的人本主义观点:第一,费尔巴哈“假定有一种抽象的——孤立的——人的个体”,“把宗教感情固定为独立的东西”。[4]56第二,因此,他只能把人的本质“理解为‘类’,理解为一种内在的、无声的、把许多个人自然地联系起来的普遍性”[4]56。从这里出发,马克思在人的问题上得出了如下结论:“费尔巴哈把宗教的本质归结为人的本质。但是,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4]56在这里,马克思还是从“人的本质是什么”的问题出发,试图用“社会关系的总和”对“人的本质”概念做出新的规定,而没有否定“人的本质”这一概念本身。
在学术界,很多人都把马克思讲人的本质的这段话看做马克思对“人的本质”的完美的、经典的定义。他们只要讲到人,就要讲人的本质;而只要讲到“人的本质”,就一定要引用马克思《提纲》中的这段话。因而这些人是完全肯定“人的本质”概念的。但是,在我看来,马克思的这段话力图用“社会关系的总和”概念去解释人,这表明马克思对人的解释已经开始想要超越传统的人本主义,想要超越费尔巴哈,想要从“现实性”上去解释人。但是,由于马克思这时还没有确立起历史的思维逻辑,因而这里的“社会关系的总和”概念还不是一个现实的、历史的概念:“社会关系的总和”还只是一个由全部社会关系构成的“总体性”概念,它并不包含“历史性”的含义,因而还不能揭示出人的历史性。要揭示出人的活动的历史性,就必须把人以及人生活于其中的社会关系放到现实的历史发展中去考察。“现实的”社会关系,是随着生产力发展而不断变革的、在不同生产力条件下具有不同性质的特殊的社会关系,正是这些“特殊的”、“现实的”社会关系,才使不同历史条件下的人具有了特殊的性质而真正成为“现实的人”。对人以及社会历史的理解,《提纲》显然还没有达到这个高度。
同时,马克思在《提纲》中还在沿用“人的本质”概念。“人的本质”概念,并不是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概念,而是传统的抽象的人本主义哲学的核心概念。“人的本质是什么”的提问方式,是传统形而上学的人本主义哲学的提问方式。它把人的本质看做人的“真正的存在”(人本身),是决定“人之所以为人”的根据,它“先在地”决定着人的“何所来”、“何所是”以及“何所去”,而现实的人则只能被理解为这种抽象本质在现实世界中的“现身”。马克思既然反对费尔巴哈提倡的那种抽象的人,当然就不应该再追问“人的本质”是什么。在《形态》中,马克思明确反对使用“人的本质”概念。他认为,“实体”和“人的本质”是哲学家们“想象”出来的“东西”[4]93,在现实中是不存在的。《形态》对现实的人的提问方式是“人是什么样的”。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这同他们的生产是一致的——既和他们生产什么一致,又和他们怎样生产一致。因而,个人是什么样的,这取决于他们进行生产的物质条件。”[4]68历史唯物主义所理解的人,是一种历史的存在。这样的人是通过他们的生产活动不断地自己创造自己、自己发展自己的现实的人。因此,人没有永恒不变的理想性本质,现实的人永远都是“在路上”。这样理解的人才是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世界观所理解的人。
可见,在《提纲》中,“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4]56这段话表明,《提纲》这时已经开始想要从社会关系上去解释人,开始了对费尔巴哈的抽象的人本主义的批判,但是,在提问方式上还没有告别旧哲学的提问方式,并试图用“在现实性上”去解释人的抽象“本质”,这正说明了马克思在《提纲》中关于人的理解还未完全超越旧哲学,因而还仅仅是新世界观的萌芽。
马克思开始用“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去解释人,这表明,《提纲》已经比《手稿》前进了一大步。《手稿》还是完全站在西方传统形而上学的人本主义的立场上,首先假定人有一个抽象的、理想的、永恒不变的本质,继而从此出发去理解和评价现实的人和社会,把共产主义社会之前的“现实的人”都看做人的本质的“异化”,即失去了本质的人(在本质上的“非人”),只有到了共产主义社会,人才重新获得自己失去了的本质(本质复归)而成为人。这种解释还完全是以抽象的人本主义为解释原则的。这样,《手稿》就把人和社会的发展过程理解为由人的理想性的抽象本质牵引着前进的“人的本质的异化和复归”的过程。因此,《手稿》还没有出现新世界观的萌芽。在《提纲》的第六条中,马克思在对人的理解上已经开始指向“现实的人”,试图用“社会关系的总和”去解释人,这表明马克思对人的理解已经具有新世界观的萌芽。但是,这里的社会关系的“总和”概念还是“社会关系一般”(缺少历史性),而不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存在的具有个性的“现实的”社会关系。这表明,马克思在《提纲》中还没有形成“历史的思维逻辑”,而如果缺少“历史的思维逻辑”,就不可能完成从抽象的人向现实的人的转变。恩格斯指出:“对抽象的人的崇拜,即费尔巴哈的新宗教的核心,必定会由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来代替。这个超出费尔巴哈而进一步发展费尔巴哈观点的工作,是由马克思于1845年在《神圣家族》中开始的。”[2]241
恩格斯在谈到黑格尔的哲学时提出了“历史的逻辑方法”概念:“黑格尔的思维方式不同于所有其他哲学家的地方,就是他的思维方式有巨大的历史感作基础。”“这个划时代的历史观是新的唯物主义观点的直接的理论前提,单单由于这种历史观,也就为逻辑方法提供了一个出发点。”[5]42因此,历史的逻辑方法,就是“历史地、在同历史的一定的联系中来处理材料的”逻辑方法。[5]43我们说《提纲》还没有完成新世界观的创造,其根据之一就在于,在《提纲》中,我们还看不到这种历史的思维逻辑。《提纲》在讲到“实践”概念时,始终都是在讲“一般实践”,没有揭示出实践的“历史性”。例如,《提纲》在讲到人与环境的关系时说:“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的一致,只能被看做是并合理地理解为变革的实践。”[4]59应该说,人和环境的改变都只能用实践去解释。在这个意义上说,《提纲》的说法是不错的。但是,由于“人与环境”的关系并不是一个超时间、超历史的抽象的关系,而是一个在历史中不断变化着的历史性的关系,因此,简单地用抽象的“一般实践”概念还不能解决人与环境之间的关系。这正是《提纲》在解决人与环境关系问题上的局限性。到了《形态》,马克思才把人与环境的关系问题放到历史中去考察。这时,马克思把人与环境的关系分解为两个对立的命题:“人创造环境,同样环境也创造人。”[4]92如果按照形而上学的思维逻辑去理解人与环境的关系问题,把实践看成是抽象的“一般实践”,把人、环境概念看成是“一般人”和“一般环境”的抽象概念,把人与环境的关系看成是超时间、超历史的抽象关系,那么这两个命题的对立就只能是一个类似于“到底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无法解决的悖论。但是,如果把人与环境的关系放到现实的社会历史中去,“历史地、在同历史的一定的联系中”去理解人与环境的关系,那么,实现这两个对立命题的统一就变得十分简单了:“人创造环境”是指前代人的实践(结果)创造了后代人进行“初始实践”所面对的“环境”,在这个意义上说,是“人(指前代人)创造了环境(指后代人所面对的环境)”;同时,由于(前代)人的实践所创造的(对后人来说的)环境,事先决定了后代人的初始实践活动的特殊性质,因而这个过程也是“环境创造(后代)人”的过程。正是前后代人之间的这种历史的联系,不断地改变了人,改变了人的环境,也改变了人与环境的现实的关系,才形成了现实的人与社会历史的发展过程。人与环境的关系本来就不是一个抽象的关系,而是一种历史的联系。由于《提纲》还没有形成历史的思维逻辑,因而仅仅用一般的实践论原则去解释人与环境问题,就显得这种解释的软弱无力。[6]
四、“萌芽”与“果实”:实践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内在统一
如果说《提纲》是马克思创立的新世界观的“萌芽”,那么,《形态》就是新世界观的成熟的“果实”。这两篇文件之间具有类似于“萌芽”与“果实”的关系。
第一,任何成熟的“果实”都是从“萌芽”发展而来,因而果实离不开萌芽;但萌芽并不等于成熟的果实,二者之间存在着根本性质上的区别。我们说《提纲》包含着新世界观的萌芽,只是说《提纲》具有成为新世界观的“可能性”,并不是说《提纲》在理论性质上就已经完成了新世界观的创造。《提纲》的这种萌芽性质,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实践概念的引入,标志着《提纲》开始告别费尔巴哈的感性存在论的旧唯物主义,指向了人的生存论的实践唯物主义。二是《提纲》开始想要从社会关系上去理解人,具有对“现实的人”的指向性。但是,由于《提纲》还没有形成历史的思维逻辑,因而它所说的实践和人都还不具有历史的性质。人还不是现实的、在历史中发展的人,实践概念还仅仅是一个包含着“主体能动性”的“一般实践”概念。因此,《提纲》还没有最后告别以抽象的实践观念为标志的实践哲学,还没有最终完成实践唯物主义的理论创造,仅仅包含了新世界观的“萌芽”。
但是,在我国学界对马克思哲学的研究中,很多人都混淆了“萌芽”与成熟的“果实”的区别,把《提纲》中包含着的新世界观“萌芽”看成是新世界观的完全成熟的“果实”,于是,《提纲》中的一般“实践论”哲学就被说成是“新世界观纲领”;而《形态》中的历史唯物主义的新世界观就只能被看成是被一般实践论哲学“具体化”出来的历史观了。这种观点表面看来是对《提纲》的重视,但实质上却是把马克思的不成熟的理论当作了贬低和否定马克思的成熟理论的工具,把“一般的”实践哲学当作了否定历史唯物主义的工具,总之,是用“萌芽”去否定“果实”,而“果实”却被看成了由“萌芽”“具体化”出来的“现象”。这种观点是与成熟的马克思的新世界观背道而驰的。马克思的新世界观,是把“现实性”作为理论的出发点的:从现实的人出发,而不是从抽象的人出发;从现实的实践出发,而不是从抽象的实践出发。只有如此,才能把马克思的历史的思维逻辑同西方传统的形而上学的思维逻辑区别开来,才能最终实现“对形而上学的颠倒”。上述观点仍然坚持从抽象的一般实践概念出发推导出现实的实践的思维逻辑,正是形而上学的思维逻辑,即马克思在《形态》中所批判的那种“从天国降到人间”而不是“从人间升到天国”的思维逻辑。
第二,虽然“萌芽”有可能生长出成熟的“果实”,但“萌芽”并不必然地生长出成熟的“果实”。“萌芽”往往包含着多种可能的理论指向,而要最后形成实践唯物主义世界观,就必须把抽象的“一般实践”转变为“现实的实践”。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把实践概念放到由《形态》所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上去理解。因此,离开历史唯物主义,就没有实践唯物主义;在历史唯物主义之外、之前,根本不存在实践的唯物主义;或者说,在历史唯物主义还没有形成的时候,就不会有成熟的实践唯物主义。实践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都是马克思新世界观的成熟的“果实”,它们本来就是同一种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强调的是新唯物主义世界观包含着的“历史的思维逻辑”、“历史的解释原则”和“历史的价值评价尺度”[7],它使得马克思创立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同时具有了新唯物主义世界观的性质和功能。实践唯物主义也是在《形态》中才得以形成的新世界观。把马克思的新世界观概括为“实践唯物主义”的特殊意义在于强调马克思哲学世界观的否定旧世界、建立新世界的革命性质。实践唯物主义体现了马克思哲学独有的革命精神和理论气质。在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世界观中,实践的观念与历史的观念是互为前提的,这两个具有不同特征的观念和解释原则都是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世界观的基本解释原则。因此,企图用实践唯物主义去贬低和否定历史唯物主义、用《提纲》去贬低和否定《形态》的做法,最后必然否定马克思新唯物主义世界观所独有的理论特质,因而必然否定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世界观本身。
参考文献:
[1]陆剑杰.实践唯物主义:彰显马克思哲学本质的真切之名[J].南京社会科学,2012(9):1-10.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3]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96.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6]刘福森.马克思哲学研究中的方法论问题[J].现代哲学,2015(4):1-8.
[7]刘福森.哲学的理论特质:马克思哲学不是什么?[J].江海学刊,2013(2):13-23.
责任编辑刘荣军
网址:http://xbbjb.swu.edu.cn
DOI:10.13718/j.cnki.xdsk.2016.03.001
收稿日期:①2016-02-25
作者简介:刘福森,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哲学基础理论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
中图分类号:B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9841(2016)03-0005-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