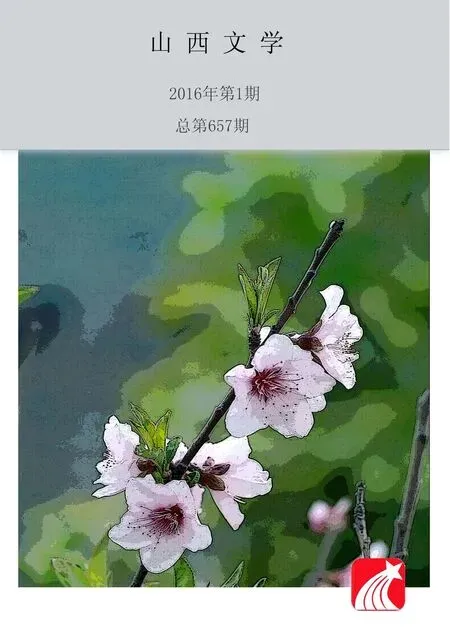从宣统四年说起
介子平
从宣统四年说起
介子平

辛亥年,武昌首义,各省响应。山西巡抚陆钟琦拒绝了合作,以死报答朝廷知遇之恩。但多数省份却是兵不血刃,一枪未放,也未见侵扰百姓,江苏巡抚程德全反正之后,为表示革命必须有破坏,遂以竹竿子挑去巡抚衙门屋檐的几片瓦了事。反正的程德全宣布独立后,巡抚更名都督,一面剪去自己的辫发表示自己的革命决心,一面收集院司各种印信,销毁于都督府大堂,与旧体制割断联系。
结束帝制,倾向共和,乃民军之意,万众之心。清室以妥协方式逊位,从此退处宽闲,优游岁月,避免了身首异处,血光之灾,国家防止了九夏沸腾,生灵涂炭,百姓也幸脱了商辍于涂,士露于野,民国则以和平继受了前朝的疆域人民。此乃中国的“光荣革命”。
上海《时报》1912年3月5日发表了一篇评论文章《新陈代谢》,形象地概述了民国成立后多种领域的“兴灭”代谢:“共和政体兴,专制政体灭;中华民国兴,清朝灭;总统兴,皇帝灭;新内阁兴,旧内阁灭;新官制兴,旧官制灭;新教育兴,旧教育灭;枪炮兴,弓矢灭;新礼服兴,翎顶礼服灭;剪发兴,辫子灭;盘云髻兴,堕马髻灭;爱国帽兴,瓜皮帽灭;阳历兴,阴历灭;鞠躬礼拜礼兴,拜跪礼灭;卡片兴,大名刺灭;马路兴,城垣卷栅灭;律师兴,讼师灭;枪毙兴,斩绞灭;舞台名词兴,茶园名词灭;旅馆名词兴,客栈名词灭。”
虽说外面已改朝换代,百姓生活仍得继续。汾阳刘家堡距县城仅八里路,在该村关帝庙《重修关帝庙碑》的落款仍为宣统四年,对面戏台侧壁残留有“平邑自诚园”戏班申海山题记的“宣统四年五月廿九、六月一、二日在此亦乐乎”,而曾为府治且繁华异常的汾阳城内,已是民国元年了。是武昌起义的成功太过迅速,国人尚未能知晓,还是另有依恋?明亡后,朝鲜君臣以为,“我朝三百年来,服事大明,其情其义,固不暇言。而神宗皇帝(万历帝)再造之恩,自开辟以来,亦未闻于载籍者。宣祖大王所谓义则君臣,恩犹父子,实是真诚痛切语也”。李朝视清廷为犬羊夷狄,私下称清帝为“胡皇”,称清使为“虏使”。除对清廷公文贺表之外,包括王陵、宗庙、文庙祭享祝文一切内部公文,仍以崇祯年号。朝鲜《仁祖庄穆大王实录》,在明亡前以崇祯年号,在明亡后以干支纪年和国王在位年号。至于私人著述,直到清末,仍有人书写崇祯年号,以至竟然有“崇祯二百六十五年”的纪年。恐非如此,对清廷的绝望早已成全民情绪,山西虽远离中枢,祸不舍远,汾阳也偏居一隅,疫不疏陬,民众企盼靡尽,舆情愤懑难释,人心已冷,兴致索然,此时的改朝换代水到渠成,大势所趋。
民初乡村,除却学堂遍设、乡校递增的变化,提倡国货、挽回利权的宣传,还有便
是盗贼公行、人心浮动的恐慌了。兵衅既开,强者响应,匪盗啸聚,黠者揭竿,肆行劫掠,差队围攻,几成历史规律。越南河内遗民阮尚贤在其《旅晋感怀》中,纪录了辛亥年的亲身经历:“辛亥九月八日,晋军起事,余在晋城,几为军人枪击者再,以外人对,获免。出投旅馆,行李荡然,惟存旧书数卷而已。”明末掘李自成祖墓的边大绶,曾被自北京溃退的闯军从老家任丘押往太原,后乘隙逃脱,孤身还家,在其《虎口余生记》中记录了一路亲睹的土贼趁火打劫、杀人越货情形。金兵毁宋,李清照携金石碑帖南渡,屡遇土贼偷盗抢劫,收藏殆尽。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周边百姓拍手称快,更随乱打劫。民众役抑既久,平日无上诉管道,王朝解体,秩序不再,乘势放纵发泄,哪有流连之情,扼腕之憾,有的却是按捺不住,兴奋异常,百姓与政府命运切割矣。于是那些兴建于冷兵器时代的坞壁,此时又得以修缮加固。刘家堡关帝庙即设于堡门洞之上,其功能在于庇护乡党,这一点上,民国元年没有宣统四年安然。清廷内阁承宣厅许宝蘅据历代江山鼎革的经验估计,每历改朝换代,中国人口必大幅减少:“世变至此,杀机方动,非生灵涂炭,户口减去三分之二或四分之二,不能安宁。”孙中山也预计到了这一点,故他在1912年1月4日,复电袁世凯时称:“文不忍南北战争,生灵涂炭,故于议和之举,并不反对。倘由君之力,不劳战争,达国民之志愿,保民族之调和,清室亦得安乐,一举数善,推功让能,自是公论。”曾被清廷派去镇压武昌起义的海军统制萨镇冰,不忍生灵涂炭,遂化装成商人,逃回福州老家,其临别赠言:“今老矣,不忍见无辜人民肝脑涂地,若长此迁延又无以对朝廷。君等皆青年,对于国家抱急进热诚,我受清廷厚恩,不能附和。今以舰队付君等,附南附北皆非所问,但求还我残躯以了余生。”他用灯语示知停泊在阳逻港的各军舰和雷艇:“我去矣,以后军事,尔等各船艇好自为之。”民初的动荡只是局部性的、小规模的,此乃历史的进步。
一棵大树轰然倒地,除却镇江驻防八镇副都统载穆、湖北安陆知府桂荫少数几个殉节者,旧官吏或脚底抹油,一走了之,或改头换面,重新上任,而不知不觉、秋毫无犯的百姓生活仍然继续着,所唱剧目,仍是《双玉镯》《梦鸳鸯》《如意图》《抱灵碑》《金刚庙》《明月珠》这样的老本子。鲁迅在《祝福》的结尾写道:“年年如此——家家如此——只要买得起福礼和爆竹之类的——今年自然亦如此。”在《阿Q正传》中则写道:“未庄人日见其安静了。据传来的消息知道,革命党虽然进了城,但还没有什么大的异样。”阶级关系照旧,风俗习惯依旧,思想意识依旧,为改元后的大致面貌。
造物所忌,曰刻曰巧,圣贤处事,惟宽惟厚。辛亥后并未对前朝人物进行清算,游戏一旦结束便不再争斗,让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这场革命真的与大众的关系不大,而阿Q们指望的秀才娘子的宁式床或摸摸尼姑脸的愿望也未能实现,唯一的改变是男人脑后的辫子剪掉了。其实,阿Q们指望的是打砸抢,是地覆天翻。是谁阻止了原本的暴力革命与政治动荡?
清末出现的革命党与立宪派两种革新力量,二者皆以救国为目标,只是手段方法不同而已。前者主张革命,后者力求改良,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两派处于对立冲突态势。国民对于立宪有所期待,而革命的胜利多少带有偶然性。平和的立宪派,较之“短衣长剑入秦去,乱峰汹涌森如戈”的革命派,其基础更为厚实,影响更为广泛,经其长期努力,朝野渐成共识,人民的政治意识已渐次开放。杜亚泉曾言:“茫茫政海中,固有二大潮流,荣洄澎湃于其间。此二大潮流者,其一为革命运动,其一为立宪运动。革命运动者,改君主国为民主国;立宪运动者,变独裁为代议制。其始途颇殊,一则为激烈之主张,
一则为温和之进步,及其成功,择殊途同归。由立宪运动而专制之政府倾,由革命运动而君主之特权废。民主立宪之中华民国,即由此二大政潮之相推相荡而成。”民国元年,南京政府公布的第一届内阁名单中,九位部长中,立宪派占六席,革命党只三席。民国建立后,立宪派的历史作用虽暂被隐匿,然君子藏器于身,待时而动,行为归于平和,却未趋于死寂,在袁世凯称帝时,立宪派乃知耻发奋,首先攘臂而起,护国讨袁。创造民国者,革命党也,再造民国者,立宪派也。
宣统三年10月29日太原首义后,为示与满清决裂,废旧年号,但新纪年未有,遂采用“黄帝纪年”。据景梅九回忆,山西大学堂瑞典籍教师高本汉离晋时,阎锡山以中华民国晋军分府正都督的名义,为之签发的护照日期为“黄帝纪元四千六百零九年九月二十三日”。“开国五千年,五族共一家”是当时的共识,但这样的纪年,显然较之宣统×年繁琐了许多,百姓的习惯是怎么方便怎么来。
南京临时政府改用阳历后,清廷也效仿之,民元1月15日,湖南籍同盟会员凌盛仪的日记道:“满清闻之,亦遂于本月十三日改为宣统四年一月一日,事事效颦,殊为无谓。”此改在独立的身份,未被理睬。5月11日,杨杏佛在北京等待留学时,给柳亚子写信道:“都中情形与南方大异,剪发辫者百无一人,且有仍用宣统四年者。”京师乃信息中枢,不存在闭塞情形,这样的纪年无疑是有意为之,盖与朝鲜使用崇祯纪年心理同。凡物有生皆有灭,此身非幻亦非真,但总有一些人,不愿承认现实政权的更迭,其中不光全是既得利益者,还有如王国维这样的文化人,心中有座坟,葬着未亡人。守旧的氛围中,中枢的京师与偏陬的汾阳,仍在宣统的旧秩序里,沐浴着最后一缕回光。
介子平,原名王介平,1964年生,山西介休人。《编辑之友》杂志社副主编,副编审。出版有诗集《青灯》《烟霏云敛》,散文集《少年文章》《消失的民艺——年画》《褪色的记忆——连环画》 《民国文事》 《风华舟青》等。
责任编辑/鲁顺民sxwx2001@163.com
- 山西文学的其它文章
- 那蓝色滑入醒来的黄昏(组诗)
- “投食”下的阅读饥饿(外二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