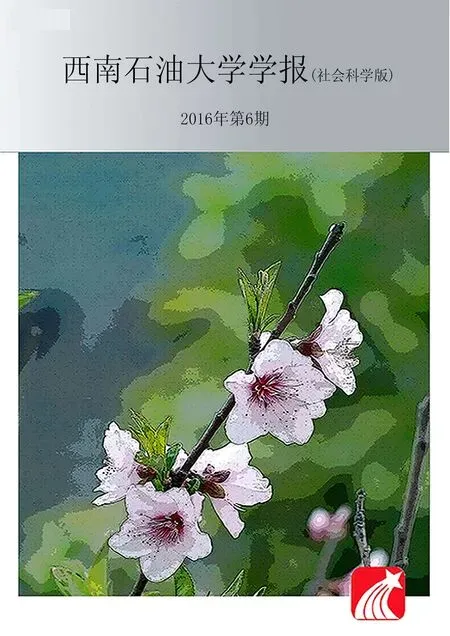刑法形式解释立场的选择
——以阶层犯罪论为视角
张晓伟,刘绍彬
兰州大学法学院,甘肃兰州 730000
刑法形式解释立场的选择
——以阶层犯罪论为视角
张晓伟,刘绍彬*
兰州大学法学院,甘肃兰州 730000
我国刑法解释存在形式解释论与实质解释论之争,这种争论与德日形式的犯罪论和实质的犯罪论有某种渊源关系。虽然有学者强调我国的形式解释与实质解释和德日就形式犯罪论与实质犯罪论的解释核心要素,即构成要件不同,但在实质上,在我国引进阶层犯罪论体系的背景下,讨论形式解释与实质解释,其核心仍然是对犯罪成立要件之一的构成要件的解释。从罪刑法定原则、立法与司法之于刑法不同功能以及人权保障的角度看,形式解释立场具有合理性。同时,在客观解释下,对形式解释论强调的排斥一切实质解释的入罪功能的观点进行修正,应当承认“国民预测可能性”判断标准的入罪意义。当然,形式解释或形式判断先于实质判断的位阶关系是以阶层犯罪论体系为存在基础的,提倡刑法形式解释论,必然主张三阶层犯罪论体系。
形式解释论;实质解释论;罪刑法定;国民预测可能性:阶层犯罪论
张晓伟,刘绍彬.刑法形式解释立场的选择——以阶层犯罪论为视角[J].西南石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18(6):57-67.
ZHANG Xiaowei,LIU Shaobin.The Selection of Theory of Formal Interpretation of Criminal Law: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lass Criminal Theory[J].Journal of Southwest Petroleum University:Social Sciences Edition,2016,18(6):57-67.
1 我国刑法形式解释论与实质解释论之争的理论缘起
1.1 德日形式的犯罪论与实质的犯罪论
德日刑法理论存在形式的犯罪论与实质的犯罪论之争,实际上是对犯罪成立条件之一的构成要件的形式解释和实质解释的争论,其根源在于犯罪论体系的演化。自贝林1906年创建犯罪构成理论后,现代刑法犯罪论体系就诞生了。贝林主张客观的行为构成要件,认为构成要件是客观的,不包含任何价值因素在内,主观内心世界的过程均属于责任的内容[1]。贝林的理论被称之为古典形式犯罪论。之后,随着迈耶“主观要素”及“规范要素”的发现,纯客观的描述性的构成要件受到了革命性的挑战,在构成要件中出现了客观构成要件和主观构成要件之分,至此,也就结束了贝林古典形式犯罪论(构成要件论)的历史,出现了新古典犯罪论(构成要件论)。在构成要件中引入主观要素后,犯罪论不断发展,如建立在威尔策尔“目的行为论”基础上的目的犯罪论,这一理论使违法性更多地包含了主观要素,使责任更倾向于非主观化和规范化;以及罗可辛以“人格行为论”为基础的目的理性犯罪论,更是强调主观人格要素在构成要件中的地位。
在这个发展的过程中,由于对主观构成要件要素在构成要件中的地位的不同认识,构成要件经历了从行为构成要件到违法类型及违法有责类型的发展。因此,德日刑法中形式的犯罪论与实质的犯罪论又可称之为形式的构成要件论与实质的构成要件论,在对构成要件的解释中就出现了对应的形式的解释构成要件和实质的解释构成要件。形式的构成要件解释论(形式的犯罪论)的代表人物大谷实教授认为“承认构成要件的独立机能,以社会一般观念为基础,将构成要件类型化的把握的犯罪论,通常被称之为形式的犯罪论”。这种形式的犯罪论能实现罪刑法定原则的要求,以及对人权的保障。他指出“实质的犯罪论……主张在刑罚法规的解释,特别是构成要件的解释上,应当从处罚的合理性和必要性出发的观点,换句话说,应当从当罚性这一实质的观点出发来解释”,并认为在实质的犯罪论面前“罪刑法定原则中的明确性抑或刑法的严格解释原则并不重要”[2]73。很明显,大谷实教授不赞成从当罚性的角度对构成要件进行实质的理解,而是主张以一般人的理解对构成要件做形式的解释。实质的构成要件解释论(实质犯罪论)的代表人物前田雅英则明显反对“只要形式的确定处罚范围就可以了”的做法,主张“合理地选择真正值得处罚的行为”,“要思考形式的该当犯罪的行为是否真正值得处罚”。他认为“单纯强调罪刑法定原则的形式侧面是不充分的,对构成要件符合性进行形式的判断是不够的,必须从实质上判断是否存在值得科处刑罚的违法性与有责性,或者说必须从处罚的合理性和必要性的观点来解释构成要件”[3-4]。从这两位学者的对立观点,基本可以清晰地看到形式的构成要件解释论和实质的构成要件解释论各自的理论点,其实质关涉到刑法规范的属性以及刑法之人权保障抑或法益保护的目的。
在日本刑法学界,尽管对构成要件的解释有形式和实质的区别,但是,对犯罪论体系的选择或坚持并没有因此而表现出分裂。也就是说,犯罪论体系发展至今,已经没有人主张行为构成要件了,而有争议的是构成要件是违法行为类型还是违法有责行为类型,即对犯罪论体系采取三阶层模式还是二阶层模式。实际上,二者只是要素的阶段分配以及对可能的违法阻却的阶段判断不同而已。换句话说,并不是主张形式解释论的学者就坚持行为构成要件或违法构成要件,主张实质解释论的学者就坚持违法构成要件或违法有责构成要件。如大谷实和前田雅英作为形式解释论和实质解释论的代表人物,但他们都坚持违法有责的构成要件类型说[5]。
1.2 我国刑法形式解释论与实质解释论
在刑法解释学中,由来已久的是主观解释与客观解释之论,即对刑法规范语词的解释,是否随着时间、客观情势以及人们价值观念的变化而变化。现在我国学者普遍赞成客观解释的观点,因此,形式解释论与实质解释论的争论是在客观解释内部产生并展开的。罪刑法定原则的确立,引起了学界对形式解释和实质解释的关注。其中,阮齐林教授较早地指出,“罪刑法定原则的确立,还将导致刑法解释方法论的转变,即由重视实质的解释转向重视形式的解释。在罪刑法定原则之下,刑法形式上的东西将居于首要的、主导的地位。犯罪首先是法律形式存在的犯罪,即刑法分则具体条文明文规定应受刑罚处罚的行为。法无明文规定,即使是滔天大罪,也不是法律意义上的犯罪。因此,犯罪的形式定义、法律特征及犯罪的法定要件将成为首要的问题”①当然,阮教授在其后的论述中认为罪刑法定原则要求形式解释论排斥实质解释论显然是片面的。这一观点引起了学界对阮教授的解释立场的争辩,有的认为不能把他当作形式解释论者,有的认为他是从片面的形式解释论转向了全面的形式解释论,但阮教授对此并没有表明最终的态度。此论述着重澄清实质解释论对形式解释论的误解。[6-7]。也就是说,在我国实质解释要早于形式解释,这是我国与德日构成要件解释从形式向实质发展的一个相反路径,主要缘于我国旧刑法坚持类推解释,并致力于推崇以社会危害性为核心的四要件犯罪论。实际上,现行刑法四要件犯罪论体系就是一种实质解释的犯罪论,社会危害性视为刑法之本质特征,四个要件或至少三个要件(除犯罪客体要件之外)均是为社会危害性服务的,即从实质上的社会危害性的角度出发认定犯罪,并不拘泥于法律明文规定的形式,这种先实质判断后可能的形式判断的逻辑显然不利于维护法的安定性,也不利于人权保障。正因为如此,罪刑法定原则的确立引起了对刑法形式理性的重视,而产生了与实质解释的争论。
基于这种争议形成的原由,有学者认为我国刑法中的形式解释与实质解释之争与德日刑法中的形式解释与实质解释表现出很大的不同。德日刑法学中的实质解释特指对作为犯罪成立条件之一的构成要件的实质解释,而我国刑法中所谓的实质解释指的是对犯罪成立的所有条件的实质解释,且在实践中被进一步扩大到了对刑法中其他刑罚规范或非刑罚规范的实质解释[8]。这一定论的正确性无法否认,只是我们认为,我国的形式解释与实质解释是以陈兴良教授和张明楷教授为代表的学者的理论框架下展开的,这些学者至少是这两位争论的核心教授,都主张对我国四要件犯罪论体系的修正,坚持引进德日阶层犯罪论体系。因此,笔者认为,在我国引进阶层犯罪论体系的背景下,讨论形式解释与实质解释也不完全与德日的形式解释与实质解释不同,至少解释的对象是犯罪成立条件之一的构成要件,这点是没有疑问的。张明楷教授明确指出“笔者所提倡的解释主要是针对构成要件的解释而言”[9];从陈兴良教授致力主张的三阶层犯罪论体系以及对形式解释的论述中,能够明确地知道他也是对构成要件的解释。笔者在此亦坚持阶层犯罪论体系下的对犯罪成立条件之一的构成要件的形式解释与实质解释论争。
实质上,在引进阶层犯罪论体系的背景下,以陈兴良教授和张明楷教授为代表的学者在我国主张的形式解释与实质解释当然是以阶层犯罪论体系为其理论渊源的,同时,双方争论的最终目的又是在我国引入德日阶层犯罪论体系。这在张明楷教授《刑法学》一书从第一版到第五版关于犯罪论的讨论,即从四要件到三要件再到客观构成要件和主观构成要件以及违法构成要件和责任构成要件的两阶层有明显的体现[10]。当然,陈兴良教授《刑法知识转型(学术史)》一书的内容也有明显体现,其中第三章为:“犯罪论体系:从四要件到三阶层”[11],更是直观地表明其立场。但是,他们两个在引进阶层犯罪论的过程中对构成要件符合性的看法或是对构成要件符合性和违法性之关系的看法不同,这种不同影响到了对构成要件的解释上。陈兴良教授将构成要件作为第一且独立的阶层,指出构成要件就是刑法分则罪状所规定的客观要件,并认为构成要件本身具有定型化的机能与人权保障的机能[12]。因此,构成要件该当性只能进行形式的解释和形式的判断,对违法性才需要作实质的判断。三阶层的犯罪论体系正是其构筑形式解释论的理念与方法论基础,反过来,形式解释论的提倡又是其弘扬三阶层犯罪论体系的有力武器。同样,张明楷教授主张构建两阶层犯罪论体系,但他不否认构成要件符合性的概念及在犯罪论体系中的地位。只是将构成要件和违法性合并为一个“不法”阶层,消解了构成要件的独立意义[12]。认为构成要件是违法类型,所以在构成要件阶段需要违法性的实质判断,即将实质判断前置。两阶层体系正是他坚持实质解释论的理念和方法论基础,同样,实质解释论的坚持也是他致力推崇两阶层犯罪论体系的理论工具。
2 形式解释论与实质解释论的论争
可以说,整个形式解释论与实质解释论是围绕对构成要件的解释而展开的,因而是贯穿整个争论始终的。如果单从解释方法的角度来看,二者无根本性的区别。但是,在罪刑法定原则之下对于解释限度的把握意味着对犯罪的认定思路有着根本的不同,集中体现为双方对形式判断与实质判断位阶关系的认识上。从陈兴良教授和张明楷教授的论述中,我们发现,形式论者与实质论者基本上都承认构成要件解释时涉及形式判断与实质判断[13]。从这个角度来讲,双方争论的不是只要形式判断或只要实质判断,而在于形式判断与实质判断之间的位阶关系。形式解释论毫无疑问地必然坚持先形式判断后实质判断,如前所述,形式解释论主张构成要件的违法类型说,即承认构成要件的违法推定机能,此时的“推定”即为形式上判断,无需以法益为指导进行实质的认定构成要件符合性的行为是否内涵违法性。因为,构成要件要素在立法者那里已经类型化了,而这种类型化正好是立法者实质判断的结果。也就是说,构成要件或各要素类型化的过程才是或者才需要实质判断,而对业已类型化的构成要件需要形式的判断,即使其担任违法推定的角色也不例外。因此,“实质判断应受形式判断的限制;若是将实质判断前置,则形式判断的制约功能会被削弱甚至消解”[7]。
实质解释论在反对形式解释论先形式判断后实质判断的同时,也不否认实质判断中的形式判断因素。如刘艳红教授指出:“纯粹的形式的判断方法对构成要件符合性判断是不可能的,实质判断从一开始就糅合在形式判断之中发挥作用。”[14]199但是,实质解释论者从构成要件违法类型说或违法有责类型说的观点出发,认为构成要件的违法或违法与责任的推定机能是一种实质的推定或者说是一种断定,尤其是在二阶层犯罪论体系下表现甚为明显,认为违法性等于构成要件符合性与不存在正当化事由,并且坚持正当化事由为消极的构成要件要素,从积极和消极两方面实质地把握构成要件符合性,将构成要件判断和违法性判断合二为一进行实质判断,因而,即使承认实质判断和形式判断的揉和,但实质上却导致构成要件符合性的判断整体上沦为实质判断,难以见到形式判断的踪影。可见,实质解释论坚持实质判断先于形式判断。换言之,实质解释论首先以法益侵害为指导对构成要件进行实质判断,然后又在处罚的必要性与合理性范围内寻求规范与事实之间的合理平衡,在此基础上才进行形式的判断是否有突破法律形式规定的可能,再一次进行实质的出罪或入罪。
实际上,在形式判断与实质判断位阶关系不同的前提下,二者是可以归属于不同主体的。或者说,在罪刑法定原则下形式解释论与实质解释论对应的维护罪刑法定原则的功能不同。实质解释论强调既维护罪刑法定原则的形式侧面,也维护罪刑法定原则的实质侧面。如有学者指出:“实质解释论眼里的罪刑法定,不仅具有形式侧面,而且还具有实质侧面。刑法在适用的过程中,不仅仅能实现形式的正义,还必须实现实质的正义。”[15]而形式解释论只坚持罪刑法定原则的形式侧面而忽视实质侧面,远离了法律的自由价值,缺乏限制立法权限的机能,容易形成国权主义刑法而恣意干涉公民正常生活。也就是说,在他们看来实质解释更有利于实现正义,保障自由。
但是,我们从陈兴良教授和张明楷教授的论著中会发现,实质上,不是完全的一面否定另一面,争议更多的是对形式侧面与实质侧面功能的不同理解。张明楷教授所言,“提出罪刑法定的实质侧面,并不意味着推崇实质侧面和贬损形式侧面,也不意味着形式侧面本身存在缺陷,即便认为形式侧面存在不足,也只是说形式侧面不能限制立法权”[9]。陈兴良教授指出:“罪刑法定原则的实质侧面在精神上与罪刑法定原则的形式侧面是完全相同的,都具有人权保障的价值蕴含……只是,罪刑法定原则的形式侧面主要是以立法权限制司法权,而罪刑法定的实质侧面是对立法权本身的限制,无论是不明确即无效还是实体内容的正当性,都是指对立法权的限制功能,因而具有宪政的功能……如果不通过罪刑法定的形式侧面对司法权加以限制,那么罪刑法定的实质侧面也只能是一纸空文。”[16]
在对罪刑法定原则不同理解的前提下,还会产生对刑法漏洞如何填补以及是否会扩大处罚范围的不同看法。这里的刑法漏洞是对刑法没有明文规定的行为,但具有严重的法益侵害性,并值得刑法处罚时,能否科处刑罚的问题,对这一问题的回答随即就会产生是否扩大处罚范围的问题。
形式解释论者通常主张通过立法的方式填补刑法漏洞,只有在有利于被告人的例外情况下,才允许通过(司法)解释的方式填补刑法漏洞,严格禁止不利于被告人的扩大解释,这种不利于被告人的扩大解释是否类推解释也是有疑问的。即便是在现代高端技术发展的社会背景下,明显存在刑法保护空白的情况,形式论者也难以赞成通过(司法)解释的方式以补足该领域的刑法规范空白。有学者指出:“对于现代社会给我们提出的现代课题。虽说刑法理论不能袖手旁观,但是,将立法的缺陷转嫁给被告人承担,随便用解释论的方式对其进行弥补,反而会引起更大的问题。”[17]实质解释论者当然也承认立法方式填补漏洞,但是,与形式解释论相反,将这种方法视作例外。根据张明楷教授的观点,只有那种通过类推解释之外的方式无法填补的漏洞,即“真正的漏洞”,才可以由立法填补,而对于通过类推解释之外的方法能够填补的漏洞,即“不真正的漏洞”,那就用解释的方法填补[9]。并主张,对刑法无明文规定但值得科处刑罚的行为,在不违反罪刑法定原则的前提下,依据处罚的必要性和合理性可以作出不利于被告人的扩大解释。
形式解释论则断然否决不利于被告人的扩大解释,也即在形式解释论看来,刑法没有明文规定但值得刑罚处罚的行为,是不能通过实质解释入罪的,并将此看作是实现法治国家必然要付出的代价。即使实质解释论者认为是在罪刑法定原则范围内,但是,不利于被告人的扩大解释本身已经超过了刑法规范的语义范围,实际上就是对罪刑法定的违反。形式解释论者承认的实质解释只有出罪的功能。但是,在本文坚持的立场下,在遵循客观解释目标的前提下,我们并没有完全否认实质解释的入罪功能,但是,我们强调通过“国民预测可能性”和“处罚必要性和合理性”的不同功能定位以解释入罪的标准(后文将述)。也就是说,在形式解释立场下,存在明显的立法漏洞时,不能全部以实现法治所必须的代价为由对严重的犯罪行为予以放纵。但是,同时需要强调,此时的判断依然是在构成要件形式判断的基础上进行的,并没有脱离形式解释的根基,只是更加充分地考虑了客观解释的因素。
3 刑法形式解释立场的内涵及其选择的合理性
3.1 刑法形式解释立场的内涵
通过对形式解释论与实质解释论基本观点的论述分析,笔者坚持我国刑法形式解释立场的形式判断先于实质判断的位阶关系。因为,从我国刑事法治发展处于不发达阶段的现实出发,当下,我国刑法的使命不应该忽视对规范形式的追求,这是刑事法治发展的前提。并且,在罪刑法定原则下追求形式合理性或规则价值是其应有之义。罪刑法定化首先是法律形式上的要求,基本功能在于限制权力、保障自由,即通过对立法权和司法权的限制保障被告人及其他社会成员的权利和自由。对立法权的限制主要通过立法范围及立法方式的限制,即立法者不能随心所欲地将某种行为规定为犯罪,而是要充分考虑行为的法益侵害性,同时要以法律明确的文字予以表述,否则就是不明确的规定,不明确即无效。对司法权的限制要求司法机关的法律适用行为在法律明确规定的范围内,否则就是不必要的,是擅权,即为法律的解释提供一个界限。也就是说,在罪刑法定原则下立法与司法具有不同的角色,二者不能混淆,通常,立法层面更多包含实质的意蕴,而司法层面更多包含形式的意蕴。
因此,在罪刑法定原则之下,坚持形式解释立场,需要对立法与司法的不同功能定位。立法者应当从实质上判断行为的处罚必要性与合理性,也就是说,立法者应当以法益侵害为指导对构成要件进行描述,寻求实质上值得刑罚处罚的严重侵害法益的行为,对其明文规定为犯罪,即对犯罪作实质上的定义。司法者则在立法规定的范围内,坚持形式理性,对行为首先作符合立法规定的判断,即首先进行构成要件符合性的形式判断,之后再作实质的违法性与可谴责性的判断,这种实质的判断更多是寻求违法或责任的阻却事由,也即消极的实质判断。这里我们也明确地看出,立法与司法中形式判断与实质判断的位阶关系是不同的,立法中将实质判断放在第一位是为立法提供依据,在这之后才考虑形式上的明确性等要求;而司法中首先要遵循罪刑法定原则,进行形式判断,在法律有规定的情况下再作实质判断,将不具有法益侵害性的行为不做犯罪处理[18]。
这种司法的形式判断的逻辑完全符合三阶层犯罪论体系下犯罪的认定逻辑,即构成要件符合性、违法性、有责性从形式到实质的判断思维。而我国传统的四要件犯罪论体系,其“一有俱有、一无俱无”的平面式要件组合特征根本不存在形式判断或形式判断与实质判断不同位阶关系的余地;并且传统四要件犯罪论体系一开始就充斥着实质判断,这种判断一旦形成,行为就被定性了,被告人无法为自己进行辩护,这是一种过分强调国家权力的作用的做法,它可能导致司法适用上先入为主的危险,不利于保障人权和实现法治[19]。因此,可以说要实现定罪的准确性,实现司法判断的正确性,实现刑法的人权保障机能就应该坚持三阶层犯罪论体系,坚持三阶层犯罪论体系也是坚持形式判断先于实质判断的逻辑前提。正如许玉秀指出:“犯罪阶层理论提供的犯罪判断阶层构造,从分析和定位构成要件要素,可以提供一个精确判断犯罪成立与否以及处罚与否的步骤,借以确保刑罚制裁制度的合理和有效。”[20]例如,面对一个不满14周岁的人实施的杀人行为,我国四要件犯罪论体系下司法人员可直接从不具有犯罪主体要件的角度进行非犯罪化评价,而其他要件就无需判断,这种方法确实节约了司法资源。但是,它完全忽视了对客观行为判断的首要性,在未进行有无杀人行为的构成要件符合性判断的前提下,直接从主体要件否定犯罪的成立,难以保证结论的正确性。因此,首先应该进行有无杀人行为的认定,要是不存在杀人行为就在构成要件该当性阶段结束犯罪的判断,并且不构成犯罪的原因是不符合构成要件;如果存在杀人行为且没有正当化事由,才能从主观责任年龄的要件否定构成犯罪,此时,是因为缺乏有责性而不成立犯罪。在这种情况下可以适用刑法第17条第4款的规定,即可以责令家长或监护人管教或政府收容教养。但是,在前种情况下是绝不能适用这款规定的。这种以阶层性进行犯罪认定的优点是非常明显的。
另外,需要强调,现在没有人承认客观的、价值中立的构成要件的存在,因此,就不可避免地要对构成要件进行实质性的判断,对此,笔者当然不否认,并且也赞成刑法的客观解释,因此,坚持形式解释论应当坚持在形式判断前提下再做实质判断。根据三阶层犯罪体系,实质判断当属于阻却事由的判断,主要是在法益冲突情况下的实质判断,目的在于寻求违法或责任成立的消极事由。但是,存在这样一种情形:对于刑法没有明文规定的具有严重法益侵害性的行为能否入罪的问题。形式解释论坚决反对实质解释的入罪功能。当然,从罪刑法定原则与人权保障的理念出发是完全可以成立的,但是,面对客观解释强调的刑法解释要结合社会发展和现实语境的观点,刑法解释在符合刑法基本精神的同时又要符合国民的一般观念。因此,笔者认为,在面对人权保障与社会保护的紧张关系时,将人权保障放在第一位的同时也要尽可能地维护两者的平衡,不能偏废其一太多。也即适当承认实质解释的入罪功能,当然,这只是在客观解释下形式解释论的进一步完善。因此,这种入罪的标准或客观解释的限度是不同于实质解释强调的以“处罚必要性和合理性”为入罪标准的,尽管实质解释始终强调这一标准是在罪刑法定原则范围之内,但是这种实质的解释已远远超过了刑法用语具有的可能含义以及国民的预测可能性。所以,实质解释论所坚持的“处罚必要性和合理性”只有独立的出罪的功能。
这里所讲的在形式解释论前提下,不能对一切严重侵害法益的刑法没有规定的行为不作犯罪处理,有时候觉得这种实现法治的代价未免太大。正好客观解释强调国民一般观念,即国民一般预测可能性在入罪方面的意义。因而,首先对构成要件作形式的符合性的判断,在遇到可能的语义模糊的情况下,即如果刑罚法规没有明文形式规定,但根据通常理解,对法益造成了严重的侵害而值得科处刑罚,此时,以“国民预测可能性”为标准对条文可能的语义进行解释,来认定严重侵害法益的行为能否包含在刑法用语可能的含义内,是否超出国民的预测可能性。也就是说,在这种情况下不以处罚必要性和合理性“绑架”刑法用语可能的含义,作实质判断而入罪。因为,以国民一般观念或预测可能性作为刑法用语可能含义的界限可以最大限度地保证刑法规范的形式判断,也能最大限度实现人权保障和社会保护之间的平衡。一般意义上,刑法用语现实发展的含义就是建立在国民认知基础上的,也正是国民对社会生活中各事物不断地认识、进一步地理解推动了现实事物含义的丰富。或者说,在某种意义上,国民的一般观念发展或预测可能性的程度与刑法用语现实含义的变化是同步的。尽管刑法用语含义与现实生活用语的普通含义存在某种差别,但它们之间同步发展的关系是不能否认的。例如,对刑法中“毁坏”一词的理解,无论物理意义还是情感角度的毁坏,无论是刑法术语还是现实语境的理解,都不能将其解释为“被害人对财物占有的丧失(基于被抛弃或隐匿财物)”[21]。这种解释已经超越了国民预测可能性,突破了罪刑法定原则之藩篱,该用语最大的解释范围应该保持在“效用毁坏说”之界限内。
当然,对刑罚法规有明文形式规定,但是明显没有达到值得科处刑罚程度的行为,此时,问题是值不值得处罚。以“处罚必要性和合理性”为准进行实质判断出罪即可。因为这种判断是有利于被告人的实质出罪判断,也是形式解释论与实质解释论共同坚持的,二者在这一点上不存在分歧。因此,在这一点上,笔者并没有完全肯定形式解释论主张的禁止实质判断的入罪功能,也没有完全否定实质解释论者以处罚必要与合理性为由扩大解释。如前所述,我们主张“国民预测可能性”和“处罚必要性和合理性”对刑法用语可能含义的判断上的不同。在形式解释的形式判断的前提下,一方面,承认实质判断的入罪功能,但是要以国民预测可能性为标准,在刑法用语含义模糊时予以判断。也即否认从处罚必要性和合理性实质判断的入罪功能,这一点与形式解释论一致,而保留从国民预测可能性实质判断的入罪可能性。另一方面,对于明显不值得处罚的行为,这本来就是一个处罚必要性的判断问题,理应从处罚必要性的角度进行实质判断而出罪,也即承认从处罚必要性实质判断的出罪功能。这样的解释立场,既在更大程度上保证了对个人自由的保障,也严惩了犯罪,照顾了对社会秩序的维护,又符合当代刑法追求形式理性,致力于实现形式的刑事法治国的阶段使命。
3.2 刑法形式解释立场的合理性
3.2.1 对形式判断与实质判断的不同位阶关系的把握
通过前述争论我们发现,一方面,形式判断与实质判断当属于不同的主体,作为立法者更应该从实质上把握犯罪的本质特征,以法益侵害为指导,通过实质判断,将日常生活中的刑法难以允许的危险行为,从处罚的必要性与合理性考虑而规定为犯罪,即实质判断是一种属于立法者的判断。因为,犯罪是符合犯罪构成的违法类型,刑法具有行为规范的性质,从刑法保护法益的目的角度来看,首先就应当将侵害法益的行为类型明确化,即要让公众事先知道刑法禁止什么,这当然为立法者之任务所为。实质上,立法者在某行为犯罪化的处理上,并不是单纯的描述性的,而必然是掺杂了其价值判断在内,他们描述的是社会上无法容忍的必须要谴责的行为[22],所以以构成要件的形式将这些行为类型化为犯罪行为。而作为刑罚法规的适用者,其适用行为必须建立在刑法已经明文规定的基础之上。也就是说,司法者首先要考虑的是刑法分则条文的具体规定,质言之,司法者首先应当进行构成要件符合性的判断。笔者认为对构成要件符合性的判断就是一种形式判断,但是,这里的形式判断不是实质解释论所批判的、依据条文的“字面含义”的判断,而是建立在立法者对法益侵害行为实质的规定为犯罪的基础上,更多的是在可能入罪的情况下的考虑。同时,我们也不否认构成要件的规范要素的存在,即笔者理解的对构成要件符合性的形式判断并不等于行为构成要件论。我们主张的对构成要件符合性形式判断,是一种类型性的或定型性的判断,旨在维护构成要件的违法推定机能。
另一方面,在罪刑法定原则的视域下,坚持形式判断先于实质判断是罪刑法定原则的必然要求。“罪刑法定原则就要求司法人员只能在形式判断的基础之上才能做实质判断,而不能将实质判断优先于形式判断。”罪刑法定原则也“强调如果法律没有规定无论如何都不能作为犯罪来处理”[18],这里的“法律没有规定”是立法者没有将这种行为描述为侵害法益的犯罪行为,因此,没有立法者的实质判断也就没有司法者的法律适用。只有对刑法明文规定为犯罪的情形,才存在形式的该当性判断的可能,在此之后,通过实质的违法性判断,或者说通过寻求是否有违法阻却事由,来决定对该行为是否认定为犯罪。如果违法阻却事由是肯定的,就没有必要也不可能认定为犯罪。因此,“在罪刑法定原则下实质判断没有独立于形式判断的入罪功能,只有出罪功能”[23]。当然,基于前面论述的强调,以“国民预测可能性”为标准的入罪判断在客观解释下是符合形式解释立场的。因此,形式判断先于实质判断是符合法治的规则理性的,是符合司法的逻辑理性的,也是符合罪刑法定原则之精神的。
3.2.2 对罪刑法定原则形式侧面与实质侧面的理解
笔者认为,罪刑法定原则作为刑法的一个根本性原则,从形式和实质两个侧面对立法者和司法者抑或是对刑罚法规的规定与适用作了规范合理的制约。也就是说,现在没有人只会承认罪刑法定原则只有一个侧面或没有一个形式解释论者只承认罪刑法定原则的形式侧面而忽视实质侧面,只会追求形式正义而忽视实质正义。所以,我们更需要探讨的是,罪刑法定原则的不同侧面是否对立法权和司法权都有限制,笔者在这一问题上坚持形式解释论的观点。一方面,对立法权的限制是罪刑法定原则实质侧面的事。因为,实质侧面强调刑法规定的明确性和当罚性,而这种要求恰好要从处罚的必要性与合理性等实质的角度去把握,如前所述,这项工作也正好是立法者要去做的。换言之,罪刑法定原则的明确性与当罚性要求是针对立法者提出的,因此,实质侧面就具有限制立法权的功能,而不可能无限扩大至对司法权的限制。另一方面,对司法权的限制是罪刑法定原则形式侧面的事。因为,在立法者制定明确正当的刑罚法规之后,司法者只需根据法律适用中的要求,即形式侧面——禁止类推、不溯及既往、排除习惯法、禁止绝对不定期刑——严格遵守已经制定的合理的刑法规范。换言之,司法者没有刑罚法规是否有不当罚的情形存在、是否不明确等的审查义务,他们的任务仅仅在于判断某一案件事实能否适用于该刑法条文的规定,即该当性判断;某一行为是否有阻却违法的事由,即违法性判断;该行为及结果能否归责于行为人,即有责性判断。因此,罪刑法定原则的形式侧面就是对司法者适用法律的要求,也只有限制司法权的功能。
同时,针对前文提到的罪刑法定原则形式侧面与实质侧面的不同价值,笔者认为,罪刑法定原则的形式侧面和实质侧面所蕴含的价值是相同的,因为罪刑法定原则本身就是在限制专横残酷的刑罚以保障人权和自由的背景下形成的,其不同的侧面根本无法脱离该原则最基本的功能,也即两个侧面均具有自由、人权保障的机能。区别仅仅在于人权保障的角度不同,形式侧面更倾向于对司法权的限制或者说是通过立法权对司法权的限制来实现人权保障功能,实质侧面则表现为对立法权的限制,保证刑法的正义性、当罚性以实现人权保障之价值。这两个侧面不同的限制机能在本质上与构成要件的类型化及对类型化的构成要件的解释相互映衬,因此,笔者认为,坚持具有相同价值意蕴的罪刑法定原则不同侧面的不同功能,也有助于实现形式判断先于实质判断的形式解释论。
3.2.3 对刑法漏洞的填补以及扩大处罚范围的态度
针对形式解释论与实质解释论就刑法漏洞的填补以及对扩大处罚范围的不同理解,笔者认为,形式解释论只有在有利于被告人的例外情形下通过解释填补漏洞的说法过于狭窄。现在,无论是形式论者还是实质论者都承认刑法漏洞的不可避免性,主要是由于立法的局限性和犯罪现象的变动性之间的复杂关系引起的。在这种情况下,应该适用类推解释之外的所有的解释方法对刑法漏洞予以填补,除非为类推解释不可,则以立法方式填补。因为,现代社会的变化是飞速的,刑法漏洞的产生和变化也是快速的,用解释的方法填补刑法漏洞有灵活适用性的好处。但是,需要警惕的是,不能陷入实质解释论者声称的以处罚的必要性为指导对刑法用语可能的含义边界来限定。也就是说,实质解释论所主张的实质解释甚或扩大解释外衣下的类推解释填补漏洞的做法不足取。即使他们一再强调其扩大解释是在罪刑法定原则内,但是以处罚必要性和合理性的入罪扩大解释,如后所述,不利于被告人的弊端显而易见。
实质解释论在论述其扩大解释时,以“处罚必要性和合理性”作理论支撑,这主要缘于前田雅英提出了一个实质解释的公式:解释允许范围=处罚必要性/核心含义的距离[24]。换言之,解释的实质的允许范围,与实质的处罚必要性成正比关系,与刑法条文用语含义的距离成反比关系。这个公式所表述的实质解释的理论被实质解释论者广泛引用。张明楷教授将据此公式而理解的含义表述为:“不能只考虑行为与刑法用语核心含义的距离远近,也要考虑行为对法益侵害的程度;因此,处罚的必要性越高,对刑法用语核心距离的要求就越缓和,作出扩大解释的可能性也就越大。”[25]这里,我们非常明显地看出,处罚必要性在实质解释中的主导作用,并且,刑法用语可能含义的范围完全受制于处罚必要性。这样的话,由于处罚必要性判断的强主观性会致使可能的语义范围丧失边界性,会使得可能语义范围“实际上是不断被塑造着的东西,这种塑造是一个永远没有完成的过程”,“如果意欲处罚某种行为,那么该行为就在可能的文义范围内;如果不欲处罚该行为,那么该行为就在可能的文义范围外”[26]。这样,在语义的模糊地带,以处罚的必要性为指导的实质解释就无法保障刑法的明确性和正当性,也无法保证国民的预测可能性。因此,这种不利于被告人的解释对被告人的“不利性”可能会达到很高的程度,甚至直接侵害被告人的权利。
所以,我们认为,一方面,无论是坚持探求立法原意的主观解释还是依据变化了的客观情势进行的客观解释,无论是强调遵循罪刑法定原则的形式解释还是主张以处罚必要性与合理性为指导进行的实质解释,所依据的都应当是刑法条文规范本身,故我们探求的应当是刑法规范视域内的立法原意或可能的客观意思,这样,就应该以刑法规范可能的客观意思为指导对处罚的必要性予以限制。另一方面,条文规范可能的客观意思的理解,我们采用“国民预测可能性说”的基准。如大谷实教授所言:“违背国民预测的处罚是不被允许的……在实质判断之前,应该从具有通常的判断能力的一般人是否能够得出该结论的角度出发,进行形式的判断。”[2]1因为,刑法用语的客观含义随着社会的发展在流变的同时,国民的认识能力也在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变化,甚至可以说,当用语的含义超出其核心意思之时,语义的变化就已经是由于国民的认识所推动的或是控制的,这两种变化具有很大的同步性。故以国民预测可能性为基准理解刑法用语可能的客观意思,并以这样理解的刑法用语可能的客观意思为处罚必要性的根据是可取的,正如有学者指出的“把追求文义作为法律解释的起点和终点”[27]。不仅可以充分彰显刑法作为行为规范的功能,而且,还有助于刑法的明确性与安定性,充分发挥刑法人权保障之功能。据此,我们的结论是,不否认扩大解释,但更强调严格限制刑法的处罚范围,对刑法没有明文规定但实质上有处罚必要性的行为,更倾向于形式解释论的观点,但又对其作了一定的修正,即承认国民预测可能性标准的适当入罪功能。断然否定以处罚必要性和合理性标准的入罪功能,其只有独立的出罪功能。
3.2.4 对刑事法治国模式的选择
刑事法治国出现的标志就是罪刑法定原则在刑事法领域内的确立。罪刑法定原则确立后经历了形式的罪刑法定到实质的罪刑法定的发展历程。相应的,刑事法治国首先要求刑法具有确定性、安定性。对何种行为构成犯罪、应处以何种刑罚首先要有刑法形式的明确规定,这一时期基于形式的罪刑法定原则而强调的是形式的刑事法治国,是对形式合理性的追求。随着罪刑法定原则向实质的演变,实质的罪刑法定要求刑法规范在内容上必须符合公平正义的理念,强调实质的人权保障[14]66。在实质罪刑法定的基础上,强调实质的刑事法治国,追求实质合理性。在罪刑法定理论日趋完善的过程中,学界敏锐地发现无论形式的罪刑法定还是实质的罪刑法定都有自身的缺陷,因此,就出现了相对的罪刑法定。相对的罪刑法定原则是折中了形式的罪刑法定和实质的罪刑法定的合理的一面。换言之,相对的罪刑法定既强调罪刑法定的形式侧面也强调罪刑法定的实质侧面,既要确保刑法规范形式的确定与安定,又要保证刑法规范内容的明确与正当,符合公平正义理念。在这个基础上,有学者提出了“包容性的法治国概念”,即将“形式意义法治国中有助于实现实质意义法治国的理念纳入到实质意义法治国之中”[28]。
虽然,刑法学界对包容性的刑事法治国概念没有明显的论述与推崇,实质刑法观的倡导者刘艳红教授在其论著中提出了“现代社会包容性刑事法治国之建构”的命题[14]95。但是,所述内容是在分析了形式的刑事法治国与实质的刑事法治国的弊端基础之上得出的,尤其是从德国经历了“二战”的惨祸后重新审视其刑事法治国模式的角度论证其主张,具有明显的现代学界主流观点的意味,即坚持形式侧面与实质侧面相统一的罪刑法定和追求形式正义和实质正义统一的刑事法治国。也就是说,对于刑事法治国的模式选择,学界没有主张单纯的形式刑事法治国与实质刑事法治国,而是承认建立在融合形式侧面和实质侧面的相对的罪刑法定基础上的包容的刑事法治国,即形式解释论与实质解论在此问题上并无分歧。但是,这种一致的见解是对我国刑事法治长远或最终要完成的目标的认识。
当代刑法的首要使命在于人权保障。我们从犯罪论体系的发展脉络——客观的犯罪论到引入“主观要素”的犯罪论到后来的目的行为犯罪论体系和目的理性的犯罪论体系——中可以清晰地看到,这种理论上的变化,实际上与刑法人权保障的发展是同步的,或者是说随着刑法人权保障理念的深入发展而推动了刑法犯罪论体系朝着更精细化的方向发展,反过来更加完美地保障了人权。前古典时期,即贝卡利亚所处时代正值欧洲封建专制主义盛行时期,刑罚残酷、罪刑擅断,为了反对封建专制、罪刑擅断,保障公民的自由。从贝卡利亚到费尔巴哈,全部的努力在于完成这一使命:“防止在刑法之外寻找惩罚的根据”也即“古典时期德日刑法学面临的历史使命是解决法外恣意的问题”[13]。这也是古典行为构成要件论得以产生、发展的原因。
随着刑法人道主义理念的进一步发展,罪刑擅断、司法专横遭到彻底的摒弃,对行为的定罪处罚朝着更精细化的方向发展,而这种精细化的任务需要刑法之完美的犯罪论体系完成,因而出现了前述不同的犯罪论体系,以保证罪刑规定的法定化,司法过程的法定化,保证判决结论的正确性与正义性,避免恣意擅断,以最大限度地保障公民的权利、自由。但是,问题是,我国刑法是否已经完全实现了摒弃残酷与擅断刑罚的阶段,或者说我国目前人权保障处于哪一发展阶段。笔者认为,我国正处在一个复杂的转型期,刑法既要全方位地保障人权又要坚决反对残酷恣意的刑罚,也就是说我国处于人权保障的初期阶段,停留在相当低的水平上。并且,由于复杂的社会环境以及理念上的障碍,我们不可能一步到位地将实现人权保障摆在最高的位置。因为,在我国有这样一种现实:司法者司法恣意的观念没有完全摒弃,司法形式理性理念没有普遍建立;国民规范意识淡薄,寻求法律救济权利的观念还没有完全树立;罪刑法定原则没有深入立法与司法中,处于法治不发达阶段。故一方面要确立形式理性,从刑法形式上提供一个正义的、明确的、类型性的判断标准;另一方面,也要重视对实质正义、实质理性的追求。因此,在刑事法治国的目标追求上,不否认最终实现实质的刑事法治国,而是现阶段,我们应该以形式的刑事法治国为基础,通过形式的刑事法治国的实践达成实质的刑事法治国的目标。这样,笔者主张在构成要件的解释上,首先应该保障刑法规范的形式安定性,其次,在形式安定性的范围内实质地判断行为的当罚性。
4 结语
提倡在我国引进阶层犯罪论体系,是刑事法治发展的要求,是认定犯罪朝着精细化方向发展的必然选择。阶层犯罪论体系环环相扣,层层推进的逻辑演进为犯罪的成立提供了科学的依据,对于不构成犯罪的行为也有充分的理由。从该当性的判断起,如果行为不能该当构成要件,则在此阶段就阻却犯罪成立,没有必要再进行后面阶层的判断;如果行为该当构成要件,则继续进行违法性的实质判断,寻求违法阻却事由乃此阶段的核心任务,若是有正当化事由,则行为就不具有违法性,因此,在此阶段就阻却犯罪的成立,也即没有进行后一阶层判断的必要;如果行为该当构成要件,并且没有违法阻却事由,则需要进行有责性的判断,这是一种积极的判断,要是行为人具有可谴责性,则应根据罪状及法定刑的规定,予以定罪处罚,要是不具有可谴责性,则是责任阻却而不能认定为犯罪。这样,就清楚地道出了认定犯罪的谨慎态度和严密的逻辑,有种后一阶段检验前一阶段判断是否正确的意蕴,因此,对于防止认定犯罪过程中的错误也有重要的价值。难怪陈兴良教授说:“阶层体系的判断规制是必须严格遵守并且通过阶层性构造而予以制度性确认的。”[29]
我国现在的平面耦合式的四要件模式,极力主张社会危害性的犯罪成立条件之外的“超要件”性质的作用。社会危害性作为犯罪的本质的观点没有错,而问题是,我国在犯罪成立判断时,将社会危害性放在了四个要件之上,在符合四要件后还要进行有无社会危害性的判断,当然,这种实质的判断一定程度上能够保障罪与非罪或罚与不罚的正确性,但是,这样的判断模式安排会架空四要件在认定犯罪中的作用。另外,对于四个要件的判断,是一种平面式的,尽管有学者从认定犯罪的逻辑或实施犯罪的过程等不同的角度对我国四个要件进行了不同的排列,但是,这种排列更多的是一种形式逻辑上的说明,而不具有认定犯罪的实质逻辑的严密性。也就是说,只要缺少一个要件就不构成犯罪,没有明确的充分的说理。因此,笔者在坚持“形式解释立场”的前提下,欣然接受引入阶层犯罪论体系的主张,并且,认为违法类型的构成要件说更符合现代社会对犯罪的认定,当然,在认定犯罪时坚持该当性、违法性、有责性三阶层的判断步骤。
[1]李海东.刑法原理入门:犯罪论基础[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8:35.
[2][日]大谷实.刑法总论[M].黎宏,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
[3][日]前田雅英.现代社会与实质的犯罪论[M].东京:东京大学出版社,1992:24.
[4][日]前田雅英.刑法的基础·总论[M].东京:有斐阁,1993:37.
[5]张明楷.刑法的基本立场[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137.
[6]阮齐林.新刑法提出的新课题[J].法学研究,1997(5):93-105.
[7]陈兴良.形式解释论的再宣示[J].中国法学,2010(4):27-48.
[8]周祥.刑法形式解释论与实质解释论之争[J].法学研究,2010(3):57-70.
[9]张明楷.实质解释论的再提倡[J].中国法学,2010(4):49-69.
[10]张明楷.刑法学[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7、2003、2007、2011.
[11]陈兴良.刑法知识的转型[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
[12]程红.形式解释论与实质解释论对立的深度解读[J].法律科学,2012(5):79-86.
[13]劳东燕.刑法解释中的形式论与实质论之争[J].法学研究,2013(3):122-139.
[14]刘艳红.实质刑法观[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9.
[15]李立众,吴学斌.刑法新思潮——张明楷教授学术观点探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67.
[16]陈兴良.定罪的四个基本原则[N].检察日报,2009-11-05(3).
[17][日]曾根威彦.刑法学基础[M].黎宏,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5:18.
[18]陈兴良.当代中国刑法理念[J].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08(3):136-150.
[19]周光权.刑法总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93.
[20]许玉秀.当代刑法思潮[M].北京: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05:59.
[21]周光权.刑法各论讲义[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148.
[22]张明楷.犯罪构成体系与构成要件要素[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86.
[23]陈兴良.形式与实质的关系:刑法学的反思性检讨[J].法学研究,2008(6):96-111.
[24][日]前田雅英.刑法总论讲义:第4版[M].东京:东京大学出版社,2001:74.
[25]张明楷.罪刑法定与刑法解释[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68.
[26]许浩.刑法解释的基本立场——对实用主义法律观的论证[J].东方法学,2008(6):137-148.
[27]陈金钊.文义解释:法律方法的优位选择[J].文史哲,2005(6):144-150.
[28]陈新明.德国公法学基础理论:上册[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92.
[29]陈兴良.刑法学:向死而生[J].法律科学,2010(1):18-30.
编辑:余少成
编辑部网址:http://sk.swpuxb.com
The Selection of Theory of Formal Interpretation of Criminal Law——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lass Criminal Theory
ZHANG Xiaowei,LIU Shaobin*
Law School of Lanzhou University,Gansu Lanzhou,730000,China
There have been controversies over formal interpretation and substantial interpretation concerning China’s criminal law interpretation,which originated from the formal criminal theory and the substantial criminal theory in Germany and Japan. Although Chinese scholars emphasized that formal interpretation and substantial interpretation in China are different from those in Germany and Japan in the core elements.In the context of introducing the class criminal theory system,the discussion on the formal interpretation and substantial interpretation should be focused on the elements that constitute a crime.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egality principle,and considering different functions of legislation and law enforcement in the criminal law,and human rights protection,the formal interpretation is more reasonable.Besides,based on objective interpretation,we should amend the emphasis by formal interpretation on excluding all incriminating functions of substantial interpretation,and recognize the incriminating significance of“likelihood of national forecast possibility”.Of course,the position relationship of formal interpretation or form judgment anterior to substantial judgment is based on class criminal theory system.Therefore, the adoption of formal interpretation must be based on three-class criminal theory system.
formal interpretation theory;substantial interpretation theory;legally prescribed punishment;the national forecast possibility;class criminal theory
10.11885/j.issn.1674-5094.2016.08.17.01
1674-5094(2016)06-0057-11
DF611
A
2016-08-17
张晓伟(1989-),男(汉族),甘肃庄浪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刑法学。
刘绍彬(1964-),女(汉族),甘肃兰州人,副教授,硕士,研究方向:刑法学。
——对传统罪刑法定原则分层策略的反思与重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