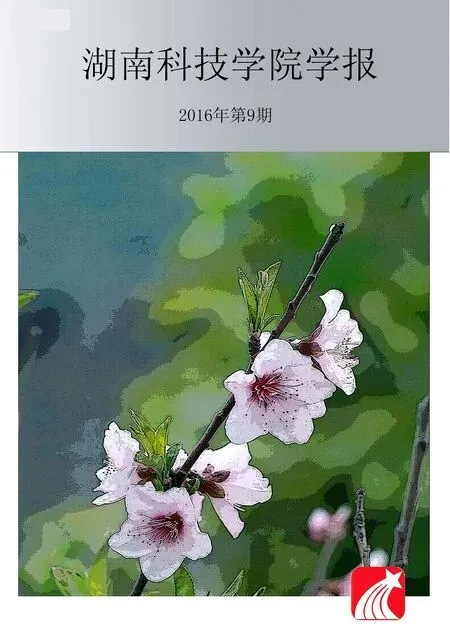略论岑仲勉突厥史研究的学术贡献
舒 薇
略论岑仲勉突厥史研究的学术贡献
舒薇
(上海大学 文学院 历史系,上海 200444)
岑仲勉是我国著名的隋唐史专家,同时也是研究突厥史的大家,《突厥集史》、《西突厥史料补阙及考证》是他研究突厥史的两部代表性著作。论文主要从岑仲勉对沙畹《西突厥史料》一书的补阙和订正,对相关的史实的考订,对突厥碑文的整理,整体研究和系统考订等四个方面论述其突厥史研究的学术贡献。
岑仲勉;突厥史;《突厥集史》;《西突厥史料补阙及考证》
岑仲勉(1886-1961),原名铭恕,又名汝懋,字仲勉, 广东顺德人。早岁在海关、铁道、盐运等机关任职,40岁左右始专心于治史,1937年在陈垣推荐下入中研院史语所任研究员,人生经历与满腹学问俱奇,被称为大器晚成的史学家。其于史学考证,有《两周文史论丛》、《墨子城守各篇简注》、《隋书求是》、《通鉴隋唐纪比事质疑》、《唐史余渖》,散篇则多收入《岑仲勉史学论文集》;于金石铭刻,有《郎官石柱题名新考订》、《金石论丛》;于边疆史地,有专著《突厥集史》、《西突厥史料补阙及考证》、《汉书西域传地里校释》、《佛游天竺记考释》、《黄河变迁史》,论文汇辑为《中外史地考证》;于诗文别集,有《唐人行第录》、《读全唐诗札记》、《读全唐文札记》;晚年据讲义编定通贯性的《隋唐史》。在史学方法上,探究史源,校其异同,辨其正误,补其缺略。学术界对岑仲勉的研究多集中在其唐史领域,本文将重点介绍其突厥史研究的学术贡献。
突厥作为我国古代活跃在北方草原上的一个强大的游牧民族,其兴衰与中原密不可分,对中国和中亚乃至世界的历史都曾经发生过巨大的影响。整个突厥汗国时期,突厥本民族并没有产生本民族的历史著作,对突厥史的研究,主要借助于汉民族史书的记载,如:《隋书》、《周书》、《北史》、《新唐书》、《旧唐书》中的《突厥史》,以及《资治通鉴》、《文献通考》、《唐会要》、《通志》、《通典》等书籍中的相关记载,包括一些文人僧人的游记杂文等等。
沙畹一书对于突厥史的研究实有重要意义,时至今日仍备受好评,但不可否认其书在史料、体例等诸多方面均存在着不足。首先汉文史料选择狭窄,以《册府元龟》和两唐书为主要史料;二是缺少“史料编年”,使得全书最后的西突厥史与前文似乎脱节;同时考证方面不尽详尽。岑仲勉为补沙畹一书的阙漏,以《西突厥史料》为基础,进行了考证和完善,写成《西突厥史料补阙及考证》。
由中华书局1958年出版的岑仲勉的《西突厥史料补阙及考证》、《突厥集史》二书,是中国学者整理突厥史料的代表性著作,两书耗时二十余年,在突厥史研究领域做出了开拓性的贡献。本文拟对岑氏研究突厥史的具体贡献略作分析。
一补阙和订正沙氏一书
较之沙书,岑氏的进步,第一也是最重要的是编撰史料编年。沙畹一书由于缺少“史料编年”,使得全书最后的西突厥史与前文似乎脱节,而岑氏所做的工作,将史料编年详细叙述,使得历史脉络和全貌更好的把握。岑仲勉注重经世之学,在史源考证方面,“创根问底”,考辨源头,“竭泽而渔”,遍搜相关史料,判别异同,判断史料等次,将史料进行对比归纳,找出史料背后的“真实”。
岑氏《西突厥史料补阙及考证》一书自序中说:“至本篇所补,专在编年。除去隋书、通典(太平寰宇记略同)及两唐书内西突厥专傅,与夫沙氏书元龟部分之正文,不复移录外,凡史部石刻有涉西突厥之时间性材料,均一一采撷,编附适当或相近之年份。如取舆前数者台观,汉籍中之西突厥遗闻,相信已得什九已上。补阙部分遇有疑难时,均就所见附加考证。惟较为复杂之问题,则另作专篇讨论。”
在史料编年摘录的基础上,在《突厥集史》中,他重新梳理了历史的脉络,按时间顺序为我们展开历史的全貌,遇有异议的史实,岑仲勉分条摘录,且附有论文来论证。《突厥集史》上册编年按照时间顺序展现了突厥兴亡的全过程,卷一编年起西魏大统八年,讫北周大象二年;卷二编年起随开皇元年,讫仁寿四年;卷三编年起随大业元年,讫大业十三年;卷四编年起唐武德元年,讫武德九年;卷五编年起唐贞观元年,讫贞观十二年;卷六编年起唐贞观十三年,讫贞观二十三年;卷七编年起唐永征元年,讫弘道元年;卷八编年起唐嗣圣元年,讫长安四年;卷九编年起唐神龙元年,讫开元十年;卷十编年起唐开元十一年,讫天宝十四载。史料编年补阙以及突厥史编年,对于我们整体把握突厥的历史有很大的帮助,通识突厥史方便了进一步研究的可能。
在编年之外,岑仲勉对相关的史料按照主题分类,将史料汇集在相关主题之下。沙畹一书汉文史料选择狭窄,以《册府元龟》和两唐书为主要史料。当然作为外国学者,对中国古籍史料的情况不甚熟悉是可以理解的,但即使是这三本史料,沙畹亦未穷尽。而岑仲勉将正史、文集、典籍、碑志、石刻各类史料中与突厥相关的内容都几乎穷尽摘录,分门别类进行整理,其用功之勤,实在为后来学人佩服。史料的分类大大方便了存疑史实的辨伪,岑仲勉两书后附的论文中所考证的问题,多来自前文史料整理时所发现的异议。
对沙畹的一些错误观点,予以考证和反驳,譬如西突厥究竟在何时分立的问题上的论述。岑仲勉首先介绍了“西突厥”、“北突厥”、“东突厥”三名,皆我国史家为求语意明了而创立,并非之自号如此。“处西方这既称西突厥,于是处东方者唐人或称北突厥”,“突厥居我之北,曰北突厥者,显就我国与彼之地理关系而立言。若西之自然对象应为东,故唐以后作家又立东突厥之别名。”[2]107随后,既然西突厥本由东突厥产生,那么两者间的政权分割始于何时。
新课程改革下的高中物理教学不再是教师一个人完成的教学活动,在课堂中更多是突出了学生的主体地位.在物理实验课程中,学生是实验的实际操作主体,在实验过程中,学生能都独立思考实验步骤和实验过程,从而得出实验结果,可以通过反复的实验验证自己的猜测,培养自身独立思考物理的能力.学生在自身实际操作过程中还可以发现问题,对于自己操作过程中的不足之处能够及时的发现和弥补,不仅能够有效地掌握相关的知识,更能够不断的提升自身的实际操作能力.
关于突厥分裂的史料众多,沙畹认为是由于沙钵略和木杆不和,因而分立为东西突厥。沙氏此说来源于《册府元龟》,岑仲勉追溯史源,发现《元龟》错误引自《旧唐书》,《旧唐书》以“木杆与沙钵略有隙”,因而分出了东西突厥,以木杆可汗为突厥之始。但是,更多的史料证明,木杆可汗在位时间为553-572年,而沙钵略在位期间为581-587年,两个可汗不在同一个时代,因此更谈不上“有隙”的问题,此说当然不能成立。岑仲勉根据《隋书》和《新唐书》相关记载,考证得到东西突厥分裂源自大逻便(木杆子)和沙钵略不和。
《新唐书》为后出之书,能根据更多材料,对上述诸说有所匡正。据《新唐书·突厥传》记:“西突厥其先纳都陆之孙吐务,号大叶护,长子曰土门伊利可汗,次子曰室点密,曰瑟帝米。瑟帝米之子曰达头可汗,亦曰步伽可汗,始与东突厥分乌孙故地有之。”即到达头时就有了西突厥。沙畹认为:“当士门、室点密之时,突厥实已分为二支”,“东西突厥之分,固始于六世纪中叶,(即土门、室点密时——引者),然政治之分立,得谓其实完成于582年(即达头可汗时——引者)也”,即沙畹认为东西突厥分裂于582年。但岑仲勉称“余则未敢苟同”,指出当时突厥其仍在西征黯戛斯、突骑施和索格底亚,自然不会分裂“西突厥之完全分立,应以大业六、七年(611-612)射匮继位之时为准”。所以岑仲勉根据《通典》得出结论,认为东西突厥分立于611年或612年。
二考订相关史实
沙畹一书在考证方面不尽详尽,而这一部分正是岑仲勉治史用力最勤之处,成就斐然。《补阙》一书中对西突厥治下的西域相关地区,岑仲勉对西域各国和羁縻府州进行了考证,如:西突厥以何时分立,从西史及突厥语推出室点密汗之尊号,西突厥世系考,证明东突厥处罗侯汗死于西征波斯及昭武即叶护之异文,唐代十六国羁縻府州数,西域十六国都督府州治地通考,曲氏高昌补说,庭州至碎叶里考,弓月之今地及其语考,处月处密所在部地考,嚈哒国都考,羯师与赊弥今地详考,黎轩、大秦与拂壈之语义及范围,曲氏高昌王外国语衔号之分析等。
岑氏《突厥集史》下册则为突厥本传、突厥部族传记以及汉文、突厥文之碑铭的校注以及相关人物的传记和碑志的考证。并附译文和论文多篇,足供研究突厥史者参考。在论述突厥本土生活的时,岑仲勉细致考订了周人和突厥民族文化、习俗的相类之处,分为封建、“族”之意义、事火、十二属、指天社誓、数名之万、尚九、殉葬、赘面、收继婚、半子、尊号、色尚蓝、铁之名称、地域观念、方向尚东等众多相同或相类似的方面,为我们展示了真实的突厥生活的风貌,揭示中华民族和突厥的密切关系。
在一些史实的论证上,岑仲勉不迷信权威,将史籍中有错误和出入的记载,通过详细的比对和考证,严密论证,得出自己的观点,还原历史的真实。如,《通鉴》开元八年下记暾欲谷掠凉州契苾部而去,结语谓“毗迦由是大振,尽有默啜之众”,马长寿以为“此结语恐不适当”,甘凉二州回纥等部不堪王君奂的压迫,北奔突厥,“直至开元十五年始可云苾伽‘尽有默啜之众’”云云。按开元十五年北奔的部落似只是抗拒的一部,所以元和时代境内还有契苾部流浪;唐末甘州回鹘之立国,也就以开元前住落此一带之部落为骨干(参看《东方杂志》四一卷一七号拙著误传的中国古王城),河西的铁勒并未扫数退回漠北。何况此种部落在太宗、高宗时已住落我国,还在默啜之前,非默啜当日所能统治,根本上不能说是“默啜之众”呢!
再有《周书》突厥传记他钵可汗说:“但使我在南两个儿孝顺,何忧无物耶!”《隋书》突厥传改作“我在南两个儿常孝顺,何患贫也!”《通鉴》一七一采用了隋傅的句语,胡三省注:“在南两儿谓尔伏、步离二人,所部分西北,皆南近中国。钱大昕通鉴注辨正二驳之,已引见周传校注。岑仲勉指出马长寿独谓胡注“此说似较允当”,是不可不加以讨论的。随后详细分条来论述自己的观点:(一)北族对侄、甥舆子辈之间,亦有区别。(如凶阙特勒碑云“朕昆弟、姊妹之诸子及朕诸幼王子。”)据隋傅,尔伏统东面,步离居西方(胡注:“所部分西北”是错的,应言“分东西”),皆他钵之侄,今说“两个儿”,究有不合。(二)他钵辖制全国,分藩之贡献,是部族制度本分事,不应作“但使……”“常……”之不定语气。(三)分统东西则茌方位为两翼,今日“在南”,于位置上说不过去。(四)最要是周傅所用之“物”字,隋唐时代对外之赏遗,常曰“赐物”若干,“物”均指丝织品而言。此外如隋文帝诏:“因入贼之物,加赐将士”沙钵略表;“此国所有羊马,都是皇帝畜生,彼有缯彩,都是此物”(以上二事均见《隋书》);创业起居注一:“义士等咸自出物,请悉买之(马也),”李大亮疏:“每见一人初降,赐物五匹。”(《旧唐书》六二。化龙池本《太平寰宇记》“物”作“绢”。)贞观廿一年六月诏;“知见在没落人数,舆都督相计,将物往赎”(《全唐文》),用法无不如此。至于“畜牧部落的首领,主要是以马回赠”(同前引《考古学报》四三页),可见“何忧无物”的话万万不适用于尔伏二人。(五)在记述他钵的话之前,周传说:“朝廷既舆和亲,岁给缯絮锦彩十万段……齐入惧其寇掠,亦倾府藏以结之,他钵弥复骄傲。”隋傅亦云:“周、齐争结姻好,倾府藏以事之,佗钵益骄。”其舆他钵的话互为联结,文甚显然。马氏书亦尝注重周、齐两方之馈送,估计每年至少有丝缯二十万段。倘依胡注立解,颇嫌自不呼应。(六)原夫胡氏立说,或因“儿”字难解,亦许反抗外人之蔑视,然而无可疑也。游牧部族之习惯,势优者对势劣者常以父辈自居,故唐太宗说延陀父事我,默啜请为武后子,毗伽认玄宗为父,毗伽死,伊然继位位,玄宗敕书依旧称为儿可汗。他钵视周、齐如两儿,无非当日争事突厥所致。
通过前面六条的论证,岑仲勉得出结论:“综此观之,胡注不可信据也明矣。这一段辩论并不是咬文嚼字的考证,而是反侵略的重要问题。唯其突厥初时凭藉优势,对北朝东西两方,采取渔人态度以实行侵略,才迫使我国不能不急图自卫,而印起隋文帝施行反间、唐太宗擒伏颉利等一串连事实,并非隋、唐敌视突厥帝国之形成,加以破坏。倘照胡氏解释,则蒙盖了突厥当日对华之野心,抹煞史实,是非不明,使沙畹责备隋、唐之谰言,得以朦混世人耳目矣。”[3]
三对突厥碑文进行整理
岑仲勉对突厥碑文进行整理,包括突厥文墩欲谷纪功碑、突厥文阙特勤碑、突厥文毗伽可汗碑三种,都是逐面逐条的注释改译。征订了如梅禄、匐、颉跌利施可汗、曲漫山、婆葛、失毕等语的对译。岑仲勉广泛应用对音方法考订边睡外域古地名,对音方法虽不十分可靠,但先生的考订极少穿凿附会,其原因在于先生通英文、法文、日文,又能藉助于工具书求出突厥语、吐火罗语中的语源和语意。[4]岑仲勉借助此法,用突厥石碑与唐代旧译对比,依据外文释读,逐字逐句翻译,再次基础上借助大量史料进行考证,从而整理出这三种碑文,为突厥史的研究打开了新的局面。
试举岑仲勉翻译的突厥文阙特勤碑为例。731年(开元十九年)三月,征战一生的伟大的突厥英雄、突厥毗伽可汗的胞弟左贤王阙特勤去世,年仅47岁。唐朝派金吾将军张去逸等送唐玄宗玺诏前往吊奠,并为他立祠庙,刻石为像。732年(开元二十年),毗伽可汗立《故阙特勤碑》,碑文由突厥文和汉文书写,其汉文碑铭由唐玄宗“御制御书”。碑分大小2块,为大理石制,至今仍矗立在蒙古国鄂尔浑河流域和硕柴达木。阙特勤碑对研究古代突厥史具有不可替代的极其重要的价值,同时也是中国与突厥友好关系的见证。史书记载,开元十五年(727年)秋,吐蕃写信给突厥毗伽可汗,约他一起侵扰唐边境,毗伽可汗不但予以拒绝,并且将吐蕃的来信送交唐朝,唐玄宗很赞许毗伽可汗的友善,在长安紫宸殿设宴款待来送信的突厥大臣梅录啜,又允许在朔方军西受降城设立互市,每年以布帛数十万匹与后突厥交换军马,以壮大骑兵队伍,并改良马种,从此中原的马匹更加强壮。
阙特勤碑阴侧三面为突厥文,碑文是以毗伽可汗的口气写的,表现了毗伽可汗与其弟突厥左贤王阙特勤的深厚感情,文中写道:“如阙特勤弗在,汝等悉成战场上的白骨矣。今朕弟阙特勤已死,朕极悲惋。朕眼虽能视,已同盲目,虽能思想,已如无意识。”“阙”是人名,“特勤”是突厥贵族子弟的封号。阙特勤碑汉文和突厥文内容有所差异,汉文碑文重点强调唐朝与突厥的友好关系,突厥文碑文则以缅怀阙特勤一生的功绩为主,对中原汉人有很多不实的描述,多用训诫、劝告的口吻提醒突厥人对汉人要保持警惕。碑文的翻译对我们理解当时的史实和突厥与中原的往来具有重要意义,岑仲勉先生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四整体研究与系统考订
中原和突厥长期存在着联系,所以拥有大量的突厥汉文资料,但由于突厥族存在的时间跨度长且地域跨度广,导致史料分散且错讹极多,这些都增加了突厥史研究的难度。而岑仲勉能够超越前人,勤勉治学,将东西突厥联系起来,进行整体研究,对突厥史汉文资料做系统的考证、整理,为后人研究突厥史铺平了道路。
岑仲勉先生在《突厥集史》一书中总结到:“《突厥集史》稿大致写定于十年以前,因行将付排,再作一回总校,间有零零碎碎的见解,插补不便,故掇拾而成此编后之记。我之研究突厥史,西突厥史既略试问津,如不兼明东突厥的情况,则得其偏而缺其全,寻其流而昧其原,未免陷于一知半解。”[5]3此是为准确而全面的把握突厥的历史全貌而做,沙畹所做的《西突厥史料》只是注重西突厥的历史,而忽略了西突厥本来就是从东突厥中分裂而来,所以研究西突厥史必须先通东突厥史,这样才可以避免在研究中犯偏概全的错误。
《突厥集史》一书,研究对象是将整个突厥汗国都纳入研究范围,包括东突厥、西突厥和后突厥。该书广泛辑集散见于大量汉文古籍中的有关突厥的史料,汇集了正史、文集、典籍、碑志各类史料中与突厥相关的内容,包括正史中的突厥本传、与突厥关系比较密切的其他诸部落的传记、突厥人的碑志、列传等等。此外,还收载了古突厥碑铭的汉译文,以及外国学者的论著选译。岑仲勉对突厥史的系统研究对于我们整体把握突厥的历史有很大的帮助,方便了进一步研究的可能,为后来的学者指明了方向。
[1]刘斌.《西突厥史料》与《新唐书》“西域史料”的关系[J].沧桑,2013,(2):45-47.
[2]岑仲勉.西突厥史料补阙及考证[M].北京:中华书局,1958.
[3]岑仲勉.突厥集史·编后再记[M].北京:中华书局,1958.
[4]邢玉林.潜精治史著作等身的大家岑仲勉[J].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2,(4).
[5]岑仲勉.突厥集史·再版后记[M].北京:中华书局,1958.
K27
A
1673-2219(2016)09-0042-04
2016-06-24
舒薇(1992-),女,湖北黄冈人,上海大学文学院历史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隋唐史。
(责任编校:张京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