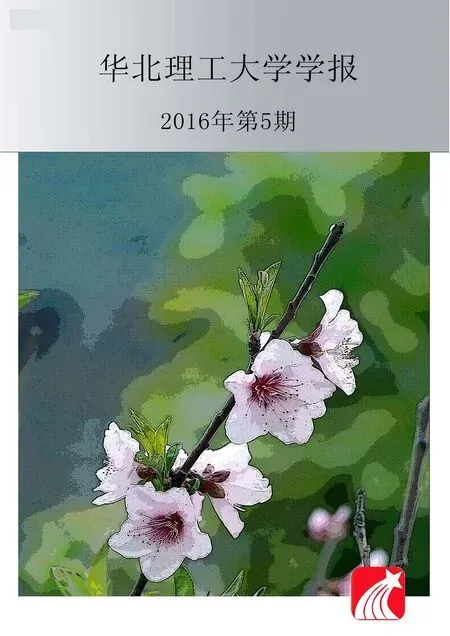近二十年清末民初侦探小说翻译研究回顾与反思
党莉莉
(西北师范大学 外语学院翻译系,甘肃 兰州 730070)
近二十年清末民初侦探小说翻译研究回顾与反思
党莉莉
(西北师范大学 外语学院翻译系,甘肃 兰州 730070)
清末民初;侦探小说;回顾与反思
清末民初的历史特殊性,其时侦探小说翻译的风靡,都曾经引起诸多学者的关注。本文通过回顾近二十年已有研究成果,反思其不足,以期对未来以全球化进一步推进,翻译学蓬勃发展,尤其是中华文化走出去的背景下的相关研究有所启示。
随着国家“中华文化走出去”方针的提出与推行,翻译的文化传播使命在国内引起了前所未有的关注,而关注的焦点较多地集中在汉译外领域,这当然在所难免,而且其中一部分的研究成果的确给我们很多启示:从中译外人才的培养,到中译外翻译模式(比如汉学家翻译,或与汉学家合作翻译),到中译外作品出版市场研究,再到中译外翻译政策的制定都取得了一定的成果。然而,如果能换个角度思考问题,或许我们在翻译与文化传播方面获得的启示会更多、更全面。
如果说翻译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相伴相生,外译中的历史同样可以揭示翻译与文化传播的一般性与特殊性。然而,可惜的是,我们目前对于外译中历史的研究仍然主要局限于目的语文化视角的范围。就清末民初侦探小说翻译的研究而言,首先,清末民初对于中国的历史特殊性是众所周知的;其次,侦探小说作为一种通俗小说在当时的广泛传播的缘由或许还有不同的阐释。由此,本文力图通过对近二十年已有清末民初侦探小说翻译研究的回顾,一方面从其中总结有益的经验与结论,另一方面从源语文化传播的角度对其进行反思,以期对未来的相关研究有所启示。
一、清末民初侦探小说翻译研究回顾
笔者通过对已有相关材料的整理,认为近二十年来关于清末民初侦探小说翻译的研究,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
(一)侦探小说翻译热潮的原因研究
侦探小说翻译热潮的原因探究方面,按时间倒叙整理如下:
在袁进2013年主编的《中国近代文学编年史:以文学广告为中心 1872-1914》中,刘云指出侦探小说,尤其是福尔摩斯系列翻译广受欢迎的原因在于侦探小说代表了现代化的科学态度、理性思维、法律观念,而这些都是当时中国所缺乏的[1]311-315。
任翔讲到中国侦探小说发生的背景时,从现代文化消费市场的初步形成,城市化的现代进程,行政及司法制度的变革以及当时社会思潮的主流趋向四个方面进行了论证,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侦探小说译介的背景。而在具体讲到西方侦探小说译介热潮是中国侦探小说发生的内在动因之一时,任翔除提到西方侦探小说的“千变万化”, 中国侦探小说的“缺失”等促使该译介热潮的原因之外,还特别提出了“西方侦探小说隐含着诸多的人文意趣”。[2]211其中包括:“神学的意境”、“哲学的意蕴”、“文化的意味”和“符号学的意义”。关于中国侦探小说的民族土壤时,任翔提到侦探小说与公案小说不但“形似”而且“神似”,同时,两者同属“乐感文化”。袁进认为,由于破案题材相似,公案小说有助于中国人接受西方侦探小说。同时,侦探小说较强的娱乐性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但更重要的是:“中国社会最初对侦探小说的接受,其实与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过程有关,与知识分子和市民阶层接受新意识形态有关”。[3]68这里的新意识形态指侦探小说中的人权思想和科学观念。
袁荻涌认为19世纪末开始的侦探小说翻译热原因在于改良运动没落,读者对政治小说生厌,而侦探作品趣味性强,与公案异曲同工,加之其异国风情和对实地调查、细致观察、应用理化、医学知识、归纳、分析、推理的重视等也符合“思变求新”社会心理,同时,侦探小说翻译对浅近文言和白话采用也使译文更通俗易懂。[4]范荣指出晚清公案小说的缺陷与域外侦探小说的兴起是有因果关系的。首先,公案小说叙事内容“科学精神”匮乏。其次,公案小说叙事模式缺乏“故事悬念”。[5]
杨义谈到:除了资本主义在中国抬头和与公案和武侠小说相通之外,更重要的是学习西方的尊重法律、尊重科学,抨击中国讼狱制度的黑暗。同时,侦探小说的“艺术构思”也有过人之处。再者,中国文学中没有侦探小说这一体裁也是一个原因。[6]冯奇,傅敬民,苗福光2009年编著的《外语教学与文化 6》中,修文乔认为当时的侦探小说翻译之所以流行,是因为,首先,侦探小说契合改良政治、启迪民智的主流意识形态;其次,当时中国的商业都市和市民文化为侦探小说提供了生存环境;再次,文学期刊、出版机构等起到了促进作用;最后,侦探小说是情与智很好地结合,符合国人的期待。[7]
张彩霞等提出:清末民初侦探小说受欢迎的原因除了当时中国社会不安定,而侦探故事的主人公不但维护法纪,而且有现代科学的查案方法这一好的外部接受环境外,还与晚清译者翻译时在文本内、外对原文进行“自由”操控有很大关系:文本外的序、跋与文本内对原文从内容到形式上“增”、“删”、“改译”,都是为了避免与传统规范正面冲突,迎合读者的欣赏和审美情趣,以免影响侦探小说教育功能的发挥。[8]。
邹白茹谈到了晚清西方侦探小说风行的三个原因:即“西学东渐”的文化大环境,侦探小说本身的文化内涵和价值导向和清官情结这个文化土壤和心理基础的存在[9]。
张昀从以下几个方面论述了这次侦探小说翻译热潮的原因:当时侦探小说在世界各地的普遍受到欢迎;西方侦探小说翻译负载着“启发民智”的历史使命;同属探案题材的侠义公案小说的流行为侦探小说的输入做了很好的铺垫;作为“赞助人”的个人和团体包括提倡小说界革命的文学家、理论家以及当时的出版机构,与他们相联系的稿酬制度,对商业利润的追逐,读者的热捧等等都进一步促成了该次侦探小说翻译热潮[10]。
在季进2004年编《未完成的现代性》所收《福尔摩斯在中国》讲演中,李欧梵则从福尔摩斯的背景讲起。他指出福尔摩斯的作者柯南﹒道尔体现了维多利亚时代基于理性和科学的实证精神。在19世纪末叶的英国通俗小说的黄金时代,柯南﹒道尔使维多利亚文学中的侦探文学臻于顶峰。至于福尔摩斯其人:一方面其生活习惯和价值系统上是百分百的维多利亚式的英国人,另一方面,其性格有孤僻、吸毒等非理性的一面,这种双重人格吸引着读者。李欧梵接着谈到了福尔摩斯在中国。他认为,福尔摩斯探案的翻译和晚清小说的发展同步,从实践来看,侦探小说译者们往往假“教化”之名行“娱悦”之实。而福尔摩斯系列最引人之处在于其主人公,因为他是当时中国社会需要的“新”人物,同时,公案小说福尔摩斯探案题材提供了“文类”的土壤,而清末以上海为代表的都市文化需要新英雄[11]。
李德超与邓静则从篇内特征和篇外因素两个方面分析了此次翻译热潮的原因。篇内特征方面,内容上外国侦探小说新颖、充满悬念,译者的归化手段,其中的现代科学知识,客观分析、推理和科学知识的运用等是重要原因。结构上,第一人称叙事方式、倒叙、心理描写等带来了全新的阅读体验。篇外因素方面,清末民初中国传统文学体系行将崩溃,新文学体系又尚未完全确立,并且小说在中国传统文学多元体系中一直处于边缘地位,加之“小说界革命”极大冲击了以诗词曲赋为文学正宗的传统文学体系。另外,与为数众多的刊物和出版机构作为真正的“赞助/赞助人”相联系的商业利益和稿费制度都有助于促使该次翻译热潮[12]。
袁荻涌在2002年《二十世纪初期中外文学关系研究》之近代翻译文学概说中认为侦探小说之所以风行是因为:侦探小说情节紧张曲折,与公案小说异曲同工,结构布局巧妙,可供市民阶层消闲;当时的侦探小说译文运用白话和浅近文言,通俗易懂;而侦探小说的翻译和刊载,多为旧派文人及他们办的主张“趣味第一”,着眼盈利的刊物所掌握。在同一本书中,讲到西方侦探小说在近代中国的传播时,袁荻涌认为:侦探小说流行主要与当时的社会、历史、文化相关。首先,1908年左右改良主义运动没落,思想文化界复古,阅读极具趣味性的侦探小说可以暂时逃避现实、获得一定审美愉悦;其次,近代侠义公案小说的流行为其奠定了基础,侦探小说的异国风情和科学理性,又能契合清末“思变求新”的社会心理;再次,侦探小说有独特的艺术魅力和较大的娱乐价值,属于乐感文化;此外,译文采用了浅近文言和白话[13]。 张萍联系中国近代社会巨大改变和小说成为思想启蒙的有力工具,认为由于侦探小说体现了公平法治,能够启迪民智,并且雅俗共赏,因而成为翻译作品的主流[14]。
任翔在2001年出版的《文学的另一道风景:侦探小说史论》中则指出西方侦探小说在近代中国的译介热潮,是在内忧外患中,国人向国外寻求救国的方法,文学界出现译介国外作品热潮,而当时的外国侦探小说已经较为丰富和完善的状况下开始的。至于侦探小说风靡的原由,任翔认为:首先,辛亥革命失败后,国人反感维新思想,侦探小说体现的科学精神等可以使国人暂时逃避现实,又契合渴望文明的心理。其次,近代侠义公案的流行为其传播奠定了基础。侦探与侠义公案相似,而其异国风情和科学理性也符合“思变求新”心理。再次,侦探小说具有独特的艺术魅力和较大的娱乐欣赏价值,属于乐感文化,符合中国人的审美心态。此外,浅近文言和白话译文也加速其流传[15]。
武润婷论及《侠义公案小说向侦探小说的演变》时提出侦探小说1907年后达到高潮,首先和中国刑律改良有关,庚子之变后,清廷就有对刑律的改良,表明了当时中国社会的需要,而侦探小说正好迎合了这一需要。其次,侦探与公案有相似之处,但情节更生动曲折,同时也是国人了解西方社会生活的一个窗口,深受广大民众喜爱[16]。
汤哲声在1999年出版的《中国现代通俗小说流变史》中指出:侦探小说在清末民初得到青睐与当时的政治思想背景、文化传统、阅读习惯、译者趣味等有很大关系。侦探小说作为科学民主的文艺作品,对处于思想变革之中的中国作家而言,包含了法治、科学实证、人权等当时所需的“西洋文明”。而侦探小说层出不穷的的情节符合中国读者由“奇”出“正”的阅读习惯。侦探智慧、勇敢的形象则满足了市民读者对社会秩序的向往和好奇心。另外,正是接受者的需求和作品对接受者所产生的影响,决定了当时译家和作家对原作的评定与选择[17]。
郭延礼谈到侦探小说受人欢迎的原因时,首先指出了它的社会原因,二十世纪初进一步的殖民地化和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发展,促进了中国都市化,市民阶层增加,培养了大批侦探小说读者。从侦探小说本身来看:第一,侦探小说描写的犯罪问题是人们所关注的社会问题的焦点之一,一方面可以满足人们揭开社会生活中秘密的好奇心,另一方面在内容上与侠义公案小说有相通之处,为当时读者乐于接受。第二,侦探小说中塑造了典型的艺术形象。第三,侦探小说故事情节起伏跌宕。第四,侦探小说体现了超人的智慧。另外,侦探小说在倒装叙事和第一人称叙事法上也是一个原因[20]。
(二)侦探小说翻译对中国文学和社会的影响研究
该方面的研究往往将侦探小说对中国文学和社会的影响结合在一起讨论。
金宁黎指出了“福尔摩斯”系列小说对程小青作品人物设置和叙事模式的影响。人物设置方面主要体现在霍桑生活习性、推断力、知识结构的设定在一定程度上受到福尔摩斯的影响。叙事模式方面的影响则主要来自于福尔摩斯系列叙事视角和叙事顺序[21]。
赵利民谈到了域外侦探小说倒叙、第一人称叙事视角对中国小说艺术技巧方面的变革以及对中国小说的通俗化的推动作用[22]。 旷新年指出:晚清翻译文学(包括侦探小说翻译)是以对充分体现了资产阶级现代性的通俗文学的切近为特点的,其中隐含了晚清对于现代性的憧憬及其特定的理解与想象方式,如声光化电、商贾国会和科学民主[23]。在袁进2013年主编的《中国近代文学编年史以文学广告为中心 1872-1914》中,汤哲声突出了侦探小说翻译促进中国小说文体现代化进程的观点,具体表现在福尔摩斯等侦探小说翻译促使中国小说的叙事角度从全知型向半知型过渡,也有利于打破中国通俗小说“史说同质”观念,引入倒叙法[1]370-374。
袁进在《近代中国人是怎样接受侦探小说的》一文中指出:侦探小说不是现实主义小说,但是它作为现代社会的产物,其中体现的科学、理性、逻辑思想等推动了当时人们对现实主义文学的理解[3]。
冯奇,傅敬民,苗福光编著的2009《外语教学与文化 6》中,就接受和影响而言,修文乔认为清末民初侦探小说翻译从对不同叙事时间和叙事角度方面的译介,到引起小说旨趣功能、创作阅读方式的潜在变迁、语言的转变、文体的变异和创作理念的更新都与文学现代化进程的发生联系在一起[7]。
张昀则谈到侦探小说翻译热潮对域外小说在中国的流传意义非凡,对新小说家的创作产生了直接影响,中国本土的侦探小说的创作更是与之休戚相关[10]。
苗怀明指出外国侦探小说的翻译和影响直接促成公案小说转变,法律题材的小说创作“在约一千一百部的清末小说里,翻译侦探小说及具侦探小说要素的作品占了三分之一左右”[24]134,其中以对外国侦探小说叙事方法及结构形式的模仿为主。
季进编 2004《未完成的现代性》所收《福尔摩斯在中国》讲演中,李欧梵在讲到中国的福尔摩斯时认为,相对而言,霍桑及包朗爱国,有正义感,反对迷信,体现了道德和人情高于法律的中国传统。从模仿层次,霍桑则更近似“后殖民”理论家HomiBhabba的“模拟”(Mimicry)。而由于对作为其背景的上海都市文化描绘不够深入,霍桑探案并不成功[11]。
王燕(2003)从四个方面谈到了西方侦探小说译介对近代中国原创侦探小说的影响。第一,从近代侦探小说产生的原因来看,首先西方侦探小说翻译引进一种全新的小说样式,启发了当时的作家。其次,侦探小说翻译培养了一批忠实的读者。再者,受侦探小说在西方风行的影响,当时侦探小说市场运作中的经济利益驱动也是一个原因。第二,从创作观念看,侦探小说的译介,使中国作家在创作之前,就对该文体有了先入为主的接受和理解。他们因而立足于本民族的文化传统,有意识地从侦探的职业和艺术形象、侦探小说的题材类型、叙事风格、写作技巧等方面对中西异同进行了比较。第三,从中国原创侦探小说的创作实践来看,由于创作观念的先行和大量现成范本的存在,中国作家在创作时有意识地摹仿译本作品写作。第四,原创侦探小说的价值定位方面,文体杂糅、创作的机械模仿、侦探形象的单薄以及断案方式的缺乏科学精神等也与侦探小说译介的影响有关[25]。
张萍指出,中国小说家对于西方侦探小说的借鉴和模仿主要体现在倒叙的运用、人称视角的选择、细腻的心理描写、氛围渲染和结构布局等技巧方面。至于清末民初翻译高潮过后,侦探文学的沉寂,张萍认为主要取决于社会历史条件和文化范式的大语境[14]。
袁荻涌在《二十世纪初期中外文学关系研究》中认为:侦探小说为新小说家们在艺术上提供借鉴,对近代作家叙事技巧方面的影响深远;侦探小说翻译还导致中国式侦探小说大量产生,至民国初年出现了黑幕、侦探小说的泛滥[13]。
汤哲声在《中国现代通俗小说流变史》中则谈到了中国侦探小说创作中的译述——根据外国小说的原作为底本边译边作、模仿、侦探与公案杂糅——公案型的侦探小说等问题[17]。
在《等待超越:侦探小说在中国现代文学中》,汤哲声认为侦探小说翻译在促使中国小说从古典型走向近代型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侦探小说中的第一人称叙事、倒叙法促使中国小说的叙事角度逐步地由全知型向半知型过渡,有助于小说家处理好小说中的时空关系。侦探小说中的穿插和补叙也对中国小说产生了影响。而侦探小说之所以有如此重大的影响,是由时代的需要、翻译界的实际状况以及侦探小说所具有特有的文体结构决定的[26]。
谢昕、羊列容、周啓志认为:由于侦探小说形式的引进,叙事顺次上,古代的按自然时序叙事,在近代有了转变,倒叙手法不但为侦探小说翻译家和评论家所关注,而且被侦探小说创作者实际运用;在叙事角度上,侦探小说翻译也促使从全知全能叙事到限制叙事的转变。不过,这种转变在当时并没有形成系统的叙事理论,只代表了小说发展的一种新的趋势[27]。
(三)侦探小说翻译中的中西文化、文学的互动研究
这方面有代表性的观点主要有:
杨一认为,虽然中国本土侦探小说对西方侦探小说有诸多模仿,但是由于被赋予了中国的民族文化,“其本土性内涵却与西方侦探小说的基本原则发生了冲突”。主要表现在“双重标准——道德与法律的冲突”,“血缘关系——家庭同社会的抉择”,和“空间意识——封闭和开放”[28]153-154。由此,杨一指出,清末民初西学东渐中东西观念的交融与对抗,是此消彼长的过程,“排斥、吸纳、变异与自我创造”伴随始终。
赵稀方通过分析吴趼人和周桂笙对《毒蛇圈》的翻译和评点,探讨了晚清现代性的引进及其文化协商的问题,并指出“一方面侦探小说翻译西方法律制度等‘现代性’面向批判中国传统,另一方面又以中国传统出发,选择、改写西方现代性。在这里,翻译成了文化冲突与协商的场所,也成了我们考察中国现代思想生产的线索[29]35。”具体而言,赵稀方的讨论涉及两个层面。从观念层面看,一方面,西方侦探小说代表的现代诉讼程序反衬出中国司法的黑暗,另一方面,传统观念也对西方侦探小说的现代性进行选择和切割,比如《毒蛇圈》的翻译一方面翻译现代性,批判传统,另一方面又以中国传统“孝”的观念诠释法国小说。此外,虽然周桂笙和吴趼人都是西方现代性的向往者,但在翻译和评点时也体现出了两人在对待西方现代性的立场上的分歧。从叙事的层面看,《毒蛇圈》是法国现代小说,却被周桂笙改写成了古典章回体小说,采用了传统小说评点的形式。而对于《毒蛇圈》开头的倒叙结构,周桂笙则在翻译时将其保留并做了介绍。不但如此,周桂笙和吴趼人还运用倒叙进行文体创新。然而“《九命奇冤》虽然模仿《毒蛇圈》,却不是侦探小说,而仍是公案小说[29]43”,因为它缺少民本与司法理念。而到了《中国侦探案》,受清廷的预备立宪影响,吴趼人甚至认为以侦探小说所代表的西方法治批评中国司法腐败是盲目崇外的表现。而周桂笙对于西方侦探小说及其所代表的法治精神则始终持积极态度。
司新丽认为中国侦探小说出现于20世纪初期,在外国侦探小说翻译和本国公案小说的共同影响下产生。正因为如此,中国现代侦探小说与西方侦探小说既有相似性又有差异性,相似性主要在于对法律意识、科学性、民主思想、人权意识等智性的追求,还在于主配角侦探形象的设置、程式化的情节模式和叙述视角方面。差异性而言,由于时代背景和社会状况不同,西方侦探小说娱乐性突出,而中国侦探小说更注重社会教育功能;出于不同的民族文化特征,在题材方面,西方侦探小说更多地关注复杂的社会关系,而中国现代侦探小说更多地关注家庭;由于道德观念的差异,在办案依据方面,西方侦探小说中法律是衡量一切的标准,而中国侦探小说中有法律和道德两个标准,如果法律和道德不一致,法律服从于道德;由于儒家思想正统的影响,在对官方侦探的评价方面,西方侦探小说往往以私人侦探为主导,官方侦探则表现出愚蠢等,中国现代侦探小说既突出私人侦探,也不诋毁官方侦探;由于作家背景不同,西方侦探小说具有严密的逻辑和科学实证,距离平民化较远,而中国现代侦探小说充满着平民色彩[30]。
孟丽从三个方面讨论了国人对侦探小说叙事模式的接受与应变。从叙事结构看情节内容的取舍,张坤德之所以在翻译中完整保留案件侦查过程,舍弃细节文字,并且选择《呵尔唔斯缉案被戕》为首次翻译小说作结,是因为中国读者偏爱故事曲折性,并且中国古代小说往往给每一个人物都设置一个完整的人生轨迹。从叙事视角看译者的署名转换,在翻译四篇福尔摩斯侦探小说时,首先,张坤德将这四篇小说全部标识为笔记作品,是想通过与中国的文言笔记小说的类比, 便于读者接受。其次,翻译之初将小说原作名称标识为故事主人公自撰 ( 即歇洛克呵尔唔斯笔记) , 随后又将故事讲述者题为作者 ( 即滑震笔记) , 则是对原作叙事人称的调整与适应。叙事视角影响下的倒叙手法方面,孟丽认为张坤德经历了从改倒叙为传统的顺叙,采用第三人称叙事视角到保留原作的第一人称叙事,采用倒叙的过程,说明译作者在翻译中逐渐对西方小说中新的叙事策略有了了解。由此可见,西方新的叙事模式的出现并非一帆风顺,但张坤德对西方叙事手法的接受和引入对传统公案小说向侦探小说的转变的推动作用也不容质疑[31]。
(四)侦探小说翻译史料整理
侦探小说史料整理方面,比较有代表性的有:
孔慧怡列出了清末民初福尔摩斯小说的所有译本和译者[19]。 而郭延礼收集的史料除了对福尔摩斯探案系列译本和译者的整理,还有对欧美和日本等国侦探小说的翻译乃至当时的侦探小说翻译家群比较详细的列举与说明[20]。
李景梅与周建华对周桂笙的翻译侦探小说进行了考证[32]。
二、清末民初侦探小说翻译研究的成果与不足
由以上综述可知,近二十年来清末民初侦探小说翻译研究的成果主要集中在对其翻译热潮原因的探讨、对中国文化和文学的影响研究以及翻译过程中西方文化、文学互动研究。其中以对翻译热潮原因的探讨最为突出。整理起来,这些原因可以归为三类:其一,中国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文学等背景,这一类研究多关注当时内忧外患中侦探小说的开启民智功能;其二,侦探小说本身的魅力所在,这一类研究多关注侦探小说的人物塑造、情节安排和叙事技巧。其三,翻译策略与方法,主要涉及从文本外到文本内的归化处理或半译半作的自由化翻译方法。显然,第一类是最重要的原因所在,几乎所有的相关研究都对此有涉及,并且往往构成其研究的主体部分。
而清末民初侦探小说翻译对中国文化和文学的影响研究主要聚焦于对中国小说叙事技巧等方面的影响。
中西方文化在清末民初侦探小说翻译过程中的互动则主要体现在中西文化从思想观念到叙事技巧的互动,很有启发性。
在清末民初侦探小翻译的史料整理方面,孔慧怡、郭延礼等人的搜集则为我们进一步的研究提供了珍贵的资料来源。
总而言之,截止目前,清末民初侦探小说翻译研究从以上四个方面——当然,以上四个研究方面的归类也不是绝对的,事实上他们之间往往有着交叉,只能说某个研究更突出某一个方面而已——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其中一些讨论在方法和内容上也极具启迪性,为我们后来的相关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但是,如果我们透过这些成绩,并以反思的态度接近它们,我们就会发现其中一个共同特征,即所有研究几乎都从目的语文化、文学——清末民初的中国文化、文学——视角出发来探讨清末民初的侦探小说翻译。从翻译研究的目的语文化转向以来,这一路经为我们的翻译研究拓展了更广阔的视野,也使得我们的清末民初侦探小说翻译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然而,翻译研究的历史告诉我们,任何一种研究路径一旦走向滥用,将会造成重复、带来遮蔽,曾经新锐的目的语文化转向也不例外。何况,联系我们这个全球化的世界,考虑到这个消费文化突出的时代,着眼于“中华文化走出去”的战略,我们的清末民初侦探小说翻译研究显然需要同时也可以展现出不同的景象。
[1]袁进主编.中国近代文学编年史:以文学广告为中心 1872-1914[C].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3.
[2]任翔. 文学的另一道风景:侦探小说史论[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 2001.
[3]袁进. 近代中国人是怎样接受侦探小说的[J].艺术评论, 2011(6): 第67-71页.
[4]袁荻涌. 中外文学的交流互润[M].贵阳:贵州民族出版社, 2010.
[5]范荣. 谈晚清公案小说生存危机下的域外侦探小说译介热[J].作家, 2010(24):111-112.
[6]杨义主编. 二十世纪中国翻译文学史近代卷[M]. 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 2009.
[7]冯奇,傅敬民,苗福光. 外语教学与文化 6[C]. 上海:上海大学出版社, 2009.
[8]张彩霞等编著.自由派翻译传统研究[M]. 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08.
[9]邹白茹.晚清西方侦探小说风行的文化解析[J]. 求索, 2007(07):173-175.
[10]张昀. 论清末民初侦探小说翻译热之原因[J]. 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6(2):73-76.
[11]季进编. 未完成的现代性[C].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4.
[12]李德超, 邓静.清末民初侦探小说翻译热潮探源[J]. 天津外国语学院学报, 2003 (2): 1-6.
[13]袁荻涌. 二十世纪初期中外文学关系研究[M]. 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 2002.
[14] 张萍.侦探文学在中国的两次译介热潮及其影响[J].中国翻译, 2002(03):55-57.
[15]任翔. 中国侦探小说的发生及其意义[J]. 中国社会科学, 2011(04): 205-220+224.
[16] 武润婷. 中国近代小说演变史[M]. 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 2000.
[17]汤哲声. 中国现代通俗小说流变史[M]. 重庆:重庆出版社, 1999.
[19]孔慧怡.还以背景,还以公道:论清末民初英语侦探小说中译[J]. 通俗文学评论,1996 (4):24-36.
[20]郭延礼.近代翻译侦探小说述略[J]. 外国文学研究, 1996(03): 81-85.
[21]金宁黎. “福尔摩斯”系列小说对程小青侦探小说的影响[J].作家, 2015(10): 42-43.
[22] 赵利民. 对话与交流:中国传统文学与外国文学关系研究[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3.
[23]旷新年编. 文学史视阈的转换[C].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3.
[24] 苗怀明. 中国古代公案小说史论[M].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25]王燕. 近代中国原创侦探小说[J]. 齐鲁学刊, 2003(2): 114-118.
[26]汤哲声. 等待超越:侦探小说在中国现代文学中[J].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 1996(02): 112-119.
[27]谢昕, 羊列容, 周啓志. 中国通俗小说理论纲要[M]. 北京:文津出版社, 1992.
[28]杨一. 当西潮遭遇中学——从侦探小说看清末民国东西观念的交融与对抗[J]. 山花, 2013(21):152-157.
[29]赵稀方. 翻译与文化协商——从《毒蛇圈》看晚清侦探小说翻译[J]. 中国比较文学, 2012(01):35-46.[30]司新丽.中国现代侦探小说与西方侦探小说之比较研究[J]. 国外社会科学, 2012(03): 129-135.
[31]孟丽. 翻译小说对西方叙事模式的接受与应变——以《时务报》刊登的侦探小说为例[J]. 理论导刊, 2007(11):128-130.
[32]李景梅, 周建华.晚清周桂笙翻译小说考论[J]. 作家,2013(24):174-175.
Review and Rethinking on Study of Detective Novel Translation during Late Qing Dynasty and Early Republic of China in Recent Twenty Years
DANG Li-li
(College of Foreign Languages, Northwest Normal University, Lanzhou Gansu 730070, China)
the late Qing Dynasty and the early Republic of China; translation of detective novel; review and rethinking
Detective novel translation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and the early Republic of China, which is a rather special historic period, has attracted many scholars’ attention. The present article, through reviewing and reflecting on the relevant studies in recent twenty years, expects to inspire future studies on the same subject against the background of further globalization and further development of translation studies as well as the policy of “Chinese culture going global”.
2095-2708(2016)05-0152-07
H315.9
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