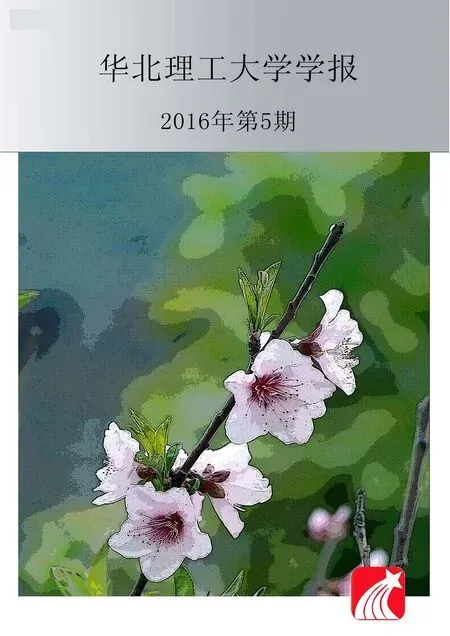《献给艾米丽的玫瑰》的逃逸法解读
康有金,侯雯
(武汉科技大学 外国语学院,湖北 武汉 430065)
《献给艾米丽的玫瑰》的逃逸法解读
康有金,侯雯
(武汉科技大学 外国语学院,湖北 武汉 430065)
《献给艾米丽的玫瑰》;逃逸法;解读
《献给艾米丽的玫瑰》是福克纳最负盛名的短篇小说。“逃逸”是法国哲学家德勒兹创造的最重要的概念,也是重要的文学批评方法。他认为文学创作就是作家寄以逃逸的重要途径,作家通过创作打破精神藩篱,挣脱心理桎梏,并集中体现在他们所塑造的人物形象上。德勒兹哲学视阈下解读该小说可以得出作者通过块茎式叙事与艾米丽的解辖域化、去脸面性和无器官身体,最终令其成就了少数派,制造了与死尸共眠的假象,为有“政治恋尸癖”的小镇竖起了墓碑。
威廉·福克纳是20世纪美国最伟大的小说家之一,于1949年获诺贝尔文学奖。他的作品晦涩难懂,也正因为如此而充满魅力。《献给艾米丽的玫瑰》是他1930年发表的最负盛名的短篇小说。作者成功塑造了美国南方没落贵族之女艾米丽·格里尔森这个艺术人物典型。小说通过颠倒的时间次序和一幅幅真实的画面,以迷宫般的事件展示了艾米丽的一生。对现实生活的变迁视而不见的艾米丽,不顾一切地坚持自己独有的、与世隔绝的生活方式,包括她的爱与恨、倨傲式的高贵和对负心恋人的报复。小说虽短,给读者留下的记忆却很悠长。国内外学者对该小说给予了广泛的关注。国内研究者从话语策略、叙事、意识形态、人际关系、矛盾冲突等多角度多视野对本篇小说进行了解读。国外学者则更加侧重了对模糊叙事、叙事声音策略、叙事时间策略的研究以及针对荷默是否同性恋[1]195-198、艾米丽的黑人情人等具体问题进行的深入探索[2]483-491。
许多人眼中的艾米丽年轻时曾如昙花一现般的风情万种,天真烂漫,对未来充满期盼;当她得知恋人欲弃其而去,便将其毒死,与其骷髅同床共枕四十年。
但这并非作者全部创作意图。换个角度重新解读会有新的发现。在法国后解构主义哲学家德勒兹(1925-1995)看来,文学创作过程就是逃逸过程。他在《谈话》中鲜明地提出了文学创作的最高目标——离开,出走,追寻一条线[3]36。这就是德勒兹哲学视野下的逃逸线,即突如其来的给主体带来本质上转变的途径,通过主体与其他主体之间先前建立起来的模糊关系,为相关主体注入新能量,藉此对外界做出反应和回应[4]145。其晚年重要作品《什么是哲学》的译者称德勒兹为逃逸线思想家[5]viii。德勒兹认同劳伦斯对文学创作是逃离人们的视野进入别样生活的理解,认为文学创作过程就是作者寻求逃逸线的过程[3]36。德勒兹哲学思想为作者和读者提供了不同的“逃逸线”,一项远离人们所熟知事物的活动[6]132。通过创作和阅读,作者和读者都实现了逃逸,发生了蜕变。德勒兹具体细化了一些逃逸方法,主要有块茎,解辖域化,去脸面性和形成无器官身体。
德勒兹哲学思想为人们提供了“块茎”式的叙事方式,通过一次又一次地解辖域化,找到逃逸线,冲出黑洞,线化白墙,拆除“脸”,成就无器官身体,实现欲望的自由流动,找到自由,重拾自我。德勒兹(和加塔里)向人们提供上述四个不同的工具,都是在为人们找到一条或多条物质上或精神上的,身体上的或心理上的“逃逸线”,“逃离”当下限制人们的物质或精神环境。
本文围绕艾米丽与其周边人物的关系,从德勒兹哲学的精神分裂分析出发,用逃逸法解读《献给艾米莉的玫瑰》,由表及里,以见知隐,从已知到未知,探究艾米丽另一种不为人知的真实人生。
一、“块茎”叙事方式与艾米丽的解辖域化
“块茎”是德勒兹最重要的概念之一,是其独树一帜的语言风格的重要标识之一,也是他(和加塔里)所采用的重要论证方法之一。“块茎”没有“基础”,不固定在某一特定的地点,是去中心化和全方位发展的。它不把事物看成是等级制的、僵化的、具有中心意义的单元系统,而是把它们看作如植物的“块茎”或大自然的“洞穴”式的多元结构或可以自由驰骋的“千高原”[7]。块茎的生长遵循六条原则:联系性原则——块茎上的任何一点都能够与外界连接;异质性原则——从块茎脱裂出来的“子体”与“母体”迥然不同;繁殖性原则——块茎从不把“唯一”当做主体或客体;反意指裂变原则——块茎可以碎裂、散播开来,但无论在新旧环境中都仍然能生长繁殖;绘图性原则——块茎的延伸和生长具有绘图性的特征;贴花转印性原则——一个块茎衍生出另一个块茎的过程如同贴花转印,其关系如同两个被转印的贴花[8]7-13。
“兰黄恋”是德勒兹最经典的块茎[8]12。兰花的授粉结种和黄蜂采蜜生存构成了一个天然的块茎。艾米丽与父亲的关系,与包工头荷默的关系,与仆人托比的关系可以看成是本篇小说中的三个“块茎”。艾米丽母亲家族精神病史可能会给艾米丽的后代带来遗传方面的影响,与艾米丽的父亲的拒绝所有艾米丽的追求者,将她牢牢困锁在家中,很少与外界接触,两者构成了艾米丽人生中的转折的第一个块茎——与父亲的乱伦关系;与父亲关系的心理惯性在荷默身上的力比多定位,和作为幌子招牌和障眼以掩盖她与托比之间的关系,构成了艾米丽生活中的第二个块茎——与荷默的暧昧关系;艾米丽要利用托比充当自己与整个杰佛逊小镇斗争的工具,与她必须设法使他长期留在她身边,打赢这场持久战,并对她的一切隐秘守口如瓶,构成了艾米丽生活中的第三个块茎——与托比之间的私情。艾米丽与父亲的关系给她造成了严重的心理与精神伤害;她与荷默之间不曾存在一丝的爱,只是力比多的定位;她与托比之间只是利用和要挟。随着叙事的高潮迭起,小说脱裂出一个又一个块茎,借助这些块茎艾米丽逐渐从原来镇民眼中熟悉的自己开始逃逸,使其人生变得扑朔迷离。
“解辖域化”是德勒兹和加塔里两位哲学大师的哲学核心概念之一。解辖域化就是生产变化的运动。作为一条逃逸线路的解辖域化,所显现的是主体的创造潜能[4]67。通过逃逸,主体离开旧有环境进入全新领域,通过创造出新的环境发掘出自身的潜能。解辖域化是把主体从限制其加入新的组织机构的各种固定关系中挣脱出来的过程[4]67,是主体为摆脱某种限制、压抑和桎梏,主动的挣脱行为。它从来都不是外在力量强加给主体的行为。解辖域化也是一种行动,主体通过这一行动离开其原来生活或活动的区域[8]508,德勒兹哲学中的解辖域化是一种逃逸方法。藉此主体可以形成精神或身体上的逃逸[5]68。解辖域化分为绝对的和相对的,积极地和消极。
一些批评家认为艾米丽与其父亲之间存在着乱伦。杰克·舍汀认为艾米丽的问题是在其父亲身上的力比多定位,或更准确地说是伊莱克特拉情结(恋父情结)。与父亲的乱伦关系是艾米丽身体上的第一次解辖域化,她不再是原来的自己。这对她的心灵产生了伤害,使她在心理上产生了依赖。这是此次解辖域化的消极一面。她不得不在荷默身上寻求力比多定位,延续着她与父亲的关系。但这次解辖域化的积极一面就是她从此开始叛逆——从与父亲的乱伦关系中她学到了此后她不再继续沿着他人规定的现成的方式行事。她成长为德勒兹哲学视阈下的“少数派”。少数派意味着对现存秩序的超越。少数派意味着不为多数派所限制,意味着无限的可变性和创造性,意味着不断生成新的东西。
与荷默的关系是艾米丽的第二次解辖域化。她正式开始了以少数派的身份同镇民们交锋。她故意在小镇的马路上和荷默一起乘着马车招摇过市,以此激怒镇民,与他们针锋相对。第二次解辖域化使艾米丽在思想上开始成熟。但她还仍然处于冲动状态下,以一己之力,孤身一人同全镇人斗争,酷似拜伦式的英雄。这在她身上凸显出了少数派的特质。
艾米丽第三次解辖域化是她与托比关系的确立。她更加理智,更加清楚自己的处境。与托比的关系只是她与小镇斗争的必要手段。她的精神开始升华,不再是盲目的冲动,更不是力比多的定位,而是一种战略战术手段的选择。
在2011年《密西西比季刊》的福克纳专栏,约翰·马休和司格特·洛闵[2]484,分别发表文章支持托马斯·阿基诺关于艾米丽与黑人仆人托比之间存在着暧昧关系的观点。但是这种关系不再是力比多的定位,也不再是盲目的情感冲动,而是理智的抉择,是艾米丽与整个杰佛逊小镇斗争的需要,是手段和要挟。
艾米丽与三个男人的关系既是她人生中三个不同的块茎同时也是三次螺旋式上升的解辖域化运动。在这期间她不断地超越自我,发掘自我,得到了脱胎换骨的变化,成长为少数派。解辖域化既是一个创造过程也是一个发现过程,主体以新环境为镜像照出一个全新的自我[9]。
二、艾米丽的去“脸面性”与“无器官身体”
“脸”是德勒兹和伽塔里的理论核心。社会经济结构和权力结构变化引发了一系列与其相对应的德勒兹称之为“脸”的社会组织机构的形成[8]175“脸”是由“白墙”与“黑洞”构成[8]167。“黑洞”排列在白墙上,洞口紧锁在白墙之上,洞体横向无限延伸。“白墙”是展示“表征”的场所。根据德勒兹和伽塔里,“表征”相当于“能指”和“所指”之和。经济结构和权利结构的变化使人们为了获取最的利益形成了各种各样的利益群体——“脸”,“脸员”必须接受“脸面性”规制——白墙冗赘,不得不将自己的主体锁藏在“黑洞”之中,完全失去自我。紧紧固着在“白墙”上的主体不仅失去了自由,失去了主动性,更失去了创造性。“脸”的不人道决定了它的的拆除是必然的[8]188。主体要把握自己的命运,最好的办法就是挣脱“脸”的束缚,拆除“脸”,去除“脸面化”,线化“白墙”,冲出“黑洞”。
由于经济结构的变化和历史的变迁,艾米丽所生活于其中的小镇杰佛逊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作为小镇这张“脸”所有“脸员”,也就是镇民们却仍然千方百计维持着他们原有的生活方式,偏执狂般地要求镇里的每一个成员都接受镇上的规制,尤其是那些多年来一直约定俗成的在各种行为取向上的一致性。
镇民们认为,凭艾米丽的高贵身份不该和那个在工地上晒的黑黑的北方佬在一起。为此,她们鼓动了牧师前往劝说,又从阿拉巴马州找来了艾米丽的堂姐妹当说客。但艾米丽仍我行我素。她坚决拒绝她们的“社会契约”和“社会死亡”。
在十九世纪的美国,存在这一个非官方的规定:被社会接受和喜爱的前提条件是接受一个“社会契约”,甘愿屈从于一种“社会死亡”[14]1。这样的社会环境剔除了在文化、种族以及性行为等方面与社会主流不同的人物,不给这些人留下舒适的生存空间,因为他们的存在导致了占主导地位的文化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不安。艾米丽的房子被叙事者描述为“丑中之丑”(an eyesore among eyesores)。这实际上意味着艾米丽是镇上人们的眼中钉肉中刺。拥有政治恋尸癖的镇上居民很渴望推倒她的房子,更渴望她“社会死亡”。然而她并没有妥协,从撵走市政官员“我在杰弗生无税可纳”到拒绝让他们“在她的门上钉上金属门牌号,附设一个邮件箱”[16]10。这样,她独自一人打败了市政当局。
艾米丽拒绝了小镇为她安排的“社会死亡”,拒绝接受它的白墙规制,蔑视任何白墙冗赘。最终她线化了杰佛逊小镇这张“脸”的白墙,从自己的主体黑洞中挣脱出来,完成了少数派的革命。
“无器官的身体”同样也是德勒兹创造的核心概念之一。无器官身体是指身体处于在功能上尚未分化或尚未定位的状态,或者说身体的不同器官尚未发展到专门化的状态。无器官身体不是一个想法,也不是一个概念,而是一种实践。无器官身体是一种极致[8]150。形成无器官身体的第一步是去除有机组织,使主体对物质利益和精神利益视而不见听而未闻。这相当于拆除脸的第一阶段,即主体开始无视经济利益的诱惑,“脸”开始失去对主体的诱惑力。形成无器官身体的第二步是去除表征性,相当于开始去除白墙冗赘,摆脱任何外在力量的束缚。第三步是去除主体性,也就是实现了“忘我”,“无我”和“超我”。这相当于拆除脸的过程中的主体从黑洞中挣脱出来。“无器官身体”分为三种:恶化的无器官身体、丰满的无器官身体和干枯的无器官身体。
德勒兹和加塔里的理论体系“精神分裂分析学”中的重要任务就是把欲望分为两种——“作用的欲望”和“反作用的欲望”。前者支配下的无器官身体是“精神分裂者”,他们不满足于对现有的事件和形势做出主流思想所接受的反应,不接受世俗、环境和规制的约束,属于“少数派”。他们当中的一些人会成为革命者和推动历史发展的力量。他们坚持思想,直接表达欲望,成为丰满的无器官身体。艾米丽无疑便是这种类型的人。
一份福克纳的《献给艾米丽的玫瑰》亲笔手稿和碳墨打印稿于2000年出版。这是未经删节的版本。这里有一段艾米丽和托比之间的对话,后来正式出版本中被删掉了。这段对话透露出托比知道有关荷默尸体的全部经过——
艾米丽对托比说:“在我死之前不要让任何人进来,听懂了吗?”“那时他们会来的,就让他们到上面去吧,去看看那屋子里到底有什么。一群傻子。就满足他们的心愿吧,让他们觉得我疯了。你认为我疯了吗?[[[] William Faulkner. “Matter Deleted from ‘A Rose for Emily’”. Polk, A Rose for Emily, 2000.]]23-24” 艾米丽这席话传递出的信息是他对镇上人们深刻的轻蔑。于是我们有理由推断停尸现场可能就是她为了报复有意设计的。她就是为了让镇上人们感到震惊和迷惑。如果她认定镇民是傻子,那么就是她在愚弄他们,满足他们认为她是个疯子的心理需求。这表明她十分清楚地了解这座小镇以及她本人的境遇。她偏执地认定镇上人们认为她精神不正常。也许她是从托比那里获得的信息。她知道镇民们一直在伤害她。牧师一定是他们鼓动来的,阿拉巴马长期没有往来的亲戚也一定是他们叫来的。如果她真地精神错乱的话,那也一定是他们逼出来的。她冒着犯重罪的风险把尸体留在自己的闺房中,就是让镇民们认为她是一个地道的恋尸癖。艾米丽的留尸行为就是要向整个镇子宣战:她拒绝静悄悄地按照那些社会经理人的安排去“死”。她不接受镇民们为她准备的“社会契约”,更不屈从为她安排的“社会死亡”。她这样做正是给那些期待自己“社会死亡”的人们一记响亮的耳光。
三、结语
艾米丽独自一人孤军奋战,用生命打了一场持久战。她的战略就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战术是利用身边一切可以利用的资源。父亲是她的精神支柱,荷默是她的挡箭牌,托比是他的交通员和最后一道护身符。最终,在块茎的叙事方式下,艾米丽通过不断的解辖域化运动,去除了脸面性,形成了丰满的无器官身体,成为了少数派,找到了物质上的,精神上的,身体上的和心理上的逃逸线,“逃离”了当时限制她的物质和精神环境。至此,作为德勒兹哲学视阈下的少数派——精神分裂者,她打败了一群德勒兹哲学视阈下的多数派——偏执狂。
艾米丽以她向镇上人们所展示的一面,在他们面前树立起一座捍卫没落贵族尊严的丰碑,以镇民们看不见的一面为小镇政治恋尸癖挖掘了坟墓,为它树立起一座墓碑。她的死正是一座丰碑的倒塌和一座墓碑的竖起。
[1]Judith Caesar, Faulkner’s gay Homer, once more, The Explicator, 2010.7:195 -198.
[2]Scott Romine. How many Black Lovers Had Emily Grierson? [J]. Mississippi quarterly, 2011:483-491.
[3]Gilles Deleuze, Felix Guattari. What is philosophy? [M]. Trans. Hugh Tomlinson and Graham Burchell.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4.
[4]Adrian Parr. The Deleuze Dictionary [M]. Scotland: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2005.
[5]Gilles Deleuze, Felix Guattari. What is philosophy? [M]. Trans. Hugh Tomlinson and Graham Burchell.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4.
[6]Constantin V. Boundas. Gilles Deleuze [M]. London: Continuum Publishing Corporation, 2011.
[7]麦永雄.德勒兹差异哲学与后马克思主义文化观念举隅 [J].江南大学学报,2013(9).
[8]Ddeuze and Guattari. A Thousand Plateaus: Capitalism and Schizophrenia[M]. Trans. and Forward by Brian Massumi. Minneapolis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87.
[9]康有金,德勒兹哲学之解辖域化,武汉科技大学学报,2016.1.
[10]Jack Scherting. Emily Grierson’s Oedipus Complex: Motif, Motive, and Meaning in Faulkner’s “A Rose for Emily” [J]. Studies in Short Fiction 17.4, 1980: 397-405.
[11]夏光. 德鲁兹和伽塔里的精神分裂分析学(下) [J]. 国外社会科学, 2007(3).
[12]John T.Mattews. All Too Thinkable? Thomas Aigiro’s “Miss Emily After Dark” [J]. Mississippi Quarterly, 2011.6:474-480.
[13]Thomas Robert Argiro. Miss Emily after dark [J]. Mississippi quarterly,2011:445-465.
[14]Russ Castronovo. Necro Citizenship: Death, Eroticism, and the Public Sphere in the Nineteenth-Century United States [M]. Durham: Duke UP, 2001.
[15]罗益民.《英美短篇小说名篇详注》[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
[16]福克纳. 外国中短篇小说藏本 [M]. 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11.
[17]夏光.《德鲁兹和伽塔里的精神分裂分析学(上)》[J]. 国外社会科学, 2007(2).
[18]William Faulkner. “Matter Deleted from ‘A Rose for Emily’”. Polk, A Rose for Emily, 2000.
Interpretation of A Rose for Emily with Methodology of Flight
KANG You-jin,HOU Wen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Wuh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Wuhan Hubei 430065,China)
A Rose for Emily; methodology of flight; Interpretation
A Rose for Emily is the most famous short story of William Faulkner.“Flight”is a most important creation of the French philosopher Deleuze and important methodology of literal criticism. He thinks writing is to find a line of flight, by which writers break spiritual fetters and psychological shackles, which is reflected on the figures they create in literature. Interpreting this story, we can see by making use of rhizomatic way of narration, the writer creates a heroine, who becomes a minority, by means of deterritorialization, dismantling faciality, becoming body without organs. In the end she erects a tomb stone for the townspeople who have political necrophilia by making them believe that she is a necrophilia and has slept together with the dead body.
2095-2708(2016)05-0180-05
I106.4
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