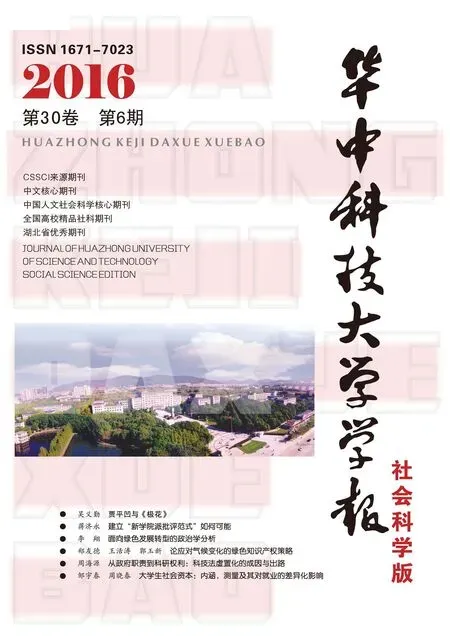贾平凹与《极花》
吴义勤教授,中国现代文学馆馆长、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主编,山东 济南 250358
贾平凹与《极花》
吴义勤教授,中国现代文学馆馆长、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主编,山东 济南 250358
贾平凹先生的创作确实是对我们今天这个时代最好的馈赠,但可惜的是,我们的时代并不能很好地享受这份馈赠,有的时候甚至还会消化不良。笔者觉得,如果单纯把贾平凹仅仅作为一个时尚偶像来消费或追捧,也许并不是理解他对我们时代的贡献与意义的正确方式。我们可以追捧他,可以在各种场合把他作为明星一样对待,这都是他的文学成就带给他的应得的荣耀。但问题出来了,这是贾平凹真正需要的吗?贾平凹其实是个内向、木讷、不喜欢抛头露面的人,但明星式的待遇却让他躲无可躲。
笔者发现,我们这个时代对贾平凹真是充满了误解与矛盾:一方面夸张而狂热地歌颂贾平凹,另一方面又常有非常尖锐的声音来质疑他与他的作品,有的时候这种质疑与批判的尖刻程度甚至超过了我们理解的限度。我们今天面对贾平凹及其作品的矛盾心态值得研究。对一个文学明星的追捧,是一种精神上真正理解与共鸣的追捧,还是仅仅作为一种现象、一种功利的追捧?这是需要认真区别的。我们正在进入一个轻阅读、浅阅读、反阅读的时代,经常听到很多人对贾平凹的不满、批评与埋怨,说他的作品读不懂、读不下去。笔者想,从上世纪80年代走过来的人一定会觉得很奇怪,时代真是变了呀。读不懂、读不下去一个作家的作品,这是作家的罪过?还是我们自身的罪过?在上个世纪80年代,不要问,一定是我们自身的罪过,我们一定会对读不懂的作家充满敬意,同时对我们自身修养的浅薄深感惭愧。而在今天,我们批判贾平凹的作品写得太琐碎、节奏太缓慢,读不懂、读不下去,理所当然,理直气壮,绝不反省自己,绝不会追究自身文学修养是否太低,对文学的热情是否足够。八十年代的先锋小说到今天仍然有很多人读不懂,但80年代从来没有人会为读不懂先锋作品而去批评先锋小说、先锋作家,今天这个局面正好反过来了。
对贾平凹的误解有很多很多的表现形式,其中有两种要特别警惕。
第一,对所读作品的所谓真实性的幻觉。笔者经常看到很多人质疑贾平凹作品的真实性。前几天,在北京一个私下场合,笔者还看到一位很优秀的青年作家慷慨激昂地批判《极花》如何不真实,说小说所写的事件根本不可能发生,逻辑上根本行不通、太假了。这其实是我们读文学作品时经常会犯的错误。读一个作家的作品是读文学自身还是读背后的现实?这是要区分的。我们不能把文学和现实混为一谈。贾平凹的作品仅仅从现实的角度去理解或者仅仅从背后中国经验的角度去理解,实际上是把他的作品局限了。文学作品可能脱胎于现实,可能来自现实很多很具体的经验,但是文学成为作品之后就已经超越了现实,就有了自足性,就有了自身的与现实不同的逻辑。因此,一定要从超越性的角度去理解文学作品,文学就是文学,它可以反映现实,但终究不是现实。这就和我们今天强调的对外文学交流、中国文学走出去一样。面对西方学者对中国文学的态度的时候,我们其实应有清醒的意识,西方大部分学者面对中国文学作品时,他们并不是真正在读文学,而是在读中国,他们只是希望通过中国文学作品背后隐藏的中国形象去阐释中国,而且他们需要的是文学作品中的中国形象符合他们对中国的他者化的理解,其实并没有把中国文学真正当成文学作品去对待。这在第一届中美文学论坛上,笔者感受特别深。美国学者大都把中国作家的作品完全作为社会学文本去对待,完全没有考虑这个作品在文学、艺术、审美上的追求,他们关注的只是中国形象。这种现象在今天中国的文学读者里也同样存在,纠缠于现实的某个问题以及所谓真实不真实的问题就是其表征。
第二,禁忌思维对贾平凹作品的误读。经常看到很多批评文章说贾平凹的作品趣味比较低下,喜欢描写生活中的屎和尿,说它的作品是屎尿横流,等等。在我们从前的文学禁忌思维里,文学确实有很多东西是不能描写和表现的。我们不应仅仅在现象层面上谈论这种描写的是非,而应认识其对文学作品审美建构的意义。有的时候,笔者也很支持对贾平凹的作品进行批评、争鸣甚至批判,但笔者希望这是深层次的批判,不要局限在表象层面上,要讲理,要有说服力。仅仅指出一个作品表层的问题,这不是我们所呼唤的批评精神,因为这些表层的问题就在那儿,看到它指出它很简单。比如,作品描写了一个人上厕所,或者描写了一些生活的脓疮,你认为这不好,这没有什么难度,太容易了。所有的人都能看出来,不专业的人都能看出来,这体现不出批评的真正力量。实际上,要真正批评贾平凹,就需要有专业和敬业地对其作品的阅读,有耐心的阅读,只有这样你才能指出贾平凹那些缺陷的来龙去脉,才能让人信服。笔者觉得,在今天的时代,对一个作家的耐心,其实就是表达对作家的尊重和敬意的最好的方式。
上面,讲的是贾平凹与我们时代的关系,下面再简单讲讲《极花》。笔者从三个对应关系来理解《极花》。
第一,坚硬与柔软。今天的作家处理的中国现实都是非常坚硬的现实,各种苦难、农村荒芜的现实、城乡冲突的现实,等等。这些现实很沉重、很坚硬,包括主人公胡蝶的命运也是很坚硬的,从乡下到城里再到农村,何等鲜血淋漓的一种坚硬的现实啊。胡蝶的内心也是很坚硬的,她被拐卖到乡下去以后,“我”冷到冰也要有硬度,破到碎了也要像玻璃一样扎破轮胎。贾平凹对现实的批判性也非常强,对村长的批判,对整个中国当今乡土衰败现实的批判,都是很深刻和尖锐的。但小说本质上又很柔软,这个柔软来自于对底层人物深刻的同情和怜悯,他是真正走进了这些人物的内心。胡蝶的形象,笔者认为实际上是“五四”时代娜拉在今天时代的新变体。娜拉走后怎样?这个在中国已经思考了一个多世纪问题,贾平凹在新世纪又再次提了出来。娜拉走后怎样?胡蝶从乡村到城市再到乡村的历程,实际上给了我们一个很残酷的答案。只不过,贾平凹是以很柔软的同情和理解来面对胡蝶的。
第二,简单与丰富。贾平凹在后记里说得很清楚,这个小说来源很简单,就是一个妇女被拐卖的新闻事件,这么多年来这个事件一直在他心里发酵。但小说并不是简单的问题小说,其背后蕴含的内涵是很丰富的,不仅仅有风俗、乡土、人的命运等层面的内容,更有着自然、人性、现代性、城乡冲突等等复杂的思考。新闻事件已经完全文学化了,文化的、哲学的、人性的、社会学的意蕴赋予小说兼具形而下和形而上双重内涵的丰富面相。
第三,现实与文学。贾平凹是一个对现实有超强敏感的人,笔者觉得他有非常好的现实触角,每天都像雷达一样搜寻着各种信息,因此他的小说总是有着很强的现实性与时代性。贾平凹的高明在于,现实再强大,都不可能覆盖文学本身,对诗性和文学性的追求永远是其小说核心。比如,《极花》本来面对的是一个很苦难、很残酷的题材,但是《极花》这个题目本身却充满了诗意和象征性。看星星、望星空,胡蝶内心心理的变化本身是很文学性的。从最初的仇恨、诅咒到后来对黑亮的感情、对孩子的感情等等,非常符合人性逻辑。面对人性和诗性,胡蝶究竟会不会回来这样简单的现实问题已经变得没有意义。因此,对贾平凹的《极花》也好,对他的其他任何作品也好,首要的仍然是把其作为文学作品来对待,现实固然是作家思考问题的出发点,作品一经完成,就会远远大于现实、超越现实,再局限于现实的角度看问题就不可避免地会陷入对作品的误读。
主持人语: 时如白驹过隙,转眼间,华中科技大学中国当代写作研究中心已经成立近五年了。五年来,承蒙海内外同道不弃,一年两度欢聚于此,为文为艺,为道为术,春秋讲学,于兹为盛。书云:“念兹在兹,释兹在兹,名言兹在兹,允出兹在兹。”念念不忘,必有回响。我中心诸同仁久有心于记念此盛事,摭拾嘉宾高言宏论,勉成我一家之言,以于当代文坛相唱和。然理想之文学阵地殊难一遇。今承我校学报主编雅意玉成,方始小试牛刀,成此专栏。幸甚。本期意在记录2016年春讲活动,可惜贾平凹、丁帆两先生的演讲因先期发表于网络,不能在此刊发,甚憾。幸约有吴义勤先生、昌切先生的大作助阵,与我中心王书婷、梅兰二位老师众说纷纭论《极花》;及中心副主任蒋济永教授谈“新学院批评”。筚路蓝缕,以启山林;春花秋实,乃是所期。
栏目主持人:蒋济永,华中科技大学中文系/中国当代写作研究中心副主任、教授;王均江,华中科技大学中文系/中国当代写作研究中心副主任、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