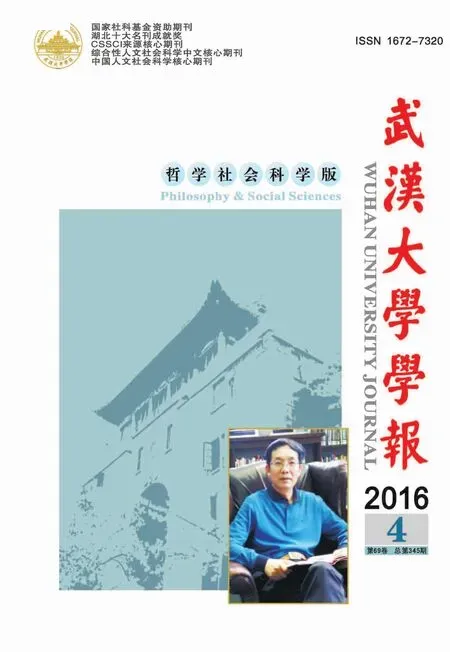政治制度、政治思想与政治制度思想
——一种理论构建的努力
季乃礼
政治制度、政治思想与政治制度思想
——一种理论构建的努力
季乃礼
摘要:以前学者把政治制度与政治思想看作是对立的两极,导致政治制度和政治思想的研究相互隔离。但实际上两者并不是相互对立的,而是相互作用。政治制度构建一个环境,对人们的政治思维进行限定,而学者和决策者的政治思想影响和推动政治制度的发展。同时,政治制度和政治思想也有相互重叠的区域,即政治制度中的思想。政治制度思想理论的提出,为判定政治制度的合理性提供依据,认清决策者和思想家的真实意图,同时为政治思想史的编写提供新的视角,也为中国现有的制度建设提供新的思路。
关键词:政治制度; 政治思想; 政治制度思想
一、 问题的提出
目前中国政治思想史和中国政治制度史的研究形同陌路,分属两个不同的领域。即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研究基本不涉及制度,中国政治制度史的研究也基本不涉及思想。从学科划分来说,中国政治制度与外国政治制度的关系更近,属于政治学下设的二级学科:“中外政治制度”;中国政治思想史属于政治学下设的二级学科政治学理论下的三级学科,称为“中外政治学说史”。
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大致有两条路径:一是从政治学的视角切入,以萧公权的《中国政治思想史》为代表,把中国政治思想史的演变大致分为封建时代、专制时代与近世,在此背景下叙述各个思想名家和思想流派。二是从历史学的角度切入,以刘泽华主编的《中国政治思想史》为代表,把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的演变归结为王权主义形成与不断发展的过程,但对中国近代政治思想的发展规律并没有作深入探讨。两者的研究视角尽管存在差异,但是研究的内容基本是一致的,即以朝代作为主轴,然后以人物列传或学派构成各个章节的内容,在叙述各个学派和各个思想家的政治思想时,基本不涉及与制度的关系。
中国政治制度史的研究也存在类似的问题。中央行政体制的变迁构成了中国政治制度研究的核心内容,除此之外,也探讨地方行政体系、监察、军事、财政、文教等制度,但很少涉及思想方面的内容。
不但政治制度与政治思想不通,而且制度和思想内部也存在古今割裂的现象。譬如,研究中国政治思想史的学者重古代,轻近代,忽略现代。他们对古代研究较多,尤其是先秦诸子,但是对后来的政治思想,尤其是近代的政治思想研究存在着明显的不足,而对中国当代的政治思想研究作为一个禁区集体回避。
与中国政治思想的研究相比,中国政治制度的研究要略好些。在政治学界,对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史的研究基本处于边缘地带,相反对中国当代政治制度的研究则属于显学,目前活跃在政治学界的名家多数以研究当代中国政治制度而闻名。但是中国政治制度的研究也存在问题:研究古今政治制度的学者相互隔离,即研究中国当代政治制度的学者一般不知或不了解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研究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学者也不懂当代中国政治制度。而且研究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学者一般在历史学界,这是中国古代史所探讨的主要内容,在政治学界以古代政治制度为主业的学者很少。
这种现象不仅在研究中国政治制度和思想的学者中存在,在研究外国政治制度和思想的学者中也同样存在。西方政治思想史的研究基本可以划分为两派:剑桥学派和施特劳斯学派。剑桥学派以昆廷·斯金纳为代表,主张在语境当中理解思想家的“文本”,语境既包括经典思想的特定社会历史背景,也包括当时的政治词汇(斯金纳,2002:3-8)。施特劳斯学派以列奥·施特劳斯为代表,主张思想应该超越历史的羁绊,回归政治哲学本身,从诸多思想家中探讨人类处境的同一性及问题的永恒性(施特劳斯,2003:17-27)。两种研究方法尽管有所差异,但不管是观念史的考察,还是单纯的哲学思辨,也基本是按照人物列传在写作,尽管到20世纪以后,分成了许多思潮或流派,但人物的思想研究依然是主流,这与中国政治思想史的写作基本相同,区别在于西方的政治思想史主要是研究有系统的政治学说,称作“政治学说史”较为合适;中国主要讨论治国之道,称之为“政治思想史”较为恰当(王乐理,2005:5-6)。西方政治思想的研究基本是从政治学的视角切入的,而且没有古今的隔离感,越到近现代叙述越翔实。
西方政治制度的写作也基本与当时的政治思潮和人物的政治思想是脱节的。西方政治制度的写作也基本没有古今的差异,而且越到近代,政治制度的论述越加详细。西方政治学的发展大体经历过三个发展阶段:19世纪末期,政治学兴起之初,主要关注政治制度;20世纪50和60年代之后,以行为主义和理性选择理论为代表的政治学研究兴起,关注的焦点由宏观的制度转向微观的政治行为,结合了社会学、心理学和经济学等相关的知识;20世纪80年代以后则是新制度主义的兴起,综合了两者的研究视角,不再单纯关注制度本身,而是与人的行动结合起来。他们关注制度对观念的影响,制度与人的心理互动(何俊志、任军锋、朱德米,2007:13;彼得斯,2011:1-24)。
值得注意的是,学者们在探讨政治学发展过程中,有意地把政治思想排除在外。但是如果我们回顾政治学发展的历史来看,在政治学没有形成一门学科的萌芽阶段,政治思想构成了“政治学”的主要内容,换言之自古希腊以来的诸多思想家,尽管没有政治学科的意识,但他们提出的政治思想对政治学的发展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政治学形成的很长一段时间内,“政治思想”和“政治理论”两个概念相互混用,以至于肯尼斯·谢普斯勒抱怨这“不合常理”(何俊志、任军锋、朱德米,2007:122)。行为主义和理性选择乃至新制度主义试图把两者区别开来,这体现了学者们学科意识的明显进步,但区分的结果是把政治思想有意无意地忽略掉了。
更需要指出的是,上述研究对理论的运用是有差异的,大体上可以归为三类:第一类无理论,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史的研究,以及部分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研究皆存在这种情况,致力于把政治或思想的演变描述清楚。第二类,狭义的政治学理论,西方的政治学科一般划分为四个领域:政治学理论、比较政治、国际政治、本国政治,其中后三个领域也兴起许多理论,但是西方的政治思想史研究以及中国国内部分的政治思想史研究均运用狭义的政治学理论研究政治思想,具体来说用自由、正义、民主等概念解释和评判一些思想家和观念,带有明显的价值判断。第三类,广义的政治学理论,中外研究当代政治制度的学者均运用广义的政治学理论,但他们有意地回避了狭义上的政治学理论,采取价值中立,运用理论的目的在于更好地解释现实、总结规律。可以说三种研究各有所长,也各有局限,但学者们在研究过程中采取了互相排斥的态度。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学者们基本上把政治制度和政治思想、古代与现代看作是对立的两极,没有关注到政治制度对政治思想的影响,没有把古代与现代联系起来,同时理论的运用方面也存在或多或少的不足。但是政治制度和政治思想应该不是对立的两极,两者之间应该有许多可操作的空间,许多可值得研究的内容。具体来说,政治制度的研究不应该在吸收其他学科理论成果的同时,忽略了对政治思想的关照,同时政治制度不应该只体现“硬”的一面,而应该有“软”的一面,从冷冰冰的制度中我们会读出一些思想、观念,一些价值、原则;而政治思想也不应该关起门来自娱自乐,只体现“软”的一面,而应该与政治学的发展同步,作为政治学的一个分支,应该借鉴政治学理论的发展成果,应该关注政治思想与政治制度的互动,政治制度构建一个环境会对人们的心理、行为有所影响,进而影响人们的政治思想,同时政治思想也会外显于人们的言行,渗透于政治制度之中。
二、 政治制度思想的释义
政治制度思想即是探讨政治制度与政治思想之间的互动,具体来说,政治制度的建构是基于什么样的政治思想以及政治制度形成之后对当时的政治思想有何影响。这里取消了“史”作为后缀,在于制度与思想的互动不仅在古代存在,在当今也比较明显。
政治制度思想中的“政治制度”是一个宽泛的概念,西方学者甚至不谈政治制度,直接以“制度”称之,在于他们与过去仅关注国家组织形式的“政治制度”相区分,把许多过去人们容易忽略的方面都纳入了制度的范围。诺斯认为:“制度包括人类设计出来的、用以形塑人们相互交往的所有约束。”(诺思,2008:4)制度既包括正式约束,如人类设计的规则,也包括非正式约束,譬如惯例,也包括行为准则。马奇和奥尔森也把制度界定为规则:“制度拥有一套程序,通过规则在其中进行选择”;规则的范围很广泛,“包括惯例、程序、协议、职责、策略、组织形式以及技术等,政治活动正是围绕着它们构建形成的。规则还包括信念、榜样、符号、文化及知识等,这些对职责与惯例起到支持、阐释的作用,当然也可能与之发生抵触”(马奇、奥尔森,2011:20-21)。阿斯平沃和施耐德也认为制度既包括影响人类行为的正式结构,譬如投票、立法等,也包括非正式结构,譬如文化实践与认知模式等(何俊志、任军锋、朱德米,2007:310)。
西方学者普遍认识到除了正式约束之外非正式约束的作用,更有的学者把与政治制度相关的信念、榜样、符号等象征政治观念的因素也包括在内,但我们把此部分作为政治制度与政治思想交叉的内容,归入到政治制度思想的范畴。因此,这里所说的“政治制度”,既可以包括传统的政治制度,譬如党和政府的各项制度,也可以包括军事、经济、法律和文化等制度,也可以包括具体的政策,制度运用中的一些具体的规则、规定,也可以包括一些礼仪等。譬如在中国政治制度史的研究中,学者们很少探讨礼仪,但礼仪也应该包括在研究的范围中,甚至包括一些潜规则,它们尽管没有落实到纸面上,但是在政治制度的运作中却发挥着实际的作用。
有关政治思想的内涵,徐大同先生解释为:“政治思想是反映一定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中的意识形态部分”,包括为维护统治而设计的政治方案,或者实现其政治统治的“出谋献策”(王乐理,2005:7)。刘泽华先生的解释相对宽泛,他把政治思想等同于政治观念,分为政治心理、政治思想和政治学说三个层次:政治心理表现为情感、倾向、成见、信念、风俗、习惯等等,具有自发性和直接感受性,并不为少数思想家所独有,多数成员或多或少都拥有;政治思想是一种理论化的政治意识,是政治心理的升华,比较系统;政治学说是系统化乃至哲理化的政治思想(刘泽华,2014:4)。
我们这里所说的政治思想,比意识形态的范围要宽泛,基本与刘泽华先生所说的三个层次相同,但刘泽华先生所说的风俗、习惯等严格来说并不属于政治心理,而是与西方学者所说的“制度”的含义较为接近。这里所说的政治思想包括民众对政治的所思所想,即一个时代的政治文化,也包括思想家的政治思想和有影响的学派、政治思潮等等,同时也包括决策者的思想、观念。
政治制度思想是政治制度和政治思想互动之后形成的独立存在,作为一种思想可能渗透于政治制度的各个层面,但不完全和制度是重合的,即政治制度中的思想,不但会体现在政治制度有明文规定的方面,而且也会外溢出来,在无制度规定之处对人们的行为形成影响。政治制度作为一种有形的规定,无法涵盖政治运作的所有层面,但思想作为一种无形的存在却可以延伸开来。譬如,一个制度中禁止官员对利益的追逐,而在制度没有规定的地方,对利益的追逐可能依然驱动官员的行为。
政治制度与政治思想可谓露出平海面的一座冰山两角,从海平面看,政治制度与政治思想是相互独立的,但在海平面以下,两者则是互通的。政治制度和政治思想表面上各自独立性很强,但随着向海底的延伸,两者的关系逐渐密切,最终实现相互的联结。有些内容我们一眼能够看出哪些属于政治制度,哪些属于政治思想,譬如仁爱、正义等属于思想,君主制、代议制、人民代表大会制属于制度。但有些则很难分清,属于两者的交叉,譬如惯例、规范、文化实践、认知模式等等。有些名称本身就是政治制度和政治思想的结合,譬如公平的规则,正义的制度等等。
这里所说的“制度”借鉴了西方新制度主义的论述,而且新制度主义注重探讨人的行为、观念等对制度的影响,与我们所说的政治制度思想有些类似。但与之区别的是:其一,新制度主义的核心在制度,而政治制度思想则强调制度和思想都是研究的核心。新制度主义探讨制度对行为、观念的影响,但其落脚点还是在制度,制度→行为、观念→制度。而政治制度思想是探讨制度与思想的互动,即制度→行为、观念→思想,或者思想→行为、观念→制度。譬如政治制度思想同样关注制度对人们的心理的影响,但探讨的是制度对人们的心理造成了哪些影响,这些影响又如何影响了人们的思想,进而对制度产生影响。其二,新制度主义关注的思想主要限于民众的层面,对思想家、政治精英的政治思想以及学派的政治思潮关注不多。如新制度主义一样,政治制度思想也关注民众的思想、观念,但以思想家和统治者的观念为主,因为这些思想和政治精英对制度的影响最大。其三,政治制度思想前面加“政治”,意味着所有的制度、思想、观念的探讨都要归结到政治的层面上来,都要与政治相关。而新制度主义研究者来自经济学、社会学和历史学等,他们所探讨的思想、制度等范围较为广泛。
三、 政治制度思想的内涵
那么,政治制度思想应该包含哪些内容呢?大致说来,应该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 政治制度中的思想分析,即现有的政治制度中包含哪些思想
制度一旦确立,即成为一个独立、客观的分析文本。所谓独立、客观,指其中包含的思想通过科学的分析能够揭示出来,只要每个人依据科学的分析方法所得出的结论,就是大家公认的。尽管有的制度在设计之初,某些领导者或者思想家对此有过明确的表述,但是制度本身所体现的思想既可能与这些表述有相同之处,也可能有不一致的地方。《独立宣言》是美国政治制度确立的基础,但其宣扬的“天赋人权”并没有在美国政治体制中得到充分的体现,美国政治制度中长期存在对不同种族的歧视,黑人长期被排除在投票权之外。再如,分权学说是西方近代以来核心的政治思想内容之一,也是欧美各国政治制度的理论基础,但是制度在发展过程中,总统(或首相)与议会的权力在不同时代的体现是不同的,由原来的议会占据主要的权力,到现在逐渐向总统(或首相)倾斜。
如何分析政治制度中的思想?一般来说是一个倒推的过程。具体来说,当时的社会流行哪些政治思想,然后分析它们在政治制度中有无体现。但政治制度演变本身也可以作为一个独立分析样本。因为有些制度确立时没有找到决策者明确的表述,但我们可以从现有的制度中分析出其中所体现的思想,仅仅从制度的演变即可发现其中的政治思想的变迁。譬如,欧美各国在19世纪下半叶开始,逐渐取消了财产、性别、种族等的限制,实现了普选权,体现了民主思想的不断发展。
政治制度中的思想是以制度为载体的,因此决定了制度中思想的内容要比传统的政治思想中所涉及的思想要窄得多。可以说,政治制度中的思想是当下的,排除了以前的一些思想,同时思想家们所提出的政治理想都自然排除在制度思想的范围之外。譬如自古以来,中外有许多思想家对未来社会提出了展望,这些“空想”是不需要载体的,但制度中的思想却不同,它附着在制度上而无法随意变动。
需要指出的是,一项制度要做出改变或修订时,学者们关注较多的是与制度改革相关的利益人或利益群体,制度改变中受益的人或群体会支持改革,受损的会反对改革,这种分析模式忽略了对思想的关照。除了利益之外,人们对某项制度的态度与对某些观念的坚守有着密切的关系。譬如,在美国有关买卖枪支是合法的,但近年来发生的几次枪击事件使许多人呼吁尽快出台禁枪令,但始终千呼万唤不出来。许多人把原因归为美国步枪协会等利益集团的阻挠,但没有关注到允许枪支买卖与人们对私有财产保护之间的关系。洛克曾经把生命、自由与财产看作是人们天赋的权利,有了财产,生命有了基本保障,言论自由、迁徙自由等也得以实现,财产应该得到保护,无论西方的学者还是民众都认为是天经地义的。在美国,枪支与私有财产的保护是密切相关的,因为对枪的忌惮,没有人敢随便闯私人的住所*笔者在美国芝加哥大学做访问学者时,曾经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芝加哥大学周围尽管时有抢劫发生,但居民并没有像中国一样给房屋安装防盗护栏。这是因为如果私自闯入民宅,房屋的主人可以用枪把对方打死而无需担负任何责任。出于对法令和枪支的忌惮,许多人敢于白天抢劫,但不敢入民宅半步。。
(二) 决策者和思想者的思想对政治制度的影响
政治制度中所体现的思想来自何方?大体上可以归纳为三方面:
第一,来自有影响的学派和学者。譬如中国古代的儒家学派,汉代的董仲舒等。他们对制度的影响主要取决于决策者的态度,决策者对某一思想的支持或反对影响着他们对制度的影响程度;在有关美国政治制度的探讨中,人们也会提到洛克、杰斐逊、潘恩、麦迪逊等人的贡献。
第二,来自于决策者。决策者的思想对政治制度的影响最大,作为权力的拥有者,他们的思想、观念对政治制度有足够的影响力。无论是中国还是西方,每一个国家或者朝代的开拓者,由于制度属于初创时期,他们的自由度较大,因而他们的思想对制度的建构影响最大。但两者之间并不是一一对应的关系,即决策者的想法不一定会体现在制度上。决策者的思想对制度的影响受以下几个因素的影响:一是领导方式的影响,即决策群体是一个领导占据主导地位还是多个领导占据主导地位;二是反对派势力的强大与否及其与决策者的思想分歧的程度;三是传统的风俗、习惯以及原有制度的惯性。
第三,是民众的预期以及固有的文化传统。民众对制度本身有一定的期盼,如果不符合他们的预期,他们可能会抗议制度,从而对思想家和决策者产生影响。尤其是民主政体的国家中,民众的呼声是政治精英必须回应的,这直接关乎他们权力的延续。
决策者按照一定的思想理论设计了一种政治制度,但在实践中可能发现制度的理念并没有体现出来,因此可能对制度做进一步修正。但也可能存在另一种情况,即依据某种理念设计的政治制度在实践中遇到了阻碍,可能导致理念的改变,进而影响制度的改变。导致改变的诸多原因中,固有的文化传统无疑是最重要的。同样的制度之所以在不同国家有不同的变种,在于大众文化的作用。大众文化有如制度机体中的血液,无论是修订还是改变制度,构成制度的血液特质应该是一致的。如果不一致的话,或者改变血液本身的性质,或者找到匹配的血型,否则制度本身很难维系。但是改变血型本身的性质往往是困难的,找到匹配的血型相对较为容易,最终大众文化逼迫决策者改变制度。在中华民国建立之初,孙中山强调民主较多,主张议会对总统的制约。但是在以后的革命实践中,用民主方式管理下属、领导革命时处处碰壁,最终使他的思想由民主趋向于集权,在建立中华革命党时要求党员向其宣誓效忠。
上述几种因素中,有影响的是学派和学者的思想,包括对政治制度的批判及其设计的政治制度方案,更重要的是提供的评判制度的原则,譬如目前流行的民主、自由、平等、人权等标准皆是西方近现代以来诸多思想家的贡献。决策者的思想,既体现为自己的思想对制度的影响,更体现为对诸多思想家提出的方案的抉择。民众作为制度的接受者,往往受制度的影响较大,主动性较小,但是大众文化是制度实践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以德国魏玛时期为例,当时德国已经建立了代议体制,民众能够通过投票选举领导人。但面临经济危机时,在希特勒的蛊惑下,民众通过选举把希特勒推上了权力的顶端。在此过程中,由于领导具有极端思想,民众具有威权主义心理,即使程序是正义的,但结果是非正义的。希特勒上台之后,强化了他的极权统治,思想家群体有的被排挤出走,譬如法兰克福学派;有的则充当了御用文人,譬如海德格尔,最终导致法西斯体制的形成。因此,即使体制是相对健全的,但是民众的政治素养没有达到相应的水平,容易受到极端领导的感染,从而导致思想的受压抑和体制的被扭曲*1931年,弗洛姆对德国工人阶级的政治心理进行调查时发现,德国工人阶级中的白领对纳粹情有独钟,参见Erich Fromm.TheWorkingClassinWeimarGermany:ApsychologicalandSociologicalStudy.Cambridge,Massachusetts:Harvard University,1984,p.209。1933年,赖希对德国工人的考察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他发现下中产阶级对专制的权威多采取迎合的态度,参见赖希:《法西斯主义群众心理学》,张峰译,重庆出版社1990年,第39页。。
(三) 政治制度对思想的影响
思想的形成受社会环境的影响较大,其中政治制度的影响无疑是最显著的。政治制度能够规范和节制人们的行为,决定着人们交往的范围和形式,从而影响着人们对政治的看法。政治制度对思想的影响可以分为直接和间接两种。
直接的影响体现为,作为培养政治思想的土壤,政治制度为思想家进行政治理想的设计提供借鉴和参考。譬如中国的春秋战国时期,为什么在诸子的国家设计方案中只有一个“君主”?是因为现实的社会中皆是君主统治各个诸侯国。而在古希腊,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为何会设计出多种政体?是因为各个邦国的政体是多元的。再如,英国久远的法律传统对英国保守主义思想的形成有着决定性的影响,这些有关法律的习俗包括:历史先例对后人的约束作用,规则是在悠久的习俗中形成的,是世代先人合作的结晶(冯克利,2015:161)。
同时,政治制度为人们的思维设定了框架,规定了思考的范围。尽管政治制度对极少数的思想家影响不大,但是对社会中的多数人还是有影响的。制度会通过制定详细的奖惩措施,对人们的言行进行节制,进而影响着政治思想的发展,也影响着思想家多寡,甚至是有无。纵观中国政治思想史的发展,春秋战国时期是百家争鸣时期,自汉代以后儒家独尊,直至明末清初才有了“启蒙”的味道,到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思想才进入真正的“现代”,突破了传统儒家思想的范式,各种思想流派纷纷出现,某种思想独领风骚一段时间之后,很快又被其他思想所代替。思想的繁盛与制度有着密切的关系,大一统时期君主保持极强的控制力和影响力,思想的控制也极为严格,很难产生有突破性和创造性的思想家。相反,君主的权威遭受质疑、大一统局面难以维系时,思想家的自由度增加,能够突破原来的禁区,从而创造了思想上的繁荣局面。我们在解读欧洲中世纪的政治思想时,也会发现类似的现象。在各国君主与教皇的较量中,教皇往往获胜,教会的势力远远超过了君主的势力。美国史学家汤普逊说:“它(指中世纪教会)到处行使的不仅限于宗教的统治,而且行使政治、行政、经济和社会的权力。它的管辖权推及到基督教国家中的每个王国;它不仅是每个国家中的一个国家,而也是一个超国家……它的管辖权是越过所有种族、民族、语言的分界限而通行无阻的”,于是在中世纪形成了教皇专制,“每个人都是教会的属民,他须对教会效忠;如果他反叛了教会,他将受处罚”(汤普逊,1998:261)。政教的这种特殊形态保证了教皇对思想异端的控制力,致使中世纪西方政治思想发展极为缓慢。
除了直接的影响外,政治制度对思想也有间接的影响。制度能够影响社会环境,规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它所营造的社会氛围会对人们的心理产生影响,从而影响着人们的思想、观念。譬如计划生育政策的实行,导致中国现在的家庭结构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形成了四二一的家庭结构,即四位老人、一对父母和一个孩子,孩子成为家庭的中心,直接冲击着“孝”的观念,进而影响了儒家思想在中国的实践。
政治制度对思想的影响还体现在,思想家和政治精英在提出自己的政治思想、观念时,往往是以影响制度的制定为目标的,他们以自己的想法能够在制度上得到实现作为自己思考的目标之一。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士人奉行“学而优则仕,货卖帝王家”的思想;近现代社会,许多思想家提出思想的目的在于为处于危难时期的国家提供治病的药方,挽救民族于危亡成为当时政治思想的主流。
(四) 政治制度之间思想的协调与碰撞
政治制度作为一套系统,由许多子系统组成。这些子系统所体现的思想有时是统一的,但有时是冲突的,子系统所体现的观念间的冲突,会影响整个制度体系的稳定,结果会导致其中的一些观念必须做出调整,以与整个系统总的理念相一致。中国传统的政治体制中,伦理政治的特色很明显,君权与父权相互支持,但是支持两套系统的“忠”和“孝”之间常常会发生矛盾,这种矛盾推动政治制度做出一些调整:一般情况下为君主效忠优先,但是在不损及君主根本利益的情况下,君主也会为“孝”大开绿灯。体现在制度中,“孝”成为官员评价的一个重要标准,一旦父母去世,官员还要辞去官职,为父母守孝三年。
在一些制度转型成功的国家和地区,譬如亚洲四小龙中的韩国、台湾地区,多遵循如下的规律:制度的改变先经济后政治,先边缘后核心。即首先对子系统根据一定的理念进行改革、试点,先易后难。渐进式的改革避免了子系统之间冲撞的剧烈,同时子系统的改革过程也是一个公民的素质不断提升的过程,从而为制度最终的转型成功奠定了基础。
四、 政治制度思想的研究意义
政治制度思想观念的提出对于政治思想乃至政治学的研究都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一) 为政治制度的合理性与否提供判断的依据
政治制度本身是否具有合理性,我们可能有许多的评价指标。如果仅从制度本身评价,可能会产生许多争议,但是有些制度如果还原其理论基础,则比较容易判断该制度是否具有合理性。譬如,探讨当今中国官员选拔制度所存在的问题,我们可以探讨当代选拔制度的人性假定。官员的选拔是察举制与选举制的结合,其中察举制有时是最重要的,察举的过程即是考察候任的官员是否是一个善人的过程,确定他是善人之后,就放松了对官员就职之后的监督。而西方的学者认为人们对利益的追求是自然和永恒的,不会因地位的升迁而有所改变。换言之,官员身在其位是有可能追逐利益最大化的,需要从体制上加强对官员的监督。由此可以看出,我们体制上存在的问题,根本上是制度所确立的人性假定问题。
有时人们对政治制度争论不休,但对一些观念却无争议。如果我们把制度进行思想的还原,就会发现制度与我们的常识所存在的不符。譬如我们都承认公平正义,但对高考如何改革却存在很大的争议。教育部曾经出台政策,敦促各地出台政策让异地的学子能够享受到本地考生的待遇。大家争论较多的是是否侵犯到当地考生的利益,但没有认识到目前高考制度的最大问题正是违反了公平正义。
政治制度思想理论的提出,意味着我们不要以僵化的眼光看待各种制度。有时,制度之间形似而实异,或形异而实似,判断的标准即是制度当中所蕴含的思想。综观欧美各国的发展,他们尽管号称代议制,但是各个国家的政治体制是不一样的。英国实行君主立宪,德国实行内阁制,美国实行总统制,法国实行半总统半内阁的混合制,但是他们的体制中所体现的民主精神是一致的。美国和萨达姆时代的伊拉克同样实行总统制,但是萨达姆的当选是不需要经过民众同意的,选举只是形式。
政治制度思想理论对于我们中国政治制度的改革也有启示。譬如,关于制度的改革以学习西方还是立足于中国国情的问题,理论界分为了右派和左派。左右两派尽管有所争论,但都承认民主的价值观,因此用民主的标准去衡量和评价制度即可,即现有的制度和改革之后的制度是否真正体现民意;换言之,民众的意见是否通过该体制得到实现,才是问题的实质。
综上所述,我们要区分两种思想:一是政治制度本身所体现的思想,二是建构制度时的原则、价值等等,后者是判定制度和制度中所体现思想的标准,以及政治制度发展的依据。
(二) 认清决策者的真实意图
设想多年以后,我们写某个领导人的政治思想,通常的做法是根据他所做的各种报告,写的各种文章等,然后撰写有关他的政治思想,但这样所揭示的思想可能是肤浅的,甚至是扭曲的。
决策者的思想往往具有两面性、模糊性和矛盾性,即他们提出了一些想法,这些想法之间本身可能就存在冲突。提出这些想法,可能是满足支持他的利益集团的需要,也可能是回应民众的需要等等。同时有些想法是决策者的真实意图,有些则是决策者的违心之论。如何判定哪些属于决策者的真实意图,政治制度的制定无疑是一个重要指标。因为尽管决策者的想法与制度中所体现的观念之间不是一一对应的关系,但是却是对政治制度变迁最大的影响者。譬如中国古代的君主号称以民为本,有些则赤裸裸地宣扬君权至上。而西方许多候选人在竞争时也提出了许多激进的口号以吸引选民的注意,譬如美国的一些总统候选人在竞争时提出反华的口号。如何认清这些政治精英的真实想法,制度或政策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评判标准,他们的许多想法在制度上要有所体现,而制度本身是客观、真实存在的。
清末立宪也是这样一个例子。尽管清政府派五大臣出使五国,他们出使之后建议清政府“欲防革命,舍立宪无他”,清政府也实行了君主立宪,但一系列制度改革暴露了其真实的意图:假借立宪之名以维护君主专制之实。从最初改革中央官制,到颁布《钦定宪法大纲》,设立带有咨询性质的资政局和咨议局,以及成立皇族内阁等等,改革的结果是清政府并没有放弃君主专制,从而与立宪派产生激烈的冲突,导致了立宪派最终抛弃幻想,奔向革命(陈旭麓,1992:230-256)。
官场有句俗语:有的只能说不能做,有的只能做不能说。政治制度当中即有一些属于决策者不能说但已经做了的,能够补充、完善决策者的政治思想。从某种意义上说,政治制度或政策是决策者思想的最终结果,是其真实意图的表现。譬如民本和君本的争论,单纯从思想家的争论,或者皇帝的言论进行分析,有时是分不清的,但是分析制度本身所蕴含的思想时就一目了然,即中国古代君主专制的体制从没有改变,体制的设定是为君权服务的,提出民本只是维系君主的权力。
(三) 对思想家有着更为准确的认识
目前政治思想史的研究多从思想家本身的思想逻辑以及学术史的演变等角度对之进行评价,忽略了对当时社会背景,尤其是制度环境的考察,从而导致了对思想家的评价往往容易出现偏差。从政治制度思想的视角考察思想家,则会对其思想在历史上的作用有着准确的定位。具体来说,可以体现在两方面:一是思想家的思想对政治制度的影响;二是制度的环境对思想家思想的影响。
思想家的思想与社会现实之间不是呈正比的关系,即不能单纯以思想家提出的思想是否为当时社会所接受作为唯一的标准。一个社会得以维系,思想家和决策者之间的关系应该是:思想家领先于这个时代提出自己的思想,而决策者对思想家提出的诸多建议能够有清晰的判断,最终在制度和政策上有所体现。但思想家的思想能否影响制度的建构受诸多因素的影响:譬如思想家提出的思想过于超前,为当时人们所不解;或者统治者出于自身的利益考量,甚至是昏庸。在考察中国历史的发展时不难发现,有些朝代末期不乏有识之士,提出了许多有意义的思想,不但对当时甚至对现代的社会治理都有所启示,但当时的统治者与思想者之间的关系出现了断裂,思想者的建议无法进入决策渠道。譬如明朝末年,出现了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三大家,但是他们的思想却很少在制度上有所体现。
但是思想家的思想不为自己的时代所理解,也可能被后世所接纳;不被昏庸的统治者所认识,也有可能被后世的统治者所欣赏。如果两者都不是,那极有可能是思想家本身的问题了。思想家对当时乃至以后的社会是否产生影响尽管不是唯一的,但应该是重要的标准。
政治制度思想的视角会防止我们评价思想家时出现过多的波动。学者们在评价某个思想家时,可能局限于自己的时代,对思想家做出夸大或贬低的评价,譬如孔子在中国历史上的形象就有不同的变化。但思想家的思想与制度的思想之间应该是一种客观的存在,如果准确把握思想家所提出的思想与制度的设定之间的关系,对思想家在历史上的定位就相对比较准确。譬如,有关人性问题,儒家的孟子主张性善、荀子主张性恶,同样韩非子也主张性恶,那么究竟哪一种观念对制度的影响更大呢?儒家的人性思想在制度上有所体现,即自汉代以后,运用儒家经典对民众、士人进行教育,但在核心的制度设计上,韩非子的人性恶观点无疑具有最重要的影响,即韩非子认为官员是逐利的,君臣之间是一种利益的交换。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设计,一方面突出了君权至上的观点,另一方面则体现了权力制衡的观点,即官员之间互相牵制,这种制度设计明显是基于人性是逐利的假定。同时,这也能解释儒家和法家在政治思想中的地位。
再如,明末清初三大思想家,如果单纯从他们的论述与现代所谓西方近现代思想家有关民主、公私、人性等的论述比较会发现某些相似性,因此有些学者认为他们的思想具有启蒙意识,断言如果清兵不入关,中国能够自我走进资本主义社会。但是如果我们按照同样的方法对先秦诸子的思想进行考察,也可能得出先秦的思想家已经具有启蒙意识,如果没有出现君主专制的秦汉,中国可能很早进入资本主义社会。问题出在哪里?出在单纯拿中国古代的某些思想观念与西方近现代出现的一些思想观念相比较,忘记了这些思想家或流派本身具有的逻辑、体系,应该从当时的社会背景以及这些思想家的整个思想体系了解这些思想的含义。社会背景中,政治制度的分析无疑占据重要的内容。
由于忽略了对当时社会背景尤其是制度环境的考察,人们对思想家的研究往往容易出现偏差。譬如,一些学者经常会赞扬东汉末年的清议运动、明朝末年的东林党,把他们与宦官斗争归为士人的自觉等等。相反,对当代以来的知识分子则普遍持贬低态度。如果我们仔细分析当时的政治制度、政策,以及制度、政策影响下的社会组织、人际关系网络等等,就可能不会出现厚彼薄此的现象。换言之,与士人意识觉醒相比,制度构建的社会环境往往对人们的思想、行为的影响更为重要。
参与以色列对二战后德国纳粹罪犯艾希曼审判的思想家汉娜.阿伦特曾经提出“平凡的邪恶”命题,认为这些罪犯中的许多人,与普通人无异,但他们为何会犯下杀人的罪行,在于他们只是整个战争系统的一个零件,没有思考,只是按照上级的指示行事(阿伦特,2011:42-43)。后来,米尔格莱姆在耶鲁大学进行了一系列的“服从权威”实验,结果证明了“平凡的邪恶”,即许多普通人,在处于相同的实验环境下,会服从尊敬的上级(耶鲁大学的教师)的指令,对一个普通的中年男人进行电击(Milgram,1974:13-31)。津巴尔多招募学生参与的斯坦福监狱实验也发现,尽管这些学生素质较高,但在斯坦福大学模拟的监狱实验中,扮演狱卒的学生在实验不到一周时,暴力倾向渐显,出现虐囚的现象。至于其中的原因,津巴尔多回应了阿伦特的观点,认为情境力量导致了“平凡的邪恶”的出现。情境力量是由规则、法律、政策等各种外在压力下所塑造的(津巴尔多,2010:1-23)。从以上的研究可以得出如下的结论:处在同样制度所创造的环境下,你也可能变成刽子手艾希曼,电击中年男人的被试者,或是虐待罪犯的狱卒。
我们不否认思想家个人的道德、精神在批判和思考中的作用,同一制度环境下,有人对社会批评,有人一味迎合社会,就是个人的道德、精神的差异。但是综观中国乃至世界历史,一个时代思想家辈出,但在另一个时代思想家又屈指可数,很明显是不同制度影响下的社会环境所致。只有结合当时的时代,尤其结合当时的制度所营造的环境,我们才能对思想家的思想有着准确的定位。
(四) 为政治思想史的编写提供更好的思路
单纯从政治思想的演变或结合制度思想的考察,两者可能会得出不同的结论。限于笔者的知识局限,仅就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编写提一些看法。
从政治思想的发展过程来看,汉代与秦代的政治思想差异很大,秦尚法,汉尊儒。但从政治制度思想的角度来看,两者的差异却没有那么明显。汉朝的政治制度承袭秦朝,制度本身改变不大,这也就意味着两者所体现的政治思想差异不大。尽管两个朝代各自打着尚法和尚儒的旗帜,但是两个朝代的政治思想是相近的。这可以印证刘泽华先生有关王权主义的判断,即无论儒家、法家,还是墨家、道家,他们的思想有一个主旨,那就是王权主义。崇尚君主的绝对权力,秦、汉两朝统治者的治理理念是相同的。
再者,儒家何时官方化的问题。传统的说法是汉武帝时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时,对此的判断完全是根据董仲舒的上书。但我们忽略了另外一个问题,即独尊和官方化是两个不同的命题,独尊之前必须有一个官方化的过程,官方化是前提,独尊是结果。对于官方化的研究我们可以从儒家的思想与汉代制度的互动来探讨,即哪些政策采纳了儒家的思想,由此判断儒家的官方化应该是汉惠帝时。
再者,对儒、法的争论也是如此。自儒家独尊之后,就有阳儒阴法的说法,以汉宣帝最为著名。究竟是否如此呢?通过对汉代的政治制度分析不难发现,许多制度的建构是基于法家的思想。尽管统治者口里不再说法家,但法家的思想、理念却在制度中得到了体现。
最后,思想史的编写者还面临着这样一个问题:一些时代思想家出现的并不多,有时越逢盛时越容易出现这样的现象,但是政治制度本身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给我们提出了一个研究政治思想的新视角。以当代为例,如果要写当代政治思想史,按照以前列传式研究的做法,就会发现除了三代领导人的思想外,几乎没有思想家。但是当代的制度却经历了多次变化,探讨这些制度变迁的思想内涵,进而分析制度存在的利弊,无疑为当代政治思想的写作提供了更好的思路。
五、 结语
政治制度能够顺利运行,除了得到各方的支持、政治系统各个组成部分协调发展外,很重要的一点是能否符合历史的潮流,尤其是在当前世界全球化的浪潮下,还要迎合世界的发展趋势。由早期的拉美照搬美国,20世纪90年代的东欧巨变,以及近期的阿拉伯之春,我们可以得到如下的启示:作为被革命的一方往往故步自封,逆世界潮流而动,最终导致被历史的潮流淹没;而作为革命的一方,盲目吸收西方的政治思想和体制,结果使国家的经济持续低迷,甚至长久陷于内乱之中。
具体到中国来说,政治制度应该如何发展?从制度思想的视角来看,目前中国政治制度的建构存在两大问题:一是缺少有影响的学者和思想流派对当前的中国政治制度进行分析、评判,进而提出设计理念。多数学者对中国政治制度的研究,要么坚持过去,要么盲目照搬西方,并没有涌现出带有中国特色的思想家。二是思想的共识和制度中体现的思想的差异。具体说来,中国从中央到地方,从精英到普通民众,对许多观念达成了共识,这些共识同时也被世界认可,但是这些观念并没有在制度中很好地体现,甚至与制度中的思想相冲突,这点是我们在更高层级的制度改革时需要注意的。
参考文献:
[1]阿伦特(2011).耶路撒冷的艾希曼.孙传钊译.载孙传钊编.耶路撒冷的艾希曼:伦理的现代困境.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
[2]彼得斯(2011).政治科学中的制度理论:“新制度主义”.王向民、段红伟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3]陈旭麓(1992).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4]冯克利(2015).柏克保守主义的法学来源.文史哲,5.
[5]何俊志、任军锋、朱德米编译(2007).新制度主义政治学译文精选.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
[6]津巴尔多(2010).路西法效应:好人是如何变成恶魔的.孙佩妏、陈雅馨译.北京:三联书店.
[7]赖希(1990).法西斯主义群众心理学.张峰译.重庆:重庆出版社.
[8]刘泽华主编(2014).中国政治思想通史:综论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9]马奇、奥尔森(2011).重新发现制度:政治的组织基础.张伟译.北京:三联书店.
[10] 诺思(2008).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杭行译.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
[11] 施特劳斯(2003).自然权利与历史.彭刚译.北京:三联书店.
[12] 斯金纳(2002).近代政治思想的基础:上卷.奚瑞森、亚方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13] 汤普逊(1998).中世纪经济社会史:下册.耿淡如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14] 王乐理主编(2005).西方政治思想史:第1卷.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
[15] 萧公权(1998).中国政治思想史.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
[16] Erich Fromm(1984).TheWorkingClassinWeimarGermany:ApsychologicalandSociologicalStudy.Cambridge,Massachusetts:Harvard University.
[17] Stanley Milgram(1974).ObedienceToAuthority.New York:Harper & Row Publishers.
■作者地址:季乃礼,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天津 300350。Email:jinaili@nankai.edu.cn。
Political Institution, Political Thought and Thought on Political Institution:An Effort of Theoretical Construction
JiNaili(Nankai University)
Abstract:Formerly scholars often looked political institution and political thought as two extremes. This tendency has resulted in the separation of studies on political institution and those on political thought. In fact, the two sides are not opponent, but interactive. On the one hand, political institution creates an atmosphere to frame political thinking; on the other hand, scholars’ or decision makers’ political thoughts influence and push the development of political institution. At the same time, the two sides have an overlap: the thought on political institution. To propose a theory of political institution and political thought, there are much significance as follows: as a standard to judge the rationalization of political institution, as a microscope to see clearly the true ideas of scholars or thinkers, as an new perspective to write the history of political thought, or as a new idea to develop the Chinese political systems.
Key words:political institution; political thought; the thought on political institution
DOI:10.14086/j.cnki.wujss.2016.04.005
基金项目:■南开大学亚洲研究中心资助项目(AS1401)
■责任编辑:叶娟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