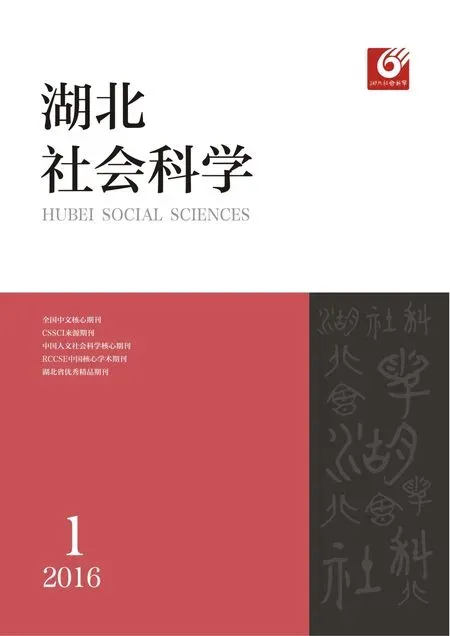论协同治理的内涵、价值及发展趋向
张贤明,田玉麒
(吉林大学行政学院,吉林 长春 130012)
论协同治理的内涵、价值及发展趋向
张贤明,田玉麒
(吉林大学行政学院,吉林 长春 130012)
协同治理是全球化时代,由跨越组织、部门和空间边界的公共部门、市场组织、社会组织或个人相互协调合作,共同解决棘手公共问题的整个过程,可以从政策制定过程、构建良善关系和善治实现方式的维度对其内涵进行阐释。作为一种新型治理策略,协同治理的重要价值在于能够通过鼓励公民参与使新兴民主得以巩固、衰退型民主能够复兴,并通过多元协同提升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的供给质量。协同治理是对现实治理难题的回应,在产生、达成与运行的不同阶段表现出特有的实践取向;而作为新兴研究领域的协同治理在理论探讨还落后于实践,需要在内涵的本质属性、利益相关者的相互关系以及运行机制的内在机理等方面进行深入研究。
协同治理;民主巩固;公民参与;民生改善;发展趋向
协同治理倡导多元治理主体(包括公共部门、企业、社会组织和个人)在资源与利益相互依赖的基础上共同参与决策制定,并协同解决公共问题。作为公共事务治理的新策略、解决公共问题的新机制,无论是美国、英国等西方国家,还是韩国、日本等亚洲国家,抑或处于民主进程、经济发展相对缓慢的发展中国家,都不同程度地出现了协同治理的踪迹。当下中国环境保护、危机管理等领域也已经开始了协同治理的有益尝试。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背景下,协同治理的内涵如何阐释、价值如何呈现、特性如何分析、理论如何发展,现有的研究仍稍显薄弱,值得深入探讨。
一、协同治理的内涵:词源学分析与多维度阐释
协同治理在实践领域的兴起已经引起学术界广泛回应。但如何从学理角度对其内涵进行有效分析,目前仍缺乏必要的界定,特别是相似概念的并行使用加剧了理解的难度。基于此,对协同治理的内涵进行梳理与分析是十分必要的。在词源学分析的基础上,将其与相似概念进行辨异可以更好把握协同的特征;同时,从多维度对协同治理进行考察则有助于从更加全面的角度理解协同治理的内涵。
(一)“协同”界说:词源学分析与相似概念辨异。
理解协同治理,有必要界定“协同”的概念。从词源学的角度来看,“协同治理”的英文形式是“collaborative governance”,也就是说“协同治理”中协同对应的英文单词是“collaborative”,其名词形式为“collaboration”,动词形式为“collaborate”,可译为“与他人共同工作,特别是为了生产或创造某一事物”。这里的“协同”指涉不同主体之间为实现一致
的目标而共同行动,强调公共领域治理主体的关系范畴,主张“共同行动”或“共同治理”。在英文语境下,与“collaboration”相似的单词还有“cooperation”和“coordination”,分别为合作与协调之意,而区分合作与协调之间的不同非常重要。[1](p24)Cooperation强调参与者之间的非正式关系,coordination则注重参与者之间正式的组织关系。三者有时候可以相互替换使用,学者们倾向于从关系正式程度来区分它们,如安德鲁·格林和安·马赛亚斯按照组织的扁平结构、自治程度和沟通强度,把组织间关系划分为竞争、合作、协调、协同和控制几种,这几种关系构成了一个连续体(continuum),合作位于这个连续体的较低一端,而协同则靠近较高一端。①Andrew Green,Ann Matthias.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and Health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London:Macmillan Press Ltd.1997,p.182.Collaboration一词在国内有多种翻译形式,如协同、协作、合作等,中国台湾地区则翻译为协力,本文采取协同的译法,在引文中则尊重原文。马蒂西奇和蒙西把协同定义成“由两个或更多组织为了实现共同目标而建立的一种互利且良善的关系模式”。[2](p11)国内学者汪锦军也持相同意见,他认为“cooperation”“coordination”与“collaboration”的层次是逐渐递进的。“协作(collaboration)是一种更为持续和深入的相互关系,它将过去分立的组织整合到一个需要完全为实现共同使命承担义务的新的结构中。”[3](p82-83)姬兆亮等人也认为,协同“既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合作,也不是简单的协调,是合作和协调在程度上的延伸,是一种比合作和协调更高层次的集体行动。”[4]这些辨析为区分与协同治理相似的几个概念如合作治理、协作治理等提供了语义和学理基础。
根据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归纳出有效、真实的协同具有以下几个特征:第一,协同具有目标一致的特征。不同主体构建某种关系,形成某种组织,必然以共同目标为主要纽带,通过共同目标把不同参与者凝聚起来。第二,协同具有资源共享的特征。在参与主体完成共同目标的过程中,需要彼此之间共享信息、知识与资源,是对公共资源的重新优化配置。第三,协同具有互利互惠的特征。协同的前提条件是参与主体在相互信任基础上的互利互惠,实现协同过程的信息、知识、资源共享;同时作为共同体的成员之间应该排除私利的诱惑与影响,实现成员之间利益共赢。第四,协同具有责任共担的特征。通常情况下,一般治理理论强调治理的多中心,实际上,多中心则意味着无中心,特别在需要承担责任的时候,多主体之间往往存在责任边界模糊、责任划分不明的问题,而协同则强调参与主体共同承担协同行动的责任。第五,协同具有深度交互的特征。协同意愿的达成与协同行动的开展需要各参与主体对行动策略不断进行谈判与协商,即使在协同行动的过程中,各参与主体也会相互依赖,他们的认知与行动都交织在一起。
(二)协同治理的内涵:三个维度的阐释。
第一,作为决策制定过程的协同治理。巴巴拉·格雷将协同治理看作一种寻求复杂问题解决办法的进程,认为协同就是不同党派超越自身视域局限,发现问题的不同侧面从而更好地理解彼此间差异,并试图寻求问题解决办法的全部过程。[5](p5)其关注的焦点在于寻求弥合党派差异裂缝的方案进程。克里斯·安塞尔和艾莉森·加什则将协同治理理解为,“为了制定与执行公共政策或管理公共项目与财产,一个或多个公共机构连同非政府利益相关者直接参与制定正式的、目标一致的、审慎的共同决策过程”。[6](p543-571)协同治理旨在为某个特定议程制定可行的决策,这一决策过程具有开放性。他们特地强调协同治理的决策制定过程区别于弗特勒尔与威廉姆斯等人所说的管理主义的决策制定模式。管理主义的决策制定模式是单方的、封闭式的,决策制定依赖于公共政策专家,而协同治理要求利益相关者直接参与决策制定的全过程。柯克·艾默生等人继承并扩展了克里斯·安塞尔和艾莉森·加什关于协同治理是决策制定过程的定义,认为决策内容在传统公共管理之外应该增加跨域治理;决策参与者扩展到政府部门之外,包括私人部门、公民社会以及社区,还有诸如以公私合营、私人社会为表现形式的联合政府或混合网络等组织。当协同治理被视为一种决策制定过程时,其核心关注点是如何确保参与者在场的情况下制定出合理有效的解决复杂问题的决策,而这些决策正是源于那些能够为集体理性选择提供行动指引且保证结果有效的协商过程。
第二,作为构建良善关系的协同治理。同其他治理理论观点一样,协同治理主体具有多元化的特征,其先进之处在于对主体间关系的探索与重新规
定。治理理论之所以受到一些质疑,甚至出现治理危机,重要原因在于尚未构建良善的主体间关系。因此,皮埃尔·卡蓝默才得出“明天的治理再也不能忽视了关系,而是应将关系放到制度设计的中心位置”的结论。[7](p11)协同治理正是一种关于治理主体关系的理论。有国外学者指出“协同关系是民众与诸如学校、企业等不同行业的组织为实现共同目标而结成的联盟关系”。[8](p74)这种联盟关系是普遍且持久的,它使以前分散的组织在全新的协作框架内完成共同的使命。在结盟关系中,不同主体之间是相互平等的,彼此之间享有平等参与决策、协商与谈判的权利,他们并不是上下级的隶属关系,而是工作上的合作伙伴关系。而且,这种关系是自愿的,并不具备强制性。虽然是一种积极的关系,但各个组织还会保持自主性、完整性和独立身份,甚至存在脱离这种关系的潜在可能,因为“真正的协同是开放的、透明的、包容的和负责的”。[9](p86)既然不具有强制性,那么协同关系又何以可能呢?原因在于协同有助于建立信任和确定性。协同治理可以通过信息共享建立共同理解,这既有助于能动者明确共同目的,又能提供必要的相关知识,其有益结果便是能动者彼此建立信任关系。在这种信任关系中,彼此之间形成一种承诺:对于共同关系与目标的界定;共同的发展结构与责任共担;走向成功的共同职责与义务并且共享资源与收益。[2](p39)至此,协同治理的参与主体形成良善的关系。
第三,作为善治实现方式的协同治理。国外学者指出,协同治理的出现,深深地根植于现实情境与公共行政过程之中,它对于公共管理者来讲已经势在必行,权力下放、技术变革、资源减少、组织间依赖性增强都大大提升了协同的水平。[10](p20)协同治理逐渐被视为一种更加有效地实现共同善治目标的方式。美国土地联盟在2006年年会上形成的“Collaboration Best Practices for the Conservation Community”决议提出,协同就是具有多元利益的个体为了共同的目标聚合起来,协同治理的过程可能涉及谈判,但其必须紧紧围绕共同的目标和共享的目的而展开。[11]以更加有效的手段与方式实现共同目标、解决共同问题是协同治理的价值所在。正如公民共和主义者主张的那样:相比于个人,协同更加强调对于社区或国家的承诺与义务。他们认为协同治理是一个整合过程,把分歧作为审议的基础以达成共同理解、集体意志、信任同情并实现共同利益。通过协同治理实现共同目标的过程往往是积极的,它至少应该能够产生更好的组织效能并降低成本。[12](p17)协同治理可以被看作一种正能量,它可以使协同更加有效、具有创造性、引起变革、带来有益成果。[13](p3)相比于国外学者含蓄的提法,国内学者提出了更加明确的观点,比如燕继荣将协同治理视为第三代善治理论,认为协同治理是公共事务治理的新趋向。[14]李辉和任晓春也提出“协同治理为实现善治提供方法和途径”,认为协同治理能够创造条件保证社会秩序和集体行动。[15]而现实领域的实践也证明了协同治理在实现善治方面的优势与价值,在美国的公共健康领域,公共或私人组织结成伙伴关系,共同计划、管理并评估社区卫生体制;在教育领域,跨部门协同在特许学校的发展与维持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由此而言,无论从理论角度还是实践角度,都在诠释着协同治理作为实现善治途径的重要意义。
二、协同治理的价值:民主巩固与民生改善
协同治理作为一种新型国家治理模式,逐渐成为对抗性、管理型政策制定与实施模式的替代者,允许公私不同利益相关者进入决策制定过程,正是开放性的决策方式与针对性的公共议题使其至少在民主巩固与民生改善两个层面体现出独特价值:
(一)公民参与与民主巩固。
20世纪初,公共行政学科的兴起确定了政治与行政的二分法,将公民参与限制在界定国家意志的政治领域,认为“公民参与日常行政管理活动是对政府日常工作细节的监督和政府日常管理措施的选择直接施加批评,这无疑是一种笨拙的妨害,就像乡下人操作难以驾驭的机器”。[16](p197-222)这种理念将公民与行政官员相互隔离。实际上,公民参与是民主的题中之义与内在要求。科恩在谈到民主的尺度时认为,“民主决定于参与——即受政策影响的社会成员参与决策”。[17](p12)无论是民主的广度(取决于社会成员是否普遍参与)还是民主的深度(取决于参与者参与是否充分、参与的性质)都与公民参与密切相关。罗伯特·达尔提出的民主过程的五项标准中,第一条便是“有效的参与”。他认为,“在政策被社团实施之前,所有的成员应当拥有同等的、有效的机会,以使其他成员知道他对于政策的看法”,[18](p43-44)否则,就会造成决策权实际掌握在极少
数人手里的情况,这有悖于民主原则。
公共行政学将公民参与排除在行政领域之外,造成了民主与行政的分离。然而,在公共行政实践中,民主与行政却是无法截然分开的。从公共行政的性质和目的来看,它执行公共决策、进行行政管理的最终指向是服务于社会发展和公共利益的,因此,公共决策的制定与执行必须遵循民主的原则,接受社会公众的监督甚至批评。从这个意义上讲,公共行政无法回避公民参与问题。协同治理理论认为,公民不仅是治理的对象,而且是治理的主体,并承认参与主体在协同过程中的平等地位,主张不同参与主体均具有参与议题讨论和政策制定的权利。这些主张和观点与民主的基本原则相一致,“协同治理理论契合了公民参与的民主理想,并为其发展与完善提供了一个崭新的契机”。[19]亦即,协同治理对于民主的巩固与复兴是通过公民参与实现的。
公民参与对于民主发展起着重要的促进作用,但是对于不同阶段的民主过程,公民参与的作用类型是有差异的。公民参与对民主的作用可以分为巩固新兴民主和复兴衰退型民主两种类型。具体来看,对于新兴民主而言,公民参与主要起到巩固的作用,它可以将新兴的民主体制通过制度化的形式确定下来,并且使广大社会公众具有坚定的民主信念,能够形成持续的民主经验。韩国学者金先赫讨论了公民参与巩固新兴民主的五种方式:第一,公民参与能够洞察与鉴别被先前专制政权或(和)现存政党所忽视、低估或隐匿的新型议题与偏好;第二,它为个体公民自我表达和身份识别提供了更加直接的渠道,从而能够缓解公民间的疏离感和政治冷漠;第三,公民参与能够使社会团体内部的预期相对稳定,为居于统治地位的国家机关提供更多聚合性、可信赖、可控诉的信息资源;第四,它能够使行为符合民主规范,从而增强民主的合法性,使其成为“不二之选(only game in town)”;第五,公民参与能够为抗衡统治者的蛮横与专断提供潜在的蓄力与源泉。[20](p165-190)国内学者王绍光则强调公民社会的内部效应,认为公民参与社团可以培育合作习惯和公共精神,培育互信、互惠、温和、妥协、谅解、宽容的品性,培育与人交往、共事的交流技能,[21](p116)而这些品质与技能无疑对民主具有促进作用。如果说公民参与通过检视民主过程的问题、培育公民的民主规范来巩固新兴民主的话,那么它复兴衰退型民主则是通过缓解投票率下降和政治冷漠的方式来实现的。众所周知,投票率下降与公民政治冷漠是民主制度遭受的阵痛,也是民主衰退的外在表现。因此需要“探求一种新形式的民主来扩展参与的机会和民主的控制,使它不仅仅在那些民主程度可能极大加强的更小的单位,而且在更大的单位也一样”。[22](p320)协同治理以其动态性和多元性提升了公民的参与程度,在协同治理体系中,政府、市场、社会和公民处于相互依赖的协同网络之中,并不断寻求联系和互动。在这样的治理结构状态下,除政府之外,市场组织、社会组织和公民都能够平等地表达利益诉求、参与决策制定,并结成伙伴关系协力解决公共问题。正是在这样的过程中,公民能够更加理解民主的深切涵义,通过参与民主过程成长为具有民主意识的社会公民,更加关心政治,增强对政治的信赖感,通过参与民主获得满足感。就此而言,公民参与是提升民主绩效与质量的重要手段。
(二)多元协同与民生改善。
协同治理的另一项重要价值在于对改善民生有所贡献:它通过促成多元协同克服公共产品和服务供给过程中的缺陷,进而为公民提供生存和发展所需的公共服务。“不论人们如何评价一种政治生活的好坏,民生问题总是无法回避的一环,因为人们选择在一个共同体中生活、愿意接受一种政治安排,即使在最容易理解的层面上也可以看作是对自身生活质量的计算与考核。”[23]从这个意义上讲,国家治理的任务是增进人民的福祉,因为民生问题的产生与社会价值、分配不公紧密相关,已经具有政治属性,所以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全面深化改革必须以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为出发点和落脚点”。[24]而解决民生问题、增进人民福祉的基本途径就是提供人民群众所需的公共服务。
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变化、发展,人民群众对公共服务的需求呈现出复杂化的特点,无论从公共服务需求的规模上,还是从公共服务需求的内容上,都极具动态性、多元化。正是这种复杂性的出现导致传统公共服务供给模式的失效,即市场失灵与国家失败。市场在资源配置、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发挥了基础性作用,但是如果超越了某个极限,市场机制的作用则会逡巡不前。公共服务具有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两个特征,但市场机制却是以私人产品的排他性和竞争性为基础的。所以公共服务领域常
常会出现“搭便车”的行为,“在这种情况下,追求成本最小化、效益最大化的‘理性经济人’就会纷纷采取不付费而搭便车的行为,私人因提供公共物品会导致资源配置的损失而不愿投资,最终会导致公共物品的严重短缺”。[25]因此,政府需要承担提供公共服务的责任,以克服市场经济的外部性。问题是,政府供给公共物品同样会面临新的困境:一是政府对公共领域的干预无效,即政府采取的宏观调控政策在实践过程中力度不足或效力不够,无法弥补市场的缺陷;二是政府对公共领域的干预过度,这主要是政府采取的调控措施力度过大,超出了弥补市场失效的范围,造成正常运转机制的紊乱,反而破坏了公共服务的正常供给秩序。造成政府在公共服务领域调控失灵的原因有很多,比如内部性问题、分配不公问题等,但是有两点特别值得关注,一点就是由于社会保障、社会福利等公共服务的刚性增长,需要大量的财政作为保障,但是政府财政负担过重,无力承担日益增长的公共服务需求。另一点是社会群体呈现多样性,社会成员对于公共服务的需求也日益呈现多样化的趋势,政府回应能力不足,无法满足多样化的需求。
由此来看,单一主体无法完全回应人民对公共服务的复杂性需求,“公共服务的供给方式需要发生变革,包括寻求新的制度性合作伙伴”。[26](p75-90)这种变革的需求催生了协同治理模式的产生与发展,反过来,协同治理有效回应了这种需求。协同治理是政府部门、市场组织和社会组织相互协调、充分沟通,形成网络化的公共服务供给结构。这种供给结构通过纵向与横向的协调重组,有效利用各个供给主体的功能优势和资源条件,为社会公众提供整体性、无缝隙的公共服务。在纵向维度上,政府通过跨越层级和部门边界的协同实现政府内部公共服务供给力量的有机整合,可以摆脱刚性的部门职责划分与行政区域划分而形成的碎片化供给困境,通过政府财权关系与事权关系的转移与重组,有效回应公共服务的动态性需求。在横向维度上,政府部门、市场组织和社会组织通过权力与资源共享建立相互信任的协同关系,充分利用专有资源并发挥各自功能优势,生产并提供不同类型的公共服务,满足人民群众对公共服务的多样化需求。特别是对于现代福利国家来讲,生产和提供庞大的福利产品和公共服务使其背负了巨大的财政负担,甚至产生了财政危机,“面对财政危机日益严重和人民需求日趋膨胀的双重困境,政府开始引进包括非营利部门在内的私部门的资源与人力,以提供原来由政府提供的公共事务”。[3](p61)通过借助市场组织和社会组织的力量,可以使政府承载的压力分流,转移到其他合作主体,减轻政府负担。
三、协同治理的展望:实践取向与理论发展
协同治理具有极强的实践性,并且在实践过程中表现除了独特的实践品格。虽然协同治理的理论研究远落后于其实践,[27](p3)但近几十年来关于协同治理理论的探讨也取得了一定成果。国内外学者试图建立一个关于协同治理的理论模型,协同治理也形成了崭新的研究领域。综合来看,可以从实践与理论两个层面对协同治理的发展做出展望。
(一)协同治理的实践取向。
第一,协同治理的产生源于对现实的回应,同时受到历史传统和制度环境的制约。全球范围内许多国家的政府正面临着相同的问题与挑战,即社会公众不堪高额赋税的重担,并且认为政府未能代表他们的利益,也没有对公共部门及其合法性给予足够的重视。[28]特别是,面临后冷战时期全球化竞争加剧、政府财政预算紧张的局面,政府回应这种挑战的能力呈现下降趋势,进而在现实挑战与回应手段之间出现了较大的嫌隙。在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采取的多种应对措施中,较为有效的方式是政府开始寻求与非政府部门的合作,共同治理棘手的公共问题,将部分财政压力和职责转移到非政府组织,实现政府与非政府部门的协同治理。虽然协同治理已经成为世界范围内可见的现象,但不同的历史传统的制度环境还是对其产生方式存在影响。美国与韩国的事实印证了这种判断。美国是老牌资本主义国家,较早地建立起民主制度,在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支付过程中较早尝试了外包的形式,并逐渐成为美国政府的重要特征。外包这种形式逐渐由公共物品供给领域向其他领域扩散,并逐渐过渡到协同治理的模式。与美国不同,韩国虽然历史悠久,但其经历过朝鲜战争之后才建立共和政体,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国家。而且在发展过程中面临着“经济发展战略的后遗症”、“全球化时代的新问题”、“民主转型的阵痛”等困难,对国家治理产生了较大压力:经济发展战略的后遗症使社会失去平衡,全球化时代的新问题使政府不堪重负,民主转型的阵痛
导致社会间的矛盾不断。这亟须通过制度创新选择新型治理模式使政府、公民社会和市场以协同的方式共同制定公共政策,但其公民社会发展不充分的事实却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协同治理的发展。
第二,协同治理的达成基于利益相关者的理性判断,同时受到情感和文化因素的影响。协同治理的出现可能是受命成立,也有可能是自发形成,但其并不是无意识行为。从理性主义的角度看,利益相关者之所以参与到协同治理的过程,是因为他们能够从协同过程满足自己的利益诉求。比如政府关注公共价值与合法性,企业希望获得经济利益,非营利组织则对获取资助有所期待。而协同治理确实在政治上具有较大的吸引力,“因为它是政治家提前解决冲突的方式之一,也就是说潜在的输家和赢家可以提前就补偿性措施进行谈判”。[27](p10)问题的关键是,如何判断参与协同治理会获得利益还是要承担风险,即利益相关者关于利益和风险的感知会影响到他们的行为选择。如果利益相关者发现公共利益能够与私人利益达成一致,他们便有了协同治理的动力;“当非政府组织的行动者发现协同治理违背他们的利益时,他们会反抗政府,而不是与之合作”。[29](p33-43)通过理性计算判断利益和风险因素,是最简单有效的方法之一。此外,情感和文化在很大程度上也会左右人的利益和风险感知。迈克尔·穆迪在研究加利福尼亚州海湾三角洲供水系统的协同政策时发现,参与者对于“协同”的理解受到其所处环境“文化”的影响,这种“文化”有的可能源于国家政治文化层面,有的则是在特定政策议程设置过程中受到思考与言谈方式相互影响所致。[30](p13-32)崔仁实则深入研究了韩国火葬场设置过程中,情感和文化因素对居民与政府协同意愿的影响。他通过建立关于风险感知的文化启发模型以及经验数据的提取,发现居民与政府的合作意愿取决于利益和风险计算与情感反应、文化取向的相互作用,其中价值观、态度与党派等因素对利益和风险感知的影响较大。
第三,协同治理的运行要求权力与资源的均衡配置,同时重视领导者的特殊作用。虽然协同治理并不必然要求权力让渡,但是权力和资源的共享无疑对于协同治理是一个巨大的推动力。“如果参与者没有能力、组织、地位和资源与其他参与者分享,那么协同治理过程则倾向于力量强大的行动者”。[6](p543-547)一个显著的例子是,美国有些环保组织对协同治理产生强烈质疑,他们认为协同治理对实业集团更加有利。埃彻里维亚就因过度倾向于经济利益致使谈判失衡问题批评了普特拉河流域协同治理规划过程。他认为经济利益集团与环保人士拥有极为不同的能力,这是由于他们的选区相当庞大且分散,环保人士通常在争取选票过程中处于劣势,因为开发者联系得更加紧密而且更便于组织经济利益。[31](p559)如果没有替弱者发声的有效对策和中立的领导者,那么协同治理则会对弱者不利。实际上,领导者的特殊作用还体现在当协同过程面临难题时确保协同过程的完整性,一是对于不愿直接参与协同的利益相关者,领导者可以通过自身权威与魅力吸引其加入;二是当不同利益相关者无法达成共识甚至存在冲突时,领导者可以扮演协调者的角色。另外,领导者在制定并维护基本法则、建立互信关系、推动意见交换、探索共同利益等方面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6](p543-547)当然,领导人的作用也是相对的,受协同治理的具体情境影响,如果利益相关者的参与度较弱、权力与资源分配不均衡、成员之间的不信任感强、对抗性强,那么领导者的作用凸显,反之领导者的作用减弱。
(二)协同治理的理论发展。
第一,协同治理研究需要准确界定其内涵的本质属性。理论研究最基本的工作是对其内涵进行准确的界定。特别是对于治理理论研究来说,目前已经形成了一个相当庞大的论域,与其相关的术语也已构成了概念丛林。在治理群簇的视域下,如何将协同治理与其他概念区分,首要任务就是对其在治理谱系中进行恰当定位,关键则是对其内涵的本质属性做出准确的界定。另外,理论研究的目的在于应用,如果无法清晰界定其内涵,那么该理论的适用性则无法确定。国外学者对于协同治理本体规定性的探讨经历了“由种到属”(on the genus rather than the species)的过程,特别是柯克·艾默生等人对克里斯·安塞尔和艾莉森·加什定义的拓展具有代表性。国外学者对协同治理概念的解析除了具有“治理”属性之外,格外重视对“协同”的分析,格林和马赛亚斯、泰德·费尔曼以及埃米莉·莱等人均对“协同”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国内学者对于协同治理基本内涵的研究也形成了多种观点,但就目前研究来看,对于其内涵的理解并未脱离“协同理论+
治理理论”的框篱,而在更多的时候,往往把重点落在“治理”的描述之上,对于“协同”的深入阐述还有待提高。就协同治理内涵的基本属性研究而言,应该从更加广阔的视角去探寻,可以尝试从历史维度和多学科视角进行研究。
第二,协同治理研究需要深入探索利益相关者的相互关系。尽管对于协同治理内涵的理解从不同角度能够给出不同解读,但一个共识是协同治理的参与主体大概可以包括政府、市场、社会组织以及公民个体。既然是多元主体共同参与涉及特定问题的公共政策制定与执行,那么关于利益相关者相互关系的研究是不可回避的问题。利益相关者的相互关系不仅是协同治理实践层面的核心内容,也是理论研究的焦点议题。根据现有文献,研究者们都注意到了该问题对协同治理过程的重要影响,也试图对其进行有效分析。比如迈克尔·穆迪按照利益偏好类型将有兴趣参与海湾三角洲供水系统决策制定与治理的利益相关者划分成农业利益相关者、城市利益相关者和环境利益相关者三种类别,根据其不同的利益诉求确定它们在协同治理中的相互关系。[30](p13-32)目前来看,相关研究对于利益相关者之间相互关系的探讨仍然较为薄弱。主要问题则表现为这样几个方面:一方面是研究中心围绕政府展开,对其他主体的研究不够充分。如果将协同过程过多地围绕政府展开,则会有回到政府垄断治理的传统模式上来的风险,所谓的“协同”也就沦为其他主体配合政府行动的工具。另一方面是对于利益相关者相互关系的规定性研究不够。协同治理要求不同主体相互配合、协同行动,但目前的研究并没有充分揭示利益相关者相互关系的应然图景与实然状态。因此,协同治理的理论研究,应该向利益相关者的相互关系进行更加深入的探讨。
第三,协同治理研究需要细致分析其运行机制的内在机理。协同治理运行机制的研究一直是学者们关注的重点内容,因为分析协同治理的运作过程,是在实践过程中使协同更有效的重要途径。国外学者对协同治理运作机制的研究相对较早。彼得·史密斯·林和安德鲁·范德文描绘出了协同治理的过程框架,他们将协同治理看作“协商—承诺—执行—评价”的循环过程。[32](p90-118)伍德和格雷利用“前期—过程—结果”框架描述协同治理的运行机制,他们认为在整个协同治理的过程中需要历经三个阶段,而每个阶段又需要达成不同的条件。[33](p139)安·玛丽·汤姆森和詹姆斯·佩里则基于前二者的研究,对协同进行了多维度考察,绘制了“协同多维模型”,从五个关键维度将协同过程分解为“作为治理维度的协同治理过程”、“作为行政维度的协同行政过程”、“作为自治维度的协调个人与集体利益过程”、“作为关系维度的打造互利关系过程”以及“作为信任和互惠维度的构建社会资本规范过程”。[10](p20-32)关于协同治理运行机制的探讨也受到了国内学者的关注,比如郁建兴和任泽涛提出了“社会协同治理机制”,描述了政府主导、社会协同,共建共享的协同治理格局。陶国根提出了社会协同机制的模型框架,包括社会协同形成机制、社会协同实现机制、社会协同评价监督机制。相较而言,国内对该问题的研究还未充分展开,这与协同治理在国内发展尚处初级阶段有关。但为了确保协同过程更加有效,则有必要了解并规范协同的过程,甚至有学者提出公共管理者应该看到协同过程的“黑箱”内部。
[1]Jane F.Hansberry.An Exploration of Collaboration Organizational Effectiveness in Denver County Human Service Organizations.University of Pittsburgh,2005.
[2]Mattessich,Monsey.Collaboration--what makes it work:a review of research literature on factors influencing successful collaboration.St.Paul, MN:Amherst H.Wilder Foundation.1992.
[3]汪锦军.走向合作治理:政府与非营利组织合作的条件、模式和路径[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2.
[4]姬兆亮,戴永祥,胡伟.政府协同治理:中国区域协调发展协同治理的实现路径[J].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2).
[5]Gray,B.Collaborating:FindingCommon GroundforMultipartyProblems.SanFrancisco: Jossey-Bass.1989.
[6]Chris Ansell,Alison Gash.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in Theory and Practice.Journa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search and Theory,2007,Vol.18.
[7]皮埃尔·卡蓝默.破碎的民主——试论治理的革命[M].北京:三联书店,2005.
[8]Himmelman AT.Communities Working collaboratively for a change.Humphrey Inst.Public Aff., Univ.Minn.,Minneapolis.1992.
[9]Ted Fellman.Collaboration and the Beaverhead-Deerlodge Partnership:The Good,the Bad,and the Ugly.Public Land&Resources Law Review. 2009,Vol.30.
[10]Ann Marie Thomson,James L.Perry.Collaboration Processes:Inside the Black Box.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December 2006.
[11]American Lands Alliance,Participants of the National Meeting on Collaboration,Collaboration Best Practices for the Conservation Community,http:// www.americanlands.org/issues.php?SubsubNo=l 148069142(March 2007)[hereinafter Best Practices].
[12]Bardach,Eugene.Getting Agencies to Work Together:The Practice and Theory of Managerial Craftsmanship.Washington,DC: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1998.
[13]Janine O’Flynn,John Wanna.Collaborative governance:a new era of public policy in Australia? Canberra:ANU E Press,2008.
[14]燕继荣.协同治理:公共事务治理新趋向[J].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12,(17).
[15]李辉,任晓春.善治视野下的协同治理研究[J].科学与管理,2010,(6).
[16]Woodrow Wilson.The Study of Administration,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Jun,1887,Vol.2, No.2.
[17]科恩.论民主[M].聂崇信,朱秀贤,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
[18]罗伯特·达尔.论民主[M].李伯光,林猛,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19]杨清华.协同治理与公民参与的逻辑同构与实现理路[J].北京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2).
[20]Sunhyuk Kim.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in South Korea:Citizen Participation in Policy Making and Welfare Service Provision,Asian Perspective, 2010,Vol.34,No.3.
[21]王绍光.民主四讲[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
[22]罗伯特·达尔.民主及其批评者[M].曹海军,佟德志,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6.
[23]张贤明.民生的政治属性、价值意蕴与政府责任[J].理论探讨,2011,(6).
[24]习近平.切实把思想统一到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上来[N].人民日报,2014-01-01(2).
[25]严炜,刘悦斋.平等合作与积极竞争:公共服务领域中的政府与非政府组织[J].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4,(5).
[26]Hyun Joo Chang.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in Welfare Service Delivery:Focusing on Local Welfare System in Korea.International Review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2009,Vol.13,Special Issue.
[27]邓穗欣,丹尼尔·马兹曼尼安,等.理性选择视角下的协同治理[A].敬乂嘉.网络时代的公共管理[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
[28]Marc J.Hetherington.Why Trust Matters: Declining Political Trust and the Demise of American Liberalism 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5.
[29]Jin Sik Choi.The Roles of Affect and Cultural Heuristics in Collaborative Approaches to Conflict Resolution:Crematory Facility Siting in Korea.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2009, Vol.13,Special Issue.
[30]Michael Moody.Everyone Will Get Better Together:How Those Responsible for California’s Bay-Delta Water System Understand Collaboration.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2009, Vol.13,Special Issue.
[31]Echeverria John D.No success like failure: The Platte River collaborative watershed planning process.William and Mary Environmental Law and Policy Review,2001,Vol.25.
[32]Peter Smith Ring,Andrew H.Van De Ven. Developmental Processes of Cooperative Interorganizational Relationships.The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1994,Vol.19,No.1.
[33]Donna J.Wood,Barbara Gray.Toward a Comprehensive Theory of Collaboration.Journal of Applied Behavioral Science.1991,Vol.27.
责任编辑 申华
D035-0
A
1003-8477(2016)01-0030-08
张贤明(1970—),男,法学博士,吉林大学行政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吉林大学国家治理协同创新中心研究员。田玉麒(1988—),男,吉林大学行政学院政治学理论博士研究生。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理论阐释与实践路径研究”(12&ZD058);教育部重大课题攻关项目“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11JZD0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