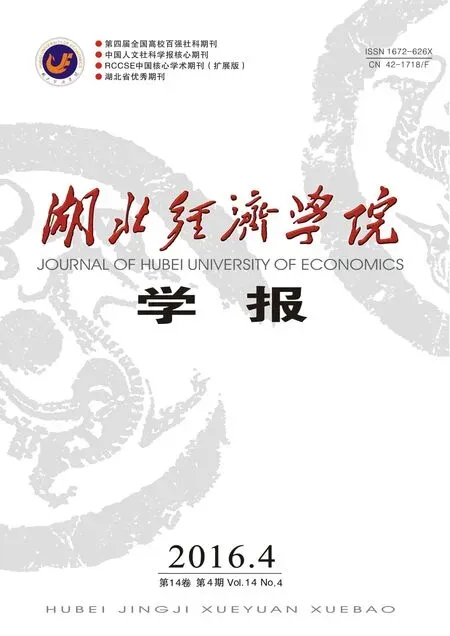刑法上“明知”之再探究
蔡士林,王惠敏
(1.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刑事司法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3;2.广西民族大学 法学院,广西 南宁 530006)
刑法上“明知”之再探究
蔡士林1,王惠敏2
(1.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刑事司法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3;2.广西民族大学 法学院,广西 南宁 530006)
“明知”的判定是司法实践中最基础最重要的环节,它决定出罪与入罪以及具体罪名,具体而言,明知是表达行为具有可罚性的内在征表,但判断其成立需要客观要素的协助,这也成为长期困扰理论和实务界的一大难点。2016年两高出台颁布《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其中第16条第2款关于受贿罪故意的推定将刑法中关于“明知”的理解推向了极点。我国现行刑法对于“明知”的使用存在“混搭”现象,故而造成了一系列困境,这使得学者不得不另辟蹊径。
明知;受贿罪;推定;刑法
一、问题的提出——“明知”概念的证成
刑法中的“明知”是作为故意犯罪判断的基本要素,据悉从1997年的刑法至今,包括9个修正案在内,法条中使用“明知”一词的有40个条文,①共计44处使用该词。具体而言,在刑法总则中只有刑法第14条关于故意犯罪的规定使用了 “明知”,其余的则集中在刑法分则中。由此便产生了一个问题,即如何看待刑法总则中的“明知”与刑法分则中“明知”的关系,而要解决这个问题,需要我们对于“明知”概念有一个明确的定位,正所谓“名不正则言不顺”。通过将“明知”与“应当知道”、“可能知道”对比,可以更深刻地认识“明知”。
(一)“明知”与“应当知道”
“明知”英语表达为“knowing”,这就表明其不同于“realize、notice”等从客观角度对于事物的认知,而是对客观的存在进行了主观认知的筛选,最终将其定义为涵盖认识因素和意志因素的集合概念。[1]在现代汉语中,“明知”的理解古今异义,通说将其拆开理解为表转折的副词。而后“明知”延伸到刑法领域,其含义便发生了改变,从目前我国的刑事立法来看,绝大部分使用的是“明知”,[2]如上文中统计的数据,44处使用“明知”,只有1处例外使用了“应知”,即刑法第219条第2款明知或者应当知道前款所列行为,以侵犯商业秘密罪论处。从这里的规定不难看出,立法者将明知与应知择一使用,其意在暗示明知与应当知道是有区别的。为了进一步界定两者的关系,有必要通过司法和理论两个路径加以梳理。
其一,司法解释路径分析。早在1997年刑法颁布以前,两高就出台了《关于办理盗窃罪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首次对“明知”进行了规定,只要证明被告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是犯罪所得的赃物而予以窝藏或者代为销售的,就定性为 “明知”。[3]换言之,我国以司法解释的形式将推定首次在主观认定上进行试验,这一规定开启了将“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作为犯罪中“明知”的司法时代。2016年两高出台《关于办理贪污受贿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中第16条第2款规定:“特定关系人索取、收受他人财物,国家工作人员知道后未退还或者上交的,应当认为国家工作人员具有受贿的故意”。该《解释》中明确使用“知道”而非应当知道,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国有的司法功利性和便利性的价值考量,但由于司法实践取证的现实困难,现有证据只要证实国家工作人员明知身边的人“不作为”,便推定其有受贿的故意。
其二,刑法理论路径分析。刑法理论界对“明知”和“应当知道”的关系展开过一场激烈的论战,归纳起来主要有三种观点。(1)排斥说。该学说认为,明知本意就是“明明知道”,而“应当知道”实际上是不知道,后者是过失对应的心理状态,前者是故意的心理状态,两者是绝对的对立,不应该将过失的心态表现解释成故意犯中的“明知”。[4](2)替代说。该学说认为,“应当知道”是一种“推定的知道”,法律规定的过失状态中的“应当知道”是一种用词不当,“推定知道”替代“应当知道”才是正确的选择。[5](3)包含说。该学说认为明知是最上位的概念,其包含应当知道,把故意视为对“不知道”的负责。此观点是从规范论的角度出发,不能主观地把故意仅视为“已经知道”,而要规范地把故意视为“应当知道”,即把故意视为“对不知道负责”。[6]在笔者看来,排斥说将“明知”和“应当知道”完全割裂开来,将其视为故意与过失的分水岭过于偏激,包含说无法将故意与过失做一明确的区分,替代说比较符合我国的现实情况,既不过分拔高“明知”的标准,也没有降低证据环节的要求。申言之,替代说在实质上符合从客观认知主观的心理判定规律。[7]
(二)“明知”与“可能知道”
“可能知道”是对客观事物认识的不确定状态表达,即其包含了知道或者不知道,各有50%的概率。换言之,可能知道是对特定犯罪对象的概括认识,是“明知”内部本身的一种表现形式,其不同于达到行为人内心确信的明确知道,只是达到了行为人内心的一种盖然的认识。[8]与其相比较而言,明知的一种为概率100%的客观化的主观表现。这种解释似乎符合普通人或者说平均人的认知标准。但当我们将法律受众的价值理念嵌入刑法法条中,会让我们处于另一种尴尬的境地。《刑法》第138条可谓对于国民法律自信的极大挑战,根据该条文的规定,理论上几乎毫无争议地认为,教育设施重大安全事故罪属于过失犯罪。[9]这就使得“明知”与“故意”犯罪的理论相背离。②或许有的学者会因此认为可以将138条作为刑法的一个例外。诚然,有原则必有例外,但例外和原则也有理念或者刑事政策上的依据。[10]笔者认为,总则中的“明知”指示构成犯罪的一般性概括式要素,而分则中的“明知”指示特定犯罪的具体唯一的要素。申言之,刑法总则的“明知”为初次的明知,而分则中的“明知”为第二次明知,两者是一个认识逐渐的过程。[11]可以认为,“明知”代表行为人对于行为在认识层面和意志层面的的最大值,可能知道则渐弱。有学者主张,“明知”未必是“故犯”,[12]通过刑法中的138条对“明知”的核心要素进行反击,其论证也难以自圆其说。其理由如下:其一,我们不能单凭刑法中一个条文的歧义,就对“明知”这个广为国民接受的含义予以颠覆;其二,对于刑法第138条出现的情形,我们可以通过司法解释或者刑法拟制的方式予以弥补。
(三)“应当知道”与“可能知道”
对“应当知道”与“可能知道”的区别解读尚未达成共识。有学者认为,“应当知道”的全称为“应当去知道”,或者“应当是知道”。[13]很明显前者侧重于义务,后者强调的是客观行为推定。也有学者认为,“应当知道”与“可能知道”是同意含义,只是措辞不同。[14]笔者赞成“应当是知道”这一观点,因为它一方面符合我国刑法中关于过失的描述,另一方面与我国语言的表达方式相契合,即一般情况下动词不予省略。
“可能知道”一词在上文中已经论证过,其表达的是50%概率的“明知”,当然这并不是一个绝对的估值,只是对事后结果平均值的反映。
综上所述,由于“应当知道”是对过失这种主观状态的描述,而“可能知道”是一个不确定的主观状态的描述。所以,“应当知道”的“明知”强度要略高于“可能知道”。换言之“应当知道”等于“不知道”或“不明知”。
二、刑法中“明知”类型化的结构分析
为了更深层次地理解“明知”,有必要将现行刑法条文中的“明知”适用予以类型化分析。
(一)交叉使用:在故意、过失犯罪中徘徊
我国将“明知”作为表达犯罪主观内容的主要方式之一,确切地说属于主观内容中的认识因素。刑法中法规罪名对其的拿捏主要分为两种情形:
1.捆绑式。其主要是指与故意犯罪相伴相生,成为描述故意犯罪的标准式搭配。例如刑法第399条规定,司法机关工作人员徇私枉法,徇情枉法,使明知无罪者受追诉、明知有罪者免受追诉才能构成徇私枉法罪。[15]除了刑法第14条关于故意犯罪的规定外,还有38处关于“明知”的应用,毫无例外都是对于刑法故意犯罪的表达。而刑法分则中的罪名,只要是故意犯罪,即便没有在法条中提及“明知”的字眼,也都潜在地要求行为人在认识层面上达到“明知”的标准。之所以不是所有的故意犯罪直接指明“明知”为其构成要素,笔者认为是由于总则的规定之后,故意犯罪的“明知”理所当然地覆盖到分则中,即使明确要求“明知”也不过是一种注意性提示。
2.例外式。主要是指“明知”出现在过失犯罪的规定中。上文中笔者也提及了刑法第138条关于教育教学设施重大安全责任事故罪,其规定直接责任人员明知……虽然学界绞尽脑汁为该特例做解读,但基本上都承认这是“明知”在过失犯罪中的大胆尝试。③其实纵观我国的刑事立法,此并非孤例,早期我国关于共同犯罪的描述,只有2人以上的故意犯罪才是共同犯罪,基于此排除了共同过失犯罪存在的可能性。但随后的司法解释将交通肇事罪的特定人员定义为共犯,打破了学界的惯性思维。不可否认,第138条是我国刑法的“创新”,但其意义如何有待考证。故在这种混合使用“明知”的情况下应该坚守原则,不可一味求新求变,而应将第138条中的“明知”改为“应当预见”或者“应当知道”。
(二)并列(选择)使用
在上文中笔者已提及我国刑法中关于 “应知”与“明知”同时使用的情形。在此需要说明的是,这里的“同时使用”并不是指“明知”与“应知”同时发挥构成要件的判定功能,而是选择性地使用但其在法律效果上是等值的。[5]我国对于“应当知道”这一术语的广泛使用源于1992年的司法解释,但几乎都是单独使用,并列使用仅此一例。对于本条文中的“应知”与“明知”的理解学界也是莫衷一是。大多数学者认为,两者是一种同位语的替换,但也有学者认为,从主观内容认识因素的强弱程度来看,“应知”是“明知”的下位概念,不可能同时使用。笔者认为,侵犯商业秘密罪为故意犯罪,我们不能因主观内容的考究而株连到原本犯罪属性。因为我国是以处罚故意犯罪为原则,处罚过失犯罪为例外,况且刑法谦抑性的要求也使故意犯罪的惩处成为主流。
刑法中将两者并列使用,司法解释中却将其分为上位概念,这使得适用上难以统一标准。由于刑法的法律效力要高于司法解释,笔者建议将刑法第219条的“应知”予以删除,只保留“明知”,唯此可依最少的立法成本来维系法的统一性。
(三)复合使用
复合使用主要是将“明知”与犯罪构成中的各要素相搭配使用,其中的犯罪要素为行为、主体、物和其他,如此便使得“明知”的使用更加多样化。我国刑法将刑法的法益或者说客体分为10类,而大陆法系国家的日本将法益分为对国家法益的侵害、对社会法益的侵害、对个人法益的侵害。以下为“明知”在我国分则中的分布:
1.明知与行为复合使用。由于行为是犯罪的核心要素,故而关于此种搭配的犯罪规定比较零散。例如,刑法中第219条、244条、285条、311条、350条、363条、429条、《刑法修正案(九)》第29条、38条、41条都分别做了相应的规定,包括明知“他人实施侵入、非法控制计算机信息系统的违法犯罪行为”、“他人有间谍行为”、“他人制造毒品”、“他人用于出版淫秽书刊”、“友邻部队处于危急请求救援”、“他人有间谍犯罪或者恐怖主义、极端主义犯罪行为”、“他人制造毒品而为其生产、买卖、运输前款规定的物品的”等。
2.明知与主体复合使用。这里的主体主要是指具有特定“身份”的人,这里的身份是指主体已经触犯刑法或被误认为触犯刑法的人。例如,刑法中第310条、373条、399条、415条便是如此,其表述分别为明知“犯罪的人”、“逃离部队的人、“无罪的人、有罪的人”、“企图偷越国边境、偷越国边境人员”。
3.明知与物复合使用。这里的物主要是指国家明令禁止的违禁品。例如,刑法中的第144条、145条、146条、147条、148条、171条、177条、191条、194条、210条、214条、218条、265条、291条、312条、345条、370条,其分别表述为明知是“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的食品”、“不符合保障人体健康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医疗器械、医用卫生材料”、“不符合保障人身财产安全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产品”、“假的或者失去效能的农药、兽药、化肥、种子”、“伪造的货币”、“伪造的信用卡”、“伪造的空白信用卡”、“毒品犯罪黑社会犯罪等所得的收益”、“伪造变造的汇票”、“不合格的武器装备、军事设施罪”。从上述列举不难看出,该类型下“明知”的使用较为集中,主要存在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犯罪中,且存在的比例也是最大的。
4.其他情形。主要存在于刑法第138条、258条、259条、360条、《刑法修正案(九)》第32条。其具体内容为明知 “校舍或者教育设施有危险”、“他人有配偶”、“有梅毒、淋病等严重疾病”、“上述虚假信息,故意在信息网络或者其他媒体上传播”。该种情形下的“明知”使用比例是最小的。
通过对于分则中“明知”的类型化分析,我们可以看出,“明知”的搭配从宏观上来说可以分为两大类:其一,主要是“明知”他人的行为已经是违法的,也可能还不构成犯罪,行为人通过作为或者不作为对其予以升华,便成为了刑法规制的对象;其二,要求行为人对于违法性认识的内容予以明知,笔者认为,这里的“法”不应局限于刑法,还应包括行政法,以此作为前置性条件。
三、“明知”在现实中的困境
通过对“明知”的概念考究和类型化分析,我们基本上对“明知”的内涵和外延有了明确界定,但现实中“明知”的司法实践却存在诸多难题。
1.法律表述不清。上文中笔者对 “明知”、“应知”、“可能知道”做了理论上的比较,但在涉及法律规范的表达上,表达不统一的现象频出。其一,从我国现行的刑法来分析。我国刑法第138条规定的教育设施重大安全事故罪是普遍认可的过失犯罪,但却使用了“明知”,这使得该规定与“明知”的适用规则格格不入。在“明知”是否适用于过失犯罪的问题尚未解决时,新的难题又产生了。我国刑法第219条关于侵犯商业秘密罪的规定将“明知”与“应知”置于同一法条之中,以立法的形式强行将“明知”与“应知”划等号。其二,从我国相继出台的司法解释来分析。我国关于“明知”最为著名的司法解释莫过于2003年 《行为人不明知是不满十四周岁的幼女而与其自愿发生性关系,是否构成强奸罪的批复》,该《批复》确立了奸淫幼女构成强奸罪应该以知道对方是不满14周岁的幼女为前提的审判规则,且指出:“不能将应当知道解释为明知的表现形式,应当知道就是不知,不知岂能明知?[16]而在2013年两高、公安部、司法部出台的《关于依法惩治性侵未成年人犯罪的意见》的司法解释中第19条对明知作了明确规定,④其最终确立了“明知”与“应当知道”等同的司法惯例。这些司法解释的合理性与否有待考证,但以上现状反映出我国无论是法律本身还是司法解释对“明知”的理解尚未达成共识。而刑法是以其严密的逻辑性来规范行为的,如违背逻辑性则难以承担保障人权的重任。[17]
2.“明知”认定困难。学界普遍将“明知”视为构成要件中的主观方面表现形式,对于刑法的发展起过重要作用。在主客观相统一的刑法背景下,行为论被提出,“明知”作为主观内容使得刑法的主观归罪得到控制,也符合人民心中对正义的观念。但我们所纠结的是“明知”在诉讼实践过程中给司法机关带来了证明的难题,且违背了正义的本质,其主要表现为以下几点:
其一,证据论的角度来解读。一方面,“明知”的这种心理因素的特征决定了其证明是缺乏合理性的。从“明知”本意来说,其是看不见摸不着的主观心理活动和认知状态,这种特性决定了它与客观方面等其他要素在证明环节上存在不同,后者是一种以物理形态存在的客观事实,通过公安机关的侦查、勘验等方式是可以大部分还原的;而前者基本上只存在于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的口供或者书证和视听资料里,否则难以达到犯罪证明所需要的标准。[18]也正基于此,司法实践过程中出现了刑讯逼供的情形,但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逐渐在我国施行的今天,这无疑对公安机关的诉讼取证提出了新的挑战。另一方面,诉讼证明中的一般原则也对证据提出了严格的要求。刑事诉讼法要求排除任何的合理性怀疑,倡导证据的唯一性。除此之外,还要求在举证责任上“谁主张,谁举证”,“明知”作为主观方面的内容也在此行列,但这在法律实践中几乎很难实现,尤其是通过客观化的形式来表现主观化的东西。例如,原因自由行为中,行为人自己尚无法准确表达自己的内心意思,更何况司法机关,故很难达到证明充分的程度。
其二,成本论的角度来解读。“迟来的正义非正义”,诉讼不仅仅是案件公正结果的获得和诉愿的表达,其实质是保障国民的权益。伴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犯罪也呈现出智能化,虽然各种新的复杂精密的诉讼过程使得实体公平得到最大维护,但程序正义难免会打上折扣,例如诉讼时间的遥遥无期和拖沓。我们不得不反思如何合理地分配司法资源。在具体的案件中,基于诉讼效率考虑而形成的先前案例很多,例如在行为人非精神病的证明问题上就采用了责任倒置。同样的道理,对于证明有受贿共犯故意的认定,行为人是否“明知”,可通过其客观的不拒绝等行为推定其明知。
3.“明知”、间接故意、过于自信过失的关系
我国刑法理论将故意细分为直接故意和间接故意,划分的依据是刑法第14条,根据该规定,⑤间接故意是指“明知”结果的发生,放任结果的发生。间接故意和犯罪明知以认识因素为标准划出了他们与直接故意和犯罪轻率(Reckless-ness)的界定点。[19]直接故意是以行为人具有积极希望之意志因素为其特征,而间接故意与犯罪的明知则是与积极之认识因素为其征表。虽然间接故意只是要求行为人对结果的可能性具有预见性,而“明知”代表着行为人对于结果在主观上具有完全的可预见性,但从法的统一性的角度来看,“明知”的标准同样适用于间接故意,这势必会成为司法审判困境的症结。
除此之外,间接故意与过于自信的过失间的区别也成为困扰学界和实务界的一大难题。“放任”与“轻信”的精细解读也只能从语言规范层面来解决模糊性的问题,无法切中案件性态之本体。[20]鉴于此,有学者主张以“复合罪过”的提法将其一网兜之,希冀通过此种方式来防止挂一漏万,继而提高办案效率。笔者对此不敢苟同,司法者作为法律的捍卫者,必须给民众以非此即彼的答复,而不可在价值选择上博弈。诚然,在“二值”之间作出一元的终极判断需要极大的勇气,但这不能成为我们将问题模糊化处理的理由。
四、“明知”问题的解决——以受贿罪为切入点
为了将“明知”问题更直观地展现出来并提出相应对策,本部分选择以受贿罪为切入点。最新颁布的《解释》虽然为贪污受贿罪的认定提供了新的途径,进而为“明知”问题解决提供了新的思维,但单独借助此恐难以形成有效的“法网”,笔者认为以下方法当为应有之义。
1.类型化思维的应用。刑法中的思维方式一般分为概念思维和类型化思维两种。概念是理解法律条文的基石,在此理念的影响下,概念成为定罪量刑活动中首先要予以把握的要素。概念性思维的逻辑运行模式是其背后的三段论原理,虽具有严谨性等优点,但其自身的局限性也日益凸显。所谓类型化思维是一种以类型为主要思维形式和基础,并在此基础上进行推理判断的思维方式。[21]无论是大陆法系还是英美法系都广泛适用类型化思维,主要是通过行为的状态和对象对该类犯罪予以把握,例如德日将故意杀人罪分为杀人预备罪、杀害尊亲属罪、杀婴罪等,而英美等国则将其分为谋杀罪和非预谋杀人罪两种类型。[22]传统的概念性思维仅仅停留在依据犯罪对社会危害的严重程度来考量犯罪,在今天的风险社会注定难以承担起惩罚犯罪、保障人权的重任。类型化思维的灵活及其背后的三段论的限定使得它在疑难案件的解决上优势凸显。类型思维除了关注法条本身的内在元素外,还对词语背后的价值观予以关切,更加注重案件事实与犯罪构成要件中的标准事实之间的关联性。目前对于“应当知道”的分歧甚至到了原则性的高度,故而有必要运用类型化的思维探究受贿罪背后的价值。受贿罪其背后被侵害的法益或者说社会危害性的认定需要类型化思维来处理,其主要破坏的是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廉洁性。申言之,受贿的数额问题只是量刑中需要予以考量的因素,而不应在受贿罪的认定环节大费周折。在受贿罪故意认定问题上,根据行为人对于认识对象所认知的状态可以知道 “明知”包含了肯定知道和可能知道两种情形,因为实践中不可能所有的犯罪都可以做到绝对的确定,而为了减轻司法机关的负担,对于某些特定犯罪可以降低主观的证明程度,但这并不意味着证据公信力的减弱,而会通过加强客观方面的证明以加强整个证据链的凝聚力。申言之,“明知”的不分要素通过客观要素证明来予以实现,例如,《解释》中要求“国家工作人员未退还、或者不上交”来作为其受贿罪故意的证据。
2.发挥指导性案例的作用。我国两高2010年通过了《关于案例指导工作的规定》,正式确立了案例指导制度。在一段时期,对于指导性案例的效力的定位并不清晰,只是规定了“可以参照,具有约束力”,那么下级法院是必须比照适用,还是仅仅作为一个参考的标准?笔者认为,作为两高的司法实践产物,其应当比照司法解释具有当然的法律效力。与司法解释相比较,指导性案例更加具体、可操作性更强,不仅在一定程度上为我国的疑难案件提供了解决之道,而且为类似案件的审理提供了法律上的统一性,防止由于法官水平参差不齐造成的不公正结果。正如《关于案例指导工作的规定》第2条标榜的一样,指导性案例必须符合以下几种情形,包括社会广泛关注的、法律规定比较原则的、具有典型性的、疑难复杂或者新类型等,但实际上截至2015年我国共发布的刑事指导性案例9例。其中涉及贪污受贿罪的仅2例:3号的潘玉梅、陈宁受贿案和11号的杨延虎等贪污案,[23]不仅数量少,而且没有对“明知”在贪污受贿罪适用的规则予以必要的关切。与此相反,《解释》对于受贿罪故意做出了大胆的设计,这使得指导性案例的功能黯然失色,故有必要以典型案例为蓝本指导下级法院对案件的审理。此种做法在此《解释》出台前的司法实践中便有所尝试,最为典型的如薄熙来案件中的别墅就是在明知其妻收受财物纵容的行为,现存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与妻子事前通谋,但最终还是以受贿罪依法判决,故笔者建议指导性案例能将“薄熙来受贿案”吸纳进去,予以推行。
3.变更待证事实。变更待证的事实,简而言之就是通过立法的形式改变犯罪的构成要素,从而消解部分待证事实。立法的形式包括直接立法和间接立法,前者主要是指刑事法规、后者主要是指司法解释或者指导性案例。上文中已经论述了指导性案例,现就刑事立法和司法解释两个方面来阐述变更待证事实。本次《解释》就对待证事实做了较为巧妙的设计,只要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在知道妻子等收受财物而予以纵容的,就视其为受贿罪共犯,具有受贿的故意。当然,变更待证事实并非适用于任何犯罪,而是适用于特定的犯罪。笔者认为毒品犯罪、恐怖主义犯罪和食品犯罪可以予以试行,这缘于其涉及重大利益且具有突发性等特点。从司法解释的角度来说,对于特定的犯罪需要对“明知”的内容予以明确,这里的明确并不是要求精确。笔者认为,可以不要求精确的数字,但要给予以一个起点数额作为量刑的基准。
4.刑法推定的运用。在罪刑法定原则的基调下不允许成文法外任何推定方法的运用,后者被视为对刑法根基的破坏。[24]但实践表明,推定在犯罪主观方面的适用有着积极的意义,因为其在整体上会平衡证明责任的分配,即减轻公诉机关证明责任而加重被告的举证责任。认识论的经验表明,我们很难做到对事物的完全认知,行为也是如此,之所以采用此种推定是为了最大限度地维护国家利益,这一点并不违背刑法的谦抑性。为了做到利益的均衡保护,推定的适用范围应集中在如贪污受贿、毒品犯罪、恐怖主义犯罪、黑社会性质犯罪上;对《解释》确立的受贿罪推定的先例,其他几类犯罪也应逐渐推广开来。刑法推定的实质是严格责任在刑法领域的应用,其为功利主义社会的征表。由于行为人证明其“明知”与否不影响案件的结果,故而有学者对推定制度予以否定,认为其会破坏司法的公正。笔者不赞同此类观点,其理由有二:其一,严格责任适用的犯罪大多数情况下行为人都是构成犯罪的,该制度肇始于英美,其设置目的是保护幼女免受性侵,防止犯罪嫌疑人逃脱法律制裁;其二,严格责任提高了诉讼的效率,强化刑事立法的社会保护机能为功利导向,推定的建立是在法治框架下的“严打”,其对打击贪污受贿罪的效果最显著。当然,推定自身的结构特点决定了其也存在着许多问题,为了保障不被滥用,有必要对其进行事前审查与事后监督,而事前审查和事后监督体系的构建还有待进一步探讨。
注 释:
① 《刑法修正案(九)》新增加5个条文。
② 有学者认为“故意犯罪”与“犯罪故意”有实质性的差别,故对于“明知”解读也不一样。在本文中,笔者认为两者只是文字上组合的不同,没有实质性的差别,故将“故意犯罪”等同于“犯罪故意”来进行阐述。
③ 关于《刑法》138条中的明知,张明楷教授认为,其不等同于故意犯罪中的“明知”,只是表明行为人已经预见到发生侵害结果的危险。
④ 《关于依法惩治性侵未成年人犯罪的意见》19条规定: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对方是不满十四周岁的幼女,而实施奸淫等性侵害行为的,应当认定行为人“明知”对方是幼女。对于不满十二周岁的被害人实施奸淫等性侵害行为的,应当认定行为人“明知”对方是幼女。对于已满十二周岁不满十四周岁的被害人,从其身体发育状况、言谈举止、衣着特征、生活作息规律等观察可能是幼女,而实施奸淫等性侵害行为的,应当认定行为人“明知”对方是幼女。
⑤ 《刑法》第14条规定:明知自己的行为会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并且希望或者放任这种结果发生,因而构成犯罪的,是故意犯罪。
[1]蔡桂生.国际刑法中“明知”要素之研究——以《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第30条为例[J].法治论丛,2007,(5):64-69.
[2]张明楷.刑法学(第四版)[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1.246.
[3]冷大伟.犯罪故意“明知”问题探析[J].烟台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5):44-53.
[4]张明楷.如何理解哈认定窝赃、销赃罪中的“明知”[J].法学评论,1997,(2):88-90.
[5]陈兴良.“应当知道”的刑法界说[J].法学,2005,(7):80-84.
[6]冯军.刑法的规范化诠释[J].法商研究,2005,(6):62-73.
[7][奥]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引论[M].周丽,译.武汉:武汉出版社,2014.88.
[8]于志刚.犯罪认识中的“故意”理论新探[J].法学研究,2008,(4):96-109.
[9]高铭暄,马克昌.刑法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370.
[10]储槐植.刑事一体化[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4.217.
[11]郑建才.刑法总则[M].台北:台北三民书局,1985.96.
[12]邹兵建.“明知”未必是“故犯”——论刑法“明知”的罪过形式[J].中外法学,2015,(5):1349-1375.
[13]周光权.明知与刑事推定[J].现代法学,2009,(2):109-118.
[14]陈兴良.刑法中的故意及构造[J].法治研究,2010,(6):3-14.
[15]王新.我国刑法中的“明知”的含义和认定——基于刑事立法和司法解释的分析[J].法制与社会发展,2013,(1):66-75.
[16]陈兴良.中国刑事司法解释的检讨[M].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2003.271.
[17]王林林.刑法分则中语境中的“明知”的认定[J]天津法学,2014,(1):18-24.
[18]刘远熙.论推定对犯罪主观方面“明知”的证明意义[J].广东社会科学,2011,(3):243-248.
[19]李韧夫.中美刑法间接故意研究[J].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5,(3):145-149.
[20]冯亚东,叶睿.间接故意不明时的过失推定[J].法学,2013,(4):143-149.
[21]李依林.论刑事司法实践中的类型化思维[J].江西社会科学,2014,(2):171-178.
[22]贾晓媛.故意杀人罪类型化研究[D].南昌:南昌大学硕士论文,2012.18.
[23]伍光红,王惠敏,蔡士林.贪污受贿罪法定刑量刑标准述评——以兼评《刑法修正案(九)》第44条[J].中州大学学报,2016,(1):25-30.
[24]黄维智.刑事证明责任研究——穿梭于实体与程序之间[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119.
(责任编辑:卢圣泉)
Research on the Criminal Law of"knowing"Again
CAI Shi-lin1,WANG Hui-ming2
(1.School of Criminal Justice,Zhongnan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Law,Wuhan Hubei 430073,China;2.School of Law,Guangxi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Nanning Guangxi 530002,China)
The judgment of"knowing"is the most basic and important link in the judicial practice,which decided the crime or not,as well as the specific charges,in particular,knowing that is an expression of behavior is to the inner table.But to judge,its founding need to assist the objective factor,which has been long plagued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a big difficulty.Recently promulgatedabout the projects about to deal with corruption and bribery criminal cases to explain some issues of applicable law,the 2th of article 16 of this presumption in criminal law on bribery deliberately understanding about "knowing"to the extreme.In the existing criminal law for the use of"knowing"exist"mixed match"phenomenon,thus causing a series of difficulties,which makes the scholars have to find a new way.
knowing;taking bribes;presumption;criminal law
D924
A
1672-626X(2016)04-0104-07
10.3969/j.issn.1672-626x.2016.04.016
2016-06-13
蔡士林(1989-),男,河南信阳人,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刑法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