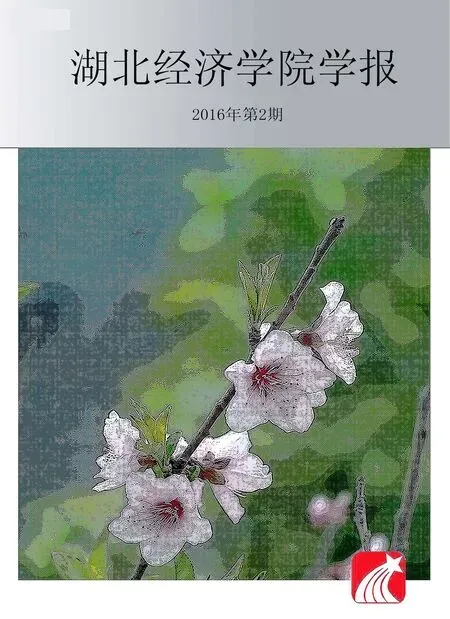残缺的家庭病态的人生
——考琳·麦卡洛小说中病态人格问题分析
徐梅
(北京京北职业技术学院,北京 101400)
残缺的家庭病态的人生
——考琳·麦卡洛小说中病态人格问题分析
徐梅
(北京京北职业技术学院,北京 101400)
家庭是当前整个社会形态的基本单位,在意识形态的生产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父母的关系及父母在家庭中的地位、分工为子女们家庭意识形态的形成提供了典型性模板。与此同时,父母之间的关系及其对子女的态度也直接影响着子女们人格的养成。澳大利亚当代著名女作家考琳·麦卡洛小说中的诸多家庭均处于残缺状态:母爱极端化、父爱畸形、子女们的人格普遍呈现出病态化特征,其作品中子女们人格的病态化过程与家庭的残缺不无关系。
考琳·麦卡洛;父亲;母亲;孩子;人格
考琳·麦卡洛(Colleen McCullough)是世界知名的神经病理学家和澳大利亚当代最具影响力的作家之一,她曾被誉为“澳大利亚活着的国宝”。从其对个人创伤性成长经历的感悟及其作品表达的共同主题来看,考琳·麦卡洛是一位悲苦意识浓重的作家,她的作品折射了她灰暗的童年经历、曾经窘迫的经济状况、作为女性被边缘化的处境、澳大利亚的民族苦难、二次世界大战和冷战的阴影等,因此她作品中的人物普遍面临各种困境。其中,较为突出的是人格养成之痛和身份迷失之苦,而这些困境的形成与其所处的残缺家庭不无关系。本文运用艾里希·弗洛姆关于爱的相关论述,对考琳·麦卡洛小说中残缺家庭所引发的人格悲剧进行深入地剖析,借以引发当代人思索,发掘文学的社会意义,促进人类文明进步。
一、残缺家庭引发的深重的创伤
虽然美国著名心理学家高尔顿·乌伊拉德·奥尔波特(Gordon Willard Allport)认为人格的养成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强调人格是“一个人内部心理物理系统的一种动态动力组织,它塑造了一个人的行为、思想和感情的独特模式”,[1](P5)但是弗洛伊德认为:“早期的童年经验在决定成年后的人格中扮演着重要的作用。”[1](P201)弗洛伊德在其《论无意识与艺术》中进一步指出:“儿童时期的各种丧失和缺失尤其容易形成儿童的创伤性体验,并形成不容易抹去的深刻创伤性记忆。”[2]由弗洛伊德关于人格形成及创伤的有关论述可以得知:一个人的童年经历对其性格、价值观、世界观的养成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儿童时期的创伤性经历更不容易忘却和修复,它会对人格的养成产生深刻且持久的影响。
考琳·麦卡洛记忆中的童年生活一片灰暗,造成考琳·麦卡洛灰暗童年生活的主要原因是父母的“失职”和“不负责任”。考琳·麦卡洛在评价自己的父亲时,使用的是诸如“可怕”、“混蛋”、“对自己的子女不感兴趣”、“从不在家”、“婚外恋”等词语。父亲对家庭极不负责任的态度让考琳·麦卡洛在父亲死后的很多年内都无法原谅他对自己童年造成的灰暗影响和严重的心理创伤。正是源于这种难以释怀的经历,在考琳·麦卡洛的诸多作品中,父亲形象都是处于残缺状态。
造成考琳·麦卡洛不幸童年的另一位关键人物是其“人生不得意”的母亲。考琳·麦卡洛认为她母亲的一生是“沮丧”、“痛苦的”。作为毛利人的后代,考琳·麦卡洛的母亲沉浸在自己的 “抑郁不得志”中,她不关注自己的家庭和孩子。因此,冷漠的母亲形象也在她的作品中频频出现,如《荆棘鸟》中的菲奥娜,其出身、言行举止就是考琳·麦卡洛记忆中自己母亲的翻版;《呼唤》中伊丽莎白的冷漠、母爱无法唤起等特征也有考琳·麦卡洛母亲的影子;《遍地凶案》、《恺撒大传·十月马》等小说中也存在着沉浸于自己的世界、对家庭和孩子毫不关心的母亲形象。这些冷漠母亲形象的出现也正是考琳·麦卡洛的母亲对幼年时期的考琳·麦卡洛造成的心理创伤使然。为此,即使成年后,在文学创作、神经病理学领域都取得丰硕成果的考琳·麦卡洛依然对父母的失职行为难以释怀。
心理学家们还研究发现,当一个人尤其是儿童面对危险、灾难或重大变故时,会产生强烈的焦虑感,其“结果就可能导致像恐怖症、焦虑侵袭、强迫症等临床症状的出现。”[1](P177)考琳·麦卡洛在童年时期遭受到的重创之一是她唯一的哥哥卡尔的溺水而亡。在考琳·麦卡洛童年时期的记忆中,每当父母争执、吵闹的时候,陪伴她躲在黑暗中哭泣的只有她唯一的哥哥卡尔。然而,使考琳·麦卡洛心理遭受更大创伤的是,在卡尔死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直到考琳·麦卡洛获得经济独立之前,她的母亲都无法容忍“考琳·麦卡洛的存在”这一事实,因此考琳·麦卡洛的处境更加艰难。为此,考琳·麦卡洛在她享誉全球的家世小说《荆棘鸟》中设置了戴恩的死亡环节,深情描绘了戴恩和朱丝婷之间亲密无间的姐弟情谊,其中戴恩即是她哥哥卡尔的缩影。与哥哥的亲密关系使考琳·麦卡洛更加无法忍受哥哥死亡的事实,所以她对死亡有了无以复加的恐惧感。死亡恐惧、死亡焦虑在她的作品中也成了一种无法逃离的苦难。源于对兄妹情谊的留恋,考琳·麦卡洛在她的诸多作品中都流露出对姐妹情谊、兄妹情谊、兄弟情谊的向往之情,如《荆棘鸟》中的朱丝婷与戴恩之间的亲密无间、《呼唤》中内尔对智障妹妹安娜无微不至的照顾、《班纳特小姐的自立》中伊丽莎白对妹妹们的体恤、《摩根的旅程》中药剂师堂兄对理查德·摩根所有事情的亲力亲为、《特洛伊之歌》中帕特罗克洛斯对阿克琉斯的倾慕等。
由此可见,不幸的童年生活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考琳·麦卡洛的人生观。但也正是因为她不负责任的父亲、冷淡的母亲、哥哥的死亡和处于残缺状态的家庭让她对爱的缺失有了深刻的体验,促使她不断地对人生苦难及创伤的修复问题进行反思。
二、极端化母爱引发的人格悲剧
在传统社会文化视野中,母爱是天然、神圣的,具有崇高的价值,备受推崇。在关于人类起源的种种传说中,《圣经》将人类的起源归于圣母玛利亚的意外怀孕,中国传统文化将人类的起源想象为女娲造人,因此无论是西方的《圣经》还是中国的神话传说都肯定了母爱的共同特征:给予、创造。但是,美国当代著名心理学家艾里希·弗洛姆却指出了母爱的极端性,他认为“母爱是一种祝福,是和平,不需要去赢得它,也不需要为此付出努力。但无条件的母爱有其缺陷的一面。这种爱不仅不需要用努力去换取,而且也根本无法赢得”。[3](P37)
考琳·麦卡洛的小说对母爱的书写阐释了艾里希·弗洛姆所言的极端性母爱。由于深重的童年创伤,考琳·麦卡洛从异化母爱导致创伤的角度,探讨了极端型母爱对子女人格、人生观养成造成的梦魇。她不同时期、不同类型的小说都指向了母爱异化导致的“非我”境遇和“非我”境遇中的自我实现受阻引发的痛苦。麦卡洛的小说既呈现了处于疯狂状态、令子女们无法自由呼吸的母爱,也呈现了冷漠、无法唤起的母爱。她作品中处于疯狂状态的母爱像一条隐形的绳索束缚着子女们自由成长的人格,专横、疯狂的母爱让子女们尤其是儿子们无法自由呼吸,乃至人性发生变异;而冷漠、无法唤起的母爱导致的后果是子女们人格的畸形发展和世界观、人生观的扭曲。
(一)荆棘式母爱导致的性格残缺
首先,考琳·麦卡洛的作品呈现了疯狂的、荆棘式母爱对儿子们性格养成带来的羁绊。艾里希·弗洛姆曾在《爱的艺术》一书中阐释了娇惯型母爱和专制、垄断型母爱对子女人格养成、自我身份确认造成的负面影响。他说“造成神经(机能)疾病的一个原因可能是一个男孩有一个十分慈爱,却又很娇惯他的母亲,同时又有一个性格懦弱或者对孩子不感兴趣的父亲。 ”[3](P41-42)
考琳·麦卡洛的 “胭脂扣系列小说”中的第一部——《遍地凶案》中的小德斯蒙德就是一位艾里希·弗洛姆所言的由于过度母爱而引发的 “神经疾病”患者:他身体羸弱、人际沟通困难、难以承受正常的学习和社会生活,因此他处处依赖于母亲,处处寻求庇护。而他的羸弱和病态则与他所在的残缺家庭,特别是过度的母爱不无关系。他的母亲菲洛米娜·斯凯珀斯是一位过度溺爱他并可以为他去死的疯狂母亲,而他的父亲德斯蒙德则是一位竭力从肉体到精神对妻子菲洛米娜·斯凯珀斯进行全方位禁锢且富可敌国的成功企业家,但父亲德斯蒙德在小德斯蒙德的生活中完全处于缺失状态。母亲菲洛米娜·斯凯珀斯将为挣脱畸形婚姻关系禁锢所做的努力、为争取小德斯蒙德的监护权而做出的牺牲、对丈夫的妥协等等统统归结于对儿子小德斯蒙德的爱,小德斯蒙德自幼被这种沉重的爱束缚着,以至于他无法正常养成完整的人格,并且向病态方向发展。
《恺撒大传·十月马》中的渥大维在众人的眼中也是一位病怏怏,富有贵族气质,“相貌俊秀、亭亭玉立”,透着女人气的男性。恺撒认为渥大维身上总散发出女人韵味的原因在于其母亲浓重的爱和过度的保护。恺撒以旁观者的身份向渥大维阐释了他男性气质缺失的原因:“由于你母亲担心你的身体状况才格外宠爱你,不让你接受每个男孩都要经受的正规军事训练,使你不懂得一个真正的男人应该具备的心理素质。”[4](P340)随着年龄的增长和自我实现需求的凸显,渥大维开始厌恶母亲和姐姐们这种“爱的软暴力”,竭力逃离她们的哭哭啼啼和无处不在的爱的重轭。
《摩根的旅程》中理查德·摩根的第一任妻子佩格由于生育能力不强,致使她将全身心的爱都投注在唯一的儿子威廉·亨利的身上,由于她“忘我”的爱限制了儿子正常的生长需求,进而引起儿子威廉·亨利的逆反,如作品中所述,“母亲在他四周筑起的高墙一直没有拆除,他对围墙里面的一切腻味透了……他的格言是‘等待’。现在终于等到了冲出‘牢笼’的一天。”[5](P64)而佩格施展母爱的过程也是消解其自身独立性的过程,因为她在女性的生育使命中迷失了自己。佩格因为爱而消解自我的悲剧性来源于母爱的特质——“给”,正如艾里希·弗洛姆所言:“她把她的养料给予她肚中的胎儿,后来又给婴儿喂奶和给予母体的温暖。对女子来说不能给是极其痛苦的。 ”[3](P22)
《恺撒大传·十月马》中自幼缺少父爱的布鲁图也是极端母爱的牺牲品,他的母亲塞尔维利亚集“美貌、智慧、邪恶”于一身,她操纵式、歧视性的教育致使布鲁图性格懦弱、缺少男性气魄。布鲁图的舅舅即布鲁图第三任岳父——加图也希望“布鲁图不要那么懦弱,多一丝男性气魄就好了”。[4](P121)母亲塞尔维利亚专横的爱、否定性的教育方式及放浪的情感生活不仅造成了布鲁图性格的懦弱、人格的低俗、视野的狭隘,而且还造成了布鲁图恋爱能力的下降、性功能的隐匿:布鲁图的前两段婚姻都是短暂而又毫无感觉的,正因为生活在专横母爱的包围中,他作为一个正常男性的身份无法得到确认、无法形成完整人格,因此他在爱情、婚姻生活中也处于“非我”状态。
(二)病态母爱引发的病态人生
考琳·麦卡洛还通过小说创作向读者阐释了病态母爱引发的子女们的病态人生。考琳·麦卡洛在《遍地凶案》中描绘了科里的妻子——莫林的焦虑式人生观,尖酸、刻薄的爱对孩子们(尤其是儿子)的生活、性格养成带来的挥之不去的灰色阴影:“12岁的儿子开始延续母亲对男人世界的挫败感,在学校里总是麻烦不断,如不修边幅,大嗓门号叫,考试成绩差等等。 ”[6](P331)
考琳·麦卡洛在《恺撒大传·十月马》中也塑造了一位急功近利、用丧失德性的行为法则教育孩子的母亲。恺撒的母亲玛特尔在罗马堪称第一号美人,她严格、挑剔、毫无同情心,不过她有满脑子的智慧。但是,在恺撒的印象中,母亲是一个可怕的人,她教给恺撒回击别人恶意诽谤的方法是:给那些诽谤他的人带上绿帽子,公开地、坦坦荡荡地做,勾引他们的老婆,然后将其抛弃,不要授人以柄。母亲的“教诲”让恺撒一度成为一个不择手段、丧失德行的政客,也造成了众多无辜女性的悲哀。恺撒虽然俘获了罗马无数女性的情感和肉体,击败了所有的政敌,但是他对自己丧失德性的行为充满了罪恶感,尤其是在感受了无所附加的爱情、天伦之乐之后,恺撒的忏悔意愿更加强烈。
考琳·麦卡洛在《遍地凶案》中还塑造了一位因为畸形的家庭生活用爱杀死儿子的母亲——芭芭拉·诺顿夫人。芭芭拉·诺顿夫人因为长期生活在成功银行家丈夫的阴影之下,无法获得自我认同的机会,发生了精神错乱,进而被史密斯利用,成了杀死丈夫的凶手;但是丈夫死后,她对孩子们的爱却愈演愈烈:她强制孩子们减肥,“彼得死后,我让大家节食……不碰面……不碰奶油……等到今年九月份汤米去上学的时候,他就会像树篱一样瘦了。”[6](P210)但是,她强制性的母爱违背了孩子们的正常成长需求,从而成了杀死儿子汤米的凶手,她的儿子汤米因为极度的饥饿误食橡皮而死。
(三)过度母爱诱发的“俄狄浦斯情结”
考琳·麦卡洛还通过过度母爱导致的极端恋母情结来阐释过度母爱对儿子完整人格养成造成的困扰和随之而来的痛苦人生。“恋母情结”源于弗洛伊德对古希腊神话俄狄浦斯弑父娶母故事的分析,弗洛伊德认为:“儿童在性发展的对象选择时期,……男孩早就对他的母亲产生了一种特殊的柔情:视母亲为自己的所有物,而把父亲看成是争夺此物的敌人,并想取代父亲在父母关系中的地位。”[7]弗洛伊德还提出,当一个人未能克制自己婴儿时代的欲望,即未能解决好他的俄狄浦斯情结的话,他就始终处于儿童的欲望与成年人的要求之间的分离状态中。《荆棘鸟》中的弗兰克就是这样一个在过度母爱的包裹下无法走出俄狄浦斯情结束缚的悲剧人物,其备受肉体需求和伦理困境的双重煎熬。
艾里希·弗洛姆指出:“某些神经病形式,如强迫性神经病同患者的单一父亲联系有关,而另一些病状,如歇斯底里、酗酒,不能面对现实生活和厌世则是同母亲的单一联系所致”。[3](P42)《荆棘鸟》中菲奥娜对弗兰克倾注的情感超过对全家人的爱,菲奥娜对私生子弗兰克超越常规的爱源于自己对已逝爱情的留恋和痴迷,她将对帕吉汗的爱全部转移到他们的儿子弗兰克身上,又由于父亲帕吉汗的缺席,弗兰克对母亲菲奥娜的爱走向极端,最终发展成无法摆脱的恋母情结。尽管菲奥娜意识到了弗兰克对自己的过度依恋及性格的暴力性发展趋势,试图规劝弗兰克去爱别的女性,但是语言的劝慰已经无法挽回深陷俄狄浦斯情结泥淖的弗兰克,他从对母亲菲奥娜的关爱发展成为对母亲的占有,发展成为带有性别色彩的男女之间的爱恋,鉴于继父帕迪的存在、社会伦理道德的约束,弗兰克无法在现实生活中释放他对母亲菲奥娜的爱,因此他的 “本我”和“超我”处于分裂状态,他也处于一种“非我”的痛苦境遇中:“他无法摆脱这件事,无法摆脱她,无法摆脱他心灵深处的种种思绪,无法摆脱他的年龄和男子的本能的饥渴。在大多数情况下,他总是设法把这些念头压下去……简直叫他快发疯了。”[8](P83)
根据弗洛伊德的“人体内的能量也遵守能量守恒”的论断,弗兰克体内由“原欲”引发的痛苦急需一个释放的突破口,“他恨不得能哭一场,或者去杀个人,去干能排解痛苦的任何事情。”[8](P57)因此,为了摆脱俄狄浦斯情结的束缚,弗兰克选择了拳击生涯作为释放痛苦的途径,在他的职业生涯中,他继续尽情发泄着对继父帕迪的仇恨和厌恶,“他的每一个对手都仿佛长着帕迪的面孔……他是多么渴望能有打架的机会啊……因为打架斗殴是他所知道的唯一能发泄自己的愤怒和痛苦的方法……”[8](P90)但是,由于性格的暴虐和社会的误解,他最终铛锒入狱,他的梦想、追求也在监狱的囚禁中付诸东流。
(四)冷漠母爱衍生的冷漠人格
考琳·麦卡洛的小说还弥漫着母爱无法唤起的悲哀及其对子女人格养成、自我身份定位造成的困扰。艾里希·弗洛姆在《爱的艺术》一书中也进一步论述了母爱包含的两层含义,即“乳汁”和“蜂蜜”。他认为“乳汁象征母爱的第一个方面:对生命的关心和肯定,蜂蜜则象征生活的甘美,对生活的爱和活在世上的幸福”。[3](P46)
由于考琳·麦卡洛对自己母亲的评价是 “生活不如意”、“失落”、“沉浸于个人悲伤”等,因此冷漠、封闭的母亲形象在她的作品中频频出现:《恺撒大传·十月马》中图尼娅的母亲、西塞罗的妻子等都对女儿们冷漠、不管不问;《遍地凶案》中卡尔米内的第一任妻子桑德拉是一位瘾君子,沉迷于可卡因不能自拔,对于唯一的女儿索菲娅毫无兴趣。考琳·麦卡洛作品中的众多人物包括考琳·麦卡洛本人都是连“乳汁”都没有得到的人,而他们的母亲更无法给予“蜂蜜”,因为她笔下的母亲们多是“冷漠”“失意”的,她们将自我封存起来,沉溺在自己的悲欢离合之中,无暇为孩子们提供“蜂蜜”。考琳·麦卡洛在两部家世小说《荆棘鸟》、《呼唤》中详细阐释了冷漠母爱对子女们性格养成的消极影响及冷漠母亲们的自我迷失之痛。
《荆棘鸟》中克利阿里家的女主人菲奥娜曾竭力忘掉自己有过一个女儿梅吉,女儿的存在只能令她回忆自己悲惨的女性命运,因为菲奥娜基于自身的不幸悲观地认为:女人的不幸应该归于女人的祖先夏娃犯下的原罪。她向拉尔夫神父诉说女儿梅吉的存在给她引发的痛苦,“什么是一个女儿?她只能使你回想起痛苦……我竭力忘掉我有一个女儿……”[8](P199)菲奥娜对女儿的“主动忘却”是对自己痛苦的倾诉,也包含对所有女性不幸的控诉。但她这种主动的“忘却”既无法给予女儿“乳汁”,更无法提供“蜂蜜”,她在深深地伤害着女儿的同时,还曾一度引起女儿的性别焦虑,误导着女儿对爱情、婚姻、家庭的偏狭理解,为女儿的自我寻求设置了一个负面引路人形象。由于对母爱的极度渴求,梅吉将爱情、婚姻等同于对丈夫和孩子的拥有,并将自己全部的人生追求定位于对婚姻、丈夫和孩子的渴求和拥有上。梅吉曾对母亲菲奥娜厌恶照顾两个最小的儿子的做法感到不满,并决意做一个公平、富有爱心的母亲:“菲奥娜对詹斯和帕西的冷漠,深深地伤害了充满她内心的那种母爱。她心想,要是我有了孩子,我绝不会偏爱他们中间的一个的。”[8](P163)但是,梅吉在婚姻梦想瓦解之后却沿袭了母亲菲奥娜的冷漠,也对诞生于自己不幸婚姻中的女儿朱丝婷充满冷漠,尤其在她对自己失意的爱情、婚姻生活迷惘、痛苦的时候,更无暇给女儿提供弗洛姆所言的“乳汁”,因此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女儿对所有亲情的抵触,对爱情、婚姻、家庭的拒绝,养成了怪癖的性格,也造成了新一轮的人生悲剧。朱丝婷的怪癖性格彰显了母爱无法唤起引发的悲哀。艾里希·弗洛姆曾经强调过 “母亲对孩子的影响无论怎样高估都不为过。母亲对生活的热爱和对生活的恐惧都具有传染性,两者都会对孩子的全面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事实上我们确实可以在孩子身上,也可以在成人身上看到,哪些人只得到‘乳汁’,而哪些人既得到‘乳汁’,又得到‘蜂蜜’”。[3](P46)按照弗洛姆的观点,朱丝婷也是一位和母亲梅吉一样在幼年时期既没有得到“乳汁”也没有得到“蜂蜜”的不幸人物,梅吉是母爱缺失的受害者,却又沿袭了母亲菲奥娜的做法,伤害了年幼时期的朱丝婷。
菲奥娜的冷漠和自我隐匿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克利里家族的不孕不育,她的儿子们集体性独身,因为母爱无从唤起的悲伤深深地伤害着他们,他们没有感受过“乳汁”带来的快乐,也从来没有见过母亲幸福的模样。在他们的记忆中,母亲是痛苦的,家庭是不幸的,因此他们集体拒绝女性、拒绝婚姻,为了赢得母亲的喜爱,他们对母亲做出了献祭般的举动,他们的一切都以母亲菲奥娜为中心:“大一些的男孩子们为他们的母亲感到悲伤,整夜辗转,他们爱她……他们一心一意地关心着她、体贴着她,不管她如何冷淡,他们都不计较。”[8](P163)
《呼唤》中的伊丽莎白源于对婚姻生活的不满,如《荆棘鸟》中的菲奥娜一样进行着自我封存,自我封存的伊丽莎白也和《荆棘鸟》中的梅吉一样,无法给予女儿们“蜂蜜”,无法在女儿们面前展示自己的幸福。虽然她常常为自己的母爱缺失感到自责,虽然她坚持不懈地履行自己作为一个母亲的职责,但是她依然无法唤起自己对女儿们发自内心的爱恋。母爱无从唤起的悲剧是导致女儿内尔·金罗斯成为“女亚历山大”的主要原因之一。
三、残缺父爱导致的身份迷失之痛
由于考琳·麦卡洛对自己父亲的评价是 “可怕”、“混蛋”、“对自己的子女不感兴趣”、“从不在家”、“婚外恋”等,因此在考琳·麦卡洛的作品中,父亲一直以反面形象出现,他们要么缺席,要么处于失语状态,要么不负责任、无爱,要么蛮横、专制。他们有时是一个在家庭中、在孩子们的世界里都无足轻重、可有可无的角色;有时又是孩子们的梦魇,代表着绝对权威,是引发孩子们病态性格、身份焦虑的罪魁祸首。正是他们的缺席、失语和畸形的爱引发了子女们的身份焦虑,造成了子女们病态的人生观、价值观。
(一)父爱缺席引发的身份焦虑
考琳·麦卡洛首先在作品中历数了父亲们的缺席对子女们性格养成带来的负面影响。在考琳·麦卡洛的小说中,引发私生子身份困惑和焦虑的直接原因是父亲的缺席,她的诸多作品均呈现了私生子们苦闷、抑郁的身份焦虑,而这一切均直接指向父亲形象的缺席。虽然考琳·麦卡洛在《荆棘鸟》中通过菲奥娜形象讲述了疯狂母爱造成的弗兰克深陷俄狄浦斯情无法自拔的悲剧,但是相对于菲奥娜在爱情中沉迷、觉醒、忏悔的鲜活,弗兰克的亲生父亲帕吉汗在这场让人为之动容的爱情中始终处于失语状态。在作品中,帕吉汗仅仅是一个菲奥娜不应该为之舍弃一切的已婚政客而已,因此他始终沉默,也因为他的沉默和缺席,弗兰克必然遭受来自传统社会的异样目光和暧昧的指点,进而导致弗兰克敏感、好胜、易怒、好斗性格的形成。作品描述了弗兰克对童年时期由于父亲缺席而引发的恐惧性困扰:“他捡起了那布娃娃……试图记起他在孩提时代是否受过奇特的恐惧的困扰。但是,在他心头留下不愉快的阴影的却是人,是他们的窃窃私语和冷眼,是母亲消瘦、皱缩的面庞,是母亲拉着自己的颤抖的手和肩膀。”[8](P7)
考琳·麦卡洛于2003年出版的第二本家世小说《呼唤》更加强化了父亲形象缺失导致的私生子身份的焦虑和痛苦。亚历山大自幼年时期就对知识充满热望,并以走进大学课堂作为容忍艰辛生活的精神支柱,但是神父的猥琐、继父丧失尊严的报复粉碎了亚历山大的知识追求梦想,而这一切均因为亚历山大生父的缺席,因为亚历山大的私生子身份。亚历山大的生父——一个令亚历山大的母亲即使遭受现任丈夫非人毒打也为之坚守贞洁的男人,在亚历山大无辜受惩、亚历山大的母亲决绝献身、亚历山大的继父丧失人格地报复、神父卑鄙无耻的讥讽、德拉蒙德家族的冷漠和敌视等纷繁复杂的世间万象中始终处于缺席状态,他无名无姓,他游离于这场人间悲剧之外。由于他的置身事外,亚历山大的童年、少年时期遭受世俗目光的审视,遭受非人的待遇,亚历山大也逐渐形成了强烈的报复心理。因为报复,亚历山大赌上了自己的婚姻和幸福,也曾一度造成自我的迷失,直到自杀之前,他才幡然醒悟自己已经被仇恨、报复耽溺得太久太久。考琳·麦卡洛的其他作品也普遍表达了父亲的无故缺席现象及其引发的性格悲剧,如 《恺撒大传·十月马》中恺撒的父亲以及布鲁图、渥大维的父亲都因不同原因退出了家庭生活。父亲形象的缺席使得母爱得以泛滥,进而导致了恺撒、布鲁图、渥大维性格缺陷的形成。
(二)畸形父爱对人格养成造成的羁绊
考琳·麦卡洛还通过小说创作呈现了畸形父爱对子女人格养成、身份确认、自我寻求带来的羁绊。《班纳特小姐的自立》中的费兹·威廉·达西由《傲慢与偏见》中严肃、傲慢、充满激情的青年变成了四个女儿和一个儿子的父亲,但作为父亲,他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失败者。他对于儿子查理的孱弱、“女性气质”、“同性恋传闻”感到痛心疾首,并决意按照个人意志来锻造柔弱、“娘娘腔”的儿子,迫使儿子查理进行严格的军事训练、学习军事政治类查理并不感兴趣的专业,曾一度造成儿子人生价值的迷惘和自我身份的焦虑,痛苦不堪;他对女儿们更是实施封闭式、隔离式的养育方式,将女儿们隔离在他的生活之外,致使他的女儿们缺乏适当年龄应当了解的知识和常识,性格养成也存在诸多问题。
弗洛姆认为,与无条件的母爱相比,父爱则是有条件的,他在《爱的艺术》中谈到了有条件的父爱的双重意义,即“消极的一面”和“积极的一面”,他说:“消极的一面是父爱必须靠努力才能赢得,在辜负父亲期望的情况下,就会失去父爱。……积极一面也同样十分重要。因为父爱是有条件的,所以我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去赢得这种爱。”[3](P37-38)《呼唤》中的亚历山大在创造了一系列奇迹和巨大财富之后,一直希冀自己也能有一个与李·康斯特万一样的儿子作为继承人,但是妻子伊丽莎白在生完两个女儿之后拒绝继续生育的现实让亚历山大延续香火的观念支离破碎。然而,女儿内尔·金罗斯的聪颖、特立独行、对自己基因的完全复制也令亚历山大着迷,受查尔斯·丢伊的影响,他也觉得有个女儿继承自己的事业是个不错的选择,于是他将全身心的爱投注到内尔·金罗斯身上,并要求内尔·金罗斯学习机械。尽管内尔·金罗斯自幼喜好医学,但是为了获得父亲的宠爱,她以顽强的意力突破性别障碍完成了机械专业的学习,获得了父亲亚历山大的认同和支持。同时,父亲亚历山大单向度的、浓重的父爱令内尔·金罗斯迷失了自己的性别身份,她以“我是爸爸的儿子”自居,否认自己的女性身份。正如艾里希·弗洛姆所强调的那样,“如果母亲性情冷淡、麻木不仁或者十分专制,孩子就会把对母亲的需要转移到父亲身上,就会变成单一的向父亲方向发展的人。……如果他的父亲很有权威,同他的关系又很密切,就更会加强他的这一发展。”[3](P42)以优异成绩、超人胆识和勇气挑战男性一直控制话语权的机械专业和医学专业的内尔·金罗斯沿袭了父亲亚历山大的冷漠和自负,她勇于向歧视女性的男性们大打出手,但是她丝毫不同情与她一样深陷性别歧视泥淖中的其他女性们,在一定程度上,她沿袭了父亲亚历山大的性别观念,她鄙视那些遭受性别困扰的女性,包括自己的母亲伊丽莎白。因此,从一定程度上来说,内尔·金罗斯的自负、狂妄、性别错位、社会责任感缺失都与父亲亚历山大·金罗斯单向度的、专横的、有条件的父爱不无关系。
《恺撒大传·十月马》中的加图是一个自律的斯多葛主义者,他主张通过禁欲、以苦为乐等克制自我本能需求的方式来净化自己的灵魂。按照弗洛伊德的说法,加图力求实现的自我是一个克制人的本能需求的“超我”。他的这种几近严酷的自虐行为也对孩子们产生了沉重的压力和挥之不去的负面影响。小加图曾深深感叹,“做一个没有任何缺点的父亲的儿子实在是太难了。”[4](P164)父亲在自杀前用干涩的嘴唇亲吻自己嘴和脸的举动曾让小加图倍感古怪,因为在小加图的内心深处还残留着童年时期父亲加图施加给他的无情的道德律令的阴影,“那时小加图声嘶力竭地哭喊着要妈妈,而他的父亲只是冷冷地教训他应该有男子汉气概……在他的记忆中,只有一个严厉的父亲,一个将无情的道德律令强加在自己软弱灵魂之上的父亲。”[4](P260)也因此,小加图成了父亲眼中“拥有各种各样的缺点,捅各种各样的篓子”[4](P164)的问题孩子。加图的斯多葛主义做法还造就了“女加图”鲍基亚不幸的一生,鲍基亚的才能让父亲加图刮目相看,但是她的性别劣势也让父亲喟叹苍天弄人:“加图想,真是苍天弄人,自己最能干最有头脑的孩子偏偏是女儿。争强好胜、无所畏惧的鲍基亚是块当兵的好材料。”[4](P164)鲍基亚作为父亲加图政治生涯的牺牲品是不幸的,她与爱情无关、与性愉悦无缘。直到与布鲁图结合,鲍基亚才品尝到爱情的甘甜和性生活的愉悦。但是,深受父亲加图政治观、人生观影响的鲍基亚也沿袭了父亲以爱情、婚姻为筹码换取政治进步的做法,因此爱情的魅力、性的愉悦在鲍基亚这里都难以抵御家族仇视、政治梦想的诱惑,在周围人眼里,鲍基亚就是一个“女加图”,是她父亲加图的翻版。为了替父亲复仇,为了表达对共和体制的忠诚,她不惜用锋利的刀子刺伤自己的大腿,逼迫自己的丈夫布鲁图参加“刺杀恺撒俱乐部”。鲍基亚的极端化性格不仅毁灭了她与布鲁图之间的美好爱情,使布鲁图深陷刺杀恺撒的不义之中,而且她的一意孤行也造成了自己的疯癫和死亡。鲍基亚的悲剧来源于她的性格悲剧,而鲍基亚的性格悲剧与她生活的家庭的混乱、与父母纠葛的婚姻、与父亲不惜一切追逐政治、权谋的做法不无关系。
《呼唤》中的伊丽莎白由于幼年父亲的无端责罚,成了一个被秘密包裹起来的人,在亚历山大的眼里伊丽莎白也是畸形父爱的牺牲品,亚历山大对伊丽莎白幼年及少女时期的生活都了然于心,他痛恨伊丽莎白幼年时期所遭受的禁锢式的生活,也了解伊丽莎白进行自我隐匿的原因:“她是一个被秘密包裹起来的人。这是因为,小时候说真话被无情地惩罚,勇于承认错误不被看作为人诚实的美德,得不到赞赏。渐渐地,她学会了不直抒胸臆,学会了保密,甚至连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这样做。”[9]
四、结语:创伤的警醒意义
作为一名残缺家庭中成长起来的女作家、神经病理学家,考琳·麦卡洛对残缺家庭的书写、对人格悲剧的呈现、对身份焦虑的反思等都引发了当代读者强烈的共鸣,因为她经受的残缺家庭带来的切肤之痛是如此的清晰、如此的脉络分明、如此深深地镶嵌在记忆中、挥之不去。考琳·麦卡洛的不幸遭遇固然令人喟叹,但是她对残缺家庭、悲剧人格、身份焦虑的书写却具有积极意义,她的书写引发了当代读者对家庭问题的反思,这与当前社会对家庭教育重要性的认识不谋而合。
正如本文开篇所言,家庭在一个人的成长过程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而父母作为家庭的主导者、孩子们的第一任老师,在孩子们的成长过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考琳·麦卡洛从创伤的角度对极端母爱、残缺父爱导致的性格悲剧、身份焦虑进行了呈现,她的意图在于启迪当代父母要给孩子一份完整的爱、一份承载着责任和义务的爱,这样才有益于孩子的成长,有益于整个人类社会的进步。像艾里希·弗洛姆所言的缺乏“蜂蜜”、“乳汁”的母爱、承载着父权意志的父爱都是不健全的爱,母亲屈于从属地位、父亲为绝对权威或父亲缺席的家庭都是不健全的家庭,极端的母爱、残缺或畸形的父爱都会导致人格悲剧,引发身份焦虑。
[1][美]查尔斯·S·卡弗.人格心理学[M].梁宁建,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
[2][奥]弗洛伊德.论无意识与艺术[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21.
[3][美]艾里希·弗洛姆.爱的艺术[M].李健鸣,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3.
[4][澳]考琳·麦卡洛.恺撒大传·十月马[M].龙红莲,汪树东,译.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6.
[5][澳]考琳·麦卡洛.摩根的旅程[M].李尧,李轶群,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6][澳]考琳·麦卡洛.遍地凶案[M].孔庆华,译.北京:译林出版社,2012.
[7][奥]弗洛伊德.弗洛伊德文集[M].卒文博,译.长春:长春出版社,2004.230.
[8][澳]考琳·麦卡洛.荆棘鸟[M].曾胡,译.北京:译林出版社,2012.
[9][澳]考琳·麦卡洛.呼唤[M].李尧,译.北京:作家出版社,2006.432.
(责任编辑:许桃芳)
Crippled Family,Morbid Life——Analysis of the Problem of Personality Disorders inColleen McCullough's Novels
XU Mei
(Northern Beijing Vocational Education Institute,Beijing 101400,China)
Family is the basic unit of the whole society.It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production of ideology.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arents and parents'division of labor in the family is a typical template for the formation of family ideology to children.In Australia famous contemporary female writer Colleen McCullough's novels there are many families being in fragmentary state:extreme motherly love,fatherly deformity,children's personality generally showing the pathological characteristics,and that all working in children personality morbid and family incomplete not unrelated.Paper uses Erich Fromm's relevant argumentation about love to analyze the pain of tragic personality caused by incomplete families in Colleen McCullough's novels deeply.Paper explores the social enlightenment e of literature,promotes the progress of human civilization,leads to contemporary people to think.
Colleen McCullough;father;mother;children;personality
I106.4
A
1672-626X(2016)02-0118-08
10.3969/j.issn.1672-626x.2016.02.019
2016-01-07
徐梅(1978-),女,河南永城人,北京京北职业技术学院副教授,文学博士,主要从事文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