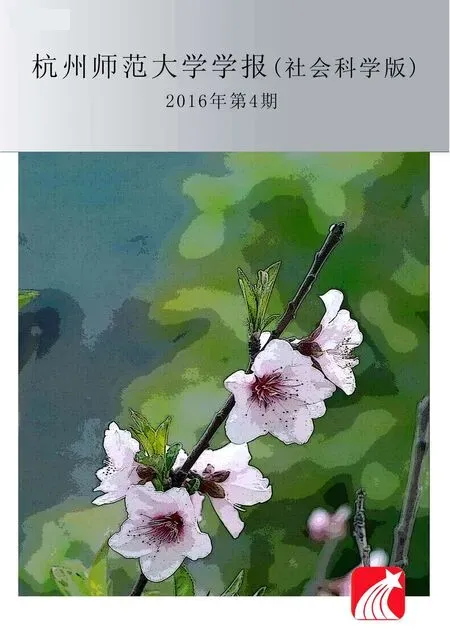告而不别黑格尔——中国当代文论学理建构轨迹的反思
王 坤
(中山大学 中文系,广东 广州 510275)
告而不别黑格尔——中国当代文论学理建构轨迹的反思
王坤
(中山大学 中文系,广东 广州 510275)
摘要:中国当代文论的学理建构,呈现出对西方思想“化”与“去”的演变轨迹,最典型的个案就是黑格尔影响力的变化。黑格尔的理论体系,围绕着先在性的绝对理念而建构,展开方式十分严密,终极目的则为囊括所有对象,一度影响深远并取得巨大成功。随着后现代思潮的进入,黑格尔体系遭受巨大冲击,同一性、本质论、二分法以及宏大叙事等,纷纷受到质疑、被悬置甚或被抛弃。应当实事求是地肯定黑格尔对中国当代文论学理建构的历史功绩,尤其应当尊重他的历史哲学视野和辩证法思维方式。一味地“黑格尔化”或“去黑格尔化”,都是不可取的。可将对外来理论“化”与“去”的交替,视为当代文论建设过程中的常态。
关键词:黑格尔;当代文论;学理建构;“去黑格尔化”
中国当代文论的建构,内涵广泛而复杂,要想居高临下予以全面把握而无一遗漏,绝非易事。但是,如从最基本的学理建构入手,比如这门学科的研究起点、研究过程中遵循的基本原则、研究所要达到的目的等等,还是能够看得比较清楚的:除去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在当代文论的学理建构中,能够发挥支配性影响的,还有诸多西方文论大家,黑格尔首当其冲。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说,当代文论学理建构的演变轨迹,也就是黑格尔思想影响力的变化曲线。
站在21世纪文论发展前沿,回顾半个世纪以来西方文论中国化的历程,许多问题现在日益明朗。比如,西方学界对黑格尔评价的变化:当他还在世时,西方学界不仅在“黑格尔化”,也萌动了“去黑格尔化”,比较典型的就有以谢林为代表的德国浪漫主义,以对意志的张扬,抗衡具有忽略个体意味的理性。随着分析哲学、符号学等等的兴起,西方学界的“叛离黑格尔”[1](PP.25-79),已经发展到系统研究马克思、恩格斯对黑格尔的“化”与“去”这一阶段,像2006年美国莱文教授的《不同的路径:马克思主义与恩格斯主义中的黑格尔》一书,就对该问题进行了相当深入的探讨。[2]
对于当代中国文论界而言,提及黑格尔,首先就是仰慕他的学术成就,感念他在正规学术训练方面的榜样作用……随着中西方文化交流的通畅,西方文论的进展正在以近乎同步的频率进入中国当代文论。经历后现代思潮的冲击之后,心平气和地思考问题,学界也能慢慢体味到,西方对黑格尔的“去”,绝非一时心血来潮;而我们对黑格尔的“化”,也能在此基础上“前修未密,后出转精”了。
作为“港湾”的黑格尔:把“船儿”拽过来
学术研究其实就是研究者不断靠近研究对象的探讨过程。通俗一点说,研究者是“船”,研究对象是“岸”;船靠岸理所当然,岸靠船有违常情。
但是,如果研究者实在太伟大了,就会形成宏大无比且不断增长的气场,置身其中,岸与船的关系难免发生错位。比如黑格尔,他的理论就在无形之中成为港湾,研究对象反倒变成向他靠拢的船只。黑格尔以绝对理念为核心所建构的庞大而又无所不包的体系,就是这么一个港湾;整个大千世界、宇宙万物,恰似一艘巨轮,径直朝着港湾行驶过来,或者说被拽过来,停靠在他这个码头里。
万一码头停靠不下这艘巨轮怎么办呢?运起气场、挥动巨手给船儿整形:使劲捏巴,尽力规整,甚或抡大锤砸;合则存,悖则弃。总之得让船儿的形状吻合码头的地势,以便停靠得妥妥贴贴、严丝合缝。难怪罗素讽刺黑格尔:宇宙是看了他的哲学著作后才演化成现在这模样的[3](P.282)。
明白了这一点,就会理解20世纪西方哲学为什么会提出“构造哲学体系已经完全过时”[1](P.20):因为,体系除了理论所具有的一切优点,还兼有无法回避的缺陷:体系一旦形成,往往如同港湾,研究对象则成为向港湾靠拢的船只;结果就成了不是研究者向对象靠拢,而是让对象向研究者靠拢。也就是说,文论的体系建构,从学理上说,是首先确立一个基点,并且认定从这个基点出发,经过既定的程序推演,可以囊括文论研究的所有对象,直至囊括整个宇宙。
只是,尽管黑格尔的港湾在规模上空前绝后,但与整个宇宙相比,还是相形见绌。船儿虽然被强行塞进港湾,却无法将其长久“摁”在那里。如果说船儿“挤爆”了港湾可能有点不恭敬的话,那么说船儿不久就“弹出”了港湾应该是公允的。
黑格尔之所以被“去”,最直接的缘由,就是颠倒了船与岸的关系。
具体来说,“绝对理念”正是黑格尔思想的起点,以此为基础,他建构起那囊括一切的港湾。
为了完满地表达他的体系,黑格尔美学理论的展开过程和唯一目的,自然而然地是这个先在绝对理念在人类感性领域的发挥和推演:“美就是理念的感性显现。”[4](P.142)由此,艺术作品的构成,就是内容与形式的二分:理念是内容,感性显现是形式。对于艺术来说,内容是第一位的,形式是为表达内容服务的;或者说,最关键的是本质,也即理念,形式不过现象而已。无论现实生活还是作品本身,现象总是表层的,本质才是内核;而对艺术本质乃至世界本质的探究,经过执著的追求,一定会指向并通达万物的基始,也就是同一性。
绝对理念对当代文论学理建构的影响,主要体现为这三大部分:二分法、本质论、同一性。
站在新世纪的学术平台上,回顾西学的“去黑格尔化”历程,大致可以看出:对同一性的挑战,始自与黑格尔同时代、以谢林为代表的浪漫主义。在尼采之前的克尔凯郭尔,以注重个体生存的方式,从学理上正面抗衡黑格尔绝对理念的衍生物,即同一性:黑格尔的理论是无所不包的,要说有遗漏的话,那么唯一的遗漏就是对鲜活的个体生命的忽视。弄清了这一点,也就可以将尼采与克尔凯郭尔相提并论,他们是同一类型的思想家;同时,还可以由此纠正人们平时多用非理性与理性相对照的做法:与理性相对照的,应该是意志。因为意志所充盈的生命色彩和个体特征,恰恰是理性所缺乏的。到了上世纪60年代,后现代之所以能够撼动整个西方学界,就因为它的矛头所向,直指忽略个体的同一性、整体性,而后现代与之抗衡的理论武器,就是对差异性、个体性的大力发掘和无限张扬。
就二分法的影响而论,西学在艺术理论领域里的“去黑格尔化”,可以追溯到索绪尔,他关于语言符号能指与所指的划分,从认识论角度看,把由来已久、被绝对理念系统化、定型化的二分法,又向前推进了一步:无论内容还是形式,无论本质还是现象,都只是人们面对现实世界,抽象、概括、提炼出来的概念、范畴,它们必须通过符号才能得到表达,更具体地说,要通过符号的所指来表达。在黑格尔以及之前的时代,人文学者还没有把实际存在的语言符号当作认识论的主要对象,所有的探讨,都是以越过或省略符号阶段的方式进行的。
自索绪尔开启符号学研究大门之后,西学也开始了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俄国形式主义对艺术的研究,为什么会集中于诗歌语言?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越过黑格尔的先在绝对理念,面对当下最直接的对象:诗歌得以表达的语言符号。所以,在他们的著作中,对内容与形式二分法的批评最为集中,代之以对艺术语言能指与所指内涵及其变化规律的研究。
我国当代文论的“去黑格尔化”,迄今主要体现为对本质论的抛弃或回避。
对文学本质的探讨,从建国之初到上世纪新时期以来,历经曲折,从工具论到意识形态论,从观念论到活动论,经验弥足珍贵,教训堪称惨痛。到了90年代,与西方文论新见迭出的局面相比,我们确实处于相应的徘徊状态,以至学界出现了文论界患有“失语症”的判断。[5]时逢后现代思潮进入我国,其中的反本质主义思路,对于本质论思路来说,不啻当头棒喝,令学界有如醍醐灌顶:一味地追究文学是什么,恰恰限制了文学的鲜活与多样,文论研究不能再沿着将文学“是”下去的思路前行了。
综合来看,黑格尔绝对理念对当代文论的影响,因其对单个人的个体性限制最大,尤以同一性为最,所以处于被“去”名单上的榜首位置。二分法与本质论,直接关乎对艺术的看法:二分法简化文学;本质论僵化文学。它们既源自西学,也“去”自西学;它们虽自西学而来,却并未随西学之去而去;当代文论中被“去”之本质论,其实已是充满中国特色的本质论了。
作为靶子的黑格尔:被拽过来的“船儿”又弹出了港湾
西方20世纪哲学所接收的最珍贵遗产之一,就是认识到哲学的关键问题还是在于客观性[1](P.7),所以分析哲学的研究对象主要就是辨别语言在指涉现实对象时,其命题的真伪;符号学则主要研究人类如何运用语言指称世界。它们与黑格尔的根本区别,在于对现实世界的看法:前者认为现实世界包括人类自身,无论有形的还是无形的,一切均是人类运用符号予以建构的结果,人类还在永不停息地探索、认识一切,抽象出新的概念范畴,运用符号予以表征,这条建构之路是无穷尽的;黑格尔则认为现实世界是先在的绝对理念的体现,这体现是可以达到完满境地的,因而他所追求的,就是把现世的一切,都解释为先在的“绝对理念”存在的体现。杰姆逊教授将黑格尔学说与结构主义进行比较,指出前者致力于组织这个世界,后者则把世界当作符号系统来解读,学理依据即在于此[6](P.2)。
西方文论学理根源的新旧之别,涉及到贯穿古今的三大问题:经验论与唯理论、实在论与唯名论、一元论与多元论。黑格尔是“唯理论与唯心论相结合”[1](P.9)的典型代表,二者虽非永远结合,但只要结合,“它们往往与一元论相合”。[1](P.15)而一元论同时又被当作忽略情感的同义词。[1](P.83)
有趣的是,以“叛离黑格尔”开始的20世纪新学说,并没有对黑格尔口诛笔伐、大动干戈,在其诸多巨著中,直接谈论黑格尔的篇幅甚至很少,因为,根据新学说,黑格尔的港湾,完全停靠不了一度被拽进来的船儿,其反弹离港已是不争的事实,无需多谈。
船儿反弹出港的方式有自动的:比如被黑格尔压缩为三官的五官[7](PP.533-536),会自动回归常识、恢复正常;也有人为的:罗素这些人就是以绕过“马奇诺防线”的方式,从根子上另起炉灶,让船儿“乾坤大挪移”,轻飘飘地弹出黑氏港湾,驶向别处。
后现代思潮可没那么文质彬彬,它以对现世差异性的无限张扬、对先在同一性的彻底解构,搅动了整个西方思想界,并极大影响了我国当代文论界。追根溯源,先在同一性的集大成者并定型者,非黑格尔莫属,非“绝对理念”而不能。由此,长期以来关于理性与非理性这对二元概念,终于等到了纠正其偏差的机会:人们常常用非理性来与理性相对,其实不然,与理性相对的,本应是意志。因为,理性的背后是先在同一性,意志的背后是现世差异性。意志所拥有的,正是理性所忽视的个体生命与存在特征。
与西方抛弃先在同一性有别,我国当代文论界对后现代思潮的接受,主要聚焦于解构本质主义;而本质主义的根源,恰与同一性、绝对理念一脉相承。
比照西学的“黑格尔化”与“去黑格尔化”,当代中国文论界学理建构的演变轨迹,如今也日渐显出“西学化”与“去西学化”两大脉络。文论界当初借助西学之力,曾将不少“船儿”拽进指定的“港湾”,经过一段时间的角力之后,一些船只现在正陆续“弹离”原来停靠的码头:近年来一些较为引人注目的成果中,相当一部分其实是“去西学化”的产物。重新认识、重新发现古人立场与见解的价值,越来越成为文论界的共识。
比如,关于宏大叙事的问题,文学研究中这种历史哲学视野的建立,其功绩与贡献,无论如何都是抹杀不了的。但是,在同一性的导向下,其忽略个别性的弊病确实越来越突出。
在我国当代文学语境中,宏大叙事是指在历史哲学视野的指导下,文学作品反映社会生活时,力求从大千世界各种纷繁复杂的现象中,提炼出本质,包括社会历史发展的趋势和规律。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当代叙事文学,甚或整个当代文学,说它是一部宏大叙事史,的确是基本符合事实的。包括古典文学作品,比如《红楼梦》,就是在这种文学观念的支配下,被解读为“中国封建社会末期的百科全书”。这种文学观念,自建国之初到“文革”结束,在我国文坛一直居统治地位。直到上世纪80年代末西方后现代思潮引进之后,情况才开始发生改变:彼时对“文革”文学及17年文学的反思,已经走出“拨乱反正”的政治需求阶段,开始从价值观念本身思考问题。后现代注重差异性、个体性的特征,刚好提供了新视角:以前太过注重同一性、普遍性了,而表现在文学中,就必然是对个体的忽略,尽管我们对社会与个人之间的辩证关系从理论上掌握得十分纯熟,但落到实处的话,最终肯定是要让个人服从集体的。也就是说我们的文学,原来一直注重宏大叙事,而忽略了个体。
利奥塔在《后现代状态:关于知识的报告》中使用“宏大叙事”一词,是用来指出:那些具有现代性质的科学一直在利用历史哲学的元话语证明自己的合法性,而支撑元话语的就是宏大叙事:包括精神辩证法、意义阐释学、理性、劳动主体的解放、财富创造等等。[8](PP.2-3)这种宏大叙事所起的作用,就是保护支配社会制约关系的机制的合法性。利奥塔的出发点,是质疑传统思辨哲学知识的合法性,典型的后现代立场。其观点自上世纪末引入我国后,关于知识合法性的问题固然引起学界高度重视。然而没有想到的是,“宏大叙事”一词因能够准确抓住我国当代文学的最大特点,所产生的影响竟然超过了对知识合法性的关注。时下的当代文学批评,如果没有对“宏大叙事”表明自己的不屑,几乎就不能入流了。即使偶有“重构宏大叙事”的声音出现,也不过倏忽而过罢了。
在无比庞杂的后现代理论中,“宏大叙事”不过一个气泡而已,然而这个气泡竟能使我国当代文坛产生剧烈震动,就因为它直接针对着深刻影响了当代文学的黑格尔学说。
黑格尔与中国当代文学的关系,真可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宏大叙事的背后,其实正是对当代文学影响最大的典型理论及其实践。而典型理论的高峰,就在黑格尔。可以说在当下的文学语境中,“宏大叙事”的批评对象,主要就是“去黑格尔化”。因为黑格尔学说的核心,就是追求普遍,展现他认定的那个“绝对理念”。
西方思想界的更新换代是比较迅速的。就在黑格尔学说达到顶峰之际,“去黑格尔化”已经开始了,且带有人身污蔑的色彩,比如把黑格尔当作“死狗”看待。这个话题,首先是由斯宾诺莎引起的:莱辛在一次与雅科比的谈话中(1780年6月7日),对当时有些人误解斯宾诺莎并将其当作死狗表示不满。黑格尔在自己的《哲学科学全书纲要》中提及此事,所持态度与莱辛相同:只有那些误解了莱辛,误解了思辨哲学的人们,才会把斯宾诺莎当作死狗。[9](P.6)马克思在引述这一历史掌故时,也表达了同样的观点:只有那些自以为是,其实根本不懂黑格尔的学问家,比如毕希纳、朗格、杜林、费希纳等人,才会幼稚无知地把黑格尔当作死狗;后来马克思还专门在《资本论》第1卷“第2版跋”中,特地郑重申明:自己就是这位大思想家的学生[11](P.24)
黑格尔的中心思想,就是强调人的意义在于使个人的东西变成普遍的东西,国家就是普遍。因而个人的最大意义,就是属于国家,而不是停留在家庭成员的阶段上。所以他在谈论精神的伦理阶段时,特别强调家庭与国家是同一个伦理实体的不同形态。家庭属于伦理的“直接存在的形态”,国家则属于伦理的“自觉存在的形态”。真正有意义、有价值的人生,是摆脱了家庭,上升参与国家生活。
黑格尔的学说,从根子上讲,是为普鲁士国家说话的:他一直在论证个人服从国家的自然性和必然性。为数不少的西方人,比如英国人和美国人,把黑格尔也当作法西斯的思想先驱,并非主观臆测。黑格尔关于战争、国家的理论确实如此:为了聚集人心,让大家放弃家庭的小利益,需要经常发动战争,因为战争能够使人舍家为国。
黑格尔学说的精要处,在于他从宇宙自然的运动中以及人类社会的发展中提炼出来的绝对理念,与辩证法一起,是一枚硬币的两面,不可分离。马克思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才是这位大思想家的学生:《共产党宣言》就是根据“正、反、合”的事物辩证发展理论,来分析社会历史演进过程和特征的: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首先生产的是它自己的掘墓人”——无产阶级[10](P.263)。也就是在这个意义上,后现代思想家德勒兹的“去黑格尔化”最为彻底:他连辩证法也要去掉。
黑格尔的绝对理念与辩证法,可以说是“从历史中来,到历史中去”。问题出在“去”的时候,他往往为了追求完满而削足适履。比如,为了证明“正、反、合”三大块的普遍性,将人的五官牵强地改为三官;为了证明德国统治世界的自然性、合理性,从世界地理的角度,将欧洲说成是“正、反、合”过程的结果,即世界的中心,而德国又是欧洲的中心[7](P.392)。
所以,西方“去黑格尔化”的声音中,随着时间的推移,切中肯綮之声越来越多。罗素以黑格尔为例,对哲学理论的价值判断所提出的建议尤其引人注目:不必追求完满,不完满的学说肯定不会全部正确,但完满的学说却可以“全盘错误。最富有结果的各派哲学向来包含着显眼的自相矛盾,但是正是为了这个缘故才部分正确”。[3](P.143)
作为导师的黑格尔:思维视野与思维方法泽被后学
黑格尔不是完人。假如他不那么在乎体系的完满,坦然地把缺陷当作题中应有之义,他的影响也许会呈现出另一种轨迹。
体系是围绕着基点来建构的,基点一旦确立就固定不变;然而世界是变化的,要把变动不居的世界装进建构完整的体系,必定会削足适履。问题的复杂在于,黑格尔理论体系的建构,是通过严密的逻辑来完成的。基点会出问题、体系会出问题,用于建构体系的逻辑不一定会出问题。比如黑格尔建构体系时所使用的辩证法,就可以继续有效。
对于当代中国文论界来说,黑格尔的意义,包含着最正规、最严格的学术思维训练。迄今在文论领域仍占据主流地位的思维视野与思维方法——历史哲学与辩证法——从纯正的学术意义上讲,可以说都是拜黑格尔所赐。时下文论界的诸多学人,要说没有仔细读过黑格尔著作的,估计不乏其人;但要说没有受到黑格尔影响的,实在难觅,除非决不认账。
在黑格尔那里,对历史哲学与辩证法的运用,有一个基本前提:始终围绕着先在的“绝对理念”而展开,其成果就是堪称体现人类思维水平的极致、无法正面攻克的“马奇诺防线”。黑格尔的叛离者们,看起来是轻松自如地绕过了“马奇诺防线”,其实,在作出这种睿智无比的选择之前,该有多少天资超常的学者为之耗费了太多心血。
文论界此前主要是在“黑格尔化”、“西学化”的道路上行进,如今面前出现了另一条道路,是否会多少有点诧异?
令研究对象向自己靠拢的思路,应当从此摒弃;先在性的绝对理念,可以考虑搁置;无意识之中对同一性的追求和对差异性的忽视,需要认真沉思。然而,把握对象的宏观视野与分析对象的辩证法,定当秉持。文论研究水平的真正提高,借他山之石攻自家之玉的真正落实,离不开“化”与“去”的不断轮回。
当下尤须注意的是,后现代由对先在性的否定,继而质疑一切可追溯至先在性的历史规律、事物本质、深层特征等等,并以人类建构世界的思路,高扬符号学研究。殊不知,人类自身的建构物中,难道其中就没有规律可寻,比如符号本身?去掉起点问题,黑格尔对过程的研究与成果,堪称宝山一座,后人可从中汲取无尽滋养,切不可盲从后现代对黑格尔的完全“叛离”。
就西方学界而论,斯宾格勒的《西方的没落》[12]不以民族而以文化作为历史的主体,将文化的发展视为有机体的生命运动和生命周期;汤因比的《历史研究》[13]提出文明形态史研究,用“挑战与应战”理论解释文明的起源、生长与发展。雅斯贝斯的《历史的起源与目标》提出的轴心期理论,世界历史分为四个阶段:史前时代、古代文明、轴心期、科学技术时代;到了轴心期,人开始出现:“这个时代产生了直至今天仍是我们思考范围的基本范畴,创立了人类仍赖以存活的世界宗教之源端。”[14](P.9)这些深刻影响20世纪的思想,无一不是黑格尔式学理的延续。
西方学界对黑格尔的“去”,除去像“死狗”那种带有污蔑色彩的刻薄言辞外,在误解基础上“去黑格尔化”的声音亦颇为常见,最典型的事例莫过于“格鲁格先生的鹅毛笔”。与黑格尔同时代的格鲁格,借批评谢林之名,讽刺黑格尔的绝对理念之类的纯粹概念:难道我手上的这支鹅毛笔可以从纯粹概念里推演出来吗?
其实,在黑格尔哲学里,有着三个“在先”:从逻辑上讲逻辑学先于自然;从时间上讲自然哲学先于人类;就自然界的潜在发展目标而言,精神哲学先于自然哲学。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并非抽象地谈论绝对理念,而是始终结合具体历史事实谈论问题,并认为历史是朝着既定方向发展的。如果不懂这三个“在先”,就一定会误解黑格尔。格鲁格误解的根源,在于理解绝对理念的体现时,认为黑格尔说的自然界和人类是从纯粹概念里推演出来的,所以他才那么充满自信地讽刺黑格尔。自格鲁格开了这种误解的先河,一直到现在,对黑格尔的误解都没有停止。而实际上黑格尔所谓绝对理念的体现,指的是它在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中的展开、表达。也就是说自然现象中一定包含着绝对理念,绝对理念一定体现在自然现象中,没有一个脱离了主体的客体,也没有一个脱离了客体的主体;现实的东西和逻辑的东西是结合在一起的。现实世界里怎么会有像格鲁格所理解的那样傻的唯心主义者呢?在三个“在先”里,黑格尔的意思其实非常清楚:人是自然界发展的最高峰,自然界本身蕴含着一个潜在的发展目标:一定会发展到出现人的阶段。因而,就目标而言,人先于自然,但时间上实际发生的却是自然先于人。
如果抛开黑格尔绝对理念的先在性,着眼于当下的话,中国当代文论可从中吸取的东西,可谓很多。以内容与形式的二分法而论,其简化艺术的弊病虽一目了然,但其现实生机仍有勃然不可阻挡之势:只要世界上的美与艺术还离不开内容与形式,后者就必须是“具体可感的”。因此就必须认可一个基本规则:“艺术不是为一小撮有文化教养的关在一个小圈子里的学者,而是为全国的人民大众。”[4](P.347)黑格尔本人说这话的目的,倒不是为了强调艺术应当为什么人服务,而是为了落实“美就是理念的感性显现”:美与艺术的表现形式必须是生动活泼、直观可感、任何人一看就明白的。
后现代艺术强调符号的能指功能,忽略符号的所指功能,其艺术观念的实践结果,就是让人不知所云。这在理论上是有意义的:未来的某个时候,人们的认知能力发展了,美与艺术是由内容与形式构成的阶段,迟早会被超越;符号的能指本身,迟早会成为主要的审美对象。但在目前,还不会成为主流。在并不精确的意义上,如俄国形式主义者所言,形式+内容=酒杯+酒。由此,只要喝酒还用得上酒杯,那么,内容与形式二分法就无法完全彻底地被“去”掉。
我国当代文学中“宏大叙事”的存在,实践的根源肯定不在黑格尔,而是叙事文学自身发展的结果。在创作中,叙事对象由个人之事走向社会之事是自然而然的过程,古今中外无一例外。比如,孔尚任的《桃花扇》写于康熙三十九年,即1700年,早于黑格尔出生近百年,其创作宗旨就是“借离合之情,写兴亡之感”。那是典型的宏大叙事。而且,从效率来讲,宏大叙事的信息含量肯定比私人叙事更多,效率更高。
但如从理论角度看问题,“宏大叙事”的源头最终是指向黑格尔的:主要在于“绝对理念”所衍生出来的同一性及其化身——历史哲学。就黑格尔来说,他本人通过对浩繁的自然和历史资料的概括、总结,认定有那么个东西存在,于是孜孜不倦地上下求索,竭尽其能地论证、建构、显现那个梦牵魂绕的绝对理念。他对理想的追求可以说无比坚定、无比执著而又无比成功。个人对理想的追求本是好事,如果这理想被强权者当作普遍模式并以强力的方式予以推广,结果是否如创始者所预期的那般模样可就难说了。在现实中,黑格尔所追求的东西就曾被斥为万恶之源,比如阿多诺在《否定的辩证法》里,就把奥斯威辛集中营这种人间惨剧的发生,归罪于源自黑格尔的同一性:“纯粹同一性的哲学原理就是死亡。”[15](PP.144,362)
后现代主张差异性、私人叙事,其启示对我们来说,不应当仅仅停留在对宏大叙事以及同一性本身的解构、否定上,而是要像黑格尔对待同一性那样,将其作为一种理想去追求。如果“去黑格尔化”不只是祛除他的观点,而是整个否定对理想的追求,将这种追求本身也予以解构、消解,那么,比起将纯粹个人的追求作为普遍理想强加给民众来,结果也许会更加令人震惊。当下的文学及理论,对此不能掉以轻心。宏大叙事,存在有痒,去除则殇。
中国当代文论的学理建构,完全去掉西学、去掉黑格尔是做不到的,完全回到古人的原初语境也是做不到的。在全球日趋同步的时代,“化”与“去”的持续循环,将会成为文论界的常态。
参考文献:
[1]艾耶尔.二十世纪哲学[M].李步楼,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
[2]莱文.不同的路径:马克思主义与恩格斯主义中的黑格尔[M].臧峰宇译.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
[3]罗素.西方哲学史:下卷[M].马元德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
[4]黑格尔.美学[M].朱光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
[5]曹顺庆.文论失语症与文化病态[J].文艺争鸣,1996,(2).
[6]弗·杰姆逊.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M].唐小兵译.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
[7]黑格尔.自然哲学[M].梁志学,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8]利奥塔.后现代状态:关于知识的报告[M]//后现代主义.赵一凡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
[9]黑格尔.哲学科学全书纲要[M].薛华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10]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11]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12]斯宾格勒.西方的没落[M].吴琼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6.
[13]汤因比.历史研究[M].曹未风,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
[14]雅斯贝斯.历史的起源与目标[M].魏楚雄,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
[15]阿多诺.否定的辩证法[M].张峰译.重庆:重庆出版社,1993.
(责任编辑:吴芳)
收稿日期:2016-06-09
基金项目:国家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基金一般项目“当代文论与‘去黑格尔化’研究”(13BZW004)、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基金一般项目“文论创新与经典重译”( GD12CZW10)的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王坤(1957-),男,湖北蕲春人,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当代文论研究。
中图分类号:I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2338(2016)04-0074-07
DOI:10.3969/j.issn.1674-2338.2016.04.008
Bidding Farewell without Leaving Hegel: Rethinking on the Evolution Tracks of the Theoretical Construction of the Chinese Contemporary Literary Theory
WANG Kun
(Department of Chinese, Sun Yat-sen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275, China)
Abstract:The theoretical construction of Chinese contemporary literary theory presents as the evolution tracks of -ism and de- on western theories. The most typical case is the variation of Hegel’s influence. Constructed on the basis of the preexistent Absolute Idea, Hegel’s theoretical system is very rigorous in logic. With the ultimate aim of containing all the objects in the empirical world, Hegel once has made far-reaching influence and received great success. With the incoming of postmodernism, Hegel’s system suffered fierce critique. His doctrines such as Identity, Essentialism, Dichotomy and Grand Narrative have been doubted, suspended or even abandoned. It is proposed in this paper that we should re-evaluate Hegel’s historical contribution to the theoretical construction of the contemporary literary theory with objective attitudes. Moreover, we should also give honor to his perspective of the Philosophy of History and thinking method of Dialectics. Any extreme of Hegelism or de-Hegelism is unacceptable. The alternation of -ism and de- shall be viewed as normal during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contemporary literary theory.
Key words:Hegel; The contemporary literary theory; theoretical construction; the de-Hegelis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