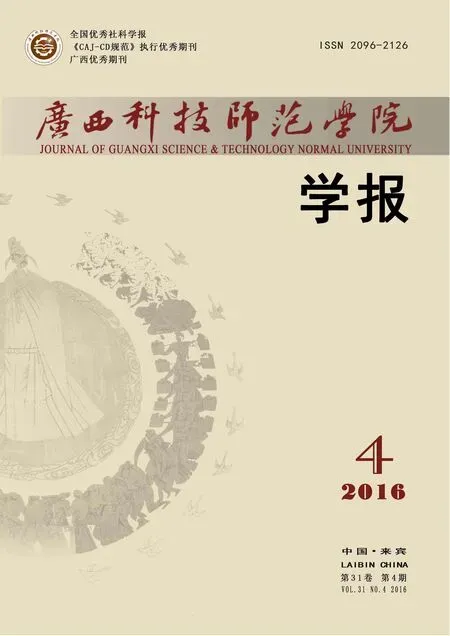壮族歌圩:审美与仪式的复合体
李英辰
(广西民族大学文学院,广西南宁530006)
壮族歌圩:审美与仪式的复合体
李英辰
(广西民族大学文学院,广西南宁530006)
壮族民歌充斥着壮族人生产生活的各个角落,壮族民歌曲目繁多,许多经典之作更是口耳相传历经百年而不缀。这一方面是壮族人喜歌爱唱的民族特质所决定的,另一方面也是与壮族歌圩这一特定的传统习俗活动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壮族歌圩是一个审美与仪式的复合体,作为审美活动的壮族歌圩让人们在欣赏那清透美妙的歌声的同时获得精神的愉悦与满足,作为仪式活动的壮族歌圩让人们在固定的时间、地点参与的过程中获得精神的圣化与神秘感。壮族歌圩具有审美与仪式的双重属性,审美与仪式在此活动中相互结合在一起,互为特性,因此深入研究壮族歌圩的审美仪式化与仪式审美化对于正确解读壮族歌圩是十分必要的。
壮族歌圩;审美仪式化;仪式审美化
壮族是一个能歌善唱的民族,歌圩文化在壮族文化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歌圩是壮族群众在特定时间、地点举行的节日性聚会歌唱活动形式,壮语称为“圩欢”、“圩逢”、“笼峒”、“窝坡”等。歌圩在壮族聚居地区分布甚广,也有各自不同的称谓,但均有“坡地上聚会”、“坡场上会歌”或“欢乐的节日”的意思。它是壮族民间的传统文化活动,也是壮族青年男女对唱情歌、倚歌择配的重要场所。
作为古代百越民族后裔的壮族,自古便流传着歌圩的风俗。在传统的春节、“三月三”、中秋节等节日,壮族民众都有赶歌圩的传统风俗。这其中最为特殊的当属壮族的“三月三”民歌节,“三月歌圩歌满天,哥妹赶圩赛蜜甜”,三月三,赶歌圩是壮族的传统节目,是一个专门为民歌而设立的壮族传统节日,在广西境内,三月三属于法定假期,这是其他地区所没有的。潘其旭在其《壮族歌圩研究》中指出歌圩在壮民族文化中的重要地位,他说歌圩“都是同壮族群众的物质生活、宗教信仰、道德风尚、心理素质、传统观念相关联并互相制约的。歌圩与各个节日往往构成一个整体,围绕着劳动生产的节奏和精神生活的需求,成为人们表达思想、交流感情和进行审美活动的重要聚会方式,是一种综合性的民族文化形态”[1]47-48。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壮族歌圩是壮族文化的重要载体,与整个民族的生活息息相关,不可分割。壮族歌圩经历了从传统的乡村歌圩到现代的城市歌圩的变化与发展,但壮族歌圩的内在属性却没有根本性的变化,它依然是一个审美与仪式相互交织在一起的一个复合体,是一个饱含着仪式特质的审美活动和一个充斥着审美要素的仪式活动,因此关于壮族歌圩的审美仪式化与仪式审美化将是本文探讨和研究的主要问题。
一、壮族歌圩:审美的仪式化
在传统的壮族歌圩发展中,经历了从“娱神”到“娱人”,从“群舞”到“群歌”的发展演变。壮族蚂节的祭祀活动就经历了这样的一种发展。壮族自古就是稻作的民族,自古就有许多与种稻相关的祭祀活动,想要通过祭祀,实现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的美好愿望,其中蚂节就是最具代表性的。蚂节又叫蛙婆节,主要活动是祭祀和埋葬青蛙,活动的主要程序是:捉蚂——祭蚂、葬蚂——化装表演——对歌。随后的发展中,蚂节活动已经演变成了一种象征性活动,祭祀蚂变成了对歌会,由对歌会发展成了歌圩活动,蚂节的功能已经由娱神向娱人转化了,对歌活动就是这种转化的标志。除此之外,汉代王逸在《楚辞章句》中记载:“楚国南郢,沅、湘之间,起俗信鬼而好祠,其祠比作歌乐鼓舞,以乐诸神。”这段话的描写反映了这种祭祀活动的原始风貌。到了明代嘉靖年间,《钦州志》有记载:“八月中秋假名祭报,扮鬼神于岭头跳舞,谓之跳岭头,男女聚观,唱歌互答……”这些都反映了原始祭祀仪式从“娱神”到“娱人”、从“群舞”到“群歌”的转化,进而形成歌圩这一群体性对唱活动的过程。
壮族歌圩不再是单一的祭祀活动,而是演变成一种壮族人喜爱的审美形式。这种审美形式是以男女对歌为主体的多种活动的集合。壮族歌圩虽有很多种类,但一般情况下传统歌圩大致有四个相关程序:首先,是歌圩开始的祭祀仪式。传统的大型歌圩在举行之前都会先行祭拜仪式,如祭拜布洛陀、歌仙刘三姐、花婆神等。其次,倚歌择配。对歌的男女双方遵循着人际交往由浅入深的一般原则,由礼貌性地打招呼到慢慢地熟悉再到深交,由最初的相遇到最后的离别,对唱的情歌一般分为见面歌、探情歌、对问歌、初连歌、连情歌、定情歌、盟誓歌、叮咛歌、离别歌[2]187这九个阶段。再次,赛歌赏歌。这个阶段则有盘歌、猜歌、对子歌、连故事歌等歌唱形式。最后,其他文娱活动。一般情况下,大型的歌圩期间还伴有抛绣球、抢花炮、斗蛋、师公戏、壮剧等活动。
在壮族歌圩中,青年男女们通过对唱情歌的形式来互相认识、传情、诉衷肠,这些情感在歌中的表达都离不开比喻、暗示、双关等表现手法的运用。歌词随唱随编,运用的表现手法符合当时的场景,表达亲切、自然、感人,这种审美化的情感表达正是壮族歌者智慧和审美意识的体现。除了情歌对唱外,壮族歌圩中“斗智斗勇”的对歌活动也吸引着人们去参与,以电影《刘三姐》中刘三姐带着众乡民与地主莫怀仁请来的三个秀才对歌为例,开始时秀才夸自己歌多,刘三姐巧妙地回答“你歌哪有我歌多,我有十万八千箩,只因那年涨大水,山歌隔断九条河”;接着秀才以问答的方式出题为难众人,秀才唱到“三百条狗交给你,一少三多四下分,不要双数要单数,看你怎样分的均”,在刘三姐的帮助下周妹巧妙应答“九十九条圩上卖,九十九条腊起来,九十九条赶羊走,剩下三条财主请来当奴才”,对唱中这样机智巧妙的回答比比皆是,不难看出壮族民众机敏、灵活的性格特点,这也是参与到歌圩这一审美活动所必须具备的素质,刘锡蕃在《岭表记蛮》中说,壮族人“无论男女,皆认唱歌为其人生观之主要问题,人之不能唱歌,在社会上即枯寂寡欢,即缺乏恋爱求偶是之可能性:即不能通今博古,而为一蠢然为豕之顽民”。由此可见,壮族人不仅重视唱歌,而且还重视歌的质量,歌圩活动亦成为了一个“考究学问”的场合。壮族人民把自己的聪明才智,机智、灵活的性格特征展现在丰富多彩的歌圩活动中,在参与的过程中得到对自身本质力量的确认,获得一种身心满足的审美体验。就像格罗塞所说:“诗歌,是为了实现一种审美的目的,运用有效地审美形式,表达人的内心或外界的现象的一种语言的表现。”[3]129壮族歌圩就是这样一种有效地审美形式,使人们在审美活动中获得美感和精神的满足感。
“音乐能够震动人的整个心灵,对人的生命产生广泛而深刻的影响。”[3]168在壮族歌圩这个重要的娱乐集会活动上,人们身心得到放松,精神需求得到满足,这样的一种娱乐方式已经深深地嵌入壮族人的生活中,滋养着壮族人民的心灵和情感,使人们在参与活动的同时能够获得一种自然的审美享受。壮族人也正是在这样的活动中展现着自身“歌化”的审美特质和审美生存方式。
同时,壮族歌圩不仅仅是一场审美活动,其中还包含了多方面的审美仪式化现象。壮族歌圩举办的时间、地点和流程是固定的,一般在每年的春秋季农闲的时候举行歌圩活动,举办的场地“于村之庙附近地段空阔之处”[1]78,也就是说歌圩一般在庙宇、神社附近的空阔地段,位于神圣之地上举行。这使得歌圩本身就带有一定的神圣性。在许多大型歌圩的活动流程上首先是要举行祭拜仪式的,祭拜的对象有布洛陀、刘三姐、花婆神等,这些都是壮族神话中的重要人物,其中刘三姐更是被称为壮族的歌仙。在歌圩开始之初举行祭拜仪式,目的是为了强化人们的仪式感,强调歌圩的重要性、神圣性,召唤着人们来参与其中。在倚歌择配环节,男女双方的情歌对唱,不仅仅是一种审美形式,更是一种祭神的仪式活动。对唱情歌的男女双方通过一场有开始有结尾的完整的对唱过程,获得情感的交流,达到愉悦神灵的目的。对此,潘其旭在《壮族歌圩研究》中说:“初民认为,人的两性关系及生育机能,对自然界(包括植物、动物,天地山川、日月星辰、风雷雨电及人格化的其他自然神灵)具有感应的作用和影响。从这种原始观念出发,他们把欢会男女,作为祈福禳灾、促使作物丰产和人畜兴旺的一种特殊手段,而人们举行庄严的仪式,参加相应的活动,实际上也就以此并首先是作为一项宗教义务来履行。”[1]91-92作为审美活动的歌圩在这里通过仪式强化了人们参与其中所获得的审美深度,是审美仪式化的重要体现。此外,在歌圩上,歌曲的旋律是固定好的,只是根据不同的场景填不同的词来唱,因此歌曲的表达不是个人的情感,而是群体共有的情感的呈现[2]202。这样反复使用的旋律具有一种神圣的力量,能够使这些歌在不同的听者耳中获得相通的审美感受,即是在强调着传统的意义,也唤起了听者心中与之相关联的情感。
承接传统壮族歌圩发展而来的现代歌圩——南宁国际民歌艺术节是关于民歌的一场盛大集会。南宁民歌节继承和发展了传统壮族歌圩,实现了从乡村歌圩到城市歌圩的转变。节目设置更加的国际化和多元化,为观赏者呈现出一场场震撼的视听盛宴。南宁国际民歌艺术节作为现代歌圩依然表现出了审美仪式化的特征。与传统壮族歌圩一样,南宁国际民歌艺术节也有固定的举办时间、地点和流程。在每年的开幕式上,都首先举行升国旗唱国歌和升民歌节会旗唱民歌节会歌的仪式,这一流程增强了参与者对民歌节的认同感。《传统的发明》一书中说到:“国旗、国歌和国徽是一个国家用以宣布自己的认同和主权的三个象征,由此它们立刻赢得了尊敬和忠诚。它们自身也反映了一个国家的整个背景、思想和文化。”[4]11南宁国际民歌艺术节通过举行升旗仪式,演唱国歌和会歌,增强了开幕式的庄严性、权威性和神圣性。因此,当作为审美主体的观众们在欣赏开幕式的审美活动过程中,获得的不仅仅是审美需要的满足,审美主体还能从中体会到审美仪式化给审美活动带来的神圣性的灌入,增强了民歌节这一审美活动的权威性和庄严性,参与者不仅获得了美感还在这带有神圣性、庄严的仪式中获得了一种对家国的归属感和认同感。
二、壮族歌圩:仪式的审美化
在关于歌圩起源的研究中,目前比较有代表性的是潘其旭在《壮族歌圩研究》中的四种观点:一是歌圩起源于祷祝丰年;二是歌圩起源于歌唱择偶;三是歌圩起源于悼念殉情者;四是歌圩起源于歌仙刘三姐传歌[1]50-53。就起源来看,歌圩与原始宗教仪式有着密切的联系。歌唱形式最初是作为祭祀仪式中的一种娱神的表演形式而出现的,原始氏族社会特定时间和地点的宗教集会使歌唱变得固定化,并通过集体性的祭祀仪式被广泛的接受和认可,又因其宗教聚会的神圣性,歌唱变得更加必要。宗教活动给歌圩的产生提供了时机、场所和条件,是歌圩起源的重要原因。在上文提到过的蛙婆节中,我们了解到蛙婆节作为祈求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的一个祭祀仪式,其祭祀的流程就包含有对歌活动。壮族歌圩还与原始宗教活动一样具有广泛的群众性和庞大的集体性,曾经有明代壮族诗人黎申产对壮族歌圩做过这样的描述,他说“岁岁歌圩四月中,欢聚白叟与黄童”,到了举行歌圩的时候,壮族无论是少男少女还是老翁幼童都积极参加,向我们展现了壮族歌圩活动的盛况。壮族歌圩与原始宗教祭祀仪式的特征有许多相似之处,这些都在显示着壮族歌圩与原始宗教仪式的密不可分的联系。除此之外,我们还可以从历史古籍中发现一些影子,例如:《说蛮》记载:“桐人……春秋场歌,男女会歌为异耳,言会歌则年岁佳,人无疾病”;清乾隆十一年修幕的《镇安府志》记载:壮人“元宵前后,以大粽、酒淆祭上神,杂坐祠前共饮,唱土歌以祝太平”。这些记载都在说明着壮族歌圩与原始宗教祭祀仪式的密切联系。我们认为,原始宗教活动就是歌圩的母体,歌圩是从它那里脱胎出来的[5]。
特纳在谈到仪式的交通与变迁的特质时,他认为,仪式是一种通过表演形式进行人际交流和文化变迁的“社会剧”[6]15。在壮族歌圩中青年男女通过对唱情歌的方式来进行情感交流,用男女相合的情感呈现取悦神灵。除此之外,每年的歌圩活动也是壮族文化传承的重要象征性活动和载体,由于壮族早期没有统一的文字,人们习歌多靠口耳相传,歌圩活动是强调和加深壮族文化记忆的重要途径。
由此,我们可以说壮族歌圩就是一种仪式活动。并且其包含的神圣性并没有因时代的发展而消失,而是内在的影响着壮族歌圩的发展。通过仪式的进行,它承载的象征意义和社会规则被所有与仪式有关的人,比如说仪式的参与者和观赏者内化。这样,仪式就实现了个人与群体的认同,并由此建立起一个社会共同体和一定的社会秩序。壮族歌圩作为一种仪式活动有着召唤人来参与其中的特殊功能,在特定的时间和空间里,参与者脱离了日常生活的轨迹,在仪式活动中获得人与人、人与社会的相互认同。在壮族歌圩中,音乐艺术是仪式庆典必不可少的强化手段,它提供了“融化自我与他人之间的人为界限的最简洁、最省力甚至也是最自然的溶剂”。音乐手段也被广泛用于团结听众。通过音乐的手段,一种超个人状态被创造出来,歌手和听众可以在其中结为一体,加入一种“共同意识”、一种共同的思维、态度和情绪模式之中[7]173。使人们在仪式过程中获得一种参与其中、统一于其中的一体感。在仪式中表演者所表达出来的东西在参与者那里产生共鸣,而仪式的表达又是与传统和形式息息相关,密不可分的,因此,仪式活动所揭示的实际上是一个群体价值。
埃伦·迪萨纳亚克指出:“艺术和仪式除了作为一般‘行为’共同具有很多相似性之外,实际上在实践中也常常是联系在一起的。在仪式庆典过程中,我们常常发现艺术:漂亮的或引人注目的物品的使用、特殊装扮的服饰的穿戴、音乐、视觉炫耀、诗性语言、舞蹈、表演。”[7]82仪式庆典中的艺术有助于把人们团结在共同的信仰和行为中。因此,人们总是倾向于将仪式审美化来完成,美化的手段已经与仪式密切联系在了一起。
在传统的壮族歌圩里,不难发现仪式审美化的倾向。壮族歌圩的举行地点多为空阔的郊外,歌圩在山水之中进行,大自然秀美的景色即会给人带来一种审美愉悦之感。参加歌圩的男男女女们无不盛装出席,精心的装扮有别于日常生活,以达到悦人悦己的审美效果。特殊的装扮有助于把参加者从事俗中分离出来,变得使其特殊。“被挑选出来使其特殊的绝对是被认为重要的东西:即作为庆典组成部分的物品和活动。”[7]99艺术在仪式活动中的合理应用使仪式庆典给人感觉良好,艺术手段在仪式中的体现就是仪式的审美化。
在现代社会,仪式活动已经完全象征化,并且这种仪式被应用到各种活动当中。政府或正式的社会团体尤其重视仪式象征意义的运用。例如每四年一届的夏季奥运会,每届都会举行隆重的采集圣火、传递圣火、开幕式表演、运动员入场、闭幕式等,这些活动无一不是一种象征性的符号。通过这一系列的仪式活动,唤起人们的回忆,从而使团体成为团体,国家成为国家。
由壮族传统歌圩发展而来的现代歌圩——南宁国际民歌艺术节无疑是一场仪式活动。但与传统壮族歌圩不同的是,它是一个政府主导的仪式活动。通过仪式,突出了政府在场,强化了主流意识。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对自然的认识逐渐的加深,传统祭祀活动的神秘性逐渐淡化,功能也由娱神向娱人转变。因此,南宁民歌节的仪式与传统歌圩仪式相比有所改变。传统的歌圩祭祀仪式是由本族的巫师来主持完成的,他们代表的是有权利和文化的上层阶级。而南宁民歌节仪式则是由当地政府领导主持的。这些领导是政府的代言人。他们的在场即是代表了国家在场。这里仪式活动的崇高指向由神变成了国家。由政府决定民歌节的主题风格,当领导宣布开幕式晚会开始时,才会唱国歌,升国旗;唱会歌,升会旗。国歌和国旗就是国家在场的直接符号表征。在这里参与者的诉求对象不再是“神”而是这场宏大叙事的晚会背后所体现的国家意志。而民歌节的目的也不只是单纯的“娱人”功能,还添加了以政府为主导的促进广西区域经济发展的新目的。因此,南宁国际民歌艺术节是一个作为现代歌圩的仪式活动。
在这场有别于传统歌圩仪式的民歌节仪式上,舞台取代了祭台,并且舞台的装饰运用了大量的民族元素,凸显了民族特色的同时也带来了绚丽的舞台效果。在2009年开幕式上的铜鼓元素的应用就是壮族民族文化符号的重要表达。象征着壮族文化的铜鼓被用做舞台装饰、领导颁发给演员的礼物应用在开幕式上,既是表达了政府对民间文化的尊重,也是借铜鼓传达着广西铜鼓的文化。通过仪式,表达了民歌节传承壮族民族文化的信息,也让我们在聆听壮族民歌的同时,能够欣赏到壮族多彩的文化,更加立体、全面的展示出壮族的民族特色文化。仪式的参与者们或着具有民族特色的民族服装或着设计精美的舞台服装,装饰的意味十足,这让仪式活动变得更具美感。
民歌节上精心编选的节目,汇集了许多国内外的优秀歌唱家和经典民歌曲目,把民歌节打造成为一个真正的民歌汇集,多民族间共同交流的平台。在这里参与者与欣赏者靠音乐交流,通过音乐产生共鸣,不同的音乐呈现,获得的是同样的审美愉悦,“音乐的魅力,也许就在于它能够把人带入一种激情洋溢的境界。它把各种强烈的情绪,调和成为一种新的化合物,使人们再难从中区分出每一个具体的构成元素。各种情感,如欢悦的、爱慕的、憧憬的、欣慰的、放松的、紧张的,等等,好像都在这一境界中露过面,但又稍纵即逝,难以捕捉。这种杂而不乱、统中有分的混合局面正是音乐强大表现力的根源所在”[3]167。
三、结论
“‘歌圩’是壮族的一种传统文化形态,它是在一定的经济、政治、地缘、宗教、审美等诸因素和条件下,所形成的特定文化事象(包括婚姻文化),遂成为联结这一人们共同体的一种精神纽带。可以说,‘歌圩’活动,生动地体现了壮族人民的信仰观念,文化心理、审美观念和生活追求,从各个方面反映了壮族的传统文化特征和历史生活风貌。”[1]59壮族歌圩在壮族的发展过程中承担着多重作用。壮族歌圩即是壮族文化传承的主要场合,也是壮族祭祀活动的主要场合,更是壮族优秀艺术文化展演的重要场合。壮族歌圩是审美与仪式相结合的一场盛会,对壮族歌圩的审美仪式化与仪式审美化现象的研究与分析有助于我们更好地了解壮族歌圩,也为南宁这座“天下民歌眷恋”的城市提供着新的发展契机和生活方式。我们的生活需要审美仪式化带给我们庄重性和神圣性,需要仪式审美化带给我们美感与认同感,这将是南宁市民作为“审美的人”诗意栖居的重要途径。
[1]潘其旭.壮族歌圩研究[M].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91.
[2]范秀娟.黑衣壮民歌的审美人类学研究[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
[3]格罗塞.艺术的起源[M].北京:北京出版社,2012.
[4]E·霍布斯鲍姆,T·兰格.传统的发明[M].顾杭,庞冠群,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4.
[5]黄秉生.歌圩与壮族的审美意识[J].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6(1):55-60.
[6]彭兆荣.人类学仪式的理论与实践[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7.
[7]埃伦·迪萨纳亚克.审美的人[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
Zhuang Folk Song Festival:a Com bination of Aesthetics and Cerem ony
LIYing-chen
(Schoolof Liberal Arts,Guangxi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Nanning,Guangxi,530006 China)
Zhuang folk song can be seen everywhere in their daily life.Zhuang folk song varies quite much.Many classical songs spread from mouth to mouth for a hundred years.On one hand,that’s because Zhuang peop le love songs and like singing,on the other hand,there’s an inseparable connection with the Zhuang Folk Song Festival,a traditional activity for Zhuang minority.It is a combination of aesthetics and ceremony.As aesthetics,Zhuang Folk Song Festival makes people appreciate the sweet music and at the same time makes them obtains spiritual enjoyment and satisfaction.As a ceremony,it makes people obtain spiritual distillation and a sense of mys⁃tery atpermanent time and p laces.Zhuang Folk Song Festivalhas the nature both aesthetics and ceremony.Aesthetics and ceremony com⁃bines together in this activities and become two sides features.So it’s necessary to clarify aesthetic ritual and ritual aesthetics in a right way.
Zhuang Folk Song Festival;aesthetic ritual;ritualaesthetics
G02
A
2096-2126(2016)04-0013-05
2016-07-26
李英辰(1991—),女,河北迁安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民族美学。
(责任编辑:雷文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