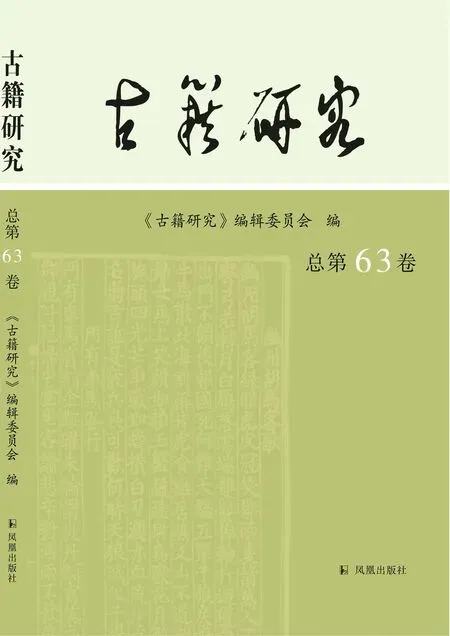《宋大诏令集》校理刍议
刘 磊
(作者单位:复旦大学中文系)
《宋大诏令集》校理刍议
刘 磊
绪 言
《宋大诏令集》一书的史料、文献价值早经学界公认。胡玉缙先生在《四库未收书目提要续编·史部·诏令奏议类》《宋大诏令集》提要(后称“胡氏《提要》”)中,评价说:“然北宋典制,所存实多,非特为制诰之渊海。其足据以参校《宋史》者不胜枚举,可与《唐大诏令集》并存矣。”中华书局点校本《宋大诏令集》(后称“点校本”)《校点说明》(后文单称《校点说明》,盖指此。)也说:“这本书对于研究北宋史事和订正补充的漏误,有很大参考价值。”并在举出了相应的例子后说:“诸如此类,俯拾皆是,不胜枚举。”*司义祖点校《宋大诏令集》《校点说明》,中华书局,1962年,第1页。王智勇先生在《〈宋大诏令集〉的价值及整理》(后称“王文”)一文中说:“《宋大诏令集》无疑是现存宋元以前诏令中最重要的一部诏令汇编,其价值在许多方面超过了宋人所编之《两汉诏令》和《唐大诏令集》。”*王智勇《〈宋大诏令集〉的价值及整理》,《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4期,第80页。特别是本书作为宋史研究的重要原始资料之一,很多诏令赖此而独存,即使是那些亦为宋代其他史籍所保存者,较之本书,其原始性、完整性亦往往而难及。《宋大诏令集》所存诏令提供了异文,所系时间往往提供了异说,则其有资于考证者甚夥。前揭王文对《宋大诏令集》的价值作了比较全面的论述,笔者则不复赘言。
在回顾《宋大诏令集》的研究情况之前,先引入一组概念,即文献研究的“体”与“用”。笼统地说“文献研究”实际上包含了文献的“体”、“用”两方面的研究。“体”是指以考证该文献的文献面貌为目的的研究;“用”指以该文献的材料为出发点,而以其他研究为目的的研究。这两个概念之所以为一组在于它们的始点都是同样的文献,而终点却不同。“体”的研究程度制约“用”。从理论上这样划分较为容易理解,但在实际处理上需要注意一些特殊情况。比如,以甲文献为材料讨论乙文献的研究,即是甲“用”的研究。但当我们换一个角度看未尝不是以乙文献的材料在进行甲“体”的研究。事实上在宋以降的文献研究中,时常会遇到这种情况。比如以《宋大诏令集》的材料校勘《续资治通鉴长编》,反过来看就是以《续资治通鉴长编》的相关材料在研究《宋大诏令集》*必须说明:二者的相关材料从史源学角度说必须是不同源的才绝对存在这种“体”“用”交互关系。也就是说甲、乙两材料具有不可比性时,交互关系是绝对的;如果确定同源(即可比)时,甲的优等材料具有绝对性,即出现只能以甲校勘乙这种情况时,“体”“用”是不能交互的。。明确了这组概念,便于下文继续探讨《宋大诏令集》的研究状况,容易看出现阶段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对理清研究思路有所裨益;同时也有利于笔者说明本文的研究主旨及划定研究范围。
由于各种原因,目前学术界对于《宋大诏令集》的研究尚处于初级阶段。主要表现在:研究成果零散、分散;相关文章数量较少,总体研究水平不高。这里先把笔者搜集到的相关研究成果做一分类评述。
第一,目前各种史料学、文献学著作,在对《宋大诏令集》的文献面貌进行描述时,基本材料不出乎《校点说明》的范围。我们必须承认,《校点说明》中的材料和观点是关于《宋大诏令集》的文献研究中最为关键的部分。但是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出,从一九六二年刊布点校本以来,在本书的文献学研究(体的研究中非常关键的部分)上并没有实质的进展,诸问题也没有得到深化。
第二,目前对《宋大诏令集》的文献价值进行整体评价的文章,只有顾吉辰先生《关于〈宋大诏令集〉》*顾吉辰《关于〈宋大诏令集〉》,《史学史研究》1990年第3期,第53-58页。(后称“顾文”)及王文两篇。王文正文分为三个部分,分别论述本书的史料价值、文献价值和整理三个问题。可清楚地看到,第一、二部分,特别是第一部分,是王文重点所在。由于上述第一点原因造成了这种情况:王文只能着力对《宋大诏令集》“用”的方面(即王文第一、二部分)加以论述;在“体”的方面(即王文第三部分)基本就属于上述第一点中描述的状况*王文第三部分讨论本书整理问题时,大部分笔墨用在论述辑佚问题上。这倒是超出《校点说明》范围之外的,然而笔者认为在本书“体”的研究方面,辑补(非“辑佚”)不是主要工作,说详后。。顾文亦分三部分:《宋大诏令集》的特点、史料文献价值、版本问题。严格地说顾文只有第三部分属于体的研究;第一部分只有最末一段可以看作对于《宋大诏令集》编辑思想的讨论,但篇幅太小,实际上也没能进入问题的核心,该节其余部分看似在讨论《宋大诏令集》的特点,实质上是对相关宋史问题的论述;第二部分论述史料价值,表面上似乎是《宋大诏令集》取材研究,实际上完全是推论性质,不具有可操作性,只是一种取材范围研究。第三部分作为“体”的研究与第一点所述状况相比,多出《宋史·李大性传》*《宋史》卷三九五。及《宋元学案补遗》附《李大性传》,目的是为李大异刊刻《宋大诏令集》提供旁证,实质性材料仍不出《校点说明》范围;最后讨论刻本不传的原因是此前尚未有人涉及的。

上文简要地回顾了《宋大诏令集》中华本刊布以来的研究历史,实际上也基本可以看作为《宋大诏令集》的研究历史。这一点也显示出学界对此问题的研究起步很晚,王树民先生在评述本书时说:“(本书)1962年中华书局……校订断句排印,从此开始为人们所见。”*王树民《史部要籍解题》,中华书局,1981年。实际上学界真正得以利用此书进行各项研究,正是在1962年中华书局刊布此书之后*邓广铭先生当年在研究《宋史·职官制》时,都没能参考本书,其难得可见一斑。。造成研究难以深入的原因比较复杂,后文有论。
在评述上述各家成果时,对“用”的方面着墨不多,这并不是说这个问题不重要。但如上所述,“体”的研究是核心问题,如果不讨论清楚,则在谈到“用”时首先就必须要面对怎么“用”,本书相关材料在使用过程中的原则是什么等一系列问题。后文还会详析此问题。
下面介绍一下本文的研究范围、目标与基本结构。本文所要考查的主要是《宋大诏令集》“体”方面的相关问题,主要讨论这样几个问题:一、本书的文献面貌,即编撰、流传及历代相关著录研究;二、本书的史料问题,主要是史料来源问题的讨论;三、校勘和辑补问题。这几个问题的讨论,目的是为了对日后进一步整理本书打下一定的基础。超出这个范围的问题暂不涉及。限于篇幅及本文性质,详尽地提出校勘细节是不可能的,因此例证是经选择的,以足以说明问题为准。正文的三节基本就是按照以上三个问题排序。
一
宋人著录中,可考的最早著录《宋大诏令集》的是赵希弁的《郡斋读书附志》和陈振孙的《直斋书录解题》。
《郡斋读书附志·子部·类书类》:
《皇朝大诏令》二百四十卷。右宋宣献公家所编纂也。皆中兴以前之典故。嘉定三年,李大异刻于建宁。
《直斋书录解题》卷五“诏令类”:
《本朝大诏令》二百四十卷。宝谟阁直学士,豫章李大异伯珍刻于建宁,云绍兴间宋宣献家子孙所编纂也,而不著其名。始自国初,迄于宣、政,分门别类,凡目至为详也。
两种著录都涉及了本书编纂、刊刻的情况,主要内容大致相同。由此可知《宋大诏令集》共二百四十卷,原题名无“集”字,宋人已不能确指其撰人。而嘉定三年李氏刻于建宁的本子当是最早的(恐亦是唯一的)刻本,约与其编成时间相距六十余年。
此外,亦见于王应麟《玉海》卷六四“艺文·诏令·诏策”著录,只未及刊刻情况:
《本朝大诏令》,二百四十卷。建隆至宣和。此集绍兴中出于宋绶之家。
《遂初堂书目》亦著录有《本朝大诏令》。
此刻本在元代是否流传已不可考知。案马端临《文献通考·经籍考·史二十一·起居注》著录“《本朝大诏令》二百四十卷”,《宋史·艺文志二·史类·故事类》著录“《宋朝大诏令》二百四十卷”,注云:“绍兴中,出于宋绶家。”*《宋史·艺文志八·集类·总集类》重出,且误题编者为“宋绶”。盖马氏所录袭自直斋,观其条下解题语明标“陈氏曰”而移录《直斋书录解题》一字不易可知。故知马氏恐非实见其书而据以著录。《宋史·艺文志》乃删并宋《国史·艺文志》而成,史有明文。然元代黄溍《日损斋笔记》论《湘山野录》所记李继迁事,云:“其子徳明既立,奉表纳款,乃以景徳三年封西平王。《大诏令》及今新修《宋史》所载并同。而《野录》无一与之合。继迁建节之制见于《实录》及《大诏令》者本云……”*亦见黄溍《文献集》卷七下。则黄氏必实见其书。而宋濂为其门人,序其书于至正甲午正月望日,则知元代士庶之家固有此书。
明代相关记载有:《文渊阁书目》卷四“《宋诏令》,一部二十四册,阙”;《秘阁书目·经济》“《宋诏令》,二十四”;《世善堂藏书目录》卷上“史部诏令类”“《宋大诏令》,二百四十卷”;《菉竹堂书目》卷二“经济”类“《宋诏令》,二十四册”*另外,还有《脉望馆书目》“黄字号”下的著录情况值得注意,在著录了“《皇明诏令》,十一本”之后,又著录了“《国朝大诏令》,三本”,紧接此后的是“《朝野杂记》,十本。”疑此所谓《国朝大诏令》或即是《宋大诏令集》。。这几家著录中,《菉竹堂书目》(粤雅堂丛书本)乃伪本,实即节抄《文渊阁书目》为之。《文渊阁书目》及《秘阁书目》的著录,说明明代内府藏有此书,但已残缺不全。《世善堂藏书目录》是私人藏书目录,是据实际藏书情况编撰,然而所涵信息太简,不能据以确定《宋大诏令集》有无全本存世。

到1962年,中华书局出版了以瞿本、读经庐本互校的校点排印本,是目前最为通行且最佳的本子;台湾鼎文书局据中华本翻印,编入《国学名著珍本汇刊·史料汇刊之一》。在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续修四库全书》中,以瞿本为底本影印收录了本书。
回顾了《宋大诏令集》历代流传及著录的情况之后,有这样一个问题值得提出:明代内府既藏有本书残本,那么在编修《永乐大典》(后称《大典》)时,是否收录了此书?*当然,在编修《永乐大典》时内府所藏是否即已残缺不得而知。

《宋大诏令集》自宋人始即不能确指其编者,今人或以为成于众手*祝尚书在《宋人总集叙录》中持此说,认为是宋绶子孙所编,但非仅一人。,或欲证确为宋绶后人,然皆无确证。史料放佚,欲考无由。本书前后无序例跋语,赵希弁、陈振孙皆云李大异所刻,然李氏亦无片言只字附于今本。故而,今日对于本书的编纂方法和过程,编辑主旨及体例诸问题无法得到确切地了解,对整理工作带来极大的困难。
二
《校点说明》推测《宋大诏令集》可能取材于北宋各朝颁行的各种诏令汇编、时政记、实录及私人编集的诏令集和官私编纂的典制书籍*顾吉辰认为本书必定取材于时政记、日历、起居注、实录、会要、各家别集、传状碑志等等(《关于〈宋大诏令集〉》)。笔者认为这一说法与《校点说明》是有差别的,它有逻辑问题:可能的来源比实际来源范围要大许多,后者的每个子项包含在前者的范围内,而前者的子项会超出后者的范围。因此,二者不具有子项目互相对应的能力,只能以整体为单位进行判断。同时,如果混淆二者还会造成泛化问题的不良后果。本书所载的诏令是特殊的,而并不能把宋代史料中的所有同一史实的诏书都同等看待。有关本书的论述中,很大一部分都有这样的问题。即记录与本书史实相同的其他宋代史料中的诏令,往往毫不甄别的被拿来用作校勘。。从理论上说,本书的编者不太可能跳过上述材料,而直接从原始的档案着手工作。且由于《宋大诏令集》的编成时间当在绍兴中,南渡以后基本也不具备让编者这样做的条件。因此,本书应该是通过搜集多种官私典籍中的诏令材料,编辑而成的*《校点说明》表示过《宋大诏令集》并非第一手史料的意见。第1页中有这样的表达:“(北宋各朝颁行的各种诏令汇编、时政记、实录及私人编集的诏令集和官私编纂的典制书籍)也该算是第一手的数据,《宋大诏令集》可能就是从上举这些书里取材的。”。
宋代文治极盛,无论官私都十分留意于文献的保存,而史馆尤为重视资料的保存,收藏丰富、系统,且加以修缮和刊布。通过宋人撰录的书目,如《郡斋读书志》《读书附志》《直斋书录解题》《玉海·艺文部》等,我们可以看到官私修纂的政书、典制书籍在南宋广泛流传,当时人获得史料的途径非常多。因此,南宋人对本书似乎并不太重视。陈振孙在评价《宋大诏令集》时,只说“分门别类,凡目至为详也”,不过是对其分类详明、便于检索表示赞许,而对其材料并不感到特殊。而周必大在《续中兴制草序》中,开篇有这样一段话:“嘉祐中,欧阳修建言:学士所作文书皆系朝廷大事,示于后世则为王者之谟训,藏之有司乃是本朝之故实。而景祐以后渐成(当是“或”之误)散失,于是以门类、年次编为卷帙,号《学士院草录》。中经兵火,文人故家仅传所谓《玉堂集》及《大诏令》者,其全书不可得而见矣。”*周必大《文忠集》卷二十。言语之间可见对本书不甚重视。当时人谈到本书史料,以为宝贵的,笔者只检得史绳祖《学斋占毕》卷三“夷齐泰伯封谥”“改室人为安人”两条,他以为两事“见于《国朝大诏令》中……而诸史往往不载”。
另一方面,在宋以后,宋代各种官私材料逐渐逸失,或宝于中秘,难于一见。通过上文对《宋大诏令集》流传情况的叙述,我们可以知道,以后即使是《宋大诏令集》也难得见。宋以后的有关材料,笔者只检得元代黄溍曾利用本书数据进行考证(见上文)的一例,且黄氏把本书与《实录》《宋史》并列,可见颇为重视。
这两方面造成了这样一种局面:宋人引用诏令时未必需要《宋大诏令集》,宋以后人又难于引用《宋大诏令集》。这就导致了在典籍中很少有明确表明引自本书的材料。在南宋诸典籍中,笔者止检得《山堂先生群书考索·后集》(后称《山堂后集》)(凡十四则)、《宋宰辅编年录》(凡四则)、《景定建康志》卷二(凡二十五则)中,有明确标明引自《大诏令》的诏书*这里判断他们所说的《大诏令》即是《宋大诏令集》,有两个理由:一、 见于著录的宋人所编诏令汇编,除《宋大诏令集》外未见再有以“大诏令”为名者;二、 如前文所考,清以前著录《宋大诏令集》者皆作“大诏令”,而无“集”字。。
《宋大诏令集》所收录诏令以完整性著称,而其他史料中所存者往往经过删削,并不完整。在研究本书中所使用的其他宋人典籍,如《续资治通鉴长编》《宋会要辑稿》《山堂后集》与《宋大诏令集》都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第一手数据,数据的不同来源造成文本的不同。由于本书所收全为诏令,故而史料的源头必定追溯到宋代官方编修。考察宋代(主要是北宋)修史的机构和相关程序,就诏令而言,最源头的编修性史料是起居注、时政记以及中央有关部门所保存的宣敕和诏书*曾巩《英宗实录院申请札子》,《曾巩集》卷三二。。历朝实录、会要、国史等又在这些源头性材料的基础上编修。而《续资治通鉴长编》《宋会要辑稿》《山堂后集》与《宋大诏令集》在这个体系中的地位又不尽相同,有时必须细致到“条”为单位,才能作出判断。当然,还有很多时候根本无法判断。
处在不同层级上的史料,往往差别极大,不加甄别地用这样的史料进行互校是错误的。我们试举一例来说明。
(甲)《宋大诏令集》卷一“帝统一·即位”(第1页)《大祖即位赦天下制》(原注:建隆元年正月乙巳):
门下:五运推移,上帝于焉睠命;三灵改卜,王者所以膺图。朕起自侧微,备尝艰险。当周邦草昧,从二帝以徂征;洎虞舜陟方,翊嗣君而篡位。但罄一心而事上,敢期百姓之与能?属以北敌侵疆,边民罹苦。朕长驱禁旅,往殄烽尘。旗鼓才出于国门,将校共推于天命。迫回京阙,欣戴眇躬。幼主以历数有归,寻行禅让。兆庶不可以无主,万机不可以旷时。勉徇群心,已登大宝。昔汤武革命,发大号以顺人;汉唐开基,因始封而建国。宜国号大宋。改周显德七年为建隆元年。乘时抚运,既协于讴谣;及物推恩,宜周于华夏,可大赦天下云云。于戏!革故鼎新,皇祚初膺于景命;变家为国,鸿恩宜被于寰区。更赖将相王公同心协力,共裨寡昧,以致升平。凡百军民,深体朕意!
(乙)《宋会要辑稿·礼》五四之一:
太祖建隆元年正月五日诏曰:五运推移,上帝于焉眷命;三灵改卜,王者所以膺图。朕早练龙韬,常提虎旅。当周邦末造,从二帝以征行;洎乔岳缠哀,翊嗣君而篡位,罄一心而事帝,谅四海以皆闻。一昨北虏侵疆,边民受弊。朕长驱禁旅,克日平戎。六师才发于近郊,万众喧哗而莫遏。拥回京阙,推戴眇躬。幼主以历数有归,寻行禅让。兆庶不可以无主,万几不可以暂停。勉徇群心,已登大宝。宜改显德七年为建隆元年改国号为大宋。
磊案:首先,(甲)所收者,自“勉徇群心,已登大宝”句以下,(乙)几乎完全没有。其次,仔细对比两者,其诏文结构大体相同,个别字词的细微不同尚不足以说明问题。但是,如(甲)的“朕起自侧微,备尝艰险”,在(乙)中成了“朕早练龙韬,常提虎旅”;(甲)的“洎虞舜陟方”,(乙)是“洎乔岳缠哀”;(甲)的“但罄一心而事上,敢期百姓之与能”,(乙)中作“罄一心而事帝,谅四海以皆闻”,等等整句不同,且诏文用骈体,而上下两句一并被调整整齐,这就只能解释为刻意改动。两者谁更原始尚无法判断,但可以断定,当时史官对所编收的诏书有所改动的*这里以改元诏为例,可以把改动者认定为当时的史官。这类诏书的整句更动不可能出于私人。笔者对比了《宋大诏令集》和《宋会要辑稿》所收的所有两见的改元诏,撇开其完整程度不论,从文理、遣词上看,还是《宋大诏令集》所收的改元诏更原始一些。。这种情况是普遍存在于《宋大诏令集》《宋会要辑稿》所收的所有两见的改元诏中的。
但是,如果不利用其他相关史料,似乎就只能考虑这样几类材料了:远在日本目前无法利用的皕宋楼本;前述共四十三则直接引用本书的史料。前者目前暂无可能,后者只占全书三千八百余则诏令的百分之一点一,显然都没有可行性。
如果研究一下诏书的基本结构,可以发现各类诏书的格式各有特色,但如果进行抽象的概括,可以看出:从结构上说,一般有两个部分组成(有时是一或三个):从性质上说,可以归纳成虚、实两个部分:实的部分是指诏令实际针对的问题;虚的部分,有时是援引前代例证,有时是纯粹文学性的引用经典,有时则是为了增强气势、表现其庄严与至高无上的权威,有时是纯粹格式的需要。
一般史籍在采用一份诏令时,对这两部分的态度是不同的。实的部分必须出现,虚的部分有时会不出现。实的部分作为史料的根本,也许会被删略,但主题内容一定会被保存;而虚的部分往往会被删削,甚至于完全删落。
因此,在考虑关于同一史实的几种诏令是否可以互校,即作为基本同一层级的材料对待时,重点在于考查它们是否被重新编排、改写过,而非是否被删节过。再举两组例证以明之:
第一组:
(甲)《宋会要辑稿·选举》三之二:

(乙)《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九,开宝元年三月庚寅:
因下诏曰:造士之选,匪树私恩;世禄之家,宜敦素业。如闻党与,颇容窃吹。文衡公器,岂宜斯滥!自今举人凡关食禄之家,委礼部具析以闻,当令覆试。(《太平治迹统类》卷二八文具略同,而“颇容窃吹”作“颇若切吹”,“岂宜斯滥”作“岂有私滥”,无“委礼部”三字。)
磊案:(乙)较(甲)为简,然如(乙)之“造士之选,匪树私恩”、“宜敦素业”及“如闻党与,颇容窃吹。文衡公器,岂宜斯滥”等句,显然对应(甲)文的“取士之道,贵实为先”“尤宜笃学”“如闻搢绅之内朋比相容,论才苟爽于无私,擢第即成于滥进”诸句。另外,《宋史·选举志一》(卷一五五)亦记此事,除年月不同外*《宋史·选举志一》载此诏在前的三年,中华书局校点本校记曰:“疑‘三’为‘六’之误。”,所录诏文节略作“食禄之家有登第者,礼部具姓名以闻,令覆试之”*考知《宋大诏令集》阙卷一七二“政事·科举一”的第四诏即是此诏,题作《举人父兄骨肉食禄者覆试诏》。。如果遇到这种改写的情况,就不宜把二者放在同一层级处理。
第二组:
(甲)《宋宰辅编年录》卷三,天禧三年六月甲午,王钦若罢:
制曰:承弼之臣,寄任尤重。所以运动枢机,感会于天人。镇静邦家,亲附于黎献。茍或显膺柄用,浸歴岁时。宜有均劳,式昭同徳。具官王钦若才术精敏,机虑研深。擢秀儒科,飞名俊域。蚤由谨简,历践荣途。顾待非常,宠灵殊特。枢庭任职,常参帷幄之谋;台席代工,遂委夑谐之寄。载司钧轴,能率典彝。言念勤庸,俾谐优逸。命傅储禁,聿隆表仪。勿忘嘉猷,往践厥位。
(乙)《宋大诏令集》卷六十六“宰相十六·罢免二”《王钦若罢相除太子太保归班制》(原注:天禧三年六月甲午):
门下:承弼之臣,寄任尤重。所以运动枢机,感会于天人。镇静邦家,亲附于黎献。茍或显膺柄用,浸历岁时。宜有均劳,式昭同徳。开府仪同三司、行尚书左仆射、兼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充景灵宫使、上柱国、太原郡开国公王钦若,才术精敏,机虑研深。擢秀儒科,飞名俊域。早由慎柬,历践荣途。顾待非常,宠灵殊等。枢庭任职,常参帷幄之谋;台席代工,遂委夑谐之寄。载司衡轴,能率典彝。言念勤庸,俾谐优逸。命傅储禁,聿隆表仪。无忘壮猷,往践厥位。可太子太保归班。
对比两处所载,最大的不同有二:王钦若的官衔是否列全;末句“可太子太保归班”的有无。实际上这两点都恰是虚的部分,(甲)重在理董宰辅沉浮之史,具列官衔徒费笔墨;此诏(乙)虽题为《王钦若罢相除太子太保归班制》,实质上重在“罢”,而非除虚衔“太子太保”。是以(甲)删去末一句。对比两者的其余内容,则结构句调皆基本相同,所以两者的互校是有价值的。如(乙)中“早由慎柬”一句,此诏乃天禧三年所颁,必不当有“慎”字,“柬”亦当是“简”之坏字。当据(甲)改正。从这组对比也可以直观地感觉到,《宋大诏令集》所收诏令的完整性确实较现存其他典籍为优。
这里,附带谈几个关于全书体例和特点的问题。
《宋大诏令集》所收诏令的完整性、原始性是人们常常提及的一大特色,从整体而论可以这样说。但并不能一概而论,举例来说:《宋大诏令集》卷六十六“宰相十六·罢免二”下收录了王钦若、寇准、丁谓、李迪等人的罢相诏书,基本都是具列官衔的。关于丁谓有前后两诏:《丁谓罢相受户部尚书归班制》(天禧四年十一月)及《丁谓罢相谪太子太保分司西京敕》(乾兴元年)。前一诏具列丁谓官衔,后者只云“具官丁谓”。而这些诏书收于《宋宰辅编年录》者一律书“具官某某”。
又,卷一一九“南郊二”《太平兴国九年南郊改雍熙元年赦天下制》,此诏存于今残本《太宗实录》卷三一太平兴国九年十一月丁卯下。两相对照,差异极大,史源上有差异。存于《太宗实录》者较近原貌,《宋大诏令集》存者文句经改写调整,所存者似重乎文辞。全部三百余字基本表述的是对于天的虔诚、对古圣贤的向往,在“可大赦天下,改太平兴国九年为雍熙元年”一句下以“云云”二字删落了相关内容。考之《太宗实录》“云云”所刊落者,是对各地罪犯的赦免规定,对各类有关税赋降以除放之恩,以及对文武官员赠官的具体规定等等约六百字的内容,而《宋大诏令集》的内容在《太宗实录》中只有不到一百字。由此可见,《宋大诏令集》的原始性与完整性是相对的,不宜一概而论。
《宋大诏令集》每类以时间编次诏书是它的又一特色,然亦有例外。如:

在卷一一九“典礼四·南郊二”及“政事门·伪国类上、中、下”三卷(卷二二五至二二七)也存在类似情况。卷一一九“典礼四·南郊二”中共十五通诏书,应分成两部分看,前八通与上一卷“南郊一”为一组,是建隆四年至宣和四年,都是关于祀于南郊的诏书*政和三年与宣和元年都是冬至日祀天圆坛。;后七通与后两卷半,即“南郊三、四、五”为一组,都是南郊赦天下制。*政和六年、宣和元年、四年冬祀赦天下制。而“伪国类”三卷中所收诏令实皆以国别,自为起讫。
以上诸门类较特殊,故特表出。从这里也可以看出,编者是十分细致的。虽然无由知其具体凡例,当研读本书时仍可感到编辑得有条不紊。
还有关于《宋大诏令集》性质的一个问题,即其编纂者是否希望把它编成一部总集。从总体上说,对于关乎北宋政治、社会、经济、文化诸方面问题的诏书,编者恐怕是希望网罗无遗的,可以考察到的很多没有收入本书的诏令,应当是编者没有条件收录,而非不愿收录。但是,可以观察到大量存于宋人别集的贺契丹国主生日、贺正旦的诏书没有收录在本书中;皇亲的大量加食邑、赠官类诏书也没有收录*《苏魏文公集》《苏轼文集》中就有大量这样的诏书。。笔者认为可能是由于内容程序化、缺乏实质内容而弃去不录*关于前者多少还有一些民族感情掺杂其中。。另外,陆德舆在《宋宰辅编年录序》中说:“《本朝大诏令》登载相麻不及执政之制。”确实在《宋大诏令集》中未见有关执政(即副相)的诏令。原因尚难推论,但是值得注意本书佚卷七一至九三,正在“宰相门”后,“将帅门”前。胡氏《提要》以为此所佚卷七一至九三为仍为“宰相门”。或者陆德舆时此诸卷已佚,而所载正是执政之制欤?
三
最后,简单地讨论校勘整理的相关问题。
中华本以瞿本、读经庐本互校,详录校记而慎于改动。这样谨慎的态度对待《宋大诏令集》是正确的,而且通过这样的整理,等于提供给读者两个珍贵的版本。这在当年此书初现于世时,是非常可取的。今天进一步校理此书,事实上大量工作是通过与各种史料比勘,而写出更加详尽的校记。真正可以勘改的地方是不多的。
中华本仍有一些显见的错误未予更正。如:
(1) 卷一七五“政事二十八·科举四”目录,第二诏题作《制奏名策问》,“制”显是“特”之误。
(2) 卷一七七“政事三十·按察”目录,有《令奉上宝册使玉旦所过察风俗诏》,观诏名不知何意。案目录,此诏上一诏为《令庆成使向敏中经田访里闾疾苦官吏否臧诏》,考《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七八,大中祥符九年(1016)五月“丁巳,命中书侍郎、兼刑部尚书、平章事向敏中为兖州景灵宫、太极观庆成使,所至仍察吏治民隐,听以便宜从事。”则知向敏中之诏即此日所下。而《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八九,天僖元年(1017)正月“丙寅,命宰相王旦为兖州太极观奉上册宝使,尚书右丞赵安仁副之。”(《宋史·本纪八·真宗三》略同)同卷,天僖元年二月“乙未,太极观奉上册宝使王旦言:‘缘路州县,调夫治道。臣以方春农事初起,悉已罢遣。’”则王旦事与向氏事性质相同,命使日亦当有诏,盖即是此处者。故“玉”必为“王”字之误。
关于避讳、避忌的相关问题似乎中华本的校点者也没有足够的注意。试举几例:
(1) 卷一“帝统一·即位”《大祖即位赦天下制》中“属以北敌侵疆”一句,《宋会要辑稿》作“一昨北虏侵疆”。“一昨”当是“昨以”之误,而“敌”字应是清钞本避忌所改,当以“虏”字为是。
(2) 卷二一三“备御上”《北敌议地界泛使再至咨访韩琦、富弼、文彦博、曾公亮诏》,中华本校记曰:“读(经庐)本‘北敌’作‘敌人’。”案《宋朝诸臣奏议》卷一三七引此诏作“北虏”,当据改。又,此诏文中有“敌情无厌”,案《宋诸臣奏议》所引“敌”作“虏”。亦当据改。又,“而辄构衅端”,案《宋诸臣奏议》所引“构”作“造”。《宋诸臣奏议》固避高宗讳,然《宋大诏令集》岂不避乎?疑此亦清人所改。
利用上文所举四十余则直接引用本书的材料进行校勘,也有一定的收获。这里仅举数例以见一斑:
(1) 卷一七八《诫约职田遵守元制诏》“辟污之始,夺农力以□求”,“求”上阙一字,《山堂后集》卷一七“官制门·职田类”(大中祥符九年七月丙寅)引作“多”;又,“敛熟之时,峻公□而奄取”,“公”下阙一字,《山堂后集》引作“文”;又,“无乡原赈济之恩”,“济”《山堂后集》引作“恤”;又,“遇灾沴且省之”,“且”《山堂后集》引作“即”。
(2) 同卷《罢职田诏》“敛而均之,孰曰不从”,“从”《山堂后集》卷一七“官制门·职田类”(天圣七年八月丁亥)引作“足”。

在利用其他史料时,首要问题还是要考察它与本书的史料是否处在同一层级上。这在上文已经论述过,也就不再举例了。
最后,关于辑补谈一点看法。在校勘时,由于可以比对本书与其他史料的关系,故尚可以利用其他材料来进行此工作。然而,辑补正是针对本书已佚的材料而言,故而比对工作也就无从谈起。所以笔者个人认为从根本上看,这种情况下的辑佚是行不通的。前文着重分析的史料层级性正说明了这个问题,在没有明确标注引自宋《大诏令》时,只能判断不同史料的基本事实是否一致,而无法判断史料层级关系,故而是否为原书所“佚”就无从论断。如果希望通过考证,把本书的基本收录情况搞清,也就是把各诏令的时代和所系史实调查清楚*这属于“用”的研究。,那么可以把其他记录相同史实的史料标注在本书每则诏令之后,以便考察研究。如,卷一七二“科举一”目录《颁〈考试进士新格〉诏》,通过时间编排顺寻的排列考证*参看本文第二节的相关讨论。,可知《宋会要辑稿·职官》一三之九所录真宗景德四年十月,对翰林学士晁逈上考试新格所下诏书为同一史实,可以补注在此条下*龚延明《〈宋大诏令集〉阙卷辑补点校(四篇)》此条下案曰:“查未获,俟考。”龚文可能没有考虑“科举门”的特殊编纂方式,所以辑补时时间编排上并不完全可靠。。采用这种方式,可以兼顾文献考据的严谨和史学考证对于材料的需求。
(作者单位:复旦大学中文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