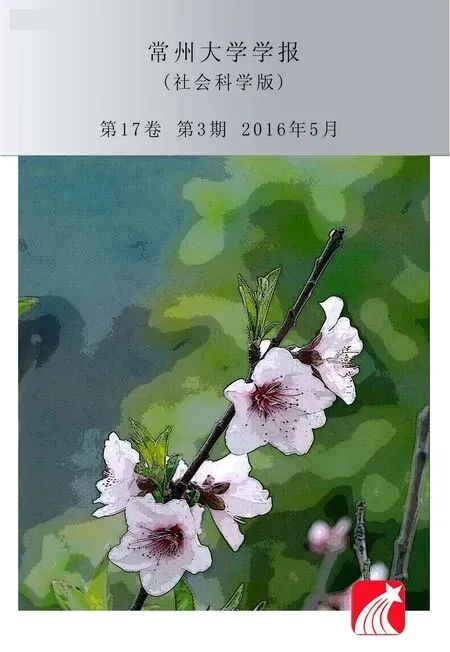从明清江南家族女性看女性文学创作的价值
娄欣星
从明清江南家族女性看女性文学创作的价值
娄欣星
摘要:中国古代女性文学的发展源远流长,特别是明清时期,女性文学呈现出家族化、群体化、地域化的发展特征。作为整个文学生态乃至文化格局中一部分,女性文学的思想与艺术价值只有置于文学生成的环境并与相关的文学活动联系起来考察才更有意义。女性文学创作由原本局限于家庭的“私领域”,扩展到与社会文化结合的“公领域”层面,不仅为家族女性提供了丰富的人生轨迹以及多重的社会形象,而且成为彰显地方文化实力的重要展现。从家族的角度来看,女性文人作为家族教育的关键人物,通过对儿女不同的教育内容和方式,为家族的发展壮大作出了突出贡献。
关键词:女性文学;创作环境;地方文化;家族教育
中国古代女性文学的创作与发展源远流长,最早可追溯到《诗经》《召南·行露》《卫风·硕人》《邶风·柏舟》《鄘风·载驰》等篇被视为是中国古代女性文学创作的滥觞。春秋战国时,亦有鲁漆室女《处女吟》、陶婴《黄鹄之歌》、赵简子夫人《河激之歌》等,以歌谣为主要形式的文学创作。汉魏时期是古代女性文学发展的第一个高潮,此时期涌现了卓文君、班婕妤、徐淑、蔡琰、谢道韫、左芬等较有影响的女文人,她们的创作反映了其时战乱频繁、民族文化冲突等特点。作为古代女性文学的第二个高潮,唐宋时期出现了薛涛、鱼玄机、李冶、李清照、朱淑真等一大批女性文学巨匠,她们的作品较多表现出唐宋文学婉约的一面。明清以后,女性文学创作更是走向新的里程碑。其时女性作家不仅人数众多,据胡文楷《历代妇女著作考》载,中国古代女作家近四千人,而明清时期高达三千七百余人,而且呈现出家族化、地域化、群体化的创作特征。她们从闺内吟咏走向闺外结社,建立了跨越家族、性别和地域的文学交游网络。在诗词文外,女性文人还参与了小说、戏剧和弹词的创作,为古代女性文学发展开辟了新的发展空间。那么,女性文学如此创作成绩的取得又产生了何等的价值和意义是本文讨论的重点。
一、女性文学创作环境的生成
中国古代女性文学创作的价值也许主要不在其本身的艺术贡献,而在于其作为整个文学生态乃至文化格局中的一部分,其思想与艺术价值只有置于文学生成的环境并与相关的文学活动联系起来考察才更有意义。古代男性与女性不同的社会地位和现实生活内容,决定了他们以不同的方式和条件实现自我价值。如果明清以前,大多数女性生活的全部在于家庭,那么明清时期女性的生活则是家庭与社会的融合。她们只有在与父母、丈夫、子女以及其他亲友所构成的环境和关系中,才能真正感受和实现生命的价值与意义。女性文学生成的环境,特别是对于明清家族女性来说,家族为其提供了多方面充足的教育资源,从家学的传承、家族氛围的熏陶、家族长辈的指导、家族资源的共享到家族成员的唱和,都成为家族女性成长与长才的必要条件。更重要的是,相比普通女性文人,明清时期的家族女性具有更多接触社会的机会,更多复杂的人生体验和经历。可以说这些因素在明清女性文学创作环境生成过程中对于女性文人的影响,才真正体现了女性文学的价值。
家族文化是中国人的一种集体无意识,每个人从出生到死亡都不可避免地要扮演不同的家庭角色,承担自己对于家庭的义务和责任。不管是谁,在思想、精神、行为上都会流露出较为明显的家族意识[1]。作为女儿,其接受的教育以知礼法、明妇道为主要内容,其目的正反映长辈对于女子的期望——尽守本分,做好贤妻良母。婚后,作为夫家的媳妇,侍奉公婆、操持家政是她们的主要任务。作为丈夫的妻子,理想的婚姻模式从“夫妇有别,三从四德”到“相敬如宾,举案齐眉”,再从“郎才女貌,比翼双飞”到“金童玉女,琴瑟合鸣”的逐渐演变[2],妻子成为丈夫的“闺中良伴”,与其联吟酬唱,成为社会普遍流传、令人称羡的“佳话”。“诚能于妇职余闲,流览坟素,讽习篇章,因益多识故典,大启性灵,则于治家相夫课子,皆非无助。”[3]文学才能成为女性相夫教子的必备条件。因此,对于女性来说,家族不仅是一种归属,更是一种责任。
在家族背景下培养的德行和才学,也影响了家族女性婚后的家庭观念、人生轨迹以及社会形象。可以说,明清时期的家族女性比以往各时代女性都拥有更多的人生状态和社会形象,在“内言不出,外言不入”[4]传统闺范受到极大冲击下的创作,更显女性文学特有的美学韵味和审美情趣。从空间角度而言,女性文人流动性的人生状态,不仅带来了创作上多样的审美价值,而且对于女性文学传播的意义更加明显。不管是随夫赴任的“从宦游”,还是以休闲娱乐为主的“赏心游”,亦或是以补贴家用为目的的“谋生游”,这三种“游”的方式都是以女性生活的具体环境和心理状态为基础,展现了女性文人借由文学吟咏而超越家庭空间限制的多种途径。藉由诗词等多种形式的文学创作了解、接触甚至融入家庭外的世界,自由真实地表达内心的情感变化,从前代展示的被儒家规范压迫和束缚的受难妇女形象跳脱出来,取而代之的是向社会展示自由真实的个体精神的女性现象。
“闺塾师”即是女性多重社会形象的重要体现之一。凭借文化资本谋生的生活方式是清初才女活动的一个新动向,也是清代女性文人的独特之处。归懋仪,字佩珊,号虞山女史,常熟人,幼承庭训,博通经史。自父亲归朝煦去世,公公李心耕解甲归田后,归懋仪迫于生计,“间为人延请教闺秀,皆井井有法度”,“俨然垂教,不为弟子而为师。且以女子教女子,授受亲而性情洽,其理更顺”[5]序。其诸多诗歌,多写于出行途中,如《吴江舟阻》《葑山道中呈简田先生》《过莫愁湖题莫愁小影次前人韵》《舟泊泖湖望月》《寓居葑溪邻家李花盛开感赋》《小寓吴门连朝阴雨占此自嘲》《泛舟秦淮》等,足迹遍及江浙一带。其《王渡阻风》一诗,云:
咫尺家山路渺茫,五年陈迹费思量。孤舟一夜潇潇雨,青镜明朝鬓有霜。[5]卷三:23
形象展示了归懋仪五年间离家独自远游,思念家乡的心境。其具有独立性与自由性的流动活动,得到了其时诸多文人的肯定。在拜入李廷敬、潘奕隽门下的同时,归懋仪亦与袁枚、陶澍、孙原湘、陈芝楣、吴蔚光、唐仲冕、张午桥、赵翼、陈文述、张掖垣、梁章钜、汪启淑等名臣巨卿多有唱和,一时诗名隆起。袁枚赞佩珊:“写就簪花妙格妍,咏来柳絮清才好。客春曾见衍波笺,诗比芙蓉出水鲜。”李廷敬更赞其“言情赋物妙传神,风雅天真本性情”,才名可与“左”、“鲍”齐名。
闺塾师,作为对“男主外、女主内”、“内言不出于阃”等传统格局的挑战,在最大程度上摆脱了传统对女性的束缚。虽然这些女性都是因生活所迫而走上闺塾师这一道路,但在这一流动性过程中建立起的文学交游网络和不断扩展的社会活动空间,为女性文人带来的收获更是异常丰硕,这不仅促进她们在文学上日益精进,而且更有利于她们声名以及作品的传播和接受,正所谓“信从者众,而诗词遂得以流传也”[5]序。
家族女性流动性的人生轨迹和多重身份的人生经验,在某种意义上,是一个对自我价值和意义重新建构的过程,具有塑造主体性认同的多种可能性。在移动过程中,性别界限也不断被解构和重构,不断塑造与改造自我形象。游历不只是单纯的观看活动,而是自我体验与环境互动的感受过程,在不同空间中,给予其更加广阔的视野,为其文学创作提供更多素材,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其文学社交网络的生成,加深自我主体意识的深度和广度,形成女性对自我的重新塑造。这些社会形象、人生状态以及文学发展轨迹的呈现,使得女性文学的创作呈现既丰富又具有时代特征的多重情态,由原本局限于家庭的“私领域”,扩展到与社会文化结合的“公领域”的层面,这正是女性文学创作的重要价值之一。
二、地方文学声誉与实力的展现
如果说对于一个家族而言,才女是名门望族不可或缺的文化资本。那么,对于一个地域来说,才女的意义与价值在于彰显地方文化实力。女性文学作为地方文学的重要一部分,是地方文学实力的重要展现。地方志也乐于通过记录女性的文学创作才能,反映地方文学的发展状况。可以说,明清时期女性文学的发展促使地方志逐渐重视女性文人及女性文学,而这一重视过程反过来又进一步肯定了女性文人的创作,激发更多女性投入到文学创作的队伍中。
其一,明清时期江南地区的地方志在凡例或序言中言及设立列女传的标准和寓意时,都肯定女性“内治而家国天下可理”的地位与作用,并不约而同地将“通经术”、“著词采”等特点作为女性入选的标准。如《乾隆长洲县志·列女》云:
范蔚宗后,《汉书》搜次才行尤高者,为列女传。不专一操,以为王政必自内始,盖内治而家国天下可理。闺门之中,其最先也。今通经术而泽风雅者,或间有其人,而明大义植伦常,足与秋霜比质者,虽穷檐部屋不可胜数于此,见教化之入,入者深也,区明风烈,昭我管彤志列女。[6]
将“通经术而泽风雅”者与“明大义植伦常”者作为彰显长洲一地彤管之盛的重要代表。
此外,《元和县志·列女》更明确指出列女“不止以节见”的观点,“凡瑀琚珩璜之节,威仪动作之度,与夫经术图史文藻吟咏之娴,并足采录。”[7]只有将这些女性汇而辑之,才足以彰其教化之盛,表其风土之厚。
这种记录标准的变化,《民国德清县新志》从幸与不幸的角度看待,言历朝列女传多传其不幸而哀之,而今多传其幸以增生趣,如“贵盛之有沈妙容等,贤孝之有俞姚氏等,才藻之有管仲姬等,瑞寿之有虞章氏等”,将苦节纯烈者与文情诗思者并足记录,以“列女志”作为“采藻与壶范亦均可得而传”的地方女性人物集;在“男女匹敌不敢或遗之意”[8]的基础上,重视女性道德伦常及文学才能的记载。可见地方志编纂者对于女性文人的重视,以及展现地方文化实力的自豪感,这些都为地方文化的发展大大加分。
其二,从《列女志》对于女性的分类来看,入选女性不再只是传统闺范中的节、烈、贞、孝等,“才媛”(闺秀、秀淑)类女性被记载入其中。在明清环太湖流域的地方志中,专门将地方才媛记录到《列女志》中的有《光绪宜兴荆溪县新志》《光绪宜荆续志》《光绪常昭合志稿》《宣统太仓州镇洋县志》《光绪嘉兴府志》《光绪嘉兴县志》《民国海宁州志稿》《光绪重修嘉善县志》《光绪桐乡县志》《光绪石门县志》《同治湖州府志》《民国德清县新志》等,如:
《同治湖州府志·列女》:节孝、贞烈、闺秀;
《光绪武阳县志·列女》:贤孝、贞孝、节孝、节烈、才媛;
《光绪嘉兴县志·列女》:贞孝、义烈、寿母、贤媛、才媛、节妇;
《光绪石门县志·列女》:节妇、烈妇、孝妇、贞女、烈女、孝女、贤母、寿母、才媛;
《民国镇洋县志·列女》:节烈、贞孝、贤能、秀淑。
而在《艺文志》或《经籍志》(《书目》)中收录才媛作品的地方志有《光绪吴江县续志》《光绪无锡金匮县志》《光绪武进阳湖县志》《光绪嘉兴府志》《湖州府志》《光绪石门县志》《同治长兴县志》等。如《乾隆吴江县志·书目》收录7部女性作品,其中家族女性作品4部:沈宪英《惠思遗稿》一卷、沈华鬘《端容遗稿》一卷、沈蕙端《幽芳遗稿》一卷、叶小纨《存馀草》等。《同治湖州府志·艺文略》著录77部女性作品,其中家族女性作品7部:孔继孟《桂窗小草》,孔素瑛《飞霞阁诗集》《兰齐题画诗跋》、周映清《梅笑集》、叶令仪《花南吟谢遗草》、李含章《蘩香诗草》、陈长生《绘声阁集》。《光绪常昭合志稿·艺文》“闺秀遗著”一门,录女性作品42部,其中家族女性作品14部:王慧《凝翠楼集》四卷,苏瑗《漱琼集》,苏琇《河梁集》,归懋仪《绣馀诗草》,赵同曜《月桂轩诗稿》一卷,鲍印《藏翰轩诗稿》四卷、《词》一卷,邵广仁《吟香阁诗集》,屈静堃《留余书屋诗文集》,屈秉筠《韫玉楼集》,屈凝《心闲馆小草》,屈敏《松风阁小草》,王谢《韵兰室遗稿》一卷,邵琬章《话月楼遗稿》等别集。《光绪武进阳湖县志·艺文》“闺秀类”著录女性作品56部,其中家族女性作品20部:庄蕡孙《玉照堂集句》、《悟香阁草》,庄德芬《晚翠轩遗稿》,钱孟钿《纫秋诗草》《浣青诗草》《鸣秋合籁集》、虞友兰《问月楼草》、庄素馨《蒙楚阁草》、汤瑶卿《蓬室偶吟》、钱诜宜《五真阁遗稿》、庄玉嘉《联香集》《翠香吟草》、庄玉芝《兰荪阁遗草》、庄盘珠《莲佩诗草》《紫薇轩词》一卷、张珊英《纬青诗稿》、恽珠《红香馆诗草》、钱湘《绿梦轩乐府》、张纶英《绿槐书屋诗集》三卷,庄宝珠《翠环琼仙诗钞》二卷。
可见地方志对于地方女性文人,尤其是出身于世家大族的才媛的重视,这也体现了明清时期女性文学发展家族化、群体化的独特性。这一独特性也促使编纂者在记载女性文学才能的同时,亦能从多方面考证其文学生活内容、文学创作特点等。如:
张氏藻,字于湘,青浦人。诗传家学,少与兄凤孙唱和,适毕镛为继妻,著有《培元堂集》。[9]
将继承家学传统及少时多与兄长唱和交流的生活内容作为张藻文学创作的重要内容或者影响张藻文学创作才能的重要原因载入地方志中。其时《列女志》的记载已不再局限于女性生平事迹以及创作特点的简单罗列,而是关注其文学源流的传承关系、文学交游网络的生成状况等内容。如:
査惜,字淑英,编修慎行妹,幼聪慧,年十五归马思赞。家有《道古楼藏书》最富,纵观唐宋以来诗文。深闺唱和以清雅为宗,有《吟香集》六卷,自为序。[10]
作为査氏家族的著名女性文人,査惜借助家族丰富的藏书资源——《道古楼藏书》,得以观览唐宋以来的诗文典籍。在深闺唱和这一交流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以清雅为宗的创作特点。短短几句亦可知査氏家族提供的成长环境对其家族女性文人创作的影响。
其三,以家族、社团为单位,明清时期的地方史特别重视女性文人群体的记载。成员间艺术才能的丰富性和创作特点的差异性是编纂者记载和评价的重要内容。如阳湖张氏,张琦四女张□英,“学诗以黄处为宗,多和平温定之旨”;张珊英,“幼喜为诗,长益工行,间有奇气,感慨悱恻”;张纶英,善书,“诗宗魏晋,不屑为绮丽”;张纨英,“尤工古文篆法”;张曜孙妻包孟缇,亦“能书工书”;张纨英女王采蘩,“能诗文,工隶书,……又善丹青”[11]。太仓王氏,王发祥妻吴氏“博览典籍,尤悉史事得失,能诗善琴”;长女王慧“工诗,……沈德潜谓其诗‘清疏朗洁,品最上’”;次女王莹,“诗清秀”;季女王芳,“才与两姊均,诗不多作,作必矜贵可传。考订声韵,尤精。”[12]家族女性群体成员间各异的艺术才能和创作特点透露出家族开放的教育和创作环境对于女性文学发展产生的重要影响,显示出家族文学,乃至地方文学的兴盛景象。
在这些女性群体中,成员间不仅存在姻娅、血缘关系,更有师承、社团等多维度的联系。以乾隆之际的清溪诗社为例:
震泽诸生任兆麟妻张允滋,字滋兰,号清溪,吴县人。幼受业徐香溪女史之门,工诗文,兼写墨梅。比归任后,偕隐林屋山中,琴瑟唱和,诗学益进。著有《潮生阁集》。继与同里张紫蘩芬、陆素窗暎、李婉兮媺、席兰枝蕙文、朱翠娟宗淑、江碧沈珠、沈蕙孙纕、尤寄湘澹然、沈皓如寄玉,结清溪吟社,号吴中十子。媲美西泠。[13]
诗社成员以张允滋为首,众人多为江苏吴县人。在同一地域中形成的社团关系,又是建立在姻娅、血缘关系基础之上的。张允滋,与张芬为姊妹关系,与朱宗淑为姨侄关系;尤澹仙与沈持玉为表姊妹关系;李媺与陆瑛为姻亲关系。成员之间复杂的联系为成员之间的相互影响以及社团活动的开展提供了良好的环境。作为诗社活动的组织者,张允滋对诗社成员的影响可想而知。如沈纕曾自叙云:“余初不喜填词,相馈之余,停针之暇,惟斤斤于无言字中。……后与清溪张姊交,观其填词,能移我情。岁戊申,始研心音律。自唐迄宋,诸名家词,靡不手自钞录,兴之所之,恒彻夜忘寝。”[14]在沈纕从“主中馈”到精研音律的转变过程中,张允滋发挥了引导、鼓励其创作的积极作用。而任兆麟作为清溪诗社雅集活动的评定者*如《翡翠林闺秀雅集》中,收录诗社成员创作的《白莲花赋》、诗、四六文词,由任兆麟评定其中“超取”与“优取”者。,对于诗社成员而言,不仅存在鼓励、提拔、赞赏之意,更具有些许师承关系的意味。
这些例子都说明,妇德与才情兼善的女性成为明清江南地方志着力建构的典范。这一变化表现出官方对于女性文人及其文学的认可,甚至将女性文学纳入到地方主义的竞争体系中:在注重女性文人创作特点的同时,也极力从多方面考证源流;通过考察女性文人的交游网络,建构出属于其时、其地女性文学的发展状况。这也从另一方面昭示了女性文学创作的价值与意义。
三、家庭教育的重要载体和内容
女性文学创作不仅是家族重要的文化资本,地方文化实力的重要展现,更是家族教育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家族后代的培养,事关家族的兴衰荣辱。“母教善者,其子之成立也易。不善者,其子之成立也难”[15]。母亲在家族教育中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在传统德行的基础上,诗文与经史兼备的“才”逐渐成为女性课子诲女的必备条件。女性的文学创作自然成为其教育儿女的必要手段和方式。
近世学者推论人种进化之基,谓基于女教,此非譽言也。考诸古昔,上而宫闱,若太姒,下二闾里,若孟母,其诞育圣贤,皆自胎教始见之,传记者详矣。至史书所述前哲之得力于母教者,殆不可胜数。盖受教于孩提时深入脑髓,故非父师之训可得而并论也。吾邑自宋元以来,多大人物,则贤母宜其夥矣。顾自来贤母多崇质朴,往往守内言不出于阃之戒,不欲其子孙表暴之于外,其经士大夫之仰慕,阃德勒之碑表,登之传记者,或什不得二三焉。[16]
作为家族文学重要的传承者,女性文人成为家族教育的关键。其文学创作作为母教的重要方式之一,融入了她们对于子女不同的教育内容和方式。明清时期家族女性的母教,在女性文学发展的影响下,产生了课训诗这一新的诗歌题材,在家庭教育中发挥了无可取代的关键作用。此类题材从顾若璞发端,到康熙时期女诗人达到高峰[17]。作为清代女性文学的重要一部分,课训诗根据对象的不同,又可分为课子诗与课女诗两种。
在课子诗中,母亲的勉励与督促是此类诗作的重点。
青云与泥涂,勤苦同一辙。志学抱坚心,宁为境所易。诵读知其人,尚友若咫尺。流光驹过隙,分阴抵拱璧。毋令寡母心,戚戚忧乾没。[18]
处世毋忘修德业,立身慎莫坠家声。[19]
立脚须端本,姱脩莫近誉。传家惟孝友,报国在诗书。世路崎岖险,投桃慎择交。薰蕕应早辨,玉石莫相淆。[20]3
在读书、立身、择友、报国等方面为儿子的人生指明方向。同时也对儿子的将来寄予厚望。“期尔早飞腾,剑跃白虹气。精心蟫简攻,锐志龙门诣”[20]22;“国恩诗礼绵家学,忠孝期无负”[20]21;“传经家世扶阳重,厚望须教慰夜泉”[21]4。继承发扬家学传统,以告慰祖先,不负家人期望。
母亲的劝诫更是在子孙仕宦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太仓张藻对于儿子毕沅的教育可谓影响深远。张藻,幼承母顾英之教,富于文采,被誉为“闺秀之能诗词而学术渊纯者,当以太仓张藻为第一”。毕沅六岁时,张藻就亲自教读《诗经》《离骚》。张藻虽在闺阁,但也通达政体。毕沅为官途中,张藻做《诫子诗》,劝诫毕沅不仅要修身:“勿胶柱纠缠,勿模棱附丽。端己励清操,俭德风下位。大法则小廉,积诚以去伪。”更要因时制宜、有所作为:“润泽因时宜,樽节善调理。古人树声名,根柢性情地。一一践履真,实心见实事。”这样才可以“上酬高厚恩,下为家门庇”。其教诲可谓训词深厚,不减颜家庭诰。高宗更赐御书“经训克家”[22]四字以褒之。
在儿子读书不顺或仕途失意时,母亲还承担起劝慰、安抚的责任。这类课子诗中,表达了女性文人对于读书仕宦的诸多见解。如刘汝藻《儿绍基报罢,抑郁不乐,作歌解之,并勗其志》云:
读书之乐四时宜,管生穿榻忘饥疲。鹏抟扶摇九万里,六月暂息何嫌迟。攻书如种树,叶茂根先固。课程如灌园,膏沃花自繁。爱博不专徒犯忌,束书不读更自弃。舒啸应成鸾凤吟,题诗且作蝇头字。勿灰凌云志,勉尔倾葵心。成连操伯牙琴,海上一曲清尘襟。高山流水足,千古子期尚在,莫谓当代无知音。[20]17
读书如种树,必先固其根本,才能枝繁叶茂。过程虽然艰辛,但知音尚在,切勿灰心自弃。句句透露出母亲对于儿子规劝和关爱之情。李含章《楏棻二儿春馆下第慰之以诗》:“四海几人云得路,诸生多半壑潜鱼。当年蓬矢桑弧意,岂为科名始读书?”[21]28更是看穿了科举仕宦之路的真谛,得出勿为科名始读书的高超见地。
在文学家族中,男性和女性都有得到教育的机会。男子的教育侧重于经史典籍,而女子的教育则侧重伦理教化,具体表现为妇德、妇言、妇容、妇功等闺范教育,规范女子为人女、为人妻、为人母、为人媳的角色职责,接受如何处理家政的训练,并负责维系家族内良好的人际互动。同时,为了适应家族联姻对于女子文艺才能的需求,接受诗文方面的教育成为世家大族女子的必然趋势。以湖州叶氏家族的周映清为例,其《令阿缃入学》云:
从来娇绕膝,今已略知闻。恩义难相掩,贤愚自此分。枣梨余自具,经传汝宜勤。未暮休归舍,童心惧放纷。
低鬟怜阿姊,与汝亦齐肩。且令抛金线,相随理旧编。双行知宛转,坐咏爱清圆。试看俱成诵,今朝若个先。[23]26
此诗主题是对于亲子课读的描写,充满了母亲的怜爱之情。第一首是母亲教诲入学的儿子切勿放逸。第二首言及与姊姊亦与儿子一起读书。两首诗见出了母亲对于儿女不同的教育期待。对于女儿,言其本分为女红针线,由于陪伴弟弟读书,才得以暂时“抛金线”。但这并不代表周映清不重视或反对培养女子的诗文创作才能。其《娇女诗》作为一首课女诗,明确提出了其对于女儿文学才能的评价和期望,诗云:
我家娇女齐蕙芬,媚如春月回微光。终朝据案弄卷轴,清吟婉转调莺簧。今年十二解声韵,七字五字吟琅琅。亦知弱腕乏警策,颇有慧语馀清锵。闺门尚德不尚艺,四诫初不夸词章。岂知陶冶有妙用,能使冰炭消中肠。温柔敦厚本诗教,幽闲贞静传闺房。但令至性得浚发,勿务浮艳鸣荒唐。我昔南楼强解事,力穷汉魏兼齐梁。即今所得尚无几,颇觉辛苦难为偿。怜汝娇憨亦不恶,岂必刘鲍争低昂。作诗因汝感畴昔,只恐明镜生秋霜。[23]10
她指出传统妇德中,与诗文词章的艺相比,道德的规范是更为重要的。所以诗作在夸耀女儿读书写作上聪慧用功,但倍感欣慰之余,也不免担心。虽然闺门尚德不尚艺,但周映清仍提出诗有陶冶性情之功用,且诗教之温柔敦厚,正好与妇德之幽闲贞静相通。在妇德与诗教之间,找到了一个合理的平衡点,即“但令至性得浚发,勿务浮艳鸣荒唐”。由此可见,周映清无疑是“才德相成”的支持者,运用裨益教化的观点,为自己、女儿辩护。但纵使支持,也不能忽视现实的力量,诸多代代相传的规矩准绳局限了女性才华的发展空间,诗歌末四句亦透露出了周映清的无奈和感伤。
对于家族女性的教育,吴江沈氏家族的沈宜修可谓其中代表。沈宜修以课儿女继承家学为己任,常与三女吟咏唱和,时人赞誉称“居恒赓和篇章,闺范顿成学圃”。沈宜修《夏初教女学绣有感》有云:
忆昔十三余,倚床初学绣.不解春恼人,惟谱花含范。十五弄琼箫,柳絮吹粘袖。竿伴试秋千,芳草花阴逗。十六画峨眉,娥眉春欲瘦。春风二十年,脉脉空长昼。流光几度新,晓梦还如旧。落尽蔷薇花,正是愁时候。[24]
此诗是沈宜修教导女儿时回忆起自己的成长历程时所作,十三岁学刺绣,十五岁学箫竹,十六岁已能画眉。结合《鹂吹集》中其他作品的记载,可看出沈宜修对女儿的教育基本遵循以下课程:2-4岁,诵诗,包括《诗经》《楚辞》、白居易《琵琶行》、《长恨歌》等;4-11岁,认字、阅读、造句;11-12岁,作诗、作文、学刺绣;13-15岁,学琴、棋、书、画。由此可知沈宜修非常重视女儿文学创作及其他艺术才能的培养,与以往只注重女子阅读女诫闺训类作品的家庭教育有很大进步。而这一进步正是通过女性文人的文学创作反映出来的:一方面,女性文人的文学创作作为家族教育的一部分,是教育子女的重要载体;另一方面,从这些记录家族教育的文学创作中,我们也可以总结出其时家族教育的内容、形式及其他相关特征等。
尽管“课子”与“课女”两者在教育内容及重视程度上有所不同,但是作为母亲,其诗文经史兼备的知识结构与德行是必须的,“女教莫诗为近,才也而德即寓焉矣”[3]。作为女性文学的一部分,女性文人将自已的所学运用到教育子女的过程中,成为影响儿女学识与前途的关键人物,并进一步维系着家族文脉的兴衰,往往比男性发挥了更加切实的作用,彰显了女性在家族中传承家学、培育后代的重要地位,体现了女性文学的实际价值。
对于家族女性来说,她们所发挥的作用已远远超越传统意义上的相夫教子、“主中馈”、男性的附庸,而是成为家族中、地域中具有一定影响力的独立个体。女性文人创作环境的生成,为女性文学的发展提供了更加宽松的环境、坚实的基础以及强大的后盾。在提高女性文学地位的同时,也彰显了地方文化的强大实力,才得以在地方志中争得一席之地。世家大族中的女性文人更将其文学创作作为家庭教育的一部分,用于激励、劝导儿女的成长,在家族文学的传承、家族势力的壮大上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女性文学取得的成绩,也从某种意义上激励了更多女性投入到文学创作中,在互相砥砺切磋中,促进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和自我价值的实现。这些正是女性文学,更准确的说是明清家族女性文学给自身、家族、地域以及整个社会带来的重要价值和意义。
参考文献:
[1]洪水铿.海宁査氏家族文化研究[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6:135.
[2]李贵连.试论明清女性文学创作主体的家族化及其根本原因[J].内蒙古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4):88-93.
[3]陈兆伦.紫竹山房文集[M]//清代诗文集汇编:第293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81.
[4]礼记·内则第十二[M].郑玄,注.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16.
[5]归懋仪.绣馀续草[M].清道光十二年刊本.
[6]李光祚,顾诒禄,纂修.乾隆长洲县志·列女[M].乾隆十八年刻本.
[7]许治,沈德潜,顾诒禄,纂修.乾隆元和县志·列女[M].乾隆二十六年刻本.
[8]吴翯皋,王任化,程森,纂修.民国德清县新志·人物志三[M].民国二十一年铅印本.
[9]王祖畬,纂修.民国镇洋县志·人物二·秀淑[M].民国七年刻本.
[10]李圭,许传霈,纂修.民国海宁州志稿[M].民国十一年铅印本.
[11]庄毓鋐,陆鼎翰,纂修.光绪武阳志余·才媛[M].光绪十四年活字本.
[12]王祖畲,纂修.宣统太仓州镇洋县志·人物八·秀淑[M].民国八年刻本.
[13]冯桂芬,纂修.同治苏州府志[M].光绪九年刻本.
[14]沈纕.翡翠楼·自叙[M]//吴中十子诗钞,清乾隆五十四年刻本.
[15]梁启超.变法通议·论女学[M]//梁启超全集:第一册,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31.
[16]郑锺洋,张瀛,庞鸿文,纂修.光绪常昭合志稿·列女志一·叙[M].光绪三十年活字本.
[17]吴琳.闺阁内部的文学空间——论清代康熙时期的女性诗歌[J].中国石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5):76-80.
[18]庄德芬.晚翠轩遗稿·杂诗示儿[M].清嘉庆刻本.
[19]恽珠.红香馆诗草·喜大儿麟庆连捷南宫诗以勖之[M]//清代诗文集汇编:第499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74.
[20]刘汝藻.筠心阁集[M].清咸丰六年刻本.
[21]李含章.蘩香诗草[M]//织云楼诗合刻,清乾隆刻本.
[22]徐珂.清稗类钞·教育类[M].北京:中华书局,1984:580-581.
[23]周映清.梅笑集[M]//织云楼诗合刻,清乾隆刻本.
[24]沈宜修.鹂吹集[M]//午梦堂集,北京:中华书局,1998:2.
Female Literary Creation Environment and its Value of JiangnanFamily Women in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Lou Xinxing
Abstract:The development of ancient Chinese female literature has a long history,especially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Female literature shows family-oriented,community-based,regional-oriented development feature.Only placed under literature environment and linked with relevant activities can ideological and artistic value of female literature have more meanings.The extersion of female literary creation from the original limited family “private domain” to the social and cultural combination of “public domain” level not only provides a wealth of life path and multiple social images of women,but also becomes an important show to highlight the strength of the local culture.From the family’s point of view,as key figures in family education,woman writers made outstanding contributions for the development and expansion of the family,through different educational content and methods to the children.
Key words:female literature;authoring environment;local culture;family education
作者简介:娄欣星,苏州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
中图分类号:I209.9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2095-042X.2016.03.014
(收稿日期:2016-02-20;责任编辑:朱世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