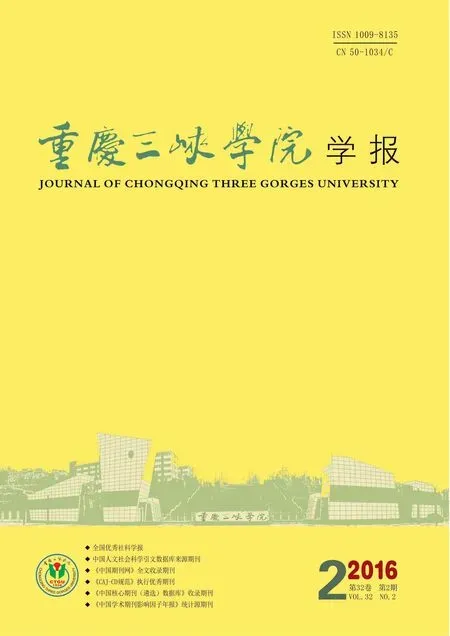哈尼村寨节日仪式比较研究
李银兵 方 露
哈尼村寨节日仪式比较研究
李银兵1方 露2
(1.贵州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贵州贵阳 580001)(2.玉溪师范学院政法学院,云南玉溪 653100)
通过对两个哈尼族村寨苦扎扎节日仪式表征出来的不同性状的调查研究,让我们真切地感受到现代化对于传统节日的冲击,引发了我们对于传统节日文化发展的无限思索。
苦扎扎;哈尼族;仪式;比较
“区域社会是整体中国的一部分,是整体中国的细胞形式,解剖某一个具有典型意义的区域社会,本身就有助于我们深化对整体中国的认识。”[1]总序1地处哀牢山腹地、红河谷畔的两个哈尼族村寨,用它们特有的方式诠释了国家力量及时代内涵在边疆民族地区的映照及反射,给人们认识当地“地方性知识”提供了诸多启示。基于此,本文从哈尼族重要节日苦扎扎节入手,通过对两个村寨苦扎扎节日仪式的描述,进而发掘两个村寨苦扎扎节仪式差异,探究其节日仪式差异产生的缘由,以就教于方家。
一、个案背景和节日概况
羊街乡位于北纬23°22′-23°31′、东经101°57′-102°08′之间,是云南省玉溪市元江哈尼族彝族傣族自治县东南部的一个呈菊叶状的乡镇,地处元江西南岸哀牢山余脉峨(莫朗)山、观音山山区,东以尼朗河、南以那诺乡分界,西面濒临清水河,西北与鸡街梁子和因远镇浦贵村接壤,东面和东北面是直下山麓,与澧江镇大水平毗邻。南北最宽13公里,东西最长17公里,总面积202.05公里。
垤霞村是羊街乡的一个村民委员会,属于边远山区,各种基础设施、农业技术等都相对落后于其他村,集体经济也不发达。尼戈上寨是垤霞村委会下辖的一个小山寨,距离元江县城大约60公里,离羊街乡政府驻地11公里,是高寒、边远山区里的一个小村庄。尼戈上寨的地理位置要经过北回归线,平均海拔为1 750米,年平均气温是21.5 ℃,为亚热带温带立体气候。尼戈上寨所处地形地貌复杂,多为山地地形,自然灾害频繁,多以泥石流为主。该村有农户70户,共288人,以哈尼族为主(只有少数几人与外族通婚),有将近100名年轻人外出务工,留守在家的大多是体弱多病的老人和小孩,劳动力明显不足,且村民文化程度比较低,大多以文盲、小学和中学为主。产业方面以农业为主,主要种植水稻、烤烟、玉米、蔬菜类、核桃树、桃树等农作物和经济果林,其中水稻是主要的农作物。
西龙小组是羊街乡坝木村民委员会的一个小村寨,地处观音山山区,属于高寒、边远山区。西龙小组距离羊街乡政府所在地20公里,距离坝木村村委会所在地2公里,离元江县政府驻地40公里。该小组处于半山坡,地形地貌复杂,高低不平,土地贫瘠。西龙小组同样为亚热带温带立体气候,自然灾害频繁,泥石流、山体滑坡和霜冻灾害严重。它的平均海拔为1 600米,全年最高温不超过30 ℃,最低温到达零下5~6 ℃。该社管辖农户70多户,人口310人,普遍受教育程度不高,大多数为文盲,少数几个人上过小学和初中,现有在校大学生2人。西龙小组的民族是以哈尼族为主,原来只是本民族内部通婚,现在与其他民族通婚的人越来越多。产业方面以农业为主,主要种植水稻、烤烟、玉米、蔬菜类、核桃树、桃树等农作物和经济果林。
在所有的哈尼族支系中,大多数节日都与汉族相同,只有糯美、糯比支系的“十月年”、“黄饭节”、“苦扎扎节”、“新谷节”及多塔支系的“春节”,梭比支系的“三月节”等才独具民族特色。哈尼族苦扎扎节的时间是在公历的六月间,因而才叫六月节,它是哈尼族在一年中仅仅次于“十月年”和“昂玛突”的一个相当重大的传统节日。这时的哈尼族人得到了片刻的闲暇,可以有一些时间去休息,并准备下一次更大的农事活动,也就是他们最忙的阶段——收获阶段。但是,在他们休息的这段时间,正值五荒六月,去年储存的粮食快要吃完,而今年的粮食又还未收获。于是,人们就非常希望得到神灵和祖宗的保佑,以求风调雨顺、五谷丰登[2]2-15。因此,苦扎扎节是一个人们向祖先和神灵祈求风调雨顺,以保佑庄稼长势良好、保佑大家大获丰收、人畜安康的节日。
二、两个哈尼族村寨苦扎扎节仪式
在调查中发现,苦扎扎节因为哈尼支系和居住地的不同,时间和仪式都有所差异,有些是从农历五月的第一个申猴日起,历时3至5天,有些是从农历6月24日起,历时3天,还有的是在五月的最后一个属龙的日子开始,历时3至5天。尼戈上寨的苦扎扎节是在农历五月的最后一个属龙的日子开始,在公历的六月中旬,历时5天,他们的庆典相当隆重。西龙小组的苦扎扎节是从农历五月的第一个申猴日算起,历时3天。
(一)尼戈上寨的苦扎扎节日仪式
第一天,村民都要去深山里带回松枝松叶,并放置在家门口,以示孝敬母亲,因为在哈尼习俗中,松枝松叶代表的就是母亲。相传,在古时候,有一以种田为生的人家,家里只有母亲和她的儿子。每天早上,作为唯一劳动力的儿子吃了饭就去田里劳作,午饭是由母亲送到田里来吃的。但是,这个儿子脾气有点古怪,无论母亲送饭的时间是早是晚,他都会殴打自己的母亲。若是送早了,他会说:“那么早送饭来,我的肚子都还没有饿!”若是送晚了,他又会说:“那么晚才送来,你是要饿死我啊!”后来有一天,儿子在田里干活的时候,看到在田埂上有一窝小鸟,母鸟正在给雏鸟喂食。此情此景,让他联想到母亲对自己无微不至的照顾,忽然就觉得自己很对不起母亲。这天,当母亲送饭来的时候,他对着母亲叫了一声“妈妈”,母亲以为他又要打她,把饭丢在地上后转头便跑,儿子跟着追了上去。母亲跑到山顶上停了下来,因为前面没路了,她只好爬到悬崖边的一棵松树上。这时儿子也追到了松树下,她一不小心就从树上跌落下去摔死了。儿子感觉很对不起母亲,想要好好侍奉她时,她却不在了。后来,人们用松树代表母亲,也代表家里的长辈。所以在过苦扎扎节的时候会去山上带回松枝松叶,并在家里杀鸭来祭奠龙神,杀公鸡来祭奠天神。
第二天,制作磨秋和迎接神人“威竹”。在天还未亮以前,寨子里的青年要上山挑选一棵长在高山顶上的笔直的松树来做磨秋杆,前去砍磨秋杆的人必须在拇指上缠上红丝线。砍好松树后,青年们要在黎明前扛回来,并且一路上要唱哈尼山歌。青年们将坚硬结实的木头抬到寨边的磨秋场上后,削细顶端,用来做轴心,并把尾端插进土里。然后,再把长长的横杆从中间凿凹,架在上面,就算做好了磨秋。值得注意的是,横杆两边的长短必须等长,而且要打磨光滑,以防划伤人们的手。另外,当日还是迎接神人“威竹”的日子,寨子里的家家户户都要杀一只鸡和一只鸭。做好的鸡放在贡桌上,并配以酒、菜、饭和茶水祭奠家神,也就是自家的祖先;鸭做好后,不是放在贡桌上,而是放在堂屋中央的地上,用来祭奠外神。
第三天,杀羊驱邪,杀牛祭祖。当日,各家要杀一只羊,煮一大锅鸡蛋和鸭蛋,象征着把所有一切不吉利的东西拒之门外,并且祭奠那些在外面因意外而死的亡灵,安抚他们不要来伤害村民、牲畜和所有的庄稼。过苦扎扎节的时候,一个寨子一般还要杀一头牛,并把牛肉分给村里面的每一户人家,用于祭奠天地和家神,以告知其本年的农活大部分已经完成了,并祈求天神和祖先保佑庄稼能够大获丰收。在吃饭的时候,晚辈要给长辈敬献水酒、肉食和饭各一碗,以示对长辈的尊重和敬爱。出嫁的女儿在这一天要回到娘家,把自己做的红粑粑送回来祭祖。
第四天,送神人“威竹”返回天庭。这一天,备好饭菜的哈尼族人,身着本民族的盛装围坐在磨秋场上,相互敬酒,祝福彼此的庄稼能够大获丰收。饭后,“摩批”(哈尼族的文明传承人)要主持撵磨秋仪式,他端着一碗煮熟的汤圆,顺着磨秋旋转的方向一个一个地朝寨子外面的方向扔出去,意味着把寨子里邪恶的东西给赶出去,然后再调转方向朝寨子里面的方向扔,意味着把外面一切美好的东西引到寨子里面来,让哈尼族人民都能幸福生活[3]116。参加仪式的人们会争先恐后地去抢食这些汤圆,据说吃了这样的汤圆能够驱逐邪恶、预防疾病。紧接着,“摩批”指导人们把磨秋空转三圈,以便让神人“威竹”和他的两个女儿坐着磨秋返回天庭,因为“威竹”和女儿们的马被偷走了,只有乘坐磨秋才能回到天上去。等磨秋空转三圈以后,人们才可以上去骑磨秋,一对对姑娘小伙轮流骑着磨秋打转。打磨秋是哈尼族人民充满情趣的一项活动,在打磨秋的过程中要求两边的人数对等,骑坐的人要用自己的脚蹬地面,有些时候是飞速旋转,有些时候升降起伏。如果磨秋的速度越来越快的话,围观的人群也会更加开心,并开始载歌载舞,为骑磨秋的人加油助兴。在此过程中,艺高胆大、身手不错的小伙子,往往就会成为姑娘们爱慕的对象。
第五天,早早起床的哈尼人要把贡桌上的桃、核桃等果实全部拿到村外送给他人吃食。而他人也非常愿意接受这些果实,因为吃了这些供奉过果实,意味着不会中毒。这一天,人们都不会干农活,而是走访亲友,聚在磨秋场上跳棕扇舞、打磨秋,姑娘小伙们谈情说爱,尽情地欢乐。
我们从尼戈上寨苦扎扎节的仪式中可以看出,这个地方的哈尼族人民对自己生活中最主要的农业生产活动,有着强烈的依赖和期望的心理,并将此转化成对自然、神灵以及祖先的虔诚崇拜和敬畏。
(二)西龙小组的苦扎扎节日仪式
在对西龙小组进行实地调查的过程中,我们发现,村里知道苦扎扎节完整仪式的只有最年长的几个老者,但几次询问也没有任何结果。村寨里大部分人对于这个节日都不是很清楚,中年人知道的内容又很少,年轻人就更不知道了。下面的内容是在询问村寨中大部分人以后总结出来的西龙小组关于苦扎扎节仪式的一些残缺内容。
第一天,是苦扎扎节的开始。清晨,每家每户都要杀一只鸡,煮熟后放在家里相应的位置,再配以酒、菜、饭、水果和肉类敬奉神灵和祖先。事毕,经过挑选的几名青年去山上砍伐制作磨秋的笔直青松树,然后抬到村寨的磨秋场,削去树枝和树皮。接着,把用坚硬结实的木头做成的磨秋杆抬到磨秋场中,将一根木头插进土里,木头的顶端要削细,当作成轴心,然后再把长长的横杆从中间凿凹,架在上面,这样就做好一个磨秋。值得注意的是,两边的横杆必须长短一致,并且要削得很光滑,以防把人们的手划伤。在西龙小组有个习俗,就是磨秋杆必须在当天的日落之前做好,而且加工磨秋时削下来的松枝松叶不能丢弃,要分发给村寨里的每家每户,作为护家或者是护身符,保佑家庭兴旺发达,年年有余。
第二天,人们会早早起床,然后在自家门口杀鸡宰羊,象征把一切不吉利的东西拒之门外,并祭奠在外意外死去的亡灵,安抚他们不要伤害人畜和庄稼。接着用酒、饭、菜、水果和肉类敬奉神灵和祖先,以此告知祖先今年的农事活动已经大体完成,请天神、祖先保佑农业获得丰收,并保佑家里面人员平安。饭后,全村人都要到磨秋场,由村寨里面德高望重的老者带着一些祭祀的物品,在磨秋杆下进行骑磨秋前的祭祀,祭祀结束后老者会把磨秋空转几下,目的是为神灵和祖先转磨秋,然后村民们再以长幼顺序开始转磨秋,整个磨秋场上呈现一幅其乐融融的画面。
第三天,这也是苦扎扎节的最后一天。傍晚,寨子里每家每户都会在家里点燃火把。人们一手高举火把,一手拿着簸箕走遍家里的每个角落,边走边用火把照亮各个角落,与此同时,要用簸箕敲打空中和家里的东西。这样做是因为家里有不干净的东西,因为“它们”怕火,所以可以用火把将之驱赶,再用簸箕敲打,寓意将之撵出家门。然后,人们举着火把来到村子外围的一个固定地点,以先后顺序,排成一条火龙,把火把留在路旁,朝东南方向延伸,以示将家里的和村寨里的邪恶驱逐向远方。事毕,人们调转回到家中,也就意味着把好财好运带回了家中,保佑家里栽种的庄稼和果林能够在接下来的日子里长势良好,获得大丰收,并让家里面的人能够健健康康、平平安安。
三、两个哈尼族村寨苦扎扎节日仪式比较
任何事物内部和事物之间都有相同点,也存在不同点,两个哈尼族村寨苦扎扎节日仪式也不例外。具体来说,差异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节日时间不同
尼戈上寨苦扎扎节的时间是从每年农历五月的最后一个属龙的日子开始,在公历的六月中旬,历时5天,其庆典相当隆重。
西龙小组苦扎扎节的时间是从农历五月的第一个申猴日算起,历时3天。
(二)砍磨秋杆的过程不同
尼戈上寨和西龙小组砍伐的磨秋杆都是青松树,但是砍伐青松树的过程和注意事项并不一样。
尼戈上寨是在天未亮以前,由寨子里的青年挑选一棵长高山顶上笔直的松树,前去砍磨秋杆的青年必须在拇指上缠绕红丝线,松树必须在黎明前砍好并扛回到寨子里面。
西龙小组则是直接去砍树,然后把青松树抬回磨秋场进行加工,在当天日落山之前把磨秋做好就行。
(三)祭奠祖先神灵的方式不同
尼戈上寨的家家户户一般在第二天都要宰杀鸡鸭各一只,做好的鸡放在家里的贡桌上,然后配以酒、菜、饭和茶水,用以祭奠家神;做好的鸭放在堂屋中央的地上,用来祭奠外神。第三天整个寨子里要杀一头牛,并把牛肉分给村里面的每家每户,用于祭奠天地和家里的祖先。出嫁的女儿在这一天要回到娘家,把自己做的红粑粑送回来用来祭祖。
西龙小组则是每家每户杀鸡,做好后摆放在家里相应的位置,再配以酒、菜、饭和水果肉类等敬奉神灵和祖先。
(四)骑磨秋前的主持仪式不同
尼戈上寨骑磨秋前,要让“摩批”主持撵磨秋仪式,他端着一碗煮熟的汤圆,顺着磨秋旋转的方向朝寨子外扔,然后再调转方向,朝寨子里面扔,参加仪式的人们会争先恐后地去抢食这些汤圆。接着,在“摩批”的指导下,大家把磨秋空转三圈,以便让神人“威竹”和他的两个女儿可以坐着磨秋回到天上去。事毕,人们才可以轮流转磨秋。
西龙小组则是由村寨里德高望重的老者带着一些祭祀的物品来到磨秋杆下进行骑磨秋前的祭祀,接着老者会为神灵祖先空转几下磨秋,之后村寨里的人按照长幼顺序开始转磨秋。
(五)苦扎扎节最后一天的仪式不同
尼戈上寨苦扎扎节在第五天结束。这日,哈尼人起得很早,他们要把贡桌上的桃、核桃等果实全部都拿到村外送给大家分食。而且,这一天大家都不会去做农活,而是聚在磨秋场上跳棕扇舞、打磨秋,姑娘伙子们在这一天也会谈情说爱。
西龙小组的苦扎扎节在第三天结束。在当天傍晚的时候,寨子里的每家每户都会在家里点燃火把。人们用火把照亮家里各个角落,并用簸箕敲打空中和家里的东西,以便将不好的或者是不顺的“东西”撵出家。然后,人们举着火把来到村子外围的一个固定地点,以先后顺序,排成一条火龙,把火把留在路旁,朝东南方向延伸,以示将家里的和村寨里的邪恶驱向远方。完毕,大家调头回到家中,也就意味着把好财好运带到家中,保佑家里栽种的庄稼和果林能够在接下来的风调雨顺的日子,大获丰收。
当然,两个哈尼族村寨节日文化除了差异之外,还有一些相同点。比如,个案背景部分相同;苦扎扎节的来源相同;磨秋的制作材料和方式相同;民族支系相同;纪念意义相同等。
四、两个哈尼族村寨苦扎扎节节日仪式差异缘由
尼戈上寨和西龙小组两个村寨的哈尼族苦扎扎节,在时间、地点和仪式上都有不相同的地方。从仪式上来看,尼戈上寨的苦扎扎节的仪式更详细,更全面;西龙小组的仪式相对简单,而且许多都是残缺的。同为哈尼族人,为什么会存在同一个节日,却有不同的仪式呢?又是什么因素导致的呢?
(一)位置因素
尼戈上寨和西龙小组分别距离元江县城大约60公里和40公里。相比之下,西龙小组与元江县城的距离稍微更近一些,交通上就比尼戈上寨更加便利,更容易受到县城经济发展和现代化的影响,从而导致一些传统思想文化逐渐发生了改变。并且,村民接触的外来文化,以及与其他民族的交流日渐增加,使得一些民族文化不断受到影响而产生变化。
(二)传承人的因素
是否有人引导和传播传统文化是节日仪式产生差异的重要原因。尼戈上寨的苦扎扎节的传说、仪式内容保留完整的原因之一,就在于当地有一个哈尼文化的传承人。据了解,这个传承人同时也是羊街乡文化站的工作人员,他不仅清楚地知道和了解苦扎扎节的传说和完整的仪式内容,而且还知道哈尼文化中其他节日,以及棕扇舞、哈尼建筑等。村子里过节日的时候,他都会去引导村民们,并让下一辈的人边看边学。在平常,他还会给村民传播哈尼文化。在传承人的引导下,村里无论男女老少都可以知道传统节日文化的具体内容,不至于流失。但在西龙小组却没有这样的传承人,这也是其节日仪式残缺不全的原因之一。
从两个村寨苦扎扎节日仪式的内容来看,有着不同的步骤,西龙小组的相对简单,没有尼戈上寨的详细。在实地调查时,笔者了解到由于没有传承人的引导,西龙小组的人们对节日仪式知之甚少。虽然,村里的确有个别老人知道苦扎扎节的详细内容,但经过多次询问都毫无结果。于是我们也只好在其他村民的零星记忆中获取残缺的资料。调查显示,村里的中青年和小孩也有过苦扎扎节的愿望,因为这是一种祈求神灵的仪式,他们崇尚神灵和祖先,无奈没有完整的仪式传下来,只能进行简化了的仪式。由此可见,传承人在传统文化传播上的重大作用。
(三)民族文化交流因素
西龙小组受其他民族文化的影响比尼戈上寨的更大,尤其是在通婚和教育上。两个村寨都打破了本民族内部通婚的约束,打开山门与其他民族进行通婚,而这个现象在西龙小组比较普遍,从而使得他们能够更多地与其他民族文化进行接触,接受了更多的社会教育理念。久而久之,在外来因素的影响下,他们走上了追求现代化的道路,接受了许多其他民族的优秀文化。虽然也继承了不少本民族的传统文化,但也丢失了一些本民族的特色文化。
(四)政策扶持因素
在西龙小组,传承传统节日和文化的政策扶持没有得到体现,村里的年轻一辈不清楚具体的仪式,已经把节日内容简化了,小孩子们几乎不知道这个节日的内容,没有人传播这些民族传统节日,人们只知道苦扎扎节,但是到底怎么庆祝却不清楚。而尼戈上寨的哈尼人民既有政策的扶持,还有传承人,县政府投资一半的资金给传承人把他家的房子改建为具有民族传统特色的建筑,并出资让传承人书面记录哈尼人民的传统文化,把传统的东西编辑成册,让后人有迹可循,有书可读,还能让以后的哈尼子民知道本民族的传统节日文化,不至于把老祖宗的东西丢失。
通过以上两个哈尼族村寨苦扎扎节节日文化发展的不同态势,我们能感受到节日文化的保护与发展是个系统工程。在这个系统工程中,文化持有者的文化自觉是节日文化发展的核心,政府支持是节日文化发展的保证,文化交流是保持节日文化发展的动力。只有将这个系统工程的各个环节协调一致,节日文化才能得到保护与发展,才能发挥民族节日承载的社会功能。
[1] 唐力行.国家、地方、民众的互动与社会变迁[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
[2] 杨雪政,袁跃萍.云南原始宗教[M].北京: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4.
[3] 史军超.文明的圣树——哈尼梯田[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5.
(责任编辑:于开红)
A Comparative Study of Festivals and Rituals in Two Hani Minority Villages
LI Yinbing1FANG Lu2
(1. School of Marxism, Guizhou Normal Universities, Guiyang, Guizhou 580001) (2.School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Yuxi Normal University, Yuxi, Yunnan 653100)
The different shapes of Kuzaza rituals in two Hani Minority villages inform us of the clashes of modernization to traditional festivals and raise our concerns to cultural development of traditional festivals.
Kuzaza; Hani Minority; rituals;comparison
C952
A
1009-8135(2016)02-0025-05
2015-11-28
李银兵(1976-),男,四川资中人,贵州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文化人类学博士,历史学博士后,主要研究文化学、历史人类学。
国家社科基金“文化创新视域下西部少数民族传统节日的社会功能研究”(项目编号:14BSH057)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