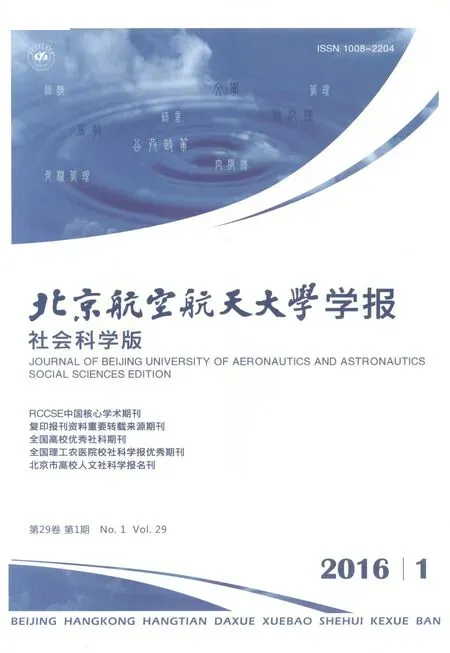低空开放背景下的低空使用权
陈学军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法学院, 北京 100083)
低空开放背景下的低空使用权
陈学军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法学院, 北京 100083)
摘要:中国的低空空域改革已经进入到了攻坚阶段。在现阶段,必须转变低空开放的改革思路,从公权力管理模式向私主体权利模式大踏步迈进。因此,必须确立民众的低空使用权,这在一方面将有助于约束公权力的肆意干预,另一方面将为“军民共管”的空域改革提供理论支撑。中国现行法上的空域资源国家所有权仅仅是一种宣示性权利,其在私法意义上相当于罗马法上的公有物。因此,低空使用权并不与国家所有权相冲突。
关键词:低空开放; 低空使用权; 空域资源; 国家所有权; 宣示性权利; 公有物
一、引言
2014年7月中国出台了《低空空域使用管理规定(试行)(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意见稿》),明确将中国的低空开放空域限定在真高1 000米以下,并且规定了低空空域类型、空域准入资格、审理机构、审理手续和审批时限等。①这一《意见稿》的出台标志着中国低空空域改革进入了具体制度建构阶段,表明空域管理制度正在逐渐从粗放型向精致型转变,具有明显的积极意义。资本市场对政策最为敏感。在该《意见稿》出台后,资本市场上的相关概念股纷纷飘红——通用航空作为少数的未开发的处女地,一旦放开政策限制,其将带来巨额的利润。②吊诡的是,自《意见稿》出台至今,通用航空产业仍然步履蹒跚,之前预计的大批量订单和投资热潮并没有出现。《意见稿》对实体经济的影响似乎微乎其微。难道中国没有通用航空市场?恐怕不然。中华民族是世界上最早的怀有“飞行梦”的民族。而实际上,很多人都表达了旺盛的飞行欲望。③改革没有推动产业的发展,恐怕问题还在于改革自身。在《意见稿》出台后,面对通用航空的冷淡局面,有主管领导无奈地表态:“当前低空空域改革已经进入深水区和攻坚期,需要破解的矛盾问题很多,任务艰巨繁重”④。
为了凿破空域改革的坚冰,学者们纷纷献策。有学者指出,改革效果不佳的原因在于低空开放空域过窄——1 000米的范围对于农林灌溉尚可,但是对于载客飞行、科技研究、航空服务业等行业的发展则远远不够。⑤有学者认为,问题在于飞机审批程序复杂,涉及单位、层级过多;通航机场和专业技术人员等严重不足。[1]也有学者认为,问题还包括中国的通用航空制造业落后,导致无法提供可选择的飞机产品;与通用航空相关的法律法规不配套,导致人们无法实际飞行等因素。[2]无疑,上述意见都对问题的解决有着一定的指导意义。然而,一项改革不应该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而应当是一项系统工程。那种“论题学”意义上的解决方法,在体系完成之后进行一定的修补,尚有其意义。但在制度建构或变革之际,需要的却是宏观思想和理论的指引。只有首先明确改革的方向、意义和指导思想,才能够实现根本的变革;也只有在宏观理论的指引之下,才能够系统而全面地解决通航发展所面临的各种问题。
中国《物权法》制定之初,就是因为没有在集体土地改革方面有清晰的思路和理论指引,才使得其和《土地管理法》等法律并不协调;而在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改革农村集体土地,放松土地流转”的背景下,《物权法》却又成为了改革的绊脚石。前车之鉴,尤为可畏。中国低空空域改革也必须在一套清晰的改革思想和理论的指引下予以展开,否则就只能是“缝缝补补”,不但难以撼动坚冰,甚至可能适得其反。
2015年是中国低空空域“深化改革”的最后一年⑥,也因此被媒体普遍认为是中国低空空域改革的最为关键的一年。然而,时至今日,中国尚没有建构出一套完备、自洽的空域改革指导思想和理论体系。改革没有了思想,就如同航行找不到灯塔,找不到方向。笔者认为,建构出一套先进的、符合中国国情的指导理论以指导空域改革,乃中国空域改革的当务之急。有鉴于此,文章尝试提出一种指导思想以求为中国的空域改革制度提供理论指导。笔者认为,实现思想和理论上的解构和重构,才是一项改革得以成功的前提和基础。
二、美国低空空域管理制度
历史证明,人类文明面临的很多问题是共通的:在一个国家出现的问题,在另外一个国家也极有可能发生;而一国改革的成功经验,也可以被他国所借鉴从而走向富强之路。整个人类社会的进步史,一定意义上说,就是不同文明之间互相学习的历史。而对于法学而言,这一规律尤为适用。德国法学家耶林(Jhering)曾谓:“外国法制之继受与国家无关,仅系合乎目的性及需要之问题耳。若自家所有已属完善或更佳,自然毋庸需求,惟若以奎宁皮药草非长自自家庭院而拒绝使用,则愚不可及。”[3]一语道出比较法之重要性。在低空空域改革方面,美国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其通用航空产业也在世界上处于领先地位。笔者意欲首先考察美国的空域管理制度,在此基础上尝试为中国的空域改革寻找理论支持。
(一) 美国空域管理制度的基本介绍
美国的低空空域高度大致相当于直高3 000米以下的空间。美国在1993年采用了国际上通用的空域体系,根据空中交通需要分为A,B,C,D,E,G六类,同时对空域的划分做了一定程度的变通,每种空域有空中交通管制服务、航空器间隔标准、气象最低标准以及飞行规则等方面要求。在空域分类中,A,B,C,D和E类空域为管制空域,G类为非管制空域。自二战后,美国政府将大约85%的空域划为民用空域,其中的绝大部分又被通用航空使用。在绝大部分美国国土上,只要有一部航空电台,就可以在3 000米海拔高度以下自由飞行;而仅仅多装一台C模式应答机,高度限制就可以提升到海拔5 400米;至于在200~360米高度(真高)以下,甚至连电台都可以没有。而某些管制空域,目视飞行规则的航空器也是可以进入的,只不过条件和程序比较复杂而已。美国空域规划和管理制度极大地促进了通用航空在其国的发展。而美国人之所以乐于开放低空以供民用,在于美国人普遍享有的“飞行自由权”思想。
(二) 美国法上的飞行权

随着美国航空产业的发达,为了进一步规范空中交通,美国在1958年成立了航空管理局(FAA),航空管理交由该部门负责。然而,这并没有改变美国人对空中飞行的态度:美国联邦法规大全第14编(即《美国联邦航空规章》,FederalAviationRegulations)明确规定公民享有空域使用的自由权利和接受导航空域服务的权利。美国在通用航空的管理上始终围绕保证公民飞行权的基本原则,在保护公共运输飞行和军事飞行所需空域的基础上,将空域最大限度地交给公民,尽最大努力放松对通用航空的管制。以飞行计划的提交为例。根据14 CFR 91.153条,在目视飞行时,应当提交的飞行计划内容包括:飞机识别码、飞机类型、飞行员姓名和地址、出发时间、预计线路、降落机场、机载人员数量、油量等。而只要提交了该飞行计划,美国人就可以自由地在空中航行。美国法律对于提交飞行计划的时间都没有太过苛刻,这点与中国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由于通用航空主要适用目视飞行规则,宽松的管理制度给美国通航发展提供了极大地便利,使得美国逐渐成为了世界第一通用航空大国。

(三) 9·11对美国航空自由的影响

美国人认为,设立ADIZ不符合比例原则,其为了国家安全——是否有效尚饱受争议——严重限制了人民的飞行自由,给人民的生产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不便,进而严重影响了美国经济的发展。其思维的逻辑起点仍然是要保障人民的飞行权:国家对私权的干预必须符合比例原则,且理由也必须详细论证。

(四) 小结
与中国航空业的发展模式不同,美国的航空产业是在空域不受监管的状态下发展起来的。后来随着该产业的日趋壮大,与该产业有关的法律纠纷日渐明显,美国才开始进行《统一航空法》的制定。因此,在美国根本不存在人民是否享有飞行权的问题——在法律出台之前,飞行权就已经被美国人民所广泛接受。而其立法也主要侧重于如何协调飞行人员和其他私主体之间利益冲突。⑦其后的航空立法无不贯彻了这一理念,无论是美国《统一航空法》还是FAA法规都是围绕保障人民飞行权的基点开始建构的。正是在这种立法思想的指引之下,美国将80%以上的空域划为民用空域,极大地促进了本国通用航空的发展。9·11事件的发生使得美国的空域安全备受重视。惊慌中的美国人采取了一些严厉的措施限制空域的使用。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理性的美国人又开始质疑自己是否走的太过了。对人民飞行权的限制应当符合比例原则,应当接受严格地论证。毕竟,自由的飞行权是整个美国航空法的基石。
三、破题之策——低空使用权
通过上文可以发现,美国通用航空之所以能执世界之牛耳,根本原因在于其最大限度地保障了私主体的飞行权。而源于中国的航空产业是国家一手扶持的产物,飞行自由观念在中国尚未深入人心。这就导致中国现行的空域改革仍然延续着官方管控的思路。笔者认为,中国的空域改革也应当趋向于赋予人民飞行自由。赋予人民飞行自由将直接改变中国航空立法的规范路径和航空管理的制度设计,这对于实现空域改革极为重要。鉴于目前中国空域改革以低空改革为切入点,不妨首先承认人民的低空使用权,而后徐徐展开。需要说明的是,文章之所以使用低空使用权而非低空飞行权的概念,乃是因为现代社会对低空使用的方式趋于多样化,如气球广告等类型。“使用”比“飞行”的外延更宽,更能保障私主体对空域资源的使用。
(一)低空使用权对规范路径的影响

而如果赋予了私主体以低空使用权则情况就不一样了。权利从积极面上意味着人民有资格获得利益;从其消极面上,则是指着国家在实践中认真回应权利诉求、认真实施权利立法、认真提供权利救济,对权利的干涉必须符合法定程序,必须满足比例原则。[4]如果中国如同美国一样,首先认为民众有权利自由飞行,那么有关部门要限制民众飞行,其就应当给出充分的论证,如“空中禁区事关国家首脑安全,因此不得低空飞行”等。从法律制度的具体建构上,必须明确规定私主体不得进入低空空域的几种情况,亦即通过“负面清单”(negative list)的模式规范, “非禁即入”。在这一思路之下,公权力必须按照“法无授权不可为”的原则,国家的权力能够得到有效的规范和约束,其权力仅限于保证那些被列入清单的领域切实得到规范或禁止。需要有关部门审批的领域也仅限于法律明确列举的事项,并要对限制条件进行合理说明,从而能真正保障市场主体的行为自由。[5]在遇到了“法律沉默”的领域,虽然也需要解释是否和法律例举情形相似,但是在有疑义时,原则上则准予飞行。
(二)低空使用权对管理制度的影响
《意见稿》第3条明确赋予了空管委对低空空域的低空管理权。中国的空域基本是由空军管理的。源于空域资源无形性、非排他性,对其管理有一定的必要性。然而,中国目前的空域使用状况是,空管委对空域资源的管理,使得其自身实际上成为了空域资源的独占者。私主体要想使用该资源,就必须获得空管委的同意,否则即为违法,甚至可能被判以刑罚。这在导致空域资源利用无效率的同时,也为有关部门提供了权力寻租的可能。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之一,在于中国的航空管理权集中于个别公权力领域,由此导致航空自由难以实现。中国虽然也成立了民航局,但是因为民用空域和军用空域在本质是难以完全区分的,民航空域实际上从属于军航空域管理。笔者认为,改革之道在于变“军队主管”“军民分管”为“军民共管”。“航空管制从本质上应当采取军民协调配合的联合共管模式,建立军民合为一体的统一管制机构, 这种一体化模式也为各发达国家广泛采用。”[6]而“军民共管”的理论基础之一就是要承认人民利用低空空域的权利。只有首先认可民众有低空使用权,才在逻辑上认可其参与低空空域管理的资格。因此,确立低空使用权的观念才能够证成“军民共管”的制度设计,推动中国空域管理制度变革。
(三)小结
承认私主体的低空使用权,一方面可以最大限度地保护私主体的飞行自由,防止公权力机关对低空空域的恣意干预;另一方面可以改革管理制度,实现“军民共管”,从而使得低空空域的管理更有助于人民飞行权的实现。由此可见,是否确立私权利对于民众而言意义重大。笔者认为,应当确立低空使用权在低空空域改革中的指导地位,并以此为理论依据,采取“负面清单”的规范路径和“军民共管”的管理制度,从根本上实现中国的低空空域改革。
四、低空使用权和空域所有权的内在契合
2004年中国民用航空总局令第122号《民用航空使用空域办法》第3条明确规定:空域是国家资源。《意见稿》第2条也规定“低空空域是国家重要的战略资源。”在此基础上,有关部门强调空域资源归国家所有。而根据所有权的排他性,有关部门似乎可以当然地限制、排除私主体对空域资源的使用。由此看来,私主体的低空使用权似乎与国家所有权相冲突。笔者认为,认定空域资源归国家所有,并不能逻辑地推导出公权力即可对空域资源实现独占。无人否认空域资源是一种重要的国家资源,就像无人否认山川、河流、道路等是国家资源一样。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私主体就不能利用国家资源了。因为如果按照这一逻辑,农夫到河流当中汲水即构成了对国家财产的侵犯,渔民到海里捕鱼也构成了侵害国家财产,市民到海里洗澡也是对国有财产的非法侵占。这种逻辑是难以自洽的。概念是思考的起点,要论证私主体享有低空使用权的正当性,就必须正确理解国家资源这一概念。
(一)为什么强调空域是国家资源
一国之所以强调空域属于国家资源,一方面是受到国际法上的主权观念的影响,另一方面则是源于空域资源的特性。
1.国家主权观念的影响

2.空域资源的特殊性使然

(二)空域的法律性质
1.对公有物(res communes)的基本介绍
罗马法中物的概念极为复杂、精细。其首先将物分为交易物和非交易物,后者又继续分为神法物(res divini iuris)和人法物(res humani iuris)。前者包括圣物、安魂物和神护物三种类型。[13]对人法物的分类则比较复杂。盖尤斯在《法学阶梯》第2卷第10段中写道:“那些由人法支配的物品或者是公有的(publicae),或者是私有的(privatae)。”在这一法言当中,盖尤斯对人法物作了二分法的处理,并以这种二分法揭示公私的二元对立。在此基础上,埃流斯·马尔西安进一步指出,“根据自然法,某些物属于一切人所有,某些物属于一个共同体所有,某些物不属于任何人,而更多的物属于个人,它们由个人因各种不同原因而获得。”[14]155在这一片断当中,马尔西安将人法物区分为一切人公有的物、团体物和私有物。然而,马尔西安随后又指出,剧院、体育场、城邦公奴属于团体物(D.1,8,6,1);河流和港口通常是公有的(D.1,8,9,1)。亦即,马尔西安实际上做了四种划分:一切人共有的物、公有物、团体物和私有物。后来优士丁尼的《法学阶梯》采用了马尔西安的观点,承认了上述四种区分。[15]
尽管如此,上述罗马法文献当中并没有界定什么是公有物。在罗马法文献里面多次提到公有物,但是它关注的是物的公共使用属性。例如,马尔西安在《法学阶梯》第3卷中写道:“而几乎所有的河流和港口都是公有的。”(D.1,8,4,1)盖尤斯认为:“根据万民法,对河岸的使用就像对河流本身的使用一样是公共的。因此,任何人可以自由地使船泊岸,将绳索捆绑在生长在那里的树上……但是河岸的所有权属于与河岸毗邻的那块土地的所有者。”(D.1,8,5pr.)[14]157在马尔西安的片段中,河流和港口被认为是公有的,但使用它们必须连带地使用河岸,为了实现此等公有物的公共使用,按事理之性质其河岸也应当具有公共使用属性。在盖尤斯的片段中,虽然河岸的所有权被认为是属于毗邻土地的所有权人,但对它的使用又是公共的。罗马人采用了私人所有和公共使用并行不悖的观念,以此解决公有物使用的问题。即使在现代意大利法当中,也存在着“用于公共利益的私产”的概念,它是指私人的财产除了为财产所有权主体而使用外,也应该为并存的公共利益使用。[16]亦即,罗马人认为,所有权形态并不会妨碍物的公共使用。公有物是从物的公共利益的角度进行的判断,公有物也可能是私人所有的,但是为了公共利益,公有物必须要满足其他人的合理要求。
(1)公有物的概念
公有物与其说是指物的所有权形态,不如说是着重于物的使用等功能属性而做出的划分。中国物权法规定了国家所有权、集体所有权和个人所有权,并没有明文规定公有物。但是,只要上述所有权负担了极大的公共利益,那么所有权的客体都有可能成为公有物。
文章认为,公有物是指直接供公众福祉或者行政主体自身存续的需要而使用(unmittelbare öffentliche gebrauch)之物,它们受到因公法上的配置(widmung)而确定的使用目的的约束(zweckgebundenheit)。[17]456—459
(2)公有物之特殊性
公法上的公有物不同于物权法意义上的物(sache)。物权法上的物包括动产和不动产,一般被认为主要是有体物。但是公有物不以有体为限。例如,中国2006年生效的《事业单位资产管理暂行办法》第3条规定:“本办法所称的事业单位国有资产,是指事业单位占有、使用的,依法确认为国家所有,能以货币计量的各种经济资源的总称,即事业单位的国有(公共)财产。事业单位国有资产包括国家拨给事业单位的资产,事业单位按照国家规定运用国有资产组织收入形成的资产,以及接受捐赠和其他经法律确认为国家所有的资产,其表现形式为流动资产、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对外投资等。”《行政单位国有资产管理暂行办法》第3条规定:“本办法所称的行政单位国有资产,是指由各级行政单位占有、使用的,依法确认为国家所有,能以货币计量的各种经济资源的总称,即行政单位的国有(公共)财产。行政单位国有资产包括行政单位用国家财政性资金形成的资产、国家调拨给行政单位的资产、行政单位按照国家规定组织收入形成的资产,以及接受捐赠和其他经法律确认为国家所有的资产,其表现形式为固定资产、流动资产和无形资产等。”公有物虽然主要由公共财产担当,但不以此为限,私人财产在一定条件下也可以是公有物,甚至产权无法明确归属但可以由任何人享用的物,如空气、阳光和水域等,也可以是公有物。正因为公有物不同于物权法上的物,因此,民法上的一些规则不适用公有物。例如:物权法上,物的重要成分与所组成的物同其命运,不可分为不同物权的客体;但是在集体所有不动产上设置的交通标志虽然为不动产的重要成分,确是独立的公有物。在民法上,集合物在以法律行为变动物权时要遵循标的确定原则,但是公法上,众多的书籍、桌椅可以组成一个统一的公有物——图书馆。
(3)对公有物的法律适用
公有物不能只适用私法规范,否则,公共目的的执行就可能受私法权利人意志的摆布。当然,公有物的本质也要求人们不得被排除在公有物的设施使用或一般使用之外。那么此时的问题就在于,对公有物是否应当适用民法的相应规范?
德国曾经对公有物适用私有财产权的相应规则,其认为公有物的法律属性为修正的私有财产权。具体而言,对公有物的规范原则上适用私法制度、确立公法支配权和区分所有权人、支配权人以及管理义务人。根据修正的私有财产权理论,公有物原则上应当适用民法当中关于所有权的规定。但是该财产权也受到公法上的支配权的限制。具体而言,公有物的使用和处分等应当建立在公务目的的基础上。公有物上有容忍第三人使用以及接受公法管理的负担。在与公法目的不一致的情形下,公法上的负担排斥私有财产上的权利。公共利益产生的对私法权利的限制,尤其是对财产所有人处分权的限制可能使私有财产权变成无实质内容的权利。但是,所有权人因此也享有好处,即其本人的管理义务和赔偿责任由公共行政主体承担。现代社会管理模式的发展使得财产所有人、支配人和管理义务人可能不是同一主体。对公有物而言,这三者通常是一致的,但是有时也并非如此。
然而,德国很快就摒弃了该理论,原因在于该理论在法律制度、权利人、义务人以及使用规范和法律管辖等方面都对公有物的发展有所不利。在这种考量下,德国法学家主张建立独立的公共财产制度。公共财产理论主张行政机关根据法律或者法理应当具备一些不可替代的进行日常活动的公有物,这些财产受专门的行政法规范的调整。在没有法律规定时,只有在与公有物目的不相违背的情况下才得以适用民法上的相应规定。这种理论在德国已经通过立法的方式被予以确认。例如:德国《汉堡州道路法》第4款第1句规定,所有被命名为公路或者自由国家和汉萨城市汉堡的不动产都属于公共财产权的范围。《汉堡州水法》第4条有关洪水防护设施的规定同样如此。《汉堡州道路法》第4条第1款第5句明确规定,民事规范不适用公有物,尤其是其中有关占有和所有权的规定。《水法》第4条第1款确立一级水域和二级水域水床的公共财产权。该法第5条第1款作出了如下限制性规定:有关不动产所有权的民事规范原则上可以适用,除非与公共水域或者水法的公共目的相冲突。该法还规定了对公有物的公法支配权、公有物使用规范和公有物赔偿责任等,全面规范了对公有物的使用和管理。
(4)对公有物的使用
根据德国的公共财产理论,人们对于公有物原则上享有一般使用权,即无需特别批准,任何人都享有按照公有物的目的使用该公有物的公共权利。[17]495私主体的一般使用权意味着公有物原则上向自然人和法人都开放,除非法律基于特殊考虑对特定人做了必要的限制,如《道路交通法》可能会限制精神有问题的人开车等。当然,出于管理的需要,在使用公有物时可能需要经由有关机关的许可。如人们在使用公路时,应当遵守公路交通的基本要求,驾驶人应当获得驾驶证等。

还需要说明的是,对一般使用权的限制,一方面源于法律的规定,另一方面也源于公有物的性质。对公有物的使用要受到公有物的种类、性质和目的等的限制。在该范围之外的使用需要特别许可。如人人都有使用公路交通的权利,但是对公路的使用应当符合“交通使用”的目的。交通,即指有意改变位置的行为。而如果在公路上摆摊设点、堆放物品、倾倒垃圾、设置障碍、挖沟引水、利用公路边沟排放污物等,则不属于符合公路目的的行为,应当不予允许。
2.空域实则为公有物

此外,根据《物权法》45条:“法律规定属于国家所有的财产,属于国家所有即全民所有。”可见,中国在立法之初,是在用国家所有替换全民所有。规定国家所有有利于对公有物进行更好地管理,因此,这里的国家所有应当理解为“国家替全体人民所有”。国家所有权本质上其实是全体人民所有权,而全体人民所有其实即意味着“不可私有”,即意味着人人都可以使用。
再者,空域作为一种无体物,很难被界定和区分。如空域和外层空间的界限一直都是一个需要解决但至今未解决的问题。这种特性使得其很难被认定为属于物权法意义上的物。然而,公有物的物的概念和物权法上的物的概念并不一致。这点前已论述,此处不予赘述。对公有物而言,其对象可以是总括的事物,也可以是无形资产,认定空域为公有物并不存在理论上的障碍。
综上,文章认为,空域资源应当定义为公有物,本质是全民共有。强调空域的国家所有权其实一方面是为了防止他国对领空主权的干预,另一方面是为了便于国家对其进行管理。由此可见,空域资源的国家所有权其实只是一种宣示性权利。空域资源自身在私法层面上应当对应的是自罗马法就盛行的公有物的概念。
(三)低空使用权乃空域性质的应有之义
如前所述,空域国家所有权的创设一方面是受国家法上的主权概念的影响,另一方面是基于行政法意义的管理便利之考量。空域国家所有权本质上并不是为了排除国内人民使用而创设的权利,其并不具有物权法意义上的排他性。此外,即使承认空域也是物权法意义上的物,源于空域巨大的公共利益色彩,国家也负有容忍私主体使用空域的义务。此乃公有物的应有之义。因此,低空使用权并不与空域所有权相冲突,恰恰相反,前者是后者的内在要求。当然,私主体的低空使用权并不意味着私主体可以不受限制地使用空域。公有物源于其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内在地要求国家对其使用进行一定的指导和监管。但是无论如何,监管的力度不能到了排除私权使用的地步,否则就违背了制度设计的初衷。而中国目前对低空空域的过度限制,一方面侵蚀了私权,另一方面也桎梏了中国航空工业的发展。
五、结论
《意见稿》的出台给中国的低空空域改革带来了一阵清风。其让国人振奋的同时,对通航产业的影响却出人意料地颇为有限。笔者认为,改革绩效不明显的根本原因在于,目前的改革是在维持有关部门对空域资源独占的前提下进行的“缝缝补补”,这根本无助于问题的解决。笔者认为,中国应该借鉴美国的空域利用模式,普遍赋予民众低空使用权。美国即是以人民的飞行自由为起点建构了自身的航空制度,即使是在9·11以后,美国仍然不愿意颠覆这一传统。正是源于这种理念,美国的通用航空业极为发达,世界排名第一。在不违背国家安全和交通管制的前提下,中国也应当允许私主体自由地使用低空空域。
确立低空使用权在低空开放中的核心地位,一方面有助于限制有关部门的权力,最大限度地保护私主体的飞行自由——其突出表现就在于“负面清单”的立法模式,“非禁即入”;另一方面有助于推动中国的空域管理制度改革,为“军民共管”提供坚实的理论基础。需要注意的是,私主体的低空使用权和空域资源国家所有权并不冲突。“空域资源国家所有权”仅仅是一项宣示性的权利,其主要是受到“主权”观念的影响以及更好地管理空域资源而设。空域资源实质相当于罗马法意义上的公有物,以满足全体公民的共同需要为目的;国家对其的管理,也是建立在保障人民需要得到实现的基础上。因此,设立低空使用权的概念具备正当性和合法性。笔者认为,只有确立低空使用权思想,才能从根本上实现空域改革。至于中国的通用航空生产能力、机场数量以及飞行员数量等不足的问题,笔者相信,只要存在着巨大的利润空间,市场会逐渐弥补这些缺陷。
注释:
① 参见:《低空空域使用管理规定(试行)(征求意见稿)》,http:∥news.carnoc.com/list/288/288814.html,访问日期为2015年3月15日。
② 据安信证券投资预报预测,未来10年在私人飞行、公务飞行、通用航空农林和工业作业等产业链的市场规模将达到3 900亿元,而通航配套市场空间也将达到3900亿元。仅仅在这些领域上,低空开放政策就将在10年内给通用航空行业提供7 800亿元的“蛋糕”。参见:《军方让步迎来低空开放倒计时,十年7 800亿蛋糕》,http:∥news.hexun.com/2014-11-29/170912172.html ,访问日期为2015年3月15日。
③ 参见:《中国已有两百多架私人飞机,飞机成富人新宠》,网址为http:∥www.chinacourt.org/article/detail/2010/08/id/421097.shtml。另参见《低空空域管理改革带来机遇,私人飞机天地将更宽》,网址为http:∥www.chinacourt.org/article/detail/2010/11/id/435443.shtml,访问日期为2015年3月15日。
④ 参见:《民航局:低空开放应至3000米》,网址为http:∥finance.sina.com.cn/chanjing/cyxw/20141124/011920897400.shtml,访问日期为2015年3月16日。
⑤ 农林业所需的高度在15~300米。但是,航空摄影、物探、遥感等飞行所需要的高度多在3 000米至7 000米;航空运动、训练以及旅游观光飞行一般在1 500米以下;跳伞活动一般在2 400米以下;广告飞行一般要求在3 000米以下。参见吕新和王霞所写的《我国通用航空空域资源发展问题浅析》,载《第十三届中国科协年会第22分会场——中国通用航空发展研讨会论文集》。
⑥ 2010年11月国务院、中央军委联合发布了《关于深化我国低空空域管理改革的意见》,明确指出中国要开放低空空域以供民用,并且公布了开放低空空域的具体时间表:2011年以前为“试点阶段”;2011—2015年为“推广阶段”;2016—2020年为“深化阶段”。详见《中央军委关于深化我国低空空域管理改革的意见(全文)》,网址为http:∥www.eeo.com.cn/2010/1116/185929.shtml,访问日期为2015年3月15日。
⑦ WARREN J D.TheUniformStateAeronauticalCode. 8 Air L. Rev. 283—285, 282. (1937)
⑧ FRED D. FRAG, Jr.AirspaceOwnershipandtheRightofFlight, 2 Rev. Jur. U.P.R.pp.107—108. (1932)
⑨ 这种立法逻辑就如同《法国民法典》制定之初不规定公民的人格权利一样,法国人认为公民的人格权乃天赋人权,无须立法明言。
参考文献:
[1] 董念清.中国通用航空发展现状、困境及对策探析[J].北京理工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版,2014 (1): 112—114.
[2] 李成智,苏道宁. 中国通用航空:问题、原因及对策[J].北京:工程研究——跨学科视野中的工程,2010(1):17—19.
[3] 王泽鉴.民法学说与判例研究:第2册[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9:22.
[4] 黄文艺.权利本位论新解———以中西比较为视角[J].法律科学, 2014 (5): 17—23.
[5] 王利明.负面清单管理模式与私法治理[J].中国法学, 2014(5): 31—32.
[6] 张千帆, 龙卫球, 董杜骄, 等.建立统一的中国航空法体系——理论初探与立法建议[J].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8,21(2):46—47.
[7] 邢爱芬.民用航空法教程[M].北京: 中国民航出版社, 2007:29.
[8] 张娜, 王静. 通用航空发展研究[M]. 北京:中国铁道出版社, 2013: 11.
[9] 陈志杰.空域管理理论与方法[M].北京:科学出版社, 2012: 1.
[10] 让·博丹.主权论[M].李卫海,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8:87.
[11] 埃莉诺·奥斯特罗姆.公共事物的治理之道[M].余逊达, 陈旭东,译.上海:三联书店, 2000:52.
[12] 李永军.海域使用权研究[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6: 226—232.
[13] 盖尤斯.法学阶梯[M].黄风,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8:56.
[14] 优士丁尼.学说汇纂[M].罗智敏,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8:155—157.
[15] 优士丁尼.法学阶梯[M].徐国栋,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5:112.
[16] 江平,S·斯奇巴尼.罗马法、中国法与民法法典化:罗马法与物权法、侵权行为法及商法之研究[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 2008:20.
[17] 汉斯·沃尔夫, 奥托·巴霍夫, 罗尔夫·施托贝尔.行政法[M].高家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2: 456—495.
[18] 崔建远.自然资源国家所有权的定位及完善[J].法学研究,2013(4):68.
[19] 金可可.论乌木之所有权归属——兼论国家所有权之种类及其限度[J].东方法学,2015(3):88—89.
•慈善法专题
主持人语:乐善好施,急公好义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而经济和社会的迅速发展又促成了中国慈善事业春天的到来。然而在法制的轨道上,慈善事业仍面临着诸多窘境。目前,《慈善事业法》已经被列为第十二届全国人大立法规划的第一类项目,并列入全国人大常委会2015年立法工作计划,于2015年10月进行初次审议。与之相关的《基金会管理条例》的修订也列入了国务院2015年立法工作计划。为此,本专题特约请了慈善法领域的三位专家撰文,分别从慈善法的公法化嬗变、慈善组织的税收优惠、信息披露与非营利组织财产权利保障等角度,借鉴域外经验,总结中国国内现状,阐述慈善法发展的趋势和国内立法迫切需要解决的制度设计。希望这组论文能够促进国内对慈善法的关注和研究,并期待一部科学合理的慈善事业法的出台,推进中国慈善事业的健康快速发展。
On Rights to Use Low Altitude Airspace in the Content of Low Altitude Open-up Policy
CHENXuejun
(School of Law, Beijing University of Aeronautics and Astronautics, Beijing 100083, China)
Abstract:Low-altitude airspace reform in China has reached the most crucial stage. At this moment, the reform should change from public management mode to mode of private rights. Establishing people’s rights to use low-altitude airspace will contribute to constraint power of intervention from the government on the one hand; on the other hand will provide a theoretical support to the current reform of “civil-military co-management”. State ownership of airspace is merely a declaratory right in public law. In the sense of private law, it should be considered as equivalent to “public goods” in Roman law. Therefore, rights to use low-altitude airspace are not conflict with the state ownership of airspace.
Key words:low altitude open-up policy; right to use low altitude airspace; airspace resources; state ownership; declaratory right; public goods
中图分类号:DF93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2204(2016)01-0047-11
作者简介:陈学军(1972—),男,北京人,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民商法.
收稿日期:2015-09-23
DOI:10.13766/j.bhsk.1008-2204.2015.0461 10.13766/j.bhsk.1008-2204.2015.05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