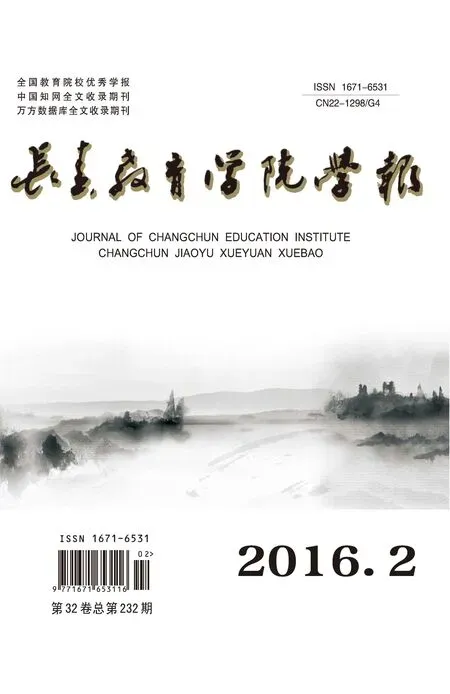重返青年卢卡奇的道路
——评邹之坤《历史辩证法——青年卢卡奇历史唯物主义思想研究》
刘丽红,罗 翔
重返青年卢卡奇的道路
——评邹之坤《历史辩证法——青年卢卡奇历史唯物主义思想研究》
刘丽红,罗翔
摘要:卢卡奇的《历史与阶级意识》被称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开山之作,我们今时重新打开这一文本,重返青年卢卡奇的思想之路,不只是因为其揭橥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逻辑路向,更在于其所敞开的是“走向马克思的道路”。重返不是重复,而是在亟待反思与批判意义上的“重返”。倘若如此,那么邹之坤教授的专著《历史辩证法——青年卢卡奇历史唯物主义思想研究》堪称是卓有成效的一次“重返”,是可资借鉴的学术努力。该著作通过对青年卢卡奇历史唯物主义思想的研究,既予我们以“重返”的方法,又示我们以“重返”的意义。
关键词:卢卡奇;历史辩证法;历史唯物主义
刘丽红/吉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吉林四平136000);罗翔/吉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在读硕士(吉林四平136000)。
卢卡奇把自己的早期著作《历史与阶级意识》看成是其“通向马克思的学徒期”。然而,在人类面临日益严峻生存问题的今天,我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却仍然如青年卢卡奇一样处在“通向马克思的学徒期”。邹之坤对卢卡奇的历史唯物主义思想进行了具有创造性的研究,这不是重复卢卡奇所走的道路,而是在批判意义上的一种重返,对我们理解以及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能够有所启迪。
一、揭示青年卢卡奇的双重“典范”意义
在西方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思想历程间,卢卡奇素被尊为开宗,其要津之位奠立于他青年时期的著作《历史与阶级意识》。诚如马丁·杰指出,《历史与阶级意识》对“西方马克思主义”诸君而言,不啻开山之作、活水之源;倘无此作问世,纷繁复杂的文本则无法聚合统一。[1]它示来者以向度,成为其理论坐标。然而,我们今时重新打开这一文本,重返青年卢卡奇的思想之路,不只是因为其揭橥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逻辑路向,更在于其所敞开的是“走向马克思的道路”。但问题在于,如何重返青年卢卡奇的道路,能否入乎其内又出乎其外,怎样扬而弃之?应该说,“重返”绝非亦步亦趋地“重复”,恰恰相反,“重返”是为了不再“重复”。正是因为在通向马克思的道路上,我们曾一再“重复”青年卢卡奇走过的弯路、歧路、未竟之路,故此亟待反思与批判意义上的“重返”。邹之坤教授的专著《历史辩证法——青年卢卡奇历史唯物主义思想研究》堪称是卓有成效的一次“重返”、可资借鉴的学术努力。该著作通过对青年卢卡奇历史唯物主义思想深入系统的研究,既予我们以“重返”的方法,又示我们以“重返”的意义。
正像20世纪的历史变幻与卢卡奇的人生跌宕,卢卡奇在青年时期思想亦几经转向:由新康德主义而黑格尔主义,终而通向马克思主义。在从黑格尔转向马克思期间,他写出了《历史与阶级意识》。正如邹之坤在《历史辩证法》中所揭示的:青年卢卡奇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一方面试图以马克思来改造黑格尔,即完成马克思所说的对黑格尔辩证法的“颠倒”;另一方面又尝试通过黑格尔来理解马克思,即完成对马克思历史辩证法的理解。然而,他既未完成对黑格尔辩证法的真正“颠倒”,也未实现对马克思哲学的科学理解。邹之坤指出,这一时期的卢卡奇“徘徊在黑格尔和马克思的两条道路之间”,可谓思想的中间物,具有过渡性、两重性的特征。这个歧路彷徨的阶段,凝结为青年卢卡奇的“历史辩证法”,即邹之坤所欲重返的青年卢卡奇的道路。《历史与阶级意识》一书便是这条道路的文字记录,抑或说是对这条道路的文本化,是重返的文本依据。
然而,犹待言明的是,作者为何要重返青年卢卡奇之路,其意义何在,与当代有何切关性?在何种问题意识驱使之下“重返”此路?如果说“重返”是在反思与批判的维度中展开的,那么它所指向的根本问题是什么?《历史与阶级意识》自问世伊始,即饶富争议,未曾或已,各方对它的理解见仁见智,相关评价殊为分歧。显然,邹之坤研究青年卢卡奇的意图,不是为了在众多“理解”中增添一种,亦无意于调解此间的思想纠纷、清点其中的知识账目,尽管这是极为必要的工作,而是为了回应一个更为切要的问题,即如何在当代人类生存状况背景下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基于这一问题意识,他深刻洞见青年卢卡奇具有的双重“典范”意义:一者,“学术典范”;另者,“教训典范”。换言之,面对如何对待并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问题,邹之坤将青年卢卡奇“通向马克思的学徒期”提升至“典范”的高度来认识,希望从中获得应对这一问题的启示。如果说,在广义上,走向马克思主义的当代人皆可视作马克思的“学徒”,势必历经学徒期,走过一段学徒路,那么,路向是否正确、践履是否彻底,对已遭遇或将面临的困境是否自觉等一系列问题,便并非无足轻重。有鉴于此,邹之坤强调,青年卢卡奇所走过的学徒之路,所抵临的境界与陷入的迷津、洞见与盲视,可为今人处理“马克思主义当代化”问题提供宝贵的思路与历史参照。
邹之坤在书的开篇即挑明这样一个问题:尽管当代人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上实绩斐然,但仍未真正逾越青年卢卡奇的学徒之路,有重蹈覆辙之虞,仍受制于青年卢卡奇思想上的两重性,在根本上未摆脱他当年所面临的理论困境。换言之,当代理解和实践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要困境,“仍然是马克思本人所要强烈批判从前哲学的那样一种根深蒂固的矛盾:究竟是解释世界,还是改变世界”[2]5?其中的症结在于,我们“总是与卢卡奇一样,站在黑格尔的意义上去理解马克思”[2]5,尚囿于黑格尔的思辨哲学(解释世界),而未能真正彻底走向马克思的实践哲学(改变世界)。对此,邹之坤做出一个振聋发聩的论断:“马克思与从前哲学的差别,直到当代也从来没有被彻底认清。”[2]5他认为,“我们当代人之所以要重新研究卢卡奇的历史辩证法,其重要意义也就在于,如何真正超越黑格尔,按照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的‘改变世界’的原则来思考当代人类的生存困境”。[2]5在此意义上,邹之坤发现了青年卢卡奇的双重“典范”性,“卢卡奇为我们提供了究竟如何理解马克思哲学、如何理解马克思与黑格尔之间的关系的一个‘学术典范’,并且他所存在的理论困惑也同时构成了对我们来说的‘教训典范’”[2]5。这就是重返青年卢卡奇道路的原因所在,也构成邹之坤整部论著的核心。
二、重建青年卢卡奇思想的整体性
不消说,青年卢卡奇之“典范”意义不会自然显现,亦非唾手可得。对它的充分揭示与深刻领会不能耽于玄想,否则或不得要领,或流于空泛;要具有反复体味的洞察力与高屋建瓴的揭示力,有赖于对“文本的深度耕犁”和思想的整体把握。如果没有对《历史与阶级意识》中众多基本概念的逐一详辨,且在整体上把握概念之间的内在关联,那么此番“重返”势必无功而退。然而,当我们叩开文本之门后,即会面临《历史与阶级意识》似乎不成体系的问题,它并非结构周密、系统完备,而是由8篇论文缀合而成的文集,且各篇的时间、议题均不相同,那么,它们是互有联系的统一体吗?卢卡奇在序言(1992)中一方面称,唯有《物化和无产阶级意识》与《关于组织问题的方法论》两篇是专为这个集子而作,而先前的诸文乃“即兴之作”,并告知读者“不应该指望这些论文有一种系统的科学的完整性”;另一方面又指出,先前的“即兴之作”是后来两篇专论的基础,其“总还是有一定的实际联系”。[3]卢卡奇自己的说法不仅没有使问题变得透明清晰,反而更加扑朔迷离,令人费解。我们究竟能否以及如何把青年卢卡奇的思想作为一个“整体”来理解?这是研究者必须面对的学术难度,也是对研究能力的考验。应该说,邹之坤在《历史辩证法》中准确地揭示出青年卢卡奇的“个人同一性”,有效地把握了他的完整面貌,从而完成了对这条通向马克思的学徒道路的整体观照。
重返青年卢卡奇的道路,意味着重建这一道路。“重建”基于重释,而重释即重构。面对《历史与阶级意识》所涉的多样的概念与问题,诸如“总体性”“物化”“阶级意识”等,邹之坤既非执于一端,只着眼于局部,亦非简单集合,仅做片段拼缀。即是说,不是对它们进行孤立的研究,也不是把它们机械地相加。他一方面将每一概念与问题看作是思想整体中的有机组成部分,并在整体视野下将其分疏,予以具体、批判性分析;另一方面又建立起各局部之间内在的逻辑关联,把它们统合为概念体系的整体。从本质看,重建青年卢卡奇的道路,就是重建青年卢卡奇思想的整体性,此即《历史辩证法》有别于其他相关研究专著之所在。随之而来的问题是,作者如何重建青年卢卡奇思想的整体性?
首先,邹之坤基于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即历史唯物主义的整体理解,对青年卢卡奇思想做总体揭示,即历史唯物主义思想。那么,到底是怎样的历史唯物主义思想呢?邹之坤进一步指出,卢卡奇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抓住“辩证法”及其“历史本性”来理解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因此,“历史辩证法”是卢卡奇对自己所理解的历史唯物主义的根本称谓。故在邹之坤的论述中,“历史辩证法”成为一以贯之、统摄全局的概念。其次,邹之坤分别从“黑格尔主义传统”“总体性”“物化批判”“阶级意识”“浪漫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功能”诸环节梳理了青年卢卡奇的“历史辩证法”思想。也就是说,在他的论述里,“总体性”“物化”“阶级意识”等概念被统摄于“历史辩证法”这一核心概念中,成为各个环节、要素观照的内容。它们是怎样相互联系而统合一处的呢?邹之坤认为,卢卡奇所理解的“历史辩证法”受黑格尔主义影响,在辩证结构上体现出“黑格尔主义传统”。“历史辩证法”由“总体性”构成其生存论基础,此基础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以“物化”为历史事实基础,把人类的历史性生存逻辑理解为历史辩证法;二是以马克思的“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原理为基础,从阶级意识的角度把社会存在结构理解为历史辩证法。它展现为两种基本形态,一方面表达的是人类“生存行动”,即“物化批判”,另一方面表达的是对“生存行动”的“理论自觉”,即“阶级意识”。同时,“历史辩证法”又具有美学意义,即“浪漫主义”。当“历史辩证法”这一思想整体得以确立时,其功能也是整体性的,超越了各局部功能的简单相加。在此意义上,邹之坤对作为“历史辩证法”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功能做出全面阐释。限于篇幅,兹不详述。最后,“历史辩证法”被邹之坤放在卢卡奇的思想总进程中来把握,即超越黑格尔并走向马克思,这不只是青年卢卡奇的道路,也是他一生的思想历程。抑或说,黑格尔与马克思之间的关系构成邹之坤理解“历史辩证法”的总体视角。基于此,可以说,邹之坤在《历史辩证法》中重建了青年卢卡奇思想的整体性,为我们呈示其思想道路的整体图景。
三、对卢卡奇之路的评判与扬弃
重返青年卢卡奇的道路,既须“入乎其内”,又须“出乎其外”。这就要求超越卢卡奇及其著作的主观、内部视角予以客观对待,进行反思性、批判性思考,并做出恰当评价与决定性取舍。惟如此,才能充分揭示其双重“典范”意义,由此我们或步武前哲,或引以为戒。可以说,邹之坤在《历史辩证法》中指明的这种反思性、批判性视野,为我们提供了评判的衡准,指引我们应持怎样的态度对待“历史辩证法”。
如前所述,邹之坤以“历史辩证法”作统摄,重建青年卢卡奇思想的整体性,同时,又将“历史辩证法”纳入卢卡奇的“超越黑格尔,转向马克思”的思想历程中来把握,即是说,黑格尔与马克思的关系是理解“历史辩证法”的肯綮所在。正如邹之坤指出的,对青年卢卡奇历史唯物主义思想的理解,最终集中在对“历史辩证法”的理解上,而对后者的理解又集中在一个核心问题上:“第一,如何看待黑格尔与马克思之间的关系?第二,如何看待卢卡奇对黑格尔与马克思之间关系的理解?”[2]175《历史辩证法》最终以黑格尔与马克思之间的关系来统摄对卢卡奇思想之路的反思,从两者关系的视角来检讨卢卡奇的得失,亦即探讨其双重“典范”的意义。倘若如此,那么对两者关系的正确理解即是我们评价的标准。那么该如何理解呢?邹之坤认为,在根本上,黑格尔与马克思之间是“解释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关系。两者皆关注人之自由的问题,但路向迥殊:黑格尔囿于纯思的、理论的、观念的领域,而马克思则进入历史的、实践的和经济的领域。可以说,马克思哲学是对黑格尔哲学的“颠倒”与超越。但这并不意味着两者全然断裂,黑格尔哲学是马克思哲学的内在环节,后者是前者的完成,两者是互为对方前提的辩证统一的关系,可将其看作是对人类生存自由的理论和实践统一的表达,历史就这样在黑格尔和马克思的张力关系和辩证关系中被实现。
基于马克思的实践哲学立场及对黑格尔与马克思关系的理解,邹之坤断定,卢卡奇作为站在黑格尔和马克思之间的人、思想的中间物,其所理解的“历史辩证法”既有积极意义,亦有消极意义。从积极方面来看,“历史辩证法”对黑格尔与马克思之间张力关系与辩证关系的深刻理解,可资借鉴。卢卡奇能够注意到黑格尔对马克思的积极影响,也试图把辩证法从“概念王国”里解放出来,予以“历史化”,这符合马克思的本意。黑格尔哲学虽造成卢卡奇的盲视,却也赋予他一种洞见,揭示出社会历史的辩证运动形式,这也符合马克思的看法。同时,邹之坤也敏锐洞察到《历史与阶级意识》所生发的“超越黑格尔主义的最有价值的萌芽”,就是说卢卡奇已经注意到应该回到马克思的经济学领域来研究马克思哲学这个重要的理论着眼点。因其尚处萌芽状态,卢卡奇并未真正贯彻,但却为我们通向本真的马克思留下一处可贵的路标,这是卢卡奇对于当代人的“学术典范”意义。从消极方面看,卢卡奇始终处于黑格尔主义的笼罩之下,没能冲破旧哲学的藩篱,对马克思哲学的理解仍陷入一种理论的态度,而非秉持现实的态度。邹之坤提醒我们不要望文生义,尽管卢卡奇也突出了“历史”“实践”的范畴,但对它们的理解并没有摆脱旧哲学的影响,不可能彻底在经济学意义上回到本真的实践概念,这导致其理论必然带有黑格尔的浪漫主义和乌托邦宗派主义的基本倾向。因此,他最终未能从思辨结构中全然脱身,未能彻底超越黑格尔真正抵达本真的马克思。邹之坤强调,卢卡奇距离马克思的这一段距离绝不是细节性的,而是根本性的,也是马克思所要集中批判的旧哲学的“症结”所在。在此意义上,我们应以之为“教训典范”,借镜观形。
邹之坤对卢卡奇“历史辩证法”的理论定位,简要说是通向本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个环节,是对“马克思主义学徒期”的一次总结。他以“扬弃”的态度来对待卢卡奇,既肯定又否定对应着卢卡奇的双重“典范”性。重返青年卢卡奇的道路自然不是为了循环重复,更不是将其轻易打发,而是为了实现对卢卡奇的扬弃,走完他的未竟之路,抵达本真的马克思。惟其如此,才能沿着马克思的路向去思考当代人类的生存困境。
参考文献:
[1]马丁·杰.法兰克福学派史[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201.
[2]邹之坤.历史辩证法——青年卢卡奇历史唯物主义思想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
[3]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49.
责任编辑:丁金荣
中图分类号:B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6531(2016)02-0003-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