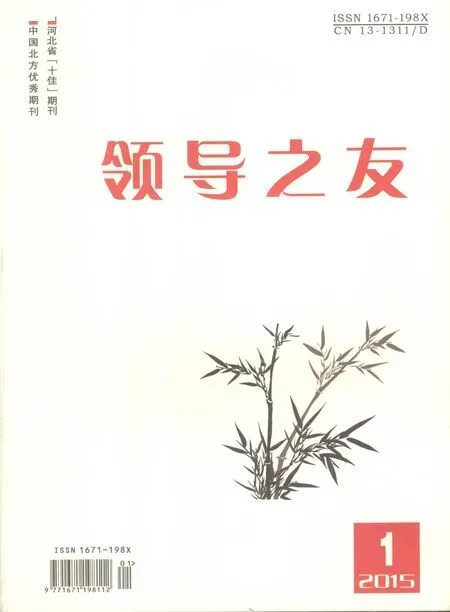京津冀协同发展联合立法的路径选择
肖 辉
(河北政法管理干部学院战略发展部,河北石家庄050061)
京津冀协同发展联合立法的路径选择
肖辉
(河北政法管理干部学院战略发展部,河北石家庄050061)
[摘要]京津冀协同发展作为国家重大战略,必然会涉及中央和地方多方面的社会关系。这些社会关系需要在立法层面加以确认和调整,联合立法机制可有效满足这一要求,其路径选择可通过联合会商、分头立法的方式,也可通过构建统一的联合立法机构行使专门的联合立法权的方式;既可以通过京津冀三地享有立法权的机关协商合作的方式,也可以采用由中央指导或协调、由三地相关机关和部门共同完成的方式;既可以采用不改变现行立法体制的柔性联合立法路径,也可构建对现行立法体制进行适度甚至深度改革的“刚性”联合立法模式。总之,应以有效解决京津冀协同发展为第一要务,充分发挥好立法的引领和推动作用。
[关键词]京津冀;协同发展;联合立法;路径选择
京津冀协同发展联合立法的提出,有其积极而有效的现实意义。在路径选择中,应当首先考虑协同发展的实际需要,这是现实问题,同时还要考虑国家政策和立法层面的要求,这是法治问题。京津冀协同发展作为国家重大战略,其对立法的需求已然十分紧迫,在各种立法模式选择的路径中,联合立法应是最为有效解决这一问题的方式,而在联合立法本身的路径选择中,我们既应从现实出发,积极选择较为可行的路径和方式;同时,我们还要立足于长远,积极探索,大胆创新,创设出更能有效促进三地协同发展的联合立法模式,为其他区域的区域合作立法提供经验和借鉴。
一、京津冀协同发展联合立法的提出
京津冀协同发展联合立法,即对涉及三地协同发展领域的事项,由三地享有立法权的机关通过立法会商的方式协同立法,或由国家主导、三地联合组成立法协商机构就相关事项协调统一后,再由三地按地方立法创制程序同步创设,或直接组成联合立法创设机构,专门就涉及三地协同发展的事项加以立法规制。
(一)问题的提出与历史回顾
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实践及在相关合作领域签署的纲领性文件,为联合立法的提出和实施提供了丰厚的历史经验。先从京津冀三地地方层面的合作与交流看,早在1982年,《北京城市建设总体规划方案》就提出了“首都圈”概念。1986年环渤海地区15个城市成立了市长联席会,使相关区域的合作得到快速发展。1996年河北省全面实施“两环开放带动战略”,进一步推动了该区域的合作。2004年以后,京津冀区域合作进入政府实质性操作阶段①参见田勇:《“廊坊共识”揭开燕赵整合序幕——访河北省省长季允石》,载《中国改革》2004年第7期。,同年2月,《廊坊共识》达成,正式确定“京津冀一体化”发展思路。2010年7月,京冀签署合作框架协议,同年10月,河北省出台《加快环首都经济圈产业发展实施意见》,在规划体系等6个方面启动与北京的“对接工程”。在协同发展上升为国家重大战略之后,三地间签署了若干个合作框架协议,确立了一些相互遵循的规则,为联合立法积累了经验。
再从国家层面看,早在1992年,党的十四大报告就提出了加速环渤海区域的开发和开放,其范围自然包含京津冀三地。2004年《京津冀都市圈区域规划》开始编制,2010年上报国务院。2011年,京津冀一体化发展正式写入十二五规划。2013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2014年2月,习总书记专门听取京津冀协同发展专题汇报并发表重要讲话,京津冀协同发展上升为重大国家战略。2014年政府工作报告指出“加强环渤海及京津冀地区经济协作”,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进入实施阶段。[1]2015年4 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审议通过《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为三地协同发展联合立法提供了重要的宏观政策支持和依据。
(二)现有的经验与做法
从国内情况来看,长三角、珠三角及环渤海区域都在区域合作及协同发展方面作了一些探索,积累了一定的联合创制规则的经验。珠三角,以南方九省(区)与港澳签订的《泛珠三角区域合作框架协议》为基础,达成了近二十个专项合作协议,从而在规则层面解决了本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的需求,保障了本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的顺利运行。长三角,其横跨宏观和微观的会商—决策—协调—执行四级联动的合作运行机制,为该区域的协同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2]京津冀三地,通过高层会商的形式就区域合作问题达成了共识,并签署了若干合作框架协议,特别是在地方性法规协同创制方面,取得了一定的突破。河北省人大常委会与北京、天津两地的人大常委会联合出台了《关于加强京津冀人大协同立法的若干意见》,建立了三地轮流负责的协同立法组织保障机制和协同立法机制。[3]应当说,这一做法意义重大,直接开启了三地间就协同发展事项进行联合立法的机制,可以为三地协同发展提供更有效的法律保障。从以往的做法来看,不管是长三角经验,还是珠三角方式,包括环渤海地区的做法,多是政府间的合作,常常通过政府文件和规章的形式加以规制和实施,从长远看,由于缺乏地方性法规层面的介入,其稳定性、长期性及利益协调的保障性都会存在一些欠缺。
(三)京津冀协同发展应该选择更加刚性的联合立法路径
京津冀区域与珠三角、长三角地区不同,三地间在发展阶段和发展水平方面落差较大,以发展阶段为例,三地分别处于后工业化、工业化和正在走向工业化三个层级不同的阶段,可以说属于“高地”与“洼地”并存;三地浓厚的行政文化色彩与长三角、珠三角的市场经济文化差别明显。但是,三地具体功能区的界定,为三地协同发展一盘棋提供了直接的政策依据和路径导向,那么,简单的沟通和交流难以适应三地协同发展战略的要求。因此,应当建立更为紧密的联合立法模式,选择更加刚性的联合立法路径,以强力的规则保障的方式推动和促进京津冀协同发展目标的实现。
二、京津冀协同发展联合立法的实施路径
在京津冀协同发展联合立法的路径选择中,应当界定好三地之间及三地与国家之间的相互关系。京津冀协同发展作为国家重大战略,已经不是简单的地区性问题,也不是普通的区域性问题,而是涉及国家整体战略的大问题,因此,在确立联合立法的路径中,必须充分考虑国家政策与法律层面的要求,必须在国家政策和法律的引领下,强调联合立法的必要与地位,选择好相应的方式和路径,确保联合立法的顺利实施。
(一)京津冀三地相互之间的合作路径与方式。
该路径的联合立法由京津冀三地享有立法权的主体负责组织和实施。就当前的经验和做法来看,主要有以下两种形式:
1.构建协商平台、建立会商机制的路径形式。在我国相关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中,通过构建协商平台、建立会商机制的方式实现共同规则的联合创制,是一种相对较为简便的路径和渠道。其优点是简单快捷,不改变也不影响现行的立法体制,在权力运行方面也没有实质性的突破,一般不会涉及国家立法层面的要求,因此简便易行。
2.各自选派代表组成联合立法会商机构的路径形式。这种路径形式与上述做法的区别仅仅在于是否成立专门从事联合立法协调和会商的机构形式。该协调和会商机构既可以是短期的、临时性的,也可以是长期的、相对固定的。有了这样的工作机构,在联合立法的信息沟通和交流、调查与研究,以及联合立法规范性文件的论证和起草等方面就会做得更加到位,也更为常态化。当然也有变通的形式,即通过共同规定的形式确立由相关各方轮流负责的方式,虽不新设专门的联合立法机构,但在轮值机制中,客观上保障了在联合立法层面对于机构设置常态化的需要,是机构存在的变通形式。
以上不管哪种路径形式,由于本身并未对现行的立法体制或机制做出任何改变,也未使现行的组织机构形态在制度层面发生变化,京津冀三地之间通过各自积极的沟通、交流即可实现,通过自主协商、会商机制就可达成,无须外部和国家层面的介入,因此,实施起来相对简便,也更容易实现。其不足之处,一是立法的效力不足,当与三地间各自的地方性规范性文件发生冲突时,难以凭借规范性法律文件本身的性质直接确定其适用效力;二是最终还需通过三地各自享有立法权的机关分头创制,不仅在节省立法成本、合理配置立法资源方面明显不足,而且也有重复立法之嫌,立法效率相对较低。
(二)中央与地方结合的路径和方式
这一联合立法涉及的领域,主要是在三地容易得到认同而又超越三地地方范围或超越三地立法权限,单纯由三地合作难以实现和完成,需要上升到国家层面的立法项目。大体可归类为如下三种联合立法的路径和方式:
1.由国家制定京津三地协同发展的基本法,在基本法指导下,三地各享有立法权的机关对协同发展中需要立法统一规制的事项进行联合协商、协同立法的方式。这一路径和方式不会影响现行的立法体制,其范围为中央单一主导的情形,是在京津冀协同发展中“专属中央立法的事项或需要中央出面协调制定统一规划和标准以及建立统一协调机制的事项。”[4]《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是指导三地协同发展的纲领性文件,从法治的角度来看,还应制定京津冀协同发展方面的基本法,以立法形式保障纲领性文件的实施。根据我国立法法规定,全国人大应从宏观角度来协调跨省市的立法事项,因此,该法律文本应在全国人大的主持下制定,或直接由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
2.由中央及有关部门(部委)主导,京津冀三地相关部门共同参与的联合立法方式。这种联合立法的形式,主要是在生态环境保护等自然环境领域或公共服务产品等领域,需要由国务院有关部委牵头或领导,京津冀三地共同编制相关的政府规章或地方性法规。
3.三地共同协商确定统一规则后,提请国家立法机关或中央政府予以确认。这里主要涉及的还是环境和生态保护领域的问题。当然,在产业对接、公共服务产品等领域也可根据需要提请国家层面的确认。如,平等的受教育权的保护问题仅靠三地地方自身的努力还难以实现,客观上需要借助于中央政府教育主管部门的职能方可落实。
(三)建立京津冀协同发展联合立法机构的路径形式
1.设立专门的创制三地间协同发展领域的地方规范性法律文件的机构。需要注意的是,这里所谈的联合立法机构,和前面所讲的联合立法协调或会商机构不同,前面所讲的机构是为联合立法提供服务的组织形态,无论临时性的,还是常设性的,都只是在信息交流、立法调研、规则起草等方面从事辅助性工作,本身并没有立法权,不是立法机构,更无权创制为三地协同发展所需要的规范性法律文件。而这里所谈的联合立法机构,本身即拥有立法权,直接创制具有法律效力的规范性文件,是严格意义上的“刚性”联合立法形态。
2.对现行的立法体制和机制进行适当调整,赋予该联合立法机构以独立的立法权限。由于该种联合立法形式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现行的立法机制,并且赋予联合立法机构以实体立法权的做法也对现行地方组织法提出了修改要求,以明确其立法职权和地位,确立其所创制的法规文本享有更高等级的效力。因此,可称之为紧密型联合立法模式或称“刚性联合立法模式”的路径和方式。[5]
3.简要评析。此种形态的联合立法路径和方式,一是有利于更好地实现和保障三地协同发展的立法目的,实现三地地方事务的自主性表达;二是有利于降解国家立法的负担,减少国家层面不必要的干预,实现地方各主体的直接利益表达;三是有利于减轻三地传统行政文化浓厚的惯性思维,真正实现三地协同发展中各类要素的自由流动,以实现资源的市场化调节;四是有利于科学界定三地在协同发展中的功能定位,确保各自的功能定位清晰明确,并能得到充分发挥;五是有利于提高三地在协同发展中联合立法的效率,降低立法成本,避免重复立法;六是有利于提升京津冀协同发展联合立法的效力等级,使联合立法的规范性法律文件及其所创设的规则更加权威,更加有效。这又反过来有利于从新权威主义的立法权限层面打破三地间长期存在的基于行政差异所导致的行政壁垒,从更高权威的法规层面最大限度地排斥行政因素的干扰,使各种市场元素能够在三地间自由流动,从而有助于市场经济文化的形成,进而建立三地统一完整、没有阻隔的市场,确保三地在差异性和互补性的协同发展中真正成为一盘棋,在各自功能定位的基础上,实现优势互补,协调发展。
当然,由于该种路径直接关涉现行的体制和机制,需要在法律等方面作出较大的调整,属于深度改革的领域,短期内尚难以实现。但尽管如此,它也应该成为在京津冀协同发展中最理想的联合立法模式,是联合立法的最佳路径和选择。
三、结语
法律的保障总是强有力的,特别是在依法治国的今天,京津冀协同发展更是离不开法律的确认、规制和保护。联合立法可以最大限度地满足京津冀协同发展对于法律规则的需求,而其中路径的选择又是至关重要的环节。在京津冀协同发展的不同时期和阶段,选择恰当的路径和方式,当是长久的课题。
[参考文献]
[1]魏进平,刘鑫洋,魏娜.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历程回顾、现实困境与突破路径[J].河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6).
[2]周宵鹏.京津冀人大协同立法重大项目联合攻关[N].法制日报,2015-05-05.
[3]薄文广,周立群.长三角区域一体化的经验借鉴及对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启示[J].城市,2014(5).
[4]常敏.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法律保障制度研究[J].北京联合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5(4).
[5]肖辉.关于京津冀协同发展联合立法的构想[J].河北学刊,2015(6).
[责编校对:赵哲]
Path Selection on the Joint Legislation in the Collaborative Development of Beijing, Tianjin and Hebei Province
XIAO Hui
(Office of Strategic Development,HebeiManagement College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Cadres,Shijiazhuang050061,China)
Abstract :As a national strategy, the collaborative development of Beijing ,Tianjin and Hebei province will in⁃evitably involve many aspects of social relationship from central and local governments. These social relations need to be confirmed and adjusted at the legislative level and the mechanism of collaborative legislation can meet this requirement. The path can be chosen by joint consultation and separate legislation as well as joint leg⁃islation system to exercise special joint legislative power; The path also can be established by cooperation through legislative agencies of Beijing , Tianjin and Hebei province or joint completion by three relevant institu⁃tion and departments guided and coordinated by central government. The path can adopt a flexible joint legisla⁃tive path without changing the existing legislative system and it also constructs a rigid mode of joint legislation from moderate and deep reform to the current legislative system. In short, it is the first priority to effectively solve the collaborative development of Beijing, Tianjin and Hebei province and completely play the leading and driving role of legislation.
Key Words:Beijing, Tianjin and Hebei Province;collaborative development ; joint legislation;path selection
[中图分类号]D9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198X(2016)01-0065-04
[收稿日期]2015-12-10
[作者简介]肖辉(1966—),男,山东省郓城县人,河北政法管理干部学院教授,主要从事法理学和立法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