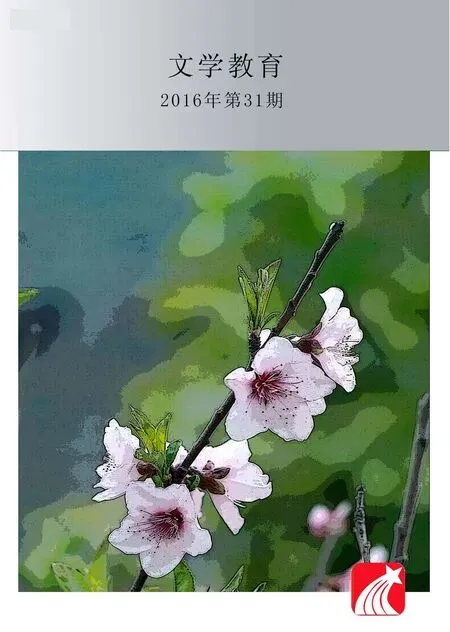德国战后文学中的“记忆话语”
刘海婷
德国战后文学中的“记忆话语”
刘海婷
“问责”与“反思”是二战后德国文学中的两大关键词,但这种自我批判的态度也并不是自然而然地产生,它总是受到时代历史话语的影响。本文试图从“记忆话语”的视角为德国战后文学清理出一条线索并将其发展大致分为三个阶段。通过对这三个阶段重要作家和作品的简要分析勾勒出德国战后文学的图景。
德国战后文学 记忆话语 反思性回忆
回忆历史是一个建构的过程,而不是恢复的过程。对历史的建构虽然必须依托存在于话语、文字和脑海中的“记忆”,但它很大程度上不是对过往事件的简单还原和重现,而更像是一种“杜撰”的对过去的编排,是“按照社会结构、意识形态、政治来进行的一种编排”。[1]在建构最近一个世纪的历史过程中,两次世界大战以及由第三帝国独裁政府导致的大屠杀不仅深刻地影响了世界格局,也对后战争时期不同国家和社会在处理历史记忆与历史叙述的问题时提出了严峻的考验。无论对负有战争罪责的“施害者”或是在战争中遭受灭顶之灾的“受害者”而言,如何在后战争时期建构对战争和大屠杀灾难的历史记忆都是一个紧迫且棘手的问题。
在国家政治话语之外,以文学方式书写的记忆一方面因无法剥离个人记忆与集体记忆的双重规约而具有更加多元的解读空间,另一方面相对国家政治话语的单一和固定,它也可以为建构历史记忆提供更多的可能性。根据笔者目前对二战后德国文学在处理战争与大屠杀记忆方面的浅陋观察,虽然“问责”与“反思”这两个最突出的关键词反复成为众多文学作品的主题,但是这种自我批判的态度并非“自然而然”,它总是受到时代历史背景的影响。笔者试图从“记忆话语”的视角为德国战后文学清理出一条线索并将其发展大致分为以下三个阶段:
一.战争结束初期(1945-1952)至1959年为“战争记忆的直观书写”期
以“废墟文学”为代表的文学作品主要揭示了战争带来的凋敝和创伤、返乡战士的无望以及普通民众流离失所的痛苦生活。[2]如君特·埃希的短诗《盘点》以毫无修饰的简练语言展示了被释放战俘贫乏的财产清单,对所剩无几的基本生活品的简单确认触及到却是战后初期最严峻的问题——生存。另一位代表性人物沃尔夫冈·伯谢特属于高中毕业后即应招入伍被送上战场的青年一代,他的返乡剧《在门外》揭示了返乡士兵面对一个被破坏殆尽的世界时的无望和无奈,像他这样的返乡者已经无法在社会中找到自己的位置。
这一时期的文学作品在回顾刚刚过去的历史时以直观地反应个体在战争中的经历及揭示战争带来的残酷后果为主,这或许与这一时期西德政权“避免反思战争,声称其脆弱的民主无法承受纳粹时代的真实记忆”[3]有关。整个50年代,回避甚至压抑反思历史罪责的态度才是时代的主流。
二.1959年至70年代末期为“对战争的反思性回忆”期
这一时期,文学的政治化倾向日益明显。[4]特别是60年代末期,“民主”和“正义”要求德国人不仅要记住而且要批判德国负有的战争及大屠杀罪责。在此背景之下,清算父辈在纳粹时期的罪行、反思纳粹历史的文学作品凸显出来。
自1959年格拉斯的《铁皮鼓》、伯尔的《九点半的台球游戏》和约翰逊的《对雅各布的种种揣测》问世以来,沉默被打破,反思和批判二战成为文学主流。因此可以说,1959年是划分德国战后文学从压抑记忆到进行回忆和反思转变的“关键的一年”,此后将近20年时间内产生的重要文学作品拒绝回避历史。伯尔作为这个时代的批判者,他的重要性尤其体现在他以经历过第三帝国及二战并且存活下来的一代人的视角精准地唤起了读者对战争的记忆。在清理对过去的记忆方面,格拉斯比伯尔做得更加深入、全面和持久,自《铁皮鼓》以来,“回忆”无一例外地贯穿了他所有的小说。
由这两位代表作家可见,这一时期作家们承担的文学使命是:用回忆坚决而有力地打破由财富堆砌起来的虚假华丽外墙,揭示掩盖在社会光鲜外表之下的、曾一度被视为不可触碰的“禁忌”的历史真实。伯尔、格拉斯和约翰逊以及追寻他们脚步的其他作家“联合起来抗拒社会集体抑制记忆的漩涡……他们的作品以受到道德驱使的‘克服过去’为主题,这样的‘克服’比战后初期匆忙完成的去纳粹化仪式要困难得多。”[5]
三.80年代以来为“对战争的双重反思与多维度记忆”期
随着“68”一代作家的成熟,回忆和反思德国历史的文学作品带有双重反思的印记并提出了新的记忆视角和维度。在这种双重反思的视角下,70年代末/80年代初期西德文坛出现了一股“父亲文学”潮流,“父亲”突然掇升为了这一时期文学的中心主题。这些作品大多以个人生平和家族历史为回忆的主线,在追问父亲罪责的个体记忆与集体记忆的张力场中探讨了如何看待历史罪责以及如何寻求自身身份认同的问题。
自90年代以来,家庭小说或代际小说的出现和流行也许并不是一个偶然的事件,两德重新统一的重大历史转折或具有激发回忆的功效,不仅一些成名的作家如乌韦·蒂姆、汉斯·乌利希·特莱谢尔和马丁·瓦尔泽等在90年代后期及2000年左右发表的作品中回顾了家族历史及自身的成长历程,一些新晋作家也围绕此主题创作了文学作品。除了站在重新统一的起点上再次回顾历史的兴趣之外,历史学家哈拉尔德·韦尔策指出,家庭小说或代际小说之所以在德国如此盛行正是因为他们较之对纳粹大屠杀及其他罪行的官方话语更加接近普通公民的“感受史”。具体而言,二战结束后两个德国的公民分别受到占领国意识形态的影响被迫接受了“施害者”或“抵抗者”的角色,但这样的角色安排与大多数人在第三帝国和战争时期的感知并不相符,事实上,更多人经历的是“损失”而非“加害”或是“抵抗”。
战后的两德时期,政治话语将不能公开讨论的德国人受害记忆挤压到个体或个体家庭的层面,受害记忆通过家庭的日常生活和交流被传承下来,而文学作为存储和传播个体记忆并使之进入集体记忆领域的媒介为被压抑的受害记忆和受创经历提供了释放的空间。90年代后期出现的家庭小说等以家族历史为背景的文学作品在个体记忆与集体记忆的张力场中重新唤起了大多数人的创伤记忆并以此开启了回忆纳粹历史时新的回忆视角,因此也就不难理解为何家庭小说在回忆家族历史时涉及到了长久以来被压抑甚至被视作禁忌的德国人经受“灾难”和“损失”的话题会引发强烈的共鸣。
四.结语
通过对德国战后文学中“记忆话语”的简要梳理可以看出,无论在哪一个阶段,文学中的记忆话语始终与政治公共话语相勾连,甚至在政治话语对历史罪责进行回避和压抑的阶段,文学作为承载和传播个人记忆的媒介能够率先承担起唤起人们进行回忆和反思的责任,从而使个人的回忆进入到集体记忆的领域,又随着时代和政治的变化逐渐扩展、加强并且形塑德国民众对纳粹历史和战争的记忆,可以说,文学是战后德国历史记忆话语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积极参与了历史话语的建构,在战后每一个重要的历史转折点上,文学不仅是政治话语变革的反映者,也是推动者。
[1]雅克·勒高夫.历史与记忆[M].方仁杰/倪复生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
[2]Volker Wehdeking/Günter Blam berger.Erzhlliteraturder frühen Nac hkriegszeit(1945-1952)[M].München:C.H. Beck,1990.
[3]劳拉·赫因/马克·塞尔登[编].审查历史—日本、德国赫美国的公民身份与记忆[M].聂露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2.
[4]Wolfgang Beutin/Klaus Ehlert /Wolfgang Emmerich/Christine Kanz/B
ernd Lutz/Volker Meid/MichaelO-pitz/Carola Opitz-Wiemers/Ralf Schne ll/Peter Stein/Inge Stephan.Deutsche-Literaturgeschichte.Von den Anfngen bis zur Gegenwart.[M].Stuttgart/Weima r:J.B.Metzler,2008.
[5]Wilfried Barner(Hg.).Geschichte der deutschen Literatur von 1945 bis zur Gegenwart.2.erw.2006 [M]. München:C.H.Beck,1994.
[6]Harald Welzer. Schn unscharf. ber die Konjunktur der Familien-und Generationenromane.In:Literatur“.Beilage zum Mittelweg 36.1 Januar/Februar 2004[J].
(作者介绍:刘海婷,博士研究生,四川外国语大学德语系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