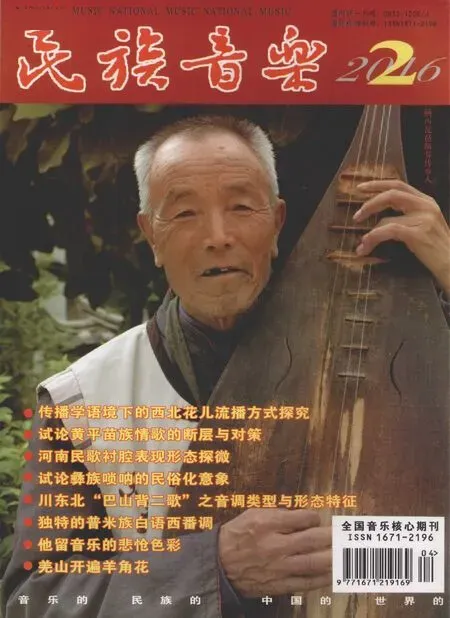论音乐典型性与音乐创作技巧的关系
周刚兵(大理大学艺术学院)
论音乐典型性与音乐创作技巧的关系
周刚兵(大理大学艺术学院)
音乐艺术,正如黑格尔所说:是“心情的艺术,它直接针对心情”①,也正如我们的祖先所云:“夫音生于人心,心惨则哀,心舒则和。然人心复因音之哀、和而舒、惨。”②这里,他们不约而同地道出了音乐艺术的美学特质之一:就是它的表情性或感情性。
音乐的表达是无影无形的乐音,它直接诉诸人类的听觉器官。生理学和心理学以及古往今来无数的音乐实践告诉我们,这种艺术语言不能提供明晰的概念和形象,它更多的是源于人们对现实生活的感受,体验即黑格尔所说的“心情”,直接打动人们的内心世界,使人们在“情动于中”时浮想联翩,通过情感的审美的波动起到伦理的社会作用。
音乐家在深入生活中,“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③,他们面对着丰富多彩的现实生活,感情洋溢,体验充沛,激发着音乐灵感,尔后以精湛的音乐技巧组织乐音“摹写”“描述”他们的心情,“音乐只反映出作曲者对一定的具体的题材契机的情感关系”④,“感受多于音画”⑤;而听众则从乐音结构的各种运动形态中体验到与作曲者相类似的感情,受到感动,领略到音乐美所反映的生活——感情美,从而在与作曲者的感情产生共鸣时激发视觉的、语言的等等联想,接受作曲者对于生活的感情态度,受到教育。音乐艺术的现实主义创作原则在与他种艺术相类比时是否可以这样来表述,即“再现典型环境中千差万别的富于个性的典型情感”。
情感是人类的精神现象,它不像其他客观事物那样具体。一般说来,它是最不概念化的东西。美术家只能通过描绘具体的视觉形象来“暗示”,间接地表达某种蕴含在被描绘客体中的感情因素,可他却不能描绘情感本身(就是抽象绘画也是如此,因为归根结底,它们都是静止不动的),文学家只能通过现实生活的逻辑运动来叙述感情和它的语言概念,也不能直接地描写感情本身。
在这方面,只有音乐得天独厚,它能通过时间中相类似的乐音运动状态来直接地“模仿”“摹写”感情本身的运动状态。(至于音乐运动与情感运动这种美学上的联系“中介”,我们曾在一篇论文中详加探讨,见《音乐研究》1984年第2期孙川的《试论音乐与人类情感的联系方式及其审美基础》一文。)
从音乐的这个美学性质中我们可以初步看出技巧的重要性,感情是无影无形、难以名状的,乐音也是如此,作曲者如果没有掌握感情运动与乐音运动的这种有机联系,他就不能胜任地驾驭自己的生活体验,不能把自己的感情纳入乐音运动的规律中,也就无从去用音乐再现个性化的典型感情了。
如何掌握这种联系呢?显而易见的,他得从第一个音符学起:学会一种全新的表达方式——音乐语言,他必须掌握这种语言的特殊技巧和技术。
这就接触到音乐的另一个美学性质,即:由于它的艺术原料是无影无形的乐音,而乐音本身就是人类精神的产物,所以它是“最精神化”的艺术。按汉斯力克的说法,音乐艺术的材料并不直接存在于现实生活中。在自然中,它并没有任何“样本”⑥,音乐的样本就是音乐本身,一个美术家如果“登山”“观海”激发了灵感,他会情不自禁地拿起画笔去描绘“山”和“海”,把自己的感受凝聚在画面上,这“山”和“海”就是他的样板。文学家处在同样情形,他是用我们大家都熟悉的语言来叙述感受,用概念来叙述“山”和“海”的形象,那么“山”和“海”情状的概念就是他的样本(当然,语言也是人类精神的产物,但它已成为人类的“本质力量”⑦之一,文学家无须再去掌握一种全新的表达方式来创造艺术)。
而音乐家在“登山”“观海”时感情充沛,他要抒发他此时此刻的感受,音乐的激流在他的胸臆中奔突回转,音乐的音响表象在他的脑际里轰鸣。这样,音乐的灵感,既不是“山”和“海”的具体形象也不是它们的概念,而是一种乐音运动,与被“山”和“海”的壮观所激发的“心情”的运动状态有着某种相似的乐音运动状态。这些灵感的样本就是这音乐表象本身。同样,如果激发作曲者灵感的现实事物不是“山”或“海”等自然景观,而是某一社会事件和人物,那么反映到他脑际的也不是这些事件和人物的形象和概念,而只是与这些事件和人物给予作曲者感情上的感受体验的运动状态相类似的乐音运动状态。
马克思说:艺术的“生产不仅为主体产生了一个对象实休,而且也为对象实体产生了一个主体”⑧。对于音乐艺术来说尤其是如此,无数音乐实践不仅产生了音乐艺术的对象实体——音乐作品,而且音乐作品也制约着音乐思维的发展,产生着主体——按音乐艺术规律亦即创作技巧而思维和创作的作曲者。也就是说,作曲者的思维活动是被一种特殊的形象思维形式——音乐思维支配着,他的体验意识已经在不自觉中化为音乐意识了。正是在这里,我们看到音乐技巧对形成音乐灵感起着多么关键的作用。
轰鸣在作曲者脑际的音乐音响表象是无数音乐实践的丰富产物——音乐作品的音响在他音乐意识,记忆和经验中的灵感结晶,他胸臆中的音乐流的状态与他此时此刻的情感动态悠然契合,这一点是他的音乐修养和经验所决定的。因为如前所述,音乐在自然界,并无“样本”。无数音乐作品在表现“登山”“观海”以及相类似的感情运动时所呈现的音乐基调一般都大同小异,颇有共性。这些音响运动已经成为作曲者在类似情绪中的音乐思维经验了,这些音乐经验和记忆才是他的音乐灵感的样本!
而更重要的是:这些样本总是以明确而色彩鲜明的技巧因素为标志的:调式调性、速度、力度以及和声、复调、旋律旋法等技巧因素的音响效果叩击着作曲者的心扉,他情不自禁的、自觉不自觉地选择适合于表达彼时彼刻情状的技巧因素,浑然一体地形成自己的灵感,飞出心房……可见,作曲者不能像一般听众那样任音乐记忆和经验在脑际中自由驰骋,他需要在生活感受高涨时下意识地分解音乐经验和记忆中的技巧因素,再下意识或有意识地把它们综合成他自己的音乐灵感。
这样说来,他如果没有一定程度的音乐修养、没有对于繁复的技术技巧的一定掌握、没有对大量作品做过感性或理性的分析,他就不可能具备真正的音乐意识;音乐作品的音响经验也不能化成他自己的音乐思维。在深入生活中,无论生活使他多么感情洋溢、多么体验丰富,他的感受和激发的灵感也许是美术的、文学的,可就不是音乐的。也就是说,他的生活感情和体验由于他不具备相应的音乐技巧水平从而不具备相应的音乐意识和思维,而不能自然流露为“音乐灵感”。这是音乐艺术的客观美学特殊性质所决定的。
在着手进行创作时,技巧的运用就更带有决定性意义了。作曲者深入生活,他是置身在特定的“这一个(黑格尔语,指具体的、个别的、确定的对象)环境中,他所体验的是他自己的“这一个”具体的感情。这时如果他所掌握的音乐修养和技巧水平,仅仅刚够激发他的音乐灵感,即仅仅刚够使他人或以前的音乐作品的音响表象化为他自己漫无章法的音响表象,那么这个音乐灵感还远不能把“这一个”环境和对于这环境的“这一个”感情体验加以典型化的概括,还不能使灵感富于个性。所以他即使写出作品来也很可能流于公式化、概念化、庸俗化,不可避免地要淹没在同类作品的汪洋中。
如果作曲者渴望去再现他在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感情,别无窍门,他只有运用相对他自己“这一个”感情运动状态来说是最恰如其分,也就是最有特色的典型音乐技巧,调动一切技巧因素把乐音加以典型的组合,这样才能如愿以偿。而这种艺术功力不言而喻绝非一蹴而就,单凭经验和感觉所能具备的。作曲者必须经过积年累月的、孜孜不倦的技术学习和技巧锻炼,必须对大量音乐作品做技巧上的分析、借鉴的功夫。在这“精益求精”的“苦行”中,作曲者把音乐技术这个“对象实体”融会贯通地消化在自己的精神中去,使自己习惯于以精深的音乐意识和思维来概括对生活的感情体验、习惯于用纯熟的音乐语言来表达这种概括。
从心理学上讲,这意味着技巧技术的学习和锻炼使作曲者在头脑中建立了音乐意识与现实生活感情体验之间的系统的、巩固的条件反射关系(这种条件反射就是前面说到的感情运动:状态与乐音运动状态那种联系“中介”)。它往往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很多音乐家也不能用语言来阐明这种联系的过程和方式。因为—我们反其意而套用汉斯力克的话来说—就是纯粹“音乐式的事物”⑨,只有通晓乐律的人才能体会得到。这种条件反射有待于生理学、物理学等自然科学精确的验证。
音乐技巧诸因素的美学性质是瑰丽多姿、各具千秋的:诸如调式调性的气质特点,和声的功能性和色彩性,节奏、速度和力度的表情特性,旋律旋法的无限可能性和巨大的感情造型性,各种曲式结构的逻辑特性,复调音乐表现力的立体性、音色的丰富表情性等等。在形成灵感以后,把握着这一切深湛浩繁的技巧因素,作曲者通过精深的技巧锻炼而建立的“音乐式”的条件反射,面对着自己的、与众不同的“这一个”生活感情体验,他可以“呼之即来”地持各种技巧因素在音乐的意识中调动起来,通过音乐修养(包含在上述条件反射中的音乐审美观)的鉴别、比较,最后选择了在借鉴、分析他人技巧和整理,提高自己原有技巧基础上推陈出新的、与“这一个”感情体验悠然契合的“这一个”典型技巧语汇(看似偶然,实则必然),尔后如“庖丁解牛”一般得心应手地处理灵感,发展主题创造出再现典型环境中典型个性感情体验的,与众不同,焕发着新的音乐美的“这一个”典型化、个性化音乐形象。这是一切优秀音乐作品的首要标志。
正如在文学中讲究“诗眼”的技巧,在美术中讲究“画龙点睛”的技巧一样,对于最不实体化(即最精神化)的音乐艺术来说,如果作曲者没有通过精深的技巧锻炼建立起“音乐式”的条件反射,面对着有声有色的生活感情体验他就不可能在无影无形的乐音迷雾中,恰恰“想起来”,必然地选择“这一个”典型技巧语汇恰如其分地表现他自己独具特色的“这一个”感情体验。
我们的结论是:在音乐艺术中,内容的典型性与个性常常与形式的典型与个性是同一的、二位一体的,只有纯熟精深的创作技巧才能产生典型化、个性化完美结合的优秀作品,这是音乐艺术的客观美学特殊性质所决定的。
为了说明问题,我们不妨列举一些古今中外著名优秀作品,对它们做一极浅显简略的技术技巧分析,以此证明一下我的论点。
在脍炙人口的《小夜曲》中,舒伯特运用了以d小调为基调,中间插入同名D大调的调性调式对比手法。这个手法用得非常精当。如果舒伯特没有掌握好转调的技巧(比如和声连接的技术),或调性色彩的音乐意识不深刻的话,他很可能使d小调一鸣到底,只求其缠绵的情调而顾不到调性调式对比的音乐美,或者很可能由于技巧不精而使用近关系转调,或在转调时和声连接不佳,这样一定破坏了这个小品的感情状态。在这里舒伯特就是选择了典型的调性调式对比技巧,再现了《小夜曲》歌词所提供的典型的、忧郁的、深情而略见起伏的感情状态。有个性特色的典型技巧的运用使它格外隽永、优美,赢得了全世界人民普遍的喜爱。
肖邦的钢琴曲以细腻的织体,丰富的音色变化,尤其是清新的和弦外音而著称。这些特色表现了在那一个特定时代,民族环境中肖邦对生活的典型感情和气质。如果肖邦对和声技术没有纯熟的掌握,和声色彩的音乐意识不深刻的话,他不可能“想起来”用丰富善变的和弦外音来处理音响色彩而又使其不失功能性,而没有这种典型的和声色彩的运用,就表现不出肖邦典型的情感体验,也就体观不出“钢琴诗人”的鲜明个性了。
苏联歌曲《风之歌》是一首很有特色的作品。杜那耶夫斯基在这里寻觅到了表达歌曲那种乐观主义精神,那种坚忍不拔、朝气蓬勃的典型感情状态的技巧手段——贯穿全曲的八分附点节奏型。当我们唱它的时候不由不被它所感动,不能不感到这个技巧手法是颇具典型化和个性化的作用的。显然,这也是技巧技术的典型化、个性化的运用所带来的音乐美。这个技巧特色使这首歌在乐坛中获得了充分的个性地位,人们一经上口就难以忘却它。
我国民歌《蒙古小夜曲》,它的主题异常简练,只有一句,而且旋法极其质朴。但在整个一个单三部结构中,这一句主题极尽扩展,压缩变化发展了自己,从旋律旋法的无限可能性中找出了一种典型的,集中发展主题的手法,贴切地表现了内蒙古大草原之夜那种典型的寂寥、单调的情调。这首质朴的民歌体现了我国民间音乐良好的技巧传统。如果没有运用这种典型化的技巧,而是像通常的民歌那样:去发展主题,肯定收不到如此凝练的艺术效果,这首歌也就不能成为如此富于个性的“蒙古”小夜曲了。
俄罗斯作曲家穆索尔斯基的钢琴组曲《图画展览会》中《两个犹太人》一曲,典型的自由对比二声部复调为我们展示了贫富强弱对比异常尖锐鲜明的两种情感状态:上声部短时值的同音反复刻画了贫穷者瑟缩发抖,胆战心惊的典型感情运动状态,下声部则比较宽时值和音程的进行表现了富有者趾高气扬,蛮不讲理的典型感情的运动状态。如果作曲家没有深刻地理解复调音乐表现音乐形象的立体性、丰富性,或没有掌握好诸如节奏的补充穿插、音程的良好结合及富于动力性和外音解决进行等复调写作技术,他既不能偏偏“想起来”选择如此恰如其分的典型技巧来表现作品的个性特色,也不能在复调写作上收到如此圆满的效果。
如果贝多芬没有在他深湛浩繁的音乐实践中形成了对音乐逻辑结沟的深刻理解和博大精深的交响思维,或没有魄力非凡的组织曲式的技巧,他就不可能在辉煌、宏大的不朽巨作《第九交响乐》末乐章中实行无比大胆的推陈出新——加入声乐部分。而如果没有这种充分典型化、个性化的技巧手法的大胆运用,就不能淋漓尽致地表现出作品“一切人们都结为兄弟”这个典型的神圣、欢乐的感情状态,以及由这种感情状态所表现的深刻的人道主义思想,从而也就不能使这部伟大的作品以超凡入圣的伟大个性而成为千古绝唱。
例子是不胜枚举的,对于我们的论点来说,真可谓“人耳皆碑”。我们之所以这样反复地论证无非也是想不厌其烦的强调:如果不自觉地、刻苦地、大胆地提高技术和技巧水平,就创造不出典型性与个性完美结合的优秀作品来,就不能尽快地适应现代社会对我们音乐事业的要求。
这篇文章就算是听众对优美动听,具有真正的、长久的音乐艺术美的优秀音乐作品的一点衷心的呼吁吧!
注释:
①黑格尔:《美学》第三卷。
②(唐)杜佑:《通典·乐序》。
③(南朝)刘勰著: 《文心雕龙·神东篇》。
④[波]卓丽莎:《音乐学问题》第99页,(人民音乐出版社)。
⑤参见《贝多芬札记》,人民音乐出版社。
⑥参见(奥)汉斯力克:《论音乐的美》第98页。
⑦参见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第78页。
⑧参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第二卷第95页。
⑨参见汉斯力克:《论音乐的美》,人民音乐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