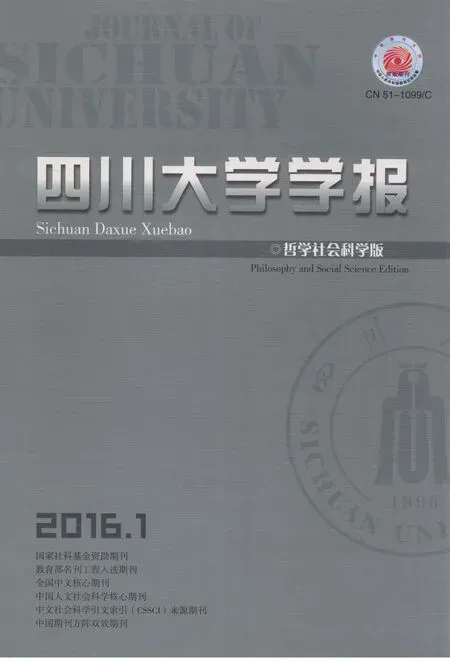苏轼:儒家居丧不赋诗的典范
黄 强
苏轼:儒家居丧不赋诗的典范
黄强
摘要:居丧不赋诗,是六朝以来直至晚清大多数诗人践行的千年习俗,直接体现了崇仰君子人格的儒家诗教的本质追求。苏轼是儒家居丧不赋诗的典范,南宋以来,受到朱熹、陆九渊、吴澄、阎若璩、焦循等人的由衷褒扬。但苏轼诗中《送宋君用游辇下》《咏怪石》二首以往或被视为居丧之作,而所有证据均不能成立。此外,苏轼题跋的《绝胜亭诗》决无可能是苏辙居母丧期间所作,而《次韵赵景贶督两欧阳诗,破陈酒戒》一首,亦并非苏轼劝他人丧制中赋诗之作。今人为古人撰写年谱,或为诗人作品系年时,往往因为不明了诸多古人居丧不赋诗,而发生种种疏漏或错误,因此对苏轼居丧不赋诗的考辨有其普遍意义。
关键词:苏轼;居丧不赋诗;儒家诗教

在中国古代诗歌史上,苏轼是继李白、杜甫以后的著名诗人,文采风流,掩映百代,豁达放旷,迥异常人。无论是在人生的顺境还是逆境之中,写诗吟诗始终是苏轼日常的功课,至老不衰。他因诗中字句遭群小指摘,以莫须有的罪名诬告,导致“乌台诗案”的发生,然而一旦恢复自由,他又诗思驰骋。虽告诫自己“平生文字为吾累,此去声名不厌低”,又禁不住“却对酒杯疑似梦,试拈诗笔已如神”。①苏轼:《十二月二十八日,蒙恩责授检校水部员外郎黄州团练副使,复用前韵二首》,《苏轼诗集》,王文诰辑注、孔凡礼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3册,第1005-1006页。这就是具有真性情的诗人苏轼。然而,作诗成瘾的苏轼在居丧期间却可以成年累月自觉搁置诗笔,甚至可说是中国古代诗歌史上居丧不赋诗的典范,由此可见其对儒家伦理道德的信守,对崇仰君子人格的儒家诗教的践行。不过自宋代以来,始终有人忽视这一点,或谓苏诗中有居丧之作,或谓苏诗中有劝他人居丧赋诗之作。真相如何?此前尚无人探析之。因为居丧不赋诗对于诗歌系年有重要影响,为苏轼进行辩驳具有普遍意义,笔者不揣浅陋,撰为此文以就教于方家。
一、南宋以来对苏轼居丧不赋诗行为的褒扬
居丧不赋诗,是六朝以来直至晚清大多数诗人践行的千年习俗,主要指为父或为母斩衰三年内(或二十五个月,或二十七个月)不作诗。《礼记·曲礼下》云:“居丧未葬,读丧礼,既葬,读祭礼,丧服常,读乐章。居丧不言乐。”孔颖达疏云:“居丧者,居父母之丧也。……丧服常,读乐章者,复常谓大祥除服之后也,乐章谓乐书之篇章,谓诗也。”②孔颖达:《礼记正义》,《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上册,第1257页下。准此,免丧除服之后才能读诗、赋诗。《孝经》亦云:“子曰:孝子之丧亲也,……言不文。”③唐玄宗注、邢昺疏:《孝经注疏》,《十三经注疏》,下册,第2561页上。然而不讲文饰不成其为诗歌,因此居丧不能赋诗。
但是,在赋诗传统极其深厚的中国古代,诗人之喜怒哀乐一寄于诗。一旦居亲丧,便须遵习俗不赋诗,丧亲痛悼之情无可寄托,对于许多诗人而言,这无疑是一种痛苦与考验。因此,尽管居丧不赋诗的习俗有着古老的文化渊源和经典的理论依据,但毕竟不具有强制性,而是一种自我约束行为。在大多数诗人践行这一习俗的同时,无意破戒者有之,有心犯禁者有之,认同接受而情不能已者有之,不置可否而我行我素者亦有之。为了指摘犯禁破戒者,著名诗人信守这一习俗的行为便格外引人注目,苏轼成为这方面具有代表性的人物。
苏轼没有明示过自己居丧不赋诗,原因当是他认为此乃题中应有之义。但上述儒家经典中关于居丧不赋诗习俗的理论渊源,苏轼在言及朝廷及民间丧葬礼仪时信手拈来,化入自己的文字中。如“礼之至者无文,哀之深者无节”;*苏轼:《赐文武百寮太师文彦博以下上第一表请举乐不许批答二首》之二,《苏轼文集》卷四十三,孔凡礼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3册,第1242页。“曾、闵之哀,丧不贰事,……退适倚庐,读丧、祭之礼”。*苏轼:《除皇伯祖宗晟特起复制》,《苏轼文集》卷三十八,第3册,第1097-1098页。此等文字,苏轼文集中所见甚多,足见儒家伦理思想和丧葬文化对他的深刻影响。
古人居亲丧之期,虽曰三年,实际上无须满三年,有遵二十五月者,有遵二十七月者。苏轼所遵为何?管窥所及,确指苏轼遵二十七月之说者为林语堂。其《苏东坡传》云:“苏东坡的宦途正要开始,母亲病故。根据儒家之礼,……守丧两年三个月之后,才能返回复职。”言及苏轼丁父忧,也有类似的说法。此书附录一《年谱》云:“一○五七,中‘进士’;母丧;服孝(一○五七年四月——一○五九年七月)”,“一○六六,父丧;服孝(一○六六年四月——一○六八年七月)”。*林语堂:《苏东坡传》,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0年,第42、74、372页。他认为苏轼遵二十七月之说。此说有官方依据。《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百四“英宗治平二年”栏下云:“臣等谨按礼学,王肃以二十五月为毕丧,而郑康成以二十七月,……天圣中更定五服年月,敕断以二十七月,今士庶所同遵用。”*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百四,文渊阁《四库全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317册,第392页。据此可知宋仁宗天圣以后,三年之丧以二十七月为期。但史书中的记载与实际的施行并不统一,欧阳修、苏轼皆以二十五月为期。欧阳修于皇祐四年(1052)壬辰三月“丁母夫人忧,归颍州”,中经皇祐五年癸巳,“至和元年甲午:公年四十八。五月,服阕,除旧官职,赴阙”。*胡柯:《欧阳修年谱》,《欧阳修全集》附录卷一,李逸安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01年,第6册,第2607页。各本《欧阳修年谱》于此皆同。丧期合计共二十五月。由此可知,北宋朝廷亦认可居亲丧之期为二十五月。故苏轼《乞改居丧婚娶条状》云:“臣伏以人子居父母丧,不得嫁娶,人伦之正,王道之本也。……丧三年,为二十五月,使嫁娶有二十五月之迟,此色之轻者也。”*苏轼:《乞改居丧婚娶条状》,《苏轼文集》卷三十五,第3册,第1009页。没有比苏轼自己的表述更有说服力的了。王肃与郑玄关于三年之丧的不同期限虽仅差两个月,但辨析清楚苏轼的取舍,则为考述其居丧不赋诗提供了准确的时间参照,此点极为重要。
据宋人王宗稷所作《东坡先生年谱》,嘉祐二年(1057)丁酉四月,苏轼“丁太夫人武阳君程氏忧”,此后经嘉祐三年戊戌,直至嘉祐四年己亥六月服除以前,二十五月中传主无诗。嘉祐四年己亥十二月,其与苏辙侍老苏舟行适楚,三人才发于咏叹,故《南行前集序》云:“己亥之岁,侍行适楚,舟中无事,杂然有触于中,而发于咏叹,盖家君之作与弟辙之文皆在焉,谓之《南行集》。”治平三年(1066)丙午四月二十五日,苏洵卒,苏轼兄弟于此年六月具舟载丧归葬于蜀,中经治平四年丁未,直至熙宁元年(1068)戊申六月服除以前,二十五月中二人无诗。*参见王宗稷:《东坡先生年谱》,《东坡全集》附录,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07册,第30、31-32页。或许王谱系简谱,为传主诗作系年非其主要任务,但现存南宋人所作的另外两种苏轼年谱中,施宿的《东坡先生年谱》将诗歌系年作为重要组成部分,傅藻的《东坡纪年录》亦包括诗歌纪年,二者均明示传主两次居亲丧期间无诗,*施宿:《东坡先生年谱》,王水照:《苏轼选集》附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第433、436页。《谱》中于治平三年丙午栏下系云:“春有《柳子玉见寄》。”但“出处”栏系云:“夏四月,宫师卒于京师,先生护丧归蜀”,则明示《柳子玉见寄》一诗作于服父丧之前。傅藻:《东坡纪年录》,《增刊校正王状元集注分类东坡先生诗》附录,《四部丛刊》初编,上海:商务印书馆,1929年,第1册,第13、16页。《纪年录》于熙宁元年戊申栏下系云:“是年(有)《和子由记园中草木》《木山引水》《寄题古东池》《绿筠堂》等诗。”但编者明言诸诗作于“公服除”之后。这就更能说明问题了。
苏轼居丧期间尚且不作诗,其他任何人有什么理由可以例外。于是如同其多方面的文学艺术成就受到推崇一样,北宋以降,苏轼被标举为居丧不赋诗的典范,特别在讥抨犯禁破戒者方面,有着极大的影响力与感召力。
最早提及苏氏兄弟居丧不赋诗的是朱熹。四库馆臣为查慎行《补注东坡编年诗》所作总目提要中言及“《朱子语类》谓二苏居丧无诗文”。*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一百五十四集部七,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下册,第1327页。《朱子语类》版本众多,内容多寡不一,朱熹此语或类似的话不见于今存诸本,但其有过这样的表述当属无疑。明人董其昌为何士抑所作《〈居庐集〉序》云:“东坡居丧,谢宾客,绝诗文,晦翁亦以为知礼。”*董其昌:《〈居庐集〉序》,《容台集·文集》卷一,《四库禁毁书丛刊》,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年,集部第32册,第130页。董其昌作如是说,则上引四库馆臣所云即非孤证。朱熹首先拈出和充分赞许苏轼居丧不赋诗的知礼行为,意义非同一般。古人很少特意标举自己居丧不赋诗,因为此乃相沿已久的习俗。朱熹此举明确昭示中国古代诗歌史上的这一习俗,并标举苏轼作为代表人物。基于朱熹的地位与声望,此举便有了非同寻常的影响。
继朱熹之后,元人吴澄有《题朱文公答陈正己讲学墨帖后》,将居亲丧是否赋诗作为一个原则问题提出来,高度评价二苏兄弟恪守习俗的典范意义。文云:
朱子答正己一书,备述为学之功,又规正己之失,盖以其人有志于学,故曲尽其言,恳切之至。厚哉,先觉之用心乎!然澄窃闻之‘大功废业’,况服齐、斩乎?古人居父母之丧,三年不为礼,三年不为乐。斩衰唯而不对,齐衰对而不言。自发一言且不可,况可与人论学哉?眉山二苏兄弟,文人尔,而其居丧也,再期之内,禁断作诗作文,寂无一语。是亦尝讲闻乎丧礼也。正己蕲学圣贤,身有母丧,而交书论学,不异常时,则三年之丧为虚矣。夫亲丧,本也,论学,末也,忘其本,而务其末,不知所论之学果何学欤?朱子固已箴其失,然舍其大而议其小,或者姑为之掩覆也耶?*吴澄:《吴文正集》卷五九,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97册,第581页。
吴澄以二苏兄弟居丧不赋诗为例,或许是受到朱熹的影响,但吴澄开创了以二苏兄弟为典范讥抨犯禁破戒者的先例。他不仅批评身有母丧而交书论学的陈正己,而且连带批评或“舍其大而议其小”,或“姑为之掩覆”的朱熹,口吻可谓严肃,其核心内容是强调居丧不赋诗这一习俗的根本宗旨。德行之教乃儒家诗教的重要内涵,笃行道德修养是其对做人的基本要求,而居丧不赋诗直接体现了儒家诗教的本质追求。吴澄此说,揭示了二苏兄弟居丧不赋诗这一行为所包含的深刻的意蕴,将苏轼在这个方面的典范意义提升到了不应逾越的“礼”的层面上。
明清两代,居丧不赋诗的习俗依然得到许多文人的践行,故引苏轼或苏氏兄弟为知音者越来越多,当然,引他们为知音的目的又是责难犯禁破戒者。这里仅试举二例。阎若璩《潜邱札记》云:
竟陵锺伯敬集有《游武夷山记》,考其时乃丁忧去职,枉道而为此。予谓伯敬素称严冷,具至性,能读书,不应昧礼至此。昔二苏兄弟居丧,禁断诗文,再期之内,不着一字。陆文安称为知礼。何伯敬严冷,反不及二苏之放旷者欤?登山何事?闻讣何时?而竟优游为之耶!予尤怪谭友夏撰墓铭,不为隐避,不为微词,反称其哀乐奇到非俗儒所能测。噫!三年之丧,天下之通丧也,岂不俗人之所能免欤?”*阎若璩:《潜邱札记》卷一,文渊阁《四库全书》,第859册,第397页。
锺惺的行为,即使在今天也未免过分。谭元春却谓之不俗之人,无疑是在挑战居丧不作诗的传统习俗。难怪阎若璩责之昧礼而声色俱厉。他不仅责难锺惺,而且连带为之辩护的谭元春。文中以二苏兄弟的知礼行为与锺惺对比,讽刺意味溢于言表。阎若璩还引述陆九渊对二苏的评价,这表明南宋时二苏兄弟居丧禁断诗文已得到普遍关注,不仅朱熹一人而已。
清乾嘉时期扬州学派代表人物之一焦循,评阅乡邦前贤汪懋麟的《百尺梧桐阁诗集》,仅有四条批语,而其中竟有两条专门批评汪氏于丧服中为诗。一条批于《百尺梧桐阁诗集》卷十二《目录》后,云:“苏东坡,诗人也,然丁父母丧则不作诗,检其全集可见。蛟门乃于丧服中为诗,吾不知之矣。”*汪懋麟著、焦循评点:《百尺梧桐阁诗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下册,第982页。可以说,在苏轼面前,任何居丧不赋诗习俗的犯禁破戒者的自我辩护都是苍白的。
苏轼居丧不赋诗,固然是对传统习俗的遵循,但恰恰是这种虔诚朴实的遵循,透露出诗人又一种可敬与可爱。说到底,苏轼以居丧不赋诗的方式来悼祭双亲,也是出于对至亲的挚爱之情,此举可谓是他作为人子表现出的至高无上的尽哀方式。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居丧不赋诗”这一文化习俗能够在北宋以后绵延不断,完成从六朝以来穿越千年直至晚清的坚守,苏轼的典范意义不可忽视!
从朱熹到焦循,历代赞许苏轼居丧不赋诗者当是通观其全集后才能引出这样的结论,至少始发此论的朱熹和自谓“检其全集可见”的焦循是认真考察过苏诗系年的。清人周广业云:“然其居老泉丧,丙午、丁未、戊申,废吟三年,故集中无诗。今居丧次而俨然哦吟,殊乖废《蓼莪》之旨。”*周广业:《循陔纂闻》卷二,《续修四库全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1138册,第588页。这就考察得更细致了。既然如此,如果主张“礼之至者无文”“丧不贰事”的苏轼,其诗集中确有居丧之作,或劝他人居丧赋诗之作,不仅意味着从南宋到晚清,从朱熹到焦循,众多学者的考察辨析失当,而且更重要的是,六百余年中逐渐形成的苏轼作为儒家居丧不赋诗的典范地位将受到质疑,苏轼的人品更是会受到质疑。这已经不仅是几首苏诗系年的简单问题了,故不可不辨。
二、苏轼诗中居丧之作辨误
苏轼诗中被视为居丧之作者主要是《送宋君用游辇下》《咏怪石》二首。查慎行《苏诗补注》于《咏怪石》后注云:“慎按,以上二首,诸刻本不载,《外集》编第四卷中。先生丁成国太夫人忧,居蜀时作。今采录。”*查慎行:《苏诗补注》卷四十七,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11册,第906页。所云颇有疏漏之处。所谓《外集》,指明人毛九苞的《重编东坡先生外集》十六卷。此书各卷起首皆标注本卷诗作系苏轼在何处或任何职时所作。卷一、卷二系于“南行”,卷三系于“凤翔”,卷四系于“史馆、居忧、杭州”,卷五系于“密州、徐州、湖州”,卷六系于“黄州、常州”,卷七系于“登州、召入翰林”,卷八系于“杭州”,卷九系于“翰林、颍州、扬州、尚书、定州、南迁”,卷十系于“惠州、儋耳、北还”。从卷一标注的“南行”到卷十标注的“北还”,顺序概括了苏轼的全部宦迹以及人生出处的几次重大经历。显而易见,卷四起首标注的“史馆、居忧、杭州”,分别指苏轼治平二年乙巳得直史馆,三年丙午丁老泉忧,扶丧归蜀,熙宁五年壬子在杭州通判任上。更有可证者,此二诗分别为《外集》卷四第八、第九题,第十一题为《杭州游山》。《杭州游山》诗后有注云:“予之初室王氏亡既累年矣。”*毛九苞:《重编东坡先生外集》,《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11册,济南:齐鲁书社,1997年,第109页。苏轼之初室王弗卒于治平二年乙巳,即使此诗作于熙宁四年辛亥苏轼初到杭州通判任上,王氏之死距此年亦已七年,故曰“累年”。这期间治平三年老泉去世。既然《咏怪石》与《杭州游山》中间仅隔一题,那么,即使前者作于诗人居丧期间,此丧又岂会是“丁成国太夫人忧”?类似的证据在《外集》卷四中还可以找到不少。毫无疑问,《送宋君用游辇下》《咏怪石》二诗即使作于丁忧家居时,此丁忧亦为丁老泉忧。更重要的是,《外集》此卷标注“史馆、居忧、杭州”,并不意味着它们一定作于居忧期间。前文已经指出,治平三年丙午四月后,苏氏兄弟居父丧二十五个月,至熙宁元年戊申六月服除。但二人直至熙宁元年腊月才自陆路返回京都,从是年六月至腊月,苏轼如果赋诗,已不在丧期之内,不违背居丧不赋诗的习俗。查慎行谓此二诗乃苏轼“丁成国太夫人忧,居蜀时作”,一是将苏轼丁父忧误认为丁母忧;二是错误地认定二诗必作于居忧期限内。《苏诗补注》提要中,四库馆臣对此书的疏漏错误多有指责,并直言“至于所补诸篇如《怪石诗》,指为遭忧时作,不知《朱子语类》谓二苏居丧无诗文”。*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一百五十四集部七,下册,第1327页。确实,查氏于此疏于考辨,难辞其咎。
冯应榴辑注《苏文忠公诗集合注》卷四十九《补编诗》收入此二诗,于《咏怪石》诗后引查慎行原按语,复云:“榴按,此诗或以先生居忧不作诗,断为非先生作。然安知非服阕后家居时所作耶?不可拘看也。”*冯应榴:《苏轼诗集合注》,黄任轲、朱怀春校点,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6册,第2431页。冯氏虽亦未细辨此居忧非居母忧,而是居父忧,但所言颇为有见。生活在乾隆年间的冯氏这样说,又足见其时苏轼居忧不作诗已为人所熟知。
然而,可惜的是孔凡礼先生的《苏轼年谱》未取冯应榴之说,反而受到查慎行此按语的误导,于嘉祐四年下系云:“八月,宋君用赴京师,有诗勉其行。……诗云‘八月秋风高’,点明季节”。复系云:“免丧。……家有怪石,植疏竹轩中,作诗。”*孔凡礼:《苏轼年谱》,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第64、65页。将《送宋君用游辇下》系于传主仍居母忧期间,而将《咏怪石》系于九月传主免母服之后。将后诗系于该年九月而非八月,并没有任何根据,将之系于八月亦未尝不可。如此则孔谱延续了查慎行的两个错误结论,还为判定《送宋君用游辇下》乃苏轼作于居母忧期间提供了时令线索。然而,只要明了苏轼信守的居丧期限是二十五个月,就会发现孔谱提供的《送宋君用游辇下》一诗中的时令线索反而证明了此诗系苏轼免丧以后所作。孔谱认定嘉祐四年九月苏轼才免丧,其《苏轼年谱》卷三于此年九月系云:“免丧。”注云:“《嘉祐集》卷十一《上欧阳内翰第四书》:‘今岁之秋,轼、辙已服阕。’《施谱》云七月,《总案》云九月。”*孔凡礼:《苏轼年谱》,第65页。按施宿《东坡先生年谱》七月免丧之说,则苏轼从嘉祐二年四月至嘉祐四年六月,实足服丧二十六个月。按清人王文诰《苏文忠公诗编注集成·总案》九月免丧之说,则苏轼从嘉祐二年四月至嘉祐四年八月,实足服丧二十八个月。但三年之丧的实际服丧期限传统上只有王肃所主二十五月之说和郑玄所主二十七月之说,具体到苏轼,更应当以其本人信守的二十五月为准。基于此,则苏轼免丧当在嘉祐四年六月,而有“八月秋风高”之句的《送宋君用游辇下》必应作于其免丧以后,《咏怪石》在《外集》卷四中列于《送宋君用游辇下》之后,自然也作于其免丧以后。如果将问题的探讨返回到正确的结论上,即《外集》卷四起首标注的“居忧”乃苏轼居父忧,因为苏洵与夫人程氏去世月份都在四月,则上述考辩结论同样适用。至此,如冯应榴所言,《送宋君用游辇下》《咏怪石》“安知非服阕后家居时所作耶”?二诗作于苏轼居丧期间的所有证据均不能成立。而此二诗为苏轼服阕后家居时所作,则还可以从苏轼本人的相关表述(尽管类似的表述并非直接针对诗歌)中,或从其诗作系年的实际状况中发现证据。
苏轼于丧礼律己甚严。其《文集》卷四十八《上知府王龙图书》云:“轼负罪居丧,不当辄至贵人之门,妄有所称述,诚不胜惓惓之心,敢以告诸左右。旧所为文十五篇,政事之余,凭几一笑,亦或有可观耳。”*苏轼:《上知府王龙图书》,《苏轼文集》卷四十八,第4册,第1389页。由此可知,苏轼居丧期间,除书信问候,不敢有所称述,只以旧文示人。文不敢作,诗则更不在话下。此书乃苏轼于嘉祐四年居母忧之际写给成都知府王素。*孔凡礼:《苏轼年谱》,第63页。《谱》中先谓王素乃王旦之孙,后据《宋史》卷三百二十“王素本传”谓其乃王旦之季子。前所谓,疑笔误。居母忧不作文吟诗,居父忧当更如此。苏轼律己既严,对皇家的丧葬礼仪也就毫不含糊。哲宗元祐三年(1088),皇叔魏王赵頵丧在殡,太常议天子绝期,不妨秋燕(宴),苏轼为翰林学士,当撰《秋燕致语》。八月二十一日,苏轼奏《论魏王在殡乞罢秋燕劄子》,认为照行秋燕,不符合礼仪;且“丧言不文”,故“未敢撰”以骈偶声律为文的《秋燕致语》。值得注意的是,奏文中还引《春秋左氏传》昭公九年“辰在子卯,谓之疾(忌)日,君彻燕乐,学人舍业”云云为证。*苏轼:《论魏王在殡乞罢秋燕劄子》,《苏轼文集》卷二十九,第3册,第822-823页。先秦以雅颂之诗歌而舞之,舍歌舞燕乐则亦舍诗。这四句话后来也成为居丧不用歌诗的古老渊源与依据之一。无论居家在朝,于私于公,均持丧礼甚严,深明至礼无文、丧不贰事之重的苏轼,无有可能居丧赋诗。
进一步而言,如果《送宋君用游辇下》《咏怪石》二诗系苏轼居父忧期间所作,那么从治平三年丙午四月二十五日至熙宁元年戊申五月二十五日的二十五个月期间,苏轼仅作过这两首诗。治平三年苏轼年三十一,正值其诗歌创作的稳定期。冯应榴辑注《苏文忠公诗集合注》卷五收古今体诗四十五首,卷首引查慎行注云:“起英宗治平元年甲辰,合明年乙巳罢凤翔任,还朝直史馆作。”卷六收古今体诗五十首,卷首引查慎行注云:“起神宗熙宁二年己酉服阕还朝,至四年辛亥任开封推官,寻改杭州通判,抵广陵作。”*冯应榴:《苏轼诗集合注》,第1册,第179、214页。王文诰《苏文忠公诗编注集成》卷五收古今体诗四十八首,并于卷首案云:“起英宗治平元年甲辰正月,在大理寺寺丞签书凤翔府节度判官厅公事任,……二年乙巳正月还朝,判登闻鼓院,二月直史馆,至八月作。”卷六收古今体诗五十六首,卷首案云:“起神宗熙宁二年己酉二月还朝,在殿中丞直史馆判官告院任,四年辛亥正月,权开封府推官,……十月抵扬州作。”*王文诰:《苏文忠公诗编注集成》,《续修四库全书》,第1316册,第95、105页。冯、王二本在众多苏轼诗歌编注本中有很强的综合性和总结性,上举两卷编年分别相同,从中可以看到一个基本事实:在英宗治平二年八月以后,神宗熙宁二年丁父忧服阕还朝以前,三年半时间内无诗编入,其中正包括治平三年四月二十五日至熙宁元年戊申五月二十五日之间苏轼居父忧的二十五个月。苏轼居父忧前后各两三年内皆有诗四五十首,如果其居父忧的二十五个月中破戒作诗,又何至于仅有区区两首?答案只有一个,苏轼居丧不赋诗。从朱熹到焦循,诸家认定苏轼居丧不赋诗,正是依据其居父忧前后诗作皆多至数十首,惟独居丧期间诗歌创作戛然而止,作出此正确判断。
此外,证明苏轼居丧不赋诗,还须排除苏辙的一首诗。苏轼《书子由绝胜亭诗》云:“‘夜郎秋涨水连空,上有虚亭缥缈中。山满长天宜落日,江吹旷野作惊风。爨烟惨淡浮前浦,渔艇纵横逐钓筒。未省岳阳何似此,应须子细问南公。’蜀州新建绝胜亭,舍弟十九岁作。”*苏轼:《书子由绝胜亭诗》,《苏轼文集》卷六十八,第5册,第2134页。玩首句之意,诗作于秋天。苏辙十九岁正值嘉祐二年丁酉,秋日正与兄居母忧,如此诗确系其十九岁作,则表明苏氏兄弟并不忌讳居丧赋诗,而且苏轼还特书此诗以作纪念。陈宏夫、高秀芳点校的《苏辙集》收入了刘尚荣先生撰辑的《苏辙佚著辑考》。《辑考》据上引苏轼所云,称此诗“应为嘉祐二年(1057)苏辙进士及第后闻母丧,随父洵兄轼返乡途经绝胜亭时作”。*《苏辙集》,陈宏夫、高秀芳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4册,第1415页。此说难以成立,一是程夫人卒于四月初七,父子奔丧返蜀,沿途当尽可能节省时日。眉山距京师虽千里迢迢,但两月有余可达,*嘉祐元年约及闰三月,苏洵率二子由成都出发,五月间抵京师,费时两月有余。参见林语堂:《苏东坡传》,第38页;孔凡礼:《苏轼年谱》,第43-44页。此为正常行程,奔丧则又当别论。不至于秋日才途经绝胜亭所在的蜀州。二是此番苏氏父子“出京仓惶”,连欧阳修等人皆不及面辞,*苏洵:《上欧阳内翰第三书》《与吴殿院书》,《嘉祐集》,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04册,第936、946页。只求早日到家,料理丧事,苏辙何至于有闲情逸致伫足绝胜亭且从容为诗?更何况,苏辙饱读经史,言及君子遵丧葬之礼绝不苟且。其《诗集传》中有云:“君子之居丧,皇皇若无所容者。”*苏辙:《苏氏诗集传》卷七,文渊阁《四库全书》,第70册,第389页。苏辙自己居丧的心境亦当如此。《栾城应诏集·夏论》云:“闵子终三年之丧,见于夫子,援琴而歌,戚戚而不乐,作而曰:‘先王制礼,弗敢过也。’子夏终三年之丧,见于夫子,取琴而鼓之,其乐衎衎然,作而曰:‘先王制礼,不敢不及也。’而夫子皆以为贤。由此观之,圣人之行,岂求胜夫天下之人哉!亦有所守而已矣。”*《苏辙集》,第4册,第1244页。《礼记·檀弓上》中,言“先王制礼,而弗敢过也”的是子夏,言“先王制礼,不敢不至焉”的是子张。苏辙所言,乃是据《诗经》毛传、《孔子家语》等书。尽管有“弗敢过”与“不敢不及”的区别,但闵子与子夏均在终三年之丧后才“援琴而歌”。在苏辙看来,这是“有所守”而不能逾越的底线。所以苏辙对悖礼之行不能容忍,其《私试进士策问二十八首》之四有云:“然则今世之所尚者,……以为文耶?则礼乐不备,冠昏丧祭之义至为浅薄,非所以为文也。”*《苏辙集》,第1册,第358页。凡此种种,足见苏辙对儒家丧祭之礼的重视,绝无可能居母丧而坦然吟咏。
苏氏兄弟居丧不赋诗,还受到乃父的影响。庆历七年(1047)丁亥五月,苏洵父苏序卒于家,八月苏洵奔丧回蜀,其后二年居丧不出,以所学授之二子,不作诗文。苏氏兄弟居母丧,对于苏洵而言,则须为妻守期年之丧,丧期内苏洵同样不作诗。其《上欧阳内翰第三书》云:“二子轼、辙竟不免丁忧,今已到家月余。……今且谢绝过从,杜门不出,亦稍稍取旧书读之。”*苏洵:《上欧阳内翰第三书》,《嘉祐集》,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04册,第936页。苏洵如此,二苏服母丧,更当如此。然则苏轼言此诗“乃舍弟十九岁作”,当如何解释?或刊刻有误,或苏轼本人记忆有误。《书子由绝胜亭诗》作于元丰年间,*毛九苞:《重编东坡先生外集》卷四十四,《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11册,第318页。此卷题跋凡注明年月者,皆系于熙宁、元丰、元祐年间,以元丰年间为多。此跋前一首为《书子由金陵天庆观诗》,末云:“元丰三年四月,家弟子由过此留诗,七年七月十六为书之壁。”此跋后一首为《跋翰林钱公诗后》,末记“元丰八年正月二十日”;则此跋当题于元丰七年七月十六日至次年正月二十日之间。距苏辙作此诗时已有二十多年,记忆有误不足为奇。苏轼文中另有明显的时间疏漏可证。其妻王弗卒于治平二年五月丁亥,《亡妻王氏墓志铭》云:“六月甲午,殡于京城之西。其明年六月壬午,葬于眉之东北彭山县安镇乡可龙里先君先夫人墓之西北八步。”*苏轼:《亡妻王氏墓志铭》,《苏轼文集》卷十五,第2册,第472页。然而治平三年六月无壬午日,且苏洵卒于是年四月二十五日,六月壬辰(初九日),朝廷应苏轼请,诏赠其父光禄寺丞,并敕有司具舟载丧归蜀,*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百八,文渊阁《四库全书》,第317册,第452页。也就是说,当年六月苏轼犹未归蜀,王弗之葬绝无可能在本月。记忆之误,由此可见一斑!
朱熹、陆九渊、吴澄读到的苏轼诗文无疑不会比明清人少,如果《送宋君用游辇下》《咏怪石》二诗系苏轼居父丧期间所作,《绝胜亭诗》系苏辙居母丧期间所作,他们不会不注意到。因此,朱熹谓“二苏居丧无诗文”,陆九渊以此为“知礼”,吴澄赞赏二苏兄弟“再期之内,禁断作诗作文”,是完全符合事实的。孔凡礼先生作《苏轼年谱》时尚未意识到二苏居亲丧期间不作诗文,于嘉祐二年系云:“是岁,弟辙赋蜀州绝胜亭诗。尝为书之。”*孔凡礼:《苏轼年谱》,第61页。在撰写《苏辙年谱》时他才意识到这一点,于皇祐元年下系云:“父洵作《名二子说》,名辙兄弟。”复考辨云:“清王文诰《苏文忠公诗编注集成总案》谓洵之文作于庆历七年奔丧归里后,不从。《霞外攟屑》卷三《居丧不作诗文》:‘吴草庐题朱文公答陈正己讲学墨帖云:眉山二苏兄弟,文人也,再期之内,禁断作诗作文,寂无一语。是亦尝讲闻乎丧礼也。’二苏能如此,当有洵之影响与教育。洵文当作于免丧后,今系此。”又于嘉祐二年下针对《绝胜亭诗》按云:“此诗疑为二十一岁免丧后作。二苏居丧期间禁断作诗作文,……此诗乃亲见绝胜亭,因而有作。本年离京师前,无缘见之。蜀州在成都之西,离眉山不远,辙免丧后至此,见此亭新落成,因赋之。”*孔凡礼:《苏辙年谱》,北京:学苑出版社,2001年,第7-8、19页。如果天假以年,孔先生能修订《苏轼年谱》,一定会确认苏轼居丧不赋诗,修正相关诗文的系年。
三、苏轼诗中劝他人居丧赋诗之作辩误
苏轼自己居丧不赋诗,自然不会劝他人丧制中赋诗,但前人或由于不明丧葬之礼的复杂性,或轻信他人、疏于考辨,误解苏轼者往往有之。宋人祝穆《事文类聚·前集》卷五十二《丧事部》“督其作诗”条云:“昔欧阳叔弼、季默以忧制中不作诗,陈履常不饮酒。东坡一日设宴两欧,至履常不饮,故不作诗。坡诗云:‘商也哀未忘,岁月忽已秋。祥琴虽未调,余悲不敢留。矧此乃韵语,未入金石流。君言不能诗,此语还信不?陋矣陶士行,当以大白浮。明当罚二子,已洗两玉舟。’”*祝穆:《事文类聚·前集》卷五十二,文渊阁《四库全书》,第925册,第853页。原诗可参见《苏轼诗集》,第6册,第1798-1799页。苏诗原题《次韵赵景贶督两欧阳诗,破陈酒戒》,引诗不全,但大体已备。如果欧阳叔弼、季默处忧制中,苏诗确实是劝人居丧赋诗。宋人谢维新《事类备要·前集》卷六十四《丧纪门》亦列此条,题为“诗集制中不诗”。*谢维新:《事类备要·前集》卷六十四《丧纪门》,文渊阁《四库全书》,第939册,第512页。宋以后,此种误解一发不可收拾。元人陈基为破戒赋诗的友人沈仲说所作《横山纪行诗》序云:“昔孙兴公赋诗以伸罔极之痛,识者谓有《蓼莪》之遗思焉,而欧阳叔弼居忧,君子盖有督其作诗者。余虽非识者,仲说固兴公之徒欤?世有君子如苏长公,则仲说贤于叔弼矣。”*陈基:《夷白斋稿》卷十三,《四部丛刊》三编景明钞本。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夷白斋稿》(第1222册,第253页)中,此序文字有所不同,今从明钞本。陈氏在此将沈仲说比做居丧赋《表哀诗》的晋人孙绰,赞赏苏轼督欧阳叔弼居忧赋诗的做法。清人周广业则极不理解其所谓苏轼的矛盾行为:“欧阳叔弼以忧制中不作诗,东坡为诗讥之,及居老泉丧亦无诗,故集中自丙午至戊申三年无诗。”*周广业:《循陔纂闻》卷二,《续修四库全书》,第1138册,第597页。自己居父忧无诗,却讥人忧制中不作诗,这样的事发生在苏轼身上可能吗?前人误解苏轼者均未深思耳。
首先,应当辨明苏轼作此诗的年月。诗题中提及的赵景贶即赵令畤,涉及的人物有欧阳修三子欧阳棐(叔弼)、四子欧阳辩(季默)和陈师道(履常)。元祐六年辛未八月,苏轼知颖州,历时仅半载,却知交甚惬。时赵令畤作签判,“两欧阳”居家颖州,陈师道为颖州教授,诸贤相与酬答,赋咏独多。内容相关者尚有《叔弼云,履常不饮,故不作诗,劝履常饮》《景贶、履常屡有诗,督叔弼、季默倡和,已许诺矣,复以此句挑之》二首。*《苏轼诗集》,第6册,第1790-1802页。苏诗诸家注本无不将包括此三诗在内的颖州诸作顺序系于元祐六年辛未八月至七年壬申三月。诗云“岁月忽已秋”,是指秋季的几月呢?此诗前第七题为《九月十五日,观月听琴西湖示坐客》,七题中有的一题数首,共有诗十首,由此可知此诗必作于元祐六年九月十五日以后。但其前既然有诗十首,而且作于不同的场合,如《送欧阳主簿赴官韦城四首》《泛颍》等,则此诗又不必定作于九月十五日以后的一二日内。此诗后第二首为《臂痛谒告,作三绝句示四君子》(四君子即陈、赵、两欧阳),陈师道次韵之,其三有“纸帐薰炉作小春”之句,*陈师道:《次韵苏公谒告三绝》,《后山集》,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14册,第594页。既云“小春”,写作时间当及十月。由是言之,苏轼作此诗当已在九月底。
其次,应当辨明“两欧阳”此次服丧的时限。据苏辙所撰《欧阳文忠公夫人薛氏墓志铭》记载,“两欧阳”之母薛夫人卒于元祐四年己巳八月二十一日。*《苏辙集》,第2册,第419页。“两欧阳”居丧不赋诗,自然受到父亲欧阳修的影响,服亲丧期限亦当同于乃父,为二十五月。即应起于元祐四年八月二十一日,迄于元祐六年闰八月二十一日,整整二十五个月。清人冯应榴《苏诗合注》于苏轼此诗“祥琴虽未调,余悲不敢留”二句下注云:“免丧当在六年冬也。”*《苏轼诗集》,第6册,第1798页。这是因为冯氏不明欧阳修父子居亲丧为二十五个月,而误以二十七个月衡之。陈师道曾酬答苏轼此诗,题为《次韵苏公劝酒与诗》,宋人任渊注云:“两欧阳以新免母丧,不肯作诗。”*任渊:《后山诗注》卷三,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14册,第771页。此说出之于宋人之口,亦当更具权威性。如前述,苏轼作此诗当在九月底,“两欧阳”免母丧已一个月,并不在忧制之中。苏轼次韵赵景贶督两欧阳诗,并不违背居亲丧不赋诗的习俗,也和他自己居父忧不赋诗的行为没有任何矛盾之处。
第三,应当辨明“两欧阳”既免母丧,何以不肯作诗?居丧不赋诗这一习俗寄寓着诗人深切的悲悼情怀,体现着儒家伦理和道德修养的水平,因此尽管丧期有定,但士君子免丧后创痛巨深,如子夏之弹琴而不成声者比比皆是,*孔颖达:《礼记正义》,《十三经注疏》,上册,第1285页下。所谓服丧虽终,心丧不已。丁忧期满者,或屡屡辞官不就,更遑论赋诗了,于是,劝新免丧者破诗戒,就成为一种传统。南宋诗人杨万里《诚斋朝天诗集序》云:“予游居寝食,非诗无所与归。淳熙壬寅七月,既婴戚还家,诗始废。至甲辰十月一日,禫之徙月也,大儿长孺请曰:‘大人久不作诗,今可作矣乎?’予蹙然曰:‘三年不为礼,礼必坏;三年不为诗,诗必颓。善如尔之请也。’是日始拟作进士题。”*杨万里:《诚斋集》卷八一,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61册,第85页。此乃受儿辈之请重拾诗笔。清人钱谦益于崇祯六年(1633)癸酉五十二岁丁太夫人顾氏忧,至少两年内无诗,*葛万里:《牧斋先生年谱》,《国粹学报》第65期,上海国粹学报社,1910年,第43-44页。故除服后有《乙亥中秋,吴门林若抚、胡白叔二诗人引祥琴之礼劝破诗戒,次若抚来韵四首》。*钱谦益:《牧斋初学集》卷十,《续修四库全书》,第1389册,第316-317页。此乃承诗友之劝而为诗。赵翼《服阕后亲友多劝赴官作诗志意》云:“祥琴才罢忍弹冠?多少锣声催上竿。”*赵翼:《瓯北集》卷二十五,李学颖、曹光甫校点,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上册,第523页。此亦是亲友之劝赴官、劝作诗。足见直至清代乾嘉时期,劝新免丧者破诗戒的传统依然一脉相承。明乎此,“两欧阳”新免母丧而不肯作诗也就很可以理解了。赵景贶督两欧阳诗,破陈酒戒,苏轼次韵之,实在不过是行另一传统习俗而已。
至此,苏轼此诗主体八句的意蕴可以明了:化用子夏(卜商)免丧后的故事,劝“两欧阳”破诗戒。《礼记》云:“子夏既除丧而见,予之琴,和之不和,弹之而不成声,作而曰:‘哀未忘也,先王制礼,而弗敢过也。’”*孔颖达:《礼记正义》,《十三经注疏》,上册,第1285页下。其“商也哀未忘”二句,言“两欧阳”如同子夏一样,丧期已过,依然不释哀戚。“祥琴虽未调”二句是以诗家语暗示“两欧阳”新免丧,说明其余悲尚在,但其实没有必要。所谓“祥琴”乃亲丧大祥祭日为节哀所弹奏之素琴,以示亲丧哀有终期。“矧此乃韵语”二句意谓诗之韵语与琴声尚有区别。琴声受情绪影响控制不住也就罢了,免丧后写诗总是可以的。“君言不能诗”二句对“两欧阳”的推脱之辞予以化解。全诗虽多达二十句,核心的意思这八句已经可以概括,总之不脱一个“劝”字。其实只要熟悉子夏既除丧弹琴而不成声的故事,就知道苏轼此诗绝对不可能是劝“两欧阳”居丧赋诗。赵令畤、苏轼的劝说结果是如上述诗题中所言,让“两欧阳”破了诗戒:“督叔弼、季默倡和,已许诺矣”。如果“两欧阳”未免丧,即使赵令畤、苏轼再劝又有何用?更何况所劝者乃恩师欧阳修之子,欧阳修居亲丧不赋诗,苏轼不可能不知道。
结语
本文虽是探析苏轼居丧不赋诗,但所考辨问题的性质具有普遍意义。学界对于古人居丧不赋诗的习俗涉猎甚少,以此之故,在为古人撰写年谱,或为诗人作品系年时,往往因为不明了诸多古人居丧不赋诗,而发生种种疏漏或错误。管窥所及,历代践行者主动明示自己居丧不赋诗者不多,因为他们认为此乃题中应有之义,例如苏轼。文人别集中的诗作能够准确系年者所占的比例很小,朝代越早,这种情况越突出。不同朝代包括服丧时限在内的服丧制度会有变化,例如先秦时期(以《仪礼·丧服》为依据),子为父服丧三年,父在,为母仅服期年之丧,而唐宋以降则规定无论在何种情况下,子为父母均须服三年之丧。对同一种服丧制度的解释亦因人而异,例如三年之丧的期限是二十五个月,还是二十七个月?期年之丧的期限是十三个月,还是十五个月?或有丁外忧期间而母复去世,丁内忧期间父又亡故,服丧之期势必交叉重叠。更有文人既要顾及这一习俗,又禁不住内心作诗的冲动,于是自行其是,对“居丧不赋诗”的期限作某种变通。凡此种种,则今人判断特定对象是否践行这一习俗须十分谨慎,务必了解特定对象所处时代的服丧制度,特别要细心研判其特定诗作的系年,然后再下结论。有鉴于此,本文或许能够提供某些有益的启示。
(责任编辑:庞礴)
§宋文化研究§
Su Shi: A Paragon of Confucian Scholars for Not Composing Poetry
during the Period of Mourning
Huang Qiang
Abstract:Refraining from composing poetry during the period of mourning is a convention practiced by most poets from the Six Dynasties to the late Qing Period, directly reflecting the Confucian doctrine of education through poetry that enshrines gentlemanly personality. Su Shi was such a good example, and he won praise from Zhu Xi, Wu Cheng, Jiao Xun and many other scholars. Despite two of his poems being suspected to be written during his mother's mourning, all the evidences cannot be established. It is also impossible that Su Zhe's “Poem of Unique Pavilion”, with a epilogue by Su Shi, had been composed during their mother's mourning. Su Shi's “Replying Rhyming Poem to Zhao Jingkuang and Two Ouyangs, Breaking the Old Taboo of Wine” was absolutely not written to encourage others to compose poetry during the period of mourning. When people today write chronicles for ancient people or ancient works and poems, they may often make errors or omissions for not knowing that many ancient people did not compose poetry during the period of mourning. Thus the textual research in this article has its universal significance.
Key words:Su Shi,no composition during the period of mourning,the Confucian Doctrine of Education through Poetry
作者简介:黄强,扬州大学文学院教授(扬州225002)
中图分类号:I207.2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6-0766(2016)01-0143-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