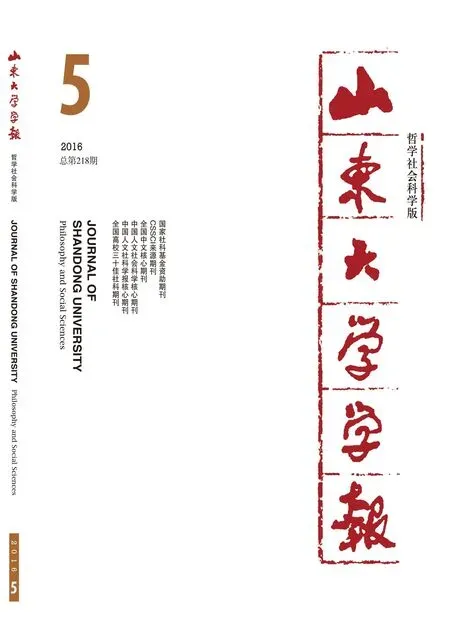从“反本质主义”到“强制阐释论”
——中国当代文艺学的“本质论”迷失及其理论突围
单小曦
从“反本质主义”到“强制阐释论”
——中国当代文艺学的“本质论”迷失及其理论突围
单小曦
中国当代文艺学的理论争鸣基本属于“本质论”范式之中的内部矛盾。“反本质主义”主张超越“本质主义”并以“建构主义”、“关系主义”、“穿越主义”等理论模式开展中国当代文艺学的建设工作,但总体上仍未脱离“本质论”文艺学范畴。而“强制阐释论”反思批判了当代西方文论,将其问题归结为“强制阐释”,提出以“本体阐释”代替“强制阐释”,但在其反对“强制阐释”和主张“本体阐释”的理论根部也深埋着“本质论”的基本观念。中国当代文艺学要获得突破性发展需要走出“本质论”范式的理论怪圈,建构现代存在论文艺学可以作为中国当代文艺学发展建设的一种选择。
反本质主义; 强制阐释论; “本质论”范式; 现代存在论文艺学
进入新世纪之后,中国当代文艺学最轰轰烈烈的两次理论争鸣莫过于几年前的“反本质主义”和当下如火如荼的“强制阐释论”了。“反本质主义”和“强制阐释论”发生的时间点不同,讨论主题也未形成直接的前后呼应。不过,如果把两者放在21世纪中国文艺学发展行程中作整体考察,就会发现它们实际上具有较强的内在关联性。这种关联既有表面上的排异性,又有深层次的相通性。就排异性而言,“反本质主义”把文学的自在性、自律性视为“本质主义”思维的产物而予以否定和抛弃,“强制阐释论”则主张只有回到以文学“自在性”为前提的“本体阐释”,才能进行有效的文学阐释;“反本质主义”主张对文艺学进行“扩容”、“越界”,使用文化研究的方法和策略进行文学研究,“强制阐释论”则认为使用文化理论阐释文学属于典型的“场外征用”,如使用不当即为“强制阐释”。就相通性而言,“反本质主义”反对的是脱离历史、语境、关系理解“本质”,但主张在历史、语境、关系中抓取文学“本质”的“非本质主义”的“本质论”;“强制阐释论”没有直接谈论文学“本质”问题,但在其反对“强制阐释”和主张“本体阐释”的理论深部却埋着文学“本质论”的根基。即是说,“反本质主义”和“强制阐释论”最终在“本质论”范式中又达成了理论逻辑上的和解。对于这种情况,“反本质主义”和“强制阐释论”并非个案,回顾中国当代文艺学的主要理论争鸣,基本属于“本质论”范式之中的内部矛盾。在20世纪哲学人文学术对“本质论”反思、批判历经百年后的21世纪,中国当代文艺学主流仍固守“本质论”范式,而需要突破这一范式寻找理论突围之路。
一
中国当代文艺学“反本质主义”挑战的对象是1980年代后形成的中国当代主流文艺理论形态,并称之为“本质主义”理论范式,而主张超越这种理论范式并以“建构主义”、“关系主义”、“穿越主义”等理论模式开展中国当代文艺学的建设工作。但如深入分析就会发现,这三个主义与它们反对的主流文论一样,仍未脱离“本质论”文艺学范畴。

至此,我们已经能够清楚地看到,“建构主义”只反它所说的那种超历史文化时空的形而上学意义上的“本质”,但并不反对有条件的具体意义上的“本质”。因为,在倡导者看来,尽管不存在绝对的、一般的、普遍的、实体性的“本质”,却是存在着相对的、历史的、特殊的、具体的“本质”的。与此同时,它“反对通过本质主义的方式言说本质”,认为“那些声称自己是唯一正确、合法的本质言说是不合法的”,但它“不认为关于本质的言说是不可能的。建构主义自己就是一种言说本质的方式”。*陶东风:《文学理论:建构主义还是本质主义?——兼答支宇、吴炫、张旭春先生》,《文艺争鸣》2009年第7期。它要使用福柯的“事件化方法”、布迪厄的“反思性方法”和其他理论家的文化研究方法建构一种政治学和知识学的文艺学,目的还是要进行一种文学“本质”言说。具体就是言说被建构起来的文学“本质”或某一文学“本质”是如何被建构起来的。可见,所谓“建构主义”其实质也就是“本质建构主义”。在具体操作中,这种“本质建构主义”不再直接给出文学本质和以此为核心的文学基本问题的具体答案,而是分析中外古今诸多文学“本质”言说的话语条件和权力关系。这样的文艺学实质上已经从原来讨论“什么是文学”的理论,变成了考察古今中外已有的文学理论流派是如何讨论“什么是文学”的理论。
“关系主义”批判和反思以往那些把文学视为“独立的,纯粹的,拒绝社会历史插手”*南帆:《文学理论新读本》,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3页。的文论形态,认为其具有“思想僵硬,知识陈旧,形而上学猖獗”的本质主义典型症状*南帆:《文学研究:本质主义,抑或关系主义》,《文艺研究》2007年第8期。,并有如下特征:1)坚持表象/本质二元对立和本质决定表象的决定论思维模式;2)以探究深度或内在性为理论旨归;3)世界图像的静止看法,而非与运动的历史相兼容;4)具有维护既定体制的保守主义倾向。这些特征中最根本的是第一条,它也是“本质主义”其他特征形成的根源。因为坚持表象/本质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必然遮蔽其他各元关系和要素间的非决定论的动态生成性品格。在“关系主义”倡导者看来,任何理论都是需要进行理论预设的。既然“本质主义”可以对事物作出表象/本质二元对立关系的理论预设,那么,我们也可以对事物作二元之外的多元关系预设,而“超越表象与本质的对立,更为广泛地注视多元因素的相互影响”。进一步说,还可以不再把多元因素中的某一元强制性地置于特殊的深度位置。倘若如此,决定论也就自然解体了。这种理论预设“显然不再指向那个惟一的焦点——‘本质’;相对地说,我们更多地关注多元因素之间形成的关系网络”*南帆:《文学研究:本质主义,抑或关系主义》,《文艺研究》2007年第8期。,“关系主义强调进入某个历史时期,而且沉浸在这个时代丰富的文化现象之中”,发现各种关系,分析各种现象,进而达到对对象的把握。落实在文学上,就是将其“置于同时期的文化网络之中,和其他文化样式进行比较——文学与新闻、哲学、历史或者自然科学有什么不同,如何表现为一个独特的话语部落,承担哪些独特的功能等等”,即“我们论证什么是文学的时候,事实上包含了诸多潜台词的展开:文学不是新闻,不是历史,不是哲学,不是自然科学……文学的性质、特征、功能必须在这种关系网络之中逐渐定位”*南帆:《文学研究:本质主义,抑或关系主义》,《文艺研究》2007年第8期。。
不难发现,与“建构主义”一样,“关系主义”的确也是反“本质主义”的,但它仍然没有放弃寻求“什么是文学”这一文学“本质论”命题。不过它反对把“文学是什么”化约为一个单一的深埋于表象之下的“本质”。它也回避了“本质”一词,而是使用“性质”、“特征”、“功能”等概念代替“本质”,作为对“什么是文学”的回答。可以看出,它要讨论的还是使文学之为文学的“文学性”(尽管雅各布森的这一著名论题被其斥为“本质主义”),即它还是要考察出文学独有的可以将之与其他文化形态相区别的特殊属性。不过,在它看来,“本质主义”的二元思维和具体操作方式并不能找到这个属性。要找到这个属性,需要使用关系性思维,将文学还原为社会关系场中的具体存在。这种关系首先是各种社会文化形态之间的横向关系,其次是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历史关系。即只有在共时性和历时性相交叉的多元关系中,才有可能抓取出文学的“性质”、“特征”、“功能”等或“文学性”。问题是,这个从多元关系中抓取到的“文学性”与从二元关系中抓取到的“本质”的区隔意义究竟有多大?分别以它们为核心概念的文学理论能够形成两种不同的文论范式吗?笔者对此深表怀疑。如果说从二元关系中把握“本质”属于“本质主义”,那么,从多元关系中把握“性质”、“特征”、“功能”仍难逃脱“本质论”范式。至于如何使用“比较”法、“文学不是什么”质询法或排除法等具体操作方式,并不能实现理论范式的超越。
“穿越主义”不同意目前中国当代文艺学提出的种种“反本质主义”的思路,认为一些“反本质主义”者没有对西方“本质主义”和“中国式文学本质论”、“中国式文学本体论”作出区别。反对西方式的“本质主义”也许是有道理的,但在今天的中国如果“彻底放弃‘本质论’或‘本体论’思维”,会使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理论的“自主化”建设更加遥遥无期。“穿越主义”认为,今天中国当代文艺学的首要任务不仅不是告别而恰恰是努力建设“中国式”文学本质论与本体论。在如何建设上,它主张“通过对中国文学如何穿越意识形态、文化观念、艺术现实所构成的现实之束缚、建立一个区别于上述现实的存在世界,以直接建立‘中国文学何以成为自身’的问题来间接回答‘文学是什么’这一中国式的本质追问,从而与中西方各种文学本体论和文学本质观,构成‘不同而对等’的对话状态”。这样就可能建构出一种由“知识论”和“价值论”复合而成的“价值知识论”文艺学。它不仅要回答“文学是什么”,还要回答“好文学是什么”。照此逻辑,“好文学是什么”就应该是“文学是什么”问题的“穿越”和提升。*吴炫:《论文学的“中国式现代理解”——穿越本质和反本质主义》,《文艺争鸣》2009年第3期。
“穿越主义”表现出的中国问题意识无疑是可取的,但问题是,它的“穿越”仍然没有“穿”出“本质论”框架。与“建构主义”和“关系主义”实际上把文学本质论划分为“本质主义文学本质论”和“非本质主义文学本质论”(可以概括为“本质建构论”和“本质关系论”)不同,“穿越主义”划分了“西方本质主义文学本质论”和“中国式文学本质论”。当然也需要看到,它没有驻足于“中国式文学本质论”,而是希望通过“穿越”把“中国式文学本质论”提升为“中国式文学本体论”。它认为,“‘本质论’倾向于回答‘文学是什么’而‘本体论’倾向于回答‘文学是通过什么区别于非文学’的”。其实这样的“本体论”还是在一个存在者和其他存在者通过什么可以区别开来的层面上打圈圈。同样,它企图通过对“什么是好文学”的分析“间接回答‘文学是什么’”的问题,仍然未能走出“本质论”思路,而同样也是归入“非本质主义文学本质论”之途了。
二
“强制阐释论”质疑和批判的对象是整个当代西方文论,特别是西方后现代文论和受其影响的中国当代文论与批评,“反本质主义”文艺学自然包含其中。严格说来,“强制阐释论”还不是一种内容完备的文论体系,而主要属于理论反思成果和相对于当代中西文论与批评中存在问题提出的文论建设观念、立场以及方法论思想。然而,这些已足以使其立足的“本质论”理论范式彰显无疑了。与“反本质主义”一样,“强制阐释论”也包括“破”和“立”两大理论板块,其“本质论”立场和理论诉求也具体体现在这两个方面。
首先,在批判反思对象的甄别和取舍中,“强制阐释论”有意无意地流露着“本质论”倾向。“强制阐释论”认为当代西方文论最大的缺陷可以用“强制阐释”来概括,有四个特征,即“场外征用”、“主观预设”、“非逻辑证明”、“反序认识路径”*张江:《强制阐释论》,《文学评论》2014年第6期。。这四点中前两点是关键,后两点是前两点的具体化。因此,抓住了前两点也就等于抓住了“强制阐释”的理论精神。从理论诉求的总体情况说,“强制阐释论”未必完全认同俄国形式主义和英美新批评,但它别有意味地将这两个流派排除在了批判对象之外。按照“场外征用”说的逻辑,这两个流派很明显地“征用”了语言学、符号学的理论。如果把语言学、符号学的分析抽掉,等于抽掉了这两个流派的理论魂魄。也许“强制阐释论”钟爱这两个流派并不取决于它们是否犯了“场外征用”的错误,而在于它们持有最为典型的文本中心论和文学“本质论”立场。俄国形式主义反对的是19世纪俄国流行的“文学形象思维本质论”。但这种反对不是理论范式层面上的,而是“本质论”范式内部的,即企图以新的“本质”——“文学性”、“陌生化”语言、文学创作“程序”、“诗功能”等代替形象思维,形成了“文学形式本质论”这一新的文学“本质论”。新批评不仅采用了俄国形式主义“文学形式本质论”的理路(尽管没有直接受到影响),而且通过对“含混”、“肌质”、“张力”、“悖论”等语言和文本形式特质的阐释,使这一新文学“本质论”得到了更为深入的探讨。新批评主将兰色姆最先把“本体”范畴从哲学领域“征用”到了文学理论与批评中,他倡导的“本体论批评”第一要义就是以文学作品或文本为“本体”。“强制阐释论”提出的“本体阐释”,主要采纳的就是这种以文学文本为“本体”、把文学文本看成文学本质来源的“本质论”文学观和批评观。
其次,“强制阐释论”坚持以“场内”、“场外”区隔了文学和其他文化形态、文论批评和其他学科,显现着“本质论”思维路径。所谓“场外征用”,即“广泛征用文学领域之外的其他学科理论,将之强制移植文论场内,抹煞文学理论及批评的本体特征,导引文论偏离文学”*张江:《强制阐释论》,《文学评论》2014年第6期。。这些学科包括哲学、史学、语言学等传统人文学科,女性主义批评、后殖民理论、生态批评等新兴文化理论,还有自然科学中的一些理论和方法。具体“征用”方式包括“挪用”、“转用”、“借用”三种。这一看法,一定程度上点中了当代西方文论与批评的要害。同时,也体现出了“强制阐释论”自身的“本质论”理论性质。如果我们把人的精神活动也看成一种文化实践行为,那么,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主要表现为人对世界的认知活动及其成果,而人文学科则主要表现为人对意义的追索方式和解释形式。文学艺术属于典型的对意义的追索方式,哲学、历史、宗教学、伦理学、人类学、心理学、语言学、符号学、文艺学等则属于典型的意义解释形式。不仅意义的追索方式与解释形式之间密切关联,而且诸解释形式之间也没有明确清晰界限。常识告诉我们,无论西方还是中国的文化源头处,并无今天意义上的学科上划分。古希伯来《圣经·旧约》、古希腊《荷马史诗》、中国先秦诸子学说无不是今天的文学、宗教、哲学、历史、教育学、伦理学等多种学科的混杂物。在今天的学科体制下,只能对它们作功能上的区别,即将其看作或用作哪门学科它就是哪门学科。我们很难说这些文化形态具有哪个学科特有的“本质”。那时,将旧约故事(文学)作宗教性解释、将《荷马史诗》(文学)作教育儿童的教育性范本来解释、将庄子的《逍遥游》(文学)作道家哲学上的解释,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了。这里无所谓“场外”、“场内”,也没有什么“征用”的问题。之所以形成了“场内”、“场外”之别,之所以有了今天的“场外征用”一说,无不与后来的“本质论”思维方式的兴起和受制于“本质论”思维思考问题有关。“本质论”思维要求对世界进行分类认知,对存在进行分层把握,特别是人为设定存在物深层“本质”,并企图以抓取“本质”方式达到把握存在本身的目的。它始于古希腊,经过近代理性主义和认识论哲学的建构,到19世纪末,已臻极致。也正是随着“本质论”思维的进一步强化,近现代学科分类越来越精细,界限越来越分明。黑格尔在《美学》中提出,一门学科要想成立的基本条件是具有明确而独特的研究对象,即要明确:“第一,这个对象是存在的;其次,这个对象究竟是什么”*黑格尔:《美学》(第一卷),朱光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年,第29页。。而要明确这两点,其实就是在把握对象的“本质”。反过来说,把握到了对象的“本质”,某一学科的研究对象才是明确的;研究对象明确了,作为一门学科才是成立的。这样,各门学科之间也就有了明晰的界限,也就出现了“场内”、“场外”之别。当然,“强制阐释论”并不反对跨学科,但同时认为文论“更要依靠其内生动力”,即是说,学科发展最终还是要依靠“场内”之力。同时,要使用“场外”理论,必需要服从“文学的特质”,否则就是非法“征用”。总之,严格区分为学科内/外,固守研究对象“本质”,是“强制阐释论”的基本思维方式。
再次,“强制阐释论”的“本质论”思维方式还体现在,它反对文学阐释的“主观预设”问题上。“主观预设”被认为是“强制阐释”的核心因素和方法,指的是“批评者的主观意向在前,预定明确立场,强制裁定文本的意义和价值”。具体操作包括:“前置立场”,即“在展开批评以前,批评者的立场已经准备完毕,批评者依据立场选定批评标准,从择取文本到作出论证,批评的全部过程都围绕和服从前置立场的需要展开”;“前置模式”,即“批评者用预先选取的确定模板和式样框定文本,作出符合目的的批评”,使用符号学模式、数学物理模型进行文学批评就是最突出表现;“前置结论”,即“批评者的批评结论产生于批评之前……批评不是为了分析文本,而是为了证明结论”*张江:《强制阐释论》,《文学评论》2014年第6期。。“前置结论”的说法没有太大的说服力,因为如果结论已经前置了,一个阐释活动已经失去了基本的动机、动力和意义,这种阐释活动在现实中并不多见。因此,这里的“主观预设”应主要表现在“前置立场”和“前置模式”两大方面。如此的“主观预设”其实是指认知阐释之前主体认可和选择用以指导具体认知阐释活动的立场、观念、范例、模式、原则等,它广泛地存在于现实的阐释活动中。可以认为,没有这种“前置立场”、“前置模式”为具体内容的“主观预设”,认知理解活动是难以想象的。理论史上,格式塔心理学派所说的“整体观念”、皮亚杰提出的“认知图示”、库恩标举的“预设前提”等谈的都是这个问题。在认知和阐释活动中,“主观预设”具有强大的功能,它以假定、投射、推断方式突破既定知识体系,创造新的价值内涵,使新的意义得以产生。其实,重视“前置立场”、“前置模式”或“主观预设”是现代阐释学区别于古典阐释学的标志之一。在海德格尔那里,“主观预设”被解释为“前结构”,具体包括“先行具有”、“先行视见”、“先行掌握”。它们内在于解释,并且为解释奠定基础:“解释从来就不是对某个先行给定的东西所作的无前提的把握……任何解释一开始就必须有这种先入之见,它作为随着解释就已经‘设定了的’东西是先行给定了的,这就是说,是在先行具有、先行视见、先行掌握中先行给定了的”*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陈嘉映、王庆节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年,第176页。。在伽达默尔那里,“主观预设”被称为“前理解”,它已经构成了阐释活动历史性形成的重要因素,也构成了阐释主体进行阐释活动的首要条件:“一切诠释学条件中最首要的条件总是前理解,这种前理解来自于同一事情相关联的存在(im Zu-tun-haben mit der gleichen Sache)。正是这种前理解规定了什么可以作为统一的意义被实现,并从而规定了对完全性的先把握的应用”*加达默尔:《真理与方法》,洪汉鼎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2年,第378页。。当然,“强制阐释论”并不反对阐释学意义上“前结构”、“前理解”,并对它们和“前置立场”作了区分性说明。认为,前者是“隐而不显”的、模糊的、不明确的作为解释发生背景而存在,而后者是目标清晰的、自觉主动的,或者干脆说是主观故意的。按照上文的分析,无论是“前置立场”还是“前置模式”都已经进入了阐释学历史性或阐释循环的内部,一定程度上它是历史和文化强加给具体阐释者的。它不是阐释者主观故意、主观选择能改变和左右的问题。所以“主观预设”中的“主观”只是假象,“预设”才是关键。而“强制阐释论”认为,“主观”是关键,“主观”可以改变“预设”,进而反对“主观预设”对阐释活动的介入,其实这是“本质论”模式下的一厢情愿。在这里,体现出的是“本质论”一贯坚持的“自足论”思维。正是在“本质自足性”意义上理解事物,才会认为,阐释之前可以没有“前置立场”、“前置模式”,阐释活动可以在纯粹客观意义上或“自然化”状态中进行。而实际上,这是无法做到的。
最后,“强制阐释论”的“本质论”特征最充分、最直接地体现在“本体阐释”的理论诉求中。相对于它所批判的“强制阐释”,“强制阐释论”提出了“本体阐释”概念,即“以文本为核心的文学阐释,是让文学理论回归文学的阐释”。在此,它特别强调,“‘本体阐释’以文本的自在性为依据。原始文本具有自在性,是以精神形态自在的独立本体,是阐释的对象”。这样,“文本的自在性”就成为了“本体阐释”的依据和关键。那么何谓“文本的自在性”呢?答曰:它“是指文本自身的确当含义是自在的。这个确当含义隐藏于文本的全部叙述之中。叙述一旦完成,其自在含义就凝固于文本,他人,包括作者无法更改”。文学阐释的基本要义就是“对文本自在含义的阐释”。换言之,“本体阐释”的目的就是阐释“文本的自在性”,或者干脆说“本体阐释”即“文本自在性阐释”。至此,我们已经可以看到,前面批判“强制阐释”种种说法的隐形理论依据,现在终于浮出了水面。我们也不难看到,这种理论思路与20世纪上叶英美新批评是非常相似的。需要指出的是,笔者没有把这里的“本体阐释”称为“本质主义”的,而是称之为“本质论”的,这是因为,它并没有完全在单一、封闭、静止的意义上理解“文本的自在性”。在它看来,“本体阐释”或“文本自在性阐释”不能一蹴而就,而需要通过“核心阐释、本源阐释和效应阐释”三重阐释、三重话语来实现。“核心阐释”是对文本“自身确切含义”或文本“原生话语”的阐释,它是“作者能够传递给我们,并已实际传递的全部信息”,它构成了“本体阐释”的第一层次;“本源阐释”阐释的是“创作者的话语动机,创作者想说、要说而未说的话语,以及产生这些动机和潜在话语的即时背景”,它构成了“本体阐释”的第二层次;“效应阐释”是“对在文本传播过程中,社会和受众反应的阐释”,它构成了“本体阐释”的第三层次。就是说,“强制阐释论”还是在一个较为开放和流动意义上理解文本意义的,这里似乎有了“建构论”的味道。不过,我们也不能就此说他已经走向了“建构论”,因为,它坚持把“精神形态自在的独立本体”作为文本的终极解释,文本一旦完成了,它的意义是他人包括作者都无法更改的。如此才会有“核心阐释”是中心、“本源阐释”只能是“对核心阐释的重要补充”、“效应阐释”只能是“验证核心阐释确正性的必要根据”的说法。*张江:《当代文论重建路径:由“强制阐释”到“本体阐释”》,《中国社会科学报》2014年6月16日。总体上,“本体阐释”走的是古典阐释学亦即被现代阐释学批评为独断型、决定论的阐释学的路子。它以回到某种客观、固定、自足性意义为旨归,其背后遵循的是“本质论”思维方式和理论法则。
三
回顾21世纪中国中国当代文艺学的两次论争,“反本质主义”最大的理论成果是让人们认识到,“本质主义”需要抛入历史的垃圾堆,无需任何留恋。但留下了一个并未澄清的问题,即应该如何看待文学理论中的形形色色的“非本质主义本质论”;“强制阐释论”的理论成果是让人们警惕雄霸一时的现当代西方文论并非完美范本,今天到了严正反思的时刻。问题是,“反本质主义”花大力气开拓出来的“建构”、“关系”等思路是否需要继续?中国当代文论又再次回到文学“自足论”、“自律论”老路上来是否可取?需认真讨论的更根本问题是,当代文艺学必须要在“本质论”范式中打圈圈吗?当代文艺学能否突破和如何突破“本质论”范式的怪圈?在笔者看来,中国新世纪文艺学建设需要反思的不仅仅是“本质主义”和“强制阐释”,还应深入到理论基础层面,对“本质论”范式进行反思。目前,中国新世纪文艺学建设的关键不是在“本质论”范式内部继续制造话题,而应是认清”本质论“范式的缺陷,进而在思想上明确,21世纪10年代过半的今天,还沉迷于20世纪中叶之前盛行的“本质论”,并将之奉为主流文论形态,不符合当代文学、文论发展潮流。新世纪中国文艺学应立足于20世纪以来现当代哲学人文学术的研究成果,寻找符合当代需要的理论范式,回应今天的文学文论现实,推动文艺学开拓出新的发展道路。
文艺学“本质论”范式具有难以克服的先天缺陷。这一问题上面已有所涉及,此处再作些深化。文艺学“本质论”范式是西方哲学“本质论”在文论上的落实与延展,而哲学“本质论”又是西方哲学本体论的变种或具体形态。西方传统哲学“本体论”(Ontology),以把握“存在”(On)为最终目的。它的具体把握方式是:以抽象的逻辑演绎方式特设出某个终极存在者,并以此作为解释一般存在者存在的依据。这个终极存在者在古希腊即巴门尼德的“一”、柏拉图的“相”或“型”(Idea,Eidos)、亚里士多德的“本体”(Ousia)。到了亚里士多德这里,“本质”得到了系统表述。在亚氏的“形而上学”中,“本体”(Ousia)是“存在”(On)10个范畴的首要范畴,处于基础和决定地位。而“本体”的4项内容中,“是其所是”(to ti en einai)最为重要,被规定为决定事物之为该事物的恒久不变属性。近代西语学者多把to ti en einai理解为“本质”(Wesen,Essence),为了强调“本质”在“本体”的决定性意义,有人直接把Ousia翻译为Wesen或Essence。黑格尔哲学的核心概念“绝对精神”(absoluter Geist)保留了Ousia和to ti en einai的基本意义,亦即它的Wesen(本质)意义,同时赋予它以主体性和运动性。黑格尔说:“哲学的任务或目的在于认识事物的本质,这意思是说,不应当让事物停留在它的直接性里,而须指出它是以别的事物为中介或根据的。事物的直接存在,依此说来,就好象是一个表皮或一个帷幕,在这里面或后面,还蕴藏着本质……事物中有其永久的东西,这就是事物的本质。”*黑格尔:《小逻辑》,贺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242页。这句话适用于大多数西方近代认识论哲学,认识论哲学的目的还是要把握“存在”,其基本路径和思维方式则是通过把握“本质”达到把握“本体”的目的,再通过把握“本体”达到把握“存在”的目的。在这个意义上,西方近代认识论哲学还属于“本质论”哲学。通过如上简单描述可以发现,“本质论”哲学的一些思维缺陷:首先,它采用了以部分代整体的和决定论的思维方式。尽管“本质”可能是“本体”的首要方面,“本体”是“存在”的首要方面,但忽略了存在者非“本质”的、非“本体”的方面,而认为抓住了“本质”就等于抓住了“本体”、抓住了“本体”就等于抓住了“存在”,是武断的、片面的和决定论的。其次,会形成“本质”中心主义。即当“本质”被确定为“存在”的重中之重后,自然它也被置于了中心地位,并形成对非“本质”方面或因素的统治和支配。而一旦某种处于中心位置的“本质”自我膨胀和滥用特权,就可能造成诸多严重后果。人们常说的各种中心主义——“理性中心主义”、“人类中心主义”、“男性中心主义”、“西方中心主义”,等,就是“本质”中心主义的具体化。今天,这些中心主义已经给人类带来了各种灾难性后果。再次,导致“本质”还原主义。如果“透过现象看本质”和“以部分代整体分析法”的过度使用,就可能造成对现象世界中非“本质”性的存在方面和因素的忽视、轻视和盲视,就可能把丰富多彩、多元立体的现象世界简化或还原为简单的、一元的本质,并自以为抓到了简化、单一的“本质”就已经把握到了存在整体和存在本身。最后,形成“本质论”的基础主义。上述几个特点叠加在一起,可能会给“本质论”带来一种错觉:探究世界和存在者的“本质”就是哲学的终极目的,而以这一目的为旨归的“本质论”哲学就应该成为其他人文学科的理论基础。
哲学“本质论”思维方式运用于文学理论,也使它的种种缺陷被保留了下来。“本质论”文论的基本目标也是企图通过“透过现象看本质”和“以部份代整体”方式达到把握文学存在本身的目的。具体做法是,把文学整体活动中的某个局部过程或环节看成是决定性,人为将之抽离出来进行抽象分析,最后把这一局部性存在属性宣布为文学“本质”,并就此认为已经一劳永逸地解决了文学的基本问题。文论史上,古老的“模仿说”及其各种后世变体——“镜子说”、“再现说”、“反映说”、“能动反映说”、“审美反映说”等,无不是着眼于文学活动中的“世界—作品”或“世界—作家—作品”的局部环节和关系,作出关于文学是对世界或某种“客观精神”的模仿、反映、再现等“本质”规定。表现说及其各种变体——“直觉表现说”、“本能升华说”、“精神主体说”、“人类学本体论说”等,都是立足于文学活动的“作家—作品”环节和关系,将作家的主体方面,诸如心灵、情感、潜意识、生命能量等的表达、表现规定为文学“本质”。我们知道,从20世纪初开始,“本质论”成为哲学反思和批判的对象,但文论领域仍滞后性地延续到20世纪中叶。如上所述,广义形式主义文论主要是立足于文学活动的“作品”这一单一环节,从语言形式、叙事结构等方面作出了文学“本质”的种种规定。
西方文论自20世纪中叶之后,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现象学文论、接受美学、阐释学文论逐渐抛弃了“本质论”思路,而是以一种新的哲学眼光关照文学存在问题。这种新的哲学思想在具体流派中表述不同,但将之统一称为“现代存在论”应该是成立的。“现代存在论”不再追问作为存在者“本质”或“是什么”的问题,而是追问存在的“如何是”问题。它立足于存在者的整体而非某个部分(尽管可能是重要的具有决定意义的部分),通过分析存在者的如何存在即存在方式达到把握存在本身的目的。以“现代存在论”为哲学基础建构的文学理论即存在论文艺学。它主张立足文学活动整体、文学文本全貌对文学进行综合性和总体性研究。这一点是适应近半个世纪以来中西方文论发展的大趋势的。有学者曾对这一趋势作过阐述:20世纪后半叶以来,“一种综合性、总体性研究早就显现出了强劲的发展态势。例如,杜威的实用主义批评、英伽登的现象学美学、萨特的存在主义文论等等,都不约而同地加强了对研究对象的综合性探讨和整体性把握,他们都注意到了传统文论将作家、作品和读者割裂开来进行孤立研究的缺陷和不足。在这一方面,现代解释学和接受美学的理论自觉性表现得更为突出”*陈定家:《文本意图与阐释限度》,《文艺争鸣》2015年第3期。。存在论文艺学反对传统“本质论”、“本体论”关于文学某一固定、单一、一元“本质”和“本体”的追索,不赞同一些文化研究派所主张的文学相对主义和意义虚无论,也不同意所谓文学“本质”多元论和在历史、语境、关系中有条件地把握文学“本质”的做法。存在论文艺学把文学存在方式和文学存在价值看成两大基本研究主题,在这两大基本主题形成的基本框架下开展文学具体问题研究。文学存在方式研究,即研究作为存在者诸文学要素和整体文学现象是如何存在的,它是以何种状态、结构、面貌整体性地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按照笔者的浅见,这些文学存在者包括世界、作家、作品、读者、媒介等具体要素,前四个要素被作为文学活动第五要素的媒介连成一个整体,形成活动过程。文学存在价值研究是对文学存在方式研究的进一步推进,即研究文学存在方式或文学活动对于人而言的价值。文学活动之于人的价值是存在论层面的,即关乎人对最根本的意义性“存在”本身追索、感悟的问题。正是在文学活动中,人“在世界中存在”的状态发生了不同于一般现实世界中的变化。此时这个“世界”是文学艺术的世界,人“在世界中存在”就具体化为了人“在艺术世界中存在”。这个艺术世界是不同于现实的超越性世界,它是个虚构世界,是个虚拟世界,是个可能世界。在这一世界中的作者以艺术创造方式不断追问意义(存在)、探索意义(存在),并将理解、感悟的意义投入文本;读者则根据“前理解”阐释文本,这种阐释不可能是对文本固定意义的还原。在文学活动中,意义不可能是一种“自洽”、“自主”、“自在”的,作者投入文本中的意义如果还处于静止凝固状态,只是文学意义发生的潜在状态,还算不上真正的文学意义。真正的文学意义是在主体间交流、“谈话”中不断生成、涌现、绽放出来的,并以这种方式存在着的。随着意义(“存在”)的不断发生,人的存在状态也在不断变化,不断走向澄明境遇。
存在论文艺学在中国当代文论发展中早已展露过头角。1990年代,在实践美学争鸣中涌现出了“存在论美学”,后来有学者把现代存在论思想与马克思的实践哲学结合在一起,形成了“实践存在论”美学。此外,后实践美学中的“生命美学”、“超越美学”也积极吸收了存在论思想,尽管有理论变形的状况。1990年代末,有学者把存在论思想用于对生态美学的研究,改造了“认识论生态美学”,形成了“生态存在论”美学。这些以存在论为理论基础的各种美学思想,给存在论文艺学提供了方法论和理论资源。在文艺学领域,早在1980年代文艺学方法论的讨论中,有学者就曾倡导过文学存在方式研究。之后,关于文学存在方式的研究尽管未进入主流视野,但一直没有中断。最近几年,笔者不惴浅陋,从今天的新媒介文化、文学现实出发,将现代存在论与现代媒介学研究结合在一起,提出了“媒介存在论”思想,并以此为哲学基础努力建构媒介文艺学,可以被视为当代存在论文艺学研究的一支。当然,关于存在论文艺学的研究,还存在着诸多问题。比如,1990年代有学者把艾布拉姆斯、刘若愚倡导的文学活动四要素说引入中国,并与马克思的人的活动理论相联系,构造中国当代文学活动论,其中就有着存在论文艺学的理论观念。而理论界却把它看成是文学“本质论”的一种。更有学者把存在论中的“存在”也看成一种“本质”,倡导“存在论的本质主义”。这种将存在论混淆为“本质论”、将文学存在方式混淆为文学“本质”的问题亟需认真清理。
总之,在“反本质主义”和超越“本质论”范式之后,在今天的理论多元化背景下,建构现代存在论文艺学应该成为文艺学建设的重要选择之一,它蕴含着推动中国当代文艺学走向新发展阶段的强大力量。
[责任编辑:以沫]
From the “Anti-essentialism” to the “Theory of Peremptory Interpretation”——The Lost of the “Essence Theory” about Chinese Contemporary Literary Theory and it’s Theoretical Breakthrough
SHAN Xiao-xi
(College of Humanities, Hangzhou Normal University, Hangzhou 311121, P.R.China)
The theoretical debates of Chinese contemporary literary theory are based on the inner contradiction about the “essence theory” paradigm. The “Anti-essentialism” makes a claim to surpass the “Essentialism” and to carry out the construction work of Chinese contemporary literary theory by the theoretical model about the “Constructivism”, “Relationalism”, “Time-travelism” and so on. But they still haven’t transcended the category of “Essence theory” literary theory in the whole. The “theory of Peremptory Interpretation” criticized western contemporary literary theories, which interpreted literature peremptorily by the way of “Off-site requisition” and “Subjective presenting”, and proposed to explain literature with “Ontological Interpretation”. However, during interpreting the “Peremptory interpretation” and the “Ontological interpretation”, it adhered to the basic concept of the literary “Essence theory”. If Chinese contemporary literary theory wants to achieve the significant breakthrough, it needs to be out of the theoretical circles of the “Essence theory” paradigm. It can be one of the choices that construct the modern Ontology literary theory as the way to develop and construct Chinese contemporary literary theory.
Anti-essentialism; Theory of Peremptory Interpretation; “Essence Theory” Paradigm; Modern Ontological Literary Theory
2016-06-08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当代数字媒介场中的文学生产方式变革研究”(10CZW011)。
单小曦,杭州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杭州 3111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