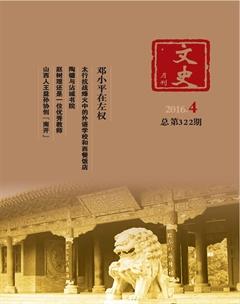容闳:中国近代留学教育的先行者
张瑞安
容闳(1928—1912),号纯甫,广东香山人,是中国近代著名的教育家、外交家和社会活动家。他不仅是近代第一个赴美留学的中国人,也是中国近代留学第一人。他克服重重困难,赴美留学,毕业于耶鲁大学,为中国近代留学事业作出了卓越贡献,被誉为“中国留学生之父”。
出身贫寒,自幼入教会学校读书
鸦片战争前,尽管清廷一直实施禁教政策,但西方传教士一直在中国沿海地区悄悄从事传教活动,并成立一些教会学校以吸引穷苦孩子入学,以此作为增强教会感染力的必要手段。1835年,为纪念英国传教士罗伯特·马礼逊,在华传教士在澳门创办了“马礼逊学堂”,由传教士郭士礼的夫人负责督导。

1828年,容闳出生在广东香山县一户贫寒农家。科举盛行的年代,有钱人家的子弟无不以科考为志。但容闳的父母无力让他接受私塾书院的传统教育,只好送他入免费的教会学校。容闳的父亲是一个受到近代商业贸易大潮冲击的人,他让容闳学西学的目的是将其培养成为一个能给容家带来财富的“通事”“买办”或“洋务委员”。容闳回忆他父亲当时的心态说:“是时中国为纯粹旧世界,仕进显达,赖八股为敲门砖,予兄方在旧塾读书,而父母独命余入西塾,此则百思不得其故。意者通商而后,所谓洋务渐趋重要,吾父母欲先着人鞭,冀儿子能出人头地,得一翻译或洋务之优缺乎。至于予后来所成之事业,似为时世所趋,或非予父母所及料也。”也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容闳被父母送进了教会学校。
学校对学童管束极为严格,规定男女学童不得在一起玩耍,但对年龄最小的容闳则给予特殊优待,命居女院中,不与男童杂处。同时,规定的教学量也很大,每日上午授课,下午集会,晚饭后还有晚课,至9点才休息。每周又有中英文考试若干次,繁重的学堂生活使得喜欢自由自在的容闳很难适应,但几年的刻苦学习使容闳的各科成绩突飞猛进。然因经费问题和鸦片战争的爆发,“马礼逊学堂”被迫于1839年停办,容闳因此失学。祸不单行,他的父亲在1840年不幸病逝。家中经济支柱断折,12岁的容闳不得不和哥哥、姐姐外出贩卖糖果和捡稻穗以维持家庭生计。
在苦难的生活中,容闳等来了“马礼逊学堂”的开学,复校后的“马礼逊学堂”迁往香港,由美国传教士布朗主持。布朗是耶鲁大学1832年的毕业生,取得神学博士学位。接手管理后,他对教学课程进行了改革,设置了数学、地理、英文、中文等。由于容闳先前曾在郭士礼夫人那里学过几年,有一定英文基础,学习成绩总是名列榜首。布朗博士认为他是一个有前途的学生,想方设法培养他,甚至在容闳欲辍学去工作维持家庭生计时,“马礼逊学堂”作出资助他7年生活费的决定。在教会学校几年的学习使容闳的知识水平提高很快。
赴美留学,终有成就
1846年的一个冬日,“马礼逊学堂”校长塞缪尔·布朗博士向全体学生郑重宣布:“因身体状况欠佳,准备休假回国调养。此行愿带三五名学生赴美留学。我已与香港基督教会的几名教友谈妥,他们愿意为每人提供2年的留学经费和父母的赡养费。诸生有愿意前往者,请起立。”
40多名中国学生面面相觑,默不做声,最后仅有3人悄然起立,其中之一就是容闳。容闳3人虽非大勇之辈,却也不乏冒险精神。要知道,当时的中国对海外世界茫然而又感到恐惧。港澳居民虽有人跨海出洋,但那是为生计所迫,不得不远走异域他乡谋生。至于出国留学,尚属史无前例,是福是祸,难以意料。当容闳回家请示母亲时,寡母怏怏不乐。后经容闳再三请求,容母才忍痛首肯,但已凄然泪下。
带着家人的牵挂,容闳随布朗进入马萨诸塞州的孟松学校就读。美国那时尚无高中,仅有为投考大学而设置的预备学校,孟松学校就属于这类学校。不过,容闳开始并未想升入大学。因为他的留学经费只有两年,1849年期满即须回国。两年时间很快到了,容闳想报考耶鲁大学,继续深造。但他一人置身异域,无所依靠,只好仍向布朗先生求助。布朗找到孟松学校校董。校董同意资助容闳入大学,但附带一个条件,容闳毕业后必须回国做传教士,容闳毅然拒绝了。他说:“予虽贫,自由所固有。他日竟学,无论何业,将择其最有益于中国者为之。……盖人类应尽之天职,决不能以食贫故,遽变宗旨也”,寥寥数语,掷地有声!容闳决心为中国谋福利,不移于贫贱,不淫于富贵,其对国家的拳拳挚爱之心,可旌可表,时至今日,仍不失为莘莘学子的楷模。

人生际会,命运往往非所逆料。当容闳拒绝孟松校董的资助后,真是茫茫人海,孤立无援。从孟松学校毕业已近一年,倘若再无办法,容闳只有束装归国了。恰在此时,布朗往美国南部探望其姊,顺道拜访乔治亚州萨伐那妇女会会员,谈及容闳升学经费问题。未料深得该妇女会会员们的同情,慨然允予资助,经费有了着落,容闳径趋耶鲁大学投考。虽然他在美国只读过15个月的拉丁文,12个月的希腊文和10个月的数学,但由于他学习刻苦用功,考试一举中的。
容闳的大学生活既丰富多彩,又充满艰辛。他在描述一年级的情况时说:“余之入耶鲁大学,虽尚无不及格之学科。然在教室受课,辄觉预备工夫实为未尽,以故备形困难。盖一方面须筹划经费,使无缺乏之虞;一方面又须致力所业,以冀不落人后也。尚忆在第一年级时,读书恒至夜半,日间亦无余晷为游戏运动。”学习之外,他还替20余名住校的美国学生当“炊事员”,后来又为兄弟会管理图书,所得收入补充学费,免除了经济上的后顾之忧。
“艰难困苦,玉汝于成”,这个苦读的中国学生终于读出了好成绩。在耶鲁,他两次夺得英文论文竞赛首奖,“校中师生异常器重,即校外人亦以青眼相向”。1854年,容闳从耶鲁大学毕业,他是第一个毕业于美国大学的中国留学生。
归国后为中国近代留学事业积极奔走
容闳既以自己是一个毕业于美国大学的中国人而自豪,又以自己是第一个毕业于美国大学的中国人而苦恼。他说:“予当修业期内,中国之腐败情形,时触予怀,迨末年而尤甚。每一念及,辄为之怏怏不乐,转愿不受此良教育之为愈。盖既受教育,则予心中之理想既高,而道德之范围亦广,遂觉此身负荷极重,若在毫无知识时代,转之不觉也。更念中国国民,身受无限痛苦,无限压制。此痛苦与压制,在彼未受教育之人,亦转毫无感觉,初不知其为痛苦与压制也。”
放眼西方,资本主义正处在上升时期,他回首祖国,满目疮痍腐败。这使年轻的容闳深感沮丧和失望。一度因此而消沉苦闷。经过反复思索,他终于从悲观中奋起。“予意以为予之一身,既受此文明教育,则当使后予之人,亦享此同等之利益。以西方之学术,灌输于中国,使中国日趋于文明富强之境。”具体而言,便是他立志要派遣更多的中国青年学子留学美国。
路漫漫而修远。容闳回国后,处在一种阴暗险恶的环境之中。当时的中国还是一个纯粹的旧中国,众人皆旧他独新,自然使他难容于当时的中国社会。容闳留美归国后,入世谋生颇为不易,曾作过律师,当过翻译,经过商,数易其职,还不时遭受失业的厄运。一个美国名牌大学的毕业生还远不如一名科举出身的小绅士。
即便如此,容闳心中派遣留学生的计划从未忘怀。他一直在寻找机会之门。他知道,靠个人的力量是无法实现自己的计划的,必须借助某些有权势而又关心公益的实力人物。机遇终于来临,1863年,容闳通过数学家李善兰,结识了两江总督曾国藩。曾国藩当时功业鼎盛,声誉正隆。容闳颇想立即通过这位实力人物推行自己的教育方案。不过,他没有操之过急,主要通过襄助曾国藩筹备洋务,且成绩斐然,以此博得了曾国藩的信任和赏识。
1870年,天津教案发生,江苏巡抚丁日昌协同曾国藩处理善后,电召容闳为译员。容闳感到良机在握,乘机进言其留学教育计划。曾国藩表示赞许,并很快和李鸿章等人联名上奏。未久,清廷批复同意,容闳十年的夙愿即将成为事实。
力促赴美留学幼童计划的推行与中途夭折
1871年,容闳等人开始了紧张的筹备工作。按照规划,决定挑选12岁左右的幼童120名,分4年派赴美国,每年30名。以今日情形推之,公费留学美国,既是首次,人数又少,竞争必定相当激烈。其实不然,第一批30人在上海招考时,竟未招足。容闳只好南下香港,在英政府所设的学校中挑选数人,才凑足定额。之所以如此,固与那时缺乏报纸广播等新闻媒体有关,但主要原因是中国当时闭塞保守,风气未开。那时大多数中国人迷信的是考科举,入仕途。至于进洋校,读洋书,则被人嗤之以鼻。因此,最后应选留学者大都出身微贱。当时,清政府要求这些洋幼童的父母出具亲笔画押的“甘结书”,其中写道:“兹有子××情愿送赴宪局带往花旗国肄业,学习技艺。回来之日,听从差遣,不得在国外逗留生理。倘有疾病生死,各安天命。”从“甘结书”也反映当时中国朝野视出国留学为畏途。“生死各安天命”,大户人家谁肯以十余岁的幼儿作此尝试!
尽管如此,在容闳等人的竭力筹划下,留美教育计划最终得以实现。1872年8月11日,包括詹天佑在内的中国政府派出的第一批官费留美学生从上海启程出洋。在1872—1875年间,清政府先后遣送120名幼童赴美留学,近代官派留学由此开端。
对容闳来说,留美教育计划花费了他十余年的心血才得以实现,无疑是步履蹒跚了,然而对当时的中国社会而言,容闳的教育计划又仿佛是一朵过早开放的花,它缺乏适宜的土壤,也缺乏适宜的气候。当花蕾初绽时,真正苦心培植的只有容闳一人。在清朝官场中,唯一支持他的实力派是曾国藩。但不幸的是,曾国藩在1872年3月便病故了。此时第一批幼童尚未正式出国。而接替的李鸿章虽然也是洋务重臣,但他和曾国藩有天壤之别,其为人感情用事,首鼠两端,喜怒无常。因此,在留学教育问题上,容闳在清朝官场中实际上是孤立的。120名幼童名义上是清政府“官派”,而事实上自始至终是容闳独当一面。容闳的职务开始只是一名留学生副监督,在容闳的周围,几乎是清一色的守旧派,连留学监督陈兰彬、吴嘉善也都是典型的顽固派,艰难困苦,可想而知。当时,江苏巡抚丁日昌相比之下要算是比较开明的官员。他曾推心置腹地对容闳说:“君所主张,与中国旧学说显然反对。时政府又甚守旧,以个人身当其冲,恐不足以抵抗反动力,或竟事败于垂成”,容闳自己也未尝没有看到这一点。

1874年,容闳在美国建造了一所坚固壮丽的房子,作为中国留学生事务所永久办公之地。容闳自称:“予之请于中国政府,出资造此坚固之屋以为办公地方,初非为徒壮观瞻,盖欲使留学事务所在美国根深蒂固,以冀将来中国政府不易变计以取消此事,此则区区之过虑也。”后来事态的发展表明容闳的这一做法有些近乎天真。顽固派的力量虽然强大,但开始时慑于曾国藩的声威,尚不敢公然反对。在曾国藩初死的两三年里,容闳还可以借助曾氏的余威抵挡一阵。当曾氏余威消殆,顽固势力如狂飙暴起。此时的容闳可以说是以一人敌一国。顽固派最关心的是所谓学生的道德和“中学工夫”。他们害怕在美国学校中读书、与美国家庭融成一片的学童们再也不愿回到儒学所规定的旧有道路上去。于是,他们在留学肄业局的大堂里挂起孔子的画像让学生随时参拜,责令学生自觉读写中国典籍,并定期到中国留学生肄业局学习汉语和中国礼仪。
但让受基督教影响的留美幼童对美国政治及社会发展无动于衷则是不可能的事。随着时间推移,中国留美学生的行为观念摆脱了顽固派设计好的“中体西用”模式,而向与美国学生一样的“西体西用”的方向日益偏离。在美国资产阶级文化的影响下,幼童们不再对四书五经、国朝律例、圣谕广训一类传统典籍或规范感兴趣,对定期的“望阙行礼”“参拜先圣”“叩头见官”一类的封建礼仪也掉以轻心,甚至公然剪掉辫子。另一方面,他们对游泳、滑冰、打球、钓鱼、骑自行车、下棋、旅行,甚至参加教堂活动很感兴趣。对留学生的这些变化,思想开放的容闳觉得并没有什么不妥,但以陈兰彬为代表的顽固派却认为是大逆不道,无法容忍,对容闳和留美幼童展开攻击,说留美幼童“适异忘本”“离经叛道”。“外洋风俗流弊多端,各学生腹少儒书,德性未坚,尚未究彼技,先已沾其恶习。即使竭力整饬,亦觉防范难周,极应将局裁撤。”顽固派的这一恶箭使容闳无招架的余地。1881年6月,清政府做出了撤回留美幼童的决定。丁日昌最初所预言的“事败于垂成”竟不幸而言中。
清政府原定幼童留美期限为15年。当1881年留美幼童分三期被全部撤回时,在美时间最长的第一批幼童也只留学9年,最短的第四批幼童仅留学6年。幼童赴美时,是从小学读起。当他们撤回时,只有詹天佑、欧阳赓两人已大学毕业,其余60余人尚在大专院校就读,另一些人还仅是中小学学生。
中途撤回的留美学生如同囚犯一般,其状凄然。当他们踏上祖国的土地时,没有熟悉的亲友的迎候,没有微笑和热情的拥抱,只有几辆独轮车将他们运载到中国海关道台衙门。沿途围观的是惊异和嘲笑的人群。到海关道台衙门后,为了防止他们脱逃,一队水兵把他们押送到一所形同监狱的“求知书院”禁闭起来。时值中秋佳节,他们期待着与自己阔别多年的父母亲友团聚,可是那种温情被剥夺了。清朝统治者的愚昧无知,使他们根本不懂得他们所糟踏的是一批学有专长的新型知识人才。在他们的眼里,这批留美学生是一批异化了的“洋鬼子”,甚至是危险分子。早期留美学生归国后受到的这种冷遇和困境,正显示晚清帝国在受到西方文明挑战时反应不良的症状。
容闳所倡导、经办的中国第一波留学运动虽然因封建守旧势力的破坏而半途夭折,但它的历史功效却并没有就此宣告终结。这批留美学生日后大都成为中国各个领域的骨干力量。在这批留学生中,从事工矿、铁路、电报业者有30人,其中矿师9人,工程师6人,铁路局长3人;从事教育事业者5人,其中大学校长2人;从事外交、行政者24人,其中领事、代办以上外交官12人,外交次长、公使2人,外交总长1人,内阁总理1人;从事商业者7人;从事海军者20人,其中海军将领14人。他们在中国走向现代化社会的过程中,发挥了“向导”和“纤夫”的双重作用。
更具历史意义的是,容闳开办的留学教育开创了中国培养人才的新途径。由于这一途径直接与西方文化接轨,绕开了洋务派学堂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保守模式,西方资产阶级的先进的科学技术和政治社会学说犹如乘上了特别快车,更迅速地洞贯中国。此后,封建保守势力再也无法将西学阻止于国门之外了,从西方教育体系中培养出来的新型知识分子本身就是西方文化的活的载体。新的知识与观念通过他们渗入中国朝野。而这种新知识与新观念对中国的“穿透”又为中国资产阶级改良与革命大规模的来临做了思想上的启蒙。
带着对晚清政府的深深失望,容闳后来参与了维新变法和辛亥革命,孙中山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后,亲笔写信给容闳,邀请他归国担任要职,并随信寄去一张照片,但不幸的是此时容闳已罹患重病,于1912年4月21日病逝于美国康州寓所,终年84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