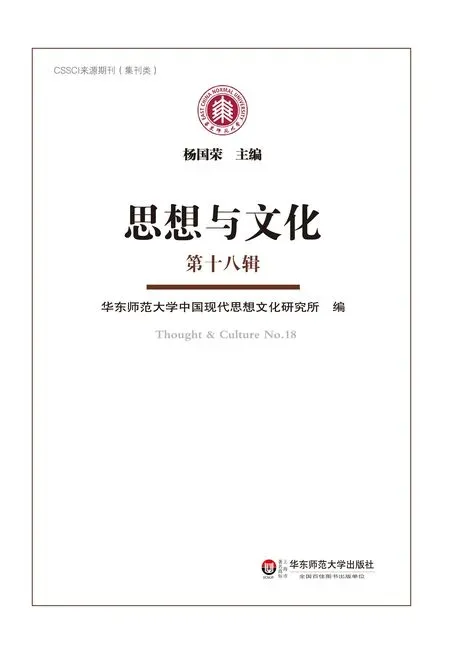宫室居住与生活政治
——以《礼记》为中心的考察*
朱承
居住是日常生活中重要组成部分,人类逐步按照自己主观意志构造居住空间,成为人类文明生活进步的重要标志。就中国传统而言,在先秦文献中,人们按照自己的意志来构造适应居住的空间,大概可以溯源到“有巢氏”的传说。“且吾闻之,古者禽兽多而人少,于是民皆巢居以避之。昼拾橡栗,暮栖木上,故命之曰有巢氏之民。”(《庄子·盗跖》)“上古之世,人民少而禽兽众,人民不胜禽兽虫蛇。有圣人作,构木为巢以避群害,而民悦之,使王天下,号曰有巢氏。”(《韩非子·五蠹》)从《庄子》和《韩非子》的描述来看,居住在树木上“巢居”形式,可以算作人们有意识地改造自然从而改善自己的居住空间。按照《韩非子》里的记述,因为可以带领大家“构木为巢”从而避免动物的侵害,那些能够营造居住空间的人甚至可以被人大家拥戴为王,在共同体中成为权威。从这个意义上来看,日常生活的居住问题便具有了政治意义。
传说固然有待考证,但在中国文化传统中,宫室建筑除却工艺、审美意义以及满足生理意义上的需求之外,还带有伦理意义、秩序意义和政治意义,具有多方面的蕴含,梁思成认为,中国建筑“或为我国人民居处之所托,或为我政治、宗教、国防、经济之所系,上自文化精神之重,下至服饰、车马、工艺、器用之细,无不与之息息相关。中国建筑之个性乃即我民族之性格,即我艺术及思想特殊之一部,非但在其结构本身之材质方法而已”。*梁思成: 《中国建筑史》,天津: 百花文艺出版社,2005年,第3页。中国传统宫室建筑所呈现的政治、社会、伦理意义,尤其是在儒家礼乐文明中体现的较为明显,围绕宫室、居住而形成的礼仪制度,是古典礼乐文明的重要内容之一。本文将以《礼记》文本为中心,从“生活政治”的角度来考察儒家关于宫室居住礼仪制度的政治意义。
一、 宫室居所与政治象征
改造自身住所是人类改造自然能力提升的重要表现,住所的改善使得人们提升了抵御自然侵害的能力,同时也标志着文明的进步。在中国古代传统里,生活环境的改善、日常生活水平的改进,都会被看作是圣人之功。从“穴居”跃进到“宫室”,同样也被视作是圣人的功劳: “上古穴居而野出,后世圣王易之以宮室。上栋下宇,以待风雨,盖取诸大壮。”(《周易·系辞下》)“昔者先王未有宫室,冬则居营窟,夏则居橧巢。……后圣有作,然后修火之利,范金,合土,以为台榭、宫室、牖户。”(《礼记·礼运》)圣王因其超群的能力而改变人们的生活,也因此获得权力的合法性,受到人们的尊崇和追随,首创宫室的能力就是圣王政治及权威合法性的来源之一。*这种说法,直到近代,依然有回响。孙中山在《三民主义》里就曾提道: “有巢氏教民营宫室,也做皇帝,那就是木匠做皇帝。”孙中山: 《三民主义》,长沙: 岳麓书社,2000年,第140页。可见,在古典的视域里,居住的问题就不仅仅只关涉生活领域,还具有政治和秩序意蕴,居住场所及其营造过程是重要的政治象征。
宫室首先是权力和威严的象征。宫室作为政权所有者的居住之地和国家议政之地,是一种权力的标志,反映着政权希望被民众如何看待。古代中国的历朝历代,建国之初,往往都首先要规划都城、建立宗庙、营造宫室,除了可能因为战争的破坏而必须重建之外,宗庙宫室的营造还有多重意义,如展现本朝的新气象、凸显新政权及其拥有者的威严、塑造宗法谱系的象征物等等。宫室作为政治人物日常居住和行使权力、处理公务的主要场所,也是展现政权威严、权力差异和礼仪等级的重要载体和象征符号,因此,考察中国古代政治文化和宫室的营造与布局,往往可以成为一个重要的切入点,历代的宫室建筑也是探究王朝政治文化的一个窗口。
秦代造阿房宫,“先作前殿阿房,东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上可以坐万人,下可以建五丈旗,周驰为阁道,自殿下直抵南山。表南山之巅以为阙”。*(汉)司马迁撰: 《史记》卷六,第1册,北京: 中华书局,1959年,第256页。如此宏大的建筑,足以显示君主的威仪和气势,更足以夸耀于天下。《史记》还记载汉代萧何劝说刘邦建设宫室事: “萧丞相营作未央宫,立东阙、北阙、前殿、武库、太仓。高祖还,见宫阙壮甚,怒,谓萧何曰: ‘天下匈匈苦战数岁,成败未可知,是何治宫室过度也。’萧何曰: ‘天下方未定,故可因遂就宫室。且夫天子以四海为家,非壮丽无以重威,且无令后代有以加也。’上说之。”*(汉)司马迁撰: 《史记》卷八,第2册,北京: 中华书局,1959年,第386页。此处,萧何将天子富有四海之威与宫室的华美壮丽结合在一起,赋予了宫室以政治意义,正合高祖刘邦匡定天下之志。王夫之认为,萧何此语鄙陋,但却实在。王夫之在《读通鉴论》里曾评论道: “其言鄙也,而亦尝非人情也。游士之屦,集于公卿之门,非必其能贵之也;蔬果之馈,集于千金之室,非必其能富之也。释、老之宫,饰金碧而奏笙钟,媚者匍伏以请命,非必服膺于其教也,庄丽动之耳。愚愚民以其荣观,心折魂戢而荧其异志,抑何为而不然哉!特古帝王用之怀异耳。”*(明)王夫之: 《读通鉴论·汉高帝·十三》,《船山全书》第10册,长沙: 岳麓书社,1996年,第88页。以壮丽的建筑来摄动人心、威撼群盲,故而帝王常常能用此来帮助其树立政治权威性。在这种政治与建筑相关联思想的主导下,汉代宫室的营造逐渐加码,宫室之华美壮丽程度不断递升,班固《西都赋》对此作了如是描述和形容:
其宫室也,体象乎天地,经纬乎阴阳,据坤灵之正位,放太紫之圆方。树中天之华阙,丰冠山之朱堂。因瑰材而究奇,抗应龙之虹梁。列棼橑以布翼,荷栋桴而高骧。雕玉瑱以居楹,裁金璧以饰珰。发五色之渥彩,光焰朗以景彰。于是左墄右平,重轩三阶。闺房周通,门闼洞开。列钟虡于中庭,立金人于端闱。仍增崖而衡阈,临峻路而启扉。徇以离殿别寝,承以崇台闲馆,焕若列星,紫宫是环。清凉、宣温、神仙、长年、金华、玉堂、白虎、麒麟,区宇若兹,不可殚论。增盘业峨,登降炤烂,殊形诡制,每各异观。乘茵步辇,惟所息宴。*费振刚、仇仲谦、刘南平: 《全汉赋校注》,广州: 广东教育出版社,2005年,第466页。
班固以瑰丽的辞藻刻画了西汉宫室的奢华与壮观,庞大的宫室建筑群体现了皇权的尊荣。汉末仲长统在《昌言》里也描述了汉代逐渐奢华的宫室建筑: “今为宫室者,崇台数十层,长阶十百仞,延袤临浮云,上树九丈旗,珠玉翡翠以为饰,连帷为城,构帐为宫,起台树则高数百丈,璧带珠玉,土被缇锦。”*(唐)欧阳询撰、汪绍楹校: 《艺文类聚》卷六十一,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1965年,第1095页。魏晋时期,何宴在《景福殿赋》中说: “不壮不丽,不足以一民而重威灵。不饬不美,不足以训后而永厥成。”*(梁)萧统编、(唐)李善注: 《文选》,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526页。在何宴看来,宫室的“壮丽”具有“一民”的政治功能,可以体现国家政权对于民众统治的唯一性,民众会因为宫室的壮丽而崇敬君主的权威,唐代骆宾王在《上吏部侍郎帝京篇》中有云: “山河千里国,城阙九重门。不睹皇居壮,安知天子尊。”*(唐)骆宾王著、(清)陈熙晋笺注: 《骆临海集笺注》卷一,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6页。此诗一语道破宫室与政治权力的关系,宫室是为政治权力服务的,用来凸显权力的尊贵。可见,在中国传统建筑尤其是与帝王相联系的住所宫殿中,其建造的目的往往已超出居住的日常功用范围,而更多的是用来显示帝王的权势尊严。“为人主上者,不美不饰之不足以一民也;不富不厚之不足以管下也;不威不强之不足以禁暴胜悍也。”(《荀子·富国》)权力拥有者常常需要借助外在物来不断强化自身的权威,同时还需要利用这些外在物来强化治理,荀子这里提到的“一民”“管下”“禁暴胜悍”,与政权的有效统治以及社会生活的有序相关,所指都是一种良好治理的效果。就荀子的这个逻辑来看,君主大力建设豪奢的居所与宫室,不仅是为了个人的生活享受,同时还具有深厚政治意味。
在宫室礼仪制度中,明堂制是最为重要的一种。儒家典籍中所记载的“明堂”,集中地体现了宫室作为权力的象征,承担着君主对于行使排他性的最高权力的需求,“夫明堂者,王者之堂也。王欲行王政,则勿毁之矣”(《孟子·梁惠王下》)。关于“明堂”的政治作用,《礼记》中描述为: “朝诸侯于明堂,制礼作乐,颁度量,而天下大服。”(《礼记·明堂位》)明堂是国家最为重要的政治场所,关系到国家权力的威严。孙希旦认为《礼记》的“明堂位”篇“记周公相成王朝诸侯于明堂以致太平”*(清)孙希旦撰,沈啸寰、王星贤点校: 《礼记集解》中,北京: 中华书局,1989年,第839页。,“致太平”就说明了明堂的政治意义,虽然对于《礼记·明堂位》中的周公与成王关系、鲁公僭礼等问题,史学界自来就有很多不同看法,但单就“明堂”的政治性意义而言,大致没有什么分歧*汪宁生先生在“释明堂”一文中,曾较为详细地介绍过明堂的由来与功能,他认为,“明堂原是公众集会之处和各种集体活动的中心,具有祭祀、议事、处理公共事务、青年教育和训练、守卫、养老、招待宾客及明确各种人社会身份等功能。进入阶级社会以后,统治者利用明堂作为祭祀和布政施教之处,但原来明堂的各种功能仍有迹可寻”。汪宁生: “释明堂”,《文物》1989年第9期,第24页。从这里也可看出,虽然早期社会的“明堂”可能承担了较多的功能,包括祭祀、教育、宴饮等,但公共性的政治事务也是其最为核心的功能。。郑玄为《考工记·匠人》中“明堂”作注道: “明堂者,明政教之堂。”唐代成伯璵的《礼记外传》中也说: “明堂,古者天子布政之宮,黄帝享百于明廷是也。”*(宋)李昉等编: 《太平御览》(上海涵芬楼影印本《四部从刊三編》),卷533,第2547页。可见,明堂是具有鲜明政治意味的场所。班固在《白虎通》里指出,明堂承担着多重功能,“天子立明堂者,所以通神灵,感天地,正四时,出教化,宗有德,重有道,显有能,褒有行者也”。*(清)陈立撰、吴泽虞点校《白虎通疏证》卷六,北京: 中华书局,1994年,第265页。昭告神灵、制礼作乐、颁定度量、表彰德行,皆为国之大事,需要在具有高度威仪象征之所举行,而明堂就承担了这样的政治功能,为国家政令提供政治正当性的场所保证,具有重要的政治象征意味。从《礼记》中来看,明堂的营造与装饰,皆显示天子的尊崇地位,“大庙,天子明堂。库门,天子皋门。雉门,天子应门。振木铎于朝,天子之政也。山节藻棁,复庙重檐,刮楹达乡,反坫出尊,崇坫康圭,疏屏;天子之庙饰也。”(《礼记·明堂位》)明堂的每一个建筑细节,都标示着它与其他建筑物的不同,且都有政治象征蕴含其中。在明堂的集会过程中,天子、诸侯以及四夷代表的站位,也是经过特殊安排并具有政治象征意义,将政治等级区分的十分鲜明,“明堂也者,明诸侯之尊卑也。”(《礼记·明堂位》)在明堂里演习的礼乐,也是经过精挑细选,即使是蛮夷之族的乐舞,也具有政治性,能显示了天子权力的广泛性,是天子权力弥漫天下的象征,这就是所谓“纳夷蛮之乐于大庙,言广鲁于天下也”(《礼记·明堂位》)。经过历代阴阳家的演绎,“明堂”及其制度多有繁琐的解读与考证,但概括而言,作为“礼制性建筑物”*张一兵先生曾指出,中国传统建筑中存在着一种“礼制性建筑”,这些礼制性建筑可以作为君权神授的象征物、权力的象征物、群体意志的象征物、社会结构和等级关系的象征物。张一兵: 《明堂制度源流考》,北京: 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5页。的“明堂”,在儒家礼乐文明传统中,主要是行使国家最高政治权力的一种象征物,也是权力合法性的一种标志,这种以建筑物来标志国家权力的礼仪传统一直延续到今天,在世界其他文明中也是如此。
《礼记》中经常通过数字的差异来表示地位的差异,换句话,尊卑等级往往体现在日常生活某个使用物的数量差异上,这一点也体现在宫室营造及其装饰上。在《礼记》中所提到的建筑中,建筑物的大小、高度和数量往往体现等级的差级,“有以大为贵者,宫室之量,器皿之度,棺椁之厚,丘封之大,此以大为贵者”(《礼记·礼器》)。人们生前住的“宫室”、死后的“棺椁”,都是以“大”为贵的,换句话说,居住大的宫室就是地位高的一种象征。“有以高为贵者: 天子之堂九尺,诸侯七尺,大夫五尺,士三尺;天子、诸侯台门。此以高为贵也。”(《礼记·礼器》)此处的“堂”指台阶,“天子之堂九尺,而阶九等……诸侯七尺,阶七等;大夫堂五尺,阶五等;士堂三尺,阶三等”。*(清)孙希旦撰,沈啸寰、王星贤点校: 《礼记集解》,第639页。宫殿立于台上,因而台阶越多就显示建筑物越高,由士而至天子,逐渐增高,秩序与等级井然,也可以通过对建筑物的认知而一目了然。这种与宫室相关的、因数量差异而表示等级差异的情况,在《礼记》文献中多见。
在礼治传统中,建筑还被用来作为化民成俗的政教之具,使之发挥超越居住和权力象征之外的功能。王夫之说: “古之帝王,昭德威以柔天下,亦既灼见民情之所自戢,而纳之于信顺已。奏九成于圜丘,因以使之知天;崇宗庙于七世,因以使之知孝;建两观以悬法,因以使之知治;营灵台以候气,因以使之知时;立两阶于九级,因以使之知让。”*(明)王夫之: 《读通鉴论·汉高帝·十三》,《船山全书》第10册,第88页。天道、孝道、治道、辞让之道以及时令,都是一种价值,这些价值都反映在建筑物及其装饰上,使得建筑物的意义被放大,成为了“政教之举”,这种思维方式,在传统宫室建筑中多常见。
性别权力的差异也是礼教的重要内容,这一点,也反映在建筑物上。《礼记·内则》中说: “礼,始于谨夫妇,为宫室,辨外内。男子居外,女子居内,深宫固门,阍寺守之。男不入,女不出。”我们知道,在传统文化中,男性拥有压倒性的社会权力,在政治上,更具有性别的独占性。男性往往可以自如走出“门”外进行各类社会交往,而女性则应该深居“门”内,将自己的行动限定在一定场所而不能逾越。美国学者罗莎莉(Rosenlee Li-Hsiang Lisa)在讨论《礼记》中的这段记述时,将其与《管子》中的相关内容联系起来,《管子·权修》中说: “大城不可以不完,周郭不可外通,里程不可以横通,闾闬不可以毋阖,宫垣关闭不可以不备。故大城不完,则乱贼之人谋;周郭外通,则奸遁逾越者作;里域横通,则攘夺窃盗者不止;闾闬无阖,内外交通,则男女之别。”罗莎莉就此指出,在中国传统礼制中,用来规范两性区分的建筑构造,与城墙等防御性建筑一样,关涉“国家的秩序与安全”*[美]罗莎莉: 《儒学与女性》,丁佳伟、曹秀娟译,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95页。。如其所论,在礼制传统中,一道建筑学意义上的门,就构成了“内外之别”的性别及其权利的区分界限,演变成了社会权力意义上的“门”,用以作为男女之防,划定男女生活自由和社会权利的界限。孙机先生在讨论四合院建筑时也说: “四合院的布局强调尊卑之分、内外之别,是宗法礼制在民居中的体现。”*孙机: 《中国古代物质文化》,北京: 中华书局,2014年,第159页。在中国古代礼制中,宫室中的权力差异、性别差异也体现在普通居民的生活当中,政治生活化和生活政治化的取向弥漫在整个社会生活中。
建筑标志着一系列等级秩序和权力差等,因此具有一定的礼制强制性,若违反建筑礼仪来营造宫室住所,可能会带来生活和政治上的混乱,因而是不允许的,也会带来惩罚。就生活而言,《礼记·仲尼燕居》上说: “室而无奥阼,则乱于堂室也。”所谓“奥”,是指室之西南隅;所谓“阼”,是指堂之东阶,宋人陈澔解释说: “盖室之有奥﹐所以为尊者处;堂之有阼,所以为主人之位也。”*(宋)陈灏撰、万久富整理: 《礼记集说》,南京: 凤凰出版社,2010年,第399页。堂、室的建造,要合乎尊尊、明主次的礼制原则,否则就会引发混乱。就政治而言,《礼记·郊特牲》中曾举例说道: “台门而旅树,反坫,……大夫之僭礼也。”不该建台门而建台门,不该在过道上使用屏障而用之,不该在堂上设反坫而设之,都是与宫室礼仪相违背的,是僭越之举。与此相类,《左传·宣公二年》里也曾记述一个宫室僭越的例子: “晋灵公不君。厚敛以雕墙;从台上弹人而观其辟丸也;宰夫胹熊蹯不熟,杀之,置诸畚,使妇人载以过朝。”僭越建筑礼仪而过度雕饰版筑之墙,与戏弄大臣、草菅人命一样,成为了晋灵公的政治罪名,因而遭到了严厉的惩罚。孔子也曾批评臧文仲道: “臧文仲居蔡,山节藻梲,何如其知也?”《论语·公治长》臧文仲僭越礼制而使用华丽的宫室,孔子对此十分不满,认为其破坏了等级秩序。孔子的这种批评,实际上是与“八佾舞于庭,是可忍孰不可忍”(《论语·为政》)的著名批评如出一辙,那就是说在生活的任何场域里都不能僭越等级秩序,不仅人的行为如此,人们活动的场所与居室也应该如此,不能例外。后世中国继承了这种等级传统,如《唐六典》卷二十三上记载: “凡宫室之制,自天子至于士庶,各有等差。天子之宫殿皆施重栱、藻井。王公、诸臣三品已上九架,五品已上七架,并厅厦两头;六品已下五架。其门舍三品已上五架三间,五品已上三间两厦、六品已下及庶人一间两厦。五品已上得制乌头门。”*(唐)李林甫等撰、陈仲夫点校: 《唐六典》,北京: 中华书局,1992年,第596页。《宋史·舆服志》也记载: “凡民庶家,不得施重栱、藻井及五色文采为饰,仍不得四铺飞檐。庶人舍屋,许五架,门一间两厦而已。”*(元)脱脱等撰: 《宋史》第11册,北京: 中华书局,1977年,第3600页。低品级官员和平民住宅的规格,不能僭越国家制度的规定而追求高大华美,否则就是违背礼制。这种数量和装饰上的约束,都与先秦儒家礼制有着渊源的关系,身份意义上的礼制,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中国古代的建筑观念,也使得人们被长久地框束于等级意识中。
从“生活政治”的角度来看,作为承载秩序性价值的生活物品、生活空间往往都具有象征意义,尤其是对于为政者来说,生活物品、生活空间最容易从政治角度来予以安排和解读。宫室作为为政者起居、议政的主要活动场所,最能展现权力差异、等级差异、身份差异,故而能成为常见性的政治象征物。
二、 空间方位与权力差异
历史地来看,对于空间、方位的注重,是中国传统宫室建筑文化的核心所在。在建筑中“辨方正位”,细致考量空间、方位的安排,既有自然意义上的原因,如采光、通风、地势等因素,还有后世附会的“风水”等非理性因素掺杂其中。建筑中的阴阳问题,本是人类居住时受制于太阳运行轨迹而产生的一种理性考量,如朱熹曾指出: “阴阳,向背寒暖之宜也。”*(宋)朱熹撰: 《诗集传》,朱杰人、严佐之、刘永翔编《朱子全书》第1册,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 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但随着一些神秘主义的演绎,“阴阳”“风水”逐渐变成了非理性的建筑考量。同时,从礼制的角度来看,空间、方位的安排特别是在政治性建筑、公共性建筑的营造中,还有政治上的考量,遵循空间与方位的礼制,往往体现着对权力分配的认同。因此,在宫室营造、室内布局、人物居处等方面,空间、方位的安排往往渗透着权力差异、等级高下的观念。如《礼记·曲礼下》上说: “天子当依而立,诸侯北面而见天子,曰觐。天子当宁而立,诸公东面、诸侯西面,曰朝。”《礼记·大传》又说,“圣人南面而听天下”,天子南向而立、面南而坐等,接受众人对其所代表之权力的膜拜,并以此表示尊贵,其他诸人也是按照权力和地位等级来安排自己的居处方位。著名建筑学者汉宝德曾说: “世界的文明国家中,只有中国人把社会的秩序具体地用空间表达出来。”*汉宝德: 《中国建筑文化讲座》,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第230页。这个论断也许过于强,但在中国的建筑文化中,用空间方位来表达秩序确实重要的建筑和政治的双重思维。这种以方位来表征权力、地位的思维方式,是中国古代传统礼制的重要内容之一*童强教授认为,先秦礼仪中的空间、方位被系统地编码,赋予了权力和秩序所要求的诸种语义。参见童强: “先秦礼仪的空间代码及其功能”,《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4期。。
我们知道,传统中国的明堂制度是国家权力的重要象征物。在明堂之上,空间与方位的安排尤其重要,是权力秩序的重要载体,《礼记》对此有着十分详细的描述,昔者周公朝诸侯于明堂之位: 天子负斧依南乡而立;三公,中阶之前,北面东上。诸侯之位,阼阶之东,西面北上。诸伯之国,西阶之西,东面北上。诸子之国,门东,北面东上。诸男之国,门西,北面东上。九夷之国,东门之外,西面北上。八蛮之国,南门之外,北面东上。六戎之国,西门之外,东面南上。五狄之国,北门之外,南面东上。九采之国,应门之外,北面东上。四塞,世告至。此周公明堂之位也。(《礼记·明堂位》)
在这样的方位安排中,“三公”地位仅次于天子,故而能据中阶之前,面对天子,“以对王为尊也”。*(清)孙希旦撰,沈啸寰、王星贤点校: 《礼记集解》中册,第840页。其他诸侯、诸伯、诸子、诸男分别按爵秩等级立于相应位置,而九夷、八蛮、六戎、五狄、九采之国的因为是“九州”之外的藩属国,故而位于四门之外,表征与中央权力有一定的距离。从明堂朝会时的不同等级的位置安排来看,与最高权力拥有者站位的远近预示着与核心权力的亲疏关系,除最高权力拥有者之外的其他人,则按照爵秩等级高低依次按预先设计的方位安排。这样的安排给人以美学意义上的和谐感,所有人都能安守一隅而不至于纷乱,但更为重要的是营造了秩序感,象征着权力差异,方位或者站位不再仅仅具有空间意义和美学意义,还具有权力和等级意义,如最高权力者面南,次者面北,再次面西,再次面东,依此罗列,体现着众人对权力秩序的认同。“立而无序,则乱于位也。”(《礼记·仲尼燕居》)秩序要求在方位上体现出来,方位传达着秩序的要求,这种以方位来表征等级差异的礼仪制度,在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和政治生活中十分多见。在国家主办的各类公开性政治活动中,以最高权力者所居的位置为中心,参与人与最高权力者之间的空间距离和位置安排,显示着各类参与人所拥有权力和地位的差异。对空间意义上的“中心”的高度重视,实际上表达了对权力和掌控的崇拜。这种空间方位的仪式感与政治权力的关系,在现代政治也依然在一定程度上展现。当这种空间方位的安排以公开的形式展现在公众面前时,人们往往会从政治仪式活动中解读现实政治中的权力安排。空间方位与权力象征的关系,在从古及今的礼仪活动中,都有所体现,构成了政治文化的一个重要内容。当然,在公共性政治活动中,合乎秩序的方位布局,尽管不是特别具有实质性意义,但对于人们理解政治活动背后蕴含的价值判断确实有一定的帮助作用。
不仅明堂如此,其他场景的方位来表征权力和身份的差异。“建国之神位: 右社稷,而左宗庙。”(《礼记·祭义》)古礼制右尊于左,意味社稷要高于宗庙。“庙堂之上,罍尊在阼,牺尊在西。庙堂之下,县鼓在西,应鼓在东。君在阼,夫人在房。大明生于东,月生于西,此阴阳之分、夫妇之位也。”(《礼记·礼器》)这里对礼器的布置、国君夫妇在礼仪活动中的方位做了详细规定,既表明了呼应天地阴阳之序,也是强调方位对于尊卑、秩序的重要性。在宫室营造过程中,比如当建筑物竣工落成时,其典礼也会利用空间方位来宣示权力差异。
成庙则衅之。其礼: 祝、宗人、宰夫、雍人,皆爵弁纯衣。雍人拭羊,宗人视之,宰夫北面于碑南,东上。雍人举羊,升屋自中,中屋南面,刲羊,血流于前,乃降。门、夹室皆用鸡。先门而后夹室。其衈皆于屋下。割鸡,门当门,夹室中室。有司皆乡室而立,门则有司当门北面。既事,宗人告事毕,乃皆退。反命于君曰: “衅某庙事毕。”反命于寝,君南乡于门内朝服。既反命,乃退。路寝成则考之而不衅。衅屋者,交神明之道也。(《礼记·杂记下》)
从这段引文来看,宰夫杀羊、雍人(厨子)举羊、滴血与祭、众官观礼、国君听事等诸环节,皆有空间和方位上的考虑,丝毫不可错乱。这是因为以血祭宫室竣工之礼,是与神明在沟通,关涉阴阳之道,而阴阳之道又是社会秩序的参照物,故而不能有所差池。这种类比性礼仪思维,是从现实政治角度来思考的。在《礼记》所述内容中,经常出现的对于天地自然秩序的模仿,其深层次目的是为了建立和维护社会生活的秩序。
在一般人的宴饮聚会中,方位也具有秩序性意义,《礼记·乡饮酒义》中说: “天地严凝之气,始于西南,而盛于西北,此天地之尊严气也,此天地之义气也。天地温厚之气,始于东北,而盛于东南,此天地之盛德气也,此天地之仁气也。主人者尊宾,故坐宾于西北,而坐介于西南以辅宾,宾者接人以义者也,故坐于西北。主人者,接人以德厚者也,故坐于东南。而坐僎于东北,以辅主人也。”方位在《礼记》中常常具有价值色彩,如上所述,“尊严”“盛德”等人道价值皆取法于自然的天地之气,而被赋予了价值色彩的“天地之气”之生发方位因而也具有了价值性,在人际交往过程中,对特定价值的认可往往形象化的表现在方位的安排上,在这个意义上,主、宾的身份与德、义的价值要与东南西北的方位合乎礼仪的搭配起来,在这个搭配的过程中,人间的秩序通过自然的方位形象具体的呈现出来,使人一目了然,进而在生活中固化为制度与风俗。
空间方位是自然意义的,人们不但以语言对空间方位予以了命名式的构造,同时还赋予其政治意义、秩序意义、文化以意义,这种人为建构起来的方位性秩序,从类比自然的阴阳之道出发,并将其贯彻到建筑理念中,再利用建筑的布置,将依据空间方位建构起来的秩序感,又通过礼仪、教化的手段在日常生活中使之反复呈现出来,成为政治生活中的传统、日常生活的风俗习惯。所谓“天道至教,圣人至德”(《礼记·礼器》),就是圣人窥见天地自然的秩序,在人类社会中构造秩序以类比自然,《礼记》中的空间方位的秩序性安排,就有种意味,并将其贯彻到各个层面的礼仪制度中。
三、 死后墓所与身份等级
在儒家礼仪传统中,不仅生活世界中的宫室、空间、方位与政治相关联,在死后的世界里,墓葬以及祭祀的宗庙建设也与政治等级密切相关,特别是帝王的陵寝墓葬,尤其体现了君主的权威,中国传统帝王的陵寝墓葬,除了亡国之君外,大都气势宏大,昭示着王权的无上权威。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秦始皇陵,“穿三泉,下铜而致椁,宫观百官奇器珍怪徙臧满之。令匠作机弩矢,有所穿近者辄射之。以水银为百川江河大海,机相灌输,上具天文,下具地理。以人鱼膏为烛,度不灭者久之”。*(汉)司马迁撰: 《史记》卷六,第1册,第265页。虽尚不能考证这种描述的确切度,但从我们对帝王陵墓的已知认识而言,类似秦始皇陵这样的帝王式陵墓,对帝王权威的充分表征,是陵墓建设时必须要考虑的重要问题。
在儒家礼仪制度的理想里,人的生前与死后,都应该将身份等级及其所配享的礼仪贯彻到底,对逝者生前的尊崇与亲爱,一样也要体现到死后的安葬与祭祀中,“敬其所尊,爱其所亲,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礼记·中庸》)。按照这种礼仪思想,那些在生前特别重视礼仪等级的贵族,死后安葬的地方要营造得如同生前生活的都邑,现实生活中的秩序也要尽可能地带到墓葬世界里,希望这种身份和等级的荣耀万世不朽,“世之为丘垄也,其高大若山,其树之若林,其设阙庭、为宫室、造宾阼也若都邑”(《吕氏春秋·安死》)。换句话说,儒家的礼仪,对于社会中人来说,是生死一贯的,生前安居之所如此,死后安息之地也当如此。当然,普通人往往因能力受限,不能实现上述安葬方式来体现礼仪的尊严。我们知道,人死后将无法感知这种礼仪秩序,所谓的墓葬礼仪是做给仍然活着的人感知的,通过具有差异性的丧葬安排,一方面体现孝道,另一方面通过延续现实世界的等级差异性,使得现实世界的人不断强化秩序感和身份等级意识。
就墓葬而言,现实生活中的等级秩序,在死后的世界里,依然重现,“以爵等为丘封之度,与其树数”(《周礼·冢人》)。棺椁是死者“居住”的地方,历代礼制中,对死后安葬之所的设置是不一样的,《礼记》曾记载,孔子逝后,公西赤主办丧葬,就是统合夏商周三代之制来安排的,“孔子之丧,公西赤为志焉。饰棺墙,置翣设披,周也;设崇,殷也;绸练设旐,夏也”(《礼记·檀弓上》)。对于逝者死后的“安身之所”,随着建造能力的进步以及礼仪的不断强化,自虞夏到殷周,不断变化,也越来越考究,“有虞氏瓦棺,夏后氏墍周,殷人棺椁,周人墙置翣扇。”(《礼记·檀弓上》)孔颖达疏曰: “有虞氏唯有瓦棺;夏后瓦棺之外加墍周;殷则梓棺替瓦棺,又有木为椁,替塈周;周人棺椁,又更于椁旁置柳、置翣扇,是后王之制,以渐加文也。”*(汉)郑玄注、(唐)孔颖达正义、吕友仁整理: 《礼记正义》上册,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238页。孙希旦对这种不断加码的棺椁建造有过辩解,“古时丧制质略,至后世而渐备,为之棺椁而无使土亲肤,为之墙、翣而使人勿恶,凡以尽人之心,而非徒为观美而已”。*(清)孙希旦撰,沈啸寰、王星贤点校: 《礼记集解》上册,第172页。在孙希旦看来,这种逐渐繁奢的棺椁建造,不只是为了美观,还有其他现实性的考虑,既是为了避免逝者的肉身免受水土侵蚀,也是为了生者不闻肉身腐烂的气味而为之厌恶,总体来说就是为了“尽人之心”。我们知道,礼本乎人情,孙希旦这种解释当然有道理,但是他忽略了一个事实,即使是棺椁建造,不同地位的人得到的安排也是不一样的,地位高的人死后将得到更大的厚葬,而地位低的则依次递减,这就说明了,棺椁制度不仅是出于孙希旦所提到的感情性因素,还有现实等级秩序的考虑于其中,死后的“居住之所”同样能体现权力和身份的差异。
《礼记》中对这种因生前地位不同而享有不同棺椁的情况作了大量的记述,如,“天子之棺四重;水兕革棺被之,其厚三寸,杝棺一,梓棺二,四者皆周。棺束缩二衡三,衽每束一。伯椁以端长六尺”(《礼记·檀弓上》)。又如,“君大棺八寸,属六寸,椑四寸;上大夫大棺八寸,属六寸;下大夫大棺六寸,属四寸,士棺六寸。君里棺用朱绿,用杂金;大夫里棺用玄绿,用牛骨;士不绿。君盖用漆,三衽三束;大夫盖用漆,二衽二束;士盖不用漆,二衽二束”(《礼记·丧大记》)。现在看来,这种安排非常繁琐,但在当时却是有必要的,因为非如此就会导致秩序的混乱。无论是棺椁大小的不同,还是棺椁装饰的不同,都跟死者生前的身份等级相关,而与死者及其亲属的偏好无关,这就是礼仪的制度性力量。礼仪在日常生活中发挥的力量在于,不管人们个性重点偏好如何,都必须按照既定的礼仪风俗或者礼仪惯例来安排自己的行为,即便在人们死后也依然无法摆脱这种定制。因此,墓葬的样式与装饰,较少地与个体情感与偏好相关,更多是与现实生活的等级秩序联系在一起。
在墓葬的问题上,男女因为在现实生活中地位不同,社会权利有所差异,丧葬中所得到的安排也不一样。如《礼记·檀弓下》中记载: “国昭子之母死,问于子张曰: ‘葬及墓,男子、妇人安位?’子张曰: ‘司徒敬子之丧,夫子相,男子西乡,妇人东乡。’曰: ‘噫!毋。’曰: ‘我丧也斯沾。尔专之,宾为宾焉,主为主焉。妇人从男子皆西乡。”男主女从的空间方位安排,一如现实的生活世界。男人在生前是这个世界的主宰,死后依然如此,主宾的次序不能倒置。即使贵为女皇,武则天死后也被安排与唐高宗合葬而享受帝王之祭礼,而没有单独以帝王的身份享受死后的“居所”。
宗庙是为了祭祀祖先所用的庄严场所,既能表达“尊尊”的秩序感,也能因此而实施政治教化,所谓“祀乎明堂而民知孝”(《礼记·乐记》),祭祀用的宗庙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因此,在建设宗庙时,更要依据身份等级的差异予以精心设置,将政治意志体现进去。按照生前的爵秩等级与政治地位不同,宗庙的建设与安排也存在不同,在《礼记》中对此也多有描述。在政治人物死后的祭祀场所的数量设置上,也可以看出身份等级的差异,“天子七庙,三昭三穆,与太祖之庙而七。诸侯五庙,二昭二穆,与太祖之庙而五。大夫三庙,一昭一穆,与太祖之庙而三。士一庙。庶人祭于寝”(《礼记·王制》)。“礼,有以多为贵者: 天子七庙,诸侯五,大夫三,士一”(《礼记·礼器》)。数量上的差异,明确地说明了政治地位的差异,昭示着现实的秩序将延续到死后的世界。后代为祖先设置的祭祀场所数量上的差异,显示了身份地位的差异,而这种差异往往是不可僭越的,“多”是贵,而“少”则意味着低下。当然,多与少等数量词与身份等级的高与低,在不同场景中是不一样的,比如在《礼记·礼器》篇里,也规定了在其他方面“有以少为贵者”“以大为贵者”“以小为贵者”“以高为贵者”“以下为贵者”等,在不同的情形下,大、小、多、少、高、低等包含着差异性的器物特征,都是贵、贱的标志,这说明,以数量来标示贵贱的差异性,在《礼记》中始终是核心之义。
在礼仪象征权力的视域中,无论生前还是死后,都要体现这种因权力、地位带来的差异感。在政治的世界里,身份差异就意味权力等级。由此可见,墓所的建筑与宫室的建筑一样,都是体现了现实政治世界的秩序,只不过墓所延续了活人世界的秩序,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了因身份等级带来的差异感无所逃于天地之间。人死后,也没有改变因生前政治地位不同而带来的待遇不同,这是传统社会中礼制弥漫于天地之间的一个重要写照。当然,历史变迁,这种因地位带来的哀荣,也会逐渐散尽,《红楼梦》中的《好了歌》所叹“古今将相在何方,荒冢一堆草没了”,则是另外一种更为深邃的历史写照。
四、 “卑宫室”与居住平等
从《礼记》中反映的居住与政治的关系来看,宫室以及墓葬、祭祀场所的营造,都反映了现实政治权力、身份地位等级的差异,这种以气势壮丽、秩序类比、身份差别甚至是神秘主义为主导的建筑思维,一方面强化了现实社会的政治秩序,在一定意义上,消弭各种僭越,有利于社会的稳定;但另外一方面,和礼乐文明中其他生活礼仪一样,不断形塑人们的身份等级意识,固化人与人之间因为政治地位的差异而带来的生活不平等,这是我们反思传统建筑文化时应当有所注意的。
当然,在儒家文化内部,也不尽然都是以推崇浮华豪奢的主张。在强调宫室与身份等级相关联的同时,儒家也注重对在宫室穷奢极欲的限制。孔子在赞美大禹时,提出了“卑宫室,而尽力乎沟洫”(《论语·泰伯》)的思想,孔子赞美大禹在当政时,以宫室事为小,以老百姓的田间水道的建设为大,进而主张圣王要不顾自己的居室之简陋,而致力于天下苍生的生计。《礼记·儒行》里对儒者的居所有所描述: “儒有一亩之宫,环堵之室,筚门圭窬,蓬户翁牖。”儒者的住所往往简陋,孔子也有对颜回“居陋巷”的赞美,都表达了儒者对于居所问题理性、积极的态度和情怀。但从实际上中国政治历史发展的历程来看,历代王朝的统治者大兴土木、营造宫阙万间则是主流,这也与儒者的情怀形成了巨大的反差,从而后世读书人都对极尽豪奢的宫殿营造保持着警醒态度,杜牧的《阿房宫赋》、张养浩的名句“伤心秦汉经行处,宫阙万间都作了土”,等等,都是这一清醒和理性态度的呈现。对于华丽宫室的批评,《墨子》里也曾有深刻论述: “圣王作为宫室,便于生,不以为观乐也。……当今之主,其为宫室,则与此异也。必厚作敛于百姓,暴夺民衣食之财,以为宫室台榭曲直之望、青黄刻镂之饰。为宫室若此,故左右皆法象之。是以其财不足以待凶饥、振孤寡,故国贫而民难治也。君实欲天下之治而恶其乱也,当为宫室不可不节。”(《墨子·辞过》)我们知道,墨子主张节用、节葬,这是对于儒家过分强调以华美来彰显权力尊贵的一种批评,也是一种平民化的主张。墨子的这种平民化主张,在现代社会得到了较好的落实。
另外,就宫室建筑与政治合法性的关系,儒家内部也曾提出过质疑。略举一例,如前所述,传统儒家对明堂制度非常看重,在后代的政治实践中多有仿制或借鉴,在理论上或者考证上也多有解读。但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同样作为儒者的明代王阳明却对明堂的必然正当性表示过质疑。王阳明认为,明堂作为一种宫室制度,只是行使政治权力的形式,如果为政者不以仁爱之心来施政,明堂上所发出来的政令也是缺乏正当性的。王阳明在《答顾东桥书》中说:
夫明堂、辟雍之制,始见于吕氏之《月令》、汉儒之训疏,《六经》、《四书》之中未尝详及也。岂吕氏、汉儒之知,乃贤于三代之贤圣乎?齐宣之时,明堂尚有未毁,则幽、历之世,周之明堂皆无恙也。尧、舜茅茨土阶,明堂之制未必备,而不害其为治。幽、历之明堂,固犹文、武、成、康之旧,而无救于其乱。何邪?岂能以不忍人之心而行不忍人之政,则虽茅茨土阶,固亦明堂也;以幽、历之心,而行幽、历之政,则虽明堂,亦暴政所自出之地邪?*(明)王阳明撰,吴光、钱明、董平、姚延福编校: 《王阳明全集》上册,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59页。
明堂及其相关制度,在王阳明看来,不过是政治权力的表现形式,在具体的政治活动中,只具有形式性的意义,而没有实质性意义。圣王的正确政令,未必出自明堂之上;极尽威仪的明堂,未必不会发出暴虐的政令。因此,政治行为的正当性其实与明堂及其制度并没有必然的联系,用明堂来保证政治正当性不过是一种附会之说。王阳明的这种质疑,对于我们反思传统的明堂制乃至那些蕴含政治意味的建筑物具有积极的意义。用仪式或者符号来保证政治正当性,虽是政治生活中的常见之事,但仪式、符号与正当性之间,并没有因果必然性,在政治实践中,并不会因为某种恰当的仪式或符号必然会带来恰当的政治行为。宫室作为这种政治符号,同样也不会必然地保证政治实践的正确与正当,只是人们在传统中,习惯将某种符号赋予了“正当性”的名义,故而政治家们总是要夺取这种符号来增加其行为的权威性与正当性。
进入现代社会以来,随着礼教思维的式微,身份等级意识为平等观念所取代,“民众第一次取代少数特权阶级成为主角”*[日]安藤忠雄: 《在建筑中发现梦想》,许晴舒译,北京: 中信出版社,2014年,第7页。,特权式、独占式的宫室类建筑及其装饰等已丧失其存在的政治性和观念性基础,多元化、平民化的建筑主张逐渐盛行。供一家一姓独享的宏大宫室营造销声匿迹,人们死后也开始盛行薄葬,无论生前还是身后,安身之所、安息之地都越来越回归居住舒适、节约安宁的本来面貌。因为皇权和帝制的终结,传统帝王的宫室、园林和居所、墓所丧失了其作为权力象征的地位,而变成人们探访古迹、追寻历史的场所。当然,因为现实的安全保卫等原因,对于寻常百姓来说,具有神秘性色彩的、新的权力符号的住所、建筑仍然存在,这在当前各个国家都是显性存在的事实。另外,由于以建筑来反映国家形象的观念的延续,象征国家政治意识形态的空间与建筑也依然存在,如现代国家多建有容纳群众集会的开放性大广场,以表示尊重群众的意愿、倾听群众的呼声以及为国民提供公共性聚集的场所;再如,承担议会或者人民代表大会议事功能的建筑也总是试图表征民主的价值,在设计时也会体现国家政权对于民主政治的理解,依然承担传递政治价值的功能,“议会建筑的外貌折射出国家传统和民主抱负,而议会建筑的整体折射出国家看待自身的方式”。*[美]迪耶·萨迪奇、海伦·琼斯: 《建筑与民主》,李白云、任永杰译,祁潇校,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3页。
如上所述,建筑尤其是政府建筑、公共建筑依然在一定程度上承担着政治象征物的功能,但是,那种因身份地位的差异而带来的居所规格、装饰的严格界限以及过度的繁文缛节逐渐淡化,人们不再以身份地位的差异而导致能住什么规格的居所或者不能居住什么规格的居所,能够用什么样的建筑装饰或者不能用什么样的建筑装饰。从新建的具有政治意味的建筑来看,可能依然具有各种文化象征性的差异,但等级性的差异已经丧失了合理性,其居住者也摆脱了与这些建筑的终身性联系,他们可能会因为担任某种公职才能享有居住的权利,一旦这种公职的任期结束,他们与这些具有政治象征性的居所就丧失了必然的联系。当然,现代社会普通人的住所差异,不再因政治社会的身份地位来主导,而改为由经济能力来主导,很多时候,以一种经济上的差异代替了政治地位上的差异。“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千载而下,此问都有天问之意义。但无论如何,人们逐渐摆脱因先天性的身份门第、社会权力等级等政治地位差异而带来的居住不平等,而更多地依赖后天个人自由发挥能力实现自己的居住梦想,虽然现实世界中人们居住状况还远未理想,但居住逐渐摆脱身份等级的桎梏,也不啻是一种历史的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