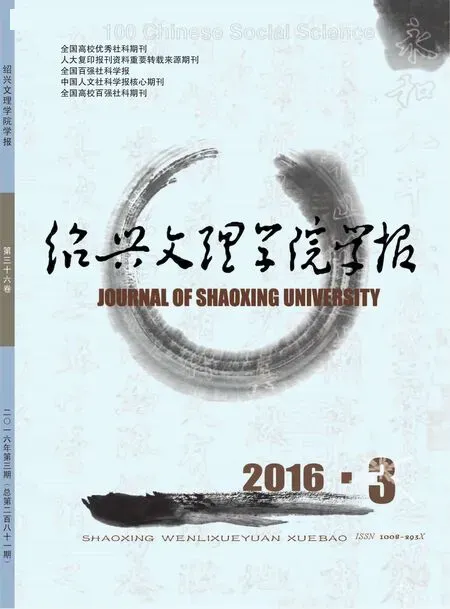晋唐笔法的传承
丛文俊
(吉林大学 古籍研究所,吉林 长春130012)
晋唐笔法的传承
丛文俊
(吉林大学古籍研究所,吉林长春130012)
摘要:晋、唐是书法史上的两个高峰,本属一脉传承,但从技法到美感风格、从书家个性到时代风尚,都有明显的区别。归根到底,还是社会生活与文化的差异使然。文章着重分析了晋、唐笔法的不同及其原委,还有它们是如何影响到美感风格的问题,同时也论及了人的社会生活体验、观念和作品之文化上的象征意义。对今天如何更好地弘扬“兰亭”精神,也指出了问题的关键所在。
关键词:晋唐笔法;传承;“二王”书法;唐楷
晋唐笔法这个论题其实是老生常谈了。在这之前,我有一篇文章,专门论述晋唐书法异同。我现在对此有一个新的体会,所以当初刘恒先生问我讲什么题目的时候,我就说讲这个论题。我想把这两年来的体会结合起来重新讲,即便是老生常谈也要有一些新的体会。
对于晋唐笔法,苏东坡(1037-1101)对此曾有一个很好的评论,他说魏晋书法“萧散简远,妙在笔墨之外。至唐颜、柳,始集古今笔法而尽发之,极书之变,天下翕然以为宗师,而钟、王之法益微。”(《书黄子思诗集后》)他的意思就是说,以钟、王为代表的魏晋书法,它的基本美感和风格是“萧散简远,妙在笔墨之外”,很多美的东西不能仅靠看,这和梁武帝所讲的“字外之奇,文所不书”是一致的。他们的观点和我们今天欣赏书法的观点有所不同,今人看书法往往看字,字外的东西感悟很少。这就是我们讲要传承“二王”书法的一个原因。那么,为什么苏东坡说“至唐颜、柳,始集古今笔法而尽发之”呢?因为真正的有划时代意义的唐人书法就是颜真卿(709-784)和柳公权(778-865)的作品,徐浩(703-783)的书法艺术有很多方面是继承前人的。后面说“极书之变”,书法到这里就有了一个极大的变化;“天下翕然以为宗师”,就是从此以后大家学的都是颜、柳的书法;“而钟、王之法益微”,指那些“萧散简远,妙在笔墨之外”的东西就越来越少了。
我想,这是一个大问题。苏东坡是从笔法讲到书法艺术的美感、风格和艺术境界,这需要我们今天重新加以温习、思考。前人已总结出了“二王”书法的基本特点,比如“凌空取势,一拓直下”,大家对此虽耳熟能详,但关键是我们能否做到?从这三十多年国展的情况来看,真正能做到“凌空取势,一拓直下”的几乎没有,哪怕是小楷,也不具备这样的艺术特点。有时我们不能光看作品,比如说在获奖作者面试时,看他们当场写的书法,有的作者写小楷,明明学的和晋人有关,但绝对不是晋人笔法,而是唐人笔法。也就是说,我们今天从感情上都希望能弘扬“二王”书法的艺术精神,但在实际上已经相当困难,因为我们连基本的笔法也不能掌握。唐人的楷法基本都是在纸面上,笔进入纸面以后离不开藏锋。那么,“无垂不缩,无往不收”这种笔法本来出于篆书,后来被运用到了唐楷之中,受到很多名家的追捧。愈是这样用笔,笔愈是抬不起来,当笔抬不起来的时候,所有的笔法基本上就是在纸面上作一种轻微的动作,就没有了“凌空取势”这样的笔法了。没有这种笔法以后,实际上作品的面目差别很大。譬如米芾(1051-1107)学法晋人,用笔大开大合,他是唯一能够“大概”得晋人笔法的人。但是,他也学法唐人,亦受到了唐人的一些影响。
今天在座的各位可以回忆一下,我们最初学书法时十有八九是从唐楷开始。为什么唐楷笔法会有那么大的变化呢?这主要是因为唐人写字实用性很强,一是字越写越大,都要刻碑;字越大,字的线条越实,入笔要藏锋,收笔就要回锋,如此便不可能写出空灵感。举个例子,董其昌(1555-1636)非常擅长临帖,他临王羲之的《乐毅论》和《黄庭经》,给人家题匾时用的就是《黄庭经》笔法。过后,他去看自己的题字,看了几次都觉得不佳。这是因为,“凌空取势”这种空灵的笔法是不能放大的,它有一定的度。如果我们把晋人行草放得很大,就失去了其本身的艺术特色。这里要说明一点的是,我们今天放大的《兰亭序》不是晋人的,它是唐摹本,而且其本身还有很多唐人的笔法,这就是晋唐笔法的差异。
唐人的书法越放大越好看,而越缩小越不好看。如果我们把颜真卿、柳公权的楷书缩小,变成小楷,就简直不能看,因为它们的笔法不同。所以,苏东坡对此的理解是很精确的:“大字难于结密而无间,小字难于宽绰而有余。”所谓的“宽绰”,就是萧散,笔画之间不要勾连,都要断开,“笔断意连”,笔势上下起伏,这样才能达到空灵的效果。在字上下起伏的过程中,所有空中的用笔都是有效的,而我们今天却往往忽略了这一点。比如,大家都知道“点如高峰坠石”,但后一句大家往往都忘了:“磕磕然其实有形”。并不是说“高峰坠石”“坠”一下便可以了,而是“磕磕碰碰”,每一次砸下的瞬间都会弹出去,这时的落笔是一个非常细微的弧线运动。斜着一点,打下来,随后旋即出锋,这个点就完成。可是,大家知道,写唐楷时没有一个点是这样写的,因为这样它就不结实,它一结实,就不空灵。所以我们在唐楷中是找不到这样一种“高峰坠石”的感觉的,它光有“高峰坠石”的力度,但没有“磕磕然其实有形”这样一种后续的动作特征。所以,为什么晋人能够做到这一点呢?有一种观点认为,晋人没有桌子,只有几案,他们是以悬腕的方式来写小楷的。当然这只是一种猜测,未必就是这样。另一种说法认为,晋人是叠格之后拿在手上写的,这也是一种猜测。但不管怎么样,那个时候的坐姿书写,即使是伏案,也和我们今天不同了。如果说我们现在是用高桌来学习书法,那么几十年下来我们的书写姿势是固定的。胳膊支在桌子上,你想取势,就必须确定好自己执笔的高低;如果坐姿不对,就无法得到晋人的笔法。所以,我认为,晋人笔法的空灵是后代人难以仿效的,除非我们有志于此。
黄庭坚(1045-1105)在写法帖的时候谈到了一个现象,他说要“论工不论韵”,徐浩不下于王献之,可以和大令(王献之)相比;但若要讲“韵胜”,则“右军、大令之门谁不服膺”。也就是说,当论“韵胜”之时,“二王”书法无人能及,后人确实是无以为继,因为他们没有了这种笔法。这里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黄庭坚学书法曾在王安石身上下过不少功夫。据李之仪的《姑溪居士论书》(《历代书法论文选续编》)记载,黄庭坚学王安石的书法可以乱真,让别人真赝难别。大家知道,王安石写字并不是一位名家,黄庭坚却几次提到王安石,认为王安石的字有魏晋古法。后来我仔细研究王安石的字,他的字确实写得不好。黄山谷之所以认为王安石的字有魏晋笔法是因为王安石写字“逸逸草草”,这是王安石的一个特点。后来朱熹很不满意,他引张敬夫的话说:“平生所见王荆公书,皆如在大忙中写。”随后朱熹发挥了一下,说他为人“躁扰急迫”,所以只能这样写字了。但是,由于王安石的字逸逸草草,所以他的用笔倒是可以经常往上抬。黄庭坚很有眼力,他看出了王安石的笔法特点。苏东坡评王安石的书法时说他:“无法之法,然不可学。”苏东坡看得没有黄庭坚细,所以黄庭坚能取法于王安石,找到对魏晋古法的理解和模仿。
今人写字,太过注重帖,过于注重形。这样一来,笔法的涵义就淡化了,笔法对美感风格所产生的巨大作用也被我们淡化了。蔡襄(1012-1067)在《论书》中说:“书法惟风韵难及。”因为宋人喜欢用韵来论书,故蔡襄认为书法最高的境界是“风韵”。“虞书多粗糙”,蔡襄觉得虞世南书较粗糙,《汝南公主墓志》确实是这样,虞世南本来传承的是晋人笔法,但他写得很粗糙。蔡襄下一句话讲述了为什么“书法惟风韵难及”的原因,即魏晋人书为什么好,他说:“缘当时人物,以清简相尚,虚旷为怀,修容发语,以韵相胜。”也就是说,当时人生活比较简单,没有我们今天这么复杂,被生活分散了太多的精力。晋人“修容发语,以韵相胜”,指那时候的人和我们今天有些不一样,他们不论男女,均尚化妆。例如曹魏时期的丞相何晏长得很白,大家以为他涂脂抹粉了,便请他吃汤圆,想让他流汗,看看脂粉会不会褪掉。结果何晏貌白如常,看来确实没有化妆。晋时男子敷粉施朱是种常事。讲话则重玄言,《世说新语·容止》(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说:“时人目王右军,飘若浮云,矫若惊龙。”这种玄言可以充分展示“魏晋玄学”风尚,展示一个人的学养、襟怀和识见,为他人提供想象的空间与修辞的美妙。就此而言,“修容发语,以韵相胜”就是一种后人不可企及的韵了。《颜氏家训·勉学》记南朝时候有一谚语,说“上车不落则著作,体中何如则秘书”。也就是说,那时候的人出门时随身带着笺帛,上了车还未落座就文思泉涌,即使是做样子,也代表了一种读书、著述的风气;“体中何如则秘书”指这些人腹内可能没有什么学问,但因为出身门第高,入仕就有一个秘书郎可以做。大家仔细想一想,一个时代,如果没有它的特殊性,怎么能够产生属于它的特殊的文化?怎么会有那么好的书法?所以,我认为蔡襄的话讲到点子上去了。正是因为当时以“清简相尚”“以韵相胜”,所以“落华散藻,自然可观”。在那种氛围下,士人只要随便写字,就有可观。这是种很有道理的见解。《书谱》说“东晋士人,互相陶染”,“纵不尽其神奇,咸亦挹其风味”,也可以为证。
米芾曾经评论张旭的书法:“张癫俗子,变乱古法,惊诸凡夫,自有识者。”为什么米芾说张旭的草书只能“惊诸凡夫”呢?是因为“草书若不入晋人格,聊徒成下品”。他在评怀素的小草时说“稍有古人意”,但又说“时代压之,不能高古”。我觉得米芾虽然怪,但他说得还是很到位的。张旭写字追求速度的时候,就会产生一种表演性。他和贺知章同列“饮中八仙”,喝醉了以后他们就到处写字,所以当时就流传有这样一句诗:“长安城内无粉壁”。这两人只要看到有白墙就上去写,在今天可以被称为“扰民”了,但古人那种对艺术的喜好和欣赏的艺术氛围要比我们今天高明不知有多少倍。
所以,当我们今天要弘扬“二王”书法、继承“二王”精神的时候,我们在多大程度上能接近他们呢?唐人的东西可以越写越大,越写越壮,这很适合今天的展览。但是,如果你要学晋人,又很容易把它学得简单化。学晋人写小行草,没几个成功的;倒是学董其昌的行草有成功的例子。董其昌自己说写行草学习晋人,但实际上没有晋人的味儿。因为他说他的字生秀淡雅,但从来不说自己的字空灵。今人写字不空灵,要做到空灵,还必须要有一种哲理支撑。现代人写字在注重字形的时候,忽略了思考,忽略了字外的东西。如果我们没有艺术理想,没有理论家的关于“字外之奇”、“笔短趣长”之类的艺术解读,字就是简单的几何符号。
书法为何能成为一种艺术?为什么能几千年来让中国人痴迷并且至今不衰?这一定有它的道理,而这道理很多,不在字内,是在字外的。今人有太多心理上的包袱,难以解脱,但我们应该学会放下,不要有太多思想包袱,虽然这很难。晋人身上有很多病态的东西是不可理喻的。比如王献之从小才思敏捷,颇有才气,任性不讲礼数。一日,王献之进了一家私人的园子赏竹,大呼小叫,意足之后转身就走,主人上前指责其缺乏礼数,王献之才作揖道歉,进屋与主人喝茶。王献之生于世家大族,乌衣子弟,他这样的行为有着特殊的时代文化背景,那个时候很多事情是不能以常理度之的,这是魏晋风度。我们今天都讲礼貌,所以学不了古人。像王羲之这样绝顶聪明的人,既有才华又有政治抱负,他年轻时曾有“东床坦腹”的出格之举,晚岁也随俗服食丹药祈求长生。但在那个时候,这就是一种风度,是生活的一项内容。例如,在肚子疼时给别人写信,即会有“甚劣劣”等言辞,字也写得非常好。他们有很多病态的东西是我们不可理解的,归根到底,从事艺术的人是要有一定感受的。
魏晋之人受儒家思想的影响非常微弱,他们主要学“三玄”:《周易》《老子》《庄子》。《老子》提倡的是“小国寡民”“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庄子》强调身体是有限的,但精神是无限的;《周易》讲的是形而上的学问,就书法而言,就是要求做到“妙在笔墨之外”。儒家讲的是经世致用,伦理教化,如此一来书法就只有法度,没了仙气,因为它要对社会负责任。魏晋人能够如此自由,是因为他们比较超脱,同时他们也有自己的思想武器,而这个思想武器是后代人不具备的。
中国第一次思想解放是在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所以苏秦能同时挂六国相印。《史记·货殖列传》中说赵地、郑地、中山的女子“鼓鸣瑟,跕屣,游媚贵富,入后宫,遍诸侯”。李斯的《谏逐客书》也说,那个时代如果后宫没有赵女、郑姬或中山女,对一个诸侯国来说就是耻辱。所以,那个时候就养成了这样一种风气,只有那样的文化和社会才能孕育出这样的人民。所以,如果不是后来秦统一六国,那个时代的书法会发展成为什么样子,真很难说。秦国大一统后,书法也成为了整齐划一的东西,到后来,两汉划一,唐代划一,但魏晋南北朝由于战乱,没有实现国家的统一,魏晋人就自由了。到了北宋,取消了以书判取士的制度,于是北宋人也自由了。但北宋人的自由和魏晋的不同,与战国的也不一样,因为他们有了市民思想文化,有了一种新的生活体验,和我们今天的改革开放有相似之处。所以,在北宋时能出现苏、黄、米,是很正常的。到了明清时代也有一次“自由”,这就是市场经济。市场经济也可以改造人,从某种程度上摆脱儒家思想的束缚。比如说八大山人、石涛、扬州八怪等,他们在进行书法创作时也可以无所拘束,因为只要他们的字有市场就行,他们不需要功名。一个人要是脱离了功名,脱离了他的官样书法,脱离了社会的责任,简而言之,就是他不追求那种书法应有的社会公共意义的时候,书法就自由了。
那么,我们今天还要不要去追求书法的公共意义?如果你追求用书法正大堂皇地去感染他人,那么它显然是有公共意义的;但当你要追求艺术个性的时候,你就必须与其拉开距离。所以,如果我们学唐人的书法艺术多,那么它离社会、离儒家思想就近;如果我们学“二王”的东西多,那么离社会、离儒家思想就远。我们今天选择学什么,其实就代表了你的理想、你的志向的一种选择。倘若你的作品更多是一种才子型的、情感型的,那么它很少有社会的公共意义,大家可以欣赏它,但它不能成为楷模,不能让大家都去学它。为什么唐人的书法大家千百年来都学呢?因为它就是为社会公共意义的书法提供楷模、提供范本的。
晋唐两系书法的不同,骨子里还是人的不同、文化的不同,或者说,这两种书法艺术的针对性,即需求是不一样的。今天,大家都提倡弘扬兰亭精神、“二王”精神,其实这只是一种口号而已,如果真要弘扬起来,还真是个问题,它会产生社会离心力。但是,学唐人的书法能产生很多向心力,它能保证儒家经世致用的基本需求,而“二王”不是。从追求人格的理想化、完美而言,我们应多学“二王”;从将作品展示给别人看的角度来说,我们就应该学唐人。任何一种书法,它的点画,它的任何一种风格现象,都具有清楚的象征意义。很多东西不是在字内产生的,而是在一种人人均可意会的、约定俗成的这样一种文化氛围中被认知的。
(根据第32届兰亭书法节“兰亭论坛”录音整理)
(责任编辑张玲玲)
Inheritance of Jin and Tang Styles in Calligraphy
Cong Wenjun
(Institute ofAncient Chinese Studies, Jilin University, Changchun, Jilin 130012)
Abstract:The Jin and Tang dynasties saw the two summits in the history of calligraphy. Though of the same origin, the calligraphy styles of the two dynasties differ significantly from the technique to the aesthetic style and from the calligraphers’ personality to the trend of the times. Essentially, what distinguishes them is the social life and cultural differences.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analysis of the calligraphy in the Jin and Tang dynasties and the causes, and the way they affect the aesthetic style, and discusses the calligraphers’ social life experience, ideas and the cultural symbolic significance of the calligraphic works. It additionally offers the way to better carry forward the “Lanting” spirit.
Key words:calligraphic style in the Jin and Tang dynasties; inheritance; two Wang’s; regular script in the Tang dynasty
中图分类号:J292.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293X(2016)03-0001-04
doi:10.16169/j.issn.1008-293x.s.2016.03.001
收稿日期:2016-05-03
作者简介:丛文俊(1949-),男,山东文登人,吉林大学古籍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书法家协会理事、篆书委员会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