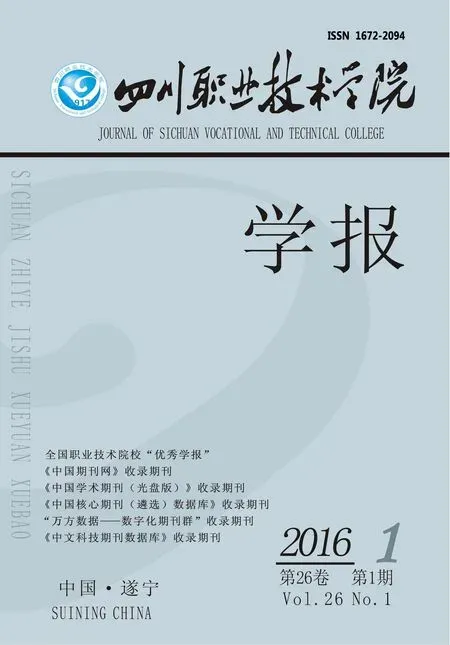竟陵派与《古诗十九首》
魏友
(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江苏南京 210097)
竟陵派与《古诗十九首》
魏友
(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江苏南京210097)
摘要:“厚”是竟陵派为补救公安派末流之弊而提出来的诗歌理想境界,也是竟陵派作诗和论诗的最终旨归。竟陵派主张求“厚”于古人,钟惺、谭元春通过对以《古诗十九首》为代表的古诗之“厚”的论述,深刻地阐释了“厚”的美学内涵,揭示了“厚”根源于性情的温柔敦厚这一创作原理,为他们“厚出于灵”的诗学理念树立了理想的创作典范,从而将学古与性灵说完美地结合了在一起,既纠正了七子派不重性灵的复古之弊,也补救了公安派失于浅率的性灵之偏,为促进晚明文学的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
关键词:古诗十九首;竟陵派;厚
万历后期,在公安派锋芒渐退之际,以钟惺(字敬伯,1574-1625)、谭元春(字友夏,1586-1637)为代表的竟陵派趁势而起。竟陵派一方面在文学主张上与公安派十分接近,在反对摹古,推崇性灵,表现自我等方面,他们与公安派是基本一致的;另一方面,他们又不满公安派末流的空疏肤浅,力图另辟蹊径,倡导用“幽深孤峭”的风格来表现“幽情单绪”,别创了以深幽孤峭为宗的性灵说。
公安、竟陵两派虽然同倡“性灵”之说,但所宗尚的旨趣迥然不同:公安派尚“趣”,主张“诗以趣为主”[1](袁宏道《西京稿序》),但有时以插科打诨为“趣”,故其末流不免流于俚俗肤浅;竟陵派重“厚”,认为“诗至于厚而无余事矣”,而“厚出于灵”[2]474(钟惺《与高孩之观察》),因此求灵致厚可以说是竟陵派论诗的主要旨趣。竟陵派的文学主张主要是通过钟、谭所评选的《诗归》来具体体现的,而《诗归》的论诗之旨,便是“反复于厚之一字”[2]474,贺贻孙《诗筏》也说“钟、谭《诗归》,大旨不出厚字”[3]。竟陵派主张求“厚”于古人,而《古诗十九首》便是竟陵派心目中难以企及的诗达于“厚”的古诗典范,因此竟陵派论《古诗十九首》之旨,同样也可归于一个“厚”字。
一
竟陵派之重“厚”,既与他们主张学古有关,也与他们意欲补救公安派的肤浅之弊相关。钟惺在《诗归序》中说:“今非无学古者,大要取古人之极肤、极狭、极熟,便于口手者,以为古人在是。使捷者矫之,必于古人外,自为一人之诗以为异。要其异,又皆同乎古人之险且僻者,不则其俚者也;则何以服学古者之心!”[2]236可见竟陵派既不满前后七子以“取古人之极肤、极狭、极熟”为学古,又不满公安派末流的俚俗之弊。七子派学古之弊,在于尺寸古法而不讲性灵,结果流于表面的模拟;公安派废古师心,取径于“捷”,结果又流于俚僻。竟陵派为补弊救偏,扬二家之长,弃二家之短,主张学古与性灵并重。正如郭绍虞先生所说:“竟陵派正因要学古而不欲坠于肤熟,所以以性灵救之;竟陵派又正因要主性灵而不欲陷于俚僻,所以又欲以学古救之。”[4]竟陵派学古的方法,在于“求古人真诗所在”,而“真诗者,精神所为也”[2]236,竟陵派以精神为性灵,而性灵所指,即是他们所标举的“幽情单绪”。
竟陵派作诗既主性灵,但以性灵为诗,其弊又在易至率易而流于肤浅,公安派即是前车之鉴,因此钟、谭二人又拈出一个“厚”字来概括诗歌的理想境界,以作为对症良药。钟惺在《与高孩之观察》中说:“诗至于厚而无余事矣。然从古未有无灵心而能为诗者,厚出于灵,而灵者不即能厚。”[2]474谭元春则在《诗归序》中自称未壮时与钟惺“约为古学,冥心放怀,期在必厚”[5]593。钱钟书先生由此将竟陵派的诗学主张总结为“以‘厚’为诗学,以‘灵’为诗心”[6]244。
因为钟、谭在不同的序、跋中多处提到了“厚”,各自所指内涵也不尽相同,因此“厚”在竟陵派的诗论中是一个含义比较复杂的概念,有时是指品德上的为人仁厚,如谭元春《与舍弟五人书》所说的“(蔡复一)说我人愈朴,性愈厚,是进德之验”[5]746;有时是指创作主体的学识修养,如钟惺提倡“多读书,厚养气”[2]254(《周伯孔诗序》),“读书养气,以求其厚”[2]474(《与高孩之观察》);有时则是指诗歌的理想境界。因为钟、谭论《古诗十九首》之“厚”主要指诗歌的理想境界,因此本文只讨论“厚”字的最后一种含义:
弟尝谓古人诗有两派难入手处:有如元气大化,声臭已绝,此以平而厚者也,《古诗十九首》、苏李是也。有如高岩浚壑,岸壁无阶,此以险而厚者也,汉郊祀、铙歌、魏武帝乐府是也。非不灵也,厚之极,灵不足以言之也。[2]474(钟惺《与高孩之观察》)
钟、谭并未对作为诗歌理想境界的“厚”的内涵作出明确的界定,但钟惺在《与高孩之观察》中从反面作了阐释。其文云:“曹能始谓弟与谭友夏诗,清新而未免于痕,又言《诗归》一书和盘托出,未免有好尽之累。夫所谓痕与好尽,正不厚之说也。”[2]474谭元春也在《题简远堂诗》中说:“夫诗文之道,非苟然也,其大患有二:朴者无味,灵者有痕。”[5]815钟、谭既以“有痕”、“好尽”及“无味”谓之“不厚”,那么“厚”所代表的诗歌理想境界便应当是“含蓄蕴藉”与“浑融无迹”。
“厚”的含义既作如此解,那么钟惺所谓的《古诗十九首》“平而厚”又当如何理解呢?周振甫先生对此的解释是:“钟惺指出有两种厚,一种是‘平而厚’,指性情真率和平,诗从肺腑中流出,自然真诚,这就是灵。一种是‘险而厚’,品格高峻,有原则性,不可侵犯,语言卓绝,其锋不可犯,这也是一种灵。”[6]248再联系钟惺对诗教的认识:“夫诗,以静好柔厚为教者也。”[2]276(钟惺《陪郎草序》)“静好柔厚”中的“柔厚”也即传统儒家诗教所说的“温柔敦厚”,温柔敦厚的诗教主张以一种含蓄委婉的方式来表达温厚和平、不愤不激的感情,追求诗歌的含蓄蕴藉之美。徐复观先生在《释诗的温柔敦厚》一文中说:“若把‘敦厚’与‘浅薄’相对,便容易了解‘敦厚’指的是富于深度、富有远意的感情,也可以说是有多层次,乃至是有无限层次的感情。”[7]37可见“厚”指的即是一种耐人咀嚼的深长意味。谭元春在《黄叶轩诗序》中也说:“匡衡说诗可解人颐,而史称其说诗深美。深美云者,温柔敦厚,俱赴其中,弟所谓是中有深趣者也。”[5]639所谓“深美”“深趣”云云,都是指诗歌的含蓄蕴藉之美,而其形成则与性情的温厚和平息息相关。
同时在竟陵派的诗论中,浑厚蕴藉还与“淡”密切相关。钟惺在《文天瑞诗义序》中说:“诗之为教,和平冲淡,使人有一叹三唱,深永不尽之趣”[2]281。其中“和平”指的是温厚和平的性情,而淡泊平和之诗之所以能“使人有一叹三唱,深永不尽之趣”,其原因即在于诗人的性情之厚。《古诗归》总评陶渊明说:“不朴不茂,不深不清,不浑不雄,不厚不光。了此可读陶诗。”“陶诗闲远,自其本色。一段渊永淹润之气,其妙全在不枯。”[8]448(《古诗归》卷九)陶诗之淡而能厚,闲而能远,其作用全在于“一段渊永淹润之气”,也即至深至厚至醇的性情。可见在竟陵派看来,由淡至厚也是作诗之旨。正因如此,谭元春说“冥心放怀,期在必厚”,而同时代的邹漪在《启祯野乘》中则说钟、谭“冥心放怀,期在淡永”[5]964,可见在时人的理解中,竟陵派论诗所主之“厚”已与“淡”紧密联系在一起。
二
据上所言,则钟惺称道《古诗十九首》“有如元气大化,声臭已绝”,即是指《古诗十九首》作者的性情至深至厚,却又绝不露圭角,而以冲淡和平之语出之,形成浑朴淳厚的境界,故而读来“声臭已绝”。而“平而厚”中的“平”,即是指《古诗十九首》性情的真率和平,而“厚”则是指诗人以曲折婉转的方式来表现自己温柔敦厚的感情时诗歌所表现出来的含蓄蕴藉之美,换句话说,《古诗十九首》的蕴藉也即性情的蕴藉。竟陵派对《古诗十九首》的这种认识是符合《古诗十九首》的精神实质的,他们在《诗归》中对《古诗十九首》的评价也是紧紧围绕这一观点展开:
苏李、《十九首》与乐府微异,工拙浅深之外,别有其妙。乐府能着奇想,着奥辞,而古诗以雍穆平远为贵。乐府之妙,在能使人惊;古诗之妙,在能使人思。然其性情光焰,同有一段千古常新,不可磨灭处。彼后人作诗者,人人拟作一番,若以为不可已之例,不容变之规。高者别求奇奥,移本色已远,若但摩娑其面貌音字,使俗人口中、手中、眼中人人得有《十九首》,至使读书者喜诵乐府而不喜诵古诗。非古诗之过,而拟古诗者之过。故乐府犹可拟,古诗不可拟也。[8]420(《古诗归》卷六钟惺总评《古诗十九首》)
《十九首》无诸古诗之新矫夺目,以温和冥穆,无可甚快,在诸古诗之上,千古无异议。诸古诗亦若将安焉?此诗品也。[8]420(同上谭元春总评《古诗十九首》)
钟惺所谓“雍穆平远”之“雍穆”者,也即谭元春所谓“温和冥穆”之意,皆指《古诗十九首》所体现出来的性情温和而不失庄重,契合温柔敦厚的儒家诗教。而“平远”意即“平而厚”,汉魏乐府之能使人惊在以奇奥语夺人眼目,而《古诗十九首》之能使人思在以平淡语造深厚之境。《古诗十九首》造语虽平淡,思致却深远,又始终不以一语道破,诗人的感情始终若隐若见、欲露不露,蕴藉缠绵,故《古诗十九首》虽无其他古诗的“新矫夺目”之姿,但又能以含蓄厚实、耐人咀嚼比其他古诗更能发人深思。
又谭元春说《古诗十九首》诗品在诸古诗之上的原因,即在于《古诗十九首》的性情之厚。陈廷焯《白雨斋词话》论“沉郁”,曰“忠厚之至,亦沉郁之至”[9]4,曰“沉郁则极深厚”[9]16,又曰“即比兴中亦须含蓄不露,斯为沉郁,斯为忠厚。”[9]28唯其忠厚,故能沉郁,能沉郁则能深厚,可见忠厚为深厚之根本。其言虽是论词,但亦可移作论诗。《古诗十九首》的深厚即在其性情之厚:感时伤世之言,而出以缠绵忠爱;怨慕幽思之意,而本诸温厚和平。故论其诗品,已臻绝顶,而远在其他古诗之上。钟惺说“深厚者易久,新奇者不易久”[2]474(《与谭友夏》),又说“真者可久,伪者易厌”[2]290(《静明斋社业序》),因此《古诗十九首》的“性情光焰”之所以“有一段千古常新,不可磨灭处”,其原因就在于其性情之厚、性情之真。正因为《古诗十九首》的作者性情柔厚,所以他的感情既温且柔,而“温柔的感情,是千层万叠起来的敦厚的感情。这种敦厚的感情,有如一个广大的磁场,它含有永恒的感染力。”[7]37又正因为《古诗十九首》的作者性情忠厚,所以他的感情并无半点的虚伪和矫饰,故而发之为诗,诗中表现出来的性情必然深具沛然于肺肝中流出之致,便永远能给人以自然而新鲜的感觉。由此,则《古诗十九首》的“性情光焰”自然“有一段千古常新,不可磨灭处”。
钟、谭在《古诗归》与《唐诗归》中还常以《古诗十九首》为准的论诗,所取也常常是《古诗十九首》的含蓄蕴藉之“厚”。如《古诗归》评徐幹《室思》说:“宛其有《十九首》风骨。”“以名义厚道束缚人,而语气特低婉。”[8]432(《古诗归》卷七)评鲍照《拟行路难》三首:“极悲凉,极柔厚,婉调幽衷。”“全副苏李、《十九首》性情。”[8]479(《古诗归》卷十二)谭元春评李陵《与苏武诗三首(选二)》之二说:“字字真,所以字字苦。字字厚,所以字字婉。”[8]389(《古诗归》卷三)钟惺评曹植《圣皇篇》说“深婉柔厚”[8]429(《古诗归》卷七),可见“婉”即深沉婉约,指的即是诗歌的浑厚蕴藉之美。徐幹《室思》、鲍照《拟行路难》抒发的虽是怨艾之情,但作者不失温和忠厚之旨,能以委婉曲折的表现方式出之,这就形成了含蓄蕴藉的风格,正与苏李诗、《古诗十九首》温柔敦厚的性格相似,故钟、谭称其宛有《古诗十九首》的性情、风骨。又钟、谭二人对前人将阮籍《咏怀诗》比肩于《古诗十九首》的做法深为不满,认为阮籍《咏怀诗》是不合正统诗教的“异调”(钟惺评语),根本无法与《古诗十九首》温柔敦厚的性格相提并论,因此《古诗归》对阮籍的八十二首《咏怀诗》只入选了三首,并对入选之诗仍有微辞,可见其删汰之繁。谭元春评语云:“古今以嗣宗《咏怀诗》几于比《古诗十九首》矣,尽情删之,止存三首。三首中气格情思,视古诗何如?岂敢向古人中吠声耶!”[8]435(《古诗归》卷七)钟、谭对阮籍《咏怀诗》的评价虽不无偏颇谬误之处,但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出二人将《古诗十九首》温柔敦厚的诗歌性格视为作诗和论诗的最高理想目的。
三
《古诗十九首》之“厚”,还在其浑融无迹。严羽《沧浪诗话》对诗学观念的影响几乎贯穿了有明一代,竟陵派自然也不能例外地受其影响。作为严羽诗法的“流裔别子”[6]245,钟、谭在诗学理念上接受了严羽“羚羊挂角,无迹可求”[10]26的文艺思想,追求浑然天成、无迹可寻的艺术境界。他们特别推崇那种“裹出一片,流出真诗”[11]120(《唐诗归》卷二十三)的浑融境界,认为理想的诗作应当“灏气自然归一朴”(钟惺诗《岱游告成示康虞茂之》),“一气流转,读之落落然”[11]226(《唐诗归》卷三十三)。这些诗学理想,追求的都是一气而下,自然浑成的诗歌境界。而《古诗十九首》就是契合竟陵派这种诗学理想的诗歌典范。
钟惺在《与高孩之观察》中称《古诗十九首》“元气大化,声臭已绝”,其实就有指《古诗十九首》浑然一体、无迹可寻的含义,他在评杜甫《万丈潭》时所说的“元气无痕”[11]55(《唐诗归》卷十八)和谭元春所说的“‘元气混沌’以上语,止宜厚其气而泥其迹”[5]764(《奏记蔡清宪公前后笺札》其八)正可与此相互印证。这种认识在钟惺对《明月皎夜光》的评语体现得更为明显:
此首“明月皎夜光”八句为一段,“昔我同门友”四句为一段,“南箕北有斗”四句为一段。似各不相蒙,而可以相接。历落颠倒,意法外别有神理。大抵《十九首》中,正反起止,有似非出于一人、一时、一事者,而终不可分为数题。即一首中亦似有非出于一人、一时、一事者,而终不可分为数首。《十九首》不必皆可选,而难去其一,其故在此。他诗则不然,知者审之。[8]418(《古诗归》卷六)
钟惺这里所说的意思其实和严羽在《沧浪诗话》中所说的“汉魏古诗,气象混沌,难以句摘”[10]151一致,说的都是《古诗十九首》章法浑成,语转而意不换,句意连贯而下,通篇浑然一体,故其既不可以句摘,一首也终不可分为数首。《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钟、谭所选《诗归》“力排选诗惜群之说,于连篇之诗随意割裂,古来诗法于是尽完。”[12]细考《诗归》一书,可知四库馆臣之说诚为不诬:除前文已提到的阮籍《咏怀诗》在《诗归》中的收录情况外,又如曹植《赠白马王彪》只节录两章,左思《咏史诗》八首仅收录二首,他多类此,无遑详举。因为《古诗十九首》在艺术结构上的浑然一体、无迹可寻,根本无法割裂字句,所以钟惺虽然认为《古诗十九首》“不必皆可选”,但欲作取舍,却又发现无从措手,实在“难去其一”,因此在《古诗归》中不得不整体收录了《古诗十九首》。钟惺在评张九龄《感遇十二首》其七时说:“拟《古诗十九首》若如此作,便妙合无痕,陆机诸人那得有此!”[11]583(《唐诗归》卷五)可见钟惺认为拟《古诗十九首》之难,正难在拟其妙合无痕。同时他在评苏武《诗四首(选三)》之一时说:“只是极真、极厚,若云某句某句佳,亦无寻处。后人一效拟,便失之远矣!”[8]389(《古诗归》卷三)可见苏李诗、《古诗十九首》的无迹可寻,其根源还是在于诗人的性情之真和性情之厚。
与钟、谭同时代的许学夷在《诗源辩体》中认为钟、谭合选的《诗归》“大抵尚偏奇,黜雅正,与昭明选诗,一一相反”,“然则《十九首》、苏李之选,乃古今名篇,不得不存,初非真好也。”[13]许学夷是在公安、竟陵两派风靡文坛之际,仍然恪守七子派诗论的人物,因此他对《诗归》一书的评价虽不无切中要害之处,但其中也不免挟有门户之见,如他说钟、谭对《古诗十九首》、苏李诗“初非真好”即是如此。竟陵派既提倡学古,又标榜汉魏古诗、乐府之“厚”,因此他们与七子派一样,对汉魏古诗都极为推崇:
钟云:唐人五言古,惟张曲江有汉魏意脉。不使人摸索其字形音响,而遽知其为汉魏,所以为真汉魏也。[14](《唐诗归》卷五)
得(车)孝则而予之所以惭汉魏而逊盛唐者,方有人乎究之。其何肯以秀逖止?陈同父奇人也,然生平不能作诗。观其为桑泽卿诗序,有“立意秀稳、造语平熟、不刺人眼目”之语,则同父真不知诗矣。诗岂如是之谓耶?郦生论山水曰:“峻崿百重,绝目万寻。既造其峰,谓已愈崧、岱,复瞻前岭,又倍过之。”我等作诗,真当作如是想。愿与孝则、(周)伯孔切磋究之。[5]675(谭元春《高霞楼诗引》)
七子派从格调说出发提倡汉魏高格,而钟、谭不谈格调,所以标举“汉魏意脉”,但二者的内涵并无区别,都是标榜以《古诗十九首》、苏李诗为代表的汉魏古诗的浑厚之格。谭元春在《高霞楼诗引》中自称束发以来,“至今诵汉魏、盛唐之诗”而自觉“惭汉魏而逊盛唐”,究其原因,则在不能追踪汉魏、盛唐之诗的浑厚之格,他所引用的郦生论山水的比喻,形容的就是汉魏、盛唐之诗那种意味深长、涵咏不尽的含蓄蕴藉风格。
钟、谭对汉魏古诗的推崇,还可溯源到他们早年的学诗经历。钟惺少年入塾读书时便好《文选》、李白诗,他自述早年学诗“大要取古人近似者,时一肖之,为人所称许,辄自以为诗文而已。”[2]259(《隐秀轩集自序》)他的同乡先辈李维桢在为钟惺早年的一部诗集《玄对斋集》作序时也说:“集中诗可百余篇,而汉、魏、六朝、三唐语,若起其人于九京,口占而腕书者。”[2]623-624其后他自创一派,于是“尽删庚戌(万历三十八年)以前诗,百不能存一”[2]260。而谭元春早年学诗,则将一部《文选》“拟之殆遍”[5]624,所以李维桢在序谭元春的早年诗集时同样也说:“友夏诗无一不出于古,而读之若古人所未道”[5]941,并誉其诗出入汉魏、晋人之间。从钟、谭的自述及早年诗作来看,他们早年学诗取乎法上,是以汉魏、盛唐之诗为取法对象的,而他们“早年的这种学习之功,多少总会在他们今后的文学事业留下某种印记,即便是起而排击王、李之学而求创变,其取向亦终不脱古人之传统,这又未必不是此际的经历暗暗为之根株。”[15]由此正可见出钟、谭论诗主“厚”而以《古诗十九首》、苏李诗和汉魏乐府为鹄的,是与他们早年的学诗经历息息相关的。钟惺在给谭元春的书信中曾说:“轻诋今人诗,不若细看古人诗;细看古人诗,便不暇诋今人也。思之!”[2]462古人诗之所指,即是钟、谭早年即极为熟稔的汉魏、盛唐之诗。
因此,钟、谭虽然抨击萧统《文选》所选古诗并非真古诗而称之为“选体”(钟惺《诗归序》),并且《诗归》在选目上有意“彼取我删,彼删我取”[5]758(谭元春《奏记蔡清宪公前后笺札》其四),也即许学夷所说的“与昭明选诗,一一相反”。但据上所论,钟、谭对《古诗十九首》、苏李诗绝非像许学夷所说的那样“初非真好”,《诗归》整体收录《古诗十九首》也绝非是因为慑于《古诗十九首》为“素所得名之诗”而“不能违心而例收者”[5]595(谭元春《诗归序》),而实是出于他们对《古诗十九首》真心的推崇和喜好,我们从一个小细节中也可见出这一点。钟惺在《书茂之所藏谭二元春五弟快手札各一道纪事》中曾记载了其五弟钟快跟从谭元春学习书法之事,其文曰:“记甲辰十月,谭友夏过予,日为客作书。予弟从旁凝视颇笃。友夏察其意之近于书也,书《古诗十九首》,使之影摹,辄肖。”[2]576对《古诗十九首》信手而书并以其作为教授书法的范本,正可见出谭元春对《古诗十九首》的喜好器重和烂熟于心。
钟、谭虽然论诗力主一个“厚”字,也自知作诗清新而有痕,除以“厚”救之外,别无他途:“痕亦不可强融,惟起念起手时,厚之一字可以救之。”[2]473(钟惺《与谭友夏》)但作为一个新兴的诗歌流派,竟陵派也不免存在创作实践与理论主张脱节的毛病,钟惺在《与高孩之观察》中自言:“夫所谓反复于厚之一字者,心知诗中实有此境也;其下笔未能如此者,则所谓知而未蹈,期而未至,望而未之见也。”[2]474然而诚如陈少松先生所说,竟陵派“这种理论与创作存在脱节的现象不足为怪,我们不能因为钟、谭的诗歌创作没能达到‘厚’的境界而贬低甚至否定其在理论探讨上所取得的成绩。”[16]竟陵派倡导以《古诗十九首》为代表的、基于性情之真的古诗之“厚”,将学古与性灵说完美地结合在了一起,既纠正了七子派专从气格才调求古诗之“厚”的弊端,也对公安派瑕瑜互见的性灵说作出了修正和新的发展,对促进晚明文坛风气的健康发展无疑起到了积极作用。正如学者所言,“竟陵派所倡之‘厚’,在理论上没有太多的独创,但在当时持殊的背景下,较辩证地救‘七子’复古之弊与‘公安’性灵之偏,启发文学走出左右摇摆的困境,这对当时的文坛,乃至对于整个文学的发展,都是一个不小的贡献。”[17]
参考文献:
[1]袁宏道.袁宏道集笺校[M].钱伯城,笺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1485.
[2]钟惺.隐秀轩集[M].李先耕,崔重庆标校.上海:上海古出版社,1992.
[3]贺贻孙.诗筏[C]//郭绍虞.清诗话续编(一).北京:中华书局,1983:141.
[4]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下卷).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99:250.
[5]谭元春.谭元春集[M].陈杏珍,标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6]周振甫,冀勤.钱钟书《谈艺录》读本[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83.
[7]徐复观.中国文学精神[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4.
[8]钟惺,谭元春.古诗归[C]//顾廷龙.续修四库全书:子部1589.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9]陈廷焯.白雨斋词话[M].杜末末,校点.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
[10]严羽.沧浪诗话校释[M].郭绍虞,校释.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
[11]钟惺,谭元春.唐诗归[C]//顾廷龙.续修四库全书:子部1590.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12]纪昀总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5297.
[13]许学夷.诗源辩体[M].杜维沫,校点.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370.
[14]钟惺,谭元春.唐诗归[C]//顾廷龙.续修四库全书:子部1589.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582.
[15]陈广宏.竟陵派文学的发端及其早期文学思想趋向[J].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1):96-108.
[16]陈少松.钟、谭论“灵”与“厚”的美学意蕴[J].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4):105-109.
[17]曹红祥.诗为情物期在必厚——竟陵派诗歌本质特征论探析[J].黄河学刊,1994,(2):6-11.
责任编辑:周哲良
中图分类号:I207.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 2094(2016)01- 0043- 05
收稿日期:2015-12-07
作者简介:魏友(1989-),男,湖南邵阳人,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古代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