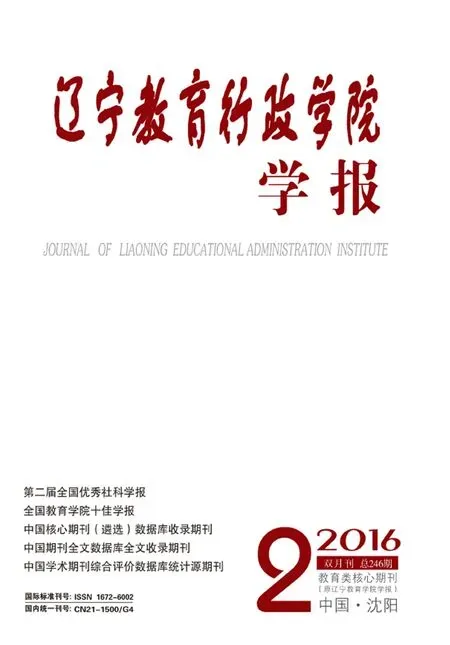从世界体系的视角看现代黎巴嫩的国家、阶级与教派
李海鹏
北京大学,北京100871
从世界体系的视角看现代黎巴嫩的国家、阶级与教派
李海鹏
北京大学,北京100871
摘要19世纪40年代起,奥斯曼帝国加速纳入欧洲主导下的现代世界体系。在欧洲丝织工业原料需求不断扩大的刺激下,黎巴嫩山地区丝织业获得迅猛发展,生丝生产成为该地区的支柱产业。丝织业的发展加速了山区南北部的人口流动,推动了新阶层的产生与分化,加剧了教派间经济地位的差异,诸多因素最终导向了1860年黎巴嫩教派内战。内战后的政治安排奠定了现代黎巴嫩国家的雏形以及政治教派主义体制的基本框架,剧烈社会-经济变迁所造成的黎巴嫩国内阶层、教派、政治认同裂痕则一直延续至今。
关键词现代世界体系;奥斯曼帝国;黎巴嫩;丝织工业
随着叙利亚、伊拉克成为中东地区动荡、地区及国际势力角逐的焦点,加之2014年恰逢一战爆发百年纪念,《赛克斯-皮科协定》再次进入学界乃至普通民众的视野,阿拉伯新月地区国家体系的“人造性”似乎被视为当前该地区动荡局势的重要根源。然而,欧洲殖民主义扩张对中东地区的影响远为复杂微妙,不仅涉及瓜分势力范围乃至建立殖民统治等政治、军事活动,同样体现其经济渗透在相关地区引发的社会变迁、政治认同萌芽等层面。本文试以沃勒斯坦的现代世界体系理论为主要分析框架,通过对奥斯曼帝国叙利亚行省黎巴嫩山地区丝织工业发展兴衰及其政治、社会影响的案例分析,从经济视角揭示欧洲渗透对中东,特别是阿拉伯马什里格地区现代国家建构乃至当代历史进程的复杂影响。
一、现代世界体系中的奥斯曼帝国
二战以来,西方国家开始出现各种带有激进色彩的发展理论,对传统的现代化理论构成重大挑战,其中以伊曼纽尔·沃勒斯坦为代表的世界体系理论影响尤为深远。沃勒斯坦认为,自15世纪起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现代民族国家为核心的世界经济体——现代世界体系便逐渐成型,其主要特点包括体系内不同层级间的中心与边缘关系、上升阶段(A阶段)与下降阶段(B阶段)的经济周期以及同一层级国家间的霸权与竞争趋势。根据该理论,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可分为中心、半边缘和边缘三个层次,中心地区在这一体系中占据支配地位,其工农业生产水平、经济结构复杂程度以及资本积累水平都处于领先地位,机械化程度高,生产具有高附加值的产品;边缘地区经济发展落后,以生产原料和农产品为主,且趋向于劳动密集型生产;半边缘地区的技术水平和资本密集程度都处于二者之间,起着避免中心与边缘直接对抗的缓冲作用。中心与边缘之间的关系是不平等的交换关系,生产的剩余价值从边缘向中心流动,进一步增强了中心的资本和技术优势;剩余资本的不平衡流动使得中心与边缘地区国家机器间的实力差距进一步增大,迫使边远地区难以打破并不得不接受不平等的劳动分工。①[P79~80,P84]政治结构层面,现代世界体系是一个由民族国家构成的国际体系,民族国家是其基本政治单元,也是其产物;国家力量是现代世界体系中中心区域实现资本积累的重要因素,客观上维持着世界体系的既有秩序。世界体系理论同样承认民族国家内部存在阶级、身份集团、家庭等次级建构,它们都是现代世界体系的产物。可以说,世界体系理论为我们理解西方扩张对非西方世界的复杂影响提供了一个系统性的、动态的视角。
作为与欧洲毗邻的世界性帝国,奥斯曼帝国远在现代世界体系在欧洲成型之前就与其西部邻邦发生了密切的经济联系。15世纪末至16世纪初,资本主义市场的生产方式和世界经济体开始发轫于西欧一隅,并很快对奥斯曼帝国产生影响。为拓展在奥斯曼帝国商业利益,法国、英国分别于1569年、1580年与奥斯曼政府达成治外法权协议,保证两国商人在帝国内自由买卖合法商品而不受干扰的权利,同时规定无论涉及民事或刑事案件、两国臣民只在本国领事法庭根据本国法律受审。然而,直至19世纪上半叶,奥斯曼帝国尚未被完全纳入触角不断延伸的世界资本主义体系。1838年,《英国——奥斯曼商业协议》是一个重要的分水岭,这一协议取消了奥斯曼帝国对其农业、手工业产品的一切保护政策,清除了欧洲扩大对奥斯曼帝国贸易的最主要障碍。自此以来,欧洲与奥斯曼帝国双边贸易额迅速扩大,其中英国取代法国成为奥斯曼进口商品的最大来源国,后者则成为英国棉纺织产品的第三大消费国;法国则是奥斯曼帝国原料和商品出口的重要对象国,19世纪60年代早期占据了奥斯曼商品出口总额的30%。至奥斯曼帝国末期,欧洲列强已完全控制了奥斯曼帝国国内贸易、基础设施乃至财政运转,其中英、法、德、奥地利四国即占据了帝国进口商品总额的3/4,同时吸收了60~70%的奥斯曼出口产品。②[P831~832]奥斯曼帝国已完全沦为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的边缘国家。
在评估纳入世界经济体系对奥斯曼帝国的影响时,沃勒斯坦强调帝国在财产权结构、生产活动中的社会关系、产业模式等三方面的根本性变迁:在奥斯曼政府推动下,包税制逐渐取代了原有的蒂玛尔制度,地方士绅逐渐转变为包税地产权的实际所有者,土地私有产权逐渐制度化;原封建骑兵管理下的自耕农沦为受包税人压榨的分成制佃农;农业生产转向欧洲中心国家所需的原料或经济作物,西方工业制成品冲击下传统手工业迅速凋零。③[P88~97]需要强调的是,欧洲经济渗透常常与欧洲——奥斯曼帝国间的军事、政治互动联系密切,奥斯曼政府推动新的农业税收模式,很大程度上即源于为缓解欧洲军事压力而建立新军事建制所带来的财政负担。此外,对横跨欧、亚、非大陆的奥斯曼帝国而言,上述影响在时间上常常是不同步的,且在不同地域具有明显的不平衡性,其在巴尔干、小亚西部、叙利亚沿海地区的影响就明显早于、且强于在帝国边缘行省。最后,欧洲经济渗透对奥斯曼帝国“米列特”制度产生了重要影响:作为对奥斯曼政府施加政治压力的手段,欧洲列强逐渐将奥斯曼帝国各少数宗教群体——即米列特——纳入其治外法权范围,并在这些群体中传播其文化影响,而充当奥斯曼——欧洲贸易中介人的基督徒和犹太人也成为帝国纳入欧洲经济体系过程中的经济受益者。奥斯曼叙利亚行省黎巴嫩山地区丝织业的发展正可作为上述判断的一个例证。
二、奥斯曼黎巴嫩山地区丝织业的兴起
黎巴嫩山地区指今黎巴嫩共和国的中北部山地地区。奥斯曼帝国时期,这一地区先后归由大马士革行省、的黎波里行省、赛达行省管理。由于地理条件闭塞,至少自11世纪起黎巴嫩山地区就成为基督徒、穆斯林各异端教派的聚居地,其中以信奉天主教的基督教马龙派和由穆斯林什叶派分化而来的德鲁兹派最具影响,前者由于历史原因与法国及罗马天主教廷长期保持着密切文化联系。与叙利亚其他地区转向地方士绅主导下的大地产佃农经济不同,这一地区以村落小自耕农经济为主。地方政治精英由家族世袭、扮演包税人角色的埃米尔和以德鲁兹派为主的封建领主组成,平民阶层则主要由德鲁兹、马龙派农民构成。经济生活方面,鉴于其有利的自然生态条件,黎巴嫩山地区在植桑养蚕领域拥有悠久的传统,主要向叙利亚内陆城镇传统丝织工业提供原料。
如果说半自治的政治地位、稳定的精英阶层、独特的经济条件和文化背景塑造了黎巴嫩山地区独特的政治文化,那么真正决定其近现代政治轨迹的则是欧洲经济渗透、特别是欧洲丝织业发展的影响。随着新大陆贵金属大量涌入欧洲,16世纪40年代起,欧洲民众开始大量购买亚洲产品,丝织品也由奢侈品转变为大众能够负担的普通消费品。17世纪下半叶,丝织工业开始在欧洲兴起,欧洲对生丝原料的需求进一步扩大。18世纪欧洲丝织工业经历了稳定增长,并于19世纪20年代后进入高速发展期。欧洲中心国家丝织工业的高速发展以及丝织产品消费需求的迅速增加,推动了桑树等经济作物在奥斯曼帝国内的广泛种植,包括叙利亚沿海省份在内的相关地区也迅速成为欧洲丝织业的原料供应地。如上所述,至19世纪中叶奥斯曼帝国已完全纳入世界经济体系,同一时期桑树等经济作物也成为黎巴嫩山地区的主要农作物,粮食产品则完全依赖由叙利亚内陆地区购买。至一战前,丝织业相关产值占黎巴嫩山自治省经济总产值的70%以上,丝织产品占其出口总额的60%以上,提供了自治省超过35%的财政收入;山区约50%劳动力从事与丝织业相关的工作。④[P165~166]
三、丝织工业与现代黎巴嫩:国家、阶级、教派的雏形
黎巴嫩山自治省时期是黎巴嫩山地区丝织工业的黄金年代,而丝织工业的某些特点则对山区社会政治进程产生了意想不到的深远影响。蚕丝生产每年仅持续约四十天,却需要很高的劳动强度,而男性多倾向于选择固定而非临时性的工作,因此丝坊中主要雇佣女性工人。根据黎巴嫩山地区民俗,穆斯林和德鲁兹教派极少允许女性在家庭外工作。因此,自17世纪起山区统治家族便鼓励山区北部的基督教马龙派农民向南部的德鲁兹聚居区迁徙,为德鲁兹封建领主服务,以提高蚕丝产量。随着人口流动的持续,黎巴嫩山南部地区的人口结构开始发生显著改变,德鲁兹聚居区逐渐转变为德鲁兹——基督徒混居区域,至19世纪上半叶已成为基督徒人口占多数的区域。两大教派由于土地所有权纠纷而爆发冲突,很自然地被企图控制奥斯曼帝国的欧洲列强所利用——部分欧洲国家开始以保护奥斯曼帝国内基督徒社群为由向奥斯曼政府施加压力。1860年,马龙派——德鲁兹派内战后,以法、英为首的西方列强介入,强迫奥斯曼政府建立一个在欧洲六国共同监管之下的黎巴嫩山自治省,在自治省内按教派人口比例划分政治权力,由此奠定了现代黎巴嫩民族国家的雏形及其教派体制的基本框架。这一不稳定的政治体制,也在20世纪70年代爆发为长达15年的血腥内战,成为至今仍困扰着黎巴嫩政治运转的幽灵。
除国家构建的进程外,欧洲经济渗透背景下黎巴嫩山丝织业的发展同样深刻地影响了山区社会的阶层分化、教派平衡乃至精英政治取向。19世纪60年代,随着丝绸价格的上涨,法国资本和贝鲁特本地银行家更倾向于贷款给本地商人和蚕茧中间商,本地资本所有的小型纺丝厂数量迅速增加。随着本地资本主导的生丝出口贸易日益成熟,一个与欧洲殖民经济利益密切相关的新兴商业中产阶级逐渐成型。另一方面,随着贝鲁特的银行家和借贷者成为生丝贸易中重要的一环,一个以贝鲁特为中心的商业——金融寡头集团开始出现。原封建领主阶层、小农和分成制佃农则受益甚少:前者虽仍掌握着大量地产,但资金渠道限制却使其无法充分利用土地、人力资源优势,很多情况下反而要为偿还欠款而出卖地产;后者则逐渐转变为单纯的蚕茧生产者,越来越受制于中间商和借贷者,山区传统的自给自足经济也因此加速瓦解。
更重要的是,黎巴嫩山各个教派从丝织产业繁荣中受益并不平衡,无论对“新富人”还是普通农民而言,基督徒,尤其是马龙派的受益都明显高于德鲁兹派。自治省时期山区建立的本地丝织厂中,为基督徒所有的丝织厂占总数量的93.0%(144/155),占据了绝对多数;德鲁兹人仅控制着7座丝织厂(4.5%),且这些工厂主没有一位来自黎德鲁兹传统六大领袖家族,这也说明了原封建领主家族的经济活动已严重滞后于这一时期山区的社会-经济转型。⑤[P32]不同教派农民家庭从丝织工业中的受益情况同样不同,这一点充分体现在丝织厂雇佣工人的教派构成上:1911年黎巴嫩山丝织厂雇佣工人总数约为14,000人,其中基督徒约占13,000人(92.85%),马龙派8,500人(60.72%),而德鲁兹工人总数仅约1,000人(7.14%)。⑥[P121~122]考虑到基督徒人口占山区总人口比例为79.7%,德鲁兹派为12.4%,基督徒农民家庭从丝织产业中受益明显更高。后续历史表明,基督徒的经济优势很大程度上塑造了其政治认同,并与法国委任统治时期乃至独立后黎巴嫩欠平衡的教派政治体制相绑定,后者也埋下了现代黎巴嫩教派问题的种子。
最后,伴随着丝织业发展为黎巴嫩自治省带来的经济繁荣,基督徒、穆斯林商业以及官僚中产阶级对这一人造实体的政治认同逐渐确立。在西方教会学校接受教育,并受到欧洲民族主义思潮影响的基督徒,特别是基督教马龙派知识分子,开始尝试构建黎巴嫩民族主义的政治话语。在他们看来,黎巴嫩是不同于叙利亚或其他阿拉伯穆斯林世界的一个独立文化实体,享有“自然的”历史边界,继承了腓尼基人开放的商业城邦传统,并共享着反抗穆斯林“侵略者”和长期自治的民族历史记忆。马龙派的这种逐渐成熟的原型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对于法国委任统治下的“大黎巴嫩”以及二战后黎巴嫩共和国的建立都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尽管后期经过复杂的修正,黎巴嫩民族主义与阿拉伯民族主义间的张力从未得到完全消解,这也成为理解20世纪黎巴嫩历史的一个重要线索。
20世纪30年代,人造丝和尼龙迅速取代生丝成为纺织工业的主要原料,黎巴嫩丝织业也遭遇致命打击。至此,丝织业完成了其在近代黎巴嫩民族国家构建和社会经济转型中的角色,最终淡出历史舞台。应该说,丝织工业仅是19~20世纪世界经济体系中的微小一环,但奥斯曼帝国于18世纪中叶被纳入世界体系,却在处于体系边缘的黎巴嫩山地区引发了剧烈的社会经济和文化转型。正是在这一转型时期,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阶级、政治化的教派开始在奥斯曼帝国的这一边缘省份逐渐成型。这一案例也充分揭示,早在对中东地区直接产生军事冲击乃至建立殖民统治之前,西方世界已通过经济渗透的形式对该地区社会产生了复杂而深刻的影响。
注释:
①江华.世界体系理论研究:以沃勒斯坦为中心(第1版)[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7(7).
②Halil Inalcik & Donald Quataert ed.An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of the Ottoman Empire[M].Cam⁃bridg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4.
③Immanuel Wallerstein et al.‘The Incorporation of the Ottoman Empire into the World- Economy’, in Hurislamolu-nan ed., The Ottoman Empire and the World-Economy[C].Cambridg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7.
④Roger Owen, The Middle East in the World Economy [M].London; New York: I.B.Tauris, 1993.
⑤Kais Firro.‘Silk and Socio-economic Changes in Lebanon, 1860-1919’, in Elie Kedourie & Sylvia G.[C].Haim ed., Essays on the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Middle East London; Totowa, N.J.: F.Cass, 1988.
⑥Boutros Labaki, Introduction à l’histoire économique du Liban: soie et commerce extérieur en fin de période ottoman[M].Beyrouth: Université liba⁃naise, 1984.
[参考文献]
[2]Kedourie, Elie & Haim, Sylvia G.ed.Essays on the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Middle East[M].Lon⁃don; Totowa, N.J.: F.Cass, 1988.
[3]Labaki, Boutros.Introduction à l’histoire économique du Liban: soie et commerce extérieur en fin de période ottoman[M].Beyrouth: Univer⁃sité libanaise, 1984.
[4]Owen, Roger.The Middle East in the World Econ⁃omy[M].London; New York: I.B.Tauris, 1993.
(责任编辑:彭琳琳)
文献标识码A
中图分类号K135
收稿日期2016-01-27
作者简介:李海鹏(1980-),男,北京人,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阿拉伯语系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阿拉伯伊斯兰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