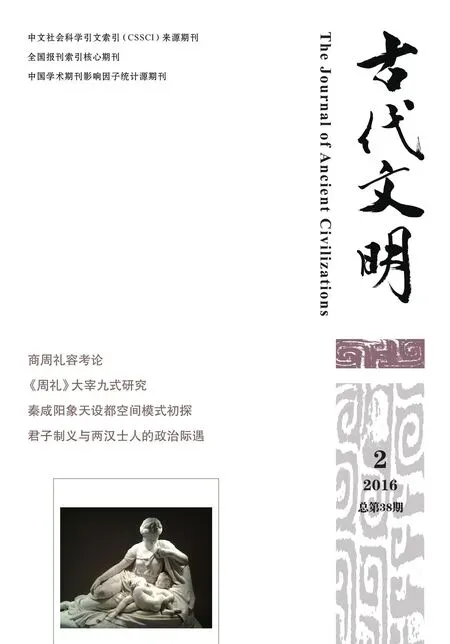日知先生的历史比较研究思想﹑实践和特点初探——读《日知文集》札记
王大庆
日知先生的历史比较研究思想﹑实践和特点初探——读《日知文集》札记
王大庆
提 要:林志纯先生(笔名“日知”)是我国世界古代史研究领域的开拓者和领路人。历史比较研究是日知先生学术研究中一以贯之的指导思想之一,他不但对历史比较研究方法本身有着深入的思考,而且还身体力行,把这种方法充分运用到了整个中外历史研究的实践当中,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不仅开辟了一片新的研究领域,而且还提出了许多富有启发性和创造性的学术观点和研究课题。
关键词:林志纯;历史比较研究;《日知文集》
2012年,五卷本的《日知文集》(以下简称《文集》)出版,该书收录了对我国世界古代史领域做出卓越贡献的开拓者和领路人林志纯先生(笔名“日知”,1910年—2007年)生前的几乎所有学术论著,既包括已经出版的著作和论文,也包括一些未刊稿。2014年,由日知先生生前所在的东北师范大学主办并以先生笔名命名的“日知世界史”奖也顺利启动。《文集》的出版和“日知世界史奖”的设立是中国的世界史研究,尤其是世界古代史研究领域的大事。
日知先生博学多识,学贯中西,在几十年的学术生涯中,不仅培养出了一大批世界古代史领域的优秀学人,为该学科的建设和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而且身体力行,笔耕不辍,著述颇丰。其学术研究“体大思精”,1语出《文集》“整理说明”,见林志纯:《日知文集》第一卷,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2年,第I—II页。高屋建瓴,提出了一系列富有创造性和启发性的学术问题,受到了学界广泛的关注,并对后来的学术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王敦书先生曾以“热爱祖国,钻研史学,献身教育,立身行道”这十六个字来概括日知先生的成就,2参看王敦书:《垦荒播种创学业,学贯中西通古今——庆祝林志纯先生九十华诞》,载《中西古典文明研究》编写组编:《中西古典文明研究——庆祝林志纯教授90华诞论文集》,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页。可谓全面而精当。作为一个该领域的后生晚辈,笔者在读研究生期间就认真拜读过先生的著述,并多次当面聆听先生的教诲。《文集》的出版,使我能够更为全面和系统地重新学习和细细体味先生的研究成果,在阅读的过程中又产生了许多新的想法,获益良多。本文即围绕自己感触颇深的一个问题,即日知先生的历史比较研究的思想﹑实践和特点,谈一些不成熟的心得和体会,想借此对先生的历史比较研究思想作一些归纳和梳理,同时,向日知先生表达崇敬和怀念之情。不当之处,敬请各位师友批评指正。
一、日知先生对历史比较研究本身的思考——比较研究的可能性和必要性
纵观日知先生一生的学术研究,使人最为印象至深和叹为观止的是先生关注的学术问题和涉及的研究领域十分广阔。从横向看,论及的古代文明包括了古代中国﹑古代埃及﹑古代西亚﹑古代印度﹑古代希腊罗马和古代中南美洲,几乎囊括了所有重要的古代文明;从纵向看,论及的问题则贯穿了原始社会﹑封建社会和中外近现代的历史。从历史研究本身的层面上看,既有对具体的﹑局部的和微观的历史过程(包括从文献学的﹑古文字的角度)的细致考察,也不乏对历史发展规律的理论性的﹑整体的和宏观的深入思考。要对如此庞大和复杂的研究领域进行把握和分析,必须要有一些一以贯之的指导思想,笔者认为,历史的比较研究就是这样的指导思想之一。在这里需要指出的是,虽然日知先生从来没有就历史的比较研究本身做出专文进行论述,而且,直接进行历史比较的文章和著作也仅仅是其全部研究成果中的一小部分,但通过学习,笔者发现,日知先生不但在几乎所有的研究中都表现出强烈的历史比较研究的意识,有着明显的历史比较研究的视角,而且对历史比较研究本身也不乏精彩的论述和深入的思考,这些论述和思考散见于很多具体历史的研究当中。下文将结合《文集》中的有关内容,就日知先生对历史比较研究本身的思考进行一些归纳和总结。
总的来看,日知先生对这个问题的思考大致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历史的比较研究需要具备哪些条件,即比较研究的可能性问题;二是历史的比较研究有什么价值和意义,即比较探究的必要性问题。
说到历史比较研究的可能性,日知先生在为其主编的《古代城邦史研究》撰写的前言中指出,近百年来中外的考古学﹑古文字学和文献学的大发展使很多已经中断和失落的古代文明得以重见天日,这些进展为中外古史的比较研究,尤其是古代城邦史的研究提供了极为丰富的资源,从而使历史比较研究的条件日益成熟和完备:
古代城邦史是近百年来考古学、历史学发现和发掘的产物,是古文字学家和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各门学者长期辛勤劳动的成果。百年以前,人们不知道有西亚的苏美尔·阿卡德,不知道有埃及的前王朝、早王朝,不知道印度河文明哈拉巴文化,不知道地中海东部有爱琴文明,也不知道中美、南美有玛雅文明和印加帝国。古代中国古籍上的夏商周三代,一向也被看作是传统的王朝世系,而城邦从来不曾说起。百年来科学的发展,使这些古代文明,这些古代城邦的历史与文化重现于世,文字多被释译,原先不懂的现在有许多已懂得了;地下的埋藏,许多已被运送到各博物馆供人们参观和研究。古代中国古籍上的记载,有不少也已得到考古学和古文字学研究成果的印证。
这样,我们今天有条件来研究世界各地古代城邦史,来研究自己祖国的古代城邦史。我们还有条件用比较研究的方法,把中西方古代国家的资料,中外古典文明的文字记录,互相补充,互相比较,而得到相互启发,举一反三之效。1林志纯:《日知文集》第一卷,第471—472页。
不过,对于历史比较研究的展开而言,仅有上述的发展似乎还是不够的,因为它并不能构成历史比较研究的充分理由,只是一些必要的外部条件,那么要进行历史的比较研究,还需要哪些内在的条件呢?正如刘家和先生所言,“无异之同不具有比较研究的条件……无同之异也不具备比较研究的条件……有相同,才能比其异同;有相异,才能比其同异”,1刘家和:《史学﹑经学与思想——在世界史背景下对中国历史文化的思考》,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2—3页。也就是说对于历史比较的对象来说两个完全相同和完全相异的事物,是不具备“可比性”的,这种“可比性”正构成了历史比较研究的内部条件。如果说是一百年来中外古代文明研究的巨大发展和资料上的积累为历史的比较研究提供了一种外部条件的话,那么,同中有异﹑异中有同的中外历史发展进程则为历史的比较研究提供了内在的条件和可能性。对此,日知先生曾多次指出,各个古代文明的具体发展道路的统一性和多样性为历史的比较研究提供了这种内在的可能性。例如,在谈到“封建主义”的问题时,日知先生就以中西封建社会为例,说明了二者的“同”和“异”为历史的比较研究提供了前提条件:
……就“拂特”(feud)或“拂特封建”(严复译名)或[中世]封建说来,是在农业生活定居地带的范围,其方式和制度,东方和西方,因地因时,各有其所宜,但中国和西欧,有许多方面,许多问题,可以互相比较,互相补充,彼此启发的。2林志纯:《日知文集》第四卷,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2年,第312页。
至于在“同”和“异”两者当中,哪一个对历史的比较研究更加重要,日知先生似乎更侧重于“同”,因为如果没有“同”的话,也就会失去了相互比较的前提和基础。在谈到古典中国何以没有出现西方古典的“黑暗时代”的时候,日知先生就强调了西方古典和中国古典的诸多共同之处正构成了二者进行比较探究的基础:
西方古典和中国古典都留下珍贵的文化遗产,政治学识遗产:民主,革命,人类平等,世界大同,国家政治制度,国家交往和组织,等等。在把西方古典文化和中国古典文化对比下,还可以在当代史学中提出一个研究的问题:古典中国何以没有“黑暗时代”而西方古典时代有之的问题!3林志纯:《日知文集》第一卷,第537页。
在《论中西古典学》一文中,日知先生再次重申了中西古典时代的“同”构成了历史比较研究之基础这样的认识:
古典时代是人类社会少年青年的成长时期。西方(欧洲)有此古典时代,中国亦有此古典时代。同是古典时代,时代相近似,社会的成就亦相当。此研究“中西古典学”之基础,亦“中西古典学”之必须提出的问题!中西古典学极富于历史上相互比较,相互启发的材料与内容!此中西古典学之宝贵也!4林志纯:《日知文集》第四卷,第465页。
总之,日知先生认为,古代各个文明之间既有“同”又存“异”的现实是历史比较研究最重要的内在条件,即“以中西古典学概括言之,有可比较者”。5林志纯:《日知文集》第一卷,第527页。
关于历史比较研究的必要性问题,即为什么要进行历史比较研究,比较研究对于世界古代史研究者,乃至于全部的中国学者来说到底有何价值和意义呢?对此,日知先生也有很多的思考和论述。
对于历史比较研究的价值和意义,日知先生多次在文章中指出,通过中外古典文明的比较研究,可以达到“相互启发,举一反三之效”。笔者认为,所谓“相互启发”,就是通过中外比较,既可以加深对外国历史和文化的了解和认识,也可以加深对自身的历史和文化的认识,在这个过程中,比较的双方都成为了对方认识自身的一面“镜子”,正如刘家和先生所言:“他(指日知先生——引者注)治外文﹑外国史可以说是为了更好地治中国史,治中国史也可以说是为了更好地治世界史”;6刘家和:《为我学世界古代史引路的老师——怀念日知林先生》,《古代文明》,2008年第2期所谓“举一反三”,就是通过历史的比较,去发现﹑归纳和总结出人类历史发展中的一些规律性的认识。不过,笔者认为,在历史比较研究的“相互启发”的功能这个方面的认识上,日知先生是有所侧重的,即他并不。主张在中国和外国文明的研究上平均用力,而是更加注重如何利用中国文明自身的资源,通过与外国文明的比较研究加深对自身的历史和文化的认识,他认为,这才是在中国的外国史研究和进行历史的比较研究最重要的也是最终极的目标。
日知先生指出,中国悠久和连续的历史和极为丰富的历史资料为历史的比较研究提供了十分优越的资源和得天独厚的条件:“我们中国有数千年从未间断的文明史,我们在古文字学﹑古代史学方面的一点一滴的收获,也许会同研究其他上古文明有互相印证的作用”。1林志纯:《日知文集》第一卷,第451页。与此同时,他也认为,“外国史知识不但对学习外国史的人有用处,而且对于学习中国史的人也有帮助”。2林志纯:《日知文集》第一卷,第423页。在谈到编辑《世界古典文明丛书》的时候,日知先生用这样两句话概括了该丛书的意义,即“旨在把西方古典文化引进中国,把中国古典文化向世界传播”,并进而指出:“Sinology或中国学,一向是以外国学者为主体的,今后仍当让位给中国学者自己主动来承担!”3林志纯:《日知文集》第一卷,第487—488页。这是何等的气魄呀!在感叹日知先生的雄心之余,可以看到,他在这个地方所要表达的既是中国的外国史研究,同时也是中外历史的比较研究最终的目标和归宿,那就是更好地了解和认识自身的文化和文明,正如他所言,“中国古典文明的真相,在今日,是在同西方古典文明文化对比下较为明确地认识到的”。4林志纯:《日知文集》第一卷,第537页。日知先生不但有这样的雄心和认识,而且在史学研究的实践上也一直坚守和履行着这样的目标和准则,在学习和研究外国古代的文字﹑文献和历史的过程中,一直没有放弃对中国古代典籍的研读和对中国古史研究的关注与思考,并试图把二者有机地结合起来。5据日知先生弟子吴宇虹介绍,“作为一个中国的世界史学者,林先生非常重视学生们的中国史的知识和水平,亲自给世界史研究生开授了几门中国古文献课”。而且,他还指出,对中国史的学习和探究正是其开创以东西方古代文明的比较研究为主要内容的“中西古典学”的重要准备和基础,“林先生利用他深厚的世界古代史和中国古代史的研究能力,开创性地进行了东西方古代文明比较研究并把这种全新的研究方式定名为中西古典学”。参看吴宇虹:《林志纯先生和我的亚述学研究》,《历史教学》,2012年第8期。
总之,就历史比较研究的价值而言,在日知先生看来,不但可以加深国人对外国历史的了解,更重要的是通过这样的研究,可以加深对自身的历史和文化的认识,同时,也可以利用中国自身的极为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为国际历史研究做出其应有的和更大的贡献,让中国的文化走向世界。
二、日知先生历史比较研究实践的一个主题——从中西古典文明的比较研究来探讨东西方历史发展的统一性和多样性
笔者认为,就日知先生的历史比较研究实践而言,基本上是围绕着一个主题而展开的,即从中西古典文明的比较来探讨历史发展的统一性和多样性。
1993年,日知先生发表了《论中西古典学》一文,提出了“中西古典学”的概念,并系统阐述了中西古典学的历史任务。6与周谷城﹑吴于廑﹑张政烺﹑胡厚宣﹑周一良﹑任继愈﹑张忠培﹑刘家和联名发表,载《世界史研究动态》,1993年第10期。1996年,他又发表了《再论中西古典学》一文,从一个十分重大的历史问题出发,即古典中国何以没有出现类似于欧洲中世纪那样的“黑暗时代”,对前文中提出的“中西古典学必须重新研究”做出了一次具体的尝试。7载《社会科学战线》,1996年第4期。1999年,日知先生的论文集《中西古典学引论》由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文集不仅收录了上述两篇文章,而且以“中西古典学”来命名,可见其纲领性的重大意义。如果说这两篇文章和一本论文集主要提出了“中西古典学”的概念,并主要从“中西邦学”的层面来进行了比较研究的尝试的话,那么以此为基础,1997年出版的学术专著《中西古典文明千年史》(吉林文史出版社)则把历史比较的范围扩大到更为广阔的文明区域,几乎涉及了所有的古代文明,同时拉长了考察的时段,从文明的起源到古代文明和中古文明,尤其是加重了古代中国文明的内容和份量,可以说,这本著作是日知先生一生学术成果的一次总结和历史比较研究思想的结晶。从以上简要的回顾中可以看出,如果用一两个词来概括日知先生一生所从事的古史研究的主要内容的话,那么“中西古典学”和“中西古典文明”无疑就是这样的关键词。
对于“中西古典文明”这一概念的内涵,日知先生在《中西古典文明千年史》中从早期的“古代希腊罗马到中世纪的西方文明”和“古代中国文明”二者之间的对比为主,扩大到了一个更为广阔的文明区域,创造性地提出了“古代文明三大地区与中西古典文明两大系统”的理论,从而把历史比较研究的视野扩大到几乎涵盖了所有欧亚大陆的古代文明。他指出:“由于语言民族系统的复杂关系,古代文明世界三大地区或三大部分中,中间北非﹑西亚(近东)﹑南亚﹑中亚﹑伊朗部分,同西方欧洲部分,事实上联系在一起了,由苏美尔文明·阿卡得文明而下的系统同克里特·迈锡尼文化而下的希腊·拉丁·日耳曼系统,互相穿插,随着历史的发展,在古代文明世界,这两部分,即中间近东至中亚﹑南亚部分,同西方欧洲部分构成了古代文明世界的西方古典文明系统,即与中国古典文明系统形成中西两大古典文明并立的局面,结局是:古典文明世界是一个古典文明整体,它包括三个古代文明地区,构成中西古典文明两个系统,如表:1林志纯:《日知文集》第三卷,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2年,第14—15页。
应该说,日知先生正是在这样一个整体的和宏观的背景下展开对中西古典文明的比较研究的。不过,需要指出的是,由于古代文明的影响﹑历史资料的分布和已有的研究成果的不平衡性等方面的原因,日知先生在这本著作中没有也不可能对古代和中世纪出现的所有古代文明进行全面的比较研究,而是选取了古典西方文明系统中的古代欧洲文明(包括希腊罗马和中世纪欧洲文明)和古代中国文明作为历史比较研究的具体的和主要的对象,从两个具体的历史问题入手,通过比较研究来探讨东西方历史发展道路的统一性和多样性。下面就这两个问题分别论述。
(一)从“民主”与“专制”探讨早期古代文明发展道路的统一性和规律性
从古希腊罗马时代开始,一直到黑格尔生活的时代,在西方流行着这样一种观点,即从文明产生之初,东西方就走上了一条截然不同的政治发展道路,以希腊和罗马为代表的古代西方文明建立了民主的和共和制度,而包括古代埃及﹑古代西亚﹑古代印度和古代中国在内的古代东方文明则从一开始就建立起专制主义的君主政体。然而,事实真的是如此吗?在日知先生的中外古史比较研究中,对早期东西方文明的政治发展道路的统一性和规律性的思考占据了很大的份量,1应该说,对这个问题的思考早在1979年出版的由日知先生主编的《世界上古史纲》(上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下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均收录于林志纯:《日知文集》第二卷,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2年)中就已初见端倪,在这本改革开放后中国学者撰写的第一部世界上古史的教材中,提出了许多新的理论观点,其中,“古代文明都经历了从城邦到帝国的普遍发展道路”,“专制主义不是东方国家的特点,而是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即帝国时代的产物”等规律性认识的提出,引发了学界广泛的关注和讨论,从中也可以看出日知先生后来的很多研究和思想的雏形。正是通过对古代中国和古代希腊历史的比较研究,他用大量的和确凿的历史事实对上述的偏见进行的全面的反思和有力的驳斥。
纵观日知先生对这个问题的研究,笔者认为,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正面地论证古代的城邦政体和民主制度并不是古希腊的“专利”,而是包括古代中国在内的早期文明普遍经历的一个发展阶段,其代表性的文章包括《雅典帝国与周天下——兼论公卿执政时代》﹑《<周礼>中的邦国和国家》﹑《<春秋>经传中的“国人”——试论古代中国的原始民主制》﹑《从<春秋>“称人”之例再论亚洲古代民主政治》﹑《中西古典民主政治》﹑《孔孟书中所反映的古代中国城市国家制度》等;另一类是反面地对所谓“东方专制主义”进行反驳,从而提出包括古代中国在内的其他古代文明,在文明产生之初“并不知道专制主义为何物”,其代表性的文章包括《“东方专制主义”问题——政治学﹑历史学两千多年来的误解》﹑《亚细亚生产方式与国家》﹑《亚细亚生产方式——不成其为问题的问题》等。2以上文章均收录在《中西古典学引论》一书中,见林志纯:《日知文集》第四卷。笔者认为,这两类文章虽然选取的角度和论证的重点不同,但面对的是同一个问题,即早期文明的发展道路是否具有统一性和规律性。通过这些研究,日知先生提出了一个大胆的命题,即“城邦”和“民主”制度是人类文明早期普遍经历的一个发展阶段,所有的古代文明都经历了从小国寡民的“城邦”或“城市国家”发展成为跨地区的大“帝国”的发展道路,专制主义的君主制正是后来才发展起来的帝国时代的产物。
在《古代城邦史研究》一书,作为国内第一部集全国的各个古代文明研究的专家撰写的古代城邦史的通论著作,日知先生在该书的前言中对上述观点进行了全面的阐发:
城邦或邦是最早的政治单位……古代或古典的国家包括起初的城邦和继起的帝国……城邦是自由民、公民的集体组织,自由民、公民是城邦的主人……由于城邦自始是同人民有紧密的关系,所以城邦的政治制度就其出发点或起步而言总是民主政治的……城邦时代没有专制君主,也不知专制政治为何物……3林志纯:《日知文集》第一卷,第469—471页。
应该说,这些纲领性质的论述并不是来自于先入为主的玄想,而是建立在对各个古代文明发展道路的具体考察和研究的基础之上的,该书在寻求和归纳早期古代文明发展道路的统一性和规律性的目标上做出了有一次有益的尝试。
继《古代城邦史研究》之后,日知先生在《中西古典文明千年史》中,从文明所经历的共同的发展阶段进一步阐发了这种“一体性”的认识:
古代文明世界是一个整体,这首先表现在国家发生发展形式和文明阶段的划分上。国家与文明同其起源。人类史由氏族部落发展为国家,由野蛮进入文明,血缘关系被政治关系所代替,国家是政治单位……典型的古典时代的国家,史学上是以古希腊人所说的polis,古中国人所说的邦,今通用城邦(city-state)定名的。经过或长些或短些的历史发展时期,城邦形式的国家发展为帝国。古典时代的国家,由城邦到帝国;古典时代的文明也由城邦阶段进入帝国阶段。城邦——帝国,城邦文明阶段——帝国阶段文明,这基本上是古代文明世界普遍存在于三大地区的历史现象,为中西古典文明所共有。1林志纯:《日知文集》第三卷,第29—30页。
就政治制度而言,在从城邦到帝国的发展过程中,则普遍经历了由民主到专制的转化,日知先生通过上述的前一类文章,以古代中国和古代希腊为例,通过希腊雅康制度(archontes,即执政官制度)和中国公卿执政制度﹑希腊“公民”和中国“国人”等对比,对这一观点进行了具体的和历史的论证。当然,这一民主制度“古代西方有之,中国古代亦有之”2林志纯:《日知文集》第三卷,第443页。的看法还是引发了很多的争议。3参看宋敏:《中国古代民主政治若干问题》,《社会科学辑刊》,1982年第4期;吕绍纲:《中国古代不存在城邦制度》,《中国史研究》,1983年第4期;启良:《希腊城邦与周天下——与日知先生商榷》,《世界历史》,1991年第2期。
在这里需要指出的是,日知先生对于民主制度是否在古代文明早期具有普遍性的问题还是留有余地的,例如,在《中西古典文明千年史》的前言中,他开宗明义地写道:“这部《中西古典文明千年史》只着重论述古代文明世界的民主政治史。应当注意的是:第一,在古代文明世界,民主政治,是属于城邦阶段,帝国时代是专制政治时代,民主政治看不见了;第二,不是所有古代城邦都出现过民主政治,有的城邦就没有”。4林志纯:《日知文集》第三卷,第1页。
最后,对于古代民主制度的来源和产生的原因,日知先生也做出了自己的解释,即古代的民主制度脱胎于古代氏族社会的原始民主制度,5日知先生在《<春秋>经传中的“国人”——试论古代中国的原始民主制》(见林志纯:《日知文集》第四卷)一文指出,“所谓‘原始民主制’,指存在于氏族社会解体时期,而持续于奴隶制城邦阶段的原始民主制度,大多数是贵族政治,这是基本的情况;民主政治在有的城邦,有的时候强些,有的时候弱些,或来不及发展就夭折了。这些看法只是以古希腊﹑罗马史为根据,因为只有这些古代国家的政治制度,近代的研究比较充分些”。他认为,随着世界古代文明研究的进展,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这种脱胎于氏族社会的“原始民主制”不仅存在于古代的希腊罗马,也存在于古代南亚﹑西亚和东亚地区,当然也包括了古代中国。在《从<春秋>“称人”之例再论亚洲古代民主政治》(见了林志纯:《日知文集》第四卷)一文中,日知先生对“原始民主制”和“古典民主制”的关系做出了更为明确的说明:“原始民主制则是由氏族社会脱胎而出,由原始社会末至奴隶社会初,先后经历了氏族公社﹑农村公社和城市公社,并以不同程度的发展水平,出现于各地奴隶制城邦的时期,在这个时期,原始民主制发展成为古典时代的奴主民主制,在有的地区,例如雅典,达到古代民主制度发展的最高点和终止点……古典时代的民主,事实上即是由原始时代氏族民族﹑军事民主发展下来的城市公社和国家的民主”。而原始民主制度的普遍出现也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古代民主制度的普遍性。
综上所述,正是通过古代中国和古代希腊的早期国家和政治发展道路的比较研究,日知先生提出了古代文明早期发展道路的统一性的认识,虽然其论证的过程并非无懈可击,对某些具体问题的看法仍然值得商榷,但笔者认为,其基本的观点和研究取向还是值得肯定的,尤其是对于破除以“西方中心主义”思想为理论基础的“古代东西方政治发展道路迥异”的传统偏见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
(二)从“连续”和“断裂”看中西历史发展过程的差异性和多样性
如果说在上述“中西古典学”和“中西古典文明”的研究中,日知先生更加侧重于归纳和发掘东西方早期文明发展道路的统一性和规律性,即重点在于“求同”的话,那么在中西历史发展过程的“连续性”和“断裂性”的问题上,则更为侧重于阐发中国和西方文明的差异性,即重点在于“求异”。应该说,不论是“求同”还是“求异”,都体现出了日知先生对历史比较研究的两个基本维度的重视。因为,不论是“蔽于同而不知异”,还是“蔽于异而不知同”,都是不可取的,只有二者并重,才能充分地和正确地发挥历史比较研究的功能与作用。
在日知先生晚年的学术研究中,对脱胎于西欧封建社会的历史经验的“封建主义”(Feudalism)的概念以及西欧历史上的这一“黑暗时代”进行了全面的辨析和思考,通过对中西封建社会历史的比较研究,提出了“中国古代何以没有出现欧洲那样的黑暗时代”这一重大的历史课题。笔者认为,这个问题的提出不但可以加深对中西封建社会的认识,而且也可以推进对对中国历史的“连续性”和西方历史的“断裂性”这一发展道路上的重大差异及其产生的原因的研究。日知先生对于这个问题的阐述,只要集中在《“封建主义”问题——FEUDALISM百年来的误译》﹑1《世界历史》,1991年第6期,见林志纯:《日知文集》第四卷。《论中西古典学之现阶段》﹑2《传统文化与现代化》,1998年第3期,见林志纯:《日知文集》第一卷。《论中西古典史上的“黑暗时代”问题》﹑3《学术月刊》,1999年第1期,见林志纯:《日知文集》第一卷。《古代中国没有西方古代史上的所谓“黑暗时代”》﹑《中国古典史上未见“黑暗时代”的原因》4两文见日知:《中西古典文明千年史》,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7年,第473—482页,亦收入林志纯《日知文集》第三卷。等文章中。
在对“封建主义”一词的来源及其通过翻译进入中国的过程和中西封建社会的具体历史特点进行了全面和深入考察的基础上,日知先生指出,这个错误的翻译不仅造成了对西欧封建社会的错误认识,同时也造成了对中国封建社会的错误理解。他指出,“封建”一词早在我国的古典时代就已经出现,其原意为“封邦建国”,“有如古典欧洲希腊人﹑罗马人之殖民建国”,因而是地道的“中国土货”,而由Feudalism翻译而来的“封建主义”,“则是地地道道的洋货”,是在蛮族入侵和希腊其罗马古典文化中断之后出现的一种新的社会经济形态,因此,“古典中国未闻未知FEUDALISM,古典中国未经欧洲那一段蛮族入侵的历史,也没有欧洲中世界那样各邦分立的时期”。5参看林志纯:《日知文集》第一卷,第488—489页。不过,日知先生并不主张废弃“封建”一词而另用新词,因为即使误译,但语言还要遵守“约定俗成”原则,只是在使用时要清楚地认识到二者在内涵上的差异。见林志纯:《日知文集》第一卷,第494页。可以看出,从对“封建主义”一词的辨析中,日知先生已经提出了“中国古代何以没有经历欧洲那样的黑暗时代”的问题。对于这个问题产生的原因,在最早发表的《“封建主义”问题——FEUDALISM百年来的误译》一文中,日知先生就已经做出了初步的回答:
不过中国中世纪和起源和西欧中世纪并不完全一样,例如,西欧中世纪以入侵蛮族所建国家为起点,日耳曼(德意志)的国家起源方式与雅典、罗马平列,中世纪国家一出现就是中世纪的了。这是历史时代背景使然。中国中世纪国家,例如魏晋南北朝各国,虽然也有胡人(北方兄弟民族)立国当政,但我们的兄弟民族是久居国之边境乃至累世生活内地的人民,他们基本习惯中国传统,且或坚持实行汉化改革的,这与西欧中世纪情况不同。所以研究西方中世和中国中世,各从历史实际出发可也……6林志纯:《日知文集》第四卷,第311页。
在发表于1999年的《论中西古典史上的“黑暗时代”问题》一文中,日知先生在对这个问题的讨论上又取得了两个新的进展,第一,从欧洲古典文明和中国古典文明两大系统出发(参阅前文),把西方历史上的“黑暗时代”的现象从欧洲中世纪文明扩展到了“古代亚述和巴比伦文明的中断”和希腊的迈锡尼文明之后的有“黑暗时代”之称的荷马时代,由此来说明,在西方古典文明系统中,历史上由于外族入侵而造成的断裂现象,即“黑暗时代”不止一次地出现过;第二,对于中国古典史上未见“黑暗时代”的原因,日知先生则结合秦汉以来的历史和有关文献,做出了更为详细和具体的阐发,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1)“古中国之兄弟民族思想”。他指出:“中国民族与兄弟诸民族,自古以来,尝有争吵,乃至战争,然兄弟之关系仍始终存在也……在这种形势下,古典中国之与四邻兄弟民族,相互关系之间,不可能产生西方尤其欧洲古代那样‘黑暗时代’的局面,是很显然的……(兄弟民族)乐于承受古中国之文化,为古中国文明之一分支。中国之民亦乐于接受兄弟民族之文化”,他以赵武灵王“胡服骑射”以及汉民族之修筑长城来说明这一点。(2)“古中国有可变之礼俗,无排他之宗教”。对此,他把古代中国与希腊文明进行了对比,指出:“中国自有礼俗。然而无不可变之事物,审其时宜而已。万里长城是要筑的,胡服骑射更是要学的。不筑长城,蛮族和兄弟民族来攻,‘黑暗时代’可能随之而至,克里特·迈锡尼宫廷文化,线形文字A与B,随之而亡矣。不学胡服骑射,将永居长城之内,坐以待毙乎?”正是因为有这样的差别,与欧洲在蛮族入侵之后进入了漫长的“黑暗时代”不同,中国在所谓“五胡乱华”之后却迎来了有着光辉灿烂的文化的魏晋南北朝时代和随唐帝国。论及宗教,日知先生指出:“宗教的排他性在中世至近代现代,对于中国以外的西方世界,至今还是特别严重的问题。然而在中国,中国的民族史上对于宗教是不存在排他性所引起的这样那样宗教纠纷……从古代到中世,中国的思想界,就宗教﹑哲学的派系区别和斗争说,比起西方来,可以说是比较自由的”。因此,正是以西方文明系统多次出现明显的“断裂”和“黑暗时代”这面镜子,日知先生看到了中国历史之“连续性”的特点:“中国的文明文化由古典下来,一条线发展,只是随时穿插或夹杂入从旁来的外来文化,如印度的,欧洲的等等”。最后,他还指出,中国文明和文化的连续性并不等于数千年来没有变化。
从以上两个方面的分析可以看出,正是通过对古代中西文明的全方位﹑多角度和多层面的历史比较研究,日知先生不仅创造性地提出了“中西古典学”和“中西古典文明”的概念,而且,通过对中西方具体历史发展过程的考察,通过对二者相互的比照,认识到了东西方文明的发展既有统一性,也有多样性,可以说,人类的历史发展过程就是统一性与多样性的一种有机的结合。通过这样的研究,不仅实现了历史比较研究的功能与作用,而且从中也凸显出历史比较研究的价值和意义。
三、日知先生在历史比较研究方法运用上的两个特点
上文分别对日知先生的历史比较研究的思想和实践进行了概要性的述评,最后,笔者还想结合《文集》,就先生的历史比较研究方法在运用上的特点做出一些总结和归纳。
前文说到,纵观日知先生数十年的学术研究,虽然涉及的领域和研究的内容十分广泛,但历史比较研究的意识﹑视角和方法是贯穿始终的,对这个一以贯之的指导思想进行一些梳理﹑归纳和总结正是笔者撰写这篇札记的初衷。应该说,日知先生对这种方法的运用是比较成功的,笔者认为,其成功之处与其说是得出了很多正确的和无懈可击的结论,不如说是发现或提出了很多值得后人进一步深入探讨和研究的课题。正如刘家和先生所言,日知先生“晚年致力于中西古史比较研究的成果,为后人开启了一片新的研究领域”。2参看刘家和先生为《文集》撰写的序言,见《日知文集》第一卷,第III页。因此,就历史比较研究方法本身的运用而言,也可以从日知先生的诸多研究成果中得到很多的启发,可以帮助相关研究者在今后的历史比较研究中沿着先生的足迹前行。对此,笔者想从以下两个方面来谈一谈日知先生的历史比较方法运用上的特点。
1林志纯:《日知文集》第一卷,第530—536页。
第一,在历史比较的过程中,遵循宏观与微观﹑整体与局部﹑理论与史实的统一。
可以说,人类历史上的现象是纷繁复杂的,要对这些现象做出合理的分析和解释,一方面需要对现象本身做出近距离的和细致的观察和描述,另一方面还要具备从个别现象抽象出普遍规律的理论素养。对于历史比较研究也是如此,一方面也要尽可能全面地掌握第一手资料,始终从历史事实而不是从抽象的观念和理论出发去探讨问题,另一方面也要对个别历史事实背后的意义进行解释,这就需要对历史发展过程有一种宏观的把握和理论上的认知。可以说,在日知先生所进行历史比较研究的实践过程中,很多地方都体现出宏观与微观﹑整体与局部﹑理论与史实的统一。对此,王敦书先生有很精当的概括,他说:“林先生治学有两大特点:一个是掌握马克思主义,具有宏观的眼光,运用唯物史观来建构不同于西方学者的世界上古史体系;另一个是高度重视原始文献和第一手资料,尽力收集新资料,吸收新成果,来研究历史,发表自己的见解”。1参看王敦书:《林志纯和中国世界古代史学科的建设与发展》,《世界历史》,2000年第2期。下面仅举一些例子加以说明。
在日知先生晚年的集大成之作《中西古典文明千年史》第一篇“绪论”部分,他就开宗明义地提出了古代文明三大地区与中西古典文明两大系统的理论,这一理论的提出正是基于人类文明的“整体性”的认识:
大约公元前三千年代以来,在此人类史上最早产生文明和国家的地带,古典文明的历史潮流,尽管发生的历史时间不一,地理气候具体条件不一,但作为古典文明和国家,一切有人居之所,始终息息相关,相互促进,形成古代文明的一个整体,完成其创造性的历史任务。人类文明在此起源了,此即古典文明世界,亦称古代文明世界。2林志纯:《日知文集》第三卷,第8页。
这种文明的“整体性”不仅体现在空间上的接近(欧亚大陆的连续性),也表现在时间上的统一上(即从城邦到帝国的演进和发展)。在这一宏大的叙事之后,日知先生就从古代中国和西方古典文明的历史发展过程出发,通过一个个小的专题,对上述的“整体性”和“统一性”做出了具体的说明和论证。可以说,从早期的《古代城邦史研究》起,日知先生的历史比较研究都遵循了这种宏观与微观的统一。一方面,宏观的和总体的认识是建立在微观的和具体的历史过程的研究的基础上,另一方面,具体的和历史的研究也不是完全孤立的,而是为了证明或服务于一个整体性的认识。
就比较研究的内容而言,在日知先生的论著中,既可以看到不少宏观的和整体性的比较,但更多的则是十分具体的历史比较研究,当中既有两种政治制度3如希腊“执政官制度”与中国“公卿执政制度”的比较,见《雅典帝国与周天下——兼论公卿执政时代》(林志纯:《日知文集》第四卷)。和两类社会人群之间4如希腊“公民”与中国“国人”之间的比较,见《<春秋>经传中的“国人”——试论古代中国的原始民主制》(林志纯:《日知文集》第四卷)。的比较,也有两个历史人物5如希罗多德与司马迁比较,见《希罗多德与司马迁》写作提纲(林志纯:《日知文集》第五卷,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2年)。或习俗6如司马迁和希罗多德都曾经记载过的亚欧北方民族的用敌人头颅作饮器的风俗之间的比较,见《用敌人头颅作饮器——司马迁﹑希罗多德同记亚欧北方民族一习俗》(林志纯:《日知文集》第一卷)。的比较,甚至从对一个词汇的理解,7日知先生有很多篇文章都旨在讨论某个关键词汇的内涵和意义,如《文集》第一卷中的《“史前”一词可否使用?》,《怎样理解马克思说的“亚细亚生产方式”?》;《文集》第四卷中的《从<春秋>“称人”之例再论亚洲古代民主政治》,《释共和——共伯[和]可以休矣》。一条资料的认识,8如《文集》第一卷中的《<论语>“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解》,《文集》第四卷中的《<水经•洧水注>引<竹书纪年>一条千年来误读悬案》。都会成为一篇文章的考察对象和切入点。
同时,还可以看到,日知先生不仅关注于具体史实的研究和探讨,而且也一直没有忽视对理论的学习和思考,尤其是也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肯于下功夫钻研,不仅写过很多有关的论文,做过经典著作的翻译,9日知先生曾经撰写过很多篇关于马克思和恩格斯论古代社会的论文,并亲自翻译了马克思的《资本主义生产以前各形态》(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年)一文。在他的最后一部专著《中西古典文明千年史》一书前言之后,还附上了一篇名为《学习恩格斯1884年的一篇遗稿》的短文。还力图把这些理论与具体的历史研究结合起来,限于篇幅,在这里不再举例赘述了。
第二,在历史的比较研究中,日知先生始终对历史资料的掌握有着非常高的要求,始终坚持着从原文出发,并力图了解和掌握最新的考古资料﹑文献资料和研究成果。
对于中西古代文明这个覆盖范围极广﹑资料难于掌握﹑语言工具要求极高的艰深的研究领域,要进行历史比较研究谈何容易,需要在古今语言的学习和资料的研读上付出更多的努力,再加上时空的遥远和文化上的隔阂,需要坐多年的冷板凳,出成果十分不易,仅仅学习和掌握某一种古代语言,深入进行某一个古代文明的研究,可能就要耗费研究者十几年甚至数十年的精力。但日知先生不畏艰难,靠着满腔的热情﹑执着的追求﹑较好的天分和不懈的刻苦努力,自学了古埃及象形文字﹑古代西亚楔形文字及古代希腊文,掌握了拉丁文及俄文﹑英文﹑德文等多种古今外文,涉及的研究领域也几乎涵盖了所有的古代文明,再加上对中国古代语言文字﹑文献﹑资料和历史的谙熟,1日知先生早年曾经治中国古史,后来,由于工作需要才转到世界古代史研究领域的。对此,先生的弟子吴宇虹在《林志纯先生和我的亚述学研究》一文中做了专门的介绍,他指出,“他自幼熟读国学经典,中国史研究功底深厚”,1950年刚到东北师大任教的时候应聘的是中国史教师岗位,“来校后,由于历史系缺少英语和俄语好的教师,已步入不惑之年的他服从学校安排,开始专业大转向,从中国史教学研究转为世界古代史及中西古典文明比较的教学研究工作”。吴老师还介绍说,在中国史领域,他不仅发表了一些有影响的成果,还是“魏晋封建论”的“主要领军学者之一”。使他得以游刃有余地游走于各个古代文明之间,从原始文献﹑最新的考古资料和研究成果出发,提出自己的观点和认识。从日知先生的这些努力和所取得的成就可以看出,他对做好历史比较研究所要进行的这些前期准备工作是十分重视的。试想如果没有掌握这些语言工具,只是借助于某一种现代语言的翻译,或从已有专著中提供的二手资料出发,是不可能对该古代文明有深入的理解和全面的认识的。与此同时,要使比较研究得以深入,就需要对作为比较对象的双方都有精深的理解和研究,为此,掌握比较对象双方的语言也就成为了基本的和不可或缺的前提条件。在谈到日知先生对外国语言的学习和原文资料的重视的时候,刘家和先生这样回忆到:
在他的视野中,不仅中西历史本身的研究是可以相通的,而且其间的研究方法和路数也是可以相通的。他常对我们说:“要用治中国史的办法治外国史。”最初时没有太留意其内在的含义,后来看到他自己的研究路数,才知道,那就是不能再把外国史的研究建立在二、三手材料的基础上了;现在我们治外国史,要像治中国史一样,扎根于原始资料,而视野必须达到学术前沿。这也就是顾炎武所主张的“取铜于山”制作精品的治学路数。这当然是很艰难的工作,但是在林先生看来,必须下定决心,一步一步地做下去。2参看刘家和:《为我学世界古代史引路的老师——怀念日知林先生》,《古代文明》,2008年第2期。
总之,历史比较研究方法本身的成功运用是需要一些必要的前提条件的,日知先生已经用自己的历史比较研究的实践为相关研究者做出了一个榜样。作为一个对历史的比较研究有兴趣的初学者,虽然自己可能永远也达不到这个高度,但仍不失为一个今后努力的目标和方向。文章的最后,笔者想借用司马迁在《史记·孔子世家》中的那句话作为结束,即“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以此表达对日知先生的敬意,并与致力于历史比较研究的朋友们共勉。
[作者王大庆(1969年—),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北京,100872]
(责任编辑:张强)
【古代地中海文明】
[收稿日期:2015年11月26日]
DOI:10.16758/j.cnki.1004-9371.2016.0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