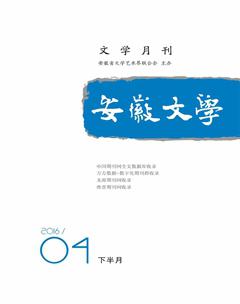借古衣冠发抒块垒
陈朱演
摘 要:《谒帅府》是桂馥暮年远仕边土,饱受官场的冷眼和世故之后,借古人之口,抒发内心不平之气的佳作,在《后四声猿序》中最具深度。同时,剧中也反映出清代知识分子那种委曲求全、丧失文人气节的普遍心态,这也是时代造成的悲哀。
关键词:谒帅府 桂馥 抒发块垒 创作心态
在明代戏曲的发展史上,杂剧和传奇此消彼长,但明杂剧已经远远不如元杂剧那样光彩夺目,堪称上品者屈指可数。在这些为数不多的佳作当中,徐渭的《四声猿》无疑是出众的。汤显祖曾经评价四声猿:“《四声猿》乃词坛飞将,辄为之唱演数遍。安得生致文长,自拔其舌。”①而到了清代,出现了一部类似作品,这就是桂馥的《后四声猿》。清人王定柱在其所撰的《后四声猿序》中认为其可以“与青藤争霸风雅”。通观二剧,无疑都是作者借古事抒发自己心怀之作。关于《四声猿》的研究较为翔实。而与徐渭所身处的思想相对宽松的晚明文艺复兴的社会环境不同,产生于清代程朱理学盛行的文化高压中的《后四声猿》,更值得我们去探究。《谒帅府》一则尤为精彩,苏轼作为被贬之员进谒帅府的艰难及其深痛的羞辱感,便是剧作者桂馥老而远仕边土之感的真实反映。对于此则,郑振铎先生给予了极高评价:“谒帅府一剧,为僚吏吐尽不平之气,足补费臣之憾矣。②
《谒帅府》是四则当中最短的一篇,只有寥寥数百字,但在艺术上丝毫不逊色于《放杨枝》 、《题园壁》 、《投溷中》三篇。作者通过自己的匠心,将人物的性格神态和心境刻画地准确逼真,堪称神来之笔。
在该剧中,苏东坡的情感经历了一个变化过程,既从满腔怒火到最后在山水间怡然自得。这也是作者在为自己创造一个逃离现实的精神家园。本则体现了清代知识分子在污浊的官场之中,为了自己的身家性命,即使深受委屈,却仍然敢怒而不敢言的心态,这一心态也与当时的文化背景有关。满清贵族入关之后,对于汉族的文人采取了打压加笼络的双重政策。一方面在康熙和乾隆年间,大开“博学鸿儒”科,让一些知识分子成为御用文人,安抚其怀才不遇的情绪。另一个方面,大兴文字狱,又借修订《四库全书》之际焚毁了大量不利于其统治的书籍。在这种压力下,文人不敢谈论时政,埋首学术,对于上峰唯唯诺诺而已,已经丧失了那种“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风骨。这也变相地刺激了清代考据学的昌盛。
作者桂馥本人就是有名的学者,为清代“说文”四大家之一,其严谨的治学思想在《谒帅府》中也有明显的体现,即小引中点明了本剧的渊源,提及的苏东坡游东湖诗,都是他注重考据的严谨治学风格的体现。作者一生的仕途仍然颠沛流离。早年是平静的居家读书生活。1794年54岁时,桂馥才得以中举,次年成进士。但却要远赴几千里外的云南任小小知县,其间辛酸悲苦,可想而知。其在云南十年,颇有政绩,学术上也是黄金期,但是赴云南时其已经60岁,这种朝拜长官,夕对账簿的官场生活,对其而言无疑是枷锁,期间辛酸可想而知,其写下本剧也是很自然地事。
桂馥把自身的经历融入古人形象塑造,抒发古今同悲的情感。作者的身上有苏东坡的影子,故而与他感同身受,借他们之口来写自己之情,这一点清代人已经看得很清楚,王定柱就说过:“先生才如长吉,望如东坡,齿发衰白如香山,意落落不自得,乃取三君轶事,引宫安节,吐臆抒感。”③1025《后四声猿》是作者晚年之作,体现了其对于屈沉下僚的知识分子的普遍同情,也借古人之口,在高压的文化环境中抒发自己胸中的愤懑之气。
《谒帅府》写不善谄媚的苏轼不得谒见府帅的愤怒之情。这一则的小引值得注意:
苏子瞻为凤翔判官,陈希谅为府,以属礼待之。入谒或不得见。子瞻《客位假寐》诗云:“同僚不解事,愠色见髯须。虽无性命忧,且复忍须臾。又有东湖诗,皆为希亮作。其屈沉下僚,抑郁不平之气,微露于游览山水之际。今读其诗,觉胸中块垒竟日不消,只可付之铁绰板耳。”④
桂馥的性格和苏轼相似,都是刚介耿直之人。其这种被上官怠慢的遭遇,作者自己也有亲身经历,其《晚学集》卷六的《答友人书》一则就论述了自己的遭遇:
“……不谒都宪,触怒获罪……今督宪既不能用我,又不能杀我,但挫折我耳。”⑤
“挫折我耳”深深刻画出了那种羁旅官场,进退维谷的复杂心态。本则满纸的牢骚和不平之气,作者写作的动机不言而喻,是借用苏轼之口来释满腹的委屈。故而本则写得格外传神,词语铿锵有力,如写谒见上官时那种小心翼翼,如履薄冰的表现:
【六么令】低眉就下,仰面攀高,强颜欢笑,伤心折腰。
这四句一韵到底,两两相对,短短十二个字,把那种低层下僚的如同娼妓一样强颜欢笑,讨好上位的辛酸心理刻画得淋漓尽致,不是亲身经历,焉能至此。
又如写官场黑白颠倒,家丁狗仗人势,对于前来谒见苏轼的敲诈盘剥:
【寄生草】公门任意胡颠倒,称呼信口加名号。门包掯勒贪心要,俺呵,垂头休说挂冠陶,温言羡慕香山老。
最后的两句也透露出那个时代的普遍心态,面对着种种人格的屈辱,这些饱读圣贤书的官员为了自己的生计已经丧失了陶渊明那种不为五斗米而折腰的气节。香山老指的是白居易,晚年的白居易在洛阳过着闲适的致仕生活。剧中苏轼羡慕或者说寄希望的是白居易那种在致仕之后,以优厚的待遇安享晚年的生活,从而让自己受的屈辱得到补偿。这也是为什么众多的官员蝇营狗苟,混迹于官场的根本原因,可是又有多少人能够真正做到呢。这无疑是桂馥对于现实的辛辣讽刺,道出了那个时代广大读书人的悲哀,也道出了自己的无奈。
剧中苏轼的情感发展也符合传统知识分子的性格,显得真实可信。
起先在面对门人放肆嚣张后,苏轼作为文人的气节显露出来:
(生起怒指介)竟有这等放肆的门官。
而可悲的是,在发怒之后,考虑到自己的现实,为了保住自己头上的乌纱,东坡居士还要自己安慰自己:
还是俺的量窄。何苦与他作对?正是:虽无性命忧。且复忍须臾。
要如何排解自己的苦闷呢,作者把东坡先生巧妙地引向了东湖的优美风光之中,让飞泉瀑布,鸟兽虫鱼的纯真可爱来排解东坡内心的愁苦。正如《赤壁赋》所说:唯江山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而吾与子之所共适。寄情山水以放任自己,这是中国文人传统的心理。而在描写东湖景致之时,作者仍不忘对于官场的黑暗加以鞭挞:
你看,泉源从高来,随波走涵涵,东去触重皋,尽为湖所贪,这湖好不廉也。
在作者的笔下,连清澈的湖水都是贪婪的,要把四周美好的景色给囊括住。在湖光山色之中,苏轼的心情得以暂时归复平静,放下了名利场中的是是非非,安心饱览秀美的景色,写诗咏怀。剧中东坡所作诗无疑是其心态最真实的写照,也是作者暮年远仕边土的同感:
但见苍石螭 ,开口吐甘清,借汝腹中过,胡为目眈眈。
余今正疏懒,官长幸见涵。不辞日再游,行恐岁满三,暮归仍倒栽,钟鼓已涵黯。
作者在尊重历史的基础上,匠心独运。为两首诗的由来设置了一个背景,使其服务于自己一吐胸中块垒的需要,这便是作者的高明之处。也可见桂馥虽为学者,却并不迂腐。诗中体现东坡对于那些身处高位的庸碌之徒的鄙视,作为文人的旷达心态。这些都是作者所向往却为时代所禁止的。同为遭受上峰的冷眼,作者只能唯唯诺诺,所以其刻画了一个在山水之间忘却是非,挥毫泼墨的东坡居士形象,作为对于自己压抑心灵的一种精神慰藉了。
然而从结尾的字里行间,我们仍可以品味到苏轼的怒气未消,胸中满是怀才不遇的愤懑:
【后庭花】恼来忍气消,愁来借酒浇,宪体威仪重,衙官屈宋高。
所谓的放任山水,吟咏性情的高雅在这一刻被揭穿了,这时的苏轼更多的是一种无可奈何,只得借酒浇愁从而获得一时的解脱,可是酒醒之后仍然免不了官场的羁旅之役,东坡居士尚且不得不不如此,生活在所谓“盛世”中的作者和一大批读书人又当如何,一切不言而喻了。
作者把满腹的牢骚和哀怨寄托于看似对于古人轶事的追忆之中,该剧的题目也包含着一种极度的哀伤,王定柱曾点明:“‘巫山三峡巫峡长,猿啼三声泪沾裳。况四声耶!况又后四声耶!”③1026诚为不虚。
该剧在演唱和选曲方面也较有特色,保留了元杂剧的固有体制。在《后四声猿》中有多种的演唱方式,如合唱、对唱等,如《题园壁》的尾声采用生旦对唱的形式:
【小生】燕燕双飞喜病栖,【旦】故巢已毁又衔泥。【小生】春深最爱讲雏好,【旦】王谢堂前旧路迷。
小生唱出美好的憧憬,而旦角则点出现实的悲凉,起到先扬后抑的作用,让人感叹此事古难全。
而相对于其他三剧,《谒帅府》中则一直是主角的独唱,其余人物仅有舞台动作而已。这一方面体现出元杂剧固有体制对于桂馥创作的影响,另一方面也是为了表达作者创作意图的需要。这种一人独唱便于主角的倾诉,强化人物的性格和遭遇。而在选曲上,则是采用北宫调曲牌,铿锵慷慨,这与苏轼那种发泄满腔委屈的情绪相吻合,做到了曲调和曲辞的完美统一。又吸收了散曲的特点,莲芳居士指出:“【翠裙服】一套,系用关汉卿《晓来雨过》散曲。”⑥1028一开头用散曲特有的赋的笔法生动刻画高官那种讲排场,摆架子,贤愚不分的样貌,为下文苏轼的遭遇埋下伏笔,语言口语化、俚俗化,曲意明朗活泼、穷行尽相。 《谒帅府》谱写了文人的一曲悲歌,抒发了古往今来能人志士怀才不遇,饱尝宦海险恶的艰辛。同时,它也体现出杂剧开始走向文人案头化的趋势,演出不再作为其唯一目的,更多作者将其变为成为感叹身世,抒写愁苦的载体。正如莲芳居士所说,桂馥此作,“得毋贾长沙续骚之意耶?”
注释
① 徐渭.四声猿序言[A]//四声猿[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4.
② 蔡毅.中国古典戏曲序跋汇编[M].山东:齐鲁书社,1989:1027
③ 王定柱,撰.后四声猿序[A]//中国古典戏曲序跋汇编[M].山东:齐鲁书社,1989:1025.
④ 郑振铎.《清代杂剧选》初集[M].山东:齐鲁书社,1989::263.
⑤ 桂馥.晚学集[A]//续修四库全书[M].第1458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698.
⑥ 怜芳居士.后四声猿跋[A]//中国古典戏曲序跋汇编[M].19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