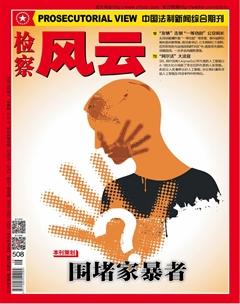从“恐二代”的选择中,我们读懂了什么
袁石
“能否引导宗教在理性温和中发展,不偏离人本、关爱的本源,不陷入激进主义的漩涡,这也依旧是不少国家所需直面的事情。”
闲暇,翻阅了TED系列之《我父亲是恐怖分子》,该书由扎克·易卜拉欣,杰夫·盖尔斯所著,书中并没有太多的理论式的剖析与说教,更多地是扎克将自己的成长故事娓娓道来,简单的故事背后却侧面展示了其父塞伊德·诺塞尔成为恐怖分子的历程,以及扎克与恐怖主义思想决裂的坚定抉择。
人类最古老的三个学科,神学、医学和法学,基本起点都源自于人本。神学让人心灵得到净化,精神得以皈依;医学为人治疗疾病痛苦,维护人的身体健康;法学则维护人类公平正义,让社会有序发展。但当三者走向极端,却又每每成为阻碍文明发展的绊脚石,生化武器令人色变,恐怖主义至今如幽灵般困扰我们,而恶法依旧在一些地区为残暴代言。
巴黎恐怖袭击的枪声尚未远去,IS依旧还在残暴肆虐,倘若以为这与我们遥不可及,那想必已然遗忘了昆明火车站发生过的事件。换而言之,恐怖主义的阴影不但并未远去,相反呈全球蔓延之势,由此从亲历者的角度去看待极端化过程具有特别的解读意义。毕竟,当我们视恐怖分子为异类的同时,他们亦将我们视为可悲的异教徒,彼此陷入妖魔化视角的背后,扎克事实上成为客观了解与衔接的中立第三人。
原本风趣、慈爱而温暖的一名父亲,由于工作的遭遇而日益自闭,转而寻求精神上的解脱,但不幸的是,阿富汗战争逃离出来的圣战煽动者成为了他极端化的导师。他开始日益沉浸在极端化的思想中而无法自拔,敌对、仇视已经成为其人生的主题词。在极端思想之下,他将自己催眠幻想成安拉的泄愤工具,并且将之付诸实施——先是刺杀了犹太捍卫联盟的创办者梅厄·卡赫纳,尔后在监狱中策划了震惊世界的世贸中心爆炸案。
“仇恨并非人与生俱来的本能,而是一场精心编制的谎言。我的父亲正是这一谎言的忠实信徒,而他曾一度想让我也陷入这一谎言中。”扎克的话用理论解读就是“文化暴力”,即选择性放大并有目的性地诠释文化中的某一方面,并用之为直接性或结构性的暴力进行辩护。
原教旨主义者以传教的名义,刻意歪曲解读经书中的部分内容,极度丑化异教徒的形象、夸大异教危害,渲染排斥、报复、消灭异教的宗教义务,同时通过虚构殉道者愿景的许诺,美化暴力并为之寻找宗教角度的合法化、正当化理由,进而鼓吹直接性暴力或结构性暴力。毫无疑问,这已然背离了神学的本意,即已泯灭了人性,忽略了人本,不仅无法让人得到心灵的宁静,反而让人充满着执念、怨念和痴念,魔念驱动之下的行径已不足以用离经叛道来形容。
但站在封建时代的角度,为获得更多的信众,宗教经书文本中难免出现彼此排斥的情况,对信仰与否的区别对待,如来世的许诺也好、地狱的诅咒也罢,更多是传教者的一种宣传方式,这些宣传方式也渐渐随着宗教改革、人类文明的进步,尤其是自然科学的进步和人格神的否定而得以扬弃。
但我们依旧无法跳跃传道者这一链条,即便在以宽容、忍让著称的中国人面前,也难免出现宗教间互撕名牌的局面。犹记得两个大妈争吵,一者指责对方所信的佛教只会要求捐赠、购买放生,而她所信的基督教则分文不取;另一者则指责对方所信的基督教并非本土,而且只会诅咒不信者下地狱,丝毫没有宽容之心……
这虽然只是一个宗教冲突的缩影,然而这种口仗却是个极好的办法。一则,冲突归根还停留在宗教探讨的阶段,也只是对各自传道方式方法的争论,本身也有利于反思;二则正如德沃金所著的《没有上帝的宗教》所言,“宗教战争如同癌症一样,是对人类的诅咒,在世界各地,人们互相残杀,因为他们憎恨对方的神”,由此这种大妈式的口角探讨,实则要比原教旨主义者的彼此搏杀反而显得理性得多。
然而,我们不得不直视的是,在不少国家,狂热的信徒拥有着强大的政治势力,即使在美国,也没有一个自称无神论者能够在美国当选重要职位。能否引导宗教在理性温和中发展,不偏离人本、关爱的本源,不陷入激进主义的漩涡,这也依旧是不少国家所需直面的事情。而这,我们显然也不能忽略前车之鉴,不仅如扎克所说,是个人关于选择的故事,也应该是一类关于宽容与冲突处理的社会文化。
栏目主持人:成韵 chengyunpipi@126.com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去极端化条例》相关内容评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