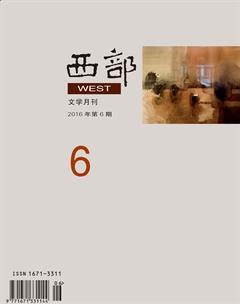来历不明的生活
王爱
一
公交车上,一个人唤我的乳名,语气亲热、自然、熟络,像一个相处多年的邻居。然而声音陌生,进入我眼睛的那张脸更是陌生。我仓促应答,内心一片茫然。她下车后,我开始在一堆日常细节中反复翻捡,却毫无所获。我找不到有效信息来证明她的存在,她跟我之间没有任何隐秘关联。到底哪个环节出现了错误,整整一天,这件事困扰着我,来历不明这个词让我心烦意乱。
我一直喜欢在木房子里听雨。温凉的唇面反复啄洗青色的瓦片,蜿蜒滴落,像透明的泪滴,总要被多情的屋檐眷恋挽留。雨水伤心徘徊、百转千回后才拖着长长的身线跃向地面,落入阳沟,发出清澈的声音。这种声音无限拉长节奏,缓慢而有韵味。好像这种滴落是一种时间和空间的延展,是一种无休止的轮回。它穿透层层烟雾,从远古时代过来,直接撞击我的心灵。幼时的我,每每由雨水激越无数遐想。我对木房子感到好奇,对我的祖先感到好奇——最初为何选择这个地方,而不是生活在别处?我们究竟传承了多少代?我的先祖叫什么名字?娶了什么样的妻子?他经历了多少磨难?除了最初的啼哭,他是否还流过泪?他的一生是怎样的一生?
在湘西小溪沟,人是没法远望的。他无法望见自己的来处,也无法望见自己的去处。无论从哪个角度望出去,他看见的只能是山。山是刚性的,大大小小,连绵不绝,从四面八方向人逼近。所幸有水,有水就有路,柔柔的水一直牵引着人寻找出口。水不会停住脚步,山也不会。山走累了,到这里收拢翅膀,歇歇脚,于是,满山的风景都在后面歇下来了。跟着山一起吐气呼吸,慢慢形成了小溪沟的万千气象。有些生灵就存了偷懒的心思,停下来就不想再挪动了,开始一心一意安家落户,它们觉得这样也非常好。
最后,山歇息够了继续赶路,延展成群山。留下我的祖先,鲜活活地过到现在。但我们没有家谱,这使我对自己的家族一无所知。关于小溪沟王家寨的由来,老人们说法不一,至今无据可考。我曾作了无数神妙美丽的猜想:湘西的群山是不是神灵故意挖出的陷阱?许多年前,我的祖先把他的全副家当打包成一粒雪白的“蛋粒”,然后抱在怀中一步步朝前跋涉。在深渊面前黯然止步,在林壑面前低头绕道,慢慢把“蛋粒”推进深坑,把家放下,开花落子,繁衍生息。从此以后,我的家族镶嵌在水井湾里,像谜一样种在大地深处。
不管我作何种猜想,都无法抵达真相。王家寨里,谁都知道,我的祖母是一个不幸早夭的妇人。她的死是一个谜,伴着许多诡异的传说。其中一种说法是因为爷爷无意中触犯了神灵,祖母因此受到诅咒,在梦中被一只大虫抓伤,受惊吓而死。她生了三个儿子,她死后,祖父缠绵病榻几年后逝去,大伯、二伯和父亲无所依恃,艰辛成长。后来,三兄弟各自成家立业。大伯身为长子,住在祖父留下的老屋里。二伯另开门户,搬到他处。父亲则在老屋下大水井前那一丘田里站稳了脚跟。
我们住在水井湾。它因房子后面那一口大水井而得名。我一直认为,这是小溪沟王家寨最美丽的地方。三十多年前,还是一丘稻田。住在老屋里的人习惯了水井湾的静默永恒,从不觉得它美,但它的确是美的。这种美,只有寨子里古老的时间知晓。大地上流泻闪烁的光阴,只要在井口里卧伏的碧水上稍作停留,便会被它羁住翅膀,圈住脚步,再也无法动弹。多年来,所有的时光走到水井湾时就这样全被截住了。田里的稻子割了一茬又一茬,鸟雀们停留了一季又一季。为了迎娶母亲,全生产队的人帮着父亲填土、搭脚、伐木。磨刀霍霍中,水井湾左边的青橄林,右边的几十棵椿木树,对面满山坡的枞树林以及后面山上的大片楠竹林,寨子上空的鸟雀、云朵、空气和风,一起见证了房子的出生。它在这个植物丰茂、雨水丰沛的地方出生。我喜欢用“出生”来叙述它,只有这个温情的词能界定生命的起始、成长和死亡。到现在,它刚好满三十五岁,被六月里的一场大火化为灰烬。
房子没了,别人都说,那是有征兆的。年初的时候,父亲去祖先墓地烧香拜祭,发现坟头那棵柏树好端端地枯萎了,父亲赶紧补种了一排小松树。但房子还是在夏天里走失了,被这场早已预示的灾难勾起惊恐哀愁的除了我们,还有水井湾后面的幺奶奶。
幺奶奶家的祖坟前长有几棵高大的柏树,浓荫密盖。只是坟周边的土地,几经变动,最后划分在别人名下。土地主人二姐热爱侍弄庄稼,是寨子里最勤劳能干的妇人。她家的每一块土地都被她打理得平整,每一处土坎边角都薅得精光,一根杂草都没有。照在土地里的阳光都是满满的,她种的阳春长势最好。但二姐家的地,被幺奶奶家祖坟上的几棵柏树遮了大半的光阴。那些柏树不知长了多少岁月,高大的枝桠撑起了一把巨伞,土地里的大半时光就被这古老的先知吸收殆尽。在一个日头旺旺的日子里,二姐抱来秸秆柴禾,把粗大的树根团团捆住,然后点火焚烧。火烧了好几天,二姐不断添柴加火,活活将几棵古树烧得枯黄。树烧死了,土地里的光阴又美了起来,二姐种的阳春更加值得炫耀了。但这场大火把幺奶奶的心都烧碎了,她坐在墓碑前大哭了一天。
二
幺奶奶原先是个得势不饶人的强悍妇人,邻里口碑并不好。谁也不曾想到,德富爷爷在给人家盖房子的时候会从楼顶摔下去,又刚好把脑袋磕在一块大石板上。幺奶奶变成寡妇后,遍尝人世间的蚀骨冷漠,气焰沉寂下来,那些往日受过她欺压的人现在反过来欺压她。这次二姐问也不问,直接烧了她家祖坟上的柏树,把幺奶奶的天都烧塌了。动祖坟是大忌,要是一般人家,早就扯了天皮。幺奶奶不敢吭声,只敢私下找人哭诉,在家怄了几天气,还是不敢吭声。
小溪沟王家寨是周边唯一没有外姓掺杂居住的小村寨,我们这支王姓家族跟周围所有姓王的人都不同字辈。没有族谱,让生活在小溪沟的王家人多年来一直感到悲戚和惶恐,不知道究竟如何追溯自己的过去,如何验证自己的生活。在少数民族聚集的地方,我们是从外地迁徙来的汉人,在此生活通婚,才变成了土家族。有人推测我们是由太原王氏迁徙山东半岛,再由琅琊祖移至衡阳。但渔溪王氏一族如何让自己的子孙分流到湘西小溪沟王家寨来的,无人知晓。
多年来我们远离外界,一直活得很孤独。我曾反复央求别人讲述汉人祖先的事情。没有人能说得清楚,因为长辈们都早逝。奶奶的死或许是唯一的传说,这让我津津乐道,热衷于在文字里反复渲染。我十几岁时,同族哥哥有到衡阳谋生的,有一年回家过年带回来一个让所有人宽心的消息。说在那里遇到了跟我们同字辈的王姓,还是一个大家族,还说那边的亲戚要到小溪沟来认亲。这让全寨人喜气洋洋,辈分最老的太公公在老屋坪里敲着青橄木拐杖,当着全寨人,庄严地宣布,要为那场遥远的相认,安排一次隆重的接待。只是这么多年过去了,小溪沟王家几位上年纪的长辈又逝去了几个,那根一直跟随着太公公的拐杖,埋在百家树里都快要发新芽了,我们还是没有等到来认亲的人。
四年前,小侄儿出生。年轻人认为用家族字辈来命名并不好听,现代人的名字应该时髦一点、个性一点。父亲则反对胡乱取名,他认为侄儿是家中长孙,取名要按照祖先的规矩来办。父亲害怕王氏一族的字辈从我们这一代没落。其实,到小侄儿下一代,我们已经不知道该用什么字辈来取名了。这是一件令人悲伤的事情,古老的传承到这一辈差不多要中断了。王家的字辈往下不知道如何走向,唯一让我们感到慰藉的是可以往上回溯好几辈。不是因为口口相传的记忆,而是以墓碑上的刻字为证。那些埋在土地里的祖先,这是他们曾经存在的唯一凭证。经由墓碑上的蛛丝马迹,我们抚摸那些永不枯烂的名字,借此找到血脉之间的神秘通道。
王家寨一直生活着一群来历不明的人。一栋房子的存在,使我看清了自己的来处,但房子未必能知道自己的来处。小时候,我曾缠着父亲,要他告诉我,这栋全寨人一起建成的房子,它的骨骼和血肉,它满身的芬芳,都分别来自于哪座山。公家湾、上脚湾、下脚湾、里沙坡、对门沟、老屋场……每一座山都有一个名字,每个名字里都长着数不清的枞树。一栋房子虽然在他们手里出生,却没有谁能说得清楚一栋房子的来历。那些适合建成房子的树木被人们从山里面一棵棵寻出、刨根、剔桠。淌着白色黏糊的汁液,光溜溜地摆放一坪,面目模糊,谁还能明白无误地指出它们到底来自哪一座山?粗壮而直的做了房梁支柱,其余的做成木板隔壁。人们把一根剥了皮的木头架放在高高的木马上,把薄利的锯齿喂进木头身子。一人端起锯子的一头,来回拉锯。随着“沙沙”的酣醉声,锯末纷纷扬落,一根木头不到半天功夫就成了厚薄均匀的木板。那些树死了,房子活了。在它们汁液浓稠的胸腔里,一定还有没来得及做完的梦。一个充满了春天气息的梦,被永久封存在还未干涸的木房子里。山野林木的芬芳没有随着季节枯死,那是为回归做好的铺垫。它们的记忆在时间里长久埋伏,等待在最好的时机里复活燃烧。
三
每年夏天,五颜六色、大大小小的虫豸就从周围的草木上纷纷跌落,奋不顾身地朝这栋新房子里爬。我家周围立刻呈现出秩序井然、色彩缤纷的虫路。年幼的我,每天唯一的任务,就是搬个小凳子,蹲守在虫豸最多的路口,手拿大石块,阻断虫豸们的去路。在这漫长的寂寞无助的日子里,陪伴我的,是一个八十多岁的妇人。她的辈分比我祖母还大,我们都叫她湾湾太太。
我问湾湾太太,虫豸为什么一定要往房子里面爬呢?她说,那是因为你家的房子感到害怕哩。它太年轻了,那些木头被你的父辈找寻了来,做成它的骨骼。它们全都失去了记忆,不知道自己到底出自哪个山头,当然会感到害怕。一感到害怕,它就会散发出气味,来吸引那些曾经在它们身上安家的虫豸,借此找回自己前世的记忆。房子看不见自己的来处,虫豸也一样。它们也是在寻找,这都跟人一样,人也在寻找。房子害怕自己来历不明,等到你父母把日子过踏实了,房子有血有肉不再空空荡荡,渐渐变得笃实沉静,它就不会害怕了。我们成了它的来历,人也就不会害怕了。湾湾太太说到这里时,就显得特别孤独。她把一切都看透了,可她却看不见自己的来处。几岁时,她被土匪劫到王家寨里,当了人家的童养媳。年轻时死了丈夫,两个女儿远嫁,唯一的儿子脾气暴戾。湾湾太太终年独住一处,她是一个没有来历的女人。
世界上的事情,都是有来历的,湾湾太太一直这么强调。我们有祖坟记录过往,也有柏树见证未来。就像在我们眼里,家是清晰可辨的,父母亲人是温暖可依靠的。我们在房子里出生、上学、工作、活着。一切都有迹可循,这是一条简洁明了的线条,线头和线尾都一目了然,没有任何悬念。一个人,除了来历,还有什么能更有力地证明他曾经存在过?湾湾太太是一个典型的湘西土家族女人,黑丝帕牢牢包住头发,经年不拆,穿一双自做的布鞋,脚上长长的裹脚布也是经年不拆。每当太阳光绕过水井湾后那一片翠竹,把金子全都撒在房子周围的椿木树上时,所有人都出门干活去了,湾湾太太就拄着拐杖从房子右边出现了。只要看到光影在青石板上轻轻一顿,我就知道她来了。一身黑衣,脸上的皱纹像椿树上的枯皮,层层叠叠地皲裂着,她的样子比寨子里任何一件事物都要显得古老,古老得就像从那口幽深的水井中走出来一样。湾湾太太是寨子里的活神仙,没有她不知道来历的事。寨子里一大半年轻人都是她看着出生的,几乎全部的媳妇都是她应允着娶进门来的。寨子里每一个人,每一个家庭,每一只家畜,甚至寨子上空的云朵,林子里的鸟雀,路口的小野花,台阶下秘密的蚂蚁巢穴,她都能随口说出来历。祖母的死,就是她说给我听的。祖母躺在散发着体香的木房子。那些虫子奋不顾身地朝她爬来,像虔诚的信徒来朝拜。这多少带有魔幻的景象一直盘旋在我的记忆里。湾湾太太死后,每年夏天往房子里爬的虫豸越来越少,房子的记忆大半干枯在时光之中。它们的气味芬芳湮没在风中,隐匿不现。
房子在时,我看不清它的来处。它死亡后,鸡笼没了,鸭栏破了,猪圈毁了,依附在房子里的一切东西都走失了。在这半年时间里,我们思绪混乱,生活无序,人人变得悲伤慌张。生活是突然来到一处悬崖边的,我们一家人悬空生活在这里,意外遭遇了断层。我知道母亲很多次从那个临时搭建的绿颜色小棚子里起床,有小半天神情是茫然的。她也许说不出那种感觉,但我知道,那就是怀疑,怀疑自己的出处,怀疑这一切的出处。这一切都显得那么突兀,一切都来历不明。她有时候听到猪叫了鸡吵了,想着该喂食了,慌急急去找家什,脚步却不知道该往哪里抬。喂食的工具都不见了,但母亲老想着它们在什么地方悄悄躲藏着。
每次从外地回到这栋木房子里,我都在角落里翻找老旧的时光碎影。一张残损的照片,一小截污秽的橡皮擦,半本语文书。这些东西看似微不足道,可它们一旦串联起来,就是我的整个童年,整个过去,我的一切,这个家的一切。现在这一切都无迹可寻,在短短二十分钟内,它们成了灰烬。
我们成了丢失过去的人,那些能证明我真实存在的一切物件都隐匿不见了。我真的有过祖先吗?我真的在童年生活过吗?我是从这块烧焦的土地上出生并成长起来的吗?谁来证明呢?那些无法证明的存在还是存在吗?这成了我有生以来精神上遭遇的最大危机。
一连几天夜里,我都梦见那些被二姐烧毁的树在哭泣。经历多少风雨人世,它们老得跟老祖宗一样老,应该跟老祖宗一样受后人尊敬。它们是神[祗] 一样的树,它们活在世上,像祖先一样,庇护子孙。谁知道什么都不懂、什么都不知道敬畏的子孙,会因为一个浅陋的理由,就用大火把它们活活烧死呢?我常常躺在离家稍远的一座瘦小的山头,和着轻风残阳,对着无限苍穹发呆,想着人的存在与虚无,无端伤感和落泪,直到暮色铺地才恹恹而回。我们在遭受大难后,感受到无路可走的恐慌和不安,才终于明白,这是一件可怕的事情。人如果抛弃了自己的过往,抛弃了自己的祖先,她就再也无法去寻找自己的来历。
我开始习惯坐在废墟堆边复习自己的记忆。我在这里出生,将来也必定会从这里出走和死亡。我身上的一切细节,毫无疑问都来自于面前这栋消失掉的房子。现在的细节都必须还原到记忆中去,跟儿时的情节一一契合,我才能够看清自己的来处。户口和身份证烧毁了,可以补换一个簇新的,一切都来得及,我们不用担心外在身份的丢失。只是从今往后,世间的风月再也来不及滋养那些坟前新植的幼苗了。我们与这栋房子所共有的一切情感细节,就只能埋葬在记忆之中了。可记忆善于做伪证,最是形迹可疑、来历不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