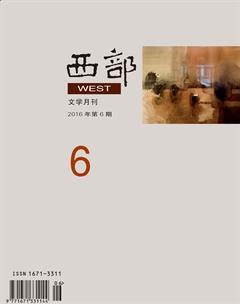青春鹦鹉
李鲁平
晴川阁上有一副楹联“洪水龙蛇循轨道,青春鹦鹉起楼台”。所有的资料无一例外介绍说,光绪年间晴川阁进行了最后一次大规模重建,竣工之时湖广总督张之洞亲自题写了这副联。光绪年间从1871年或1875年算起,到1908年,有三十多年的跨度,晴川阁到底哪一年竣工的呢?张之洞题联究竟是哪一年呢?我一直想弄明白,但寻来找去,阅读了张之洞上晴川阁、为汉阳铁厂选址以及他在晴川阁接待俄国皇太子尼古拉·亚历山德洛维奇等许多资料,都没发现写作楹联的时间。幸运的是,最后在一篇介绍张之洞在湖北的楹联创作的文章中,找到了这副楹联的创作时间。
张之洞题写这副楹联的时间是1902年。
其时,一个新世纪刚刚开始。作为晚清洋务运动的倡导者、践行者,张之洞孜孜以求的“湖北新政”在工业、商业、教育诸领域都有了令人兴奋的气象。因此,借用司空图的“青春鹦鹉”表达他内心对“中兴”景象的无比向往和憧憬。一百年过去了,汉阳这个张之洞当年用“青春鹦鹉”形容的地方已经面目全非了。龟山的背后,张之洞当年雄心规划的铁厂、兵工厂,绵延十里的洋务事业都已无踪迹,依旧的只是汉江的流水和晴川阁的风姿。
离张之洞题写这副楹联一百一十年后,西安铁路局一位见习路线工在四川达州的一座铁路桥上巡查线路时,发现一条钢轨上铸有一行繁体字“1902年汉阳铁厂造”。年轻的线路工为这一个世纪的穿越和遭遇,感到无比神奇。当然,当年武汉近代工业的辉煌还遗留在很多地方。这些是张之洞不可能知道的。他当年选址龟山北麓建设他倚重的铁厂和枪炮厂,很大一个原因是考虑水上运输和他监督的方便,纯粹从工业和经营的角度看,张之洞当年的决策带有太多的理想主义和浪漫主义色彩。他认为只要把人选对了,加之帝国的权威和强有力的政府监管,所谓的大冶铁矿与武汉的距离、运费、贪污、腐败等等,都是小事一桩。对张之洞的理想、热情,李鸿章等一贯采取批评立场或者干脆不理,但张之洞固执地在龟山北麓实施起他的民族工业之梦,尽管从后来的生产和经营证明,他的决策并没有达到预料的效益和成果,但客观上却将中国近代工业化向前推进了几十年。武汉也因他奠定的基础,成为少数几个具有完备工业体系的大都市之一。
这样想来,“青春鹦鹉起楼台”真的就淋漓地再现了张之洞内心满怀的理想和近乎狂热的激情。写这句话的时候,张之洞六十五岁,已经不再年轻了。今天再读他一百多年前写下的文字,不由得被一个没落皇朝捍卫者的家国情怀所感染。
张之洞在龟山挥洒的浪漫和激情让我想到一个熟悉的朋友胡君。
他是我青年时代的朋友,也是一个充满浪漫情怀和理想的朋友。那些年他就住在与汉阳铁厂一路之隔的月湖街。胡君只年长我一岁,但因为聪明,十五岁就上了大学,学的是流体力学专业,八十年代初就分配到江汉路附近的一个厅级机关。我大学二年级的时候常常不辞辛苦,从学校坐车到武昌江边,坐轮渡过江,穿过江汉路,沿着中山大道去他那里见面。那个时候,他的办公室有一台电脑,是早期的初级的电脑。我对这个电脑感到很神秘,每次就带着自己写好的诗歌,让他帮我打印,然后对着打印出来的那张纸胡思乱想半天,觉得这是件不可思议的事情。
胡君很快调到王家巷附近的一个航务部门,并住到了江汉桥下面月湖街上的航务局宿舍。从此,月湖街成了我熟悉的一个地方。那时去他的宿舍,下长江大桥后,在鹦鹉磁带厂这边下车,再从一个涵洞穿过江汉桥到月湖那边。涵洞狭窄,来来往往的三轮车、自行车、行人,你挤我、我撞你,跌跌撞撞出涵洞后,沿老街走几百米,便是航务局宿舍。
那些年,我们几乎每周都见面。他狂热地写诗、写电影剧本,参加我们这些在读大学生的诗歌活动。巧合的是,我的妻子也分配到了航运系统代管的一所中专,这样胡君便经常来到我们居住的学校做客,并与我妻子的同事谈起恋爱来。很长时间,不是他到长江边我的住处,便是我们到汉江与月湖之间他的住处。他对政治、经济、文学都充满兴趣,兴奋地议论当时经济管理的落后、弊病,解释自己的各种改革方案,他研究《资本论》和经济学,告诉我们他正在思考的课题,反复说自己要考经济学研究生,决心改写人们对政治经济学的认识误区,建立一个新的经济学体系……这样的聊天常常从上午见面开始,持续到下午我们分手。那个时代,我们年轻,没有焦虑,没有紧张,没有压抑,没有彷徨,有的就是梦想、激情。
这样愉快的闲聊和经常性的见面很快被打断。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中期,时代的波澜突然壮阔地席卷了我们。巨大的生存压力,紧张的生活节奏,让我们彼此很难保持密切的往来了,当年的激情似乎一下子烟消云散,再也没有心情聊天和畅谈理想了。
现代化进程改变了我们每一个人的人生面貌,有的是剧烈的动荡,有的是轻微的波动,有的是表象上一目了然的曲折、颠沛、多变,有的是隐秘的内心世界的不安、焦虑、压抑。胡君先是承包了单位的一个公司,接着离了婚,又结了婚,后来自己又成立公司,开发关于教学质量管理的软件。我去过东湖开发区他的写字间,他向我解释他的软件如何操作,如何提高教学管理的效率和科学性。介绍完毕,就鼓动我为他介绍中小学教育界的熟人。那个时代没有大众创业的说法,而且我对“做生意”从来就没有兴趣。多年来,我习惯了个体式的劳动,对这种需要组织一个团体去实现价值的方式,我是本能拒斥和恐惧的。尽管如此,我还是听完了他的介绍,并把他介绍给一个地市州的教科院,那个教科院组织了一次培训活动,发下去了一些软件。后来我听说,软件的货款并没有全部收回来。我把胡君介绍给当地人就回到了武汉,我觉得我只能做这么多了,后面收回货款的事应该由胡君自己去办。
我们又都各忙各的了。我也渐渐淡忘了这件事,中间似乎胡君来过电话,问能否催催回款,我大约觉得这不是我中间人的事,加上这些年自己东奔西跑都不知道方向了,便没有认真去对待。其间,我们也偶尔见面,跟过去相比,他少言了,憔悴了。他说老婆去深圳工作了,他要去深圳给老婆装修房子。我婉言劝阻,但他对老婆离开武汉、去深圳定居不但没有意见,反而宽容得很。不久后的一天,突然听说他病了,在同济医院做了化疗。我赶到同济时,他在老家来的一个小伙子的搀扶下,刚刚走到医院的门口,准备回家休养。一个曾经满腔豪情要研究中国经济、要拍电影、要成为一个有思想的企业家的胡君,在万物生长的初夏似乎已经枯萎。他在家休息期间,我去过两次,一次是晚上,在月湖他的宿舍,他说已经恢复了,我有一点不敢相信,但依然为他高兴,匆匆聊过几句,就在夜色中道别了;另一次是在汉阳的新五里,他的另一处房子里,这次他已经无法认识前来探视的我们。
那时,他才四十出头,壮志未酬。
我由此跟汉阳再无联系。在武汉的三十年中,与胡君无关的汉阳之行,我有过,但极少,一次是陪同外地朋友去归元寺参观,另一次是带着家人去归元寺,还有一次,独自去过龟山,上过晴川阁。在那个时代,晴川阁并不是一个著名的景点,也没有多少人去旅游参观。南岸嘴以及附近的汉江、长江江滩公园更没有修建。彩虹桥同样没有。龟山如同一座野山,没有人留意和关注。而今,龟山北麓的几个工厂已经改建成创意社区,蜿蜒曲折的小道两边布满不同艺术风格的酒吧、工作室、画廊。胡君所居住的那一带,从江汉桥往西,依次是琴台文化艺术中心、琴台钢琴博物馆、琴台大剧院,当年的街道和房子大都荡然无存。龟山以北、汉水东西,一百多年前,张之洞燃起的复兴之火再次被点燃,汉阳正经历又一次隆重的洗礼。
踏上麻石台基,走过红墙朱柱,登上悬于江水之上的晴川阁,目光所及,汉水西来,瘦石嶙峋,龟山的岚光树色还在。伫立栏杆边,万里的风、千里的雨、三秋的水一同扑来。如此佳境,在我们的青年时代,我与胡君竟然没有一同来见识过。他的理想、激情本应在这朱漆彩绘的亭台楼阁中抒发,他纷繁和疲惫的人生也应在这窗含的烟雨中梳理。一只“青春”的鹦鹉也应在此兴起自己的“楼台”。
司空图在《诗品》中把“青春鹦鹉,杨柳楼台”作为诗歌的第十三种品格“精神”。无非是说不要勉强,而是要求之于内在的积累与通透,顺应心性的自然流动。张之洞在龟山北麓实施他雄伟的中兴梦想时,有压力,有无奈,有失望,也有挫折,但张之洞没有匆匆倒下。我想这与他同时也是一位学养深厚和眼界开阔的思想家有深刻的关系。置身风云激荡之中,每一个人的命运都有极大的不可知性,每个人都难以把握命运。由此,内在的那一份精神的奠基和支撑就更加可贵了。
站在晴川阁上,我不想责怪胡君,倒是遗憾我们没有像袁宏道所说的“晴川阁下南条水,一日同君荡几回”,也没有像李白说的“预拂青山一片石,与君连日醉壶觞”,这些浪漫、畅怀的交游和作乐,袁宏道、李白和他们的朋友,都干过,而且还是在汉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