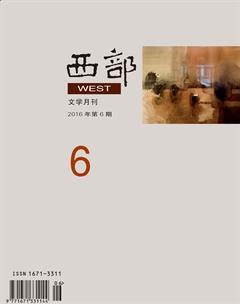萤火时代的两个精神样本
霍俊明
我们就开始走进一座树林 / 那里不见有什么路径的痕迹 / 树叶不是绿的,而是晦暗的颜色 / 树枝不是光滑的,却是卷曲而多节 / …… …… / 我已经听到了四边发出哀鸣 / 但是没有看到发出哀鸣的人 / 我因此完全吓呆了,站着不动 / 我想我的夫子相信我是在想:/ 这些众多的声音是由那些因为怕我们 / 而在丛林里隐匿起来的人发出来的。
——但丁《神曲·地狱篇》
但丁的隐晦的树林和四处的哀鸣正是诗人的心象对应,这是精神的炼狱,是灵魂的盘诘,是诗歌终极关怀的本质化回声。这个古老的回声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仍在继续。我记得骆一禾在一首诗中有这样的句子:“黄花低矮却高过了墓碑。”那一截石碑在时间和尘世面前却是微渺而不值得一提的。诗人就是在精神隐喻层面撰写墓志铭的人——“在这里,死亡仅仅作为生命的关键节点,向我们展示各种深入语言的可能性。据此,我们可以探究生命的意义和为后来者重新设定生命的目的和价值。墓志铭不仅以证明死亡的力量为目的。因此,个体人类的死亡在精神万古流长的旅程中是不会彻底地一次性完成的。诗人一腔忧惧而满怀信心,皆源于对‘墓志铭所刻写的言辞的敬畏。”(陈超《从生命源始到天空的旅程》)确然,从终极意义上考量诗人不仅为自己写下了特殊的墓志铭,而且也镌刻出了人类共同的难以规避的命运。死亡之诗也就是永生之诗。由此考量当下的中国诗人,这样的诗人存在吗?也许一切都是未知,也许有人已经有了自己的答案。
回到当下的诗歌现场,这似乎是一个热闹无比的时代,尤其在新媒体和自媒体的推波助澜之下。诗人的自信、野心和自恋癖空前爆棚。面对着难以计数的诗歌生产与日益多元和流行的诗歌“跨界”传播,诗歌似乎又重新“火”起来了,似乎又重新回到了“公众”身边。但是凭我的观感,在看似回暖的诗歌情势下,我们必须对当下的诗歌现象予以适时的反思甚至批评。因为在我看来,当下是有“诗歌”而缺乏“好诗”的时代,是有大量的“分行写作者”而缺乏“诗人”的时代,是有热捧、棒喝而缺乏真正意义上的“批评家”的时代。即使是那些被公认的“诗人”也是缺乏应有的“文格”与“人格”的。正因如此,这是一个“萤火”的诗歌时代,这些微暗的一闪而逝的亮光不足以照亮黑夜,只有那些真正伟大的诗歌闪电才足以照彻。但是,这是一个被刻意缩小闪电的时刻。
是的,我们讨论新诗从来没有变得像今天这样吊诡而艰难。我必须再次指认,这是一个有“诗歌”但是缺乏“诗人”的时代,而在“诗人”当中我愿意选取雷平阳和陈先发这两位诗人作为精神样本谈谈这个时代的“诗”与“人”。而之所以选择雷平阳和陈先发,不仅在于他们各自的诗歌精神路向与美学取向的差异性,还在于他们的写作在这个时代的某种启示性。限于篇幅,我只以雷平阳的长诗《去白衣寨》和陈先发新近完成的组诗《新九章》为例做以点带面的辨析。
样本之一:“坛城”:虚妄之词与无去来处
在故乡的地界上
却自己欠自己一个异教徒的上帝
—— 雷平阳《去白衣寨》
在这个写作的精神难度空前降低而涣散莫名的时代,能够旷日持久地坚持精神难度和语言难度的诗人实属罕见,而雷平阳是这一少数的代表之一。
我曾经对雷平阳说过,他是中国当下汉语诗人中最会“讲中国故事”的。这不仅在于我和他的几次相遇都听他在会场和酒桌上慢悠悠地讲述云南“边缘空间”的沉暗故事与中国寓言,而且这一讲述“中国故事”的冲动还体现在他一直以来的长诗和诗歌写作当中。而在此过程中,雷平阳寓言化的诗歌话语方式在我看来绷得太紧张了,也就是这种目的性有些突出的诗歌写作方式和经验以及想象力状态会一定程度上使诗歌的生成性、不可知性的偶然性因素削弱。当然,对于雷平阳这样的成熟且风格明显的诗人而言,自觉性和自主性的写作阶段是情理之中的事情,但似乎写作的“瓶颈”期也在到来。从云南回来时我提了厚厚的一大摞雷平阳的散文随笔集,在随后的日子里我一直在比照他的诗歌文本与非诗歌文本之间的互文关系。我发现一些相同的故事和片段出现在诗歌和散文中,当然处理的方式和重心是不同的。我也一直期待雷平阳能够对自我限囿进行突破。那么,由此再来读他的长诗《去白衣寨》,这是不是他的一次诗学的突破呢?我也想听到更多阅读者和评论者的声音。
雷平阳精神性的寓言和对现实的生命感转化能力逐渐凸显出“悬崖饲虎”和“聚石为徒”的诗人形象。每个人都处于两个时代和迥异经验的悬崖地带,你不能不做出选择。在2014年夏天的暴雨中,我曾在一朋友处看到雷平阳的四个斗大的书法“聚石为徒”。这样说并非意味着雷平阳是写作的“圣徒”,我想强调的是其写作的“精神来路”和“思想出处”。但是,雷平阳近些年在诗歌中则不断强化着“虚妄之词”,换言之,他的精神来路和去处都受到了根本性的挑战。能够容留自我精神的空间似乎不再——“用脚踢一块石头 / 希望石头支持她的谬论 / 我则把自己塞进石头 / 在石头里望着她 / 除了翻滚,咬着牙,什么也不说”。
雷平阳长诗中冷僻的、寒冷的、荒芜的、朽烂的“白衣寨”让我想到的是藏传佛教里的“坛城”(梵文音译“曼陀罗”“满达”“曼达”)。
2015年夏天在布达拉宫我第一次与那小小的却惊异无比的坛城相遇。那并不阔大甚至窄促的空间却足以支撑起一个强大的无限延展的本质性的精神空间与语言世界,这是精神和心髓模型与灵魂证悟的微观缩影。
而无论是用金、石、木、土、沙子或是用语言、精神建立起来的坛城,最终也只有一个结局——
我想,这个小镇很快就会泯灭
幻化为空,重新成为荒地
但谁也不知道,这脆弱的生命
到底还能供我们挥霍多久
雷平阳新近完成的长诗《去白衣寨》延续了多年来他的诗歌主题和精神主旨,即对个体“现实”精神命运和整体现代性景观的疑虑和反抗,但最终的结果是词语和精神的双重虚妄。正如我在评价他的长诗《春风祷》时所说的诗人所目睹的“历史遗迹”“时代风景”已经变形并且被修改甚至芟除。“真实之物”不仅不可预期而且虚无、滑稽、怪诞、分裂、震惊的体验一次次向诗人冲涌而来。虚无的诗人已经开始失重并且被时代巨大的离心力甩向无地。在此时代情势之下诗人的“祷辞”就只能是一种虚无体验的无奈验证之举。显然,长诗《去白衣寨》仍然属于“祷辞”的诗歌话语方式,只不过内省、虚妄、无着的意绪更多是通过反讽、悖论和寓言的拟场景以及戏剧化的方式得以反复凸显。正如诗人在该长诗的开篇所明示的——“一直想去一个地方,它叫白衣寨,但我不知它在哪里。人世间的幻虚之所,我只能到诗歌中去寻找。有很多人给我指引,为我提供了生者与死者共用的地图,在人间与鬼国我因此步履沉重。边界消失、人鬼同体,就连我自己的言行举止都吸附了太多的阴风与咒怨。我穿过河山、旷野、村庄,一路向前,所到之处都不是记忆和想象中的乐土,世界散发着腐朽的气息,挽歌声里人心颓废。白衣寨,设想中的天边的客栈,它也变成了苦难灵魂的集中营”。雷平阳曾自忖“我很乐意成为一个茧人,缩身于乡愁”。而吊诡的是一再抒写和反刍“故乡”的人最终却没有安身立命之所。这就是雷平阳的写作宿命。
就诗歌文本世界而言,显然“白衣寨”并不是现实中实有的(不只是一个雨林中冷僻的四周有很多溶洞的边地小镇,“人丁少于象冢,狮虎皆为仆役”),而是诗人企图通过文字建构起来的精神之所。但是这种“故国挽歌”式的怀想、追念的精神性愿景最终面对的似乎只有遗照式的残骸和废墟。这又是一个游荡的灵魂——对现代性景观予以批判的游荡者。既然是“批判”与“否定”,那么这种精神伦理观和语言美学的背后要建立起来的是怎样的“新景观”呢——“她砍倒一片竹林和紫藤 / 想搭建永久的居所 / 但又觊觎那些无人的石头房子 / 她高声问我:‘我应该怎么做 / 才能让新建的房屋 / 拥有记忆和出处,拥有道德感 / 并有鬼神暗中护卫?”还是说诗人最终也无力建立这一具有相当难度的精神景观——“因此,我的一生就交给了最后一件做不完的事:在象冢的旁边 / 修筑一座座只埋葬袈裟的衣冠冢”?这最终只能是一场虚妄的语言徒劳之举?
在1980年代后期以来的先锋诗界尤其是长诗写作中“语言乌托邦”曾一度成为诗人的造梦仪式,“诗到语言为止”并非只是一个诗人的美学观念。但是,到了雷平阳这里,语言乌托邦已经解体,“诗人的原乡”(现实和精神的双重意义上的)已经被斩草除根,由此诗人再向远方、向天空、向自我内心和语言深处寻找一种所谓的“白衣寨”就只能是一场幻梦。这必然是个体主体性精神的无着分裂,是语言的虚妄,是失魂落魄的丧家犬,是不合时宜的恋旧者,是精神的无来去处的尴尬性境遇——“春草稀疏的江岸欠我一幅骑牛图 / 平坦的田野欠我一幅农耕图 / 小路欠我几个额上流汗的农妇 / 池塘欠我一阵蛙鸣和捣衣声 / 屋顶欠我丝绸一样的炊烟 / 寺庙欠我一个个心事重重的香客 / 村庄欠我天人合一的生活现场 / 树荫欠我讲故事的人 / 以及那荒诞不经的故事”,“就连从我头顶飞过的孤雁 / 也欠我一声哀鸣 / 我是如此的恋旧,如此深入骨髓地可怜自己,在故乡的地界上 / 却自己欠自己一个异教徒的上帝”。
白衣寨,是全诗展开的中心地带,也是精神性愿景的依托性装置,更重要的是这是一个戏剧性和寓言化的“拟场景”。
迷离惝恍又真切刻骨都统一在呛人鼻息搅拌血液的寓言化的诗歌氛围之中。这一场景介于现实与寓言之间,更是像一场白日梦式的景观,比如《白衣寨》中那个老年瓜农在河滩瓜田里挥舞着铁锤不断砸烂西瓜的场景,两个人骑在即将被施工队刷成红颜色的生锈的引水管道上。而多年来,实际上雷平阳的很多代表性的诗歌都具有“拟场景”化的特征,包括那首《杀狗的过程》。这种“拟场景”“寓言化”的文本效果显然要比那些过于胶着于“现实生活”的写作更具有超拔性和疏离感,而这种疏离恰恰又是建立于主体对现实和生活的精神介入基础之上的。换言之,我们都在谈论诗歌与时代、现实的关联,而我们却时刻在漠视这些日常生活的真实景观与诗歌镜像和诗人精神主体之间的对应关系。值得强调的是,雷平阳诗歌中的拟场景即使有时候呈现为实有之物,但是这一实有之物在当下迅速推进的城市化和现代性景观中也大多成了追悼的亡词和精神的虚妄之词。“贴身肉搏”的结果却是“失魂落魄”。而寓言化的拟场景最终要达到的结果就是“魔幻现实主义的寂静”。
首先需要强调的是长诗在意象和场景上的视觉化效果。其中最突出耀眼的就是红色的场景和意象,比如“红土”“天空的吸血管“鲜艳的瓜汁染红了流水”“腐烂的桃花”“一只鲜红的气球”“一条即将被涂红的引水管道”等。而这一红色的视觉化的过程显然并非简单对应于所见所感的现实物态,而是建立于个人化的历史想象力和求真意志的基础之上,是对历史个人化与个人历史化相互观照和精神往返过程的印证与强化。
白衣寨,让人想到的则是桃花源。
“前面就是梨园了 / 白色的梨园,在红土上闪烁”。
但是,白色的、芬芳的、诗意的、农耕的“梨园”瞬间就被一种强大野蛮的力量击碎摧毁了——“走在空无一人的村庄里 / 我们看见桃树下桃子腐烂 / 梨树下烂梨飘香 / 村庄的魂魄已经走掉 / 地底下的废墟破土浮到了地上 / 她来到自己的家门口 / 站着,看着门上的铁锁和蛛网 / 想不起来亲人们都去了哪儿”,“腐烂的桃花铺满废弃铁轨”。
白衣寨的精神空间中“故国”“村庄”“土地”“河流”“山顶”“稻草堆”的荒芜和废墟般的存在,再次印证了雷平阳对现代性城市化景观的警惕和批判意识。而这种批判意识必然使得诗人面对两种性质不同的景观和空间以及时间性背后的历史法则,比如乡下王屠夫凄怆地死于乡下猪圈,而五个儿子则“在五座城市的五间出租房里酣睡”。由此意识出发,诗人也必须对与此相关联的语言系统和意象谱系的“病症”进行重新的“清洗”,“月亮,我在一个肮脏的乡下诊所里 / 与医生讨价还价 / 补回来的硬币像一堆月亮 / 她浑身的水泡像月亮 / 为了止痛,她大声叫着 / ‘杂种,月亮,杂种,月亮…… / 医生说:噢,月亮 / 输液的梅毒患者也说:噢,月亮 / 他们叫着他们自己的月亮 / 唯独一个濒死的老人,无人守护 / 他一声不吭,偏着头看月亮 / 那真实的月亮挂在诊所的屋檐上 / 只有这个月亮是上帝的月亮”。这就使这首长诗还具有元诗的精神趋向,这指向的是“乡土诗歌”语言的沉疴以及苍白浮泛的“伪抒情”方式,与此相应要建立起来的是有生命感的有效性和及物性的话语方式——“黑夜只是睡觉的时间段 / 我们发现并夸大为黑暗”。
“在错乱的道路上”“无望是我们的信仰”。这注定是一场羞耻、怪诞、分裂、妄想症式的寻找与遗落并在的精神之旅。逆行、错乱、返乡的道路,“废弃的铁轨”预设了全诗的精神方向。
是的,“冷飕飕的坟地”“黑夜”“肮脏的乡下诊所”“铁屋子”的场景出现了——前方只有坟墓。这是存在性的关于时间焦虑的诗歌命题的重演——生死,命运,时间轮盘上的骰子……这不能不让人想到当年鲁迅散文诗中的那个黑衣的夜行人过客——“约三四十岁,状态困顿倔强,眼光阴沉,黑须,乱发,黑色短衣裤皆破碎,赤足着破鞋胁下挂一个口袋,支着等身的竹杖”。
甚至长诗《去白衣寨》的拟场景都与鲁迅的《过客》具有精神性的相似——东,是几株杂树和瓦砾;西,是荒凉破败的丛葬;其间有一条似路非路的痕迹。而当年鲁迅笔下黑衣人过客所遇到的女孩在雷平阳这里得到了“精神性的轮回”。全诗中反复出现的正是一个“她”,这个“她”同样是一个拟场景化的存在——不具体,不真实,但是又不断与诗人的精神主体进行拉抻甚至撕扯性的对话。两者之间形成的正是长诗特殊的声音和语调,恰如舞台两侧一个面影一个背影的位置。这两个位置正好是诗人寻找和返回的精神性隐喻。但是,既然前方是坟墓,返乡又是无地,那么这种悲剧性命运的产生就不只是“唏嘘”二字可以涵盖得了的——“我见过很多返乡的婊子 / 她们从良了,但没有一个男人 / 能满足她们的肉欲”。这显然是雷平阳对诗歌和“精神返乡”的文化冲动的反省、检思与批评。是的,很多当代诗人似乎都同时走在“回乡”的路上,但更多的则是浅层的、庸俗化的、单向度的精神表层细胞,而非灵魂的激荡。是的,“还乡”以及“还乡的人”有时候也是可疑的,他们并不应该据有完全意义上的道德优势,更重要的则是时间和社会法则背后的深层机制和心理动因。陈超在八九十年代之交的诗歌中曾写道“逝者正找回还乡的草径”,海子则是“和所有以梦为马的诗人一样 / 我不得不和烈士和小丑走在同一道路上”。如今在雷平阳这里“还乡”的路上又多了一个“婊子”。这恰恰是“不洁”的诗所具有的不可替代的重要性,反之那些具有道德和精神洁癖的写作者恰恰是最可疑、最不可靠的。
一切都在改变,荒诞主义的结局似乎早已经注定,连乡村的后裔们也已改变了基因——肉体的、血缘的、文化的、道德的——“他们在荒村里,失教于天道 / 纷纷撇开了血缘,学会了独立 / 自称是墓地或废墟上 / 旁若无人地长大的一代 / 亦称粉碎的一代 / 他们目光阴沉,习惯了抛弃与屈辱 / 像喝足了狼奶与激素的机器人 / 一身的邪劲儿,随时准备 / 戴上我们的脸谱,以我们之名 / 锋芒毕露地向我们猛扑过来…… / 以诗人的身份,混迹于他们中间 / 我知道,这是一场被培育 / 和操纵的、继往开来的自杀运动”。这已不只是虚妄之词,也是绝望之举。既然无路可返,自我精神主体的白衣寨又只是一场幻梦,那么这个时代的“诗人何为”似乎又成为了大是大非的艰难疑问。
样本之二:从《小于一》到《新九章》
在任何一个时代都会有极少数的诗人让那些专业阅读者们望而却步。这一类别的诗人不仅制造了足以令人惊悸的诗歌文本,而且他们自身对诗学的阐释能力已经远远超出了大多数的专业批评家。
一
在打印完陈先发新近完成的组诗《九章》(包括《斗室九章》《秋兴九章》《颂之九章》)时正值黄昏,我走进北三环附近的一家蓝色玻璃幕墙建筑的电影院。电影播放前的一则广告是关于白领创业的,我只是记住了那句话——“遇见十年后的自己”。在电影院的荧屏光影和三环路上的鼎沸车流之间,哪个更现实?而诗人能够做到的不只是提前遇到十年后的自己,还应该与多年前的自我和历史相遇,而这正是诗人的“精神记忆法”不容推诿的责任。
多年来,布罗茨基的《小于一》一直是我的案头书,多年来我同样在寻找一个精神对位的强力诗人。我们都在寻求一份这个时代知识分子的精神自传以及诗歌文体学的创造者。尽管一再付之阙如,尽管一再被各种千奇百怪的诗歌现象和奇闻所缠绊。说实在话,我也无力真正与陈先发这样的“自我完成”型诗人做出我的判断。当我最初拿到他硬皮本的《黑池坝笔记》的时候我并未找到有效的进入文本迷津的入口,也正如陈先发自己所说“令人苦闷的是常常找不到那神奇的入口”。那种表面的无序膨胀与内在繁复的逻辑收敛,庞杂、晦暗、丰富和歧义以及多样侧面的精神自我正像那些凛然降落的雪。你只是在视觉和触觉上与之短暂相遇,而更长久地它们消隐于你的世界,尽管它们仍然以另一种形态存在着,面对着你。也许,这就是诗人特殊的语言所锻造出来的精神现实,对隐在晦冥深层“现实”的好奇与发现成为诗歌的必然部分——“我们活在物溢出它自身的那部分中”。由此,我只能采取硬性的割裂的方式来谈谈对陈先发新近的组诗《九章》的零碎感受。在黑夜中,我似乎只看到一个黑色背影被风撩起的衣角,而那整体性的事实却最终不见。
在我看来陈先发的诗歌约略可以称之为“笔记体”。那种在场与拟在场的并置、寓言与现实夹杂、虚实相生迷离惝恍滋味莫名的话语方式成为现代汉语“诗性”的独特表征。诗人通过想象、变形、过滤、悖论甚至虚妄的方式抵达了“真实”的内里,还原了记忆的核心,重新发现历史遗迹和现实的魔幻一面。甚至这种“笔记体”在陈先发的复合式互文性文本《黑池坝笔记》中被推到了极致。
那么诗人为什么要写《九章》呢?
当读到陈先发的《秋兴九章》的时候,我必然会比照杜甫的《秋兴八首》,甚至在黄灿然和沈浩波那里都曾经在诗歌的瑟瑟“秋天”中与老杜甫对话。在这种比照阅读中,我更为关注的是那个“一”。这个“一”正是陈先发的特殊性所在,无论诗人为此做出的是加法还是减法,是同向而行还是另辟蹊径,这恰恰是我们的阅读所要倚重的关键所在——“诗性自分裂中来。过得大于一或过得不足一个”。
无论是一首独立的诗还是《九章》这样的组诗,诗歌的生成性与逻辑性、偶然性与命定性是同时进行的。由此,陈先发的组诗中那些相关或看似无关的部分之间的关系就变得愈益重要,与此同时,我更为注意那些看起来“旁逸斜出”的部分。这一不可被归类、不可被肢解、更不可被硬性解读的“旁逸斜出”的部分,对于陈先发这样的诗风成熟且风格愈益个人化的诗人而言,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因为对于很多诗风成熟的诗人而言,很容易形成写作的惯性和思维的滑行,比如诗歌的核心意象以及惯用的话语类型。而就核心意象以及话语类型来说,很多诗人和批评家会指认这正是成熟诗人的标志,可是当我们转换为另一种观察角度,这又何尝不是固步自封的另一种违心托词。任何写作者尤其是诗人不可能一辈子躺在一个意象以及围绕着一首诗写作。正是陈先发诗歌中生成性的“旁逸斜出”的部分印证了一个成熟诗人的另一种能力——对诗歌不可知的生成性的探寻以及对自我诗歌构造的认知与校正能力,而这也是陈先发所强调的诗歌是表现“自由意志”的有力印证。
与此同时,这一“旁逸斜出”的部分或结构并不是单纯指向了技艺和美学的效忠,而是在更深的层面指涉智性以及“现实”。陈先发对“现实”曾予以了个人化的四个区分,而显然其中更为难以处理的是公共化的现实。而就生活层面的与公共化的现实部分相应的诗歌处理而言(比如《室内九章·女工饰品》),陈先发非常好地平衡了道德伦理与诗歌美学话语之间的平衡,大体在虚实之间转换。内部致密的精神结构与向外打开的及物性空间恰好形成了张力,而这种张力在陈先发这里精神层面上凸显为虚无、冷寂、疼痛、悖论的类似于悲剧性的体验和冥想——“我嗅出万物内部是这 / 一模一样的悸动”,“我们应当对看不见的东西表达谢意”。这正与陈先发的诗学“现实观”相应。
组诗《九章》延续了他对世界(物象、表象、世相、真相)的格物致知的探询和怀疑能力,而此种能力则必然要求诗人的内心精神势能足以持续和强大。在很多诗人那里“历史”和“现实”往往割裂开来,而只有真正的诗人才能领悟到二者之间彼此打开的关系,这种历史的个人化和现实的历史化在《九章》中有突出性的印证,比如《地下五米》《从未有过的肢体》。这也是陈先发写作出《黑池坝笔记》的深层动因。那轻霜、乌黑的淤泥以及灰蒙蒙的气息所弥漫开的正是诗人对世界的理解方式,这种理解方式已经在多年的写作践行中成了个体节奏的天然呼吸。陈先发诗歌因为极其特殊的精神气质和文化诗性而很容易被指认为耽溺型的“蜗居的隐身者”写作代表。但是,这显然是一个错误的判断。陈先发的诗歌并不缺乏日常的细节,不忌讳那些关于整体社会现实以及历史场域的“大词”(比如“现实”“时代”“共和国”“中国”“故国”),只是最为关键的是,陈先发并没有沦为1990年代以来日常化抒情和叙事性写作的诗人炮灰(当然陈先发的部分诗作不乏“戏剧性”),也没有沦为无限耽溺于自我想象和雅罗米尔式极端化个体精神乌托邦的幻想者。他的诗都是从自身生长出来的,并且没有“大词癖”。没有大词癖并不意味着没有诗歌话语的精神洁癖。陈先发的诗歌多年来之所以风格学的面目愈益突出,就在于他维持了一个词语世界构筑的精神主体自我,与此同时他也在不同程度地加深着个人的精神癖性,而没有精神癖性的诗人在我看来是非常可疑的。这种值得怀疑和辩难的精神癖性在很多诗人那里体现为对立性,也就是他们不是强调个体的极端意义,就是极力强化诗歌社会学的担当正义。显然,这两种精神癖性所呈现的症候在本质上是同一的。一个优秀的甚至重要诗人的精神癖性除了带有鲜明的个体标签之外,更重要的是具有容留性,是在场与拟在场的平衡。由这种容留性出发来考察和阅读陈先发的诗歌我们可以注意到一个事实,那就是各种“杂质”掺杂和渗漏在诗行中。这种阻塞的“不纯的诗”正是我所看重的,再看看当下汉语诗界那么多成熟老成的诗人的写作太过平滑流畅了。这些光滑、得心应手而恰恰缺乏阻塞、颗粒和杂质的诗歌因为“油头粉面”而显得尤为面目可憎。值得强调的是,这种“油头粉面”的诗歌既可以是个体日常抒情意义上假大空的哲理和感悟,也可以是以义愤填膺的广场英雄和公知的身份出现。
二
“陈先发的柳树。”
这是我阅读陈先发的组诗《九章》以及笔记之后一个突然冒出来的句子。
多年来陈先发一直营设着特殊的“精神风景”格物学知识。比如“柳树”(“垂柳”)无论是作为物象、物性、心象或是传统的“往事”载体、“寓言体”以及“言语的危邦”,在陈先发的诗歌和笔记中已然成为核心性的存在。围绕着“柳树”所伸展开来的时间以及空间(河岸、流水、飞鸟、映像)显然构成了一个稳定性与未定性同在的结构。在《秋兴九章》的开篇,诗人再一次引领读者与“柳树”相遇——“在游船甲板上看柳 / 被秋风勒索得赤条条的运河柳”,“为什么 / 我们在河上看柳 / 我们往她身上填充着色彩、线条和不安 / 我们在她身上反复练习中年的垮掉”。就语言表达的限度和可能性上而言,为什么是这一棵“柳树”而不是其他树种?
这是精神仪式,也是现代性的丧乱。而这种秘密和不可解性恰恰就是诗歌本体依据的一部分。
陈先发的汉语“诗性”和“精神风景”,一定程度上体现为古典性“遗物”(“一种被彻底否定的景物,一种被彻底放弃的生活”)与现代性“胆汁”(怪诞、无着、虚妄)之间的焦灼共生。
陈先发往往站在庭院、玻璃窗(注意,是现代性的“玻璃窗”而不是古典的木制门窗)前起身、站立、发声。那些自然之物和鸟啼虫鸣与诗人内心的声音时常出现龃龉、碰撞。但是,这些自然之物显然已经不是类似于王维等古代诗人的“雨中山果落,灯下草虫鸣”的封闭和内循环的时间性结构。这些自然之物更多处于“隐身”和“退守”的晦隐状态,或者说这些物象和景观处于“虚辞”“负词”的位置——因为现代性的“水电站”取消了古典的流水。古典性的草虫鸣叫与现代性的工具嘶吼时时混响。这不仅在于内心主体情绪扩张的结果,而且还与“现代性”景观的全面僭越有关。但是这也并不意味着“已逝”的“古典性”和“闲适山水”就是完全值得追挽和具备十足道德优势的,“难咽的粽子”恰好是陈先发就此的态度。此时,我想到的是诗人这样一段话:“远处的山水映在窗玻璃上:能映出的东西事实上已‘所剩无几。是啊,远处——那里,有山水的明证:我不可能在‘那里,我又不可能不在‘那里。当‘那里被我构造、臆想、攻击而呈现之时,取舍的谵妄,正将我从‘这里凶狠地抛了出去。”这是自我辨认,也是自我诘问。具体而言,陈先发的诗歌一直持有着生存的黑暗禀赋。无论是在指向自然景观还是面对城市化生活的时候他总是在有意或不经意间将沉滞的黑暗晦明的死亡气息放大出来,“一阵风吹过殡仪馆的 / 下午 / 我搂过的她的腰、肩膀、脚踝 / 她的颤抖 / 她的神经质 / 正在烧成一把灰”(《斗室九章·梨子的侧面》)。甚至陈先发敢于预支死亡,能够提前将死亡的细节和精神气息放置在本不应该出现的位置和空间。这也是为什么陈先发钟爱类似于“殡仪馆”场景的精神图示和深层心理动因,“死者交出了整个世界 / 我们只是他遗物的一部分”(《秋兴九章·七》)。
这恰如闪电的陡然一击,猝不及防,瞬间惊悸。是的,我在陈先发的诗歌中总会有不期而遇的惊悸感,而这正来自于“挂碍”和“恐怖”。陈先发却将这种惊悸感和想象转化为平静的方式,正如一段胫骨的白净干彻让我们领受到曾有的生命血肉和流年印记,“我们盼望着被烧成一段 / 干干净净的骨灰”。《斗室九章》的“斗室”空间决定着诗人的抒写视角,而陈先发在斗室空间的抒写角度不仅通过门窗和天窗来向自然、已逝的时间和现代性的空间发出自己的疑问,也就是不只是在镜子和窗玻璃面前印证另一个“我”的存在,比如“有一天我在窗口 / 看着池中被雨点打得翻涌的浮萍”(《室内九章·女工饰品》)、“站在镜前刷牙的两个人”(《室内九章·斗室之舞》)、“我专注于玻璃窗外的夜色”、“在母亲熟睡的窗外”(《室内九章·诸神的语调》),而且他出其不意地在斗室中向下挖掘以此来尝试通向自我和外在的各种可能性。斗室更适合冥想,生死的猜谜和自我的精神确认成为不可或缺的主体趋向。在一些明亮的、浅薄的、世故的、积极的诗人那里,往往排斥的是黑色的、灰色的、消极的和不需要铭记的事物和情感,而陈先发却对此有着有力的反拨,“灰色的/消极的/不需要被铭记的//正如久坐于这里的我/被坐在别处的我/深深地怀疑过”(《斗室九章·死者的仪器》)。
“虚构往日”“重构今日”“解构明日”的不同时间区隔及其中的共时性的“我”就可以任性而为般地对话与盘诘,个体精神的乌托邦幻境不是不在陈先发这里存在,关键是他已经不再堕入到物我象征的“蝴蝶”的沉疴和泥淖中去。精神延展和锻打的过程更具有了某种不可预知的复杂性。
三
我之所在陈先发的《九章》题目中冠以“新九章”,正是我对汉语诗性和践行可能性的思考。
“新”曾一度成为进化论意义上的文学狂妄和政治体制集体文化幻觉,“新”也一度成为各种运动和风格学意义上当代诗人们追捧的热词。这些都是极其不理智不客观不够诗学的。而我强调的“新九章”恰恰是由陈先发的组诗以及多年来他的诗歌写作实践和诗学理念所引发的命题——而不是泛泛意义上的“话题”,甚至比“难题”的程度更重。一个已然的常识是古典诗歌的“诗性正义”是不容争辩的,甚至早已成为真理性的知识,可是现代新诗却不是,因为权威的“立法者”的一再缺席,其命运和合理性一直备受攻讦、苛责与争议。那么,一百年来,汉语新诗的“诗性”与“合法性”何在?这必然是一个现在不能解决的“大问题”——不仅关涉大是大非,而且讨论的结果必然是无果,甚至歧义纷生。可靠的做法是可以将这一话题具体化和个人化,也就是可以将此话题在讨论具体诗人和文本的时候应用进去。
具体到陈先发的诗以及新作《九章》,他所提供的汉语新诗的“诗性”和“新质”是什么呢?这种“新质”到底是何种面目呢?多年来,谈论新诗的“诗性”的时候,先锋性、地方性、公共性、传统性、现代性和后现代性是被反复提及的关键词,但是这些关键词被具化为个体写作和单个文本的时候又多少显得大而无当。由此,陈先发所提供的“新质”并不是其他论者所指出的什么桐城文化的传承,阅读感受上的神秘、晦涩以及儒释道的教义再造,在我看来,这种“新质”恰恰是来自于他复杂的生命体验和现代经验,对“已逝”部分的诗学迷恋,对个人化的历史想象力以及个体主体求真意志的精神构造。只有在此意义上确立了陈先发的诗人形象,才有可能真正理解他的诗歌文本以及文化文本。既然对于诗歌而言语言和生命体是同构的,那么以此谈论“生命诗学”也未必是徒然无益的虚辞。这必然是语言和生命体验之间相互往返的交互过程,由此时间性的焦虑和生存体征也必时时发生在陈先发这里,比如“摇篮前晃动的花/下一秒用于葬礼”。
陈先发的汉语“诗性”还表现为“洁”与“不洁”的彼此打开和共时性并置。
诗人需要具有能“吞下所有垃圾、吸尽所有坏空气、而后能榨之、取之、立之的好胃口”。而在我们的诗歌史所叙述的那些诗人那里,素材和道德的“洁”被提高到无以复加的地步,而那些“不洁”的素材、主题和情绪自然被视为“非法”和“大逆不道”。阅读史已经证明,往往是那些看起来“干净整洁”的诗恰恰充当了平庸的道德审判者,在内在诗性和语言能力上却没有任何的发现性和创造性。在我看来,那些被指认为“不洁”的诗恰恰是真实的诗、可靠的诗,是有效的诗,反之则是“有过度精神洁癖的人终将无法继承这个世界”。记得一个诗歌阅读者曾向我寻找答案——为什么陈先发写父亲的诗非得要写生殖器和白色的阴毛呢?①
我当时无语。
可怕的“干净”阅读症仍然以强大的道德力量和虚假洁癖在审判诗人和诗歌。
对于陈先发而言,诗歌的“洁”与“不洁”显然不是被器官化、生理性的阅读者强化的部分(比如“一座古塔 / 在处女大雾茫茫的两胯间 / 露出了 / 棱和角”),而是在于这些诗所出现的文化动因机制以及诸多可能性的阅读效果。陈先发的诗歌中不断出现“淤泥”(类似的还有“地面的污秽”)的场景和隐喻,而这几乎是当代汉语诗歌里非常罕见的“意象”构造。这一意象和场景并非是什么“洁”与“不洁”,而是诗人说出了别的诗人没有说出的现实和精神景观。当然这也包括当代诗歌史上的那些道德伦理意义上被指认为“不洁的”诗,因为这些诗中的“不洁”禁止被说出与被写出,那么恰恰是冲破道德禁忌写作的人建立起了汉语的“诗性”。只不过这种非常意义上的有别于传统诗学的“不洁”,在阅读感受上往往给人不舒服、不干净、不崇高、不道德的刻板印象罢了。
陈先发诗歌的自况、自陈、自省语调是非常显豁的,同时这种语调使得他的诗歌程度不同地带有以诗论诗“元诗”的性质。具言之就是那些关于写作本体的关键词时时会出现在诗行里,“我的笔尖牢牢抵住语言中的我”,“我们活在词语奔向对应物的途中”,“它击穿我的铁皮屋顶,我的床榻我的 / 棺椁,回到语言中那密置的深潭里”,“香樟树下,我远古的舌头只用来告别”。显然,元诗的尝试对于诗歌写作者来说无疑具有重要性——这不只是一种诗学阐释,更是对自我写作能力和限囿的检省与辨别。
暮年的杜甫在夔州的瑟瑟秋风中遥望长安自叹命运多舛,他道出的是“寒衣处处催刀尺,白帝城高急暮砧”。而此去千年,一个诗人陈先发在秋天道出的则是“穿过焚尸炉的风 / 此刻正吹过我们”。
在汉语新诗的写作史上,能够留下独特的不可替代的具有汉语新质的“一”,显然是每一个写作者的追求,尽管更多的结果是被集体淹没于沙砾之中成为无名的一分子。显然,如果我们放弃了文学史的幻梦,那么诗歌减负之后直接面对个体生命的时候,陈先发的诗歌让我想到的是他这样一句话:“跟一般失败比较,试图回忆过去就像试图把握存在的意义。两者都使你感到像一个婴儿在抓篮球:手掌不断滑走。”
再次回到这篇文章的开头,你是萤火时代的一道道暗影还是那被刻意缩小的闪电?或者是那个集结了幸运与不幸的掌灯人呢?
注释:
①诗句出自陈先发的长诗《写碑之心》:“又一年三月/春暖我周身受损的器官。/在高高堤坝上/我曾亲身毁掉的某种安宁之上/那短短的几分钟/当我们四目相对/当我清洗着你银白的阴毛,紧缩的阴囊。/你的身体因远遁而变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