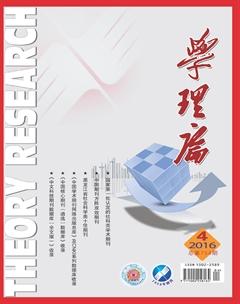曾纪泽使俄前后的心路历程
郑红飞
摘 要:作为中国最早的一批出使西方的外交家,曾纪泽在当时国内风气未开,保守气氛浓重的环境下,能运用西方的外交手段解决伊犁问题实属不易。本文旨在通过分析他从被任命为出使俄国的钦差大臣起,到中俄双方条约签署前后的心理变化,更深入地理解这次谈判的复杂性。
关键词:曾纪泽;心理活动;《伊犁条约》
中图分类号:K25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6)04-0146-03
在以往研究曾纪泽出使俄国签订条约的论文中,大多都把研究的重点放在他与俄国谈判的过程中,较少注意到他在谈判前后的心理活动,这就人为地割断了他从接受任命到条约签订这一整个过程,而他的对俄谈判策略是早在到俄国之前就已形成。因此本文试图通过对曾纪泽在上面所说的整个过程的心理活动的分析,更加深入的理解这次谈判的复杂性。
既然中俄双方是就伊犁问题展开的谈判,因此有必要在这里简单地介绍一下伊犁问题的由來以及中俄之前就这问题进行的几次接触。伊犁有九城,其中惠远城最大,是当时伊犁将军的住地,也是新疆的军政中心。俄国通过签订中俄《北京条约》和《勘分西北界约记》两个条约,割占了中国大片领土,伊犁就直接与俄中亚的领土接壤,而俄国对伊犁也早就垂涎已久,“肥沃的伊犁地区是向东延伸的一个坚固堡垒,并入俄国是相当有利的,因为这样不但极有助于保卫我们的领地,而且还会使中国受到威胁。”[1]只是在等时机的到来,19世纪60年代新疆各地的叛乱就为俄提供了一个绝好的机会。1871年7月,沙俄趁机占领伊犁,为使自己得行为“合法化”,沙俄驻华公使照会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强调“为了安定边境秩序,只以回乱未靖,代为收复,权且派兵驻守,俟关内外肃清,乌鲁木齐、玛纳斯各城克复后,既当交还。”[2]在这之后,中方曾于1872年1月、6月、7月三次和俄方谈判收回伊犁,均被俄国以新疆其他地方未收复为由遭拒绝。到了1878年左宗棠大军勘定南疆后,伊犁问题才又被提到日程上来。1878年6月,清政府决定派遣钦差大臣崇厚出使俄国,商谈交还伊犁问题。次年10月2日,崇厚在未经清政府同意下,擅自与俄方签订了《里瓦几亚条约》《瑷珲专条》《兵费及恤款专条》以及《陆路通商章程》等。其中的主要内容有:“(1)俄国归还伊犁地区,中国将霍尔果斯河以西和特克斯河流域一带割让俄国;(2)俄商在中国蒙古地方和新疆全境免税贸易;增辟中俄陆路通商新线;(3)赔偿俄国兵费和“补恤”俄民共银卢布500万元;(4)增设嘉峪关、科布多、乌里雅苏台、哈密、吐鲁番、乌鲁木齐、古城等七处领事。”[3]360-362这一条约签订后,清政府拒绝批准《里瓦几亚条约》,并将崇厚革职问罪,定为斩监候。同时在1880年2月12日任命曾纪泽为出使俄国的钦差大臣,负责和俄国进行新条约的谈判。曾纪泽,字讦刚,大学士曾国藩之子,以荫补户部员外郎。光绪四年,任出使英法大臣。早在出使英法之前,曾纪泽就对国内各地的教案有着深刻地认识,他认为“办洋务难处,在外国人不讲理,中国人不明事势。中国臣民常恨洋人,不消说了,但须徐图自强,乃能为济,断非毁一教堂,杀一洋人便算报仇雪耻。”[4]334从中可以发现,他是主张用和平的方式来处理与洋人交涉的问题,反对当时国人盲目的排外。此时的他已在西欧生活了将近两年时间,对西方的文明有了更加深入的认识,相比较国内对崇厚及他所签条约一致的反对声,他更能从西方外交惯例的角度来客观的评价。在1880年3月29日与丁日昌的通信中他提到“夫全权大臣与一国帝王面定之件,忽欲翻异,施之至弱极小之邦,然且未肯帖然顺从,况以俄之强大,理所不能折,势所不能屈者乎!”[4]171他此时有这样的看法也不足为怪,因为按照当时的西方外交惯例,这一条约的签订是符合外交程序的。从他的这一看法中也能觉察到这次修约的过程并不会一帆风顺,他在为自己今后的处境而担心。这封信中有句话最能反映他此时的心情,“总署有总署意见,京官有京官意见,左帅有左帅意见,俄人有俄人意见,纪泽纵有画策,于无可着棋之局,觅一劫路,其奈意见分歧,道旁筑室,助成者鲜,而促毁者多,盖不蹈地山覆辙不止也。”[4]171他此时担心的是自己如果在对俄谈判中态度强硬,则中俄两国势必爆发战争;如果他态度不坚决的话,可能步崇厚的后尘,陷入了两难境界。也许信里的最后一句正是反映他此时的无奈,“总之,毁约亦非译署本意,特为言路所迫,而纪泽适承其累耳。”[4]172作为一名臣子本应为朝廷分忧,这也是他的职责所在,没有选择的余地。这里面其实反映晚清外交活动的一个普遍现象:本来在正常的时候,外交家是代表本国政府签订外交协定的,本身并无单独签约的权利,所签的条约也要经过中央政府的批准才能生效。但在晚清,由于中国有为尊者讳的传统,因此那些士大夫们便将本应指向朝廷的矛头转向这些和外国签约的大臣身上,而这些大臣们也成了朝廷的替罪羊,背负着卖国贼的骂名,遗臭万年。
在充分考虑到自己的艰难处境以后,曾纪泽也不是坐以待毙,而是积极寻找应对的办法。在1880年3月29日给总理衙门的回电中,他先把自己对这次出使俄国谈判的一些想法陈述了一次,认为“中国与俄争辩伊犁一案,无论俄人如何不公,如何欺骗,然使臣既已请其国君画押矣,再遣使者数辈,亦断不能挽回,徒助波澜,徒添痕迹而已。”[4]172也就是说这个时候不宜再派使臣去俄,即使去了也不会有任何效果的。不过紧接着他又依据自己这几年对西方外交的了解,提出一个他自认为比较合理的方法,“请一西洋小国评定是非,剖断交易,使因此而原约稍有更改,固属甚佳,即使小国所断仍如原约,无所更改,则我之曲从为以全公义于天下,非屈于势也。”[4]173这个建议在我们现在看来是相当幼稚的,大家可能会奇怪为什么这个时候的曾纪泽和以后在谈判桌上据理力争的他会判若两人呢?从前面他一系列的言语中,我们不难发现在曾纪泽刚得知自己成为使俄的钦差大臣的时候,心理承受的压力之大是可想而知的,因为在他看来这是一件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事情。当然这也和他当时获取的信息量少有关,他在回电的时候还未曾知道他的前任崇厚谈判的细节、所签的各项条款的具体内容以及朝廷对他这次出使的任何指示,心里没有把握,同时可以看出他这时的一系列想法、主张都是基于这么一个前提的:上次中俄双方的谈判是一次正常、平等的谈判。当后来他得知上述条约内容以后,上面的这一前提也就没有了存在的理由。
1880年4月23日曾纪泽收到了总理衙门给他寄来的对崇厚所定条约、章程、专条等的逐条签注及《附议专条》《中俄约章总论七条》共6个指令性文件,并且指示他“此次办法,自以全收伊犁为是。否则,仅议条约,酬予通融,倘能就绪,尚是中策。若俄国不能全交伊犁,且执与崇厚所议约章专条,妄事争辩,或与崇厚所议外,横生枝节,不得就我范围,则惟有随时随事,请旨遵行,宽其时日,缓以图之。”[4]174曾纪泽在了解了上述内容后,自然改变了自己最初的想法,认识到俄国的本质在于剥削和侵略中国,双方先前的谈判并非像自己所认为的那样平等合理,中国损失的权益之大超过他的想象,“卒之还我者不过一隅,而岩险襟带之区,仍复据为己有,复于通商章程,占我无穷厚利,又多留隙,以作后图,其计亦诚巧矣。”[4]173应该说直到这个时候他才真正地深入到条约内容去认识中俄谈判的实质。在以后的时间里,他仔细研究了上次条约的各项细节,并且在这个基础上形成了自己对随后谈判所应采取的策略。1880年5月27日在总理衙门“将约章各条分别可准、不可准及应商三端酬议办法”(也就是具体谈判的办法)到来之前,他向清朝最高统治者上书陈述自己的意见。在这份奏折中他将当时的社会舆论分为两种:主战与主和。对于主战派的意见,他认为俄国“其意不过欲借伊犁以启衅端……我中原大难初平,疮痍未复,海防甫经创设,布置尚未悉周……迄北一带,处处与俄毗连,是有鞭长莫及之势,一旦有急,尤属防不胜防。”[4]26对主和派中主张放弃伊犁的一派,又指出“伊犁全境,为中国镇守新疆一大炮台,细察形势,良非虚语。今欲举伊犁而弃之,如新疆何?更如大局何?”[4]27对主张缓取伊犁的一派,他认为如果疆界不定的话,则中国须在边界派驻大批部队,浪费大量的军饷,同时也延误了海防的建设,对将来国防建设影响巨大。从上述他的言论中可以看出,他是主张运用谈判的手段永久解决伊犁问题,以绝后患,同时又竭力避免双方战争的爆发。接着他又将条约的内容分为分界、通商、偿款三种,强调三者中分界最为重要,通商次之,偿款又次之。他这样划分的依据是根据西方签订条约的习惯,“查西洋定约之例有二:一则长守不渝,一可随时修改。长守不渝者,分界是也。……随时修改者,通商是也。”[4]27-28就是说分界的部分一经签订就不能再修改了,签约的时候也是最困难的,因为这必定是一方受损,一方得益的。相反通商的部分可以双方约定一个时期修改,有什么不利于自己的条款到时可以废除或者更改。之所以把偿款看得最轻,他觉得在当时那种情况下,要想挽回前两部分的权益只能牺牲赔偿。应该说他上面的谈判策略是符合当时国际政治的大环境,俄国是强国,中国是弱国,要全面修改崇厚所定条约是不切实际的,只能抓住关键,牺牲次要的。他为什么会偏偏在这个时候向皇上上这道奏折,其中有什么更深层次的用意呢?从这份奏折呈上的时间来看,正好在总理衙门给他有关这次谈判具体意见来到之前,他在这时可能已经意识到总理衙门可能会把崇厚所定条约的大部分条款均予以驳斥,给他接下去与俄国谈判留下周旋的余地太少,谈判难度增加。后来收到的总理衙门给他的指示是,“应坚持收回伊犁全境,坚持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中划分塔尔巴哈台、喀什噶尔边界的规定;不得同意俄商經嘉峪关取道西安、汉中到汉口贸易和俄商行船松花江至伯都钠沿途贸易的要求,也不得同意俄商在天山南北两路贸易不纳税的要求;再次要求俄国引渡白彦虎等;可同意俄商前往嘉峪关贸易,并准俄商在沿途之哈密、巴里坤、古城指定一处进行留货贸易;准俄商在嘉峪关设领事;嘉峪关贸易可减税三分之一;同意赔偿五百万银卢布;同意原约中伊犁居民‘愿迁居俄国入籍者,均听其便的规定。”①把这个指示和曾纪泽前面的意见相比较可以发现,两者在维护领土方面是一致的,均坚持收回伊犁全境;在通商方面,总理衙门只允许做一点让步,和他所主张之间有一定的距离;在偿款上,总理衙门只同意维持上次谈判的数额,这显然和他主张的应增加赔偿数额的建议恰好相反。如果按照总理衙门的指示进行接下来的谈判,在他看来难度太大,但又不便明着和总理衙门作对,因此在奏折的最后他提到“若臣言力争分界、酌允通商之说稍可采,则在廷诸臣自必考究精详,斟酌尽善,乃定准驳之条;即臣说全无是处,通商各条必须全驳,臣俟接准总理衙门文牍,自当恪照指驳之条,逐一争辩。”[4]29表面上自己一定会遵照这个指示与俄国谈判,实际上是希望自己的主张能得到最高统治者的支持,以便在谈判中能按照自己事先的策略进行。从后来给他的回电中提到的“如有应行量为变通之处,仍当随时察看情形奏明请旨。”[4]31这一句看来,此举还是得到一定效果的,至少让他有了回旋的余地。
到俄国以后,他于1880年8月24日照会了俄外交部,根据总理衙门给他的指示提出了修改崇厚所定条约的6条要点:“(1)交还伊犁全境;(2)塔尔巴哈台、喀什噶尔边界,按《勘分西北界约记》规定,如实有小处须酌改,应由两国特派大员查勘而定;(3)俄国要求嘉峪关通商,尼布楚、科布多增开商路,如第一条议定后可允许;(4)除嘉峪关可设俄领事一员外,其余留待以后酌议;(5)哈密、巴里坤、古城,俄国可择一处进行留货贸易,如张家口例;(6)新疆贸易,不比沿海地区,如处处免税,则中国吃亏甚重,尚须商量办理。”[5]这一方案遭到了俄国方面的拒绝,并且威胁要派代表去北京谈判,这显然击中了清政府的要害。得知这一消息后,总理衙门连忙给曾纪泽来电,“面奉谕旨,俄事日迫,能照前旨争重让轻固妙,否则就彼不强中国概允一语,力争几条,即为转圜地步,总以在俄定议为要各等因。”[4]41清政府在这个时候是彻底屈服了,放弃了先前那些不切实际的谈判建议,把这次谈判的权力完全交给了曾纪泽。这点可以从他和总理衙门的电报中可以看出,他于1880年8月29日给总理衙门汇报最后一次谈判情况后,一直到1881年1月24日谈判基本结束后才和总理衙门汇报情况,而这段时间正式谈判的关键时刻。这可以说是这次谈判的转折点,因为从此以后曾纪泽可以按照先前制定的策略来与俄人周旋,谈判的手段也较以前灵活许多。1881年10月2日双方重开谈判,他决定在通商、偿款方面继续做出让步,同时在分界的问题上面也做少许的让步,放弃伊犁西部的少许领土,坚持收回具有战略意义的特克斯河流域,再遭俄国的拒绝。谈判继续往后推延,直到1881年12月27日俄外交部给他送来两件照会,节略一件,等于给他下了最后的通牒,他于是把这次的内容发给了总理衙门。到1881年1月16日接到了总理衙门电报,认同了条约的内容,“览来电均悉,该大臣握要力争,顾全大体,深为不负责任,即着照此订约画押,”[4]46到此可以说他这次任务基本完成,中俄双方在1881年2月24日正式签订了伊犁条约,主要的内容有:“(1)俄国将伊犁地方归还中国;中国将霍尔果斯河以西、伊犁河南北一带地方划归俄有;根据本约规定的界线,在塔尔巴哈台地区‘酌定新界;在喀什噶尔地区‘照两国现管之界勘定、安设界碑。(2)中国赔款900万银卢布,限两年内偿清。(3)俄商在蒙古地区贸易照旧免税,在新疆各城贸易‘暂不纳税;准俄商前往肃州贸易,由俄国运入该处的货物,按旧例减税三分之一。俄商贩货由陆路运入中国,可照旧经张家口、通州前赴天津,或由天津运往别口和内地市场销售;俄人得在设领各城及张家口建造铺房、行栈。”[3]381-385该条约的内容大致与曾纪泽使俄之前所制定的策略吻合,从中也可以看出他在谈判中关于具体条款的制定及任何的让步都是有原则的,就是他所说的分界要力争,通商和偿款问题可以灵活处理。这一点长期的为人所忽视,只看到了他在谈判过程中就具体某一条的力争,而没有看到他在出使俄国之前的活动,殊不知这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人为割断后并不有助于我们更加深入地了解这次谈判过程。
在条约签订后的次日,他向皇上陈述这次签约过程中的艰难之处,总结有六条“(1)西人待二等公使之礼,远逊于头等,而视定义复改之任,实重于初议。(2)按之万国公法,使臣议约,从无不候本国君主谕旨……屡以崇厚违旨擅定之故晓之,奈彼闻所未闻,始终不信。(3)原约所许通商各条,皆布策驻京时向总理衙门求之多年而不可得者……彼随据为已得之权,再经熟商,彼即市其莫大之惠。(4)传播失真之语,由于译汉为洋,锋棱过峻之词,不免激羞成怒。(5)无怪一言不合,俄使即以去留相要。(6)故随由电请旨,非旬日所能往还,敌廷之询问愈多,专对之机权愈滞。”[4]51-53在这个时候上这道奏折,充分体现他对当时清政府负责的态度,他知道国内的那些保守大臣们会以这次签约签订为契机,看到西洋各国并无想象中那么可怕,他们自己在国内的高声呼吁还是有效果的,把谈判成功的功劳全往自己身上揽,混淆视听。曾纪泽在这时提醒他们,双方谈判并非他们认为得那么简单,以后和西方各国的交往还得以诚相待,不要轻言战事。可惜的是国内大多数人并没有领会到他得用心良苦,而且西方各国也并非如他想得那么公正,紧接着清政府面临了更大的外交危机,而再也没有像这么成功的谈判出现,有的是更加多的不平等的条约。他的意见并没有挽救清政府,这应该说是他那一代外交家的悲哀。
参考文献:
[1]库罗巴特金.俄日战争的总结[M]//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沙俄侵华史: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228.
[2]新疆图志:第54卷·交涉志[M]//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沙俄侵华史: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251.
[3]王铁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1册[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2.
[4]曾纪泽.曾纪泽遗集[M].喻岳衡,点校.长沙:岳麓书社,1983.
[5]曾纪泽.金轺筹笔:卷1[M]//王希隆.中俄关系史略:一九一七年前.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1995:270.
[6]王希隆.中俄关系史略[M].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19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