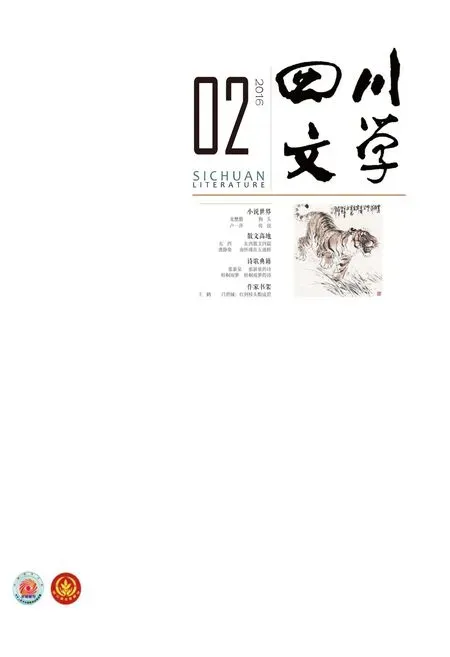东西散文四篇
东 西
东西散文四篇
东 西

东西,原名田代琳,1966年出生于桂西北,被评论界称为“新生代作家”。主要作品:长篇小说《耳光响亮》《后悔录》《篡改的命》;中短篇小说集《没有语言的生活》《救命》《我们的父亲》《请勿谈论庄天海》《东西作品集》(六卷)等。部分作品被翻译为法文、韩文、德文、日文、希腊文和泰文出版,多部作品被改编为影视剧。中篇小说《没有语言的生活》获首届鲁迅文学奖;长篇小说《后悔录》获第四届华语文学传媒盛典“2005年度小说家”奖。广西民族大学住校作家。
德保,纯美的壮乡
从南宁出发,往西南笔直而行,三个多小时的车程就到了德保县。各地的县城大同小异,长方形的水泥盒子、不宽不窄的马路、一家接一家的店铺……如果不是有人提醒“德保到了”,我还想给这地方随便取个什么名字。但是,第二天清晨,我就发现了自己的草率。
推开窗,首先看见的就是城西北的独秀峰。它高高地站在钢筋水泥房中间,像一座标志性建筑。必须把后脑勺全部贴到脊背,才能看到山顶。山壁是灰白的岩石,岩石上恰当地点缀一篷篷绿树,仿佛上帝的盆栽。半山腰上,有一古建筑,后来才知那是观音阁,始建于乾隆五十五年(公元1790年)。此阁在200年间,因人类文化观念的变化而数次遭遇折腾,仿佛今天城市的拆迁,推了建,建了推。到了1981年,有关部门在原址上建了叠翠亭和回廊。它们伸向空中的翘角和瓦檐,就像文化商标,给我以连续的遐想。原以为只有桂林才是“山在城中、城在山里”,到了德保县城方知,这八个字不仅仅是描写桂林的专利。县城的北边有后龙山、古恒山、北屏云山,东边有芳山……可怜无数山,实在数不清,它们围在县城周边,模仿羊群奔跑的姿态。
这已经算得上是一座不平庸的城了。但是,它偏偏还有一条穿城而过的鉴河。这条最终流入右江的河流,在德保县境内绵延70公里。县城,只是它经过的地方。正是它的经过,使德保这座城一下就有了灵气。早餐之前,我沿河走了一段,发现水是透明的,可以饮,可以泳,定神一看,水里还有鱼。在许多城市都把途经河流当成垃圾传送带的今天,能在建筑群中看到如此清澈的水,我的心不禁为之“呯呯”,并以此判断这里还是一片净土。
接下来的旅游,终于证明了我的判断。不管是在燕峒乡看矮马,或是在巴头乡看红叶,或是在小西湖看水……空气是清新的,树叶一尘不染,河水超级透明。在我经过稻田和水渠的时候,皮鞋难免夹带泥土,甚至偶尔也会被牛屎追踪,但这不会给我“脏”的信息,反而强化了“净”的概念。只能说明,我的旅游观念升级了。曾经,我把旅游理解为看名胜,结果发现凡名胜之地,必人头攒聚、摩肩接踵,最终不得不把看景变成看人。后来,我转信王安石。他在《游褒禅山记》中说:“世之奇伟、瑰怪、非常之观,常在于险远,而人之所罕至焉。”这绝对是旅游的真理,特别是在人口众多的中国,只有险远之地,游人少去的地方,才会有美景完整地保留,才会有洁净的空气让我放心呼吸,才会有安静的空间让我闭目享受。而德保恰恰可以满足以上各项要求。这里的风景点没有别扭的建筑,全部都是纯自然,包括歪斜的小路、粗糙的木栅栏;这里没有瞎编的民间故事,看山是山,看水是水,看树是树。你只管往前走,没有太明确的目标,不必担心太著名的景点被遗漏,伸手可以拔草,俯身可捡红叶,高兴时还可以就地打滚。亲近自然是人类的天性,难怪加拿大一少年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要向他们的立法机构申请在草地上打滚。为他,加拿大竟然取消了这一禁约。
德保县境内聚居着壮、汉、瑶等九个少数民族,其中壮族人口占97.8%。在这里,其它民族只是小小的装饰。壮族村寨的建筑大都是干栏,分三层,下面关牲口,中间住人,楼上堆放粮食。堂屋里摆着织布机,那些以蓝、黑、灰为主色调的服饰,都是壮家女人们织出来的。虽然我在各种晚会的舞台上,看见过壮族艳丽的服装,但到了德保一比对,才发现舞台上的那些服装都是加工过的,颜色和式样既鲜艳又夸张,相当于蔬菜放了化肥,猪肉加了激素,已经不是原汁原味。那种纯棉的手感,那种与皮肤的亲密妥帖,只能从德保壮家的织布机上织出来。由于这里是清一色的民族,各种风俗保存得较为完好。开耕、播种都有仪式,婚嫁迎娶非常讲究。有时不经意地一瞥,你会看见人们在田间地头祭青苗。屏气凝神之际,你会听到山歌像雨一样远远地飘来。壮族青年谈恋爱,依然以对歌为主。人群只要聚在一起,立即就能形成歌圩。这里还保留着“答歌为婚”的风俗,青年人如果不会唱几嗓子,那就有沦为“剩男剩女”的危险。
壮民族一直具有包容性。某些地方的壮族已经汉化,他们说卷舌音,穿西装打领带,本民族的信息在他们身上渐渐弱化。但德保的壮族却一直完整地保留着本民族的特性,包括饮食习惯。他们是壮民族的活标本。因为他们纯正,这里的风景才纯正。从古至今,天空还是那么湛蓝,地上还是那么茂盛,就连空气也是原生态的。
德保县的南面与越南毗邻,是地地道道的边疆。
济南旧颜
人的年龄越大,就越喜欢老的物件。仅仅是因为怀旧吗?我想还有原因,那就是老的物件可以衬托人的年轻,包括古老的城市。
济南这座城到底有多老?只要看看路边的指示牌你就知道。什么舜耕路、舜井,什么历山门、千佛山、趵突泉、大明湖、李清照故居……一个个名字像锥子似的,夹杂在济南惨案纪念堂、解放路、民生大街等等指示牌中间,冷不丁地吓人一跳。
所以,不管现在的济南如何崭新,我都假装不看,脑海里只有一个想象的格式化的济南,它“户户泉水、家家垂柳”……于是,便穿街过巷去找。在友人的陪同下,先到了上新街。本街在民国初年形成,青砖铺路,墙壁斑驳,一些门楼和大院还在。当年这里名流政要云集,学者、高官、洋务代办、民族企业家,像老舍、方荣翔、黑伯龙等人的故居均位于此,曾是老济南的文化政治中心。
老舍故居是个精致的小小院落,有展示厅、厨房、卧室和书房,院里有口老井。上世纪30年代,老舍先生执教于齐鲁大学,在此居住四年,写下了有关济南的大量散文。济南的山水,济南的城市,济南的春夏秋冬都被他毫不保留地赞美,甚至赤祼祼地向读者发出邀请:“设若你的幻想中有个中古的老城,有睡着了的大城楼,有狭窄的古石路,有宽厚的石城墙,环城流着一道清溪,倒映着山影,岸上蹲着红袍绿裤的小妞儿。你的幻想中要是这么个境界,那便是个济南。设若你幻想不出—许多人是不会幻想的—请到济南来看看吧。”(引自老舍的《一些印象》)。我对济南的大部分想象,均来自他的描写。因此,要看济南,就先到这里报个到。毫无怀疑,他的文字是诚实的。但毕竟80年过去了,他描写的那个诗意的济南,只能碎片化地存在。
上新街51号,还保留着一个大大的老院子,这是“世界红万字济南母院”,又叫“济南道院”。始建于1934年,竣工于1942年,是济南近代建筑中规模最大的仿古建筑群,前后共有四进院落,沿中轴线依次为照壁、正门、前厅、正殿、辰光阁等主要建筑,两侧东西厢房以廊连接。院子里有大树,有亭子,有石碑记载建院经过。日伪期间,有善男信女问老祖什么时候抗战胜利?老祖说等道院全部落成,日本人就会撤离。为兑现这句诺言,道院后的“辰光阁”落成后,一直没有粉刷,直到现在。红万字会的宗旨以道教为主,信奉自己所创造、能超越各宗教的“老祖”,主张儒、道、佛、伊斯兰、天主教五教合一。不得不承认,这是一个创新,貌似“结集出版”,其实需要胆量和飞扬的想象力。而这样的想象就发生在济南的上新街,它再一次证明此地专门出产奇思妙想。
还有点小资。不信你到“小广寒”去看。位于济南市经三纬二的“小广寒”,是德国人于1904年兴建的电影院,它比北京、上海的电影院都建得早。现在这里已改成餐厅,木地板是当年的,跺跺脚就像踩着自己的高祖。每间屋角都摆着一些跟电影有关的器具,比如各式各样的放影机。二楼大厅可以一边吃饭一边观影,都是老电影,可以点播《列宁在1918》之类。一楼的边廊和天井摆着西式桌椅,最适宜恋人聚谈。“一杯红酒配电影”,唱的就是这里吧。
正是“小广寒”兴建的这一年,即清光绪三十年四月一日,济南奉准自开商埠,允许洋人和中国人并处这一次“开放”,中外商人纷纷在此设立商行,经营各种土洋货贸易。商埠区外国人修建了不少洋房,虽然历经战乱,但仍可在高楼大厦间偶然瞥见白墙红瓦。一些济南老字号也已修复使用,像“宏济堂”早就恢复了号脉抓药,甚至成了旅游景点。
最后,去了曲水亭街。这里泉声不息,杨柳垂岸,一排排老房子保存得较为完整。有人在泉池游泳,有人在泉井里取水,几只白鹅逆流而上。顺水望去,大明湖近在眼前,岸边柳枝成片。水是城市的血脉,树是城市的头发。原来,济南血脉通畅,头发茂密。
也许我在寻访老济南时,忽略了另一个济南。那个济南年轻,充满活力。但是,大凡写文章的都有一个悖论:他们的身体喜欢住在新建的高楼大厦,享受现代化的种种便利,心灵却要飞向古老的街道寻找诗意;他们喜欢炫耀城市的历史,却又害怕它血管堵塞,头发脱落,甚至偏瘫。所幸,济南高龄还生机勃勃,崭新还保留旧颜。
寂静的山群
远远地就看见一座座山,很高,很尖,很密。山体是石灰岩,地貌是喀斯特地貌。除了山麓的耕地是庄稼的颜色,其余都是绿,像一层厚厚的苔藓,绿得深,绿得重,或者就是墨绿。那些墨绿是灌木、草和藤,它们紧紧抓住石缝里有限的土壤,拼着老命生长。有些灌木的根扎在悬崖的半壁,身体却一路攀升直冒出崖顶,去跟别的植物抢阳光。于是,紧紧贴着崖壁的一根根木就像一根根藤,为了生存不得不变异。正是这些以亿计以兆计的细小植物们勾肩搭背,才织成了一张张绿色的网,像衣裳那样把山结结实实地裹住,生怕它走光。
夹道的山都有一千米以上的高度,每一座山都像一座塔,独立地戳在哪里,只有底部相连。要想望到山巅,就得让后脑勺贴着脊背,把目光一点一点地抬上去。当看到白云蓝天的时刻,也就看到了山顶。山顶尖得像刀削似的,已经刺破云天。没有鹰,只有飘着的云和透过云层的阳光。因为山的洁净,天就显得更蓝,仿佛水洗一般。好像也没有虫鸣鸟唱,只听见嘭嘭的心跳。
静啊,真静!
山是密密挨着的,又高又多,因此就挡了视线,就有了狭窄感,跟着就有了孤独。把这种孤独慢慢地洇,也许就有了绝望,仿佛与世隔绝。忽地回头,发现来路在坳口拐了弯,看得见的只短短一截,找不到伸向远方的意象。对面的山上,有一条曲曲折折的小径,像蛇行草丛。顺着小径的台阶往上爬,气越喘越粗,腿愈行愈抖,很快就汗流浃背了。但歇了歇,又往上走,好像是检验自己的体质,又像是闷住的鱼要把头伸出水面。
终于登上了五百来米的山巅。一眼望去,顿时惊呆。上千座、感觉是上万座巨峰一下就撞入眼帘,它们排过去拥过来,像大海的波涛在起伏。地球仿佛都被它们颠晕,以至于不知道是山头在晃或是腿在晃?我看到了一种气势,看到了一种比天空还要宽的宽。山在这里集结,变成了山群,一直连到天边,和白云霞光融为一体。因为是大面积的峰丛,如果以山尖为水平线,能隐约看出地球的弧型。每座山都不偷懒,都是亲自拔地而起,因而就像集结的部队,就像在做团体操。不仔细分辨,它们都是山。稍加注意,便发现它们各有各的姿势,各有各的表情。如果不是因为地壳运动,就算是上帝想把这么多山堆在一起,也会感到力不从心。张家界和这里比起来仅是盆景,华山和这里比起来只是一座。这里是一片、一大片,是山的海洋,绿的海浪。
久久地看着,只有云,只有蓝天,与山群为伴。
尽管气势磅礴,但它们还是太寂静。一片阳光投射下来,只照着某座山的半张脸,但群峰侧目。一只蚂蚱振动翅膀,仿佛音乐,它们都竖起了耳朵。一场雨落在某个山头,群山都像洗了澡。是不是因为太遥远所以寂静?是不是因为太辽阔所以无声?因为寂静,山群显得更为辽阔。因为无声,孤独变得无边无际。从前,只晓得草原宽广,只懂得沙漠广袤,只知道黄土高原天宽地厚,今天才发现,原来喀斯特地貌的山群也可以宽阔无边!正在孤独的时刻,远处的山丛升起一柱炊烟,那是农家烧饭的信息,山间立刻就有了烟火气。再细看,崇山峻岭间竟有小路盘旋。没想到,在这么陡峭的山崖竟然生活着布努瑶。更没想到,红水河就隐身其间,从这些坚硬的山群穿过。
忽地,一曲瑶歌传来,山里终于有了声音:可爱的芝巧帮呃\山遥又水远\路险又山高\五个月没有一次相会\十个月没有一次见面\两只鹞鹰住两山\两只虾公游两泉\两颗星星各照夜\两把弓弩各根弦\望花再把蜂蝶引\望桥重把道路连……可爱的芝托帮呃\两只斑鸠相会在珍珠坡\两只画眉相逢在莲花岭\两只鱼儿同游一池\两只凤凰共一林\如果你有金子一般的心\请用欢乐的歌声\来温暖我这冰凉的心……
歌声久久地回荡,在静静的大化县七百弄山群。
梦 游
提着一口巨大的箱子,我来到了珠海。
码头,一艘战舰迎接我,似乎要去打仗。小心地上了战舰,发现甲板上有四门大炮,分别指向前后。进了舰舱,都是熟悉的面孔,是一群平时只打嘴巴仗的作家。他们来这里干什么?我为什么要来这里?正在纳闷,有人摆上扑克,爱打牌的都围上来。茶几不时摇晃,周围的身体忽左忽右。战舰起航了。围观者三三两两地出去,整个休息室只剩下打牌的。牌桌上明争暗斗。心想,这船不会是去黄岩岛吧?
船的速度比思想还快,只眨眼工夫就钻进了万山群岛,停靠在桂山码头。拖着箱子出来,发现天海一片湛蓝,波浪轻晃,战舰小得像一只摇篮,人小得像只蚂蚁,箱子被蚂蚁提着。即便是桂山这么大的岛,也像是搁在汪洋中的一块糖,给人以随时都可能被融化的错觉。海太平了,海太宽了,如果没有类似于桂山这样的岛屿,我不仅没有方向,甚至连整个人生都会迷茫。糊里糊涂吃了一顿海鲜,又提着箱子上船,往下一个岛行去。
在甲板上看海,除了蓝还是蓝,蓝得都有点不太真实。想想陆地上酸涩的空气、混浊的污水、地沟油、有毒胶囊和三聚氢胺奶,立刻就觉得自己来对了,应该在这里呆上一辈子。风徐徐扫在脸上,每一口都舍不得放弃。海上有这么好的空气,难怪“1900”不愿意上岸。“1900”是电影《海上钢琴师》的男主角,他一出生就被遗弃在船上,由烧炉工收养。他无师自通,练成一名钢琴师,尽管有初恋情人的诱惑,有经纪人到岸上去弹琴的煽动,但他对红尘俗世深怀戒意,宁肯死在船上也不敢踏上陆地半步。想着想着,在梦里睡去。醒来时,又到了一座岛,不知道它的名字,反正是万山群岛中的一座。大家坐下来,人影浮动,有东北的、上海的、贵州的、湖南的、江苏的和北京的……
糊里糊涂过了一夜,第二天一早又上船。中午,到了一个叫东澳岛的地方。田瑛说去年此时,他在这里协商笔会,忽然接到我的电话,便约定今年必须来。我不记得打过电话,更不相信这种巧合。于是,坚信我在梦里。但田瑛的声音那么真切,并伴之以鱼的美味。在喋喋不休的劝酒声中,我躺到一棵树下。树冠如盖,遮住阳光。凉风吹来草香。这么躺了一会,屋里的人都出来了。他们在阳光的直射下红光满面,相互搀扶,走下长长的台阶。一个叫朱燕玲的女子忽然一闪,脚崴了一下。我听到她在责怪,说是我劝她喝多了。我劝过她吗?怎么不记得了?
一群人看过灯塔,陆陆续续地走到一处小海滩,弯腰捡宋朝的瓷片。有人捡到了,惊呼。有人没捡到,就爬到礁石上拍照。我在一把躺椅上打盹,独享阳光和海风,听时间静静流淌。多少年了,我总是从电脑外壳的老化来判断时间的流逝,感知季节的更替,舍不得花时间到大自然里呼吸、聆听。来了东澳岛,才知道自己犯了多大的错误。真闲啊,这一刻,把平时的工作、合同、应酬、牢骚、甚至感情都放下,像局外人那样打量着大海,身心彻底地松弛,更像勒·克莱齐奥笔下的“自然人”,慢慢地变成了植物或地衣。旁边,一个作家的声音时断时续。他怎么也会在我梦里?捡瓷片的人回来了,我跟着他们一起去另一处海滩。这处海滩较大,有人在游泳。山崖边正在建房子。带路的说那是正在建设中的休闲度假宾馆。说话间,五星级宾馆拔地而起,灯火璀璨,木廊石阶历历在目。是幻觉或是穿越?
万山群岛共有150多个岛屿,像上帝撒在海上的豆子,这里一颗那里一粒。我在高密度的岛屿之间穿行,已经忘却日子。记不得是哪一天,我来到某个岛上的浮石滩,滩上全是圆鼓隆咚的巨石,像大型动物的蛋那样摞在一起,一大片。无法想象它是怎么形成的?是谁把它们搬到这里来?坐在那些石头上,臀部一直有麻酥酥的感觉,生怕会从石蛋里孵出怪物来扰乱地球。但是,空气仍然是好得不行,舍不得马上离开,冒着孵出怪物的风险也要在那里坐上好长一段时间。海浪轻击石岸,卷起细白的雪花。涛声时强时弱,把耳朵拍得十分舒爽。记不清怎么离开,又怎么钻进了一条长长的隧道?隧道是原来的军事基地,现在开放了。在隧道里走着走着,就走到了外伶仃岛……
醒来时,我躺在自家的别墅里。推开窗,外面就是大海,就是一片平展展的水做的土地。涛声阵阵,海天一色。跑马溜溜的海上,一朵溜溜的云。我被干净包围,被悠闲包围,被一种莫名其妙的幸福感包围。记不得什么时候住进来的?怎么会有这么一栋别墅?正想着,有人拍门,说出发了。一击脑袋,才知道还在岛上,但已经把梦做回家里了。如此错乱的逻辑,只会发生在梦里,只会发生在纤尘不染的岛上。我拎着箱子出门,真不愿意离开。
多少天之后,我跟夫人说自己梦游了一次万山群岛。她说你真的去过,不信看看你的微博。上网一查,微博上有我躺在岛上的铁证。原来美的地方都像梦境,差的地方才叫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