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治·奥威尔:潦倒巴黎伦敦
许志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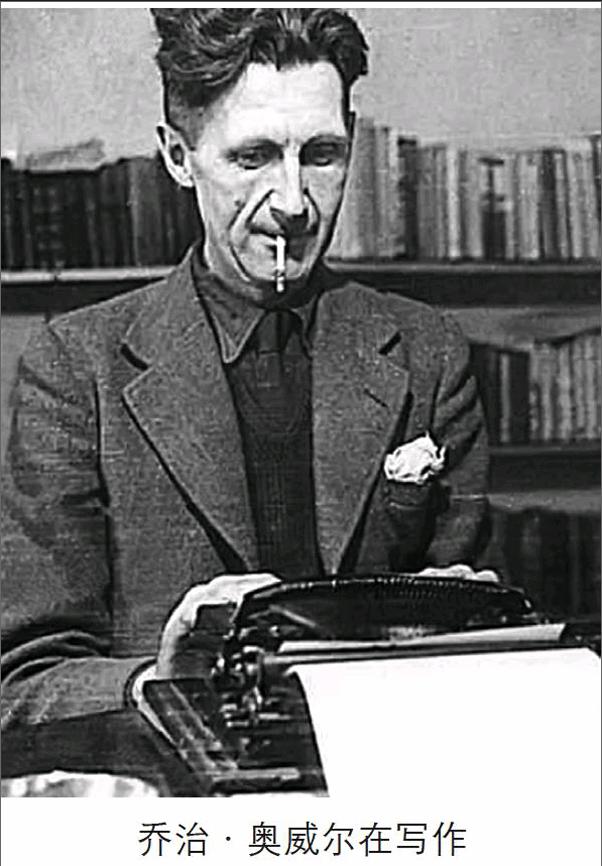


一
上世纪二十年代去巴黎流浪的文人艺术家,几乎都有一段贫穷落魄的经历。吃了上顿没下顿,千方百计拖欠房租,硬着头皮进当铺,和穷人、酒鬼为伍……何止是巴黎,任何地方,穷艺术家的日子都是难过的。像毕加索,穷到冬天烧画布取暖,简直是没辙了。相比之下,保罗·奥斯特的自传《穷途,墨路》(于是译),其描述的境况堪称优越。穷途也者,穷字当头,其物质性贫困首先就令人不堪承受。有人说毕加索穷归穷,还是要画画要做爱。但毕竟是饿着肚子画画做爱。这个方面乔治·奥威尔是深有体会的。说起流浪艺术家的贫穷经,他不忘引用乔叟的话,“贫穷之境况,害人真不浅”。究竟是怎样害人法,他写了本书说明,写他在巴黎伦敦辗转流浪的故事,所述种种细节,都离不开一个穷字。
他说一旦遭遇贫穷,就不得不掉入“谎言之网”。碰到卖烟的,问你为什么烟抽得少了,碰到洗衣妇,问你衣服是否送去别处洗了,你都支支吾吾讲不清。吃饭时间装作出门去餐馆用餐,其实是去公园看鸽子。反正整天要撒谎,并且为谎言付出代价。去面包店买一个法郎一磅的面包,女店员切了不止一磅,而你口袋里只有一个法郎,想到有可能要多付两个苏,只好落荒而逃。街上遇见混得好的朋友,赶紧躲进咖啡店,而进咖啡店就得花钱,你用剩下的一点钱要一杯黑咖啡,里面却掉进一只死苍蝇。人一穷,倒霉的事也会多起来。等到每天连六法郎花销都难以保障,活着就纯粹是“难挨加无聊”了;因为填不饱肚子,在床上一躺就是半天。见到商店橱窗的丰盛食品,“一种几欲泪下的自悲、自怜感袭上心头”,想抓起一块面包就跑。有这种念头是很自然的,没这么做是因为胆小。要知道,连续一星期吃面包和人造黄油,人就不成其为人,“只是一个肚子,附带几件器官”。饥饿,卑怯,无聊,像波德莱尔诗中所说的“年轻的骷髅”,这便是贫穷赐予的东西。
当时同在巴黎,海明威、亨利·米勒也都受穷,读一读《流动的盛宴》和《北回归线》便可得知。可以说,海明威描写的贫穷是浪漫的,奥威尔的却是辛酸的,亨利·米勒的则是浪漫和辛酸兼而有之。从他们的自传性作品看,奥威尔对贫穷这个主题的描绘最为集中,其流浪艺术家的境况最为不堪。《巴黎伦敦落魄记》(孙仲旭译)揭示物质性贫困施加于生理和精神的作用,堪比挪威作家克努特·汉姆生的《饥饿》。汉姆生写的虽是小说,而且是颇富想象力的小说,可那种饿得想吃自己手指的细节,怕是有实际体验为基础的吧。
奥威尔在巴黎住了两年(1928-1929)。此前他辞去帝国警察的公职,打算搞写作,此举遭到家人反对,他便只身前往法国,做起了流浪艺术家。他有积蓄,有时教英语贴补用度。后来不幸染上肺炎住院治疗。医院公共病房这段凄惨经历,在其《穷人如何死去》(1946)一文中有动人的记述。出院后又遭到抢劫,也真是倒霉。旅馆房客中有一个自称是排字工的意大利小伙子,配了多把钥匙,洗劫了众人的房间。奥威尔的财产只剩下口袋里未被掏去的四十七法郎,他在巴黎的日子便十分落魄了。
落魄并不仅仅是指每天靠六法郎为生。对中产阶级知识分子来说,沦入底层而与穷人粗人为伍,这才是更不堪的境地。说到这一点,奥威尔的独特之处便显示出来了。他去巴黎是搞文学,其间写过两部小说,可他基本上不和作家、知识分子来往。巴黎乃人文荟萃之地,固然不是穷人的天堂,却是文人艺术家扎堆冒险的福地,比在别处都更容易获得成功,否则不会有那么多人争着去过那种忍饥挨饿的生活了。奥威尔去巴黎没有追求浪漫和时尚,而是混迹于乞丐、游民、妓女、酒鬼、劳工中间,与所谓的“被社会排斥者”(social outcasts)为伍。他在自己那个阶层几乎没有朋友。虽说穷困潦倒是出于无奈,可他对物质境遇的改善确实也抱着无所谓的态度。他的生活方式是有些怪异的。一个审美的纨绔子弟,亦即具备良好艺术感觉的人,恐怕只有在左拉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意义上才会接受辛酸龌龊的生存,而左拉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又何曾是像他那样,饿得比旅馆里的臭虫都不如。总之他流落底层,实实在在体验了穷困的滋味。
他住的旅馆房间,“墙壁极薄,只比火柴盒厚一点儿,为了遮住缝隙,墙上用粉红色纸糊了一层又一层,但是已经松脱,里头臭虫藏得密密麻麻。靠近天花板那里,整天有长长的臭虫队伍在行进,像是一队队士兵。夜里就下来了,像饿死鬼一般,让人不得不每隔几个钟头就起来对它们大开杀戒。有时臭虫闹得太厉害,房客会点硫磺把臭虫熏到隔壁,这样一来,隔壁的也会以牙还牙地用硫磺熏他的房间,把臭虫再赶回来……”
房客不比臭虫体面多少。“有一对夫妇四年没换过衣服,他们的房间臭得从楼下那层就能闻到。”房客主要是外国人,来来去去尽是些古怪角色,组成贫民窟离奇污秽的“众生相”。巴黎贫民窟并非新生事物,在欧仁·苏、巴尔扎克、左拉(甚至狄更斯)笔下就有过大量描绘,而奥威尔熟悉的外籍流民生活,此前的作家鲜有涉及。例如酒店洗碗工,这个职业就没有被好好描述过。巴黎饭店的厨房佣工清一色是外籍流民,其生存状况少为人知。奥威尔走投无路时在两家饭店做洗碗工,每天干十一或十四个小时,挣二十五个法郎。在厨房干活像是置身于但丁的地狱:
……来到地下一处狭窄的过道,那里低得要弯着腰,热得让人透不过气来,还很暗,隔几码才只有一个昏黄的灯泡。那里像是阴暗的迷宫通道,有几英里长—事实上,我想总会有几百码长—奇怪地让人想起大客轮上靠下面的几层,二者同样既炎热又狭窄,食物热气腾腾,厨房锅炉如发动机一般发出隆隆噪声。我们经过几个门口,不时听到一声咒骂,或者看到火炉的红光,从冰库里还吹出一阵叫人发抖的穿堂风。
洗碗工是酒店里最低贱的工种,其秽恶让人不堪忍受,但总比躺在床上饿肚子好。《巴黎伦敦落魄记》的巴黎篇章写得最详细的是洗碗工的部分。奥威尔的英国口音和小胡子与周遭环境有些格格不入,而这只能更加突出他潦倒的境遇。
英国人在国外通常被视为体面人,像他这样在巴黎做洗碗工是够沦落的。而一个人饱尝失业和饥饿的滋味,也就顾不得体面了。落魄也有给人安慰的一面:“知道自己终于真正到了穷困潦倒的地步,会有种如释重负的感觉,几乎感到愉快”;“可以说身上越没钱,越是少担心……你浑身上下只有一百法郎时,你会吓得魂不附体,等到你只有三法郎时,你就很是无所谓了。因为三法郎会让你直到明天还有吃的,你也不可能考虑明天以后的事”。
若非亲身经历,不会有此心得。
然而,贫穷像麻醉药一样渗透全身时,人们对这种处境的特殊性是没有意识的。即便你是一个艺术家或观察者,也不能减轻这种处境在你身上的效用,除了屈从于它的既像是麻木又像是极乐的感觉,不会再有额外的伤害或补偿了,而这种状况在任何乞丐和流浪汉身上都会有所体现。丧失体面也就丧失了欲望,丧失了正常的一切。
奥威尔写出了贫穷的状况及危害,书中形形色色的人物和细节莫不告诉我们,被遗弃的境地最像是一剂麻药,人们首先是透过那层药效感受自我的,每个流浪汉都是如此。在伦敦收容所,奥威尔半夜被同屋弄醒,那个手无缚鸡之力、邋遢猥琐的家伙居然想跟他搞同性恋,被制止后便乖乖顺服了。他怕的并不是奥威尔的拳头,也不是内心的羞惭,实质是他对这种处境中任何额外的羞辱或补偿已经没有感觉了。
二
《巴黎伦敦落魄记》揭开底层生活鲜为人知的一角,其形象和细节新颖,描述栩栩如生,从写作角度讲是很有原创性的。
奥威尔在《我为什么写作》(李存捧译)一文中宣称,“好文章就像一块窗玻璃”,“如果作家不能持续努力地抹掉自己的个性,那他所写的东西就没法读”。也就是说,他崇尚清晰、准确、客观。成熟的奥威尔文体便是如此:具象的画面,清澈冷静的短句,精准的细节,有着上乘的新闻体写作所具备的优点。但他的语言从来都不像是“一块窗玻璃”那么简单。
以《巴黎伦敦落魄记》为例,此书讲述凄惨的贫困和绝望,让人感同身受,但无可否认的是它的叙述相当有趣,甚至夹杂着巴洛克式的怪诞和幽默。不止一篇英语评论文章拿它和卓别林的电影作比较,指出其叙述所包含的喜剧性特点。
有个章节讲如何瞒过房东把衣物送去当铺。房东怕房客提了箱子开溜,坐在门房里监视。奥威尔的朋友鲍里斯心生一计,上去套近乎,用他宽阔的肩膀挡住房东的视线,以咳嗽一声为暗号,奥威尔提了衣箱溜出去。鲍里斯胆量过人,有说有笑,嗓门大得足以压过奥威尔的脚步声,两个人表演一出双簧戏,成功地骗过了房东。由于身份文件不齐,当铺拒收衣物,结果白忙乎一场,两人还是饿肚子。这类滑稽场景还能举出不少。正如有论者指出,奥威尔“把喜剧推向愁惨和痛苦的边缘”,这一点和卓别林相似。
有些场景还带有闹剧的特质。伦敦的游民去教堂吃免费茶点,一边吃喝,一边听人宣讲教义,吃完了不许离开,得做祷告,“和我们的天父说几句话”。他们在一片脏茶杯中间跪下来,挤眉弄眼,开荤玩笑,而且把圣歌唱得乱哄哄的。说是免费吃喝,谁知会这么麻烦,有个游民当场咒骂道:“操蛋!不过管他妈的,反正都是打发时间。”
伦敦收容所浴室,“五十个脏兮兮、一丝不挂的男人挤在二十平方英尺左右的房间里,人挤人,只有两个浴缸和两条黏糊糊的擦手毛巾可用”。轮到奥威尔,“问用之前可不可以先洗一下浴缸,上面有一道道灰垢”,门房说:“闭上你的臭嘴,赶紧给我洗!”
“浴室”一节让人想起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死屋手记》。那种自然主义式的、骇人的低俗场景中不乏喜剧和闹剧元素,这一点颇有俄罗斯文学特色。你也可以说是法国或爱尔兰的,但不是典型的英国文学。米歇尔·莱蒙在《法国现代小说史》(徐知免、杨剑译)中指出,法国文学是“在一九一八年之后进入世界主义时代”。奥威尔这本书的一个文学特色便是其世界主义色彩,耐人寻味的是,他并非是通过与巴黎的精英文学圈接触而获得的。这一点相关研究或可加以关注。奥威尔的人格和思想方式有浓厚的英国特质,而他在写作中融入的观念和趣味已经超越自身传统,以其特有的方式汇入时代文化潮流。
不知是凑巧还是设计,书中两个角色鲍里斯和帕迪,带领作者游历巴黎和伦敦底层社会(像维吉尔带领但丁游历地狱),一个是俄国人一个是爱尔兰人。尤其是鲍里斯,这个角色简直像是从俄国小说里跑出来的,给此书巴黎部分的叙述增添了令人发噱的戏剧性。
奥威尔是在住院时和鲍里斯认识的,两人成了患难之交。鲍里斯做了酒店洗碗工后,把食物藏在大衣里偷出来给奥威尔饱餐一顿。他介绍奥威尔做洗碗工。第一天干完活,酒店要和奥威尔签一个月的工作合同,可后者想到过两周要去鲍里斯朋友开的饭店做工,怕这样做不够地道,便拒绝了合同。鲍里斯听说后大发雷霆,对这个英国佬的迂执深感痛心。
“笨蛋!没见过这样笨的笨蛋!有什么用!我给你找到活干,你却马上搞没了!你怎么会这么愚笨,竟然提起另一家餐馆?你只要答应干一个月就行了。”
“我觉得我说我也许不得不走,这样可能显得诚实一点。”我争辩道。
“诚实!诚实!谁听说过洗碗工是诚实的人?我的朋友—”他一把抓住我的衣服翻领,非常恳切地说,“我的朋友,你已经在酒店干了一天活,看到了那儿是怎么回事。你觉得洗碗工有多少荣誉感可讲吗?”
……
“可是如果我毁约,工资怎么办?”
看到我如此之蠢,鲍里斯拿拐杖在人行道上猛捣,嘴里喊着:“你要求每天付工资,这样你一个苏也亏不了。你以为他们会去告洗碗工违约?洗碗工的地位低得不值得告。”
这种令人暗自捧腹的段落,和果戈理的小说放在一起不会逊色多少。作者有时像冷静严肃的新闻记者,有时像颇有喜剧天分的小说家,很难区分这两者的界限。
《巴黎伦敦落魄记》的体裁属性似乎不易确定,作者本人也不知该如何归类,是自传、报道还是游记?看起来似乎都像。此书讲述作者的亲身经历,说自传是恰当的,但风格有点像小说。奥威尔有些作品,像《绞刑》(1931)、《射象》(1936)等,究竟是纪实还是虚构,让学者也产生争议。应该说,经验和意图是实在的,细节和剪裁有所加工,大凡自传类作品均有此特质,奥威尔的也不例外。
就体裁属性而言,《巴黎伦敦落魄记》和笛福的《瘟疫年纪事》较为接近,是一种独特的混合体裁:有第一人称报道,有故事里套着故事的叙述,有非连续性的轶事、评论和离题话,其对社会学、人类学和政治学的关注决定了他对素材的处理和运用。第三十二章研究伦敦的俚语和脏话,第三十六章引用官方统计数字列表说明赤贫男性和女性的比例,这些做法和笛福的如出一辙,甚至语气也像,例如,“就流浪汉问题,我想谈几点粗略的看法……”“下面谈谈可供伦敦的无家可归者选用的住宿方式……”等等。
没有必要区分奥威尔是新闻记者还是小说家,他写报道时总是发挥作家特有的洞察力,正如他写小说时身上始终活跃着一个社会评论家的角色。虽说是自传性作品,奥威尔的底层书写却有其冷静务实的意图,也就是说他要对社会问题发表看法。
以洗碗工而论,因为肯定有人要去餐馆用餐,所以就得有人一星期擦洗八十个小时盘子,他认为这种观点是不对的。洗碗工的实际工作效率和待遇都大可提高,社会消费心理和消费结构也存在诸多可改进之处。在酒店干过活就知道,所谓高档享受是名不副实的。员工累死累活,顾客花大价钱,真正得益的是老板。洗碗工每天工作十到十五个钟头,就没空闲思考如何去改善处境,他们实质成了“餐馆的奴隶”,并不比可供买卖的奴隶自由多少。而社会让苦力和贫困存在的一个根本原因是“害怕群氓”,认为只有让人忙得没时间思考才更安全,因此精英人士对改善工作环境、解决贫困现象多半是持保守立场,即便他们不喜欢富人,但跟穷人相比,更愿意站在富人一边,不想冒险改变现状。奥威尔认为,对群氓的恐惧心理,对富人和穷人的差异性认识,都是出于想象,因为对实际状况缺乏真正了解。
人们鄙视乞丐,但有多少人真正了解他们呢?因为这些人不能像教师或文学批评家那样“挣”口饭吃,就是一无是处的寄生虫?奥威尔说,乞丐这一行确实没有用处,但许多高尚的行业其实也没用处。和卖专利药品的推销员相比,乞丐的为人更不诚实吗?恐怕不见得。其实我们并不真正关心行业是有用还是无用,我们关心的是牟利。他责问道:“现代人谈了那么多精力、效率、社会公益服务等等,但是除了‘挣钱、合法地挣钱、挣更多,别的还有所指吗?”
这倒不是说流浪汉都是好人,他们不过是普通人而已。“要是他们比别人坏,那是他们的生活方式使然,而非他们选择那种生活方式的原因”。原因在于现行体制,造成流浪汉的种种不幸还是跟法律问题有关。伦敦的游民无所事事,靠收容所解决不了问题。他建议每间济贫院都经营一个小农场或一块自用菜地,让身体健康的游民都有活干,这样就可以给他们提供更好的饮食。简言之,现行体制必须设法让流浪汉自食其力,而不是让他们毫无目的、毫无必要地受穷、受罪。
奥威尔喜欢谈论法规、法案的问题,从法律的角度提出建议,这是英国人的习惯。相信社会可以在协商和立法的基础上改进,相信一本书或一种观点所带来的舆论建设作用,因此他(和笛福)才会那样认认真真地写书探讨问题。就此而言,写作旅行报道的V.S.奈保尔是继承了奥威尔的衣钵,而且也真的是像英国人那样思考和说话。谈到流浪伙伴帕迪不敢偷牛奶,奥威尔评论说:“是因为饥饿而产生的畏惧让他讲究品德。只要有两三顿填饱肚子,他就有胆量偷牛奶。”针对帕迪那种自卑自怜的气质,他总结说:“两年吃面包和人造黄油的生活不可救药地降低了他的境界,他靠吃这种以次充好的差劲食物活着,直到他在思想及身体上都等而下之。夺走他男子气概的,是营养不良而不是自身恶习。”我们也常常在奈保尔的书中听到这种口吻的议论。
有人说,奥威尔是“贫困的临时居民”(a temporary dweller in poverty),并非真正的流浪汉和乞丐;他比巴黎伦敦的游民更容易摆脱困境。此话不假。事实上也是如此,他摆脱贫困的一个途径是写书,包括这本以贫困为主题的书,一九三三年出版时获得成功,正值大萧条最低落的时期,而它的读者应该是中产阶级而非流浪汉阶层。和编辑讨论此书标题时,他认为“落魄者”(down & out)一词不合实情,说“洗碗工”(dishwasher)才更确切。他并没有把自己当作游民的一员,也“没有为此书感到骄傲”,出版时还要求以笔名发表,于是埃里克·阿瑟·布莱尔(Eric Arthur Blair)便替代了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
奥威尔的观点有时接近马克思主义,实质是左翼中产阶级立场,带有中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使命感。讲到洗碗工被奴役的问题,他的表述和《哥达纲领批判》很相似:“一个除自己的劳动力外一无所有的人在任何社会和文明中都必然成为那些拥有物质劳动条件的人的奴隶。”而他认为,关键在于中产阶级精英的觉悟,如何以较完善的法规和保障制度让穷人获得工作。
如果是波德莱尔写他的波西米亚艺术家自传,观点会不一样,至少不会那么务实和理智。他会说:游民真的想要法规意义上的自我改造吗?人们固然需要工作,但人们也需要自杀,因为自杀(或堕落)是一种内在的需要……绝望总是有着别一种含义,而自我唾弃想必也包含着某种奇特的愉悦。谁说不是这样?但这么说,离奥威尔的思想就远了。
奥威尔可以写一个游民恶毒诅咒上帝,转眼间又跪在屋里祈祷,将贫穷的歇斯底里症状写得入木三分,但他不会从撒旦主义的立场看问题。魔性或神性的问题,波西米亚艺术家的“特殊敏感性”问题,同时代人的这些关注都不在他观察的取景框之内。他只是试图传达“从被动的普通人那里发出的声音”。谈到亨利·米勒的《北回归线》(参阅奥威尔《在巨鲸肚子里》),他称赞作者“能够从有限的素材发掘出最大的成果”,却又为该书写的不是普通人而感到遗憾。
他在自传末尾宣称:“我想弄清楚洗碗工、流浪汉和河堤路上的露宿者心灵深处的思想。目前,我觉得自己只不过对贫困有了些皮毛的认识而已。”他让我们相信,他在流浪岁月中看到的、接触到的都是一些普通人,要了解这些人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而要不作夸饰并且不带过滤地把他们写出来,恐怕就更为不易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