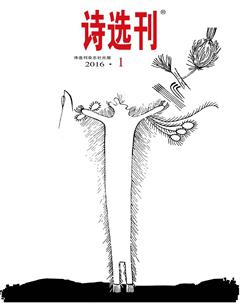吉狄马加与非洲的精神联系
李鸿然
2014年10月,中国当代著名诗人和文化学者吉狄马加获南非“2014姆基瓦人道主义奖”,并被授予“世界性人民文化的卓越捍卫者”称号。颁奖词中称,这是为了表彰他在诗歌艺术领域的卓越造诣和在文化传播方面做出的突出贡献。此奖曾授予纳尔逊·曼德拉和劳尔·卡斯特罗。这是亚洲人第一次获得这个奖项。吉狄马加几十年如一日,坚持“为土地和生命而写作”,致力于中国文化和世界文化的传承与保护,在引领和推动国际诗歌创作发展和世界各国文化交流方面做了许多艰苦卓绝的工作,其奠基性、开拓性和创造性贡献世人公认,获此殊荣,当之无愧。他在颁奖仪式书面致答辞中强调:“我将把这一崇高的来自非洲的奖励,看成是你们对伟大的中国和对勤劳、智慧、善良的中国人民的一种友好的方式和致敬,因为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在南非人民对抗殖民主义侵略和强权的每一个时期,都坚定地站在南非人民所从事的正义事业的一边,直至黑暗的种族隔离制度最终从这个地球上消失。”如果说荣获“姆基瓦人道主义奖”能充分说明吉狄马加与非洲最紧密的精神联系,那么他的获奖答辞则清楚地指出了自己获奖的基础和前提,是我们考察他与非洲紧密精神联系时应当深思的。
情系非洲“黑人兄弟”
吉狄马加1985年24岁时出版的第一部诗集,即获得国家级诗歌大奖的《初恋的歌》,就有不少直接或间接书写非洲的篇什,其中1983年写的《古老的土地》,30多年来一直受到国内外读者和诗人的高度评价。“我站在凉山群峰护卫的山野上,/脚下是一片神奇的土地。/这是一片埋下了祖先头颅的土地。/古老的土地,/比历史更悠久的土地,/世上不知有多少这样的土地。/……我仿佛看见黑人,那些黑色的兄弟,/正踩着非洲沉沉的身躯,/他们的脚踏响了土地,那是一片非洲鼓一般的土地,/那是和他们的皮肤一样黝黑的土地,/眼里流出一个鲜红的黎明。”这首诗真实生动地描绘了非洲人民的生存境遇和生命活力,把他们生活的沉重、不屈的奋斗和美好的梦想表现得淋漓尽致。作品的最后写道:“古老的土地,/比历史更悠久的土地,/世上不知有多少这样古老的土地。/在活着的时候,或是死了,/我的头颅,那彝人的头颅,/将刻上人类友爱的诗句。”热爱世界上所有“古老的土地”,不论生与死都在头颅“刻上人类友爱的诗句”,当然会打动世界上所有地方的所有人,包括非洲“黑人兄弟”。作品问世不久,吉狄马加在接受埃及《十月》杂志记者泽西拉·比耶利博士访问时,又应比耶利的要求,专门朗读了这首诗,于是埃及和非洲各国人民迅速地听到了中国诗人的心声,感受到中国人民和非洲人民灵犀相通,中国梦和非洲梦有共同性。进入21世纪后,这首诗在国外以不同的语言文字传播,引起了更广泛更强烈的反响。亚非拉和欧美诗人不时提到这首诗,因为诗中不仅表达了对“黑人兄弟”的深情厚谊,还表达了刻骨铭心的“人类友爱”。正是这种博大的“人类友爱”,缩短了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之间的心灵距离,这首诗才引起非洲人民和世界人民的普遍共鸣,并成为世人公认的经典。
非洲人杰地灵,对人类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可是现在非洲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也面临不少本土性和全球性问题。吉狄马加始终情系非洲的和平与发展及“黑色兄弟”的福祉,并写诗分享其欢乐,分担其忧愁。
非洲与世界其他地区一样,在现代化过程中一直面临着精神信仰的缺失和物质主义的侵蚀,许多独特的本土元素逐步消失了,吉狄马加为此曾再三写诗表达忧思。如《最后的酒徒》:“你的血液中布满了冲突/我说不清你是不是酋长的儿子/但羊皮的气息却弥漫在你的发间/你注定是一个精神病患者/因为草原失去的影子/会让你一生哀哀地嘶鸣。”2007年8月《南方周末》记者问他:“酋长”、“羊皮”、“精神病患者”这些词对一个彝族诗人意味着什么?他说,“精神病患者”是一个象征,指人类现代化过程中“自身的精神失衡”,“在现代化的过程中,恐怕全球都如此,彝族也不例外,很多值得留存的东西、个性的东西开始泯灭了。”接着他又援引高尔基的话说:“非洲死一个部落酋长,相当于在欧洲毁掉一个博物馆,这无疑是一件最叫人心痛的事。”中国彝人一一非洲人一一全人类,都面临“精神失衡”,这是被美国评论家称为“中国西部一位伟大灵魂”的诗人无法消除的心结。2007年吉狄马加写的另一首诗《我听说》,也心忧如焚:“我听说/在南美安第斯山的丛林中/蜻蜓翅膀的一次震颤/能引发太平洋上空的/一场暴雨/我不知道/在我的故乡大凉山吉勒布特/一只绵羊的死亡/会不会冻醒东非原野上的猎豹/虽然我没有在一个瞬间/看见过这样的奇迹/但我却相信,这个世界的万物/一定隐藏着某种神秘的联系……”前面一首诗担忧非洲精神“失衡”,文化个性“泯灭”;后一首诗则以自己故乡绵羊的“死亡”和东非猎豹能否“冻醒”为喻,同样沿着中国彝人一一非洲人一一全人类的诗学思维路线,表达是对中非和全球物种消失、生态失衡的焦虑。非洲战火绵延,暴力不止,饥饿和瘟疫时刻威胁着人类,因此吉狄马加在《科洛希姆斗兽场》、《鹿回头》、《回望二十世纪》、《那是我们的父辈》等许多诗篇中不断呐喊,呼吁结束战争、停止暴力、解救被饥饿、瘟疫和艾滋病逼到死亡边缘的人们。“我知道科洛希姆斗兽场/可以容纳六万观众/他们在那里欣赏/杀人的欢畅/我知道这不是远古的神话/丧尽天良的杀戮/亘古以来就从未消亡/从波兰平原库特诺的焚尸炉/到如今黑种民族/在南非遭受的屈辱”,“我将我的脸庞/贴在科洛希姆斗兽场的/老墙上/当刀剑的撞击停息/当呻吟再没有回响”;“……非洲的饥饿直到今天还张着绝望的嘴/我曾相信过上帝的公平,然而在这个星球上/还生活着许许多多不幸的人们/公平和正义却从未降临在他们的头上。”这类让人读后难以抑制惊悚、震撼、愤懑的诗性画面,蕴藉着博大的人类之爱,也显现了对非洲人民无比强烈的兄弟之情。
高度评价非洲现代文学及“黑人性运动”
原始、奇异、破碎、危险等,是世人对非洲的基本想象;非洲文明、文化、文学落后于世界潮流,几乎是包括文学界在内的社会各界的共识。由于长期受西方文学中心论的影响,中国当代作家对非洲文学所知甚少乃至无所知者比例较大,知之较多认识较深者比例很小,因此在“中国作家谈外国文学”这类图书里,谈西方文学者比比皆是,谈包括非洲文学在内的非西方文学者寥若晨星,报刊上关于非洲文学的文章历来罕见。吉狄马加进入中国作家协会领导层之后有意改变这种状况。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他已成为中国文学创作领域对非洲现代文学最关注、最了解,也对介绍和评论非洲现代文学最热情、最给力的作家和文学领军人。在吉狄马加大约20部著作中,诗集里有许多关于非洲的诗歌,诗文集、演讲集、访谈及随笔集里有大量介绍和评论非洲文学的文章,其中介绍和评论非洲现代作家作品的文章最多。因为他的评论是在全球化演进、现代化嬗变和世界文学潮流起伏消长的大背景上立论的,所以话语中表现了吉狄马加特有的大视角和大气度。他的评论全面、新颖、深刻,给人以闻所未闻的感觉。这对纠正当代文坛漠视非洲文学的错误倾向,扭转众多作家对非洲文学认知缺失的局面,引导广大读者阅读非洲文学作品和扩大世界文学视野,以及推动中外文学交流与对话,都具有重要意义。
新世纪伊始,吉狄马加在2001年第三期《世界文学》上发表重要文章《寻找另一种声音》,立即引起广泛关注,外国文学出版社2003年9月以此文题目为书名,推出“我读外国文学”专集,收录文章37篇,作者有莫言、贾平凹、刘心武、余华、张炜、苏童、冯至、袁可嘉、郑敏、海子、王小波、于坚等36位,无一不是名家。他们文笔从容,文章质地厚重,反映了当时中外文学交流的最高水平。但是名家们大多谈的是读西方文学的体会,谈非西方文学者少,谈的内容也不过三言两语。莫言、残雪谈及拉美文学,吉狄马加之外,没人谈非洲文学。36位作者中既谈西方文学又谈非西方文学,而且从根本上和整体上评论非洲文学与拉美文学者,是吉狄马加。吉狄马加文章中表现的世界文学观念和文学价值观念,以及对非洲文学的评论,在新旧世纪之交中国文坛上堪称空谷足音。其要点有三:第一,吉狄马加认为,世界文学“是世界不同国度、不同种族的文学”,不同国度和种族的文学大师们,“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的文学奇迹”,使人们“真正认识了这个世界”。他们不朽的作品,也成为人们“精神世界中最重要的一个部分”。吉狄马加对世界文学这种认识超越了西方文学中心论,他对文学认识价值和精神意义的把握也是十分正确的。第二,吉狄马加高度概括了黑人现代文学对非洲大陆划时代的贡献和对世界不同文明应当共存互鉴的启示作用。他说:“黑人现代文学,是二十世纪一个重要的文学现象,不少黑人作家的作品,今天已成为世界人民“公认的经典”,这些作品“把一个真实的非洲和黑人的灵魂呈现给世人”,使人们懂得“这个世界上每一个民族的文化都是不可替代的”,从而“更加关心别人的命运,关心不同文明和文化的共存。”第三,吉狄马加特别推崇出生于马尼提克岛的诗人塞泽尔和出生于塞内加尔的诗人桑戈尔,盛赞他们提倡的“黑人性”运动,认为他们摆脱欧洲文化中心主义影响,从黑人文化中吸取灵感,把源于他们祖先流传的神话历史,神圣语言以及残酷的现实生活,都完整地融入自己的创作世界,在短暂的时间内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创造了一个现代神话”,对世界上一切弱势群体的文学如何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示范”。他说,自己阅读桑戈尔充满祖先的精神,语言仿佛是非洲祭祀梦呓和祈祷一样既感亲切又感有无穷生命力的文学,“就像一股电流穿透了我的全身”;他还说,阅读被称为“非洲现代文学之父”的阿契贝和曾获诺贝尔文学奖的索因卡的作品,也曾给他“难以估量的影响”。显然,吉狄马加对于误解非洲但不固执己见的人们来说,仍旧有不少启示性。
近十年间,吉狄马加的非洲情怀上升至更高层面,他同非洲的精神联系更为紧密,推动中国和非洲文明、文化、文学的交流互鉴更加不遗余力。单看其演讲,就能证明这种趋向。他2005年11月9日在清华大学的演讲《漫谈我的文学观与阅读生活》,2008年10月16日在“当代世界文学与中国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的演讲《当代世界语境下的中国诗人的写作》,2009年7月10日在中韩作家对话会上的讲演《中国西部文学与今天的世界》,2009年11月23日在鲁迅文学院的演讲《多元民族特质文化与文学的人类意识》,2012年8月10日在国际土著民族诗人圆桌会议上的演讲《我们的继续存在,是人类对自身的救赎》,都一再谈论非洲,对非洲文明、文化、文学的论述比以前更全面、更充分、更深入。他谈论非洲现代文学,是站在21世纪这个时代的高度,以全球视野和人类意识观察思考问题的,不像一般作家和诗人那样局限在写什么、怎么写、写得怎样等层面;而身为作家与诗人,他评论非洲现代文学,又特别看重黑人精神和黑人心灵的创造性表达,关注文本的精神性、心灵性、地域性和民族性。从上述演讲中可以看到,他对非洲现代作家作品和文学现象的感悟和认知,特别是对非洲现代文学世界意义和人类学民族学价值的分析、理解与评说,不少方面超越了有关文学理论家和文学史家。其中在国际土著民族诗人圆桌会议上的演讲就是典型的例证。这篇演讲题为《我们的继续存在,是人类对自身的救赎》,为会议的主旨演讲,中心内容是论证世界土著民族、土著文化和土著文学的“继续存在”对当今人类解救危机和世界减少灾难的伟大意义。其中,最关键的话语就是从非洲诗人艾梅·塞泽尔说起的:“伟大的马提尼克诗人和政治活动家艾梅·塞泽尔呼吁以‘历史权利,来进一步关注土著民族的文化传承,他所提出的‘黑人性,无疑是非洲以及世界黑人文化复兴运动的最为重要的理论基石。艾梅·塞泽尔给了我们一个宝贵的启示,那就是我们必须找回属于自己的‘历史的权利,为真正实现和保护我们的地球家园文化多样性而付诸行动。从21世纪开始以来,将多样性当做一种现代性的象征来用已经成了人类的普遍共识,或者说成了绝大多数人所认同的一种具有道德精神的基本原则。可以说,今天生活在世界不同地域的各个古老民族的存在和文化延续,将是人类对自身的救赎,因为我们曾长时间缺乏对不同文化和传统的理解及尊重。”中国的世界文学史,有的根本没有论述塞泽尔,有的只作了简单介绍,吉狄马加在一个国际学术会议的主旨演讲中对塞泽尔及其倡导的黑人性文化复兴运动作如此崇高的评价,可以说“史无前例”,是多重意义上的超越。如果我们知道吉狄马加2012年还创作过专门献给塞泽尔的诗篇《那是我们的父辈》,读过“塞泽尔,我已经在你的黑人意识里看见了/你对这个世界的悲悯之情/因为凡是亲近过你的灵魂,看见过你的眼睛的生命个体/无论他们是黑种人、白种人、还是黄种人/都会相信你全部的诗歌/就是一个离去和归来的记忆……”读过这种充满崇高诗情和深邃历史哲理的诗句,我们对非洲现代文学的认识,对人类文化多样性的认识,当然还有吉狄马加与非洲精神联系的认识,就必然更全面更深刻了。
献给纳尔逊一曼德拉的诗蕴藉着高尚而深邃的精神意义
在世纪之交有关非洲的诗歌中,吉狄马加的《回望20世纪——献给纳尔逊·曼德拉》是一首大诗、奇诗,富有探索性和独创性的好诗。它在人类几千年历史的坐标上,书写当今世界100年的历史,向世界发出了黄钟大吕般的声音。作品以“你(指20世纪)好像是上帝在无意间遗失的一把锋利无比的双刃剑”为总体隐喻,通篇都是“世界太息”和“世纪太息”,其中也包括对非洲人民遭受殖民统治时期悲惨命运的感喟,对非洲黑人土著文化相继消失的嗟叹。此诗的副标题“献给纳尔逊·曼德拉”,寓有深意。曼德拉是世人公认的非洲黑人解放运动领袖,非洲各族人民反抗新老殖民主义斗争的伟大旗手,也是20世纪人类精神的代表。纳尔逊·曼德拉这个名字已经是一个不朽的符号,以“献给纳尔逊·曼德拉”为副标题,增添了诗的内涵,扩大了诗美空间,既凸显了非洲人民数不尽的历史灾难和艰苦卓绝的抗争,也彰明了当今世界的时代主潮和人类的崇高精神。《回望20世纪》70多行,用“我们”10余次,把“你”作为“20世纪”代称用了30余次,这种写法让时间获得了生命,在诗里形成了对话机制,同时也激活并贯通了文路,使全诗情思浩荡、大气淋漓。“你为了马丁·路德·金闻名全世界/却让这个人以被别人枪杀为代价/你在非洲产生过博卡萨这样可以吃人肉的独裁者/同样你也在非洲养育了人类的骄子纳尔逊·曼德拉/你叫柏林墙在一夜之间倒塌/你却又叫车臣人和俄罗斯人产生仇恨/还没有等阿拉伯人和犹太人真正和解/你又在科索沃引发了新的危机和冲突/你让人类在极度纵欲的欢娱之后/最后却要承受艾滋病的痛苦和折磨/你的确认人类看到了遗传工程的好处/却又让人类的精神在工业文明的泥沼中异化而死亡……”这首诗内容与全球五大洲相关,与非洲的现实困境和精神危机当然也有切实联系。其文本的话语系统蕴藉深厚,极富张力,表达总在显现与隐藏、有解与无解之间,艺术天地极大。作品并没有舍弃形象意象隐喻象征,同时又把20世纪众多矛盾对立的人或事并置,构成历史悖论,在真善美和假恶丑的对抗对撞中呈现百年的历史哲学,从而激发人们的想象与思考,使读者在情感和理智上得到提升。把非洲“吃人肉的独裁者”博卡萨和非洲养育的“人类的骄子”曼德拉比较对照,其思想冲击力和艺术震撼力是不言而喻的,认识非洲和世界的复杂性,正可由此进入。面对20世纪数不清的历史悖论,如果读者深入思索,从曼德拉身上就可以找到不少解惑的突破口,看到人类历史的光明面,并且以正确的姿态面对21世纪。
2013年12月5日,纳尔逊·曼德拉逝世,全世界都为他逝世而哀伤,用各种各样的形式深切地悼念他,几十亿人民以数千种语言表达着自己的悲痛。吉狄马加的方式是用世界使用人口最多的汉语在几天之后写出了出于自己灵魂深处的诗句。这是一首长诗,2013年12月10日,即世人向曼德拉遗体告别之前问世,题目是: 《我们的父亲》。在吉狄马加心中,曼德拉是我们在精神上永远不会死去的父亲,他伟大的人格和巨大精神力量超越国界、种族以及不同的信仰,深刻地影响着人类对自由、平等、公正的价值体系的重构,从而为人类不同种族、族群的和平共处开辟出更广阔的道路。“我仰着头——想念他!/只能长久地望着无尽的夜空/我为那永恒的黑色再没有回声/而感到隐隐的不安,风已停止了吹拂/是在一个片刻,还是在某一个瞬间/在我们不经意的时候/他已经站在通往天堂的路口/似乎刚刚转过身,在向我们招手/脸上露出微笑,这是属于他的微笑/他的身影开始渐渐地远去/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知道/他要去的那个地方,就是灵魂的安息之地/那个叫古努的村落,正准备迎接他的回归……”这是长诗的开篇,用高视角和大视境,写非同寻常的悼念:仰着头长久地望着无尽夜空的想念。然而“永恒的黑色再没有回声”,不经意间“他已经站在通往天堂的路口”,出神入化的描述,凸显了一种中外诗人都在孜孜追求的“神性”,但是吉狄马加追求的这种“神性”,不是属于上帝们的那种“神性”,而是人类尊崇的一种“精神”或“精神性”。你看,那个已经站在通往天堂路口、我们无限想念的人在向我们招手了,而且脸上还露出了我们非常熟悉的“属于他的微笑”。可以说,这样开头是神性、人性、诗性的变奏与交响,汇合着不同国家、不同种族、不同文化背景和宗教信仰的亿万人民群众的无比悲伤与无限崇敬。法国一位文学评论家说,“吉狄马加是一位伟大的讲故事的人。我们信他的故事,我们跟随这些故事,尽管它们是悲剧性的。也正因为它们是悲剧性的。在今日诗歌中拥有故事的敏感,这是一种极其罕见的天赋。”这段话在吉狄马加《我们的父亲》中,也得到了印证。在富有神性的开篇之后,吉狄马加就开始给我们“讲故事”了——从“一个黑色的孩子,开始了漫长的奔跑”讲起,讲“这个有着羊毛一样有着卷发的黑孩子”怎样“沿着他选择的道路”百折不挠地前进,怎样面对“监禁、酷刑、迫害以及随时的死亡”,怎样“带领大家去打开那一扇名字叫做自由的沉重的大门”,怎样“九死一生从未改变”、“始终只有一个目标”,怎样坚信“爱和宽恕能将一切仇恨的坚冰溶化”,最后达到目标时又怎样“用平静而温暖的语言告诉人类——忘记仇恨!”这的确是一个故事,不过不是一般的故事,而是一个惊天地泣鬼神的故事,一个顶天立地受到全人类敬爱的人类精神领袖的故事,而吉狄马加讲这个故事的时候也极为充分地运用了他已操练、创造了30多年的“吉狄马加诗学”,把这个故事从头至尾由外到内彻底地精神化、心灵化、审美化了。应当说,30年来每一阶段都有不少“标示当代诗歌等高线”、“写得足够大气、诚挚、灵动,充满抒情汁液”(唐晓渡语)的吉狄马加,这些年来还有不少“超越”了“当代诗歌等高线”的好诗、奇诗和大诗,本文论及的《回望20世纪》、《那是我们的父辈》和这首《我们的父亲》,都是这样的诗篇。
诗歌阅读广泛的读者,读吉狄马加悼念曼德拉的诗时,也许会联想到美国诗人玛雅·安杰卢同一时期悼念曼德拉的诗。安杰卢是一位有传奇色彩的黑人女性,美国民权运动的知名人士,卓有成就的美国作家和诗人。作为美国黑人女诗人的杰出代表,她1993年曾在克林顿总统就职典礼上朗诵诗歌,轰动一时。2013年12月6日,即曼德拉逝世第二天,美国国务院公布了一段时长四分四十秒的录像,内容就是安杰卢“代表美国人民致纳尔逊·曼德拉的颂诗”。此诗题为《他的日子结束了》,开篇为“他的日子结束了”。/结束了。/消息乘着风的翅膀而来,/不愿驮起这份重负。/纳尔逊·曼德拉的日子结束了。//消息传到我们美国,/不意外,可还是不想听到。/我们的世界突然变得黯淡,/我们的天空铅一般沉痛。//他的日子结束了。//我们看见你们,南非的人民,无言地站立,当那最后的门猛然关闭,/再不会有旅人归来了……”全诗也歌唱了曼德拉的伟大人格和精神力量,赞颂了他反对种族隔离制度的历史功绩,表达了对人权、自由、和解、宽容的肯定和热望。两首长诗各有千秋,然而两位诗人在历史观、文化观、世界观和价值观上的差别也明显或隐蔽地活跃在字里行间,甚至同用“人权”、“民主”、“自由”等词汇,所指也大为不同,需要细心解读。要而言之,安杰卢是以美国为中心视角的,吉狄马加采用的却是中国——非洲—世界共同视角。诗的标题《他的日子结束了》和《我们的父亲》,差异是极为明显的。诗行中的话语差异更明显。按血统说,黑人安杰卢与曼德拉同源,但其诗“他”字连篇,“这里,在美国,我们……”成为标准句型;而吉狄马加笔下,“我们的父亲”却不曾离口,这不是故意做作的称谓,不是矫情,与“黑人兄弟”、“我们的父辈”称谓一样,都表现了特殊的亲情,带有诗人的血温。称呼之内,有文化身份与写作立场问题。“曼德拉是我们在精神上永远不会死去的父亲”,是说曼德拉精神不仅属于他个人和南非,也属于我们中国人和全人类,不仅属于过去和现在,也属于未来。总之,吉狄马加《我们的父亲》是吉狄马加创作中不可多得的杰作,很有可能成为世界诗坛悼念曼德拉诗歌中的经典,因为它不仅表现了中国诗人吉狄马加与非洲的精神联系,也表现了中国人——非洲人——全人类之间的精神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