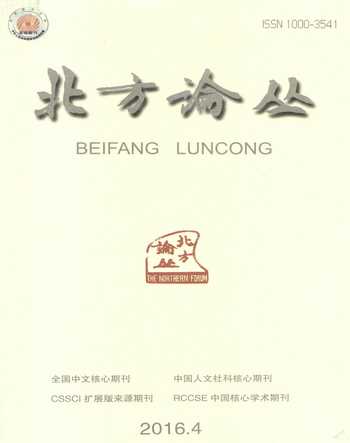“妙手空空”与近代诗学精神
潘静如

[摘要]近代诗学理论家陈衍论述近代诗学时曾提出“妙手空空”一说,为汪辟疆、钱仲联等学者所继承。陈衍将近代诗学里的“妙手空空”现象归咎于诗人学问的匮乏,但这一解释有失偏颇。晚清民国之际,中国社会处于从礼俗社会向法理社会的转型阶段。借助于阿尔都塞的“症候式阅读”理论,可以说,近代诗歌创作里的“妙手空空”现象乃是近代士人及其诗学精神的体现。
[关键词]妙手空空;陈衍;郑孝胥;症候式阅读
[中图分类号]1206.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3541(2016)04-0022-04
研究近代诗歌与诗学的著述很多,但关于“妙手空空”这一批评术语似乎很少有人注意,尤其是它背后隐藏的更为深微的意蕴。
关于“妙手空空”,陈衍《石遗室诗话》云:
今春在海藏楼见苏堪诗有为审言作者,似颇著意。因问审言何人,苏堪言李姓,详名,有著述,能诗。近见杂报端有数首,非近日妙手空空一派。
又云:
余于前编《诗话》偶录李审言数诗,谓非近日诗人妙手空空者可比……至此诗使事雅切,仍以“非妙手空空儿”评之耳。
汪辟疆(1887-1966年)
《光宣诗坛点将录》云:
审言本精选学及杜韩,益以博览,及为同光体,言皆有物,迥异乎妙手空空者矣。(自注:按近人学宋,多藉一二空灵字面可彼可此者,填委成篇,为世诟病。杨圣遗、秦右衡、李审言诸家,皆一生手不释卷,博闻殚见。诗虽稍并,特出之以示准则。)
钱仲联(1908-2003年)《近百年诗坛点将录》云:
杨钟义晚号圣遗居士,以良乡圣水而名。著《雪桥诗话》,为满族诗人之重要文献。《圣遗诗集》,典雅宁静,大异近人之妙手空空者。
一望而知,“妙手空空”是相对“使事雅切”而言,意指学问上的匮乏。汪辟疆自注“近人学宋,多藉一二空灵字面可彼可此者,填委成篇”是具体解释。但什么是“一二空灵字面可彼可此者”,汪辟疆没有细说。考陈衍《石遗室诗话》卷八云:
作诗文要有真实怀抱、真实道理、真实本领,非靠著一二灵活虚实字、可此可彼者斡旋其间,便自诧能事也。今人作诗,知甚嚣尘上之不可娱独坐,“百年”、“万里”、“天地”、“江山”之空廓取厌矣。于是有一派焉,以如不欲战之形,作言愁始愁之态,凡“坐觉”、“微闻”、“稍从”、“暂觉”、“稍喜”、“聊从”、“政须”、“渐觉”、“微抱”、“潜从”、“终怜”、“犹及”、“行看”、“尽恐”、“全非”等字,在在而是,若舍此无可著笔者。非谓此数字之不可用,有实在理想、实在景物,自然无故不常犯笔端耳。
可以断言,陈衍此处“靠著一二灵活虚实字、可此可彼者斡旋其间”一句,是汪辟疆自注所本。那么,所谓“空灵字面”正是指“坐觉”“微闻”“稍从”“暂觉”等词而言。陈衍揭橥妙手空空这一批评术语,是从学殖的深浅、才力的富瘠、情事的真伪着眼。但近代诗人不约而同地“以如不欲战之形,作言愁始愁之态”,似乎不能仅仅从这一角度立论。
有理由怀疑,陈衍非议这一风气的背后,隐有所指,因为陈三立(1853-1937年)、陈曾寿(1878-1949年)特别是郑孝胥(1860-1938
大量文本表明,这样的表达不限于郑、陈等人,而是弥满在晚清民初诗人的集子里的,像梁鼎芬(1859-1919年)“剩有孤吟酬罔极”、俞明震(1860-1918年)“剩觉江山种种非。”“将衰微觉悲欢异”、陈宝琛(1848-1935年)“坐怜东海几扬尘”“诸公犹及当平世”、姚永概(1866-1923年)“微觉芭蕉败叶喧”、曹经沅(1891-1946年)“微闻猁犬憎兰佩”“僧话微怜朝士少”“微觉花前异我春”、樊增祥(1846-1931年)“终怜南向鹧鸪啼”、李详(1858-1931年)“剩觅清溪长板桥”“正及秋光且赋诗”、林思进(1874-1953年)“渐恐中年悟客尘”“稍闻守岁通宵语”、赵熙(1867-1948年)“微闻芍药香谁似?稍喜柴桑菊未寒”、沈瑜庆(1858-1918年)“行看沧海障横流”、瞿鸿横(1850-1918年)“微剩途金迷蛱蝶”、李宣龚(1876-1952年)“坐觉万牛真可挽”等等。关于这一点,笔者曾在讨论曹经沅《借槐庐诗集》的时候匆匆带过:
壤蘅诗学,一以海藏为归,遣词造句,亦步亦趋,盖十得其五六。集中诸联若《重九后七日海藏召集李园》“冷节呼俦如有例,枯枰敛手恐非才”、“微闻猁犬憎兰佩,忍见铜驼卧草莱”、《丁卯九日》“僧话微怜朝士少,阵云偏逐塞垣高”、《孤桐五十生日》“尽有百城供枕薜,微闻万口说清贫”、《奉怀香宋翁》“每从人日怀吾党,微觉花前异我春”,“微觉”“微怜”“微闻”云云,皆海藏家法也。海藏诗喜用“惘惘”二字,壤蘅亦无以外之,《次太夷九日韵》“佳日真成惘惘游”、《樊山老人枉和江亭之作》“顾曲城南惘惘听”、《次韵奉答花近楼主九日见怀》“拂槛西山惘惘青”、《壬申重九》“花下行厨惘惘思”,均是显例,“拂槛西山惘惘青”一句尤警拔,以“惘惘”二字状“青”字,如有神助,虽在海藏集中,不可多得也。
总之,诗人正是通过“坐觉”“微闻”“稍从”“暂觉”“聊从”“政须”“微抱”“潜从”“终怜”“犹及”“行看”这些吞吐掩抑的“虚字”来表现一种似咽如悲、才醒复醉、欲语还休、将愁未愁、“言愁始愁”之态的。但诗人毕竟没有直接使用“愁”“悲”“痛”“愤”这些字眼,似乎可以说明这些质实的字眼并不是最能表现他们的心境和情绪的。因而,他们一方面宁可选择使用看、觉、从、闻、须、及这些表示客观行为或感受的中性词;另一方面,又通过虚字来丰富或模糊其意蕴,传递一种曲折微深的感受或心理。这是古典诗学所强调的“真实本领”“使事雅切”所无力承担的。换言之,“蓄积贫薄”未必是造成这一现象在晚清民初之际“在在而是”的主因,“妙手空空”反倒是主体有意识的选择。
那么,他们到底要传递怎样的感受或心理?如前所述,这不是简单干脆的愁、悲、痛、愤一类的感情。同时可以肯定,他们所要表达的感情与愁、悲、痛、愤相接近。过此以外,他们要正面表达自己的感受或心理是困难的,或者自己也不是十分了然的。这时,其意识有一个指向,但又是含混、模糊的,有时甚至是空缺的。从语义学精神分析的视角来看,潜意识或无意识并不是不存在,只是很难完全表征出来。晚清民初的这种群体现象,实际上,正宜通过症候式阅读(symptomatic reading)加以理解。这充分指向他们的精神世界。他们通过“坐”“微”“稍”“暂”“政(正)”“潜”“行”“终”这些含混的、空灵的、含有多重可能性的词语来暗示那种难于言说的意绪——汪辟疆曾拈出的“惘惘不甘”是最接近这一意绪的。这些诗人当然可以直接使用而且确实经常使用“惘惘”一词,但毕竟还是把这一意思给说破、说狭了,不能表达更微妙的意绪,至少“不甘”的意思就很难被包蕴进去。这几乎是中国古典诗歌语言在表征功能上的极限了。现代新诗,不论作者还是读者,都参与意义重建的过程,是一种个性化的创造,它在表达含义的曲折玄微上,比古典诗歌拥有远为广阔的空间。古典诗歌,尽管有风格上的不同,但成规(convention)以及共同的文史知识背景决定了它在表达上的稳定性、有限性和同质性。所以,同样是“惘惘不甘”,现代新诗也许可以拥有无数种表达方式,但古典诗歌却相当的趋同,陈衍抱怨的“在在而是,若舍此无可著笔者”,正可从这一角度来观照。
接下来的关键问题是,他们为什么偏爱“坐觉”“微闻”“稍从”这些并不算很明朗的词?也许某一首诗当中,他们确有所指、确有所感,但群体性的长时段的症候式写作,就很难这样理解了。为此,笔者相信文学有自己的“季候”,它与整个时代息息相关。不过,在展开这一点之前,我们不妨从技术层面先加以解释。从诗学的角度讲:第一,就像古今学者注意到的,诗歌中虚字大量而广泛使用始于宋代,恰好大部分近代诗人都可以归为宋诗派,因而继承了这一重视虚字的传统;第二,明七子的那种“百年”“万里”式的高唱或乾隆时期的“纤巧甜滑”早已引起审美疲劳,从诗学发展的内在理路来说,必然会有所变化,近代士人的这种风气实际上是道咸以来诗学转轨的继续,亦即所谓“抑高唱而使之喑,摧盛气而使之绌”;第三,郑孝胥、陈三立、陈曾寿等人可称近代诗坛的领袖,很容易引起模仿效应。
然而,这些因素恐怕还不是最充分或最完备的解释。我认为,文学/诗学有自己的“季候”,近代诗人群体性的长时段的症候式写作,必须放在这一脉络中加以理解。换言之,光宣文X/近代士人对“妙手空空”的偏爱,不光与传统的家国身世之感相关,还与近代新的变局有密切关联。在近代尤其是光绪中后叶,一方面是国家饱经内忧外患,从而引起近代士人的家国身世之感,这是历代士人都可能会经历的;另一方面,是遭遇了“千古未有之大变局”,外在表现是士农工商四民社会正在加速解体,特别需要指出的是,这一趋势远在科举制废除以前。汪晖在《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拈出“天理”与“公理”两个框架,展现前现代中国的“裂变”及“现代中国”的“起源”。这是大的方向。但我的讨论并不局限在这里。光宣文人出自古老的“礼俗社会”(Gemeinschaft,英译community),正如这一概念的提出者托尼斯(Tonnies)及其后的沿用者所观察到的,在工业时代或者说“法理社会”(Gesellschaft,英译society)确立以前,“礼俗社会”遍布于世界各地。过去通过英译而译成“共同体”并不能准确反映这一词语的核心意义。依托尼斯之见,礼俗社会是一种个人的直接的社会关系,人们的角色、价值、信仰都建立在这种社会关系上,而法理社会则属于间接的社会关系,非个人的角色、正式的或公开的价值与信仰都建立在这种社会关系上。马克斯·韦伯在1921年出版的《经济与社会》中,对此做了扬弃,他认为,Gemeinschaft是根植于个人的直观感受,亦即情感的或传统的直接感受,而Gesellschaft以社会关系为基础,根植于互相协定的理性契约,商业合同就是最好的例子。一言以蔽之,“礼俗社会”是一种以“自然意志”为主导的“理想型”(Ideal type)社会。儒家文化是礼俗社会的产物,当然保留了这诸多特征,正如美国社会学家索罗金(Pitirim A.Sorokin)在英译本Gemeinschaft and Gesellschaft前言中提到的,以社会伦常而论,托尼斯给Gemeinschaft归纳的母亲与孩子,父亲与孩子们,兄弟姐妹们,朋友们,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们这五重关系,特别接近孔子所赞扬的父子、兄弟(长幼)、夫妻、君臣、朋友这“五伦”(five fundamental social relationship)。
但随着礼俗社会的不可持续,一切将发生改变。四民社会是最悠久的礼俗社会类型之一,它的逐渐解体,首先意味着士人的权势将悄悄发生转移。记得美国历史学家理查德·霍夫斯塔德特在1950年代曾提出“地位政治(status politics)”理论。简单说,大多数历史学家把政治看作一种受促进或保全私人的物质利益的努力,这个单一来源滋养的(即为这个单一原因所决定的)行为形式,霍夫斯塔德特却在这种对有组织的自私的表达之外发现了地位政治,即这样一种公共行为模式,其大部分能量来自于焦虑——对失去权力或特权或“种族纯粹性”或社会支配的焦虑。这一论断相当富于洞察力。如所周知,传统的士/士大夫阶层,在近代特别是废除科举制以后,正在经历一个权势转移的过程。由此,延续了几千年的士/士大夫政治传统面临中断。这是近代士人面临的新情况,过去那些不言而喻的终极依据不再有效,整合了宇宙秩序、人间秩序的儒学体系开始动摇甚至崩溃,他们面临着价值秩序、文化范型和自我理想的失落。不论它有没有立即成为事实,这种危机会悄悄地被“为此文化所化”的士人感知;也不论自觉或不自觉,这种危机会投射或渗透到最敏感的士人的精神世界或潜意识之中。这样,在整个晚清民初之际,他们的确被某一种力量驱动着,选择使用“坐”“微”“稍”“暂”“政”“潜”“行”“终”等字眼来表征那种突然而来、纷然而凑、似有若无、无可奈何但又难以言状的深层意识,最终表现为精神上的惘惘不甘。这种群体性的症候式的“惘惘不甘”
(不是悲伤、愁郁或别的什么感受),笔者视为光宣文人或近代士人的精神基质(basic quality of sprites),而“妙手空空”恰好承担了这一“文学季候”的需求。
对“妙手空空”作这样的“阐释”或“超拔”是危险的。不过,我所做的不是“训诂”,只是“阐释”,而且仅仅是阐释其中的一个可能的面向。最重要的是,我希望把我的阐释建立在一种“文学季候”之上。在我看来,近代士人群体性的长时段的症候式写作,使这种思路成为可能。近代士人生当“千古未有之变局”,自然会“春江水暖鸭先知”。笔者认为,不论自觉或不自觉,这一切会投射或渗透到最敏感的士人的精神世界或潜意识之中。他们落笔时,未必都念兹在兹,然而群体性的症候式写作,有非他们自己所能知其所以然者。通过“症候式的阅读”(symptomatic reading),“妙手空空”找到了安放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