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物育种技术发展的回望与思考
何红中 周瑞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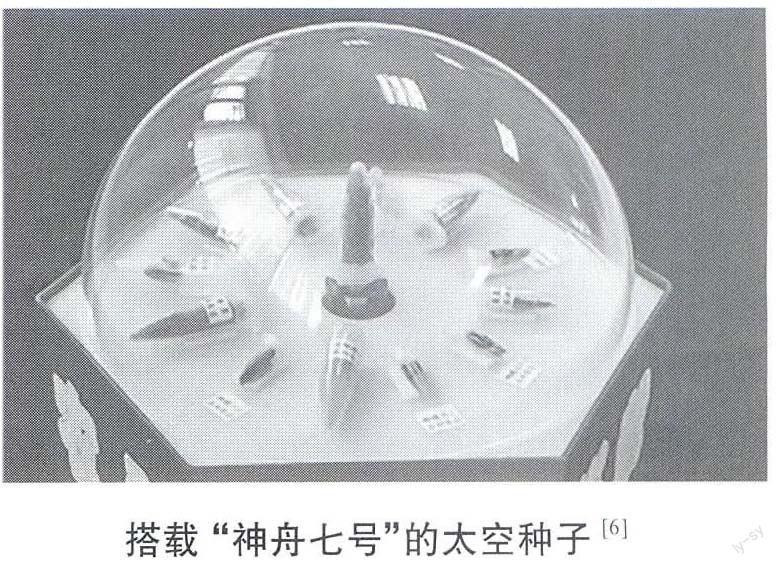
在中国,作物育种有着悠久的传统,到近现代通过引入西方先进技术,重又走到了世界的前列。随着转基因育种技术的崛起以及面对由此带来的生态与健康风险,中国的作物育种研究更应当在现代与传统技术之间寻求均衡发展。
选育优良作物新品种是提高作物产量、改善作物品质和增强作物抵御不良环境能力之根本途径。伴随着人类农业生产经验的积累和科学技术的进步,作物育种方法不断得以更新、发展与融合。考古发掘证明,中国拥有一万多年的谷物种植历史。华夏先民在作物育种的理论与实践上留下了丰厚的遗产。到了近现代,中国科技人员借鉴西方育种技术,开发了大量农作物优良品种,并在某些领域达到世界先进水平。然而,新兴转基因育种技术的引入也引起了社会争议,带来了生态及健康方面值得关注的潜在风险。本文综述中国作物育种的历史及现况,并思考其发展方向。
先民对作物遗传和变异性之认识
遗传与变异是物种形成与生物进化的基础,对此加以认识是品种选育的前提条件。从早期的果实种子采集到作物的驯化,先民们想必对作物的某些遗传和变异特性有所了解,并对其中一些性状进行了有意或无意的选择,最后培育成人工栽培作物,并给它们取了专门名称。甲骨文和《诗经》中有“稷、粱、糜、芑”等字,就是对谷类不同品种或类型的称呼。
对作物遗传性的认识
我国保存的一些古典文献资料显示,古人很早就认识了作物的遗传性。如著成于公元前329年的《吕氏春秋》一书中,有“夫种麦而得麦,种稷而得稷,人不怪也”的记载。这种朴素的认识表明,当时人们已经把作物的遗传性看作是正常的自然现象。
东汉王充在《论衡·奇怪篇》里用“物生自类本种”描述生物遗传性,他说的“本种”有“种的概念含义。他还把在自然条件下能否交配产生后代作为种的特性。这跟18世纪瑞典生物分类学家林奈(C.Linnaeus)关于物种“按生殖规律”产生的概念相似。
北魏时期的《齐民要术》将遗传现象称为“天性”、“质性”或“性”等。“性”是相对固定、世代相传的,生产中必须依据作物不同的“性”,采取不同的技术措施。这些大致相当于现代遗传性的概念。《齐民要术》还指出了同一作物的不同品种,其遗传性不同的现象。比如说,谷子“质性有强弱”,粱、秫“性不零落”,对当时的育种工作无疑是具有指导意义的。
对作物变异性的认识
关于作物的变异性,中国古代早期文献亦有记述。《诗经·豳风·七月》就说:“黍稷重穆,禾麻菽麦。”又《鲁颂·閟宫》云:“黍稷重穆,稙樨菽麦。”重、穆、植、稚,毛亨释为“后熟日重,先熟日穆”,“先种日植,后种日稚”。古人用重、穆、稙、稚来称呼谷子的不同品种类型,表明已经认识了同一作物的性状也会发生变异的事实。
《国语·晋语四》说:“黍稷无成,不能为荣。黍不为黍,不能蕃庑。稷不为稷,不能蕃殖。”作物发生变异将因不能正常繁殖而影响种植。王充在《论衡·讲瑞》中同样认为,特殊变异的特性不能遗传而自成种类。“试种嘉禾之实,不能得嘉禾”,看来当时人们曾进行过试种,发现不能保持亲本多穗的性状,从而表明“嘉禾”是不具遗传性的变异。
北魏贾思勰对作物变异性有了更深刻的认识。《齐民要术·种谷》有曰:“凡谷成熟有早晚,苗秆有高下,收实有多少,质性有强弱,米味有美恶,粒实有息耗。”不仅指出了不同谷子的成熟期差异,还指出了其他各种性状差异。这属于生物变异性范畴,或者是以生物变异性为基础的。贾思勰又说:“山田种强苗,以避风霜;泽田种弱苗,以求华实也”,不同地域对谷子的性状有不同要求,可以改变其最后的性状。
王充把“物生自类本种”和“命定论”联系起来,不承认物性是可以在一定条件下改变的,他只注意到生物中不可遗传的特殊变异,而忽视了生物遗传过程中逐步积累起来的新性状的可遗传变异。贾思勰指出谷子的性状不但可以遗传,而且可以改变,从事实上揭示了生物变异的普遍性,并考察了这种变异发生的条件和原因,比王充是一个巨大的进步。
古人对作物生长发育、遗传变异与环境关系的认识是不断提高的。元代王祯的《农书》指出:“凡物之种,各有所宜。故宜于冀、兖者,不可以青、徐论;宜于荆、扬者,不可以雍、豫论。……谷之为品不一,风土各有所宜。”又明代宋应星《天工开物·乃粒》说:“生人不能久生,而五谷生之;五谷不能自生,而生人生之。土脉历时代而异,种性随水土而分。”自然环境随着时间的流逝在变化,物种的遗传性也会随着环境条件的改变而有所变异。
古代作物品种选育的实践及历程
古代对于品种遗传性和变异性的认识是先民对作物进行驯化和栽培的长期实践结果,反过来又指导了作物栽培实践和各种育种活动,并促进了育种技术上的发明与创新。
早期作物品种选育
有关作物早期驯化中的品种选育细节,可以通过一些民俗学资料来寻求答案。例如,我国南方的一些少数民族仍保留着原始农业的成分,很早就开始进行选种和传种活动。
台湾东南小岛兰屿的雅美人,把不同的谷子撒播后基本不再管理和保护,虽在收获时注意选割最大的穗并按大小分别堆放捆扎,却没有任何选种行为。不过,正是这种粗放的做法,使得生长期的植株跟莠草杂生,促成野生基因型和驯化谷子的渐渗杂交,保证了野生基因向栽培型输送,从而孕育出一些新的品种,培育出的谷子有利于原始表型的生存。
进入驯化的高级阶段后,人类的品种选育能力得到提高。台湾当地少数民族已注重除草和疏苗,并有意选择那些较高又整齐的单茎植株,收获时一个一个折取穗,分品种进行,捆扎成束背回家再第二次选种,接着干燥贮藏。疏苗和穗选对品种选育有决定性意义,因为这样容易丢掉原始的基因型、避免同进化型植株发生杂交的可能性。从收获到贮藏,再到暂时持续地隔离和分别下种,有意识的品种选育是作物驯化过程中一个关键性的转折点。
早期文献也记载了先民从事良种选育的活动。《诗经·大雅·生民》中有:“诞后稷之穑,有相之道;茀厥丰草,种之黄茂,实方实苞,实种实裦,实发实秀,实坚实好,实颖实栗,即有邰家室”。“有相之道”指选择耕地,“茀厥茂草”指清理场地,“种之黄茂,实方实苞”指选种。“黄茂”是光润美好,“方”是硕大,“苞”是饱满或充满活力。这实质上是一种谷子的粒选法,也是对选种的具体要求。
混合选择法育种
混合选择法是一种非常古老的育种方法,指从作物品种群体中,根据一定的表现性状如株型、成熟期、产量、抗性等,选出具有近似特点的优良个体如单穗、单铃等,与下一代混合留种、种植的育种方法。
最迟至西汉时代,人们已认识了混合选择法的精髓,这在《汜胜之书》中有明确记载。例如,书中说麦子的选种应“候熟可获,择穗大强者”,谷子的选种则应“取禾种,择高大者”。至北魏时期,作物的混合选择法在技术上有了新进步。《齐民要术·收种》说:“粟、黍、穄、粱、秫,常岁岁别收,选好穗纯色者,劁刈高悬之。至春治取,别种,以拟明年种子。……其别种种子,常须加锄。……先治而别埋,还以所治蓑草蔽窖。”这是在穗选法基础上建立的一套从选种、留种到“种子田”的育种制度,与今天混合选种法颇为相似,比德国在1867年改良麦种时使用的混合选择法要早了1300多年。
到明代又出现了在粒选基础上的系统选育技术。耿荫楼《国脉民天》主张五谷、豆类、蔬菜等“颗颗粒粒皆要仔细精拣,肥实光润者方堪种用”,要求种子须种在种子田内,且种子田要“比别地粪力、耕锄俱加数倍”,第二年“用此种所结之实内,仍拣上上极大者作为种子”,如此“三年三番”便能选育出优良品种。耿荫楼所阐述的有关混合选择法的理论和技术,显然比《齐民要术》中总结的育种方法更先进和完善。
混合选择法操作简便省事,对当地生态环境具良好适应性,可以通过一次选择获得大量种子并尽快应用于生产,有时能在较短时期内从原有品种的群体中分离出优良类型,还可使异花授粉作物避免因近亲繁殖而造成生活力衰退。当然,由于不能对中选个体进行后代鉴定,这种方法难免会导致因遗传特性不良的个体混入而降低选择效果的情况。
单株选择法育种
所谓单株选择法,就是从某些优良性状的单株(穗)作物中,选育出一个新的优良品种的方法,亦称“一株传”、“一穗传”。目前,世界上一般把单株选择法归功于农学家德维尔莫兰(L.de Vilmorin)在1856年开始的甜菜选种。实际上,中国人很早就普遍采用此法培育作物品种了。
根据北宋欧阳修《洛阳牡丹记》和蔡襄《荔枝谱》记载,后来被称为“御袍黄”的牡丹和“小陈紫”、“游家紫”、“宋公”、“龙牙”4种荔枝,都是在单株变异基础上经人工选择培育而来的。应该说,中国单株选择法培育花卉、水果品种的历史非常悠久,但不知何故,关于大田作物单株选择法的记载要晚得多,较早见诸文献的有两个农作物品种,即“白粟”和“御稻”。这两个品种都跟清朝的康熙皇帝有关。
《康熙几暇格物编》有如下记述:“乌喇地方树孔中忽生白粟一科,土人以其子播获,生生不已,遂盈亩顷。味即甘美,性复柔和。有以此粟来献者,朕命布植于山庄之内,茎、干、叶、穗较他种倍大,熟亦先时。作为糕饵,洁白如糯稻,而细腻香滑殆过之。”白粟单株选择育种的成功,给了康熙很大的启发。后来他又应用单株选择法,成功选育出一种早熟高产的优质水稻,因“其米色微红而细长,气香而味腴,以其生自苑田,故名御稻米”。后来他又在承德和江南大力推广种植御稻,在承德解决了以前种稻不成熟的问题,推进了水稻的北移,在江南则促进了双季稻的发展。
康熙及时吸收劳动人民的经验,运用单株选择法,亲自进行新品种的试验,目的明确,步骤完整,并将选育、试种、品种对照试验以及推广的全部过程详细记录下来,与现代单株选择程序已完全吻合。这是古人运用单株选择法育种的典型事例,为世界选种史增添了一份弥足珍贵的科学实验文献。
另外,清代包世臣著有《齐民四术》一书,其中的“农政”一卷讲到,育种要在肥地中选择单穗,分收分存。他把这种单穗选择育种称为“一穗传”,那实际上也是地地道道的单株选择法。
单株选择法简便易行,且多次单株选择可定向累积变异,有可能选出超过原始群体最优良单株的新品种,收效快,是古人常用的有效育种方法。当然,相对于混合选择法,单株选择法也有缺点,即费时、费工、占地,用于异花授粉植物易引起后代生活力的衰退。
集团选择法育种
集团选择法由混合选择法衍生而来,是指当现有品种类型较多时,可按不同性状如早熟和晚熟等,分别选择单株,将性状相同的单株归为一个集团,混合留种,下一代再按集团分别种植,并与原品种及对照品种比较,最后选出较优集团加以繁殖和推广。
清代有类似现代集团选择法的记载,见于包世臣所著《齐民四术》第一卷《农政》“养种”一篇:“稻、麦、黍、粟、麻、豆各谷,俱有迟早数种。于田内择其尤肥实黄绽满穑者,摘出为种,尤谨择其熟之齐否,迟早各置一处,不可杂。晒极干,黍粟各种,以绳系悬透风避湿之所。稻种少者,亦可择肥好之穑,断一节悬当风如黍粟。”这里提到将作物早、晚熟的单株分别摘出,分别存放选种,就是当时的集团选择法育种。
集团选择法适用于异花授粉和常异花授粉作物,特点是简单易行,节省人力、物力、财力,且后代生活力不易衰退。该育种法比混合选择法快,但比单株选择法要慢。
近现代作物育种技术发展举要
近代育种技术和理论的发展始于西欧。1719年,费尔柴尔德(T.Fairchild)最早进行植物人工杂交并获得杂种,但作物育种的大规模迅速发展则要归功于孟德尔(G.J.Mendel)。大田作物的传统育种比较重视杂种优势的研究与利用,现代育种则更多利用生物技术展现特殊优势。就技术角度而言,现代除有传统的育种外,还大力开拓新的途径与方法,包括人工诱变育种、倍性育种、细胞和基因工程育种等。这里选择读者可能感兴趣的几种加以介绍。
诱变育种法
诱变育种是指通过物理、化学因素诱导动植物发生遗传特性的变异,再从变异群体中选择符合人们某种要求的单株个体,进而培育成新的品种或种质的育种方法。它要通过引起植物基因突变来实现。现代诱变育种历史可以追溯到1920年代后期,自1970年代以来,诱变因素从早期的紫外线、X射线发展到γ射线、B射线、中子、多种化学诱变剂和生理活性物质,诱变方法从单一处理发展到复合处理;同时诱变育种与杂交育种密切结合,大大提高了诱变育种的实际意义。
1957年,中国农业科学院成立了我国第一个原子能农业利州研究室。1960年代中期开始在水稻、小麦、大豆等主要作物上利用辐射诱变培育新品种,且在生产上得到了应用。1960年代以来,基于太空环境诱变的航天育种渐渐起步,我国进行了较全面的研究和应用,航天育种研究已达到世界先进水平。目前,我国通过诱变育种已经培育了水稻、小麦、棉花、玉米、谷子、大豆、蔬菜、油菜、绿肥等作物的诸多优良品种。
染色体工程育种法
染色体工程育种是指按预先设计,有计划地添加、削减和替换同种或异种染色体,或者染色体片段甚至整个染色体组,以改变植物染色体组成,扩大有利变异范围,进而培育新品种或新种质的育种方法。染色体工程育种包括单倍体和多倍体育种等多种方式。
单倍体植株经染色体加倍后,选出的优良纯合系表现整齐,可缩短育种年限2~3年,如果能进一步提高诱导频率,并与杂交、诱变育种等结合应用,则在作物品种改良上的作用更为显著。中国应用单倍体育种法已育成了烟草、水稻、小麦等的一些优良品种。
多倍体育种是指利用人工诱变或自然变异等,通过细胞染色体组加倍获得多倍体育种材料,选育出人们需要的优良品种。1916年,温克勒(H.Winkler)在番茄与龙葵嫁接试验中发现了番茄的四倍体。我国于1950年代开始多倍体育种研究,1970年代以来已培育出三倍体和四倍体的西瓜,四倍体的甜瓜以及萝卜、番茄、茄子、芦笋、辣椒和黄瓜等的多倍体材料。
中同通过染色体工程培育了一批优良新品种。例如,将小麦与长穗偃麦草杂交育成了小偃4号、5号和6号,其中小偃6号已成为北方冬麦区的主栽品种,截至2015年,累计推广面积达1000万公顷,增产400万吨。用棉属中A染色体组的亚洲棉与G染色体组的澳洲野牛比克棉,人工合成了AG复合染色体组亚比棉。它集棉、油、蛋白质多用途于一体,并具有抗病、虫、鼠害的优良种性。
细胞工程育种法
细胞工程育种是指利用细胞全能性的原理,用植物体细胞融合与杂交及组织培养的方法获得杂种细胞,从而改良植物品种或创造植物新类型的技术。
1937—1938年,温特(F.W.Went)、戈特雷(R.J.Gautheret)和诺贝古(P.Nob6court)由于发现生长素和B族维生素对植物根生长有促进作用,并离体培养了胡萝卜组织,使细胞增殖,从而一起成为植物组织培养的奠基人。1962年,华裔加籍科学家高国楠发现聚乙二醇可促使植物原生质体融合,植物细胞融合技术初步建立。1972年,美国科学家卡尔森(P.S.Carlson)等人用NaNO3作为融合诱导剂,进行烟草原生质体融合,获得了世界上第一个体细胞杂种植株。从此,细胞工程育种进入快速发展时期。
人们利用细胞工程育种技术,已经培育了大量具有抗旱、抗倒伏、抗病虫害特性的优质高产品种,大大提高了粮食产量。在这方面,我国已迈入世界最先进行列。目前,已经有上百种植物能由原生质体培养再生植株,还出现了属间和族间杂种原生质体的培养,从而超越了种间、属间和族间有性杂交的不亲和性障碍,有可能给植物育种带来新突破。
转基因育种技术之发展及安全性问题
转基因育种技术是根据育种目标,从供体生物中分离目标基因,经DNA重组与遗传转化或直接运载进入受体作物,通过筛选获得稳定表达的遗传工程体,并由田间试验与大田选择,育成转基因新品种或种质资源的育种方法。
转基因育种技术的发展
转基因育种研究始于1980年代初。1983年全球第一例转基因烟草在美国问世,1986年全世界有5例转基因育种首次获准进入田间试验,1994年首个转基因育种产品“延熟保鲜转基因番茄”在美获准进入市场。转基因育种实现规模化应用到现在已近20年,转基因作物的种类、种植面积、加工食物品种和应用人群迅速扩大。目前,市场上的转基因作物有大豆、玉米、棉花、油菜、马铃薯、南瓜、西红柿和木瓜等(前三种作物种植最广泛)。全球主要农作物种植面积中82%的大豆、68%的棉花、30%的玉米、25%的油菜都是转基因品种;全球商业化应用转基因作物的国家已达65个,批准商业化种植的转基因作物增至28种。
中国的转基因育种研究始于1980年代实施的“863计划”。之后,转基因耐储藏番茄、抗病毒番茄和甜椒、抗虫烟草和棉花等一批转基因植物接连问世。另外,国家“973计划”、战略性新兴产业计划、科技部专项计划等也对转基因育种给予了更大支持。特别是从2008年实施“转基因生物新品种培育”科技重大专项以来,实现了棉花、水稻、玉米、小麦、大豆五大作物的转基因育种与常规育种技术之深度结合,自主创新研究得到快速发展。目前,我国已拥有一支上万人的转基因研发队伍,初步建成世界上为数不多的,包括基因发掘、遗传转化、良种培育、产业开发、应用推广以及安全评价等关键环节在内的转基因育种创新和产业开发体系;已拥有一大批功能基因及相关核心技术的自主知识产权。
有关转基因育种安全性的争议
虽然从1990年代中期开始,转基因育种已进入产业化生产阶段,但这种技术的安全性至今仍在全球范围内引起激烈争议。有的反对者认为,转基因育种可能对人类的健康及生存环境构成威胁。1999年美国康奈尔大学的一个研究组在《自然》周刊上发表文章声称,转基因抗虫玉米的花粉飘到一种名叫“马利筋”的杂草上,用其叶片饲喂大斑蝶导致44%的幼虫死亡。又如在加拿大由于基因漂流,个别油菜植株可以抗一种或多种除草剂,被人称为“超级杂草”。同样的争论也牵涉中国。2002年6月的英文版《中国日报》发表《转基因棉破坏环境》,而“绿色和平组织”在其网站上刊登26页的报告,声称“棉农将面对不受控制的超级害虫”,“转基因抗虫棉不仅未解决问题,反而制造了更多问题”,“棉农将被迫使用更多、更毒的农药”。
针对上述的争议事件,一些研究者经调查指出,争议或由于所依据的实验本身存在错误,或由于所涉及的问题中包含其他的环境因素影响,或由于科学推论不严谨等,假如以此来禁止转基因育种是没有道理的。尤其关于中国的抗虫棉事件,重要事实是,转Bt-CrylA基因抗虫棉已得到多年认证与实践,挽救了岌岌可危的棉花生产,大大减轻了棉铃虫对玉米、大豆等的危害,使棉花杀虫剂用量降低了70%~80%。它还出口到印度和巴基斯坦等国。
在制止盲目排斥转基因育种的同时,也应科学认识转基因育种的潜在风险,这类风险可能存在于许多方面。一是“超级杂草”的风险。目前转入作物的基因以抗除草剂为多,其次为抗虫和抗病毒,然后是抗逆。若这些基因逐渐在野生种群里定居,就可能具有潜在的选择优势,演化为难以控制的“超级杂草”。二是35S启动子生物安全性的风险。启动子为基因表达所必需,决定外源基因表达的空间、时间与强度等。35S启动子是其中最常用的,被转入许多转基因植物中。问题在于,如果35S启动子插入隐性病毒基因组旁,可能重新活化病毒;启动子插入某一编码毒素蛋白质的基因上游,可能增强该毒素的合成。三是抗生素抗性标记基因生物安全性的风险。目前,转基因育种使用细菌编码的抗生素抗性基因作为选择性标记。但越来越多的报道指出,细菌可以获得对多种抗生素的抗性。这导致人们怀疑:转基因植物中的抗性基因是否会通过食物,在肠道中水平转移给体内微生物,而影响抗生素治疗的有效性;是否会使人体产生耐药性。四是转基因食品安全性的风险。转基因食品对人类的可能危害主要有三大类:含有已知或未知的毒素,对人体产生毒害作用;含有已知或未知的过敏源,引起人体过敏反应;使食品某些营养成分或质量发生变化,从而危及人体健康。五是作物遗传多样性的风险。与常规品种相比,转基因作物因在品质改良、良种选育等方面具有优势而被广泛种植,这就减少了常规品种的种植种类与面积,造成作物遗传多样性逐渐减少,影响农业生态系统的整体稳定性。
结语和展望
古代中国人通过不断实践和反复验证,积累了关于遗传变异和选种育种的丰富经验与知识,培育了诸多优良作物品种,这是值得我们珍视的宝贵遗产。用现代科学理论来解释,先民的各种育种技术都是基于杂交育种方式,其本质就是基因重组,只不过是在自然条件下发生的。先民们积累的关于遗传和变异性的认识,局限于直观的现象描述和感性层面,未形成相对完整并具有分析归纳特点的现代遗传学概念。
但历史与现实仍存在交集,直到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我国科学工作者仍在继承原有的品种改良传统,取得了很多成果。之后,他们积极学习外国先进的育种技术,谱写了中国农作物育种的新篇章。中国近现代作物育种为时不过一百多年,但通过新技术的引进和运用,已取得十分了不起的成就,且在很多领域走到了世界前列。另外从育种史角度看,以往每种育种方式都经过几十年甚至上千年的改良与检验,而随着现代生物技术的飞速发展,转基因育种的产业化速度大大高于其他方式。目前,转基因育种已成为新的科技革命的强大动力和创新的重要方向。
今后中国作物育种技术要在转基因与传统育种之间寻求均衡发展,要从保障人类健康、发展农业生产、维护生态平衡与社会安全的宗旨出发,循着辨证思考、科学验证与审慎而行的途径,进一步摸索发展农业生产力之有效途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