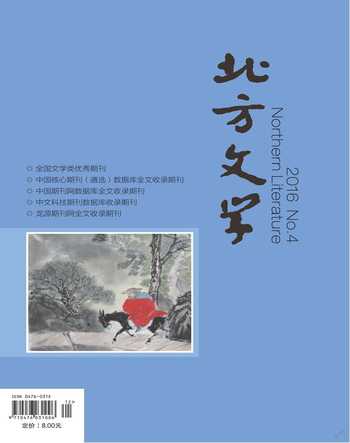《红旗谱》与《白鹿原》——家族“政史”与“秘史”
丁晓莹
摘 要:《红旗谱》和《白鹿原》作为当代家族历史小说的经典之作,都具有宏大的史诗性叙事的特点。它们都是以几个家族间发生的故事为主线,对特定时期的历史特点和社会背景进行描写和诠释。但是二者因为创作年代以及作者对于当时社会的历史态度的差异,而使得它们家族叙事的视角大相径庭。总体来看,《红旗谱》可以说是一部“政史”,而《白鹿原》则是一部民族的秘史。即前者多是从政治角度来进行家族叙事,而后者则更多的从民间视角来叙写家族的历史。
关键词:家族叙事;政治;民间
梁斌的《红旗谱》是“十七年”文学中的革命历史题材小说,在上世纪五六年代里,工农兵阶级是“革命历史小说”描写的主要对象,《红旗谱》也不例外。在这样一部正统的小说里,主人公一定是代表朴素农民阶级的朱老忠,作者热情讴歌朱老忠,赞颂社会主义革命。而在《白鹿原》中,作者并不真正关心最后是谁统治和征服了白鹿村,作者探讨的是传统的道德秩序有没有被打破以及在现代化冲击下传统文化的生存问题。梁斌处在建国初期的环境中,不得不考虑小说创作的政治影响;而陈忠实在90年代这样一个相对开放的时代里,在历史小说经历了由政治性到启蒙的转折后,不得不以民间的姿态来对整个社会文化进行审视进行文学创作。
一
梁斌和陈忠实都是农民作家,小说中都写到了维系家族血亲秩序的工具—祠堂。但两者祠堂叙写得作用却大不相同。《红旗谱》中的庙堂已经成为阶级斗争的工具。在描写冯兰池要砸掉锁井镇上的古钟时,镇上的人们都认为冯老兰是在霸占公有的“庙产”,而朱老忠的父亲朱老巩也因此而与冯氏家族结仇。而后来冯氏把四十八村的庙产契书给他看时,他更是气愤不已。庙堂以及古钟对千里堤的人民来说是十分重要的,而以朱、严两家为代表的贫民阶级,对于地主阶级冯氏的愤恨在于冯老兰的强取豪夺。这里对庙堂的描写表明俩两大家族产生矛盾的根源是经济水平的差异所致使其阶级差别。到后来春兰甚至有意穿了带有“革命”字样的绣花衣服去了庙会。春兰之的举动是因为庙会作为传统的节日,是村民邻里之间相互交流走动的最好时机。而这样描写体现出春兰决意参加革命的决心。在《红旗谱》这样的红色经典小说中,宗庙祠堂已然成为政治阶级叙事的工具。
《白鹿原》中的祠堂却始终是民间历史文化的代名词。这里的祠堂近百年不倒,它是白鹿村传统的仁义道德文化的承载体。仁义村大大小小的许多事物都是在这祠堂里进行的。白、鹿两家拿出自己的大笔钱财来,出钱又出力的修建祠堂,是对白鹿村传统乡规民约的一种保护和维持。而后来在祠堂里对淫荡的田小娥实施酷刑,以及对白孝文的鞭打,都是在维护传统的儒家基本道德秩序。后来黑娃等人革命后将祠堂毁坏,是对这种传统家族秩序的一种反抗与推翻。白嘉轩等将祠堂修好后便在其中立碑,上面写着“仁义村”,同时他们还将祠堂作为新式学堂来使用,这说明白嘉轩秉承着祖辈父辈们沿袭的理念,立志要把白鹿原“耕读传家”的仁义传统传承下去。陈忠实对家族祠堂的是从文化角度入手,意在探讨传统儒学在家族里的生存危机,是站在民间文化的角度上来进行反思。而梁斌在创作《红旗谱》时,对家族庙台的描写则是强调地主阶级对于农民阶级的蛮横剥削,是一种建立在国家权力基础之上的意识形态书写。
二
《白鹿原》和《红旗谱》分别塑造了诸如白嘉轩、鹿子霖、朱老忠、冯老兰等鲜明人物形象。但因为它们的叙事视角不同,小说中的这些人物表现出风格迥异的性格特点和道德人格。
从阶级性来说,《红旗谱》所塑造的核心人物都有十分明显的阶级性,朱老忠属于典型的农民,而冯老兰则是有钱有势的大地主。朱、冯阶级性的不同,决定他们注定只能是仇人,他们之间只能是矛盾和冲突,而在《白鹿原》中这种阶级性却并不是作者叙写的重点,甚至可以说在是几乎不存在的。白嘉轩是富农,也可以说是所谓的地主阶级,可是他与长工鹿三之间并不存在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相反,他们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关系,为维护白鹿村的传统习俗而共同努力。如果按照国家权力所推崇的方式来写,那么白嘉轩与鹿三只能是雇佣与被雇佣的关系。同属于“地主阶级 ”的冯老兰和白嘉轩,在性格以及为人处事方面截然不同的。冯老兰被梁斌塑造为一个十恶不赦的土豪恶霸,朱、严两大家族子子孙孙也因为冯氏一族的无理霸道而惨遭压迫和欺辱。作者有意通过这种家族对立来表现阶级对立,突出小说政治意识形态的叙事特点。由此可见,梁斌也是当时国家权力的代言人之一。而《白鹿原》并没有把家境殷实的白嘉轩一家塑造成为像冯氏一样欺善怕恶的恶人形象,而是把他写成一个尽职尽责,安分守已,为白鹿村的乡民做出巨大的贡献的理想男子。由此可见,在这部小说里没有像《红旗谱》一样的阶级斗争和矛盾,没有绝对的阶级成分划分,只有遵守乡规民约与否之分。
三
两部小说都塑造了许多知识分子人物形象,《红旗谱》中的贾湘农与《白鹿原》中的朱先生两个人物都是知识分子阶层,但由于小说叙事视角不同,致使人物角色有所差异。贾湘农是共产党员,为宣传社会主义事业而去农村开展思想动员工作。对他而言党就是一切,小说突出了其政治地位和政治目标,这也从侧面说明了在革命家族题材小说里,任何一个人物,不论文化程度的高低,都具有一定的阶级性和意识形态性。而《白鹿原》中的朱先生,则是“神仙”一般的知识分子。朱先生给人的印象是儒雅、讲究,每次遇事都能逢凶化吉,且多次充当家族间矛盾、沖突时的和事老,由此可见,朱先生身上体现的是恪守儒家道德的理想文化人格与品格,也就是说,作者更倾向于塑造这样一位民间圣人,而不是在作品中将人分成三六九等,或是不同的阶级成分。同样是知识分子,可是在两部长篇历史小说中对于理想型知识分子的塑造却是截然不同的,归根结底,还是因为《红旗谱》与《白鹿原》是站在不同的叙事角度来进行叙述的,在宏大国家叙事结构里,知识分子应该是具有鲜明的阶级觉悟的,同时也应该积极地宣传民主革命;而在民间叙事里,人与人之间并没有明显的阶级之分,有的只是仁义道德,儒家知识分子为维护传统礼教而克己奉公。
西方著名批评家韦勒克在其《文学理论》中曾指出小说中的“人物塑造有静态型的,也有动态型和发展型的。”①以具体的核心人物为例,《紅旗谱》中的朱老忠应该算是一个动态的人物,而《白鹿原》中的主人公白嘉轩则是一个相对静态的人物。这里的动态主要指的是人物随着社会时代的变迁而发生的变化,即人物并不是一直呈现出一种状态;静态则指的是人物在历史变迁中始终保持一种较为稳定的状态而不变。朱老忠是一个动态的人物,主要是因为他在党的领导和教育之下“成长”了许多,刚开始朱老忠只是一个地道的农民,带有强烈的家族复仇情绪,遇事有些鲁莽、冲动,后来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大环境里,他成长了,在精神和思想层面上都有很大的进步。一开始他对共产党还有所怀疑,当然这是由其自身的阶级局限性所致,而当他觉悟发现只有在党领导下才能打倒诸如冯老兰这样的土豪劣绅时,他决定加入共产党的行列。通过朱老忠的成长作者想表达的是国家机器对于其个人成长的重要影响。如果没有党的领导与关怀,他不可能摆脱封建思想,树立正确的价值观。而《白鹿原》中的白嘉轩一直都是一个静态的人物。不论外面的时代怎样风起云涌,他依然尽职尽责的守护着白氏一族,以及整个白鹿村。可以说,白嘉轩一直生活在传统的民风淳朴的“儒家”社会里,不论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如果他们踏足白鹿村,并掀起腥风血雨,那都是他应该“抵制”的对象。因而历史时代的变迁并不影响白嘉轩的性格发展以及为人处事的方式,更没有对其造成思想上的指导,在他心里,最重要的是宗法血缘,正统的人伦秩序,而不是阶级斗争。
结语
作为五十年代国家权力指导文学的代表作之一,《红旗谱》在叙事结构上是宏大而广阔的,而且是严格地按照阶级意识形态的标准来描写农民家族与地主家族之间的斗争;而在开放多元化的九十年代形成的《白鹿原》则是运用民间文化批评的角度来塑造儒与非儒家族之间的恩怨情仇。两者同为家族历史小说,但是叙事视角却是完全不同的,这与他们各自所处时代的政治环境有密切联系,也与作者的写作态度息息相关。一个运用的是正统的国家叙事话语,而另一个则是来自于民间的话语。
注释:
①[美]勒内·韦勒克:《文学理论》,文化艺术出版社2010年1月,第249页。
参考文献:
[1] 梁斌.红旗谱[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0:1-569.
[2] 陈忠实.白鹿原[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1-632.
[3] 曹书文.中国当代家族小说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1-3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