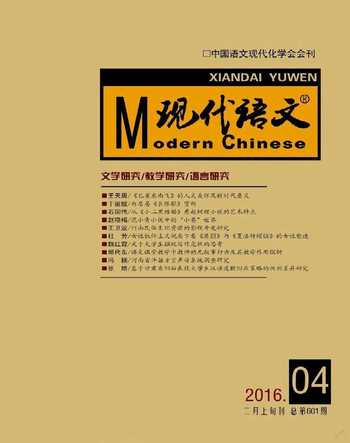寻找精神诗意的栖居地
摘 要:近年来,底层写作作为一种写作热潮进入了文学史的创作领域,以一种新的写作思潮的形式丰富着当代文学的文学史写作,显示着文学史不断发展的蓬勃生机。底层写作是否可以归为思潮创作,仍需时间的检验。然而底层写作毕竟使一个群体、一个阶层走进人们的视域,成为了人们关注的对象。本文试图通过方方的《奔跑的火光》来阐释底层写作这一文学现象。
关键词:底层写作 《奔跑的火光》 “自下而上”
《奔跑的火光》是方方在新世纪极具影响力但却十分矛盾的一部作品。说它具有影响力是因为这部作品继续了方方对于社会下层人民生活的关注,继续了方方对于原生态生命意识的同情与无奈;说它具有矛盾性是因为这样一部内容深刻的文学作品却没有得到文坛上相应的重视。它被淹没在方方众多的作品当中,甚至很少有批评家关注它。然而,《奔跑的火光》的价值却是不容忽视的。它发表于2001年,这时正是中国底层写作刚刚起步的新时期。这篇小说对于底层写作的意义,无疑是起到了开山之作的重大作用。
一、底层写作与“自下而上”的文学书写
在对文学作品的书写问题上,有两种角度可供我们来选择,一种是自上而下的文学书写方式,这种书写方式把古代的帝王将相作为文学作品所着重书写的对象,对人物的生活起居进行细致的描摹,在对人物的书写过程中来对人生、对世态进行言志与抒情;除此之外,还有一种文学书写方式,即始于西方的“自下而上”的文学书写方式。文学作品创作中所提倡的“自下而上”的写作方式缘于历史学的书写方式。这种书写方式是以下层阶级的眼光来关注历史,得名于汤姆逊的《自下而上看的历史学》(载于《时代周刊文学副刊》)。这些史学家把关注的注意力从统治者和精英人物转向普通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活动和经历,以哈特编的《列兵威勒的通信,1809—1828》为肇端。自古以来,历史著作的传统都必须是描述伟人的行为和动机。司马迁作《史记》,“历帝王之岁月”“录人臣之行状”。[1]虽然他们已经开明到能为陈涉吴广立传,甚至为盗跖立传,但普通民众的踪迹依然难寻。在西方史学著作中,从来也是皇帝、国王、教皇、将军充斥其间,没有普通民众的地位。而随着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普通民众越来越受到人民的重视。正如恩格斯所说的:“自从阶级产生以来,从来没有过一个时期社会上可以没有劳动阶级而存在。……有一件事情是很明显的,不从事生产的社会上层无论发生什么变化,没有一个生产者的阶级,社会就不能存在。”[2]这种史学研究的方法在文学创作上就表现为对底层人民的关注,描写底层社会的原生态,即近年来很热门的所谓的“底层写作”。
把普通的百姓作为书写对象,在文学作品中,一些有身位的、能左右历史进程的人不再出现在文学作品中,他们所描写的对象,往往都是某个公司的小员工、书记员,普通农民、打工者。他们用着肩扛摄像机的方式来对主人公进行动态生活的描述,不掺进自己的感情,也可以说是对人物进行冷叙述,但是人们仍然可以在这些作品中感觉到作者对世态的批判,或者是对人生的感怀,这也可以算是对底层写作的另一种解释。底层写作注重对社会底层阶级的关怀,注重对人物苦难的感伤性描述。《奔跑的火光》就是以一位下层歌者英芝短暂的一生来结构全篇。英芝从始至终都是以一个弱质女流的形象充斥于作者的眼球,她没有工作、没有爱情、没有亲情,甚至她唯一的信念房子对于她来说也仅仅是一个梦想。在她的周遭,只有她一个人在為了梦想而努力,这也让她成为了一个异形人。“这个世界大多数人是用脚趾头来思索世界和选择道路的,如果有人偏要用头脑和思想选择道路,那么就应该承担起不合潮流的孤寂,像一个身躯佝偻得如同问号的老人一般,伫立在路边静静地观望和怀疑。”[3]
二、底层写作与对“底层”之界定
近两年,“底层写作”正在成为一个备受关注的话题。《文艺争鸣》2005年第3期开辟“关于新世纪文学?在生存中写作专辑”,推介“打工文学”“打工诗人”。2005年6月15日,《中华读书报》刊登了《新世纪文学的“新表现”》一文,明确提出:“新世纪文学”不可忽视“打工文学”。[4]至此,沉默多时的“底层写作”终于浮出水面,在正统批评界争得一席之地,由自说自话,走向众人评说,接受批评界的审视、打量。对于一个新的文学现象,这无疑是件好事,它打开了学术界研究“底层写作”的大门。自2004年以来,“底层写作”在中国文学界引起了越来越广泛的关注。这些作品登上了《当代》《人民文学》《上海文学》《十月》等大型文学期刊,2006年《小说选刊》改版,开始对“底层写作”进行积极而持续的关注。《小说选刊》是当代文学界具有风向标意义的一种选刊,我们可以将它的改版视为“底层写作”为文学界高度认可的标志。
底层写作从一出现便成为了一个毁誉参半、褒贬不一的文学现象,它本身有着太多的不确定因素,对概念的界定、对所谓“苦难”的描述、对其文学性的评价以及这一文学现象中所彰显的情感和立场都是不确定的,底层写作尽管受到各界的关注且呼声很高,但是对底层写作的界定问题也不断地受到人们的质疑。究竟何谓底层?底层写作的标准又是什么?
“底层写作”主要是指以底层为描写对象的文学,但这并不只是一个关于题材的概念。在内容上,它主要描写底层生活中的人与事;在形式上,它以现实主义为主,但并不排斥艺术上的创新与探索;在写作态度上,它是一种严肃认真的艺术创造,对现实持一种反思、批判的态度,对底层有着同情与悲悯之心,但背后可以有不同的思想资源;在传统上,它主要继承了20世纪左翼文学与民主主义、自由主义文学的传统,但又融入了新的思想与新的创造。
评论家阎晶明将“底层”归为“知识分子的一个说法。它最主要的意义是对社会阶层的整体的观照”,[5]城市平民、农民工,还有更复杂的群体集合到这个概念之下,命之为社会底层。描写底层写作的小说一个共同的特征就是将关注的焦点集中于社会的底层群众,这些弱势群体,在商业化的大潮中逐步陷入困顿。在改革退潮后,越来越多的普罗大众找不到自己生存的位置,人们迫切需要一种精神上的指引来把这些人带到生活的主流轨道上来。底层写作描写的就是这种困顿中的大众情怀。方方是八十年代末新写实小说的领军人物,同时,她也是较为关注社会底层的作家之一。方方这部小说《奔跑的火光》描写底层较为成功,却因为其《风景》的太过炫丽而不太被大多数读者、评论家所关注,这部作品就是以描写底层歌者英芝的爱情、婚姻为主的《奔跑的火光》。
三、苦难:底层写作说不尽的话题
《奔跑的火光》是方方2001年出版的一部中篇小说,这篇小说的篇幅不是很长,短短百余页,然而方方通过它展现给我们的,却是一个愚昧女人的成长史,一个畸形道德的家庭史,更是一个民族的愚昧史。方方用她深刻的笔触还原了一个冷酷的“风景”。这篇作品,没有像《风景》获得了满载的荣誉,作为一个标志被写进文学史,也不如《落日》,像一把刀刻在读者的内心深处,使读者在自省中反思人性的终极意义。《奔跑的火光》像一个遭人怜悯的孩子,迫使你在接近它的时候带着哭泣的声音。
如果说在《风景》《落日》中,方方是带着既同情又无耐的眼光来书写社会,那么,在《奔跑的火光中》,这种目光却变得尖利起来。在对主人公英芝命运的关注上,使人感到的是一个渴望坚强、向往独立的无助女人委屈的、哭泣的声音。“英芝是凤凰垸的美女,是‘三伙班的歌唱家。一时的风流,毁灭了她美丽的梦想和追求。男人嗜赌,输掉了英芝卖唱卖身的钱。英芝无路,为求生存再卖身。奔跑的火光张开了血盆大口,吞噬着仇恨,吞噬着罪恶,一根复仇的火柴,将英芝送上了不归路,一出愚昧而无知的情感悲剧,一个让人心寒的火的故事。”[6]
在对底层写作进行书写的过程中,方方并不是最为突出的一位,然而她对底层人民的关注,对于弱势群体的关照,却使自己的笔触如一把尖锐的刀,刻在普通大众读者的心上。使读者在读到她的作品时,都是带着精神疲惫的哭诉的声音。时至今日,所有的迷雾都在时间的渐变中转为清晰,一个个不可知的对于底层写作的质疑也使得這种拨开薄雾见天日的文学现状得以透彻。在文学思潮的发展史上,底层写作是否可以概括为一种文学思潮,还需要更久远的时间的印证,但是唯一可以确定的是,底层写作已改变了历来的对于文学史的不平衡的写作现象,使普罗大众进入了文学作品的写作领域,使一个个鲜活的、又略带青涩的文学形象跃然纸上,使我们在对社会中存在的不公平、不平等现象显现出前所未有的深层次的关怀,这种对于人生的彻底感悟状态,也是给日益式微的文学写作注入一股新鲜的活力。
注释:
[1]刘知几:《史通·列传第六》,《史通通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1978年版,第46页。
[2]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九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315页。
[3]陈染:《私人写作》,北京:作家出版社,2004年版,第3页。
[4]刘洋:《新世纪文学的“新表现”》,中华读书报,2005年06月15日。
[5]任华南:《当“底层写作”成为流行词》,中国青年报,2006年5月22日。
[6]方方:《奔跑的火光》,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第1页。
(姚飞 辽宁沈阳 沈阳交通技术学校 1100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