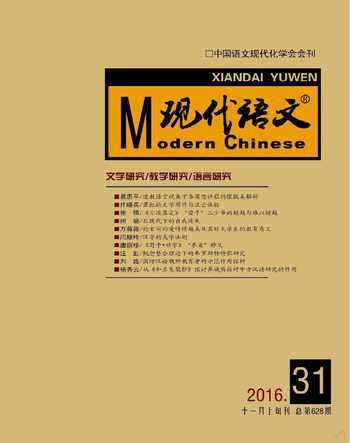《宣讲拾遗》与劝世文宝卷
摘 要:民间宣讲是用“俚俗歌词”讲唱一些传说故事、时事传闻,表彰民众认为的美德、善行的一种宣讲。这种宣讲也称“说善书”。[1]宣讲善书的目的在于劝善惩恶、教化民众,具有教化功能。而教化功能也是宣讲宝卷的主要功能之一。文章简要对比宣讲善书的代表作《宣讲拾遗》和劝世文宝卷,探讨二者之间的关系。对它们在劝善教化方面所做出的有益尝试进行分析总结,对于当下社会公民的道德建设、构建和谐社会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宣讲拾遗》 宣讲 善书 劝世文宝卷 劝善
善,应该说是中国社会最基本的道德准则。民间广泛流传的善书以劝善教化为目的,宣讲善书更是民众追求善的一种体现。善书的编者在内容、形式、语言等方面做出了有益的尝试,有效地发挥了善书的教化功能。同样以劝善教化为目的的劝世文宝卷的出现,与善书的广泛流传紧密相连,也成为民众精神家园的有力支撑。时至今日,我们对于善的追求并没有改变,只是我们需要更加有效地引导和帮助。借鉴宣讲善书与劝世文宝卷在劝善方面的成功之处,有利于公民自身的道德建设和社会和谐氛围的形成。
一、宣讲善书
善书的内涵和外延十分广泛,内容复杂,形式多样。广泛来讲,所有的劝善之书均可归入善书。日本研究善书的学者如服部宇之吉、小柳司气太、酒井忠夫均持此观点。[2]与日本学者对善书研究的宏观视角不同,我们在实际中经常用到的是善书的一个狭义的概念,即“宣讲”,这种宣讲也称“说善书”。车锡伦先生对宣讲善书这样解释:“但在民间也出现另一种‘宣讲(其出现的时间不详),即用‘俚语歌词讲唱一些传说故事、时事传闻,表彰民众认为的美德、善行。它们也倚称‘宣讲:‘不拘乎地,不择乎人,不限以时,不滞以礼。宣之而如歌词曲,讲之而如道家常,因较之设学谨教,尤便于家喻户晓也。这种宣讲也称‘说善书”。[3]民间宣讲善书是受到了宣讲圣谕的启发而产生的。这一点也得到了学界的公认。但是,民间宣讲善书与官方宣讲圣谕又不同。首先,它们的性质不同。民间宣讲善书是民间自觉的、非官方性质的一种自发自我的教化。而宣讲圣谕,从它产生之日起就带有官方的性质,即是“在地方官的指导下,由各地乡绅、士人、耆老富裕阶层合作开展的官设宣讲。”[4]
其次,它们在内容和形式上也不同。民间宣讲的内容加入了深入人心的故事,采用民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具有娱乐性。而官方宣讲圣谕则条目固定、形式较为刻板。[5]因此宣讲圣谕在各地方宣讲推行时,身处社会下层的民众难以理解,很难收到实际的教化效果。也正因如此,民间宣讲善书受其启发,通过改变内容与形式,更加地贴近民众生活,广泛被民众接受。《宣讲拾遗》[6]作为代表作处处体现着上述宣讲善书的特点。
《宣讲拾遗》刊印于同治十一年(1873年),从卷首的自序中可以推断,《宣讲拾遗》的作者是出版乡村善书的书肆、兼任同善会的乡村书塾主人,姓庄,号跛仙。庄跛仙是在看到“乡党邻里间,有厌《集要》之故”的现象之后,希望借助更通俗易懂、更容易实践的《宣讲拾遗》,使之为民众重新听闻宣讲,从而达到宣讲教化的目的。[7]
围绕这一目的,《宣讲拾遗》在内容选择、表达形式、印刷方式等方面进行了有益的尝试,体现了其民间性的特点,顾及到了教化对象的广泛性和文化水平的局限性。
《宣讲拾遗》所采集的内容更加通俗易懂,朴实简明,也更加容易践行。它采取民间广为流传的故事传说,如:“燕山五桂”(即《三字经》:“窦燕山,有义方,教五子,名俱扬。”)、“三娘教子”“安安送米”等。故事紧密结合民间宗教信仰(城隍、土地、灶王等),传达了中国传统的孝亲、友善等思想。这些家喻户晓的故事所反映出的人生道理,成为民众日常所秉持的一种生活行为规则,使他们行善弃恶,安分守己。正是因为故事中这些平常人的事迹,使得劝善惩恶的思想从认知的层面上升到了实践的层面,行善不再是有钱人、上层阶级的专利,平凡的人也可以通过简单的孝顺父母、与人为善等行为来获得福报,做到知行合一。
《宣讲拾遗》中的故事采用民众喜闻乐见的形式,说说唱唱。“说”指散文,前面有“宣”字作为标注,内容通常是叙述故事发生的时间、地点、缘起、人物介绍等;“唱”一般指七字或者十字的韵文,前面有“讲”的标注,内容一般为人物的独白、对话、所想所见等。
此外,清代书坊的兴盛也成为《宣讲善书》广泛流传的有力推动者。从地域上看,《宣讲拾遗》广泛流传于甘肃、山西、江苏等18个省市。许多善书局,如上海广益书局、大成书局、章福记书局,济南同善书局等都曾刊印发行。清光绪癸未年季秋(1883年9月)的新镌木刻本卷末有详细的捐资人的籍贯、姓名、捐资金额。捐资人中陕西、山西人较多。最后有捐资金额的总数“六十四千五百文”,共印《宣讲拾遗》二百部。由此也可以看出,《宣讲拾遗》主要以善人捐募集资的形式流通。这种方式同时也是《宣讲拾遗》故事中所宣扬的捐资行善以获得善报思想的体现。
二、《宣讲拾遗》与劝世文宝卷
道光年间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运动的失败对晚清社会造成很大的影响,这不仅体现在政治的丧权辱国、贪污腐败,经济的衰弱,人民生活困苦,更加体现在给社会民众心理造成的伤痕。面对内外交困的社会局面,想要修复这种创伤和破坏的民间人士,发挥善书的传统,自觉地捐资刊印善书,劝善教化民众,为民众提供了他们急迫需要重建的精神家园。
与《宣讲拾遗》在同一背景下流传和发展的宝卷也发挥着社会教化的功能。宝卷是一种十分古老的、在宗教和民间信仰活动中,按照一定的仪轨演唱的说唱文本。[8]由于演唱宝卷一般都“照本宣扬”,因此演唱宝卷称为“宣卷”,它集宗教信仰、娱乐、教化功能于一身。宣卷从其本质上来说是一种民间信仰活动[9],因此它首要的还是民间信仰的特征。宝卷的教化作用可以概括为“劝善”,宝卷发展到后期,劝世文宝卷出现,其教化功能得到加强。
(一)劝世文宝卷
劝世文宝卷这一名称的提出见于车锡伦先生《中国宝卷研究》。[10]按照宝卷的发展过程将宝卷分为宗教宝卷和民间宝卷,劝世文宝卷就属于民间宝卷。《中国宝卷研究》中对于劝世文宝卷的介绍相比其他类型的宝卷来说较为简略。
根据车先生的阐述,笔者从《中国宝卷总目》[11]和孔夫子旧书网上历史拍卖的宝卷中,辑出劝世文宝卷共18部,其刊刻或抄写时间主要集中于清末民国时期。这一时期,无论是宣讲善书还是宣讲宝卷,都进入了一个兴盛繁荣的时期。
关于劝世文宝卷的编者和抄写人,在相关的研究中并没有定论。《潘公免灾宝卷》之后有“板刻捐资姓名”,详细开列了捐资人籍贯姓名,每人至少捐资刊印五十部。清末人民在生活困苦的艰难环境下,能够出资刊印五十部甚至更多宝卷的人士,应该属于当时的富裕阶层。木刻本《太上感应宝卷》,卷首的序文概括了感应篇的特点和发展历史。另有龙角居士的序文,其中详细介绍了“三教弟子各执其是,交相诋毁,是以旁门林立,异说风生,以致大道半明”的社会现象。手抄本劝世文宝卷,没有抄卷人身份信息的明确提示,但抄写文字有固定的字体风格,书面整洁清晰。其中的《善福报宝卷》还有校对之后,红笔修改的痕迹。
综上所述,劝世文宝卷的编卷人和抄写人应该是民间社会中有一定经济基础和文化知识的人,他们重视自身的修养和宝卷劝善教化功能的实现,希望通过编辑和传抄宝卷来使“愚夫愚妇”明白从善去恶的道理,使社会风气有所改善。因此,劝世文宝卷中所选取的大多是孝亲、友善、以及因果报应的伦理故事,采用的形式多为民间宝卷的形式,唱七、十字唱词。
(二)《宣讲拾遗》与劝世文宝卷
劝世文宝卷中,明显受到《宣讲拾遗》影响的是《佛说至孝成仙宝卷》和《佛说爱女嫌媳宝卷》。《宣讲拾遗》的刊刻年代为同治十一年,这两部劝世文宝卷的抄写年代是宣统年间和清末民国时期。《宣讲拾遗》与两部劝世文宝卷具有时间上的承继关系。
两部宝卷的内容与《宣讲拾遗》第一训“孝顺父母”中讲述的两个故事一样,都说的是杨一哭坟孝亲和爱女嫌媳(即传统的“安安积米奉亲”)的故事。其形式上的相似性,更加能够证明《宣讲拾遗》对这两部宝卷的影响。两部宝卷在抄写时,只是删去了民间宣讲善书中“宣”与“讲”的标注。很明显,这两部宝卷基本照抄了《宣讲拾遗》中的两个故事,并未做任何改动。
民间宣讲善书和劝世文宝卷,其共同劝善教化的创作目的,促使它们在各自的发展过程中产生交集,宝卷向善书逐渐靠拢,尤其是劝世文宝卷身上处处体现着民间宣讲善书的痕迹。但需要指出的是二者终究不是同一事物,它们的源出不同、性质不同。车锡伦先生在《中国宝卷研究》中,进行了全面的概括。[12]
三、《宣讲拾遗》与劝世文宝卷的价值和影响
天下之物,最动人耳目者最易入人心。《宣讲拾遗》与劝世文宝卷的传播使民众明白了什么是善、怎样行善。虽然《宣讲拾遗》与劝世文宝卷不是同一事物,于民间社会而言,它们都是劝善之书,其中所承载的许多伦理教化内容,比如力行孝道、取财有道、宽以待人等,都是历经检验所沉淀下来的中国优秀的思想传统。它们成为民众生活的行为准则和内心精神世界的寄托,对民众的生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经济快速发展的今天,多元文化相互碰撞融合,普通民众迫切需要建立自己稳定的精神家园,我们开始重新审视中国传统文化,寻找适合自己的安身立命的“根”。我们需要富有时代精神的“《宣讲拾遗》和劝世文宝卷”来宣扬以“善”为核心的传统道德,正确引导人们的行为。相比之前,我们有了更多的资源和途径,著作、电视电影、报刊杂志、网络自媒体等都应该成为重要而坚定的力量,回归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多一些真诚,少一些媚俗、商业化的成分,使人们能够从中汲取到充足的养分,弥补因现代化带来的道德和信任的缺失,帮助民众建立起自己坚实的精神家园。
注释:
[1]车锡伦:《中国宝卷研究》,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558页。
[2]刘岳兵,何英译,[日]酒井忠夫著:《中国善书研究之“序说”》,南京: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
[3]车锡伦:《中国宝卷研究》,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559页。
[4][5][日]酒井忠夫:《中国善书研究》,2010年版,第524页,第509页。
[6][清]冷德馨,庄跛仙著:《宣讲拾遗》,北京:华夏出版社,2013年版。
[7]以上参见卷首“宣讲拾遗序”:“愚才疏学浅,不娴文辞。适有冷君,号德馨者,晤言书乐堂庄君,号跛仙者,手集古人遗事数款,条切身心,病中世俗,欲附枣梨,以资宣讲。恨无序语,嘱余为文,以冠其篇。愚思庄君之善心可表,冷君之美意堪嘉,遂不揣谫陋,草彻俚语。”
“序”:“近世所宣讲者,有《集要》一书,就十六条之题目,各举案证以实之,善足劝而恶足惩。行之数年,人心有转移之机。考其书,乃潜江王文选先生所采集也。余心焉慕之,兹又于古今所传有关教化之事,择取若干条,仿《集要》之体,而畅其义旨,颜之曰《拾遗》,亦恐乡党邻里间,有厌《集要》之故者,为之一新其听闻焉。鄙意之所存仅此,夫何敢同《集要》之书,遍传宇内哉?不意宣讲诸先生,谬为赏鉴,怂恿付梓,余深愧言之不文,不堪行远,特于镌成之日,书数语以自表云尔。”
[8]车锡伦:《中国宝卷研究》,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页。
[9]车锡伦:《中国宝卷研究》,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3页。
[10]车锡伦:《中国宝卷研究》,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5页。
[11]车锡伦:《中国宝卷总目》,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02年版。
[12]车锡伦:《中国宝卷研究》,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559-560页。
参考文献:
[1]王培元抄本.佛说爱女嫌媳宝卷[Z].清宣统辛亥年(1911年).
[2]佛说至孝成仙宝卷[Z].清末民国抄本.
[3]木刻本.潘公免灾宝卷[Z].咸丰八年(1858年).
[4]太上感应宝卷[Z].民国木刻本.
[5]山东刘明则抄本.善福报宝卷[Z].清光绪元年(1875年).
[6]真修宝卷[Z].清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刻本.
[7][清]冷德馨,庄跛仙.宣讲拾遗[M].北京:华夏出版社,2013.
[8]孙雪梅译,[日]酒井忠夫著.中国善书研究(增补版)[M].南京: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
[9]车锡伦.中国宝卷总目修订本[M].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00.
[10]车锡伦.中国宝卷研究[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
[11]游子安.从宝卷道善书——近代劝善方式之传承[J].文学遗产,2008,(2).
[12]吴震.明末清初道德劝善思想溯源[J].复旦大学学报,2008,(6).
(温晶晶 山西太原 山西大学文学学院 030006)